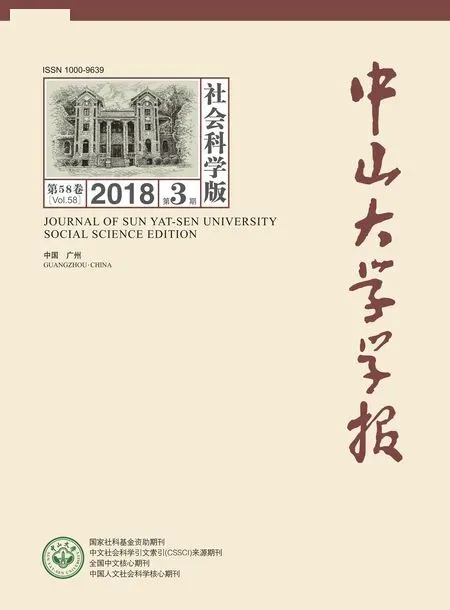中国古代咏史诗中的比较思维*
马 昕
咏史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常以借古讽今的比体写法完成个性化的情感抒发,并以此容纳于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当中。到中晚唐,由于诗人群体知识结构的改变以及时代学术风气的变化,诗歌开始融入更多的知识和理趣,咏史诗的议论色彩也随之得到加强,“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运用自己的史识,对古人往事发表评论,或褒,或贬,或讥刺,或翻案”*陈文华:《论中晚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自此之后,议论传统成为咏史题材的一项特色,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很多见识高超、议论惊警的佳作。为了形成新颖透辟的观点,咏史诗人逐渐摸索出一种比较式的思维方法。他们发现,单独分析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逐渐难以获得观点的突破;而将其与同类型其他对象展开比较,往往能得出新的视角和看法。在论证的科学性上,这当然不能与现代史学界所流行的比较史学方法相提并论,但也不能抹杀其独特的思想价值。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咏史诗中的比较思维进行梳理与评价。
一、咏史诗比较思维的理论萌芽
对历史进行比较,在中国古代早有传统。尤其是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人物品藻之风,就将人分为不同品级,比较其才性之优劣。《世说新语》就包含了很多这类评语,例如《德行》篇:“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8页。张华将王朗、华歆的类似行为进行比较,认为王朗只得形骸之外,不如华歆远甚。而张华生时,王朗、华歆皆已作古,这就相当于一则对多个历史人物展开的比较性评价。而将比较思维植入咏史诗,则集中地出现于中晚唐时期,与咏史诗议论传统的出现相伴随。晚唐的汪遵、许浑、杜牧等人都有这类作品得到后世的注意。宋代以降,人们对咏史比较思维的揭示,几乎都与这几首代表性作品有关。
汪遵《长城》诗云:“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彭定求等:《全唐诗》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961页。这首诗将秦始皇与尧进行比较,以尧之仁德见出始皇之暴虐。许浑也有一首《途径秦始皇墓》,诗云:“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彭定求等:《全唐诗》第16册,第6138页。这首诗同样讽刺秦始皇,却改用汉文帝为参照,其构思与汪诗近似。南宋末年的谢枋得在《注解选唐诗》中评价道:“汉文霸陵与秦始皇墓相近,秦皇墓极其机巧,汉文陵极其朴略,千载之后,衰草颓坟,无异也。然行路之人拜汉文陵,而不拜秦皇墓,为君仁不仁之异,至是有定论矣。”*陈伯海主编,孙菊园、刘初棠副主编:《唐诗汇评》(增订本)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29页。谢枋得对许诗的解释非常准确,也看出了比较的意味,却没有将其提炼为一种思维方法。直到明代万历年间,胡应麟也对汪遵、许浑这两首诗作出评价,则隐隐浮现出对比较思维的注意。《诗薮》内编卷6:
汪遵《咏长城》:“虽然万里连云际,争似尧阶三尺高。”许浑《咏秦墓》:“一路空山秋草里,路人惟拜汉文陵。”用意同而语格顿超。然汪诗固是学究,许作犹近小儿,盛唐必不缠绕如此。(李涉“歇马独来寻故事,逢人惟说岘山碑”。许本模此。而以汉陵影秦墓,则尤工。然较盛唐逾远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6,载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572页。
胡应麟评语中的一个“影”字,道出汉陵与秦墓之间的比较关系,也是对比较思维的凝练而生动的概括。同时,胡应麟也注意到,许诗存在对李涉诗作的模仿,因为李诗也是用羊祜来反向影射于的残酷。看来,以某一人物为参照,凸显另一人物的特征,这种手法是容易模仿甚至能够速成的,这就涉及作诗格套的问题。而晚明正是诗格诗法类著作集中出现的时代,在《诗薮》之后不久,王槚的《诗法指南》应运而生,这是一部著名的诗法著作,刊成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比《诗薮》晚了十多年。该书前卷总论近体诗作法,后卷则对各类型诗歌的创作方法与格套进行举例分析。后卷“讽谏诗法”条,引用了许、李二诗,王槚案云:“此二诗俱是题外引证,同一机括。上诗即汉文之贤,以形秦皇之暴。此诗即羊祜之贤,以形于之酷。但美一人,则其不言者可知,意在言外,皆可风也。”*王槚:《诗法指南》后卷,载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3册,第2437页。所谓“题外引证”,相当于直接道出了比较思维的内涵。王槚还指出了比较法的优长——“意在言外”,也就是诗人不直接说出对秦始皇的批评意见,而是通过对相反人物汉文帝的歌颂,造成委婉的效果。
《诗法指南》虽然只是一部诗法著作,这类作品历来都不大受诗评家的重视,但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却往往是潜移默化、不可忽视的。比如清初著名的诗评家贺裳,在其《载酒园诗话》中几乎复制了王槚的评语。贺氏说:
昔人称退之“一间茅屋祭昭王”为晚唐第一。余以不如许浑《经始皇墓》远甚:“龙蟠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韩原咏昭王庙,此则于题外相形,意味深长多矣。*陈伯海主编,孙菊园、刘初棠副主编:《唐诗汇评》(增订本)第4册,第2616页。
所谓“题外相形”,正是对“题外引证”说的复制。“相形”二字也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比较”。贺裳认为,韩愈《题楚昭王庙》只是就昭王言昭王,如能在“题外”另寻参照,与主题人物“相形”,更能营造出“意味深长”的审美效果,这也几乎是对王槚观点的重复。贺裳的评论,摆脱了诗法著作对格套的简单揭示,开始深入探讨比较思维方法的审美效果,这无疑更切近诗学本身的趣味。
在清代主要的诗学阵营中,神韵派、格调派都偏向于典型的唐诗风格;而清初王渔洋对宋诗的短暂追捧,清代中期的浙派和肌理派以及晚清的同光体,虽都重宋诗,却更偏向于以学问典故取胜的“硬宋诗”,而非以议论取胜的“软宋诗”。因此,清代诗坛对咏史议论或持批判态度,或者根本漠视,似乎只有崇尚灵机巧智的性灵派能为其留下一丝缝隙。但性灵派中的赵翼却也对咏史诗中的翻案议论发难,他的批评主要针对杜牧的咏史诗。《瓯北诗话》云:
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方岳《深雪偶谈》所谓“好为议论,大概出奇立异,以自见其长”也。如《赤壁》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题四皓庙》云:“南军不袒北军袒,四老安刘是灭刘。”《题乌江亭》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皆不度时势,徒作异论,以炫人耳,其实非确论也。惟《桃花夫人庙》云:“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63—164页。
赵翼在诗评家的身份之外,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因此看待历史事件的因果是非时,往往具备史家的宏阔视野,而不会斤斤计较于一人一事。他在这段评语中集中批评了杜牧的多首翻案作品,却独赏其《题桃花夫人庙》一首,诗云:“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23页。该诗在对绿珠悲剧命运的叹息中蕴藉地表达了对息夫人失节苟活的讽刺,正是运用了比较思维。赵翼称赞此诗“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准确地揭示了比较思维的优点正在于蕴藉含蓄。在比较中,诗人可以不直言主题,不直下断语,自然能够缓和咏史议论所带来的生硬、尖新之弊。如果说明代的诗法著作中对比较思维的认可是为了初学者作诗的便利,那么清代以贺裳和赵翼为代表的较为严肃的诗评家,对咏史诗比较思维的认识,则要深刻得多。
但是以上材料并不能说明,在中国古代的咏史诗批评观念中,诗评家对比较思维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理论自觉,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萌芽”。中国古代的诗评传统本就轻视思维义理的层面,古代诗评家对咏史诗中思维方法的归纳也基本上是缺失的,对其中比较思维的揭示自然也只能停留在蜻蜓点水的层次上。本节仅能做一些探赜索隐的工作,无意于建构出新的批评传统。但这些零星出现的材料,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使我们找到看待这类创作现象的视角与维度。下面我们从基本任务、使用技巧和主观性缺陷这几个角度,对咏史诗比较思维进行评价,仍然要对古人的这些看法有所借鉴。
二、咏史诗比较思维的基本任务
章学诚在《删订曾南丰〈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著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此史之所为作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章氏此语正好揭示出史学阐释的两项基本任务:一是探索“兴坏理乱之故”,即分析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二是评议“是非得失”,即对历史人物的行为做出价值判断。而在咏史议论的过程中,正确地使用比较思维,也有助于完成这两项任务。
(一)推论事件因果
人们探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往往容易受历史叙述的诱导,聚焦于某些局部或偶然的因素,而忽略掉一些潜藏在叙述背后的深层机制。而将类似事件进行比较,再寻求二者的差异,可以尽可能获得历史发展中的“单一变量”,如同物理实验一般,得出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例如,自古以来就有“女祸”的说法,在君主专制的体制背景下,史评者经常将国家政治的败坏与君主个人的品行作为过度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君主的后宫私隐都被纳入政治评价体系。所以,一些深得昏君宠爱的女子总被当作政治失败的“替罪羊”。但昏君之所以成为昏君,更多应归因于其自身的行为缺失,宠信女子也只是其昏聩的一种“果”而已,并非所有恶行的根本原因。西施和杨贵妃是承受此类争议的主要对象,而为她们开脱罪责的呼声,在中晚唐开始演变为一种新的认识潮流。譬如罗隐《西施》诗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雍文华校辑:《罗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页。如果说吴国的灭亡,尚可归罪于西施;那么越国日后的灭亡,显然不能再作此推演。正是将吴国和越国的灭亡进行了比较,才使我们认识到,国家兴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女人身上。罗隐还有一首《帝幸蜀》,诗云:“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雍文华校辑:《罗隐集》,第157页。再加上韦庄的《立春日作》:“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韦庄著,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1页。这两首诗谈到的都是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时,唐僖宗逃亡蜀地的事情。僖宗逃亡的起因与路线,都与一百多年前的玄宗类似,但是僖宗幸蜀却跟女子无关,这次总不能再将祸国罪名推到女人身上。通过僖宗和玄宗的比较,可知杨妃本来也不是安史之乱的元凶,真正的罪责还要君王本人来承担。
除了探究原因,推论结果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只不过这是一种可能的结果,比较思维要与假设方法相结合。我们以历代咏史诗中谈论极多的昭君主题为例。咏史诗人多对昭君出塞表示惋惜,认为汉元帝与毛延寿共同铸成了大错。但昭君出塞对西汉王朝来讲究竟利弊如何,还需再作反思。南宋萧澥《昭君词》云:“琵琶马上去踌躇,不是丹青偶误渠。会得吴宫西子事,汉家此策未全疏。”*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822页。将王昭君与西施作比较,实则以西施为样板,为王昭君做出了一种假设。如果王昭君留在汉宫,被汉元帝宠幸,其结局很可能像西施惑乱吴宫一样,使汉代政局出现类似的结局。再看王安石的名作《明妃曲》(其一),诗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0册,第6503页。王安石将王昭君与陈皇后阿娇相比,认为闺怨不分塞南塞北,即便王昭君不嫁匈奴,日后也难免长门之怨。阿娇正如前车之鉴,为我们完整地描绘出昭君如果不出塞,将会得到怎样的人生结局。在这里,比较对象之间的共同点比不同点更重要,使我们看到特定环境下人生永恒的悲剧命运。
(二)评价人物优劣
对人物优劣是非的评判,当然首先依赖其言行。但世间的行事标准本就不一,单看本身而不认真推敲当时的环境与条件,全面、细致地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就难免受到历史叙述与传统观点的左右。一旦与其他人物展开比较,环境与行为的差异就会暴露,我们也就能为人物评判寻求别样的可能。
第一种情况是,环境相似,但历史人物的行为截然相反。如果我们对相反的两种行为都能给出合理性解释,这本身就包含着自相矛盾式的不合理风险。例如袁枚弟子何士颙有一首《项羽》诗:“忍辱从来事可成,英雄盖世枉伤神。但知父老羞重见,不记淮阴胯下人。”*何士颙:《南园诗选》,《丛书集成三编》第44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503页。我们单看项羽的故事,会为其慷慨悲壮感动;再单看韩信的故事,却又会称赞他的智慧,并同情理解他身受凌辱时的苦楚。现在,诗人将项羽不肯过江东和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相比较,终于承认了二者行为之间的矛盾性,继而再从韩信受辱却得以成就伟业的结果,转过头来批评项羽缺乏忍辱负重的品质,终究只能将天下拱手让给刘氏。
有时,两个人物的基本行为是一样的,但在行事过程中仍存在某种差异,这也可以作为比较的切入点,从而将二人分出高下。例如纳兰性德《咏史》(其二)云:“一死难酬国士知,漆身吞炭只增悲。英雄定有全身策,狙击君看博浪椎。”*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1页。诗人以张良刺杀秦始皇却能全身而退,与豫让复仇身死作比较,认为真正的英雄应有全身之策,不能只凭一腔热血豁出性命。
不过,凡事也都不能过度简单地看待,人生的选择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着多种的合理可能。有些诗人的价值观较为达观,就能对截然相反的人物行为作调和式的分析。例如清人屈大均《木末亭拜方正学先生像》末二句:“莫问三杨事,忠良道各分。”*屈大均:《屈翁山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25页。朱棣靖难取得胜利之后,方孝孺坚持贞操,拒不合作,至死不渝,有独善之誉;而杨荣等人则主动迎降,看起来是有失名节的。但后来,以杨荣为代表的“三杨”竭力辅佐成祖、仁宗、宣宗,成就了明代数十年的盛世,有兼济之功。诗人认为,方孝孺与三杨,在面对相同处境时的生死抉择固有不同,但只是外在的“异”;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各自尽到了臣子的职责,皆可称为“忠良”,这便是内在的“同”。
第二种情况是,行为相同,但历史人物面对的环境却有异,这时就可突出环境的重要性。例如柳宗元《咏荆轲》诗中有四句:“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柳宗元:《柳宗元集》卷43《咏荆轲》,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60页。明人韩洽《荆轲七首》诗亦云:“寸刃入虎窟,生死在眉睫。秦政非齐桓,如何欲生劫。”*韩洽:《寄庵诗存》,《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9册,第214页。曹沫劫持齐桓公和荆轲刺杀秦王嬴政,二者都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采取行刺手段,二人也同入《史记·刺客列传》。但毕竟,齐桓公是一位明达君主,曹沫也非亡命之徒,所以曹沫尚能生还,柯盟之劫的结果是鲁得失地,齐得美誉,两全其美;而荆轲所面对的处境早已大大不同,秦王性情狡诈,崇尚勇力,荆轲不仅没能成功,还使自己身死秦宫,连带整个燕国也陷入极大的被动。柳宗元、韩洽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都揭示了时移世异的基本道理。而柳宗元更露骨一些,直接评论荆轲的“愚”,做出了对人物优劣的评判。
三、咏史诗比较思维的使用技巧
咏史诗运用比较思维,是为求得更深刻更合理的观点认识,以其机巧灵慧使诗人获得逞智斗奇的优越感,给读者带来醍醐灌顶的满足感。但想真正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些特别的技巧。
(一)题内比较与题外比较
如上文所说,王槚将比较思维称作“题外引证”,贺裳则称作“题外相形”,总之都突出“题外”二字,也就是在咏史主题之外另寻参考对象加以比较,而不要在故事内部去找。
所谓的“题”,是与主要历史人物有关的整个事件背景。例如在战国时期齐人复国克燕的故事中,田单行火牛阵,连下七十余城,无疑是主要人物;但在攻打聊城时,齐军却与燕国守军僵持一年,最终是鲁仲连劝降聊城守将,鲁仲连也是整个事件内部的一个人物。若将田单与鲁仲连进行比较,就属于题内比较,缺少兴味。例如汪遵《聊城》诗云:“刃血攻聊已越年,竟凭儒术罢戈鋋。田单漫逞烧牛计,一箭终输鲁仲连。”*彭定求等:《全唐诗》第18册,第6956,6877页。这首诗并没有靠比较思维获得深刻的见解,整体上显得很平凡,就是因为题内比较是人们在读史的过程中自动就会完成的领悟,无需咏史诗人再次揭发。可见,比较思维的关键技巧在于联想能力,将本无关联的两个对象放在一起比较同异,最终竟然建立起联系,这才让读者有受教与启发的快感。
田单行火牛阵与鲁仲连投书下聊城这两件事之间至少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距离。而有些更加糟糕的题内比较,甚至就在同一事件的主客双方之间来进行。例如彭定求《五人墓》:“偶泛蓬舠绕郭来,摩挲墓碣久徘徊。重看俎豆登乡社,尚想干掫捍党魁。白刃争撄千载烈,青云并附九京哀。萧萧松柏凌秋爽,遗臭生祠安在哉!”*沈德潜选编,吴雪涛、陈旭霞点校:《清诗别裁集》卷10,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于谦《苏李泣别图》:“啮雪吞毡瀚海头,节旄落尽恨悠悠。孤臣不为一身惜,降将应怀万古羞。绝塞旅魂惊永夜,秦关归兴动高秋。表忠麟阁图形像,未数当年博陆侯。”*于谦:《忠肃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376页。彭定求将五人与魏忠贤作比较,分别是被害者与加害者;于谦将李陵和苏武作比较,分别是劝降者与被劝者,都属同一事件的主客双方。因此,这两首诗的观点也就很寻常。诗人似乎也无意于创立新奇之见,不过是一次临墓而叹或因图而赋的“命题写作”罢了。
题外比较胜过题内比较,古代的诗评家也有过这类看法。比如上文所引的许浑《途径秦始皇墓》,秦始皇与汉文帝并不同时,不在同一故事系统中,当然属于题外比较。而将秦始皇与扶苏比较,却属于题内比较,唐人曹邺有诗,说“行人上陵过,却吊扶苏墓”*彭定求等:《全唐诗》第18册,第6956,6877页。,比较的趣味就不如许诗。宋人范晞文评曰:“《始皇墓》云:‘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惟拜汉文陵。’曹邺亦有‘行人上陵过,却拜扶苏墓’,扶苏非有德于人者,意亦不如许。”*范晞文:《对床夜语》,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9页。“意”之不如,或许正是缺乏题外比较的趣味。
但是话说回来,题内比较也不是全无创新的余地,只不过参照对象应是读史者常常忽略的“隐藏人物”。试看胡曾《博浪沙》:“嬴政鲸吞六合秋,削平天下虏诸侯。山东不是无公子,何事张良独报雠?”*彭定求等:《全唐诗》第19册,第7428页。张良是韩国贵族之后,且有博浪沙刺秦的壮举。诗人对那些同为六国后裔的贵族公子发起质问,在秦并天下、实施暴政之时,你们都在哪里呢?六国贵族子孙众多,必定有很多背负亡国大仇之人,但史书里绝少提及他们的复仇。他们或许都在某些角落里龟缩苟活,而不像张良这样付诸壮烈的行动。张良的品质,便从一干“隐藏”着的众人中凸显出来。
“隐藏人物”也不一定是这种无名无姓的集体存在,也可能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只不过他潜藏在故事的某个角落,没有与主要事件发生直接的关联。可一旦能联系到这样的人物,就能给人造成恍然大悟的感觉。例如钱谦益《戊寅元日偶读史记戏书纸尾》(其四):“汉家争道孝文明,左右临朝问亦轻。绛灌但知谗贾谊,可思流汗愧陈平?”*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5页。绛侯周勃曾弹劾过陈平,陈平反而在政治上对周勃多所帮衬。这不禁使人发问:当周勃嫉恨、排挤贾谊之时,可曾想过陈平对自己的包容和退让呢?在贾谊被贬的故事中,周勃、灌婴等人与贾谊直接发生联系,而陈平的形象,包括他的品格与作为,都隐伏在了汉文帝时期的朝堂上,司马迁不直接提到他,但无法掩盖他的客观存在,这就属于“隐藏人物”,钱谦益将他从“幕后”请到“台前”,完成了一次有趣的比较。
(二)发掘特殊的共同点
在比较中寻求参照对象,需要彼此之间有某种共同点。或是身份、地位相同,如秦始皇、汉文帝同为帝王,周勃、陈平都是汉初名臣;或是经历、事迹相似,如屈原、贾谊都有怀才不遇、贬于沅湘的经历,曹沫、豫让都做过行刺劫持的勾当。但以上这些共同点都在寻常的范畴当中,要想形成新意,依靠的是比较对象与比较角度的特点。而有时候,共同点本身也会足够独特,比较对象之间在某个人们不曾注意的细节上巧妙地联系起来,就容易营造出令人会心的趣味。
例如宋人柴望《梦傅说》:“傅说为霖寤寐中,高宗一念与天通。后来亦有君王梦,不是阳台便月宫。”*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4册,第39912页。首二句是指商王武丁梦中将傅说比作甘霖的故事;后二句则举出楚王在梦中与女子合欢的故事以及唐玄宗梦中向仙人、龙女学音乐的故事。两相比较,同样是做梦,楚王与唐玄宗都是在梦中行淫乐游玩之事,武丁却是在称誉贤臣。今昔比较,令人生出后世君王不如上古圣王的感慨。不过,梦在这几个故事中仍居于比较重要的位置。这首诗的难点仅在于将包含梦境的君王故事连缀起来而已。
有的时候,还可以主动发掘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共同点。例如袁枚《诗会分咏美人,霞棠拈得绿珠,连作五首不惬余意,乃请老人拟赋两章,恐有鲍老登场之诮,奈何》(其二):“人生一死谈何易,看得分明胜丈夫。闻说息姬归楚日,下楼还要侍儿扶。”*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14页。这首诗看似只写了息夫人一人,但“下楼”这个情节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坠楼而死的绿珠。同样是要屈身侍奉他人的关键时刻,又同样身处楼上,一个要跳下来,一个却要侍儿扶下来。袁枚在“下楼”这件事上居然找到了息夫人和绿珠的共同点,可谓绝妙才思。不过,息夫人和绿珠的比较,还在常规写法之内,毕竟是杜牧《题桃花夫人庙》这首名作就已经开其先河的,袁枚再写,多多少少对杜牧的想法有所继承。又如沈绍姬《咏古》(其二):“为报韩仇奋一椎,副车虽误亦雄哉!淮阴也是韩王后,何用当时蹑足来?”*沈德潜选编,吴雪涛、陈旭霞点校:《清诗别裁集》,第397页。将张良和韩信作比较,一者去刺杀秦始皇,一者却连市井恶少都不敢杀。张、韩二人生当同一时代,青年时期的性格确实恰好相反,作这样的比较已经不算新鲜了,但这首诗还是写出了新意。因为诗人推想,韩信也姓韩,应为韩国后裔,为何韩国的仇恨要让张良去报,韩信只知道隐忍自存呢?宗族出身这件事,被诗人挖掘出来,成为一个富有新意的共同点。
而有的共同点就不仅没人想到,而且确实支撑起整个比较的框架。例如王夫之《咏史二十七首》(其一):“箕子生传《洪范》,刘歆死击《谷梁》。叛父只求媚莽,称天原是存商。”*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3页。都面临国家即将倾覆的处境,箕子守志逃亡,刘歆却助纣为虐。不过,很少有人将这两人放在一起比较。王夫之却找到他们之间一个独特的联结点,即都有传承经典的事迹。《尚书·洪范》记载了箕子传授天道五行之事;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代表学者,大倡《左传》,而排抵《谷梁》。虽然都是儒家经典的传承者,但一者趋炎附势,全无儒者风骨;一者大讲天道五行,原来全是为延续殷商国运。传经,只是二人表面的共同点;而是否真正具备儒者品质,才是他们内在心灵上的差异。
四、咏史诗比较思维的主观性缺陷
在咏史诗中运用比较思维,固然能得出一些富有新意的看法,在灵机与巧思中蕴含才人之诗的趣味;但才人之诗毕竟缺乏学理支撑,逻辑的机巧中每每暗藏漏洞与危险。我们必须正视咏史诗比较思维的种种缺陷,尤其是其中的主观性与随意性。
(一)创作情境带来的主观性缺陷
比较必须在不同对象之间展开,但在具体的创作情境中,对象与对象之间天然地处于不完全平等的地位,存在着主客差异。咏史诗直接歌咏的对象居于“主位”,用来与之参照的题外对象则处于“客位”。咏史诗人之所以选择某个人物或事件作为直接的歌咏对象,甚至在诗歌标题中将其置于惟一显要的位置,很可能因为他早已对其抱有正面的情感与认识。那么,拿来与其进行比较的参照物,就容易处在不利的地位上。诗人容易对主位对象存有偏袒之心,而对客位对象过于苛刻,甚至不够尊重。尤其是那些登临古迹而作的怀古诗以及因画而赋的题画咏史诗,这种主客偏见只会更加严重。一是因为,诗人登临古迹时面对着与主位对象直接相关的历史环境,容易对其怀有更多的理解;或临画而赋时,画中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也容易唤起咏史诗人的同情。二是因为,怀古诗和题画咏史诗都处于某种应景写作的环境中,对主位对象过于刻薄,会有大煞风景、不合时宜之嫌。
例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6:
晚唐王贞白诗:“山色四时碧,溪光七里清。严陵爱此景,下视汉公卿。”不著议论,而行以古直之气,最属高格。惜其下接云:“垂钓月初上,放歌风正轻。”局振不起,晚唐通病。末云:“应怜渭滨叟,匡国只论兵。”欲扬子陵,遂抑太公,何无识乃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6,载郭绍虞编选,福寿荪校点:《清诗活续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94页。
清人胡本渊《唐诗近体》评此诗:“以太公相形,见此台之风独高。”*陈伯海主编,孙菊园、刘初棠副主编:《唐诗汇评》(增订本)第6册,第4456页。揭示了诗中的比较意味。因为王贞白的歌咏对象是严子陵,就因此而贬抑姜太公,潘氏认为这是一种“无识”的表现。
又如宋人李师中《子陵二首(其一)》:“阿谀顺旨为深戒,远比夷齐气更豪。半夜光芒侵帝座,有谁曾似客星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册,第4871页。诗人认为严子陵在君主面前能做到不卑不亢,同榻而眠也毫不避忌,这种坚贞、正直的作风,对那些“阿谀顺旨”的小人来说可为“深戒”。但诗人又偏偏要说严子陵“远比夷齐气更豪”,作此判断,却未给出丝毫理由,恐怕也只能用创作情境带来的主观性缺陷来解释了。因此诗以子陵为题,诗人眼中便只见子陵,而不容其余。这样的比较也会流为信口开河的意气之论。
(二)参照对象带来的主观性缺陷
比较思维的逻辑漏洞还源自参照对象——选取不同的参照对象,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选取何种参照对象,当然会受诗人知识视野的影响,但如果在同一位诗人的不同作品中因为参照对象的变化而改变了历史评价的立场,就更能看出其中的主观性缺陷。
例如,苏轼在宋神宗嘉祐八年(1063)二十七岁时任职于凤翔,此时他志得意满,仕途顺当。这一年,他作了一首《秦穆公墓》,诗云:“橐泉在城东,墓在城中无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识公墓。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4册,第9108,9528页。古人多认为三良殉葬出于被迫,但苏轼发现了其中的蹊跷。秦穆公在位时,大将孟明视在与晋国的交战中屡屡战败,仍被穆公赦免,为何却要杀掉三位贤臣为自己殉葬呢?穆公前后的行为矛盾指向一个答案:三良为穆公殉葬其实是出于自愿的。苏诗进一步指出,古代早有这种杀身酬知己的事情,例如齐之二人自杀以谢田横。到宋代,人们少有这种大义凛然的行为,就以己度人,以为三良殉葬也是出于胁迫。这样一比较,竟使三良之死重于泰山。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苏轼正在贬所惠州,又作了一首《和陶咏三良》*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4册,第9108,9528页。。此诗以晏子不为齐君死节为参照,认为三良殉葬并非出于大义,而是如鸿毛般微不足道。前后两首诗的写作时间相差三十余年,苏轼的生活处境也大有不同。宋人胡仔就发现:“东坡《秦缪公墓》诗意,全与《三良诗》意相反,盖是少年时议论如此。至其晚年,所见益高,超人意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载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65—3966页。宋人吴子良也说苏轼晚年所作是“饱更世故”*吴子良:《吴氏诗话》,载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8册,第8707页。的结果,俞德邻也说“老成之见与少年异”*俞德邻:《佩韦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140页。。但他们都没有指出:苏轼晚年“所见益高”,其实只是替换了比较的参照对象而已。田横主仆和晏子,都与三良之死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也因此都存在类比的余地,至于选择哪一参照对象,得出何种结论,就仅凭诗人自身的主观选择了。比较思维的主观性缺陷也就暴露出来。
不过,苏轼这两首诗的参照对象与三良之间的共通性都大于差异性,因此其结论还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前诗表彰忠贞,后诗珍视生命,各有其在道德上的美好追求。既然如此,总是追究其在逻辑思维上的漏洞,难免有吹毛求疵的嫌疑。可如果这种逻辑漏洞愈演愈烈,就会演变为我们不能接受的诡辩和谬论。我们必须对参照对象提出一些要求,一旦违反这些要求,比较思维就容易沦为诡辩。
第一个限制条件是,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异性要在一定限度内,如果差异性远远大于共通性,就不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逻辑上出现严重的漏洞。就苏轼两首咏三良诗来看,秦穆公与三良、田横与其仆从,都包含着君臣相知的成分,所以都在可以接受的比较范围内。但王士祯有《秦穆公墓》一诗:“雨霁陈仓晓日红,杖藜来访槖泉宫。千年断碣荒烟里,一片残春秀麦中。黄鸟哀时良士尽,碧鸡飞去霸图空。子车遗冢犹邻近,长与坑儒恨不穷。”*王士祯:《带经堂集》,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8—519页。王士祯将坑儒与三良相提并论,前者并无君臣相知的前提,所以严重缺乏说服力。
第二个限制条件是,以参照对象来说明本体,需要先将参照对象的情况证明清楚,才能形成有效类比。否则会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比较证明,甚至会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元人宋无的《甘罗》诗:“函谷关中富列侯,黄童亦僭上卿谋。此时园绮犹年少,甘隐商山到白头。”*顾嗣立:《元诗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9册,第21页。甘罗十二岁建功于秦国,被秦王政赐任上卿。诗人认为,在战国末年的乱世中,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愿意在乱世之中建立一番事业;而当时的四皓也正当年少,难道就甘心隐居在商山了此一生吗?诗人通过对甘罗的揣摩,也对四皓的心态产生了质疑。但如果反过来,是否也可以说:在乱世中仍有四皓这样淡泊名利的隐士,甘罗担任上卿难道就只是为了一己的名利吗?以甘罗来揣摩四皓,与反过来以四皓来揣摩甘罗,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其关键原因就在于:诗人并不能确切地证明甘罗的隐秘心理,以此揣摩四皓的心态,就缺乏说服力,会陷入“相对而言各自成立”的思维陷阱。
第三个限制条件是,不能以某些极端情况为参照物,这样会在无形中将道德底线调得过高或过低,诗歌的伦理追求也会在这种逻辑伎俩的翻云覆雨中荡然无存,不可不慎。例如前引杜牧《题桃花夫人庙》,以绿珠之殉节指责息夫人苟活,正是以极端情况来要求一般,而罔顾息夫人三年不与楚王言的行为所已经展现出的坚贞傲骨。从义理维度衡量这首诗的水准,除了暴露诗人的头巾气之外,并不具备多么高明的思维水平。这种议论看似新颖,实则蕴含着套路化写作的危险。清人邓汉仪也有《题息夫人庙》一首,乃步樊川原韵而成,诗曰:“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就是将息夫人与历史上万万千千的人物作比较,回归一般情况之后,息夫人仍应得到后人的赞赏。沈德潜评此诗:“其用意处,须于言外领取。”*沈德潜选编,吴雪涛、陈旭霞点校:《清诗别裁集》卷12,第238页。邓汉仪是明末诸生,入清后矢志成为一介遗民隐士,这个时代的诗人难免要面临仕与隐甚至生与死的抉择,遗民文人对死节行为的反思反而更加深刻*参见马昕:《明清之际遗民士人的历史论说与名节观念》,《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当然不会像杜樊川那样空有些意气之见。
要求所有人向着极端的道德高点去进发,固然是强人所难,过度抬高了道德底线;但认为只要不达到极端的道德低点就值得称赞,又会过度降低道德底线,陷入“五十步笑百步”的误区。后者常用来为一些饱受批评的历史人物寻求开脱,只不过是选取了特殊的参照对象而已。例如唐人郑畋《马嵬坡》:“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彭定求等:《全唐诗》第17册,第6464页。诗人认为,与陈后主投井自辱、国亡身死相比,唐玄宗能当机立断舍弃杨贵妃,仍不愧为“圣明天子”。如果不是和陈后主作比较,而是哪怕和历史上最平庸的帝王相比,都很难说已经穷途末路、威严扫地的唐玄宗还是个圣明天子。
(三)比较标准带来的主观性缺陷
选取不同的比较标准,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王安石《邵平》:“天下纷纷未一家,贩缯屠狗尚雄夸。东陵岂是无能者,独傍青门手种瓜。”*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0册,第6709页。邵平是秦朝末年人,被封为东陵侯;秦灭亡后沦为平民,以种瓜为业。诗人将其与周勃、灌婴作比较,认为后二人在秦朝时不过是贩缯屠狗之辈,趁着乱世才得到发迹的机会,不如邵平倚门种瓜来得超脱高洁。但清人贺裳批评王安石的这种看法:“此诗乍观则佳,细思则谬。邵平身居侯爵,不能救秦之亡,何称能者?观其说萧相国,盖一明哲保身之士耳。绛、灌与高帝同起徒步,少困闾里,自是秦之失人,反以其屠贩为笑乎?”*贺裳:《载酒园诗话》,载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第220—221页。以功业为标准,则邵平之功无论如何不如周勃、灌婴的开国之功。王安石为能抬高该诗主要吟咏对象邵平的地位,就改以地位出身为标准对人物进行比较。如此一来,周勃、灌婴纵再有不世之功,也只能以贩缯屠狗之徒来看待;邵平即便只是倚门卖瓜一老翁,仍然挂着一个东陵侯的招牌。这种翻新之论实在难以令人心服。
而一些有力的比较论证,则会突出不同历史人物之间的“同”,诱导读者采取同一标准看人,从而对特定历史人物给出更加公允的评价。例如南宋宁宗时期力主抗金的韩侂胄,因北伐失败而遭到投降派的杀害,成为历史的教训。李东阳不满于韩侂胄的下场和历代受人指责的待遇,写了《两太师》一诗:“和议是,塞外蒙尘走天子。和议非,军前函首送太师。议和生,议战死。生国仇,死国耻。两太师,竟谁是?”*李东阳:《怀麓堂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17页。同样被加以太师之衔,韩侂胄议战而死,秦桧议和而生。但为何同样主战的李纲、韩世忠、辛弃疾等人却得到了后人的称赞,韩侂胄却总被当作笑柄?诗人呈现出历史评价的不公与矛盾,最终是要为韩侂胄翻案辩白。若以成败论是非,其实也不通。袁枚有《遣怀杂兴》一诗,将南宋大将张浚与韩侂胄放在一起比较。张浚同样抗金失利,却不仅未遭深责,后来仍然身居高位。诗人说“何以不加诛,人异事则同”*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第2册,第853页。,就是想提醒读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用一把尺子丈量,不要因循旧说,不加反省。
但以同一标准看人,有时也容易过度突出历史人物之间的“同”,而抹杀其间的“异”。例如元人郭钰的《王猛咏》:“五马渡江老臣泣,垂死丹心在王室。当年非不思南来,王谢岂能生羽翼。魏相张仪尚为秦,聊借羌苻展才力。江南虽僻不可图,青史千年谁独识。”*郭钰:《静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198页。诗人将王猛和张仪相比。张仪虽是魏人,却效力于秦国;同样,王猛虽是汉人,也可效力于前秦,不必承受“身为汉臣而仕于胡廷”的指责。但这样就忽略了张仪和王猛在其他方面的差别,比如张仪出走秦国是被苏秦故意气走的,出于不得已;而王猛辅佐苻坚则是出于君臣遇合的主动选择,少了些无奈落魄的遭遇,却也多了些政治伦理上的瑕疵。
以同一标准看人,还容易将恶人恶行稀释掉,在一定程度上为恶行“脱罪”。例如张问陶《咸阳怀古》:“鄠杜莺花负好春,武皇遗迹已成陈。通天台观连云起,莫指阿房独过秦。”*张问陶:《船山诗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页。诗人认为汉武帝的穷奢极欲不逊于秦始皇,不应该单单指责秦朝有阿房宫。这一比较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虽然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也不能因此而减少对秦朝暴政的控诉。
以上三个方面的主观性缺陷,都建立在诗人主观上忽视的前提下,也就是咏史诗人自觉有理而实则无理。但有时候,诗人其实自知无理,而只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趣味,而戏谑为之。这样的作品虽然在逻辑上无理,但在文学上具有别样的欣赏价值。例如苏轼《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一):“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4册,第9200页。诗人将范蠡与申公相提并论。春秋时期楚国的申公巫臣为得到美貌的夏姬,故意挑起事端,促成吴、晋伐楚。苏轼则暗示:范蠡挑起勾践灭吴,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西施。这一类比显然毫无事实依据,但作者在诗题中已经明言“戏书”,恐怕并不真认为范蠡有此用心,而只是开一开古人的玩笑,追求些机智的趣味罢了。
总而言之,比较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手段,在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创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涉及的作品很多,更重要的是,比较思维的理论意蕴非常丰富,且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有助于我们探查文学之内的创作技巧与风格追求以及文学之外的评史传统与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