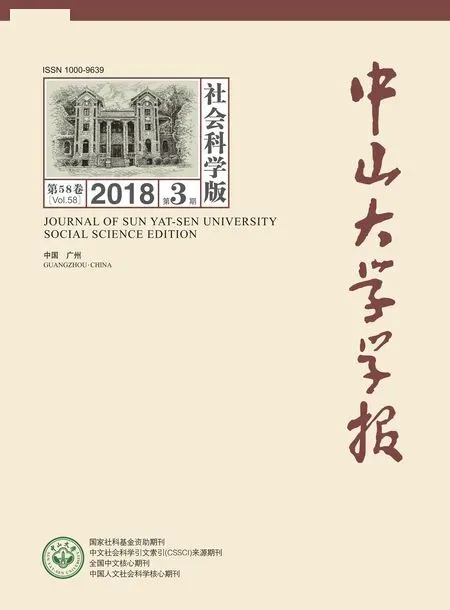阳明心学对甘泉心学的三层批评*
——从工夫面向看
赖 区 平
一、引 言
王阳明(守仁,1472—1529)龙场悟格物致知之旨,至后期乃揭致良知教。其后学皆秉承致良知宗旨,但据研究,阳明与其后学之主要问题意识已有所转变:“对阳明而言,其问题意识主要是针对朱熹‘格物穷理’之‘求之于外’与‘支离’而发,故阳明关注的是工夫的‘入路’问题”,而“追求‘第一义工夫’是阳明后学的主要问题意识,它意谓:道德实践的本质工夫,必以本体的呈露觉悟与保任护持为优先,而非只是意念杂思的克除”*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第664、667页。。值得追问的是:阳明及其后学这两种不同的主要问题意识,其间转变是如何可能的?比较而言,仅就儒学中有心学偏向的一系来说,孟子以后,有陆象山(九渊)、杨慈湖(简)、陈白沙(献章)、湛甘泉(若水)、王阳明等,何以象山、白沙等后学无此关于本体工夫(即第一义工夫)的主要问题意识之生成(而甘泉后学若有此主要问题意识,当亦多因阳明学之影响所致),唯独在阳明及其后学中才有此问题意识、才出现对本体工夫的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并由此而影响整个中晚明儒学?换言之,阳明心学究竟比象山、白沙、甘泉等之心学有何殊胜之处,而能开出本体工夫的新视野?
从工夫面向的视角来考察阳明中后期思想转变之理路,可见阳明中后期都贯彻了从工夫之方法、根据、目的三个面向对朱子学之支离、义外、务外等流弊之批评,并提倡相应的心学主张:只有一个工夫、只有一个本体(心即理)、向里用功(复其本体),此亦可谓心学一系的基本主张,尤其是后二者;阳明后期揭致良知教,对自身所倡静坐、诚意等中期教法的弊端及局限不断反省而突破,凸显工夫之动力、起点、准则等三个新的工夫面向,使其工夫教法更加精一*以上所论,以及对工夫之诸面向如工夫之方法、根据、目的与工夫之起点、动力、准则的具体描述,参见赖区平:《王阳明中后期思想变化之理路试析——从工夫面向的视角来看》,王博主编:《哲学门》(总第3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1—254页。。可见,至少在后期揭致良知教,阳明之问题意识实已不止于针对朱子学流弊,同时是针对心学一系内部的流弊和局限*诚然,阳明针对心学一系内部流弊和局限的考虑,仍非指向“凸显工夫之动力、起点、准则等三个新的工夫面向”所可能带来的新流弊或局限,而后者是中晚明心学对阳明学流弊所着重针对的。。
这还是就阳明自身心学思想的比较而言。站在心学立场上,比较考察一下阳明心学与心学内部其他家派思想的异同,也有其自身意义。以下主要从工夫(本体)之不同面向这个视角,探讨阳明对另一心学大家、同时是其挚友的湛甘泉(若水,1466—1560)之心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为中心)的批评。
从工夫面向之视角来看,大致可将阳明心学对甘泉心学、随处体认天理说之批评归结为三个层次。就字面针对性来看,三层批评依次针对天理、随处、体认三个词。具体而言,第一层批评从工夫之根据、目的方面,指出“天理”有可能被误解为心外之理,延续了对朱子学末流的警惕和批评;第二层批评,从工夫之根本目的的针对性方面,指出甘泉之说“恐主于事”,而未真正抓住本体头脑,未直接针对工夫之根本目的,体现出对本体工夫这一阳明后学主要问题意识的自觉和关注;第三层批评,则进一步从工夫之起点等面向,指出甘泉之说即使抓住本体头脑,也未能指点工夫之起点等面向,由此反显出致良知教之“尤简易明白”,其中也展开关于工夫之本体的深入分析,并对本体工夫问题做更进一步探讨。
二、第一层批评
人们一般多注重阳明对甘泉学说(“随处体认天理”说)的第一层批评,即认为甘泉之说“求之于外”*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按,此处实指对甘泉格物旧说之批评,详下。。连甘泉本人也以为阳明以其说为“义袭”“求于外”*甘泉《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言:“陈世杰书报吾兄疑仆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为求于外。若然,不几于义外之说乎!”([明]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卷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572页)按此书作于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参见黎业明撰:《湛若水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5—76页)。又嘉靖八年己丑(1529)阳明去世后,甘泉作《奠王阳明先生文》言及:“遥闻风旨,开讲穗石:但致良知,可造圣域;体认天理,乃谓义袭;勿忘勿助,言非学的。离合异同,抚怀今昔。切磋长已,幽明永隔。”([明]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卷3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220页)“遥闻风旨”,即听陈世杰所转述。可见,阳明其实并没有在甘泉面前直接表示过“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为“求于外”“义袭”,甘泉只是根据别人的转述而确认此事,但转述者的叙述是否确切,是否省略了某些背景或条件,则不得而知。。此实是从工夫之根据这个工夫面向,批评甘泉之说有析心与理为二之弊端,从而也导致在工夫之目的上求理于事物。此实即言甘泉之说已入于朱子学末流(俗儒)。事实上,至少就阳明流传文字而言,很难见到直接明确之批评。
阳明言:“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功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来喻以为恐主于事者,盖已深烛其弊矣。”*[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此段包含两层批评,且侧重第二层批评(详下),而亦有可通于第一层批评。大意言甘泉之说虽鞭辟近里,然仍有被误解的可能性(而非必然导致误解),此即第一层批评,指随处体认天理说本身并无问题,而更多指向用此工夫者之病,也就是恐怕有学者将“天理”当作心外之理,以致不反诸身心以体认天理,却求理于事物。故阳明言此是针对“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俗儒)而言,因此退一步言“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阳明又进而言“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若认得心即理,而不在心外寻求天理,则随处体认天理自然无病。
阳明《答方叔贤》又说:“论象山处,举孟子‘放心’数条,而甘泉以为未足,复举‘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数语。甘泉所举,诚得其大,然吾独爱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见其大者,则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实加切近之功,则所谓大者,亦虚见而已耳。”*[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4,第175页。甘泉以天理为“吾心中正之本体”*[明]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卷1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690页。,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明]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卷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571页。,故格物非在外,亦必不离本心而泛泛然去格。在阳明看来,若泛泛然强调穷格天地万物之理、随处体认天理*有学者辨析“天理”的两个具体内涵(本体意义上的天理,名物度数之知识),指出甘泉的“天理”概念含混不清,而引来阳明“求之于外”之批评。参见郭晓东:《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与湛若水哲学之比较》,《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第83—85页。,而不着重点出“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7,167,168页。标点略有改动。这一头脑,则恐怕就实际的工夫指引而言,说得虚大而未能切己用功,卒未免朱子学流弊。此可谓第一层批评之深意,但仍不构成实质批评,而只是有保留的外在批评。
三、第二层与第三层批评如何可能
如上所言,一般多注重阳明对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第一层批评,就连甘泉本人亦然。对于阳明其他的可能批评,则多未注目。但在阳明,第一层批评还是外在批评,真正的内在批评在于第二、三层:后两层已脱离朱子学末流之外在误解,属于心学一系之内部批评。而其线索,首先在于阳明本人的论述。另外,阳明弟子如邹东廓(守益,1491—1562)、钱绪山(德洪,1496—1574)、王龙溪(畿,1498—1583)的论述,可为佐证。凡此下面将详述。此处主要考察第三点,即阳明对甘泉格物说的批评,以与其对随处体认天理说的批评相参。
前面曾提及阳明对甘泉学说“求之于外”的批评。此批评可见于《传习录》,但彼处实际上并非对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一说的批评,而是对甘泉格物“旧说”的批评:“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7,167,168页。标点略有改动。按此条后文又记:“己卯……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7,167,168页。标点略有改动。正德乙亥即正德十年(1515,阳明44岁),己卯为正德十四年(1519,阳明48岁)。可见甘泉后来对格物已有新解,阳明亦认为与己说相近,而此时阳明还没有揭致良知教。
在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阳明49岁)揭致良知教*钱绪山《年谱二》言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阳明50岁),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34,第1278页)。陈来认为阳明于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阳明49岁)已提出致良知说(参见氏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0—152页)。此处从陈说。后,阳明仍说:“致知格物,甘泉之说与仆尚微有异,然不害其为大同。”*[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5,第184页。按,此书作于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又说:“世杰来,承示《学庸测》,喜幸喜幸!中间极有发明处,但于鄙见尚大同小异耳。”其下细论甘泉《学庸测》内容:“‘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似有毫厘未协,然亦终当殊途同归也。修齐治平,总是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致知之说,鄙见恐不可易。”*[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5,第181页。按,此书作于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所谓微异大同、大同小异、殊途同归,可见阳明已大致认同甘泉之说。若是阳明仍以为甘泉格物、随处体认天理等说是求之于外、义袭,即仍停留于第一层批评,则怎么还可能说“大同”“同归”?所谓大同、同归,即在心即理、向里用功等心学一系基本主张、大本大原上,并无区别。进而,所谓微异、小异、殊途,也就是在心学基础上的内部各种不同:除了字义训释、解经方式外,就随处体认天理而言,主要即体现在阳明的第二、三层批评上。
四、第二层批评
阳明又言:“‘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6,第201页。按,此书作于嘉靖五年丙戌(1526)。又言:“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6,第219页。按,此书作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即甘泉之说非朱子学末流,而已属于心学一系思想,故“大约未尝不是”“无大相远”;但与致良知教相比,终究稍逊一筹,即“尚隔一尘”“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致良知教更“直截”,随处体认天理则更“迂曲”。这具体是指什么呢?
阳明接着说了一个“种植”譬喻*[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6,第219页。:致良知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体认天理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诚然,目的只有一个,但这一个目的可从两方面来得到表述、实现。致良知说是直接奔着根本目的来做工夫:“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若实现了根本目的,则次要目的自然也随着实现。体认天理之说,则着重在实现次要目的,由此而渐渐达于根本目的。“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只有最终实现根本目的,次要目的之实现才得到根本保证。可见,二者在工夫之根本目的上有直接、间接之别。致良知说更直截,体认天理之说则更迂曲些:此即“直截迂曲之差”。
阳明曾通过援引门人邹东廓来书,正面表露甘泉之说的缺陷:“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功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来喻以为恐主于事者,盖已深烛其弊矣。”*[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6,第206页。按此书作于嘉靖五年丙戌(1526)。邹东廓来书今不存,但可见类似说法*[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卷10、1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93、508、619页。。此即对甘泉之说的第二层批评:“恐主于事。”邹东廓后来主戒惧本体之说,并将戒惧工夫(即阳明所谓“戒慎恐惧功夫”)分为三种:戒惧于事为,戒惧于念虑,戒惧于本体*[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卷15、17,第734、819页。。依此,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说,恐亦有只戒惧于事为、念虑之嫌,而未能戒惧于本体。阳明致良知教,则直接专注于良知本体,强调在此本体上用功,亦即“戒惧于本体”。从工夫面向的视角来看,随处体认天理之说虽然蕴含甚或点出了头脑,即天理本体,但在实际用功时仍有可能未以之为重心,未真正以天理为头脑,而滑落到事为念虑这些工夫之境域或次要着力处,注重随事随处、逐事逐念之为善去恶这种零碎、枝节工夫,此即“主于事”。
可见,此层批评主要当是指向“随处体认天理”之“随处”二字*阳明将“随处”说为“随事”。甘泉曾明确强调“随处体认天理”之“随处”非“随事”。在他看来,“随事”指有事时,而“随处”兼含有事无事(参见[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04页)。不过,阳明所理解的“随事”之“事”,其实也可兼有事、无事而言。且观阳明他处并未再改称“随处”为“随事”,故笔者推测因下文将述及东廓所言“恐主于事”,故此处改“处”为“事”,以顺起下文。总之,阳明的意思是:哪怕“随处”是涵盖有事无事而言,而不仅限于有事时,也只是主在事情上面(无论是有事时还是无事时),而不是主在本体上。因此,虽然阳明在字面上将“随处”说成“随事”,但在义理上并未误解甘泉之说。。此虽是心学工夫,然又有意无意地导向某种“主于事”的零碎工夫,类似于所谓“一日三点检”,即着重于“茂其枝叶之生意”,经此一层转折方可“复其根本”,如此则非如致良知之着重良知本体,而直接“培其根本之生意”。
实际上,此处所言已类似于本体工夫与其他零碎工夫的区分。阳明此第二层次之批评,实已与阳明后学之主要问题意识无大差别。主于本体即是本体工夫,主于事(事为、念虑)则是第二义的。因此,通过阳明心学与甘泉心学的比较,通过前者对后者的批评,可见至少在阳明后期,已形成阳明后学那种关注本体工夫(第一义工夫)的问题意识。只不过在阳明,未必是主要的问题意识,而最多是前沿的问题意识。
五、第三层批评
第三层批评的要点是:即使甘泉之说真正抓住“天理”本体这个头脑,在本体上用功,而属于本体工夫,那也还不够,也只是指示工夫之目的等面向,而未能如致良知教那样凸显工夫之起点、动力、准则等重要面向,未能如致良知教之尤亲切明白。在阳明的文字中,实未有直接对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的第三层批评。以下主要从三方面来说明:一是参照阳明对孟子集义之说的评论,二是阳明、甘泉及其后学对“天理”二字之观感,三是阳明高弟王龙溪、钱绪山对甘泉之说的批评。
(一)“集义”
阳明说:“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59,144页。集义之“义”虽亦指示本体,但难直接把握,毕竟需再转个弯(“心得其宜之谓义”*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59,144页。),故一时使人难于实际体认到头脑;而点出个“良知”,则“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10,第178页。,当下即可认取,当下便有实下手处做工夫。事实上,通过点出“良知”本体,致良知不仅凸显工夫之起点,而且还直接凸显工夫之准则、动力。总之,致良知不仅简易明白,且比其他心学教法显得“尤”简易明白*[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6,第213—214、222页。按,二语见于阳明答两位弟子的书信,分别作于嘉靖五年丙戌(1526)、嘉靖六年丁亥(1527)。,其中包括阳明中期教法如静坐、诚意,包括孟子之“集义”,也自然包括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这就涉及阳明对甘泉之说的第三层批评。随处体认天理固然也点出了天理本体,但主要指向工夫之根据和目的,而未能凸显工夫之起点、准则、动力等面向,即不如致良知之尤简易明白。
(二)“天理”
前述“第一层批评”言及“随处体认天理”本自无病,但“天理”有可能被误解为心外之理因而求理于事物。此被误解之可能性本身,表明随处体认天理尚非究竟一着,而仍需转个弯澄清误解,方有实下手处。此在甘泉门下已有所验。甘泉揭“随处体认天理”,以“天理”二字为大头脑*[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第885,889、890,890页。。然门人却屡有“何谓天理”“难为下手”“天理难见”*[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第885,889、890,890页。之疑,即是明证。对此,甘泉说:“天理二字,人人固有……故途之人之心,即禹之心,禹之心,即尧、舜之心,总是一心,更无二心……唐人诗亦有理到处,终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须要得其门。所谓门者,勿忘勿助之间,便是中门也……责志去习心是矣,先须要求此中门。”*[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第885,889、890,890页。其思路仍是通过本心来指点天理。更要紧的是,末尾又言“须要得其门”:“随处体认天理”作为头脑工夫,“天理”作为工夫之头脑,却居然尚未能指点出门面,还要再说个“勿忘勿助之间”作为中门,方得其门而入。即此已可见其尚未能直截了当指示工夫之起点。就此而言,甘泉教法确不及致良知之易简明白。
(三)“致与体认,终当有辨”
此第三层批评在阳明高弟王龙溪、钱绪山那里,也可见一斑。其时多有主张调停阳明、甘泉二家宗旨者,龙溪、绪山则或强调或委婉指出阳明致良知教之优越。龙溪针对“认得天理,即是良知;致得良知,即为天理。一也”之说,而言:“是则然矣。致与体认,终当有辨。谓之体认,犹涉商量;致则简易直截,更无藏躲处。毫厘之间,存乎默识,非可以意解测也。”钱绪山则言:“良知天理,岂容有二?先辈假此以示人,乃话柄耳。若夫致与体认之功,迂直烦简,毫厘之机,存乎悟者之自得,非可以口舌争也。”*参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2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37、591—592页。王龙溪记载的钱绪山之语,并未标明何时所说;龙溪自己说的这番话,则是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说的,并且是在给友人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写的行状中所追述,这至少表明他此时还坚持此说,而甘泉已于三年前(1560)去世。
首先,“是则然矣”“良知天理,岂容有二”,表明两人亦皆认同阳明、甘泉之说大同小异;其次,两人又认为,“致良知”之“致”与“随处体认天理”之“体认”二者有“迂直烦简”之别、“终当有辨”,前者更简易直截。这具体指什么?
“体认”之所体认,从工夫面向的视角来看,主要只是作为工夫之目的,是尚待努力去求取的工夫之终点,故“犹涉商量”;致良知之致,则直接以良知为工夫之起点(以及准则、动力),良知当下见在,只需将良知扩充至极,推极于事事物物,故简易直截到“更无藏躲处”。此显系阳明“尤简易明白”之说。“致”与“体认”之比较,即工夫下手处之比较:良知凸显并作为工夫之起点,故只要当下承领以致其极;而天理更多强调作为工夫之目的、终点,故还需体认商量。可见,致与体认之别,根源于两种心学教法所主之本体(工夫头脑,即良知与天理)所凸显的工夫面向之不同。
大致说来,集义之“义”、随处体认天理之“天理”,着重从性体、道体指点,而致良知则直接从心体、知体指点。与性体、道体相比,良知心体更直接展示本体的生动活泼、灵明虚灵的一面,这在工夫之起点、动力、准则面向中得到清晰展现。就工夫之诸面向来说,工夫之方法、根据、目的这三个面向,尤其是工夫之根据,从心体、性体、道体皆可得到说明,甚或从性体、道体可得到更好说明;而工夫之起点、动力、准则这三个新的面向,尤其是工夫之起点,则经由良知心体才得到确切落实。阳明致良知教之殊胜义端在于此,即凸显出工夫之动力、起点、准则这三个新的工夫面向,高扬了良知心体的一面。此从阳明及龙溪、绪山对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第三层批评,亦可清晰见出。
在某种意义上,这已表明对工夫之本体的深入简择,并由此而对本体工夫(第一义工夫)做进一步规定。本体工夫即抓住本体头脑,在本体上用功。从工夫面向之视角来看,即是直接以本体为工夫之根本目的,悟得并保任本体。通过此处关于工夫之本体的考察,还可以对本体工夫做进一步规定。在本体上用功,直接以本体为工夫之根本目的,诚然已入于本体工夫之域;但问题还在于,此“本体”凸显了哪些工夫面向。义、天理、良知(以及性、道、至善、独体)等等,都表示唯一的本体,就此而言,它们也只是一个,各自都蕴含、确保工夫面向之整全性;但落实到具体的工夫指点上,就义、天理、良知等各自的内涵规定来说,不同的本体指点用语也确实凸显了各自不同的工夫面向。因此在工夫教法中,对本体指点语、指示词,有谨慎选择简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阳明学极强调工夫之亲切简易,而“良知”无疑比义、天理等能更简易直截地点出工夫之起点(及动力、准则),故以“良知”为更好的本体指点语,而致良知则成为尤简易直截的本体工夫*然而,甘泉等所更强调的未必只是亲切简易,故其所青睐的本体指点语也就不同,其所标举的本体工夫也有所异。即使同以致良知教为本体工夫,也因强调面向不同而有别,观阳明后学之良知异说可知。。
由此可以确定关于本体工夫的两个层次:第一,在本体上用功,直接以本体为工夫之根本目的,此是本体工夫的前提条件。第二,所择取的本体指点语,更适宜地凸显了相应的工夫面向,因而成就更好的本体工夫。阳明心学对甘泉心学的第二、三层批评分别对应于本体工夫的这两个层次。
六、余论:反批评和救正
总观阳明心学(致良知教)对甘泉心学(随处体认天理说)的三层批评,其中,第一层批评还是外在批评,体现对朱子学流弊之警惕;第二、三层批评是在心学内部进一步的内在批评,体现致良知教之尤简易明白,使得阳明心学殊胜于其他心学流派,良知学优于一般心学,也使得阳明学开展出对探讨本体工夫乃至工夫之本体的新视野。当然,凡此批评和殊胜处皆循阳明心学一方之思路而言。事实上,从甘泉这方面来看,阳明所论皆未必成立;进一步,甘泉还反过来对阳明有所批评。
就第一层批评而言,此只是有保留的外在批评;如上引述,甘泉多所辩驳;且此点学界所论已多*参见张立文:《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学术研究》2013年第9期,第21—22页。,故不赘述。反过来,甘泉认为“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第883,881,885,900页。,此乃偏于内。专求于外固然是支离,是内非外也是支离,二者皆有所偏*[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第883,881,885,900页。。就第二层批评来说,亦如上述,甘泉指出“随处”并非偏于有事时,而是无间于动静,且“随处体认天理”也点出“天理”这个“大头脑”*[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第883,881,885,900页。。至于第三层批评,甘泉有如下回应:致良知让人承领太易,使学者认情识为良知,猖狂荡越名教。故甘泉思以“天理”(随处体认天理)救正之:“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不相用不足以为知。夫良知必用天理,则无空知;天理莫非良知,则无外求。”*[明]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卷1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705页。按,此书作于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虽言良知、天理“相用”,实则以天理为主,天理自然是良知,而良知则“必用天理”,否则便成空知、师心自用*[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第883,881,885,900页。。甘泉对良知之如此理解未必适当,故阳明本人已斥之为“似是而非”*[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6,第218页。,阳明弟子如钱绪山、王龙溪则多有辩护*[明]徐爱、钱德洪、董沄撰、钱明编校整理:《徐爱 钱德洪 董沄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2,第35页。。如此,甘泉之论亦似某种外在批评。
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批评亦可能深中其弊。甘泉弟子曾问及阳明与一僧言“禅家有杂、昏、惺、性四字”,其中有“尘念既去,则自然里面生出光明,始复元性,此之谓性”。对此,甘泉言:“……圣人与释氏说性不同。圣人言性,乃心之生理,故性之为字,从心从生。释氏言性,即指此心灵明处便是,更不知天理与心生者也……释氏以此生理反谓为障,是以灭绝伦理……光明者即可谓性乎?否也。”*[明]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卷1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652页。姑不论所述阳明故事是否属实,阳明指点学者虽不离“良知即天理”之一面,但确实也强调良知本体之为光明、虚灵的一面。在甘泉看来,阳明是过于强调后者,乃至淹没前者了。就儒者之学而言,本体之为“生理”“天道”这一面是不可或缺的,在儒学工夫论中也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儒家区别于释氏的根本之处。若不够重视甚或忽视此一面,则恐相关的本体、工夫之说终不免有各种局限、流弊,乃至沦于释氏之学。故甘泉着力凸显本体之天理、生理面向,以批评、补救致良知教之偏。
实际上,无论甘泉之批评是否切中实质,至少其对致良知教之总体担忧是有理由的。阳明身后,致良知教逐渐流行学术界,时代学风已更换,以至于对良知作为工夫起点、准则、动力之过分强调,已造成新的问题。诚然,致良知教有其胜场,尤其是高扬良知心体之一面,而阳明后学多秉承此义,尤其是王龙溪和泰州学派,更是自觉宣扬此义。然而事物往往是两面性的。反过来看,也可以说正是对心体殊胜义的过度强调,由此使其相应的诸流弊(参以情识、荡以玄虚)之出现得以可能,并相应地引来阳明学内外的各种批评(自我批评)或救正。且更多已非甘泉“良知必用天理”式之批评,而是在继承致良知思想之基础上的内在救正。从思想史的脉络总结看,这些批评、救正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对本体工夫之基本内涵的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对工夫之本体的重新衡定。前者如阳明学内部聂双江(豹)、罗念庵(洪先)即限定良知之为本体而非发用、致力于使致良知教归于涵养一路;后者如其他阳明后学王塘南(时槐)乃至公开表示不信致良知教者如李见罗(材)等,则逐渐开出不同于偏重心体、心宗之致良知教的另一脉性宗思想*可参侯洁之:《晚明王学宗性思想的发展与理学意义——以刘狮泉、王塘南、李见罗、杨晋庵为中心的探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直至刘蕺山(宗周)明确分别心宗、性宗而统合之,凸显性体,以救正致良知心体偏重灵明虚灵一面所带来的流弊等。当然,此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