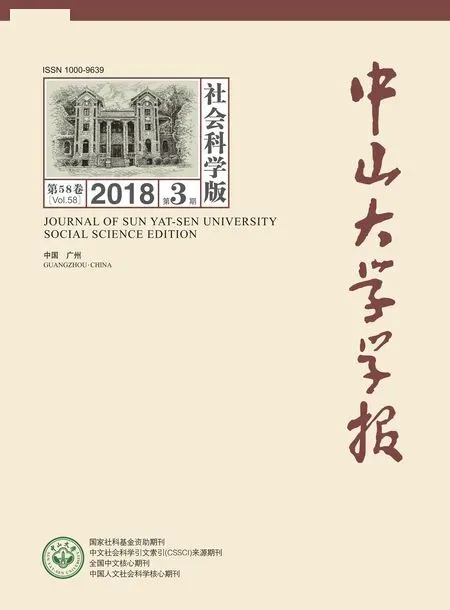齐物逍遥与知性知天*
——孟庄的不同旨趣及其互补关系
丁 为 祥
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能没有比孟、庄更吸引人的思想家。一方面,他们年岁相近、出生地相连,且分属儒道两家的二代巨擘。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旨趣绝不相侔:孟子往往通过批判一切、检讨一切的方式以夯实儒家的人文基础,庄子则往往是嘲笑一切文明设施与人伦建构而一任其性。于是人们纷纷设想孟、庄两位相逢的场面:究竟是孟子批判了庄子,还是庄子嘲笑了孟子?他们不仅没有相逢,而且从来都没有提到过对方;这种情形,简直就像两位才艺高超的达人,虽然作坊相邻而又手艺互逆,但却只是专注自己的世界而已。人们又纷纷从楚、鲁之不同的文化背景或儒道两家不同的思想谱系出发,以分析孟、庄两位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色。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固然可以揭示孟、庄两位思想所以形成的不同基础,但并不能说明其思想旨趣之具体形成,也不能说明其不同的特色;即使从儒道两家不同的思想谱系出发,也只能说明其所以形成的大致方向,仍然不能说明两家思想之具体特色。这样一来,孟、庄思想的不同特色就只能归结于二人不同的入世心态与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
一、不同的出发点:天性与德性
庄子的《逍遥游》虽然以“逍遥”标宗,但其逍遥主要是通过鲲鹏与学鸠的反复比较凸显出来的,是通过“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逍遥游》,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7年,第19,32页。来表现其所谓“无待”(“彼且恶乎待哉!”)追求的,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外在的客观标准;作为人,或者也可以表现为所谓“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逍遥游》,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7年,第19,32页。。这样一来,从理论的角度看,庄子所谓的“逍遥”似乎只有一个“无待”的规定;但如果从生存实在的角度看,“率性自适”似乎可以说是其所谓逍遥的基本原则。
关于庄子的逍遥,郭象注解说: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鴳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逍遥游》,第1页。
郭象的这一注解两次提到“任其性”。其发展则是将庄子的“无待”置于“有待”的基础上,并明确认为“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这是对庄子思想的一种深入。从“尺鴳”到“大鹏”,无不生存于“有待”的世界;因而所谓“无待”,只能实现于“得其所待”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只有在“有待”范围内,才有可能达到所谓“无待”而逍遥的地步。
那么,庄子这一“无待”而又“逍遥”的心理期盼究竟源自哪里呢?这就首先源于其最直接的人生感受:“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齐物论》,第63页。这真是透彻心髓的悲哀!如果说这只是对人生有限性的伤感,庄子真的是在追求与天地同寿吗?显然,仅从其以“鼓盆而歌”来应对其妻子之死以及其所塑造的“真人”之“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53页。来看,庄子根本就不是要追求长生久视,而只是要超越、摆脱所谓人伦文明带给人之生命的重重扭曲与种种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庄子的“无待”与“逍遥”与其说是在追求一种实然基础上的生存状态,不如说主要是一种人生境界。
构成这一境界之根本出发点与权衡标准的,恰恰就是随着人之禀气赋形而来的“天性”。“天性”*《孟子·尽心上》云:“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吴哲楣主编:《十三经》,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1423页)这一概念虽然为孟子所提出,但最足以表达庄子的追求。请看庄子的呼吁: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秋水》,第648页。
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骈拇》,第350页。
所谓“无以人灭天”就是对人之自然天性保持一种尊重与“谨守”的态度。“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则又说明所有的人文教化都无法去掉人的生存之忧;不仅不能去除人的生存之忧,而且所有的人生之忧恰恰是所谓人文教化强加于人的。很明显,庄子这里明确坚持一种天性自然的立场。正是在这一立场上,庄子才有其所谓“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达生》,第721页。的人生态度。
如果说庄子对人生抱定一种天性自然的立场,孟子则恰恰相反。在人生的基本立场上,孟子往往是从人的道德善性出发的。在孟子看来,只有道德善性才真正代表人的天赋人性。孟子的这一立场,不仅有子思“天命之谓性”*《礼记·中庸》,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560页。的根据,而且还有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而又不证自明的所谓“不忍人之心”的现象。关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举例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65—1366页。它也包括《大学》所谓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礼记·大学》,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586页。之类。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人本来就存在仁义礼智的四端之心。
孟子的这一出发点典型地表现在他与告子的人性之辩中。在人性问题上,告子的观点接近于庄子,或者说他们都是以自然天性为基本人性,因而告子也就将所谓道德善性视为人伦教化或人文加工的产物。所以,对于孟子的性善主张,告子首先正面阐发自己的人性观点,然后对孟子的观点加以反驳。他们的辩论是这样展开的: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③④ 《孟子·告子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406,1411,1411页。
告子以杞柳与桮棬的关系比喻人性与仁义的关系,说明在他看来,人性并不必然表现为仁义,正像杞柳并不必然为桮棬一样;杞柳固然可以加工为桮棬,但同样可以做成其他器物。这说明在告子看来,孟子所谓的性善论实际上是把人通过人伦教化所形成的善视为人性本来就具有的善,这等于是“以心善言性善”,或者说是把先天本然的杞柳直接视为经过后天加工而形成的桮棬一样了。告子所谓的“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一说实际上是认为人性既可以为善(桮棬),也可以为不善(其他器物);就人的本然之性而言,则只能说是一种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但又可善可恶的自然之性。这正可以说是对自然人性的一种经典表达。
在孟子看来,善是人性所必然蕴涵的,是人内在本有而又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人生取向。他对告子的反驳是:“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孟子认为,善是人性本然固有的,是顺着人性的自然发用而必然表现出来的;如果将善视为人伦教化——所谓人为加工的产物,那么,这种善就不仅是像小人“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一样的故作之善,而且对人来说,所谓善也就只能成为一种“外铄”的“伪善”了。如果将善视为一种外铄或“为作”的产物,善也就从根本上缺失了人性的根据。如此一来,所有的善也都将成为一种故作的装样子之善。实际上,这就成为对善与人性的一种莫大伤害。所以孟子归结说:“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实际上就是究竟应当从“天性”还是“德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理解人伦文明,包括善。这一分歧既是儒道两家的基本分歧,同时是孟子与庄子的根本分歧。孟、庄关于人生的不同设计,包括其各种不同的理论建构,都是从这种不同的人性论出发的。
如果从孟子对人的分析看,他又常以所谓“四体”比喻人之所不可或缺的“四端”。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者,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66页。又说:“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③这说明,在孟子的语境中,虽然曾以人之所不可或缺的“四体”来比喻人人所本有的“四端”,但“四体”又是分大小的:所谓小体,就指耳目口鼻所代表的感性之欲;所谓大体,则代表“心之官”及其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四端”。因而,只有从人的“大体”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人的“四端”。
关于“大体”与“小体”的关系,孟子说:
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④
从这个角度看,孟、庄的思想分歧就表现在作为其出发点的大体与小体、道德善性与自然天性之间。庄子既然主张依其“故”、安其“性”并等待其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命”,那么他也就是一个反对任何文明建构的自然天性主义者。
二、不同旨趣:齐物、逍遥与知性、知天
庄子为什么要将人伦教化与人伦文明看作是其“逍遥”追求的主要障碍呢?这是与其人生感受以及其人生的根本志向密切相关的。对庄子来说,既然人生不过是一个“与物相刃相靡”的过程,那就是说,所谓人生不过是一种不断受到戕害的人生;而作为权衡是否受到戕害的标准,就是人之既“不能断”、也“不能续”的自然天性本身。正是从人的天性出发,庄子才提出“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的比喻和说明。也正是从这一关怀出发,庄子才将楚王的卿相之邀视为沦丧其“天性”的诱惑,于是有了“持竿不顾”*[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秋水》,第662页。的抉择。
这种谨守“天性”的人生究竟应当从哪儿做起呢?这就必须放弃对世界的干预,尤其是要放弃那种一心想改造世界或改造人生的意愿。庄子通过“渔父”对孔子的嘲笑来表达这一关怀: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
客指孔子曰:“彼何为者也?”
……
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问曰:“有土之君与?”
子贡曰:“非也。”
“侯王之佐与?”
子贡曰:“非也。”
客乃笑而还,行言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渔父》,第1121—1124,1124页。
在对孔子的这一点评中,庄子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既“危其真”,又远于道。所以成玄英疏云:“夫劳苦心形,危忘真性,遍行仁爱者,去本迢遰而分离于玄道也……”*[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渔父》,第1121—1124,1124页。这说明,庄子根本就不赞成儒家改造政治的人伦理想。当然,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道家的一种传统。
庄子也绝不赞成儒家那种将自己视为世界主人的思想,而这一点同样是通过对孔子的调侃加以表达的。请看庄子对孔子“困于陈蔡”一事的分析与说明: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翐翐,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山木》,第744—749页。
这里,庄子将孔子的“陈蔡之困”完全归因于其个人的“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而其建议则是应当像意怠在鸟群中一样:“近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这就是庄子所谓的“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这样一来,儒学也就真正成了一种鸟兽之道。
不仅如此,庄子还通过所谓“真人”“至人”“神人”的榜样作用,提出了一种他最认可的生存方式: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50—251页。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预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惔,乃合天德。*[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刻意》,第592页。
所谓“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式的生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呢?如果说“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还可以说是一种鸟兽之道,那么,现在就应当追求一种草木瓦石式的生存。所谓“不思虑,不预谋……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就是对草木瓦石生存之道的恰切描述, “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也就彻底走向“物化”之途了。所以,庄子的“逍遥”完全是以“齐物”为前提;也只有在“齐物”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达到所谓“逍遥”的境界。
庄子将人“物化”以“齐物”的方式,被后来的邵雍概括为一种以“反观”为特征的“观物”法:
天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北宋]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观物内篇》,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9页。
邵雍“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式的“反观”法,就相当于庄子所谓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人间世》,第163页。。但是,邵雍所谓“不以我观物”主要是要排除“以我观物”之主体色彩或“我”之主观的因素,所谓“以物观物”主要是希望能够从“物”的角度来打量世界、观察人生。这种将人彻底“物化”的方式是对庄子“齐物”思想的活用。如果说庄子的“逍遥”建立在“齐物”的基础上,“齐物”就是要以“物”之自存的方式作为人的生存之道。
孟子的人生观完全是通过对人性的重重辨析所确立起来的,因而道德善性也就成为其规划人生的基本出发点。庄子通过“齐物”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其实在孟子思想中同样存在,但孟子完全是通过相反的对人之道德善性的涵养与扩充的方式实现的,这就和庄子表现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走向。比如,对于庄子陶醉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齐物论》,第88页。,孟子就有如下表达:“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孟子·梁惠王下》,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55,1356页。孟子既提倡“与人乐乐”,当然也赞成“与众乐乐”。甚至,孟子还明确坚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55,1356页。孟子的“乐”完全建立在人的道德善性的基础上,这就与庄子具有完全不同的色彩。
对于庄子的“齐物”追求,孟子也完全可以通过“尧舜与人同”*《孟子·离娄下》,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95,1392页。的方式表现出来。区别仅仅在于:庄子坚持人必须“物化”,然后才能“齐物”;而孟子的“同”仅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并且是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95,1392页。这种“几希”之点的基础上“与人同”的。这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庄子的“同”是从人的角度下滑、消解式的齐于物;孟子的“同”是在“几希”之点的基础上超越上达的“与人同”,从而成为道德理性基础上的“同”。
至于作为体现庄子最高理想的齐同“天地”、情通“万物”,这在孟子思想中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418,1420,1421页。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418,1420,1421页。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418,1420,1421页。
这些描述都有“同”与“通”的含义。所不同的是:庄子是以下滑、消解式的以“齐”求“同”,孟子则是通过超越上达式的以“统”来实现“通”;庄子是以“物”之生存来规范“人”,孟子则是以“人”之道德善性来提振并观照“物”。在对孟子这一思想的诠释中,张载明确指出:“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阴阳,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正蒙·神化》,[北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6页。这也是一种“和”与“通”。
到了王阳明,孟子这种“知性”“知天”的追求指向被明确概括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而“人己”“物我”之间,完全成为“目视耳听、手持足行”的关系。阳明的《答顾东桥书》指出:
……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5页。
王阳明是孟子以来儒家心性之学的集大成者。这段描述就是通过所谓“目视耳听,手持足行”的方式来表达儒家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阳明这种万物一体之仁究竟是以孟子精神诠释了庄子,还是以庄子的精神武装了孟子,似乎成了一个“庄周梦蝶”式的问题。
三、理想、超越与遍在、落实
在孟子与庄子不同面向的探索中,其思想旨趣的异质性是非常分明的。我们暂且不管孟子从儒家人伦关怀出发的知性知天追求与庄子建立在人之自然天性基础上的无待追求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坐标,仅从哲学理论的角度看,他们的不同追求也就明确表现为如下特征:孟子始终高扬道德性、理想性的超越,而庄子一贯坚持齐物、逍遥之遍在性追求与自然性落实。
从孟子来看,他为什么一定要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现象出发,以发掘人人所同具的“不忍人之心”?又从这种“不忍人之心”出发,以确立人人所必具的“四端”,从而以所谓“此天之所与我者”与“我固有之”的方式来确立人之道德善性的天道本体依据呢?应当承认,当孟子展开这样的探索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就是一种关于人生道德善性的理论探讨,也不会想到这就是一种关于人生道德实践追求的理论设计,他所不能自已并且也必须对自己进行说明的就是为什么“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的产生居然还是“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一句话,任何经验的、功利的甚至包括所谓习俗的因素,都不是这种恻隐之心产生的真正根源。所以他最后才不得不总结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66页。在这一基础上,孟子才追溯性地推论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408页。并从比较的角度指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411,1411,1411页。至于其所谓的知性知天追求,说到底也不过是这种关系之一种合乎逻辑的展开而已。
当孟子对人之道德善性展开这样的探讨时,并未想到这就是对人之主体精神及其世界的拓展,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精神奠基,但他无疑想到了这就是在天道性命相贯通背景下能够确立人性的天道本体依据。这样一来,孟子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天人贯通之学。从这个角度看,孟子也是从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思想背景出发,从而纵向立体地撑开了人的精神世界,因而可以说是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理论奠基。但孟子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想,他只是希望如何能够使人都成为“大人”。从其知性知天的指向来看,他也只是希望人们能够自觉其“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411,1411,1411页。,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人”而已。
如果对孟子的这一思路进行哲学理论的权衡与思考,那么它显然是一条现实人生基础上的超越上达之路;所谓知性知天,其实就是张载所诠释的“皆以其德和阴阳,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但是,作为一种人生追求,孟子的这一超越上达之路却并不具有人伦生活的普遍性,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的士君子。比如构成孟子现实人生抉择的大体小体之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无疑具有人伦普遍性,但却并不具有人生实践追求的普遍性。就是说,虽然为大人,也不能无小体;虽然为小人,也不能无大体。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够从其大体出发。对于人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同选择,孟子明确指出: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411,1411,1411页。
大体小体人人同具。虽然孟子希望人们“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但他并不能保证人人都必然会“从其大体”。从大体小体之辨出发,又经过“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层层区别,以指向知性知天,最后的结果可能只是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52页。。这样看来,所谓缺乏现实生活中的人伦普遍性,也就成为孟子知性知天之超越追求的最大不足了。
孟子思想的这一不足,正好为庄子所弥补。正像孟子对人之精神世界的撑开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理论一样,庄子对于人之自然天性的守护也不是为了弥补孟子思想在人伦普遍性上的不足,而主要或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困惑。已如前述,庄子对于人生的最大感受,就是其所谓的“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因而其最强烈的希冀,就是如何能够彻底扭转这种不断受到戕害的现实,从而全性葆真、以尽其天年。但是,作为现实而又必然“有待”的人生,人如何能够从“有待”走向“无待”、从“与物相刃相靡”的状态走向完全不受戕害、从而洒脱自在的人生呢?从孔子“困于陈蔡”的经历中,庄子发现“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这说明“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但是,只要坚持“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就必须像意怠一样完全退守于鸟兽之道。鸟兽虽然能够“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但它们能够免除伤害吗?所以也就必须继续退处。在《山木》中,庄子又发现,无论是不会鸣的雁还是成材的树,都无法免除被杀或被清理的命运,这就必须使自己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不断地退处,而每一次退处,都可以使自己处于更大的群落之中,从而也就减小了被伤害的可能。但是,无论其怎样退处,都只是对伤害的一种减少,却无法从根本上免除伤害,这就像“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逍遥游》,第13页。一样,于是这才有了作为古之真人生存之道的“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人生境界,从而也就有了“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之彻底“物化”的向往。因为在庄子看来,只要能够彻底“物化”以“齐同”于“物”,才能成为对人生伤害、扭曲的彻底摆脱。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这里每一次的“退处”,对其人而言,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隐藏”;而每一次的“退处”,不仅会使自己处于更大的群落之间,而且使自己的生存获得了更大的普遍性。当其最后达到“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时,也就使自己彻底“物化”了,从而也就彻底“齐同”于“物”了。到了这个层面,固然可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存在普遍性,但同时是其作为“人”以及其人生之一种完全彻底的“物化”。就庄子的“物化”及其“齐物”追求而言,他当然不是为了获得所谓存在的普遍性才“隐藏”于世并“齐同”于“物”的,但这种“退处”与“隐藏”以及其“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的追求,同时成为对其存在之普遍性的不断拓展;每一次的“退处”,从“人”到“鸟兽”、又从“草木”到“瓦石”,也都使其生存——存在之普遍性获得一种指数级的上升与拓展趋势。作为儒道两家的二代巨擘,孟子与庄子的不同追求究竟是一种有意地“对着干”还是一种无意为之的自然走向呢?
四、结语:人伦文明的双向支撑
在上述分析中,孟、庄以其人伦与自然、德性与天性的不同追求,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走向。但是,当我们怀着一种人文重建的心理来重新审视孟、庄的思想创造时,他们的不同追求又恰恰表现出了我们的人文关怀之两种不同的侧重以及人伦文明或人伦世界的两个极点,从而也就构成了对于人伦文明的双向支撑。
所谓人文关怀是从儒家的角度取义,站在儒家立场上来品评从根本上源于道家的庄子思想能够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鉴。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这就是所谓儒道互补;但从今天之人文重建的角度看,则又可以说是在儒道融合基础上的相互支撑与推陈出新。
已如前述,如果以个体为本位,孟子固然也承认人都具有大体和小体;但如果以社会为本位,则孟子不仅有“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54,1354页。的主张,甚至还明确指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54,1354页。
这说明,从个体之生存所需(小体)到治国理政的制民之产,孟子都思考到了;就连庄子所念念守护的“天性”,也首先是出自孟子的概括。但孟子思想的基本指向,既不是仅仅满足于个体之小体所需,也不仅仅停留于“制民之产”——所谓发展产业的层面,而是为了让天下人都能够有士君子之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思想才显现出了其难以取代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天性”一说固然是出自孟子的揭示和概括,但对人之自然天性的尊重与守护,毕竟是庄子思想的核心。即如前边屡屡征引的“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以及“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中,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够对人、对动物之天性的关注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就向中外历史上所有关注人之自然生命(当然也包括动物)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关于人的思想根本不尊重人的自然天性,那么其关于人生的设想与论说如果不是陷于必然的失败,也就必然要以对人之天性的扭曲和戕害为代价。如果说儒家本来就是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那么这种人文主义也就必然要建立在充分尊重人之自然天性的基础上。
这种尊重人之自然天性的主张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就儒学作为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而言,其所有的教化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人之天性的基础上,或者说起码不能建立在违逆人之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也就充分显现出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04页。的重大意义,或者说起码应当坚持子贡所诠释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269页。的原则。因为对人之自然天性的尊重是所有人伦教化包括所谓思想宣传活动的底线,也是儒家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底线保证。至于《中庸》所谓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以及“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礼记·中庸》,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564,564页。,同样建立在这一底线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所谓思想教化与宣传才能真正跨越人己物我的界限,从而真正达到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475页。的境地。
其次,作为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儒家并不仅仅满足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包含着对整个世界的人与万物关系的重新梳理与安排。这就是子思所谓的“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564,564页。。这当然是就人类最高目的而言。我们这里且不说“与天地参”的问题,但儒家万物一体之仁的关怀及其精神指向则是应当贯彻始终的,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吴哲楣主编:《十三经》,第1353页。到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完全可以说是一根而发而又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王阳明《大学问》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来含括儒家对于人己物我关系的理解与疏通: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968页。
所谓万物一体之仁就是以儒家的仁爱情怀来润泽万物、观照天地。这里也存在一个基本底线:人类固然可以通过动物驯化的方式来服牛乘马,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服狮乘虎,更无法训练食肉动物使其一律食素,这就存在着动物天性的限制,存在着尊重动物天性的问题。所以,由尊重人之天性进而尊重动物的天性,也是儒家万物一体之仁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中国思想史中一直就有所谓儒道互补一说。那么,儒道两家究竟从哪些方面实现其互补呢?这就是道家天性与儒家德性的互补。一方面,儒家的道德理想固然代表着对人伦文明、人类秩序的开拓与设计,包括人对超越的知性知天之追求与向往;另一方面,道家以其对人与动物之自然天性的关怀与尊重,从而为儒家的人伦文明提供了一种底线的保证。对中国文化而言,如果说儒家的道德理性代表着人伦文明所以前进、发展的方向与动力,那么,道家以其对自然天性的关怀与尊重,不仅承担着儒家人伦文明之底线的作用,而且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人文精神的一种根本保证。所谓儒道互补,就体现在儒道两家德性与天性的相互支撑与相互促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