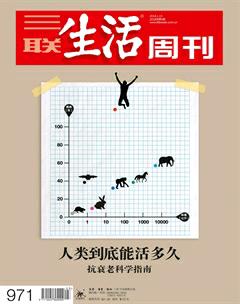测量衰老
袁越
任何一种自然现象,如果你无法测量它,那你就无法研究它,衰老自然不会例外。事实上,衰老的测量本身就是最好的研究方式,只有先搞清楚如何测量衰老,才能弄清衰老的本质。
測不出的年龄
假如你是一名边境警察,有一天你抓到了一个非法移民。按照你国法律,如果他年龄不满18岁的话可以申请避难,否则就要递解出境,可他身上没有搜出任何能够证明年龄的文件,你会怎么办呢?
你很可能会求助于科学家。如今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我们已经能够从一个人的血液和DNA判断出他的民族成分、身体状况、饮食习惯甚至工作性质等等很多细节,像年龄这样的基本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吧?
可惜你错了,年龄还真的不好猜。目前有一部分国家的移民局采用的是智齿法,即通过X光扫描判断智齿的发育情况,以此来推断年龄。但是,新的研究表明,智齿的发育速度并不均衡,速度快的15岁便发育完成了,速度慢的则可能拖到25岁,依靠这个方法来判断年龄非常不可靠。
还有一部分国家是依靠骨龄来判断年龄的,但研究发现这个方法同样存在误差,一个15岁的少年很可能已经具备了成年人的骨骼形态,但也有人直到25岁后骨骼才发育完成,如果仅仅依靠骨龄法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年满18岁的话,最多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判断失误。
还有什么更准确的办法吗?很遗憾地告诉你,没有了。
你可能会感到迷惑,为什么年龄这么简单的事情居然这么难测呢?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年龄会给人以一种很容易测的感觉呢?答案很可能和树的年轮有关。这是个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测年法,估计每个小学自然课的老师都教过。与此类似的还有贝壳测年法,只要数一数贝壳上的花纹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它的年龄了。
这两个例子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这两种生物的生长速度都和季节更替有很强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就是靠天吃饭,只有这样才会在身体上留下关于岁月的印迹;二是这两种生物的身体都是坚硬的固体,这才能把生长速度的变化永久地保留下来。这两个特征在人类身上是不存在的,一来人类是高等动物,我们的生活状态早就和季节没有太大关系了,完全取决于自身,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二来人类的身体是活的,每时每刻都在更新,任何印迹都很难永久地保留下来,所以说人的年龄是很难测量的,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
这里所说的年龄指的是时间年龄(Chronological Age),也可称之为绝对年龄,真正的科学家其实并不关心绝对年龄,毕竟大部分人都有身份证。他们关心的是生物年龄(Biological Age),可以近似地将其理解为衰老的程度。如果生物年龄能被及时准确地测出来,那么长寿和衰老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先说长寿。长寿药为什么研究不出来?最大的原因就是科研人员等不起。你想,如果你的目标是开发长寿药,那么按照现有的新药审批制度,你必须找到很多志愿者,起码从中年开始就让他们吃你的药,然后一直等到他们去世为止,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种药和对照组相比到底有没有效。这种临床试验没人做得起,起码在目前的新药研发架构中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再说衰老。抗衰老药物研发同样存在因终点不明确导致时间过长的问题,像上一篇文章提到的那个二甲双胍TAME试验就至少需要等5年才能看到结果,而且还是一个间接结果。要知道,目前绝大部分新药的临床试验都是在3个月内完成的,像这种需要持续5年以上的临床试验几乎是不可能的。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发明出一种可以随时测量,准确度又相当高的生物年龄测量法,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想开发一种抗衰老药吗?只要找人来试吃一下,三个月后再测一下生物年龄,和对照组一比,就能知道这个药管不管用了。
各位读者千万别小看这些方法论上的细节,很多看上去没那么难的问题,最终都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实验方法而成为难解之谜。事实上,美国FDA之所以始终不认为衰老是一种病,个中原因与其说是科学层面的不认同,不如说是技术层面的不现实。你想,如果始终找不到测量衰老的有效方法,那就不可能按照现有的新药审批原则和标准来批准任何抗衰老药物。也就是说,除非FDA修改现有的新药审批框架,否则没有任何一种抗衰老药能够通过审批。美国FDA不傻,不可能去做这样一件注定将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于是,抗衰老研究领域有不少研究者的主攻方向就是如何测量衰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医院里已经有一套测量老年人衰老程度的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测量步频、握力和起立速度等等。这套方法测的只是运动系统虚弱程度,但人的衰老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虚弱”这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再加上这几项指标的精确度都不高,只能作为参考,无法用于临床试验。
还有一些准确度较高的生化指标也可以用来测量衰老程度,比如血压、血糖、静态耗氧量和胆固醇水平等等,但这些指标也仅仅反映了循环系统和新陈代谢机能的衰老程度,仍然很不全面。
于是,很多人想到了DNA,似乎只有DNA这个生命的总指挥官才有可能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年龄到底有多大。
看似完美的端粒理论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要从法国医生艾里克西斯·卡莱尔(Alexis Carrel)讲起,他发明了血管缝合术,使得器官移植成为可能。因为这项伟大的发明,他获得了191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获奖之后,卡莱尔的兴趣转移到体外细胞培养上来。他很想知道在试管里培养的脊椎动物体细胞到底能活多久,于是他从1912年开始培养小鸡的成纤维细胞,不但定时更换营养液,而且还要按时移除多余的细胞。这个实验一直做到1944年他去世为止,此后他的助手又接着做了两年,直到1946年才停止,时间跨度早已超过了一只鸡的正常寿命。在这34年的时间里,这群细胞一直在不停地分裂繁殖,似乎永远不会停歇。于是后人得出结论说,每一个脊椎动物的体细胞单独拿出来都是可以永生的,衰老是发生在更高层面的事情。
这期间也有很多人试图重复这个实验,但都失败了。不过他们本能地怀疑自己的实验操作技术不好,或者营养液配方有问题,毕竟卡莱尔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太可能出错。
60年代初期,一个名叫伦纳德·海佛烈克(Leonard Hayflick)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家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他在实验室里培养的人体细胞过一段时间就会停止分裂,无论怎么处理都不行。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海佛烈克没有迷信权威,而是亲自设计了一系列精巧的实验,证明卡莱尔的实验结果有可能是误差导致的(比如营养液里混入了新鲜细胞),甚至干脆就是造假,他的那套细胞永生理论是不正确的,正常的脊椎动物体细胞存在分裂上限,后人将这个上限命名为海佛烈克极限(Hayflick Limit)。
后续实验证明,不同脊椎动物的海佛烈克极限都不一样,人体细胞的上限大约为40~60代,再也多不了了。这个计数是从受精卵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如果从年轻人身上取出来的细胞,在培养皿里活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相反,从老年人身体里取出来的细胞就会死得更早,仿佛细胞内部有一个生命时钟,从一生下来就开始不停地走,直到大限将至。
这个发现让研究衰老的学者们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此前的假设完全错了,衰老并不是高级层面的事情,而是从细胞本身就开始了。于是大家迅速调转了方向,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细胞上,一场发现生命时钟的竞赛开始了。
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的澳大利亚生物学家,她发现海佛烈克极限存在的原因是染色体上的一个叫作端粒(Telomere)的东西。原来,DNA分子的复制需要用到DNA合成酶,这种酶有个致命的缺点,使得染色体无法百分百地被复制到下一代,而是每次都会剩下那么一小段复制不了。这样一来,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丢失一部分信息,长此以往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大自然进化出了这个名叫端粒的东西,解决了这个难题。
虽然名字里有个“粒”字,其实这玩意儿就是位于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DNA而已。但这段DNA基本上就是一大堆重复序列,不携带任何信息,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成为DNA合成酶的“抓手”,每次复制时丢掉的那一小段DNA都是从端粒里丢出去的,这样就不会影响有用信息的传递了。
经常有人将染色体比作鞋带,将端粒比作鞋带一端的那个坚硬的带扣,这个比喻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大体意思是对的。带扣存在的目的就是保护鞋带,一旦带扣松了,鞋带也就散了。同理,端粒的价值就是保护染色体,一旦端粒没了,染色体也就散架了。两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带扣只要小心使用一般是不会坏的,但端粒的损伤却无法避免。染色体每复制一次,端粒的长度一定会缩短一点点,直到用完为止。此时细胞就到达了海佛烈克极限,再也无法继续分裂了,因为下一次分裂一定会丢失一部分有用信息,导致细胞死亡。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干细胞是如何无限制地分裂下去的呢?这个问题同样是被布莱克本博士解决的,她发现了端粒酶(Telomerase),能够把缺失的端粒补齐。负责编码这种酶的基因是人类基因组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细胞里都有一份拷贝,但是正常情况下人类体细胞中的端粒基因不会被表达,因此也就不会有端粒酶。只有受精卵和干细胞的端粒酶基因才是活跃的,因此也只有这两类细胞的端粒能够被及时地修复,保证它们可以一直分裂下去。
端粒和端粒酶的发现再一次震惊了衰老研究领域,大家都被这个简单而又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迷住了,一致认为衰老的秘密即将大白于天下。很快,一大批研究结果出来了,端粒和衰老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清晰。比如,细胞的寿命和端粒长度几乎成正比,如果通过转基因方式培育出端粒较短的小鼠,那么它的寿命也会很短。再比如,端粒的缩短会诱发癌症、心血管系统疾病、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症等很多老年病,甚至一个人年轻时受到的心灵创伤,易怒的性格,以及过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等等,都会导致端粒长度缩短,从而缩短此人的寿命。还有,适当的体育锻炼会增加端粒的长度,从而延长寿命……
这一系列发现让人激动不已,端粒迅速成为长寿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吸引了大批科学家的关注。大家相信端粒长度可以成为测量衰老程度的绝佳指标,从此一个人的真实年龄就可以很容易地测出来了。200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如期颁给了呼声最高的布莱克本和另外两位对端粒研究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从此广大老百姓也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大家都期盼着科学家们能够发明出激活端粒酶的办法,似乎只要这件事能成功,人类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可惜的是,大家都高兴得太早了。激活端粒酶确实可以让细胞长生不老,但却会诱发癌症,得不偿失。事实上,正常细胞之所以会发生癌变,就是因为这些细胞发生了基因变异,激活了原本一直沉睡着的端粒酶,从而让自己具备了无限分裂的能力。
另外,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端粒长度和年龄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起来,反面的案例越来越多。比如小鼠最多只能活三年,但小鼠细胞的端粒远比人类的要长。再比如,父亲年纪越大,生下来的孩子端粒就越长。这两件事很难用端粒理论加以解释,说明这个理论肯定有哪里不对。
这次我采访了十几位衰老领域的研究者,没有一个人还在研究端粒,甚至没有一个人主动提到“端粒”这个词,端粒研究由盛转衰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就连他们也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的追问下,大家一致认为端粒理论虽然听上去简单优美,但毛病恰恰就出在“简单”二字上。衰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每个组织或者器官的衰老程序都不一样,不能期望用一个简单的端粒理论来解释一切。
最终的答案,似乎还得从DNA分子携带的信息中去寻找。
大数据抗衰老
我从洛杉矶出发一路向南,两个小时后就来到了圣地亚哥(San Diego)。这是美国西部的第三大城市,和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特区一起并称为美国四大生物技术基地。我的这次“人类长寿探秘之旅”的第三站就设在这里,我要访问的是一家名为“人类长寿”(Human Longevity Inc.)的公司,我很想知道这家公司到底有何本事,竟然敢取这么大胆的名字。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克雷格·温特(Creig Venter)。他当年单枪匹马挑战全世界,最终和美国政府主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战成平手,双方在同一时间共同颁布了第一个人类全基因组序列。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当年只有温特坚信“散弹枪测序法”(Shotgun Sequencing)要比当时流行的传统基因测序法更加优秀。其实这个散弹枪法需要计算机技术的强力支持,当年的电脑发展水平尚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温特很有远见,他预见到了电脑技术日后的飞速发展,等到美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如今的基因组测序用的全都是散弹枪法,传统测序法已经被淘汰了,所以那场战斗其实是温特赢了。
这件事很能说明温特的性格特征,那就是胆大、自信和果断。
一战成名之后,温特又做了一件轰动世界的事。他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条DNA长链,将其导入去除了基因的细菌内,把后者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实验虽然必须依靠现成的细菌作为受体才能完成,但温特坚称这就是人造生命,因为他相信生命最本质的特征是信息,而信息全部是由DNA分子所携带的,因此只要DNA是人造的,那么整个生命也就相当于是人造的。
完成这件壮举之后,他成立了这家“人类长寿”公司,试图把他在DNA测序方面积累的经验应用于人类健康领域。或者套用一句俗语,他打算“知识变现”。我联系了很长时间,终于获得了这次宝贵的采访机会。
这家公司的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周围清一色玻璃大楼,里面驻扎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高新技术公司,干什么的都有。采访被安排在午饭时间,地点就在温特的办公室,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你来这儿之前采访过其他什么人吗?是否已经和奥布雷·德格雷(Aubrey de Grey)和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见过面?”这是温特见到我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采访过巴克研究所和南加大老年学院,但没采访过你说的这两个人。”我如实回答。
“哦,那就好。”温特面无表情地回答,“这个行业里有很多疯子,说过很多漂亮话,但那些话都是骗人的,不要信。”
温特所说的德格雷是一位长寿狂人,他认为能够活到1000岁的人已经出生了。而这个库兹韦尔是《奇点临近》一书的作者,他认为脑机接口技术即将实现,人类将以这个方式获得永生。
“将来永远不会出现一种神奇的药能让人永生,所有这么宣传的人都是为了骗钱。如果你想永生,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温特接着说道,“死亡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可避免的事,但衰老不是,所以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延缓衰老,增加人类的健康寿命。”
我这次采访到的所有科学家都是这么说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各不相同,因为大家对于导致衰老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温特相信衰老是因为DNA复制差错越积越多,以及修复差错的能力越来越低,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人体细胞里的DNA每时每刻都在复制,出错是难免的,再加上很多环境因素也会导致DNA发生突变,比如一个人只要去海滩上晒会儿太阳,皮肤细胞就会发生4万个基因突变。”温特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的DNA复制系统会修正一部分基因突变,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清除剩下的突变细胞,问题不大,可一旦修复的速度赶不上突变的速度,衰老就出现了。”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检测公司可以帮助用户检测自己的基因突变,但他们用的大都是芯片法,测的是已知的若干个常见突变位点。而且芯片法本身有技术缺陷,会出现很多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不是很可靠。作为基因测序领域当之无愧的老大,温特决定干脆测全基因组序列,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准确的数据。
“用我们的方法,平均每个人可以找出8000个独特的基因突变。”温特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对我介绍说,“然后我们会把基因数据和这个人的生理数据进行对比,从中寻找规律,发现问题。”
温特所说的生理数据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体检。但是,作为一个凡事都要做到极致的人,温特所说的体检可不是简单的测测血压量量血糖那么简单,而是包括了上百种生理指标的测量,以及全身核磁共振成像扫描(MRI)这样高精尖的技术。后者相当昂贵,一般普通门诊是不会提供的,想做的话只有到温特这里来,当然价格也会很高。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5万个客户,这就相当于收集了5万个病例,已经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了。”温特说,“当然这还很不够,我的目标是积累100万个病例,这样分析起来才会更准确。”
温特的思路其实和市面上其他几家高端健康咨询公司差不多,那就是通过基因测序找出每个人独有的基因特征,再通过体检了解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最后把这两套数据合在一起进行对比,从中找出规律。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相关性(而非因果性)研究,大数据分析是这类研究的命脉。数据量越大,得出的结论就越可靠。“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收集到的这5万个数据判断出一个人的年龄了,误差在10%以内。”温特说,“如此大规模的研究以前都是要有政府资金支持才能完成的,我们现在全凭向顾客收费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基因检测公司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一边提供健康咨询服务一边收集顾客的基因数据,然后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寻找规律,以便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这是个典型的正反馈模式,前途是很光明的,但这个模式要想运转起来,前期一定要想办法获得客户的信任。温特选择的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的模式,服务对象也定位于高收入群体,对于前期的要求就更高了,这种模式也只有像温特这样在行业里有良好口碑的人才能玩得起。
“别看我们公司的名字里有‘长寿这个词,但我们不是一家专门研究衰老的公司。我们是一家实用性很强的公司,我们的目标就是治病,并通过治病来延长寿命。”温特对我说,“如今50~74岁的美国男性当中,有40%的人活不到74岁。女性的这个比例是20%,但也太高了。这些人不是死于衰老,而是死于各种疾病。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DNA测序和体检,判断出一个人最大的危险来自哪里,然后给出建议,帮助他预防可能出现的疾病。要知道,如今50岁以上的人当中有2.5%的人体内已经有了足以致死的癌细胞,如果我们能预先发现它们的踪迹,将其杀死在摇篮里,就能挽救这些人的生命。”
温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改变医学的面貌。在他看来,传统的医学本质上就是数据辅助下的临床科学,但他相信未来的医学将是临床辅助下的数据科学。他要通过大数据来预防疾病,抗击衰老,让人活得更加健康。
甲基化生物钟
温特没有详细解释这家公司是如何通过基因分析来判断年龄的,但从他的描述可以大致猜出他们的思路,那就是把每个人的基因突变模式和这个人的实际年龄输入电脑,借助计算机的力量寻找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然后总结成规律。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大数据应用场景,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物统计学研究者都是这么做的,这其中就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遗传系教授史蒂夫·霍瓦茨(Steve Horvath)。他因为发现了DNA甲基化生物钟而成为近期衰老研究领域炙手可热的人物,我专程去洛杉矶采访了他。
霍瓦茨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对长寿问题很感兴趣,于是他在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去哈佛大学拿了个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然后凭借这个学位在UCLA遗传学系找到了一份工作,研究方向是疾病的遗传标记物。这项研究其实和温特所做的事情是类似的,都是试图从海量的基因突变中寻找和某种疾病有关联的标记,然后就可以反过来用基因突变预测疾病了。他尝试过癌症、心血管疾病、自闭症和老年痴呆等几乎所有的常见病,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特别显著的成就。
2006年他决定放弃单个疾病的研究,专攻衰老。“我越来越相信单个疾病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衰老的程度,比如糖尿病确实是一种老年病,但很多其他因素也能导致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只是衰老的一种表象而已。”霍瓦茨对我说,“我相信每个细胞内的DNA分子上都会有一个普适的衰老时钟,控制着这个细胞的衰老过程,这才是衰老的本质所在。”
霍瓦茨和他手下的一名研究生一起把收集到的大量基因突变和年龄数据输入电脑,从中寻找蛛丝马迹,结果却一无所获,甚至差点让这位学生毕不了业。经过这番挫折,霍瓦茨得出结论,即使年龄和基因突变有关联,肯定也是非常微弱的关联,很容易淹没在海量的基因数据之中。
2011年,霍瓦茨决定试试DNA甲基化(Methylation)。众所周知,DNA是由ATGC这四种核苷酸首尾相连组成的长链,这四个字母的排列顺序决定了不同基因之间的差别。但后人发现DNA分子上会有一些核苷酸被连上了一个甲基,这就是甲基化。通常情况下这个甲基会出现在CG位点上,即一个字母C后面紧跟着一个字母G的那个位置。人类基因组中大约有2800万个这样的位点,它们都是潜在的甲基化位点。常用的甲基化测量法只能测出其中的几万到几十万个位点,但这也已经大大超出了普通人的研究能力。
经过一番考量,霍瓦茨决定只选取其中的几个和年龄关系似乎比较密切的位点,测出它们甲基化的比例,然后再看这个比例和年龄到底有何关系。比如他从某个组织或器官上取出100个细胞,先测A位点,有35个被甲基化了,65个没有,那就把A位点记为0.35,然后再测B位点,得出一个比例数值,依次类推。然后他把这些比例数值合在一起,再和年龄相比较,看看能否找出两者的关联。
这里面的年龄数值可以用受试者采样时的实际年龄,但这个显然是有误差的,因为一个人的实际年龄很可能和他的生理年龄不符。幸好UCLA在90年代时曾经做过一个大型的跟踪式健康调查,抽取了很多志愿者的血样,并一直保留在冷库里。霍瓦茨想办法拿到了这批血样,测出了这些人当年的甲基化比例,然后再和这些人今天的健康状态相对比,以此来校正他们当年的生理年龄。
最终霍瓦茨推导出了一个公式,只要把测出的甲基化比例带入这个公式,就可以算出这个人的实际年龄,两者的相关性高达96%以上。“其实这个公式很容易推导,因为两者的相关性实在是太强了。”霍瓦茨对我说,“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过各种疾病的基因标记,每一个研究起来都非常困难。衰老这件事本身看似极为复杂,但它的基因信号却是最强的,因为衰老是普世的,任何人都会经历这一步。”
霍瓦茨将这个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兴冲冲地投给了《基因组生物学》(Genome Biology)杂志,没想到却被编辑退稿了,理由是这个数据实在是太完美了,肯定哪里不对!
平心而论,这位编辑的怀疑不无道理。要知道,此前关于基因和年龄的相关性研究已经有很多了,得出的结论远不如霍瓦茨的漂亮。比如当年端粒研究还很热,可最终算下来端粒长度和年龄之间的相关性还不到50%,霍瓦茨的这个96%实在是太刺眼了。
不过,这封退稿信却把霍瓦茨惹怒了。他一口氣灌了三瓶啤酒,然后借着酒劲给编辑写了一封质问信,并毫不犹豫地点了发送键。没想到这封信居然起了作用,这篇论文终于发表在2013年10月号的《基因组生物学》上。霍瓦茨在论文中公布了他推导出来的算法,于是很多实验室纷纷用自己的数据对这套算法进行了验证,结果好得出奇,其中一家来自荷兰的实验室得出的相关性竟然高达99.7%!
从此霍瓦茨就出名了,他发明的这个甲基化生物钟也名声大噪。理论上这个算法所使用的甲基化位点越多,最终结果应该就越准确,但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平衡的结果是霍瓦茨决定采用353个位点,测一次的成本大致为300美元左右,以此推测出的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别能够控制在两年以内,某些情况下甚至更高。不过霍瓦茨认为这个精度还是不够高,尚不能用于临床试验。
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已经用这个方法测量了很多次,得出的结论大都和已知的衰老研究相吻合。比如肥胖的人测出来的年龄往往要比实际年龄大,正在尝试饥饿疗法的人测出来的年龄往往要比实际年龄小。
“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估算不同组织和器官的衰老程度,比如我们发现小脑的衰老速度往往比较慢,说明这个部位非常重要。”霍瓦茨对我说,“女性的乳腺组织则往往要比身体的其他组织老那么几岁,很可能这就是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之所以那么高的原因。”
说到癌细胞,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癌细胞比正常组织老很多,比如有的白血病病人的血液测出来的年龄可以高达200多岁。但也有一些癌细胞会显得更年轻,目前还不知道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点很有趣,那就是所有干细胞测出来的年龄几乎都是零,这说明人工诱导干细胞就相当于生命的重启。”霍瓦茨说,“这个结果很好理解,因为决定一个细胞状态的不是基因组本身,而是基因的甲基化。”
不知各位读者想过没有,我们身体内的细胞有千千万万,每个细胞的基因组序列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细胞会分化成好多种不同的类型呢?答案就是每个基因的活跃程度有差异。这个差异是由DNA的甲基化控制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DNA分子的不同修饰方式控制的。研究DNA修饰方式的学问叫作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这是最近20多年来遗传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霍瓦茨的甲基化生物钟就是这门新学问所结出无数个丰硕成果中的一个。
“我按照我的这个公式反过来推算了一下,发现120岁并不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年份。起码从理论上说,我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活过120岁。”霍瓦茨说,“当然了,我相信即使一个人非常严格地控制自己的饮食起居,什么事情都做得绝对完美,也不可能永远活下去,但我相信未来的人类能够通过药物干涉或者其他方法活到200岁。这方面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山中伸弥发现的人工诱导干细胞方法证明,理论上我们可以让已分化细胞返回到干细胞状态,因此人类是可以重返青春的。只不过山中伸弥的方法太极端了,也许将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较为温和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
甲基化和基因突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甲基化理论上是可以逆转的。基因突变是DNA分子本身的变化,修正起来极为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基因疗法如此困难的原因。但甲基化只是DNA分子的外部修饰,可以通过酶反应将其逆转。目前这个领域尚处于研究阶段,但这个思路听上去很有前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结语
采访结束前,霍瓦茨主动说起了他自己的一個小心得:“我的计算表明,衰老过程不是从40岁才开始的,而是从人刚一生下来就开始了。事实上我认为衰老和发育是同一个过程,两者受同一个甲基化程序所控制。”
霍瓦茨的这个想法让我立刻想起了衰老的测量方式。其实测量衰老是人类的本能,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都会本能地会去猜他的年龄。在他20岁之前,我们其实是通过他的发育程度来猜年龄的,但当他30岁以后,我们的依据就变成了衰老。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育和衰老还真的可以统一起来。
“照你这么说,衰老就是基因控制得了?因为发育肯定是基因控制的生理过程。”我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发育和衰老都是依靠甲基化来完成的,而整个甲基化过程都是在基因控制下才能实现的。”霍瓦茨回答,“不过我不敢肯定衰老是基因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大自然没有理由进化出衰老这个功能,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衰老是发育的一个副产品。任何人都需要发育,否则你就没法长大成人,没法繁殖后代了。但当你结婚生子,完成了繁殖任务后,这个过程却仍然在继续,可惜结果却正相反,从发育变成了衰老。这就好比一架飞机的引擎,起飞的时候当然需要它,但如果一直转个不停,最终飞机一定会失去控制而撞到山上。”
最后这个比喻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再一想,难道飞行员看到前面的山后不会转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