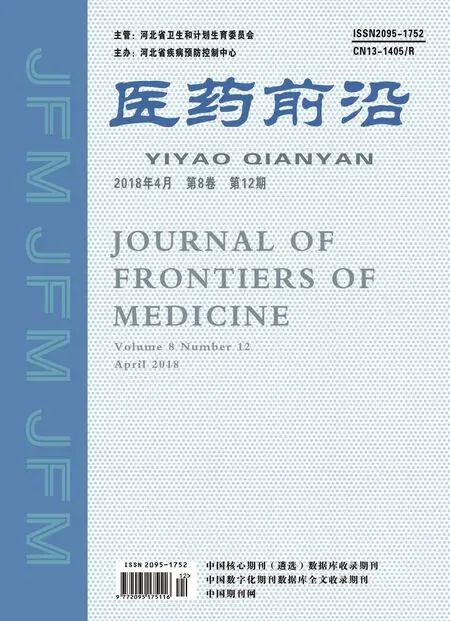颅咽管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1贵州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 贵州 贵阳550004)
(2贵州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贵州 贵阳550002)
颅咽管瘤(craniopharyngioma∶CP)是胚胎时期残存的颅咽管上皮细胞发生的肿瘤,属先天性上皮肿瘤,常位于鞍区,发病率约1.7~2/1000000人[1]。目前手术治疗仍是CP首选的治疗方式,但鞍区结构复杂,手术难度大,术后并发症多。现对我科2012年9月至2017年12月之间收治的36例CP患者的治疗情况,分析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男25例,女11例;平均年龄31.0岁(范围:6~62岁);入院时高颅压表现29例,视力下降、视野缺损24例,其中双侧视力下降19例,单侧视力下降5例;下丘脑-垂体功能障碍12例。
1.2 影像学资料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颅脑CT、MR平扫和增强扫描,必要时完善头颈部动脉CT血管成像(CTA),需选择经蝶手术入路的患者,行颅底CT薄层扫描;通过以上检查初步判断肿瘤的特点与毗邻结构的关系,其中瘤体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楚21例、分界不清15例,视神经受累11例,颈动脉系统受累7例,垂体柄受累4例,下丘脑受累2例。囊性12例、实性5例、混合性19例,钙化13例,合并幕上脑积水9例。肿瘤主体位于鞍上33例(其中中上斜坡1例,松果体区1例),主体位于鞍内3例;而肿瘤体积以近似椭圆形进行计算,(A×B×C)/2,其中A,B,C是指在3个方向上瘤体的最大直径。肿瘤体积范围:0.9~90.0cm3,平均体积,19.8cm3,最大肿瘤直径约6.0cm×5.0cm×6.0cm,最小肿瘤直径 1.20×1.00×1.50cm。
1.3 评估标准
(1)患者功能状态的评估:采用Karnofsky(KPS百分法)功能状态评分标准。
(2)肿瘤切除程度的评估:通过术中显微镜下所见并结合术前、术后患者颅脑MRI的图像进行体积对比分析,评估肿瘤切除的程度。全切除:术中显微镜下见瘤体或囊壁全部切除,术后MRI提示无瘤体残留;次全切除:术中显微镜下见残留少量粘连的瘤体或囊壁,术后MRI提示肿瘤切除体积在95%以上,影像学可见极小瘤体或囊壁;大部切除:术中显微镜下见残留较多瘤体或囊壁、术后MRI提示肿瘤切除体积在60%~95%,可见明显的瘤体或囊壁。
1.4 手术方法
手术方式的选择主要依据肿瘤的大小、位置及生长方式决定。33例采用骨瓣开颅入路,其中经翼点入路12例、前纵裂入路8例,冠状切口经额下入路7例,胼胝体-穹窿间入路6例。3例采用神经内镜辅助下经鼻-蝶入路。翼点入路,以翼点为中心做菱形骨瓣,切口可根据暴露需要向中线、颞后部适当延长。常规入颅后应仔细分离视交叉、视束与颈内动脉之间的间隙,并充分利用这些生理间隙对肿瘤行分块切除。额下-前纵裂入路,骨瓣尽量靠近前颅窝底,入颅后沿前纵裂牵开额叶内侧面,暴露肿瘤,谨慎处理肿瘤表面血管和正常穿支血管后分块切除。胼胝体-穹窿间入路,以右额做马蹄形切口,骨瓣内侧显露矢状窦边缘,沿双侧外耳道连线垂直分离,在室间孔上方纵形切开穹窿,到达第三脑室,暴露肿瘤后分块切除。经蝶手术入路,常规处理双侧鼻腔后,置入神经内镜。切开右侧鼻中隔带蒂黏膜保留,寻找蝶窦开口,沿双侧蝶窦开口磨除鼻中隔后部、蝶窦前壁骨质,打开并消毒蝶窦腔,暴露鞍底。确认中线后磨除鞍底骨质暴露硬膜,烧灼鞍底硬膜并放射形切开,利用解剖间隙分块切除肿瘤。术后采用明胶海绵、人工脑膜,自体阔筋膜、带蒂鼻中隔黏膜,分层覆盖并应用纤维蛋白胶黏合修补颅底。
2.结果
2.1 手术切除结果
肿瘤全切24例,次全切除6例,大部切除6例,对大部分切除患者术后4例行直线加速器放射治疗,1例行伽马刀治疗,1例未行任何治疗。
2.2 术后并发症
术后电解质紊乱31例,其中高钠血症21例,低钠血症6例,高钠、低钠血症交替出现4例,出院时仍存在高钠血症2例、低钠血症1例;尿崩症21例,出院时仍需药物治疗7例;垂体功能低下26例,其中甲状腺功能减退20例,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8例,性腺功能减退2例,均予以相应激素替代治疗。癫痫发作7例,其中1例死于癫痫持续状态,其余患者癫痫症状在出院前均控制,出院后规律口服丙戊酸钠抗癫痫治疗;脑脊液鼻漏并颅内感染1例,予以行腰大池置管引流,手术修补漏口,抗感染等治疗后,好转出院;运动性失语3例,多为短暂性,出院前明显改善;肢体偏瘫4例,予以康复理疗,出院前肢体肌力有所好转,但均未恢复到术前水平;继发性动眼神经麻痹2例;术后术区血肿形成2例,其中并发脑疝形成1例(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后好转出院),家属拒绝手术并死亡1例。中枢性低血压、高热3例,1例死与中枢性低血压并循环功能衰竭。术后1个月内视力下降9例,视力改善1例,26例视力无明显变化。2例病情危重,因经济原因,家属拒绝治疗签字出院。
2.3 随访结果
采用电话随访或门诊随访。随访33例,随访时间5~60月,平均30.5月,随访期间肿瘤复发5例,复发时间在1~5年之间,平均3.3年,其中2例复发并重度梗阻性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2例行伽马刀治疗后再次行开颅手术治疗,效果均较满意。随访期间患者功能状态评分,能维持日常正常活动(90~100分)19例,生活基本能自理(60~80分)11例,生活不能自理(小于60分)1例,死亡(0分)2例,平均80.30分。
3.讨论
3.1 术前评估与手术方案的选择
术前肿瘤的位置、大小、生长方式及与周围结构之间的关系,是选择不同手术入路主要的影响因素。只有术前充分明确瘤体与下丘脑、视神经、垂体柄及重要穿支血管的关系,才能有效的保护其结构完整,避免不必要的损伤。而术前手术方案的制定往往还与手术医生对该疾病的整体认识、局部解剖结构及不同手术入路的熟悉、理解程度有关。为了提高对术区周围解剖结构的认识,促进不同手术方案的选择、提高手术效果及推进手术经验的交流,不少神经外科医师对肿瘤进行了分型,其中应用较广的是Hoffman、Yasargil、Samii对其进行的分型,分型依据多以瘤体位置与所累及部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划分。与大多数分型不同的是国内漆松涛等人依据肿瘤的起源部位与周围膜性结构对其进行的分型,即QST分型法,认为:“可将CP分为颅外Q型肿瘤、蛛网膜下的S型肿瘤和部分卷入第三脑室底内的T型肿瘤,并无脑实质起源的第三脑室内型CP,并认为所有CP均从起源点由下向上生长”[2]。但事实上这些分型真正在临床应用时往往不能依据某一分型一蹴而就,多需综合考虑,详细通过影像学表现研究肿瘤与下丘脑、垂体柄、视神经等重要结构之间的关系,结合不同手术入路的优势、弊端,最终决定是选择何种手术入路,是否需联合其他手术入路似乎更为合理。
本研究中仅以简单的鞍内及鞍上对肿瘤进行分类统计,在手术入路选择时,多基于影像学表现结合相应手术入路,以术中充分暴露瘤体,缩短手术路径,在尽可能全切除的基础上,减少不必要的损伤为基本原则进行综合评估后选择[3]。对于瘤体位于鞍旁、鞍上并偏于一侧时多该入路。该入路应用普遍,大多数神经外科手术医生对该入路局部解剖较熟悉,术中视野暴露充分,镜下同侧结构显示清楚,牵拉小。但对对侧、视交叉靠后、三脑室及体积较大的肿瘤切除困难[4]。对瘤体位于鞍上中线、视交叉、第三脑室前部的肿瘤常选该入路。术中可较好的显露双侧大脑前动脉A1、A2段、垂体柄及下丘脑等结构,可在直视下仔细分离。但术中存在额窦的开放可能增加颅内感染、脑脊液漏的风险。由于路径及操作时间较长可能会对额叶及嗅神经造成不同程度的牵拉和损伤[5-6]。对瘤体完全或大部分位于第三脑室时多选该入路。到达第三脑室近,沿胚胎发育间隙逐层分离对大脑皮层及神经纤维的损伤相对较小。但因手术路经较长,操作空间较小,术中可能损伤下丘脑、穹窿,术后发生脑炎、脑积水可能性大[7]。对瘤体位于鞍内常选该入路。创伤小、无需开颅、术后并发症少。但对手术器械要求高,操作复杂,手术医生学习周期长,脑脊液漏发生率高。尽管目前关于采用该手术入路切除鞍上CP的不少报道,但与开颅入路切除鞍上CP的疗效仍待进一步确定[8]。
3.2 术中操作要点
导致术中肿瘤全切困难和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原因常与术中肿瘤暴露不补充,瘤体、瘤周钙化,重要结构受粘连、侵蚀等有关。且任何手术入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术野盲区,而术前难以通过影像学完全进行准确判断。为了有利于术中肿瘤的充分暴露,开颅时颞部骨瓣应尽可能靠近前颅、中颅窝底,额部骨瓣尽可能低,暴露前颅窝底。采用释放脑脊液,过度换气、快速甘露醇静滴、腰大池置管引流等方式缓慢降低颅内压力,扩大手术视野,减少对脑组织的牵拉、损伤。下丘脑的核团包括视交叉上方的视上部,漏斗后方的结节部;乳头体的乳头部,下丘脑还构成了第三脑室的下壁及前外侧壁,当肿瘤临近或累及上述结构时,术中应谨慎处理,若术前或术中发现下丘脑结构受累明显时,不应盲目追求肿瘤全切除,应限制性切除后行放射治疗,避免发生严重的下丘脑损伤增加患者围手术期及远期死亡风险[9]。另外下丘脑与肿瘤血流供应是不同的,前者由大脑前动脉、前交通动脉、脉络前动脉发出的分支供应,后者多由大脑动脉环发出的穿支供应,术中应进行判断,尽可能保持下丘脑穿支血管的完整。同时应避免使用双极电凝在临近下丘脑区域进行止血,电凝止血仅用于瘤体表面的出血[10]。垂体柄是保证正常神经内分泌激素运输极为重要的结构。术中对垂体准确的辨认是有效保护的前提,正常垂体柄呈橘黄或橘红色,从视交叉后缘通过鞍隔孔与垂体后叶连接,因CP常位于垂体柄前方,导致正常垂体柄形态、位置发生改变。术前应根据影像学仔细寻找并指导术中对垂体柄的辨认,当辨认困难时可借助垂体上动脉及垂体柄表面静脉髓纹进行寻找确认。若术中发现肿瘤与垂体柄粘连严重,剥离困难或垂体柄明显受侵袭时,可离断垂体柄,原则上应从远端离断[11]。因研究表明[12],远端离断后的垂体柄可出现神经血管重建,功能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 另外对肿瘤切除时无论是实性还是囊性肿瘤,都应从瘤内开始分块切除,首先降低瘤内压力,为分离瘤壁提供操作空间,大多数肿瘤与正常组织之间存在完整的模型结构,术中沿蛛网膜平面缓慢剥离瘤壁可安全切除。而过早切除囊壁,可能导致断裂的囊壁碎片缩向深部,而造成肿瘤残留。
】
[1]Aldahmani K, Mohammad S, Imran F,et al. Sellar Masses: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J]. Canadian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Sciences Le Journal Canadien Des Sciences Neurologiques,2015, 43(2): 291-297. DOI:10.1017/cjn.2015.301.
[2]漆松涛,潘军,包贇等.颅咽管瘤的QST分型特点和手术治疗[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17,33(11):1088-1093.DOI:10.3760/cma.j.issn.1001-2346.2017.11.003.
[3]Prieto R, Pascual J M. Accurate craniopharyngioma topography for patient outcome improvement[J]. World Neurosurgery, 2014, 82(3-4):e555-e559. DOI:10.1016/j.wneu.2014.06.026.
[4]毕建华,王小峰,齐春晓,等.鞍上及鞍内颅咽管瘤经翼点入路和额底入路手术疗效的研究[J].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17,(2):120-125.DOI:10.3969/j.issn.1672-7770.2017.02.010.
[5]倪洪早,范月超,陈晨,等.经额下纵裂入路显微手术切除颅咽管瘤的研究[J].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16,13(1):9-12.DOI:10.3969/j.issn.1672-7770.2016.01.003.
[6]李伟,王增武,秦时强,等.经额底纵裂终板入路手术切除侵犯第三脑室肿瘤[J].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17(9):646-647.DOI:10.13798/j.issn.1009-153X.2017.09.012.
[7]程荆,江普查,曹长军,等.颅咽管瘤显微手术的疗效分析[J].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16,21(1):1-3.DOI:10.13798/j.issn.1009-153X.2016.01.001.
[8]Jeswani S, Nuño M, Wu A,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utcomes following craniotomy and expanded endoscopic endonasal transsphenoidal resection of craniopharyngioma and related tumors: a single-institution study[J].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2016, 124(3):627.DOI:10.3171/2015.3.JNS142254.
[9]Müller H L. Diagnosis, treatment, clinical course, and prognosis of childhood-onset craniopharyngioma patients.[J].Minerva Endocrinologica, 2017.42(4):356-375 DOI:10.23736/S0391-1977.17.02615-3.
[10]石祥恩, 周忠清, 吴斌, 等.颅咽管瘤切除术与下丘脑功能保护(附1182例报告)[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17,(11):1107-1112.DOI:10.3760/cma.j.issn.10012346.2017.11.007.
[11]李爱军,兰青,王道奎,等.经颅鞍区肿瘤切除术中垂体柄的辨认与保护[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13,29(11):1160-1163.DOI:10.3760/emaj.issn.1001-2346.2013.11.028.
[12]Herkenham M,Lynn A B,Johnson M R,et al.Character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annabinoid receptors in rat brain: a quantitative in vitro autoradiographic study[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1991, 11(2):56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