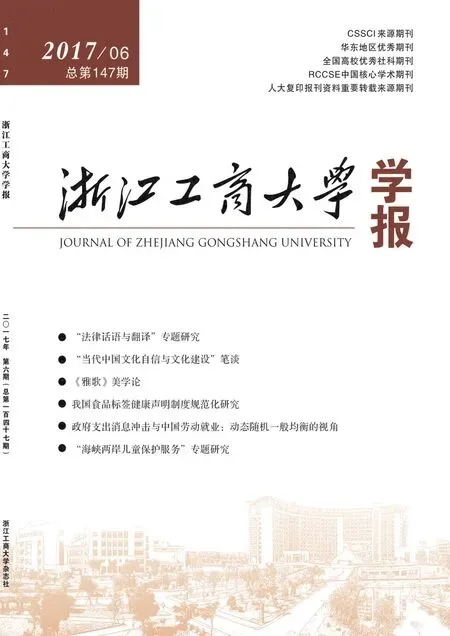“危险”的性意识:对福利院残疾儿童性教育的反思
钱霖亮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一、 引 言
2005年4月中旬,一则有关福利院的爆炸性新闻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根据媒体的报道,江苏省南通市福利院将其院内收养的两名十多岁的智障少女送到当地医院实施了摘除子宫的手术。事件曝光后,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以月经给这两名残疾少女带来病痛为由为绝育手术辩护,并声称他们曾经尝试教这些女孩如何处理月经但失败了。在考虑到女孩的利益(摆脱痛经困扰并消除遭遇性侵犯而怀孕的风险)和保育人员的工作压力后,该院领导决定让她们绝育。实施手术医院的医务人员认为这种做法不人道,于是在网上曝光了这个事件,众多媒体随后跟进。此后,福利院的相关责任人和进行手术的医生被送上了法庭[1]。
已有学者曾经从残疾人权益保护[2]、儿童权益保护[3]和人权[4]等不同的角度讨论这一事件。社会学家潘璐和叶敬忠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福利院工作人员和医生剥夺智障少女再生育权利的行为实际上揭示了相当多中国人对残疾人在性、婚姻和生育等方面权利的漠视。[5]尽管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当笔者在2011年对浙江省一家福利院进行田野调查时重新阅读这则新闻,却产生了一丝疑问。这个事件确实可能反映了不少国人对残疾女性涉及性方面的偏见,但是公众对残疾男性的性又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两者是否一样呢?鉴于中国福利院官方规定的收养年龄是16岁以下的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乃至更广大的公众对那些年龄更小的残疾人的性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将机构养育残疾儿童的性以及保育人员对此的看法作为福利院儿童日常生活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所处的机构环境和在此环境下他们的生存状态。文章意图回答下列三个研究问题:(1)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如何看待和处理残疾儿童的性问题,包括他们的性意识和性行为?(2)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看待和处理残疾儿童性问题的方式如何影响儿童的日常生活?(3)残疾儿童自己如何思考和感知性与性别问题,又是如何表达自身需求的?
在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尽管没有遇到像南通福利院那种戏剧化的事件,笔者通过对福利院儿童日常生活的参与观察和对保育员的正式及非正式访谈获得了不少关于院中残疾儿童(尤其是青少年)涉及性意识和行为的材料。这些素材显示了保育员(全都是女性)通常从生物医学(bio-medical)的角度来理解残疾儿童的生理及心理特征。她们认为性意识(sexual consciousness)是一个人发育成熟的标志,因而只有当儿童长大成人后才会具备。考虑到笔者调查的福利院中大部分的儿童都有疾病和残疾症状,保育员们认定这些孩子会受其病症影响而处于发育滞后的状态,这种状态进而推迟乃至限制孩子性意识的形成,使他们(至少暂时)成为了“无性”(asexual)或者“性方面不成熟”(sexually immature)的个体。但与此同时,她们却又经常在这些孩子身上发现许多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性意味的行为。这一发现使得保育员们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她们乐于看到孩子们形成中的性意识,因为这说明他们的成长发育还在继续,并且有可能最终长成为一个“正常人”。但另一方面,她们担心这些的孩子在具备性意识后会做出出格的事,因为他们的“发育滞后”使他们缺乏判断能力,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除此之外,她们也认为智力残疾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正常”的性意识和行为的产生,比如同性恋和娘娘腔。考虑到这些风险,保育员们在养育实践中更倾向于管理和惩罚那些表现出性意识和行为的儿童,而不是给予他们性教育,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引导。但如下文将要呈现的,这些严厉的管制措施非但没有扼杀残疾儿童的性意识和感知,反而促使他们发展出一些策略性的手段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本项研究希望能够对多个学术领域贡献新的经验素材和比较视野。首先,通过提供一个关于中国福利院保育人员对待和处理残疾儿童性问题的民族志个案,笔者意图丰富残疾研究(Disability Studies)领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揭示不同社会和文化场景中人们对残疾人性生活的想像的相似性。迄今为止,对残疾人性生活和观念的个案积累仍旧集中于西方社会,中文研究寥寥可数。例如以“残疾人性生活”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标准检索,所得文献仅有三篇。以“残疾人性观念”“残疾人性意识”和“残疾人性行为”搜索,所得结果皆为零。以“残疾人的性”这样泛化的关键词进行搜索,所得文献也不过15篇,算得上学术论文的更少,且没有一篇涉及福利机构救济的残疾人群。从现存的研究文献数量和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提供的见解来看,残疾人的性生活远未成为公众和学术界关注的议题。而其不受关注的原因,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常常认为残疾人不会像正常人那样具有性需求,也根本没有行使性功能的能力”[6]。此外,有学者认为残疾人的性生活、婚姻和生育问题是人们容易感到尴尬的话题,因而多倾向于避而不谈[7]。此项研究以实际的田野观察素材反驳了上述大众偏见,证实了残疾人同样具有性意识和性需求。但与此同时,中国福利院中的残疾儿童和青少年与西方的残疾人一样仍就被其照顾者和公众视为“无性人”或“在性上不成熟的人”[8]。就像文章中的保育员,西方社会许多非残疾的人(包括不少照顾人)在处理残疾人的性问题时往往也采取过分保护的措施,限制那些被假定为“性单纯”(sexually innocent)的残疾人接触性信息[9];或者是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惩罚表现出性意识和行为的残疾人[10]。基于实证研究的跨文化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把对残疾人的性歧视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全球性议题来理解,而非一个想像中的全球性问题或仅仅是区域的、特殊文化的问题。
其次,笔者希望能够对中国的残疾人研究和儿童研究分别作出新的贡献。中国的残疾人研究有着深厚的积累,但已有的研究集中于讨论国家的残疾政策、残疾人的社会融入和排斥、职业地位等方面,较少涉及性生活[5,11]。在儿童研究领域,不少学者从性教育和性虐待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儿童的性问题[12-13],但却基本没有涉及残疾儿童。在此意义上,笔者的研究实际上处于这两个领域的交叉地带,将性(sexuality)的变量引入中国的残疾人研究,也将残疾的变量引入中国儿童性意识和行为的研究。尤其针对后一领域,尽管不论残疾与否,儿童在中国社会都被认为是“性单纯”的群体,因其脆弱而易受伤害;但与健全儿童不同的是,残疾儿童在一部分照顾者和公众的眼中因为他们的“发育滞后”而被认为其性意识的形成也会滞后,其产生的性意识由于受到生理缺陷的影响使之成为无法自控的危险人物。残疾与性的汇集使得这群孩子成为了儿童群体中的异类,他们的生理损伤令他们的身份受到污名化[14],他们的性又令他们成为有可能挑战社会禁忌、造成道德恐慌的“不正常的人”[15]。这些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偏见和歧视对这群孩子的日常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笔者的研究即是通过戈夫曼式的对普通人与污名者日常互动的观察来审视福柯所谓的“危险”的“不正常人”的社会生产机制及其后果。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儿童性行为的控制和教育,即上述生产“危险”的“不正常人”的机制,本身可视为福柯所谓的广义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一部分,体现了权力如何透过知识生产对人进行管理的艺术。福柯本人曾经大篇幅地讨论过18世纪欧洲反对儿童手淫的社会运动。按照当时的社会观念,儿童的手淫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乃至死亡,会对儿童自身、家庭、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生存造成威胁。于是社会精英开始透过医学知识对家庭和教育机构当中的儿童性教育和管理进行干涉,这便开启了儿童性行为医学化、病理化的历史进程[15]261-289。西方社会残疾人的性行为同样也经历了上述过程。因为健全的社会精英对残疾人性行为有不适感,他们甚少在针对后者的性教育中考虑如何满足其性需求,而更多思考如何通过医学和其他手段进行有效的控制[16]。在众多控制儿童和残疾人性行为的方式中,很重要的一项手段便是以生物医学的名义对这些群体的性进行污名化,由此构成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技术[17]。本项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福利院的场景中,保育人员同样对残疾儿童的性意识和行为有不适感,并利用生物医学的知识来合理化她们对后者严厉地管制——在这些不适感和管制措施背后除了宏观的社会观念(比如福柯和残疾研究学者所指出的主流社会对儿童、残疾人的性歧视)之外,还有微观的个体利益和意识,包括下文所述保育员们对自身和其他儿童安全的考虑,以及儿童性行为对其工作可能造成问题的担忧。就此,这一个案除了希望能够填补中国语境中关于残疾人在性生活方面的研究缺憾以及中外残疾人在此方面的跨文化比较之外,也希望对福柯的治理术与生命政治理论作一些补充:当我们讨论治理技术的运作逻辑时,我们不仅应当关注宏观的权力机制,也需留意个体权力施展者微观的动机,一项治理项目的开展往往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福利院的场景中,保育人员对残疾儿童性意识和行为的管制,既包含了中国社会健全的“正常人”支持的主流观念,也牵涉到她们作为儿童照顾者和管理者的权力和利益。把握这多层次的权力运作逻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福利院残疾儿童的生存状态,以便为后续可能的国家政策调整和社工介入提供学术支持。
二、 研究方法和地点
本项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是浙江省的永江福利院(化名),该院成立于1992年初。根据院内职工的说法,1990年代该院收养的绝大部分儿童都是健康的女婴,她们中的大多数最后被国内和国外家庭领养。大约从2002年开始,越来越多进入福利院的弃婴儿身患疾病或残疾。在笔者调查期间(2011年3-8月),登记在案的儿童约有80人,其中50人在机构内养育,30人寄养在农村家庭。所有这些孩子中70%为3岁以下的婴幼儿,95%的孩子在官方医学记录里被认定为“病残儿童”。2011年3月的一份全院儿童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80个孩子中,39人患有脑瘫或者唐氏综合症,9人患有唇腭裂,2人有先天性心脏病,5人为肢体残疾,另有22人患有其他类型的疾病和残疾,完全健康的只有3人。严重的疾病状况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孩子被永江本地家庭领养的概率,因为本地人通常只想要完全健康的婴儿。国外家庭有可能会领养轻度乃至中度残疾的孩子,但重度残疾(比如智力残疾和严重的肢体残疾)的儿童也不被接受。因此,迄今为止留在福利院中的十几岁的青少年和大龄青年都是智力残疾者和严重肢体残疾者。这里有必要提一句,尽管在一些国际和国内官方医学鉴定的标准中脑瘫不属于智力残疾的范畴,但永江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和很多来访者都将脑瘫和唐氏综合症一并视为智障(就笔者所知在其他一些福利院也有类似情况)。工作人员将这些残疾的青少年和大龄青年分成两队,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留在院内帮助保育员照顾更小的孩子,其他的则送到农村家庭寄养。在笔者调查期间,有9名这样的孩子留在院内(6个男孩,2个女孩),另外还有1名女孩因为被寄养家庭认为“乱性”而退回院里。由于这些孩子在保育员眼里都有性意识的征兆,他们构成了研究的儿童对象群体。
作为一项主要考察照顾者对待残疾儿童性问题态度的研究,永江福利院的6名保育员构成了研究的照顾者对象群体。这些女性都出生在本地农村,年龄介于32到55岁之间,都已生育自己的子女。事实上,性别和育儿经验是福利院在招聘保育员时考虑的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入职之后,新任的保育员会接受一些职业培训,包括如何抚养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但所有这些培训的内容完全不涉及儿童的性问题。截至笔者调查期间,所有在任的保育员都已在岗5年以上,最长的有10多年,她们对其照顾孩子的性格和习惯都相当了解。通过对保育员们的正式与非正式访谈,以及对她们和孩子们日常互动的观察,笔者意图探究她们对残疾儿童性问题的看法,以及在具体的照顾实践中如何回应那些表现出性意识和行为的儿童。
笔者经过永江福利院的院长批准,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该院进行为期半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机构资料文献方面,主管的院领导也给予了笔者很大的便利。但在田野调查期间,许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更倾向于把笔者视为一名男保育员,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本人都和其他保育员一起在照顾孩子。与保育员和孩子的互动建立起笔者与他们的深厚友谊。在随后几年的数次回访中,不少大龄儿童还能记得笔者。保育员们最初并不怎么信任研究者,她们怀疑笔者是院领导派来监督她们工作的人。但是随着相处的日子渐久,她们知道笔者并不是,而且还减轻了她们的工作负担,因此改变了对本人的态度。随着友谊渐深,她们也愿意同笔者分享育儿经验和对儿童性格习惯的观察,在照顾儿童时也不再忌讳做出一些她们不太愿意让外人看到的行为,譬如体罚。体罚是中国父母常见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之一[18],但在福利院中,类似的行为更容易被旁观者视为虐待儿童[19-20]。按照保育员们自己的说法,她们体罚孩子的动机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孩子好,让他们今后不再犯错。而笔者的参与观察则发现,尽管她们会采用体罚措施,但有很多可能引发亲生父母体罚孩子的事由,譬如小孩打架、调皮、挑食,都不在保育员体罚福利院儿童的犯错名单里。对她们来说,这些不过是一些小事。比如方阿姨就认为,两个小孩打架,过了一会又成好朋友了,大人根本不需要为此费神;如果为这种小事就体罚孩子,不仅孩子受气,保育员们自己也要生气,而经常生气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不利。按照这种思路,保育员们发展出了自身的体罚策略,那就是“抓大放小”,而这里的“大事”主要是那些她们认为有可能造成恶劣后果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残疾青少年表现出性意识和行为。本篇文章的主旨即试图回答为什么保育员们会以如此严肃的态度对待残疾儿童的性问题。
除了保育员的观点,笔者也试图探寻福利院儿童自身就其性问题的看法。但鉴于这些残疾青少年(更不用说更小的孩子)有限的语言能力以及研究者自身对残疾人的交流方式有限的涉猎,笔者最终无法像对待平常人一样对他们进行正式的访谈。尽管如此,在许多不同的场合笔者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使用了一些字眼,而这些字眼是非残疾的普通人经常会拿来表达性感觉或性需求的。除此之外,笔者和保育员也时常能够观察到他们在公开场合做出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非残疾的普通人眼里是具有性意味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参与观察仅限于公开场合,并不试图窥探残疾儿童的隐私,尽管他们的性问题在福利院中已经公共化了)。在这里,如果我们假设残疾儿童仍旧能和非残疾的普通人一样思考和学习的话(这是残疾研究学者的一个基本学术立场),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他们使用的字眼和表达的行为看作是他们自身思考性问题和学习性知识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推论残疾儿童与非残疾人可以共享一些表达性感觉和需求的方式,而这些方式揭示了残疾儿童在性问题上具备一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21]。据此推论,笔者在下文中将把残疾儿童的语言和行为表达作为正式访谈的替代信息来展示他们自身的观点。
三、 残疾儿童性意识的征兆和保育人员的困惑
笔者第一次意识到残疾儿童性问题的争议性是在2011年4月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清清(16岁男孩,唐氏综合症患者)在浴室里洗澡,保育员方阿姨正好路过,发现浴室门开着,小萍(7岁女孩,先天性癫痫症患者)站在门口往里面看。方阿姨走上前去,结果发现清清一丝不挂地在跳舞给小萍看。阿姨非常生气,把小萍拽出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骂她,“一个女孩子看男人洗澡,不要脸”,然后又说她“和清清这种智障的人一样傻”。小萍大哭。其他保育员就过来劝方阿姨,说小萍还小,不懂性这些东西,但方阿姨仍然不解气。等清清穿好衣服,她把他也拽过来打了一顿,边打边骂,还给正在休假的主管清清的朱阿姨打电话控诉。结果第二天朱阿姨来上班时又把清清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朱阿姨和其他保育员解释说清清平时在性方面还是很保守的,不穿内裤都不敢出浴室,生怕被别人看到,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表现得那么奇怪。然而当笔者问朱阿姨清清是否有性意识时,她却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我也不确定……我觉得孩子一般要长大成人了才会有性意识。像清清这样的青少年,正好处在快要成年的阶段,所以也有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性意识……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性的东西到底懂多少。他一生下来就有唐氏综合症,这种病会影响人的智商。一般来说智力不好的人会比平常人发育慢一点,所以性意识的形成也会慢一点,也有可能永远没有性意识。”
说完这话,朱阿姨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前后矛盾,因为她刚刚提到清清不穿内裤不敢出浴室是因为他在性方面比较保守,这意味着他是有性意识的。朱阿姨同样也对清清在小萍面前跳裸舞这个事件感到困惑。她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清清有性意识,他这么做是为了吸引异性;另一种则是他完全没有性意识,根本不知道在异性面前跳裸舞意味着什么。方阿姨也有同样的困惑,她不知道小萍是已经有了性意识,因而对异性的身体产生了兴趣;抑或是她完全不了解看异性洗澡意味着什么。
这次事件之后,笔者发现保育员们对残疾儿童的此类行为都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虽然很多时候她们倾向于认为这些行为具有性意味,但并不确定残疾儿童做出这些行为是否受到他们性意识的驱使。按她们的理解,残疾儿童由于其残疾应该不具备性意识,或要在很久之后才会产生。另一个表明这种理解思路的例子发生在国威(10岁男孩,脑瘫患者)身上。有一次笔者和保育员们都看到他亲了洋洋(3岁女孩,唇腭裂患者)的嘴,笔者就问保育员国威是不是有性意识了。有的保育员不置可否,但朱阿姨和张阿姨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们认为国威是从电视剧里学会了这个动作,把它复制到自己的行为上,因而纯粹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模仿。尽管如此,当朱阿姨看到国威这个动作时,她迅速地把他拉开了,并且警告他不准再亲洋洋。对朱阿姨来说,不论国威的动作是否受到他的性意识驱使,这种动作本身是被禁止的。在她和其他保育员看来,亲吻不仅是与儿童年龄不符因而需要被限制的行为,它本身还具有危险性。为了防止危险,她们尽其所能地不唤起儿童们的性意识,比如说每当她们在讲成人话题时,一旦有孩子靠近,她们就会立即停止。即便如此,她们想像中的危险还在酝酿,因为残疾儿童在性方面的天性与普通人一样不可避免。
四、 残疾男孩性意识的公开和保育人员的惩罚
尽管最初还有所怀疑,经过几次事件后保育员们开始确信清清是有性意识的,而且认为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引起她们担忧的事例又是由方阿姨曝光的。有一天下午她正好去洗衣房取洗好的尿布,发现清清在里面脱小梅(7岁女孩,脑瘫患者)的裤子。看到这一幕,方阿姨震惊了,她立刻拉着清清去见其他保育员。在其他保育员责骂清清的同时,方阿姨又把他打了一顿,并且警告他如果再脱女孩的裤子或者光着身子给女孩看,就把他阉了。同时她对其他保育员说,这次如果不是她恰好撞见,小梅恐怕已经被清清强暴了,那样她们作为工作人员的麻烦就大了。其他保育员感到奇怪的是清清从哪里学来这种行为的。张阿姨忽然想起她曾经看到福利院的中年男门卫在保卫室里看黄片,而且还经常播放20世纪90年代那种画面里有穿泳装女性的唱片。因为不少福利院的男孩子会去保卫室玩,张阿姨怀疑他们是从那里获取了性信息。后来保育员们还派代表去跟门卫商量,让他不要再让福利院儿童看到这些东西。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清清看上去变得“老实”多了,没有表现出任何在保育员看来带有性意味的举动。但是很快李阿姨说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她说自己和朱阿姨,以及方阿姨和张阿姨值班的时候,清清会很老实。可是当吴阿姨和毛阿姨值班时,因为她们经常会走开(回宿舍拿东西或者到外面接电话),清清就会趁机骚扰女孩子。李阿姨发现这个秘密是因为有一次她下班后回福利院拿东西,吴阿姨和毛阿姨正巧都不在,她在楼底下就听到依兰(16岁女孩,脑瘫患者)在楼上大叫,阿姨上去一看发现清清正追着依兰跑,手里抓着她已经被扯下一半的衣服。李阿姨在讲述这个事件时气愤地说:“你是没看到那个场面,太可怕了!依兰一边躲一边大叫着哭,清清拉着她的衣服在后面追。如果我当时不出现,估计依兰就被他强奸了!……你看,这个男孩子其实很聪明,他知道怎么把握机会。但是他也很傻,傻在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不知道自己做这种事情会有什么后果。这种青春期的男孩子最危险了。那次以后我特别提醒吴阿姨和毛阿姨值班的时候不要随便离岗,而且要特别盯着清清。如果我们不盯着他,他肯定还会再犯。他犯事不用承担什么责任,最终倒霉的还是我们保育员!”
当笔者问李阿姨为什么她觉得清清肯定会再犯,她回答说:“因为他是智障,脑子不好。正常智力的小孩,你教过几次之后他就知道这种行为是错的,会懂得自律。但是智障的小孩他教不会,根本不懂。或者他可能懂一些,但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只能靠我们来管了。”
智力残疾儿童要么没有性意识,要么性意识不健全,这是保育员们普遍的看法,而这种状况被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他们的残疾导致的。保育员们不仅对这类情况较为严重的性意识表现严正以待,对那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儿童举止也格外关注,因为它们有可能就是潜在的危险信号。比如朱阿姨发现军军(15岁男孩,唐氏综合症患者)看到电视里的亲吻画面时会用手遮住眼睛。正如其他学者曾经讨论过大众传媒对儿童性意识和行为塑造的影响[22],保育员们相信残疾儿童的性信息主要来源就是电视节目。朱阿姨此前认为残疾儿童的亲吻动作只是一种模仿行为,但军军的表现令她开始觉得这些孩子也可能明白亲吻的含义。她说:“我以前觉得残疾小孩肯定不懂这些,但是当我看到军军这么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儿子和其他亲戚的小孩也曾经这么做,这是一种害羞的表现。所以残疾小孩也知道亲嘴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尽管如此,朱阿姨接下来的理解却走去了不同方向:“我觉得残疾小孩能够理解亲嘴和其他一些带有性意味的行为的含义,有性意识,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他们的身体和心理还在发育,说不定有一天能变得跟正常人一样。但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大,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已经滞后了,尤其是那些智障的小孩。他们的智力水平导致他们对亲嘴和其他带有性意味的行为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比如说正常的小孩只亲他最爱的人,但是福利院里的残疾小孩,你也看到了,什么人都亲,男孩子还亲男孩子。他们不懂爱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律。”
正是残疾儿童对性“不全面”的理解令保育员们倍感焦虑。对她们而言,宁愿让小孩不知道这些行为也比让他们一知半解的好,因为后者只会造成“不正常”和“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保育员们开始习惯于看到电视中播放有性意味的情节就立即换台。但是有部分孩子已经习得了节目中的用语和动作,与军军关系非常亲密的小瑜(12岁女孩,脑瘫患者)就是其中一个。小瑜有相当不错的语言能力,说话内容也常常出人意料。有好几次笔者听到她叫军军“老公”,让他亲她的嘴,或者抱住她。尽管军军的语言能力要差很多,但不久之后他也学会了这个套路,让“老婆”小瑜亲他抱他。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大白天躺在一张床上,用被子蒙住身体,外人看不出他们在里面干什么。每当保育员看到这个场景,她们都会阻止并对两个孩子进行惩罚,警告他们不能亲嘴、抱在一起和躺在一张床上。但在阿姨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两个孩子会一切照旧。担心小瑜最终会以怀孕收场,福利院将她送到农村去家庭寄养。在小瑜走后,笔者观察到军军一度情绪非常低落,并常常问笔者小瑜去哪里了。
相比于作为潜在威胁的清清和军军,林波(16岁男孩,脑瘫患者)已经成为福利院里公开的危险人物。他被认为在20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强迫依兰和他发生了性关系。第二天早上依兰用不流利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告诉保育员她的私处很痛,保育员发现她的生殖器官有明显的损伤。当被问及是谁造成的损伤时,依兰指向了坐在不远处的林波。负责照顾依兰的张阿姨认为尽管她是脑瘫患者,但懂得的事情很多。与此同时,她的表达也非常清晰明确,因而认定林波性侵犯了依兰。虽然林波自己不承认,保育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报给院领导,领导决定另外给林波安排住处。在讲诉这个事件时,张阿姨说还好依兰没有怀孕,不然这个事情都不知该如何解决了。她认为林波的行为是受其性意识驱使的,在有性意识这点上他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问题在于他的残疾导致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无法意识到这样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个事件同时也给保育员自身的人身安全敲响了警钟。看着身边的男孩越长越大,有的个子甚至比她们还高,保育员们开始担心这些男孩既然敢对女孩们虎视眈眈,保不定也会对她们下手。张阿姨坦言,让林波搬出去不仅考虑女孩们的安全,也是为了她们自己。出于同样理由,在笔者调查期间保育员们也在考虑让清清和军军搬走。
五、 残疾男孩性心理的污名化
除了会延迟和限制性意识的产生,保育员们认为残疾(尤其是智力残疾)还会扭曲福利院儿童的性别观念和角色。她们给笔者举了几个“不正常”性别观念的例子,其中包括同性恋和娘娘腔,认为这些都是大脑损伤导致的精神疾病。*在中国,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鉴于智力残疾对这些保育员来说也意味着“脑子有问题”,她们就把这两者混在了一起。小伟(15岁男孩,脑瘫患者)的例子就经常被她们拿来论证智力残疾和同性恋之间的因果关系。小伟跟小兵(8岁男孩,视力残疾)的关系很好,甚至会经常抱起后者来亲。当他看到其他人抱小兵或者亲他时,小伟就会非常生气地去打那个人。保育员认为小伟这么做是出于嫉妒。还有一次,她们深夜起床给婴儿喂奶时发现小伟坐在清清身上,并亲吻熟睡的清清。这些例子使得保育员们深信小伟已经有了性意识,但却因为脑瘫走错了方向。
15岁的小华(唐氏综合症患者)被认为是另一个“性别观念扭曲”的孩子。小华经常会在自己房间里身披一张床单,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保育员认为他的动作就像是在唱戏,唱的时候还会翘起兰花指。按照她们的看法,只有女人和太监才会翘兰花指。作为一名生理上的男性,小华在行为上的女性化令保育员们侧目,后者将他男性气概的缺失归咎于他的智力残疾。也有保育员认为这和他爱看的电视剧有关,尤其是《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包含了许多传统戏剧元素的电视剧在中国热播多年,几乎每年暑假都会在电视上重映。剧中女主角就身着纱衣,唱台词时总会翘起兰花指,甚至它的男主角都是由一名女演员扮演的。考虑到小华特别爱看这部电视剧,尤其痴迷于剧中两名女主角,她们的名字也经常会在他自己的表演中出现,保育员们认为他在模仿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性别角色。尽管有这个外在因素的影响,智力残疾仍被认为是造成他性别观念扭曲的决定性因素。吴阿姨是负责照顾小华的保育员,她是这么说的:“我也不知道小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娘娘腔,但是已经这样好多年了。有的阿姨说他是受电视剧的影响,尤其是《新白娘子传奇》,我有点怀疑。许多小孩,包括我们自己都喜欢看这个电视剧,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性别观念上变得跟他一样不正常?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他的智障。”
听了吴阿姨的话,笔者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智力残疾会扭曲残疾儿童的性别观念,那么为什么其他智力残疾的孩子,比如清清和军军,没有出现类似小华的行为。吴阿姨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觉得这可能跟智力残疾儿童大脑的构造有关,大脑不同部分的功能失效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智力残疾。比如说脑瘫就有很多种类型,有的人因为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导致了身体活动的困难,有的人因为语言神经中枢受损导致说话沟通困难。我觉得小华的情况可能是主管他性意识的那部分大脑构造出了问题,具体那个部分叫什么,你就要问医生了。”
通过将小华的女性化表演和男性气概的缺失病理化(pathologized),吴阿姨在智力残疾与她想像中“扭曲”的性别观念之间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她甚至会用看似“科学”的医学语言来阐述这种联系。以貌似客观中立的医学话语来对社会越轨行为(social deviance)进行污名化已经成为了文化正统主义者惯用的手法[23]。福柯在论述围绕性的权力运作时就曾发现个体性行为在成为公共议题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医学化的科学问题,它伴随着公共权力的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塑造出新的社会控制机制[24]。在永江福利院的场景中,包括吴阿姨在内的保育员在收集到一些孩子不太符合正统行为规范的表现后就将他们标签成在性别观念和角色上“不正常”的人,并进而用实际上她们自己也未必精通的医学话语使这种不正常性本质化(比如吴阿姨就无法确切说明究竟是哪一部分大脑构造的损伤导致了小华的行为),将它归咎于不可逆转的生理残疾。在这里,“病态”的性别观念加剧了已有的残疾造成的社会偏见,使得这部分儿童蒙受着双重污名。不过这一双重污名也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由于保育员本身对脑科学、神经科学等现代医学,以及同性恋、娘娘腔这类社会文化现象缺乏深度的了解,只将后者理解为残疾症状,而残疾本身是不可逆转的,那就意味着这些症状也是不可治愈的。这使得她们没有像一些中西方父母一样寻求医学机构的帮助对这些儿童进行改造。在日常的照料实践中,虽然她们将同性间的亲密接触和女性化的举止视为“不正常”并加以训斥和阻止,但总体上并不像对上文中那些在性方面具有攻击性的男孩那样严厉。按她们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这些孩子“脑子已经坏了,改不过来了”。而根据笔者的观察,这也是因为这些男孩不会在性方面对福利院女孩和她们自身造成直接威胁的缘故。
六、 残疾女孩的性意识及其处理方式
机构养育的女孩通常都被认为在性方面很单纯脆弱,比如文章中的小梅和依兰;所以像小瑜这样在性方面看起来比较开放的女孩会让人感到特别。如果我们接受保育员们的判断,认定小瑜的行为具有性意味,那么像她这样善于表达自身需求和感受的女孩有可能更进一步地成为了男孩们的性启蒙者,教会了他们和异性亲吻、拥抱和睡在一起。这个例子或许可以证明残疾少女/女性在性问题上具有能动性,并且在性活动中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非只是被动的受害者。这对于残疾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欣喜的发现,但对保育员们来说则未必。她们对残疾女孩性意识的理解有两极化的倾向。在一个极端,尽管她们同样会惩罚表露出性意识和行为的女孩,但惩罚力度一般来说会比男孩轻。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接受生物学的观点,认为女性一般比男性更早熟,即便是残疾,残疾女孩也会比残疾男孩更早熟。她们因此更容易接受一个具有性意识的残疾女孩。二是女性仍旧被认为在性关系里处于被动的角色,她们或许会主动,但却不会有攻击性(在小瑜的例子中,她是叫军军亲她,而非她去亲军军),因而危险程度较低。但在另一个极端,一旦残疾女孩在性方面表现出攻击性,保育员们也决不会容忍。
16岁的小丹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据说她原本按医学鉴定属于中度智障,但是因为在行为表现上太让人震惊,福利院工作人员将她上报给上级或者介绍给慈善人士时都说她是重度智障。保育员们怀疑小丹之前在某个农村家庭寄养的时候被中老年男性侵犯过,以致她养成了一个异样的习惯:每当她看到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就主动脱衣服或裤子,然后拉那个男性的手摸自己的乳房或者私处。因为这个异样的习惯,她在每个寄养家庭都呆不长。最后寄养她的是保育员方阿姨的婆婆,可是一个月之内全村的人都知道她家有这样一个女孩,成为了当地一大丑闻。方阿姨的婆婆没办法只好把小丹退回福利院,而方阿姨本人也对这个决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她担心自己的丈夫会被这个性意识“不正常”的女孩勾引。小丹回到福利院后一切照旧,几乎每次都把来访的上级领导和慈善人士吓坏了。在所有教育和惩戒手段失效后,福利院只好以更高的寄养费用将她送回了农村家庭。
七、 讨论与结论
在西方社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公众对残疾人性生活的态度在往积极的方向转变[25-26]。然而中国的残疾人仍旧在自己的性、婚姻和生育权上面临挑战[5,11]。鉴于他们被认为是“无性”的人,其性表达总是被忽视,抑或被压制。这其中,残疾儿童的性蒙受着更重的污名,因为儿童在大多数的文化中本身也被认为是无性的[27]。有研究者发现中国父母甚至不愿意跟他们的成年子女讨论性问题,更不用说少年儿童了[28]。对性普遍回避与忽视的态度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很少有学术研究涉及残疾儿童的性意识和行为。但正如文章所示,性也是残疾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引起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关注。
本项研究考察了一家中国福利院中的保育员对待处理残疾儿童性问题的方式。她们依据生物医学的观念将残疾儿童视为“无性”或者“性方面不成熟”的个体,但在日常生活中又频频在这些孩子身上发现具有性意味的行为,这令她们非常焦虑。在处理这些表现出性意识和行为的儿童时,保育员们在话语上将这些孩子标签为“危险的”或“不正常的”,认定他们的生理残疾状况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和智力发育,导致滞后的、残缺的抑或扭曲的性意识,以配合她们在行动上采取严厉的管制手段。采取这些污名化话语和管制手段的背后,保育员的动因不仅是她们作为身体健全“正常人”对残疾儿童性意识觉醒的担忧和必要的治理,也包括了在福利机构语境当中她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就后者而言,她们认为残疾儿童因其生理条件的限制,对其进行性教育很难产生正面效果,反而可能唤起他们的性意识并导致不良后果,这既会给她们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也有可能给其他儿童和她们自己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险。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在观察福柯式治理术的具体权力运作过程时不应只看到宏观的社会观念,治理技术实施者的个人动机也是治理项目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而在被治理的残疾儿童这一边,尽管受到信息阻塞和严厉的管制,他们仍旧拥有性感知能力并作出相应的性行为,有的孩子(比如清清)甚至发展出一些策略性的手段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据此,文章所展示的保育员与残疾儿童就性问题的互动亦可解读为一个不利于性表达的机构环境与残疾人在性方面的能动性相互斗争和协商的动态过程。
当然,仅仅依靠作为弱势群体的残疾儿童自身去获得性表达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在受到信息阻断,缺乏正确性教育引导的情况下,残疾儿童即使通过一些策略获得了性表达权利,他们也未必知道哪些是合乎社会伦理的性表达方式,由此可能会导致一些越轨的性行为。有关注残疾人性权利的理论派学者建议政府和教育机构倡导针对残疾人的性教育,在特殊教育机构中设置“残疾人性权利的倡导”与“自慰议题”等课程,引导残疾青少年在正确的性观念下成长,在日后生活中能对自身的性需求有正向的认知[6]。这一建议的初衷固然是好的,但我们仍需要考虑在现行福利机构制度和社会氛围下实现它的可能性。譬如有报道就发现不少为残疾人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服务对象提出性需求时也会感到尴尬,不知该如何处理[29]。更大的障碍还在福利机构方面。笔者在调查期间就曾婉转地与永江市福利院领导及保育员讨论过进行儿童性教育的可能性。但他们的态度回到了笔者的研究发现:尽管承认残疾儿童也可能有性需求,他们认为在这些孩子发育成熟之前最好不要唤醒他们的性意识;尤其针对智力残疾的儿童,有些工作人员声称这些孩子因为他们的脑损伤,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发育成熟,而发育不成熟条件下产生的性意识是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的,因而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不如不形成性意识。其他的工作人员,包括院领导,也持有类似看法,并且认为残疾儿童的性问题并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些观点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儿童性教育的一般性认知,即儿童本身应当在成年以前保持无性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因为牵扯到残疾人生理状况的医学化想象而具有其特殊性——残疾人因其生理条件的限制,要么没有性意识,要么只有不健全、不成熟的性意识,这种意识引导下的性行为只会是“不正常”和“不负责任”的。在这两种观念的桎梏之下,企图劝说福利机构开展儿童性教育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的。因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还在于改变机构工作人员和公众对儿童、残疾人群体性需求的看法。考虑到目前学界和官方对儿童福利的讨论尚未涉及这一问题[30-31],对残疾人的性权利维护也还停留在理论倡议的阶段[6],后续学术、政策和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可以考虑首先制定一个旨在改变机构和社会对待残疾儿童性问题看法的方案,以便创造一个对残疾人性生活更友善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官方、社会组织和学界可以继续探索对残疾儿童进行性教育的可行方式。
[1]鞠靖.福利院切智障少女子宫之人道伦理争议[EB/OL].(2005-06-09)[2016-12-20].http://news.163.com/05/0609/14/1LQFU4R80001122E.html.
[2]张学军.对于弱智女性实施强制性绝育的民事法律制度研究[J].当代法学,2006(3):47-60.
[3]顾加栋.智障儿童权益保护的多视角考量[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93-95.
[4]ALFORD W.Who speaks for whom—China,disability and rights[EB/OL].(2006-12-11) [2016-12-20].https://www.ihrec.ie/documents/prof-william-p-alfordwho-speaks-for-whom-china-disability-and-rights-inter national-human-rights-
day-lecture-11-december-2006/.
[5]PAN L,YE J Z.Sexuality and marriage of wom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 male-squeezed rural China[J].Sexuality & disability,2012,30(2):149-160.
[6]刘中一.残疾人的性:一个社会人文视角的考察[J].残疾人研究,2015(4):60-63.
[7]万文鹏.残疾人的性生活、婚姻和生育问题[J].心理与健康,1997(1):6-7.
[8]SHAKESPEARE T,GILLESPIE-SELLS K,DAVIES D.The sexual politics of disability:untold desires[M].London:Cassell,1996.
[9]BERNERT D.Sexuality and disability in the lives of wom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J].Sexuality & disability,2011,29(2):129-141.
[10]ISLER A,BEYTUT D,TAS F.A study on sexuality with the parents of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J].Sexuality & disability,2009,27(4):229-237.
[11]KOHRMAN M.Grooming que zi:marriage exclus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disabled 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J].American ethnologist,1999,26(4):890-909.
[12]陈晶琦,王兴文,DUNNE M.239名高中男生儿童期性虐待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5):345-347.
[13]ZHANG W J,CHEN J Q,FENG Y N.Young children’s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to sexual abuse prevention:a pilot study in Beijing,China[J].Child abuse & neglect,2013,37(9):623-630.
[14]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6]GILL M.Already doing it: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sexual agency[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5:85-95.
[17]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8]乔东平.虐待儿童: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式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9]Human Rights Watch Asia.Death by default:a policy of fatal neglect in China’s state orphanages[M].New York:Human Rights Watch,1996.
[20]钱霖亮.建构保育员母亲身份的挣扎:中国福利院儿童照顾者的情感劳动[J].台湾人类学刊,2013(2):175-182.
[21]BERNERT D.Sexuality and disability in the lives of wom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J].Sexuality & disability,2011,29(2):129-141.
[22]LOU C H,CHENG Y,GAO E S.Media’s contribution to sexual knowledge,attitudes,and behaviors for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in three Asian cities[J].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2012,50(3):S26-S36.
[23]CONRAD P,SCHNEIDER J.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from badness to sickness[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24]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3-33.
[25]GILMORE L,CHAMBERS B.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attitudes of disability support staff and leisure industry employees[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2010,35(1):22-28.
[26]WILKENFELD F,BALLAN M.Educators’ attitudes and beliefs towards the sexuality of individual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J].Sexuality & disability,2011,29(4):351-361.
[27]ROBINSON K.Innocence,Knowled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hood [M].New York:Routledge,2013.
[28]CUI N,LI M X,GAO E S.Views of Chinese parents on the provision of contraception to unmarried youth [J].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2001,9(17):137-145.
[29]曲辉.当社工遭遇残疾人性尴尬[J].三月风,2014(4):32.
[30]王杰秀.构建中国特色儿童福利体系的基本路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6):107-110.
[31]邓锁.社会投资与儿童福利政策的转型:资产建设的视角[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6):1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