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劳动年代
晓宇

在莱索托马塞卢村庄里生活的村民
在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系,弗格森不紧不慢地转过座椅,起身和我握手寒暄。他穿着棉麻衬衣,卡其色裤子,圆头户外鞋,这一身打扮在满是T恤短裤的斯坦福校园中显得突兀。身份的突兀也是我对弗格森作品的第一印象。我应该怎样介绍他?人类学家,政治学家,非洲学家或公共政策专家?似乎每个头衔都差些意思,又言过其实。
1985年,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他的研究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关注的问题是国际发展政策的实地影响。在他身上,既有把眼光放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关怀,又没有因为批判的立场失去对政策干预的兴趣,以至于在作品的结尾,总会引入“我们要做什么”的发问。
出于交叉和模糊的身份,弗格森看上去总在反抗常识。他的第一本书是有关非洲内陆国家莱索托的。莱索托是最大的国中国,地处南非国土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国际援助涌入欠发达的莱索托,仅1979年莱索托就收到6400万美元的官方援助,平均每人能得到近49美元。然而,蜂拥而至的国际资本对于经济收效甚微。弗格森发现,这些项目看似在扶贫目标上失败了,不过在官僚体系扩张的目标上却一直在成功。它们把国家治理问题变成“技术问题”,然而项目实施中又不可能绕过各层利益,只能卷入国家官僚体制的运作。于是在“去政治化”的大旗下,官僚体系不断地扩张膨胀。
“去政治化”的判断很快卷入了90年代开始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动的偏重市场和私有化的“结构调整”,不仅没有带来普遍的经济增长,反而加剧了当地社会的不公和政治波动。弗格森在赞比亚铜矿带的研究,指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没有带来地区繁荣和现代化的实现,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催生了一大批被排挤在世界经济秩序之外的“弃民”。
弗格森没有停留在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不公的批评上,他开始关注国家和公民对这种状态的应对策略。201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专著《给那人一条大鱼》。书中聚焦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现金转移”(Cash Transfers),即直接给目标群体发放现金救助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南非为例,2013年全国GDP的3.4%直接用于给穷人发钱,覆盖全国超过30%的人口。在某些方面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灵活机动,比如幼儿养育补助指定的接收者,规定不需要是孩子的父母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而是事实上照顾幼儿的人。在总体社会效果上,受惠于这样的社会福利,南非的饥饿家庭在2002至2012年间从29.3%降至12.6%。这不仅挑战了主流发展话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圭臬,也彰显发展中国家正在试验的特色社会救助系统,不受困于自己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阶段。
现金转移不单是区域现象,它也被认为是全球性的“静悄悄的革命”。拉美国家在90年代率先开始了类似的政策尝试,博茨瓦纳、莱索托、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将地方试验上升为全国政策。弗格森认为,政策变化后,公民不只是通过在市场上交换劳力来谋生,而是参与公共和社会资产的直接分配:如果石油和土地是公共资产,为什么公民不能从它们产生的利润中直接获取属于自己的份额呢?
这种新式分配政治的背后,伴随深度的全球产业和劳工市场的变革。离开弗格森谈论的非洲,仅在2017年的英国,“零工经济”(Gig Economy,例如Uber出行或是Deliveroo外卖行业)雇佣的人数110万,和全国最大的雇佣机构国家保健署的员工人数相近。
我们也许正在告别长期在固定行业中的劳工经济。在高频度的流动和不稳定的状态下,现金转移式的社会救助模式出现,建立在固定领土和行业上的认同是否继续存在?以弗格森的例子说,一个来自索马里的小商贩,在南非的市集上谋生,同时准备办澳大利亚的难民申请,他的归属、身份和工作在不停地重建中。对他来说,国家和社会身份意味着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从个人经历开始。作为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学生,你为什么选擇了非洲和国际发展的主题?
弗格森:我一开始是学生物的,后来对围绕环境展开的政治议题感兴趣,找到了人类学。恰好,教我人类学的都是非洲专家。当时为了应付导师,我途经莱索托,在路上带的书正好是福科的《规训与惩戒》。我到莱索托首都时,满大街都是发展援外机构。南非因种族隔离政策被禁运,任何想要接触南非的组织都驻扎在莱索托。同时,莫桑比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莱索托的发展项目也惊人地相似,都在进行技术官僚的机构设置,撇开和政治的联系。莱索托的例子可能最极端,和全球经济的紧密关系和结构性的政治不平等,在发展规划中几乎统一地消失了。一旦在莱索托发现去政治化的存在,就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共性。这好像成了民族国家的普遍症候。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观点中,国家似乎是充满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官僚机构的扩张代表国家权力的延伸,但一方面国家在全球资源流动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和人群的控制又在不断弱化。可以说,它在形式上的扩张伴随事实上的弱化?
弗格森:我倒没有想过这样的概括。我担心的是,思想界对于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容易陷入到单方面的反国家或是反建制的立场。实际上国家可能没有想象中那样无所不在或是弃公营私,它产生了出乎预料的结果。即便福科在谈及新自由主义时,也不是彻头彻尾的攻击,而是考虑到它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如同你很难说反对权力一样,你也很难否定国家,它只是权力行使的方式。问题是你要什么样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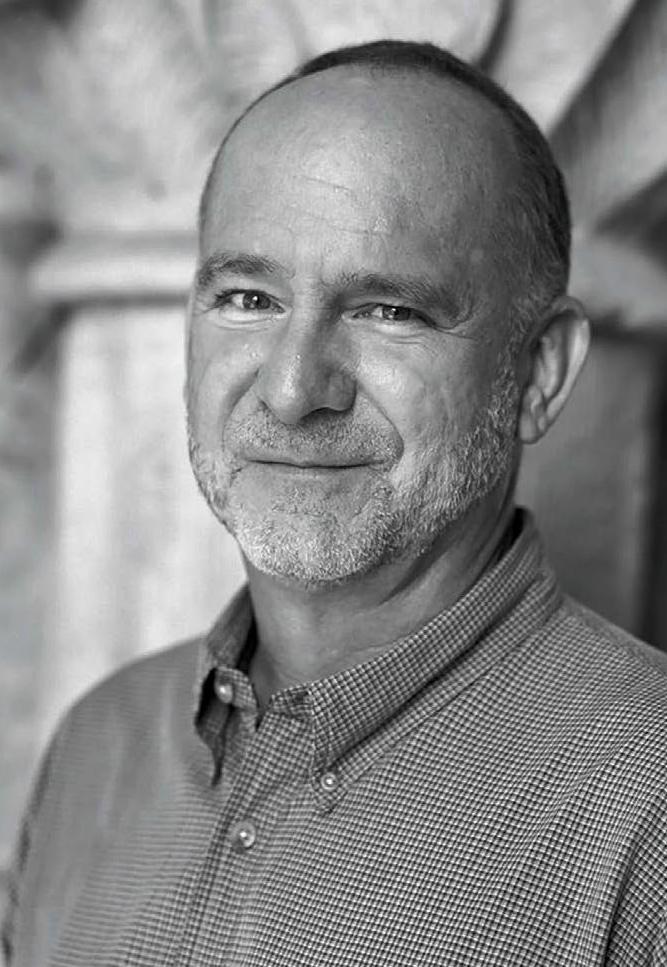
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弗格森
现金转移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它在不需要过多国家能力的前提下,进行治理的变革。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国家经常有转型社会的宏大愿景,比如改革财产的所有制、转变家庭关系这些充满野心的规划。事实上,很少有国家有足够的能力真正达到这些预期,尤其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发放小额现金不需要大规模的行政能力。特别是考虑到技术手段的进步:你不需要知道这人的出生日期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如果是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发放,你所要知道的信息就是这个月的钱有没有到账。现金转移在信息和行政方面不需要过多能力建设的情况下,产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非洲国家的案例在治理方面的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参考?
弗格森:诚实来说,我们现阶段并不清楚。拿南非政府来说,它不能代表非洲国家。它的状态很特殊,甚至不是“很非洲”。
可以说,就南非国家的情况,我们看到向民众进行现金救助的有效性。如果你有退休金,你会十分信任这个体系,它每月按时发放,每年会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这对于国家的社会服务至关重要,普通人相信这些服务保证送达。
对于许多其他非洲国家来说,民众对于国家没有这个程度的信心,因此现金转移体制化的程度也低一些。它们可能不是长久性的国家制度,而是外来的援助机构支持的中短期的项目,由外来的援助机构支持。这也会在民众中产生对现金转移的不同看法,长期的制度化运行会让民众认为这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而如果短期依赖外来资金,民众可能把它当作是“天上撒钱”的馈赠。
三联生活周刊:你谈到了福利救助制度对于社会思想和身份的影响,它可能把人们处在不稳定经济环境中的焦虑,转化成新的政治运动和分配需求。这种分配是可持续的吗?
弗格森:对。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现金转移的“意义”:他们对民众意味着什么?由此来窥见它的政治含义。这不仅仅是人们拿钱的问题,大多数政策应用方面的研究都在看人们是怎么花这笔钱的。
我的问题不一样。我想问的是,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这笔钱意味着“我完全没有用了,要依赖其他人和社会发慈悲了吗”?这样的想法当然会有相应的后果。人们会感到厌恶,失去上进心,加深去政治化的趋势。但如果你说,我们的国家因为丰饶的矿产有大笔的财富,那作为公众的一员,你有资格获得这份公有财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每月会给你分红。如果是这样想,人们的反应会很不一样。
之前有研究专门访谈了南非的失业青年。询问他们对每月获得社会救助的想法时,他们普遍觉得不妥,觉得不应该无功受禄,而是希望有工作机会。对另外一组青年的访谈中,研究者换了提问的方式,询问他们同不同意公民享受国家资源获利的分红,他们都表示了赞同。这是对同一笔钱在同样的发放过程中完全不同的反应。以“合法分配”(Rightful Share)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和我们通常对于社会救助的想象不一样。
关于可持续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明白当下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新的一代年轻人发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不断萎缩,没有新的收入支持和分配手段才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年轻人或是被排挤在生产体系之外的人不会躺下等死,他们会以某种方式要求分配,这些主张必须得到回应。
三联生活周刊:这里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产生的社会福利制度,却在抵制去政治化的趋势,把人们重新政治化起来?
弗格森:当然,这些现金转移的计划还在初期,我们对于它们的政治影响还是以推断为主。在南非实行的政策也不是以“合法分配”作为依据。我把南非和纳米比亚作对比,为了找出未来政治方式的可能方向。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社会义务和国家责任的范畴,尤其是空间上的流动对国家的冲击。曾经国家以固定的领土作为社会身份的容器。大规模的跨国跨境人口流动,挑战了这样的传统羁绊。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人们过去谈及改善境遇时,往往说“向前看”,琢磨怎么在目前的环境下进步;而现在都在打听怎么“向外走”,以空间的转移来换取境遇的改善。
个体生存策略的变化也意味着国家的治理要做出调整。如果国家的社会福利系统是以公民身份作为基础的,那在领土内的非公民怎么办?在南非,許多底层的贫穷人群并不是南非人,社会中形成公民/非公民的对立。国家的福利系统,如果以社会发展为目标,是否要修改以公民身份受惠的原则?
这也是我最近讨论的话题。以现金转移为例,政策有直接和间接的效用,除了直接用于日常生活的补助,它也意味着中小商业可以依赖于每月有定期补助的消费者。如果一个社区里大家都没有钱(无论是公民还是非公民身份),那也意味着没有商业机会。在社会范围内分散资本,增加人们寻求生计的机会,才能减少高风险的移民或是偷渡行为。但同时我们又要考虑,移民的不一定是最底层的群体,反而是已经有生计的人,有资源跨越国境。这提醒我们政策的目标在复杂的现实中难以圆满完成,国家为了减少不稳定性做出的举措,可能又会加剧流动性。
三联生活周刊: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劳工经济的转型。当代的稳定工作越来越少,短工和临工变成常态,无业游民(Precariat)成为新的阶级。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关于临工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全球的趋势吗?
弗格森:做赞比亚矿工研究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我注意到这些年轻人(他们不算是任何类型的“工人”)“闲逛”在市中心。他们被称为lambwaza,我在《现代性的期待》一书中提到过。但后来我才理解这个现象的重要性。随着大批矿工被解雇,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开始依靠即兴的“闲逛”来维持生计。在南非,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是不容置疑的,分析起来也很困难。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民众来说,在当下的经济社会转型中,他们对劳动价值的观念有没有发生变化?和固定行业或是场所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身份是否成为了过去?
弗格森:有时人们不愿意放弃旧的理念,即便在世界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我在南非观察到,尤其是男人很难放弃那种对于雇佣劳动的想象。非洲学家弗朗哥·布尔马西(Franco Barchiesi)把这称作“劳工的忧郁症”。但人们同时也会想方设法地适应新的条件,体力劳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需要。工薪阶层的女性已经注意到这些变化,对婚姻不如以前那么热衷了。当男性发现他们生理上的力量不像过去那样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权力时,他们会经历“男子气的危机”。有一些学者以此来解释地区内日益增加的针对女性的暴力。
在社会身份的问题上,我不得不再强调,这是个实证问题,在不同地方答案肯定不同。在这个前提下,我观察到一种现象可能在全世界不同地方多多少少地出现:通过现金转移或是其他的社会支付,公民权利演变为生计手段。即便在我们没有划入福利国家范畴的国家内,这些社会支付成为日益重要的生计来源。这就引起了关于国家归属感的问题。如果公民身份建立在“我会不会领到国家的定期支付”,那么,对于新来的移民来说,他们可能最需要这些福利手段,但由于不是受惠的群体,难以形成国家范畴上的“集体归属感”。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的作品中反复涉及“我们应该做什么”的讨论。我最后想问,在你看来,知识界要怎么样超越“仅是批判”的常态?
弗格森:批判有它的位置,我并不是要贬低它。但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尤其是所谓“新自由主义”),我感觉我们已经达到了贫瘠的程度,一遍遍地重复陈词滥调的批判,没人能从中学到什么。所以我想激起同行更大胆的一些行动:不仅说明我们反对什么,而且应该是我们要实现什么政治或是政策目标,直面回答我们要什么的挑战。我认为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它不是说我们要拒绝批判性思维(即便最好的主意也需要反思),而是把批判性事件和真正的政治纲领和目标联系起来,超越言辞上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