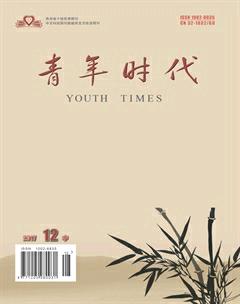试论《红楼梦》中林黛玉性别角色的缺失
毛媛媛
摘 要:《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爱情中寻找自我,最后又在爱情里迷失自我,从女性的角度来看,爱情虽然具有一种激励人心的神奇力量,但在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中,在主流话语的主导与影响之下,林黛玉激发的只能是自我牺牲和自我的否定,这也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林黛玉的性别角色的缺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
关键词:怨女;林黛玉;性别角色;男权中心话语权
爱,这是一个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但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最稀缺的就是爱。虽然从汉乐府开始她们就有了指天发誓要留住爱情的决心,她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失去,她们播撒着爱、向往着爱、憧憬着爱,然而收获到的爱却很少很少。
中国古代称那些该有配偶而找不到配偶,或者有倾心的人但却不能与之厮守的年轻女子称作“怨女”,这里的“怨女”可与“旷男”相匹配,总体地反映了理想爱情的匮乏。封建社会只有“休妻”之说,女人要遵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地遵守男性中心话语标准,完全没有自由选择爱情和婚姻的权利可言。男性与女性在婚姻上的绝对不平等,给女性的心灵带来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红楼梦》描绘了围绕着宝玉这个多情公子的众多女性的故事,展示了一副以男权为中心女性遭受不幸的画卷。在男权社会境遇中,女子的命运大多是玉洁冰清,从一而终,而男人则全然不同。紫鹃曾对黛玉说:“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这是《红楼梦》的文本背景,也是这位丫鬟眼中的世界,一个被男性话语权统治的世界。专横跋扈的王熙凤,即使再能干,却也抵不住贾琏在外沾花惹草,或续婢纳妾,甚至必须要容忍丈夫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寻欢作乐。《红楼梦》中纵然也有一些地位贫贱的丫鬟女仆或卖俏或偷情,那至多也是被男人当作玩物或者泄欲的对象,作为女性很难说她们从中得到了多少真正的快乐。然而,绝大部分的女性都在显示她们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坚贞。即使是与贾琏通奸的鲍二家的媳妇这样一个“淫妇”,在事情闹穿了以后也不得不自杀身亡。被逐出大观园的两个丫鬟,不论是“偷情”的司棋,还是清白无辜的晴雯,辞世时对于自己都有定论。司棋认定“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了,决不肯再失身给别人的”;晴雯更是认定“既担了虚名,索性如此”临终将贴身衣袄与指甲一并交与宝玉收藏。这种大胆的举动对大家闺秀、名门小姐则是不可能想象的。她们的追求,不过是保持情感与肉体的专一与统一,这其中,林黛玉可以说是这种追求的极致。
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坚贞的,又是封闭的;是一往情深的,又是疑虑重重的;是刻骨铭心的,却又是不能等同的。林黛玉的钟情相较于贾宝玉众多的“姐姐”与“妹妹”,实在是一种现实的讽刺。黛玉曾责备宝玉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这话多少有点苛刻,却也道出了几分宝玉素来的性情。宝玉曾信誓旦旦地对黛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不无痛斥地说:“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作和尚?”果然,事隔几日,当袭人说到死时,宝玉竟当着黛玉对袭人说:“你死了,我作和尚去。”林黛玉当下伸出两个指头笑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儿。”在《红楼梦》中我们随处可以读到宝玉对女性的“多情”及“泛爱”,也随处可读到黛玉对宝玉的“痴情”和“专一”。男权社会对贾宝玉的宽容还表现在他与除黛玉之外女子的情感纠葛上。他不仅与屋里的丫鬟袭人、碧痕等有染,并不失时机地与别房的丫鬟调情,致使金钏投井而亡。此外,虽然在宝玉和宝钗在完婚之后仍然多次为黛玉的死而悲痛欲绝,甚至还一度陷入痛苦、痴傻的状态,但这其中多半也还是有“通灵失去”的缘故。
黛玉对于宝玉这种爱情的执着痴迷,其实是符合封建社会男性的审美期待的,他们所欲求的女性要对他们一心一意,从一而终,绝无二心。最后宝玉与宝钗完婚,黛玉悲呼怨叹凄凉辞世,其中虽然有别人设置的花招以及非人为的障碍,但不能不说宝玉在情感上是有负于黛玉的,她的痴情被贾母看作是“忒傻气”,不如宝钗那么懂“分寸”。黛玉时常讥讽挖苦别人,为一点点的不顺心不如意而感慨自己的身世悲苦,并嗔怒宝玉,累及别人。黛玉向来的猜疑、偏执和幽怨并非完全无来由,这与其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天性所致,不如说是对爱的压抑的一种排遣。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黛玉已经获得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情人,也饱尝了情感上的甘苦,似乎算不得一个货真价实的“怨女”,然而她毕竟没有和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是在情感上怀着极大的痛苦和怨恨而去的,应该说,这种怨恨的情绪与怨女伤春之情并无本质的区别。爱情的艰难与痛苦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女性在劫难逃的命运。“在我们的文化中,每一个女人都被规约为男人的对立和补足。”女性受到男性中心话语权的控制,无法表达作为女性所应该有的权利,无法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爱,无法让追求变得合理化,无法像男人要求女人一样要求他们对于爱情的坚贞。这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消解,解构了男权主义字典中关于女人的意义,当人们问“爱是什么?”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和对方置于男性审问的角度,通过这一审问,女性的欲望于是就在男权话语中消失了。
英国的玛丽·沃斯顿克拉夫特在《妇女权力论辩》中指出:“女性当其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时候,她的美德便是循规蹈矩地完成这种单一的責任。至于生命最大的目标——展露个人才华与个人尊严,则与女人无关。……当她的丈夫不再是她的情人时(这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必然会降临),她那取悦他人的渴望,将会随丈夫的冷淡而逐渐槁木死灰,甚而成为痛苦的来源,而爱情——在所有情欲中最易凋落的一种——将被猜忌与空虚所取代。”林黛玉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不论被挚爱,或者被忽视,她都很少快乐。可以说,她的快乐是建立在宝玉“挚情”的基础之上,一旦这种理想的精神世界破碎在父权道德观的男性泛爱的心理之下,她便郁郁寡欢,最终以求死之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诚然,林黛玉不可能意识到,女人首先应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自由权利,视为不依赖他人而存在的物种,才能够在两性之爱中找到平衡点,而不是帮助男性完成驾驭女性的形式。于是林黛玉的悲剧命运已是注定,她不可能跳出时代的巢穴,强迫别人将自己视为“可爱的人”,而不是他的附庸品。
人类漫长的发展史曾压抑和毁灭了多少个林黛玉,又养育和纵容了多少个贾宝玉。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所描述的都是在“个人自由”被侵蚀,“性别角色”被缺失的痛苦和挣扎中沉浮,不能不令新一代女性重新反思自己作为女性所应该具有的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追求,从而确立自己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莫伊拉·戈登斯.想像的性别:道德、权力与身体[M].纽约及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6.
[3]冯沪祥.两性之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