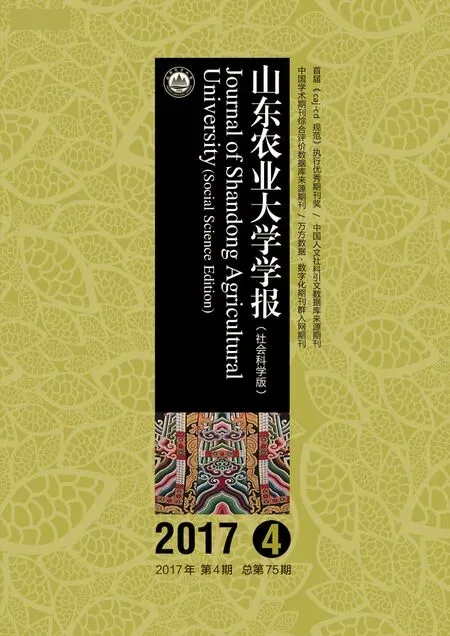《闲居集》所见明代中后期士农的城乡认知
□张景瑞
□兴,拯民左衽而衣冠之,……俗淳庞质朴无文。宪孝时,岁大穰,都鄙夜户不闭,然淳朴渐漓,好游子弟飞鹰走狗,六博踏鞠,携媚妓弹鸣筝,东门外街巷清夜管纮之声如沸。而富者豪于财,侠者豪于气,役财骄溢,武断乡曲,有司始以法绳之,法严令具自此始。武宗时,流贼乱山东过滕,滕大被杀掠。而世宗时,土木祠祀事大起,又南絓越北絓边,大珰贵人祠官将兵,数乘传往来境上。滕益多募兵,萧然繁费,富侠之家,大率破,民偷甘食鲜衣,淳庞之气益漓浮薄,以至父子兄弟异釜而炊,分户而役。[9]
《闲居集》所见明代中后期士农的城乡认知
□张景瑞
明人李开先所著的《闲居集》对明代中后期士农阶层的城乡认知及社会状况都有所记录,对研究明代中后期的城乡关系大有帮助。李开先罢官归家后,长期城居,虽然他时常表达出对城市喧闹、忙碌生活的不满和对乡居生活的向往,但始终将乡居生活作为城居生活的补充。《村女谣》中的“红娥女”,则直接表达对乡居生活的不满。李开先的城居与“红娥女”的抱怨,都反映出时人对“城乡差异”的认知。这一认知的形成,则与嘉靖朝社会治安恶化与赋役不均相关。
明代中后期;《闲居集》;城乡认知;李开先;红娥女
城乡关系是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但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城乡经济、人口流动、行政控制等方面,而对于城乡认知,即时人对城乡差异的理解、想像及书写的研究,则略显薄弱。在“城乡连续统一体”的框架下,牟复礼(F.W. Mote)曾认为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心理上的城乡差异。在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陶陶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身份与透视》(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中,多位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1]然而传统中国,尤其是士农两大阶层,果真不存在心理上的城乡差异吗?笔者认为是存在的。那么,士农阶层的城乡认识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形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进一步的探讨。而明人李开先所著《闲居集》对士农阶层的城乡认知及明中后期的社会状况都有所记录,对研究明代中后期的城乡关系大有帮助。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子,济南府章丘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曾任太常寺少卿,嘉靖二十年(1541)因“九庙灾”被免官回籍,开始长达二十七年的闲居生活。归家后,他广置田产,治第于县城西南隅,
长期定居于城市,间或居住在乡村。《闲居集》正是他归家后所作。本文拟以《闲居集》为中心,结合方志等相关文献,探讨明中后期城居士绅和乡民的城乡认知及其形成原因。①
一、乡村的“田园牧歌”与城市的“理想国”
李开先曾言:“自吾祖至父行,世惟力田,居村落,止择一可读书者来城市。”[2]493罢官回乡后的李开先,可以视为李家第一代城居者。然而其诗文中却时常流露出对乡村闲适的向往和对城市喧闹的不满。试举两例:
到此不思归,离亭上钓矶。
喜看村坞好,始觉市城非。
山带浮云色,川明落日晖。
飞鸥惊不下,是我未忘机。[2]196
厌居闹市罗华宴,定向幽严结草菴。
眼暗齿摇俱不虑,蒲英黄菊偏山南。[2]361
李开先之所以“喜看村坞好,始觉市城非”,一是长期城居可能使他产生一种负罪感,“远居离祖真吾罪”;[2]275二是城中的应酬太多,“终年应客无闲暇,镇日因人判是非”。[2]366然而对乡村生活田园牧歌般的描述,在明清时期甚至整个古代并不少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描述早已成为文人表达个人情感和展现乡村生活的固定模式,其中所包含的个人情感并不仅限于对乡村的感情,背后往往有一种道德情感或政治隐喻。[3]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将这类诗文简单等同于李开先的城乡认知。
纵观李开先二十七年的闲居生活,不难发现其言行矛盾之处:尽管诗文中称“厌居闹事罗华宴”,但其大部分时间仍生活在城市。乡居生活始终只是城居生活的补充,是他调节城市忙碌生活的一种方式。为躲避城中繁忙的应酬,章丘县城南二里的园林南园是李开先乡居的首选处所。“予家城市,人事丛委,应酬为劳。老母在堂,于礼不能远离,日惟避喧南园内。”[2]811章丘城南三十里的祖村绿原村即南村也是他乡居住所之一。“既而以避人与事,依予南村,家童驰报:‘远客至矣!’”[2]415这说明在李开先看来,城乡并非浑然一体,二者不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断裂”更为明显,而长期城居的事实也表明城市生活对李开先的吸引力终究战胜李开先对它的不满。
与此同时,李开先对乡村生活的印象也绝不会是“蒲英黄菊偏山南”式的悠闲自得,年少时艰辛的乡村生活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其为母亲撰写的墓志铭中,记载了一位含辛茹苦的女性形象:“先大夫为庠生,居城市,日用仰给予南村,时有不足处,母自凑补之,不令先大夫知也。”[2]630父亲过世后,家庭生活更加艰苦:“家无厚积,加之迎医治丧,费用久而且多,生计日否,戚党诮而轻视之。……有急则货簪珥,稍裕则又复之,屡货屡复,岁以为常。”[2]630-631如此艰苦的乡村生活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这也必定影响其城乡认知。
李开先早年在乡村的艰苦生活绝不会是个例,反而是农民生活的常态。城市生活不仅吸引士绅地主城居,也吸引乡下人。村落乡民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早已有之。[4]明代中后期的章丘县同样存在此种现象。
研究民众心态,资料的匮乏是一大难题。在大多数文献中,民众无法自我表述,而只能“被表述”。这就需要我们对史料进行更为细致的解读。《闲居集》中收有《女有美而嫁村夫者叠前韵为诗惜之》一诗,值得关注:
丽姬下嫁老村农,淡扫蛾眉绾发浓。
长叹幽兰生粪壤,堪怜废鼓伴金钟。
房栊那得安身处,井臼亲操弱臂舂。
愿逐阳台神女去,朝云暮雨杳无踪。[2]285
此诗题后有作者注释,“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古今事其有偶同者哉?”《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最早是一首乐府诗,南朝齐谢脁所作,描写的是战国时期赵国宫中的一位才人嫁给厮役后怀念宫中旧时生活。[5]根据这句注释,可以推测这位貌美女子此前肯定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很有可能就是生活在城市。“阳台女”典出《高唐赋》,后人多以阳台女形容多情女子。[6]虽然貌美女子宁愿不守妇道也要逃离农村困苦生活的心愿可能是李开先的揣测,但她不愿忍受年老村夫和乡村生活却是真实的。
有趣的是,在这首诗后,李开先又作一首《推美妇之意代为答诗》:
勿论经商与力农,礼成夫妇自情浓。
莫轻去手同秋扇,每话同心及晓钟。
为了三缫常少睡,能精五饭在多舂。
齐眉举案何人者?今古虽殊愿比踪。[2]285
这首由李开先代美妇写的诗,完全是李开先自己的认识,其要表达的与其说是美妇与丈夫的恩爱,不如说是传统思想对夫妻关系的劝诫。李开先必定是在目睹了美妇对乡村生活不满后,才会写下这具有劝诫意味的诗。这说明貌美女子厌恶乡村生活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说《女有美而嫁村夫者叠前韵为诗惜之》这首诗只是表达美貌女子对乡村生活的厌恶,那么《闲居集》中《村女谣》主人公“红娥女”则直接表达出对城市生活的极度向往。
三条路儿那条光,那条路可上东庄?
东庄有个红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
村田虽好他不喜,一阵风来两鬓糠。
灶旁门外鸡随犬,院后家前马伴羊。
一心嫁在市城里,早起梳头烧好香。
一壶美酒一锅饭,一盏清茶一碗汤。
从今不见恼坏事,里老催科又下乡。[2]87
相比《女有美而嫁村夫者叠前韵为诗惜之》和《推美妇之意代为答诗》,这首《村女谣》虽也收入《闲居集》,但更像是对当时流传歌谣的记录,而不是李开先的原创。在“红娥女”看来,饲养鸡犬马羊完全是件烦恼事,乡村生活并非如部分文人笔下的那般清闲自得。相反,她认为闲适的生活在城市。“一壶美酒一锅饭,一盏清茶一碗汤”则部分构成她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可见,明代中后期章丘地区的乡村农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城乡有别。
李开先的城居与“红娥女”的抱怨都是城乡有别的表现。李开先矛盾的言行并不是个例。文人既批判城市,又选择城居,对此现象,施坚雅解释为:“在文人的心目中,既存在着城市的禽兽世界和乡村的禽兽世界,同时也存在着乡村的田园牧歌和城市的理想国;就是这种二元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尽管城市生活有诸般危险,士大夫仍有颇高的城市成分,又为什么尽管城市有诸般吸引力,他们大多数却过着乡居生活。可以想得到,城市缙绅(以及在职官吏)强调的是一个论点,乡村缙绅(以及退隐官吏)则强调另一个论点。”[7]317-318施坚雅的二元论解释对我们理解明清士人的城乡认知颇有启发,但仍过于简单化。对李开先而言,城居与乡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补的。城居与乡居的交替,使得李开先既能享受城市生活又可避免完全沉溺于城市的“禽兽世界”。而对“红娥女”等村夫村妇而言,城市生活的吸引力犹为突出,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城市“理想国”与乡村“禽兽世界”的对立也就更为明显。
那么,这种心态是如何形成的?李开先为何虽对城市生活不满,向往乡村生活,却长期居住在城市?以“红娥女”为代表的村夫村妇会为何厌恶乡村生活,向往城市生活?这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城市生活的吸引力为何比乡村生活更强?只有深入了解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才能对如此城乡认知形成的原因有进一步的解答。
二、社会治安恶化对城乡认知的影响
章丘地区原本淳朴的社会风气在明代中后期逐渐消逝。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儇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和第二十四回《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将成化前的章丘县描述成一个“乌托邦”似的理想社会②,与此后章回塑造的成化朝后的“反乌托邦”社会反差强烈。[8]298-320嘉靖《章丘县志》和万历《章丘县志》都没有记载当地风俗演变的过程,但山东兖州府滕县方志却有所记载:
□兴,拯民左衽而衣冠之,……俗淳庞质朴无文。宪孝时,岁大穰,都鄙夜户不闭,然淳朴渐漓,好游子弟飞鹰走狗,六博踏鞠,携媚妓弹鸣筝,东门外街巷清夜管纮之声如沸。而富者豪于财,侠者豪于气,役财骄溢,武断乡曲,有司始以法绳之,法严令具自此始。武宗时,流贼乱山东过滕,滕大被杀掠。而世宗时,土木祠祀事大起,又南絓越北絓边,大珰贵人祠官将兵,数乘传往来境上。滕益多募兵,萧然繁费,富侠之家,大率破,民偷甘食鲜衣,淳庞之气益漓浮薄,以至父子兄弟异釜而炊,分户而役。[9]
《滕县志》记载风俗转变的时间点与《醒世姻缘传》相一致,章丘县的情况也应大致相同。
社会风俗的恶化,必然导致治安恶化。嘉靖年间盗贼问题犹为严重。其时为对抗南倭北虏,山东各县多有募兵,章丘县也是兵源地之一。李开先曾作诗《江南倭夷作乱杀伤山东民兵二首》纪念抗倭牺牲的家乡士兵。与此同时,与章丘县接壤的青州不时有民变发生。“白气直冲斗,十七日初昏,有白气起心次直冲斗。绿林昨弄兵。虽云成扑灭,青州草寇杨子元等称兵,旋即就擒。天变不虚生。”[2]111动荡的局势给盗贼作乱提供时机,加之粮食歉收和赋役压力,盗贼问题愈发严重。对此,李开先告诫地方官要加强武器装备。“今枪刀弓箭之外无别器,自四方多事来,如鸟嘴铳、佛朗机、神面盗、火箭、边箭、纸砲、浑甲、暗弩、钩、刀、披镰等,备极精利,此亦不可不乘间制造者。”[2]869
事实上,无论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都因盗贼作乱而改变。城市的节日气息较此前淡薄,就连元夕节也不如以往。“自从岁不登,寇盗时攘攘。佳节虽云同,乐事不及往。”[2]44乡村不仅不能夜不闭户,白天也要紧闭家门。“三苗犹未茂,谓谷、黍、稻三苗。二麦已微收。巨户昼长闭,畏盗及债主并催租者。缫车夜不休。”[2]150李开先作为城居地主,为保护田产,观察周边治安状况,在各处庄园建起平楼。“有楼不专看家,为一场二圃设也。时或蔬果盈圃,禾麦登场,只令一仆据楼坐望,虽巧于盗者,亦不能售其奸”;[2]832“今太平日久,生齿繁多而盗贼充斥。又以其属异县也,构楼以防不虞,顾讳焉而以‘逍遥’名之”。[2]834平楼的大量出现和其建造样式与抵御盗贼紧密相关。“三十年前,四乡平楼,可屈指数。今则民贫盗伙,十村而六、七,虽负郭亦有之。甃皆砖石,大约高二十尺上下,平其颠,利于飞石御敌。”[2]827
牟复礼认为传统中国的城乡之间并不存在“在内为城,在外为乡”的界限。他指出:“那个看来似乎可以充作明显界线的城墙,事实上却并非什么在内为城、在外为乡的分界。在真正的危机时期,城墙可能具有划分保护区和非保护区的实际界线的性质,但在大部分时期,大部分中国人却没有体验到这一点。……古来有句常言‘小难避乡,大难避城’,也许正是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可能酿成对国家权威造反的社会骚乱,从来都并非发源于城市;对城市人口,总是管制得较好的。然而在战争或大乱时,城市常成为激战的场所与抢掠的对象。这句老话因此就表示了:城市这样一种独立于常是无法无天的农村之外的安全堡垒,在中国并未存在过。”[7]115-116然而“城墙”在明清城乡认知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
章丘县城在成化年间修过,之后逐渐坍圮,至正德年间,因受刘六刘七部队的军事威胁,知县才组织邑人再度修葺,并在战乱中发挥重要的保卫作用。嘉靖《章丘县志》中记载:
章丘故有城,成化间张侯庆尝一修之,迄今四十余年矣。正德己巳,吕侯以进士来尹兹邑。视蒙之后,百废俱兴,独以城渐倾圮,怀于邑焉。顷之盗起,远迩骚然。侯重有忧色,乃集邑父老而告之曰:“死守,令之职也。城之修劳□力,吾不忍焉。事急矣,且奈之何?”于是,父老皆稽首出涕曰:“父母城我卫我也,劳我逸我也,役何敢辞。”遂卜日就工。邑人毕作,越旬而□成,实辛未孟夏也。城高若干丈,阔若干尺,周□视其旧又深。若隍堑严,若楼稽精,若器□圯者复之,缺者增之。故□盗贼充斥之时,所过风靡罔不失守,而此城独完。[10]16
相比于西方城市,中国的城市自然无法与乡村完全割裂,但“父母城我卫我也”则表明邑人已经完全认识到城市不仅仅单纯是居住的场所,也是一个抵御外来入侵的“安全堡垒”。
城市比乡村更安全的认识也体现在嘉靖年间颜神镇建城一事上。颜神镇“越淄川、临淄县界,属之益都,隔府人民相搀,各县流移杂处,平时武断于乡曲,肆情于博剧,出则纠众攻打,逼之则啸聚成群,弄兵探丸,鸣铙吹角,讼词繁于阖邑,猖獗甲于东藩”。[2]864时任山东按察副使、青州兵备使的王世贞为改善当地治安,提出于颜神镇建城。李开先则认为城不可全恃,“脱使有城可以凭藉,其能当伐戮燔烧之虐哉!况乎倡乱之人,居止正在衙门之右,更可于县衙之中,复立一子城耶!”[2]868他建议在颜神镇设县,通过提高行政级别达到扭转治安的目的。
此外,李开先还建议将位于颜神镇城外的监狱移置于城内。李开先认为:“禁狱所以收犯防奸,今去城半里许,主管之官,既已隔绝而不亲;监守之人,或致疏虞而可虑。倘以轻生之素性,而劫必死之重囚,事不预处,罪有攸归。盖旧无城而今有城,无城则内外俱为散地,而官须亲其巡警;有城则启闭各有定期,而势不得以并兼。且厅侧重门,尚有反狱者,况疏漏若此哉!若移置城中,则官得亲而人加谨,凶民不生幸心矣。”[2]868这体现出李开先的三个观点:一是“无城则内外俱为散地”、“有城则启闭各有定期”,表明城乡之间并非如牟复礼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什么在内为城、在外为乡的分界”;二是城市比乡村更为安全;三是城市安全性的根本来源是政治力量。③
总之,明代中后期章丘县的治安趋于恶化,盗贼问题越发严重,以致城乡生活的氛围都因此改变。社会治安的恶化使得城市的防卫作用和安全性更为突出。部分农村士绅为保护自身和财产安全移居城市,而乡民却只能忍受盗贼的侵扰,这对城居士绅和乡民城乡有别认知的形成无疑有直接的影响。
三、沉重的赋税徭役对城乡认知的影响
在《村女谣》中,“红娥女”不喜乡村而向往城市的原因之一,是乡村有里老催科。里老虽是征收赋税的执行人员,但却代表整个赋役制度。可见赋役制度已影响到当时乡民的城乡认知。
嘉靖年间,赋役的确成为章丘乡民的沉重负担,以致于选择抛荒土地而逃亡的民户不在少数。李开先对此多有记载。试举两例:
近多贪暴为民牧,里老下乡众遭毒。
征徭偏是及穷独,光明不照逃亡屋。
民火动摇元命促,安得缓征薄敛,免使闾里向隅哭![2]79
怨咨夏馑免,亢阳难有秋。
逋负不能偿,逃亡不可留。
贫者卖儿女,富者卖马牛。
倒悬谁与解?沉痼何时瘳?[2]43
逃亡的乡民中除下户外,也不乏中产之家。“典卖田产,市鬻女男,离弃乡井,苦死牢禁,不惟下户,虽中户亦有之矣!”[2]872而章丘县一百零三个图(里)中,逃亡严重的图只剩下数家民户。“一百三里,人户一百一十,定数也,节因逼累,一里止存十排,两三家、四五家,全逃者亦有之。以致粮草拖欠,地土荒芜,如西锦七图下、三十四等图,十排存只数家。”[2]871无怪乎万历《章丘县志》称数十年前的情景是“蹙额告困”、“十室九空”、“鬻田如粪土”、“□乡井如脱桎枯”。[11]大量民户逃亡、土地抛荒,这也是李开先等有财力的地主可以大规模购买土地的原因之一。
那么,明代中后期章丘县的赋役状况究竟如何?笔者根据嘉靖《章丘县志》和万历《章丘县志》将明代章丘县的赋税情况绘制成表1。

表1 明代章丘县赋税情况
资料来源:嘉靖《章丘县志》卷一《赋贡户口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五七,第52-55页;万历《章丘县志》卷十二《条编》,南京图书馆藏,78a-86b。
注:*嘉靖《章丘县志》记载是“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三石一升五合二抄二撮”,万历《章丘县志》记载是“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三石四升一合八勺二抄二撮”,以嘉靖《章丘县志》为准。
** 嘉靖《章丘县志》记载是“三百八十三斤一十四两六钱四分”,万历《章丘县志》记载是“三百八十二斤一十四两六钱四分”,以嘉靖《章丘县志》为准。
表1显示洪武至嘉靖朝,章丘县的田赋额不高,变动也不大,但嘉靖年间为何出现民户逃亡、土地抛荒的局面?观察明代章丘县耕地面积的变化就会发现,从永乐十年(1412)至嘉靖八年(1529)知县祝文冕清查耕地前,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耕地面积只增加56.57顷。而嘉靖八年祝文冕进行的耕地清查共查出51.65顷的清出地和1000多顷的诡寄地。
大量田土被巨姓豪族隐匿是耕地面积长期不变的主要原因。嘉靖《章丘县志》记载:“邑巨姓率以隐匿土田,至有家足千亩而板籍不满十之一。”巨姓豪族又通过诡寄、洒派等方式将本应承担的赋税转移给中下户,这无疑会造成不同户等承担的赋役不均,中下户面临的赋税压力最为沉重。“每遇举税,扶同书算洒派下户,以欺赤贫,鬼蜮?(上巛下贝)涊而根株盘结。虽屡经良吏,莫能动。祝侯清查多方,悉按举税簿帙,以收实数。又下令首报者赉□,否则重坐,而百余年宿弊顿革。”[10]55而巨姓豪族中不乏士绅,李开先甚至发出“概县地亩数,总计一万九百顷有余而已,士夫田多,征纳能有几何”的感慨。[2]872-873虽然祝文冕进行土地清查,但未能根本改变中下户赋税沉重的状况。
除赋税外,各项差役也是导致民户逃亡的重要原因。“章丘大差,税粮外,有均徭、银力二差;孳牧、驿传二马头支应。里长收粮大户,两河夫役、南北要路供费,加以水旱虫蝻,民贫而流,盗起而侈。”[2]870章丘县养马的数量是济南府各县中最多的,“骒马七百四十四匹,每匹十官丁折养马一百分,儿马一百八十六匹,每匹五官丁折养马五十分,共该八万三千七百分。编造计算人丁,尚少三十分,不足养马之数。凡遇买备用,只得加添银两。陆续人逃亡而马倒死,一马百分,止存五十、六十分,俱令马头包赔。”[2]872这已超出民众的承受能力,以致民畏马如畏虎。
与此同时,里甲差役在嘉靖年间成为一项重役。“初制,里甲理乡间小词讼,事大方呈县堂,后只催办粮差,今目为受打木鱼、使钱魔王矣。正官支用犹可,余则自取,常数索要食物,及油烛、硃墨、纸张、简套,一应有用打造,一切无名科罚,出行跟随答应,任吏标票给取。”[2]876而各项杂徭甚至致使里甲民户倾家荡产。“额编公用银二百两,官吏折俸,孤老冬衣布花,新官到任器具,旧官受奖礼仪,俵马部粮官盘费尚且不敷;所有合用廪给、心红纸札、公私酒席、冬夏铺陈、公馆修理物料,军匠造册上食,考校生儒纸笔花红,操练壮勇赏劳,雇赁马匹乡官处上司送礼,县送门神桃符,俱系无名杂费,银数不下万两,皆是里甲出办。一岁之间,有一里使银二三百两者。如往年李良相等使银七百两,坐此荡产弃家。”[2]871
面对如此沉重的赋役,士绅所具有的优免特权无疑是一道护身符。在《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回《狄贡生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中,薛教授就对狄员外说道:“如今差徭烦、赋役重,马头库吏,大户收头,粘着些儿,立见倾家荡产。亲家,你这般家事,必得一个好秀才支持门户。如今女婿出考,甚是耽心,虽也还未及六年,却也可虑,倒不如趁着如今新开了这准贡的恩例,这附学援纳缴缠四百多金,说比监生优选,上好的可以选得通判,与秀才一样优免。”[8]644-645薛教授劝狄员外为子捐贡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士绅的优免特权可以帮助狄家躲避沉重的赋役,以免因此倾家荡产。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显然是普遍存在的。
滨岛敦俊指出,嘉靖后,江南士大夫城居化切断了士大夫与乡村居民的关系,“士大夫阶层也就不存在约束自身负担徭役的动力。江南士大夫没有任何顾虑地全面通行避役,造成了‘役困’这种严重的情况。……利用乡绅阶层优免特权,进行诡寄等避役行为,可说是萌牙性的‘官户’、‘大户’的避役、滞纳造成了中产阶层的没落,这是正德末年和嘉靖初期开始出现的情况。”[12]通过表1和此前的分析可以发现嘉靖年间的章丘县同样存在士绅利用自身的优免特权逃避赋役的行为,也同样导致中产阶层的没落,而章丘县的士大夫城居化现象同样始于嘉靖年间。农村士绅城居化不仅切断了士绅与乡村居民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乡民对城市生活的想象。
在“红娥女”等村夫村妇的想象中,市民生活是悠闲的,而事实绝非如此,市民的徭役负担也相当沉重。“市民是亦一苦民:不领公银,不免私差;一报在官,自备什伍鞍马,或令之出牌勾摄,或令之戎装接送。驱民就吏,以此为多。”[2]873“红娥女”之所以认为城市生活悠闲,很可能是受农村士绅城居化的影响。农村士绅通过城居肆无忌惮地逃避赋役,而与士绅相比,面对赋役不均的乡民们没有选择,除了逃亡,就是隐忍。二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在乡民眼中,城市与权力、身份联系在一起。这应是“红娥女”认为城市生活悠闲的深层原因。
四、结语
中国前近代的城乡关系十分复杂,城乡认知只是其中的一方面。牟复礼提出的“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的城乡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其观察中国城乡关系的切入点偏重于城市,且存在过于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嫌疑,以至陷于一元化。任吉东指出:“我们观察中国城乡关系的切入点,不应该只局限在站位于城市,而也应该移身于乡村和市镇层境,从下而上的视角无疑会对中国城乡关系的脉络特性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起码可以使城市与乡村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加以分析比较。”[13]本文以济南府章丘县为例,将李开先和“红娥女”分别作为城居士绅和乡村农民的代表,观察中国前近代动态而多元的城乡关系。
属于士绅阶层的李开先,罢官归家后长期居住在章丘县城内,未回到祖居的绿原村。虽然他时常表达对城市喧闹、忙碌生活的不满,但却不愿长期乡居,始终只是将乡居生活作为调节生活的一种方式。《村女谣》中的“红娥女”,则直接表达对乡居生活的不满和对城市悠闲生活的极度向往。他们的行为都表现出城市生活的吸引力。之所以会形成如此认知,除城市具有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外,嘉靖朝恶化的社会治安和沉重的赋役都是重要原因。一方面,明代中后期章丘县的盗贼问题越发严重,以致城乡生活的氛围都因此改变。社会治安的恶化使得城市的防卫作用和安全性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士绅的城居化以及士绅利用自身的优免特权逃避赋役,使得乡村居民尤其是中下户承担的赋役更为沉重,以致中产阶层没落,不少民户选择抛荒土地而逃亡。这二者都对当时士农城乡认知的形成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本文的“士绅”是指通过科举的“正途”和捐纳等“异途”取得功名或有官僚身份的家居者。
②在这个理想社会里“人以孝弟忠信是敦,家惟礼义廉耻为尚。贵而不娇,入里门必武:富而好礼,以法度是遵。食非先荐而不尝,财未输公而不用。妇女惕而三从之制,丈夫操百行之源。家有三世不分之产,交多一心相照之朋。情恰而成婚姻,道遵而为师弟。党痒家塾,书韵作于朝昏;火耨水耕,农力彻于寒燠。民怀常业,士守恒心。宾朋过从而饮食不流,鬼神祷祀而牲牷必洁。从御鲜花之服,疏布为裳;不入僭制之居,剪茅为屋。大有不止于小康,雍变几臻于至道。”
③城市安全与否是相对而言的。城市具有的政治力量也是“小难避乡,大难避城”的根源。一方面,城市具有的政治力量足以抵挡“小难”时的外来威胁,另一方面,城市因其具有的政治力量而在“大难”时成为军事力量争夺的主要目标。实际上,乡村在“大难”时也深受战争的创伤。因此,在“大难”时,城乡都无安全可信。而在明代中后期尚未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等“大难”前,城市还是较乡村安全的。
[1]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17-40, pp.58-84, pp.85-106.
[2] 李开先.李开先全集[M].卜键笺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3]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代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异变[M].北京:三联书店,2010:62-71.
[4]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4:338-342.
[5]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七十三杂曲歌辞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8:1039.
[6] 陈宏天、赵海福主编.昭明文选译注[M]第二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1023.
[7]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8]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李国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9] 杨承父.万历滕县志:卷三风俗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9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22a-23b.
[10] 杨循吉.嘉靖章丘县志:卷一《建置总论》[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五七[M].上海:上海书店,1990.
[11] 董复亨.万历章丘县志:卷十二条编[M].南京图书馆藏,63b。
[12] 滨岛敦俊.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A]//复旦史学集刊·第三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9-20.
[13] 任吉东.城市史视阈下的中国传统城乡关系观念述评——以西方学者为中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K248
A
1008-8091(2017)04-0007-07
2017-04-17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张景瑞(1993- ),男,汉族,山东省枣庄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