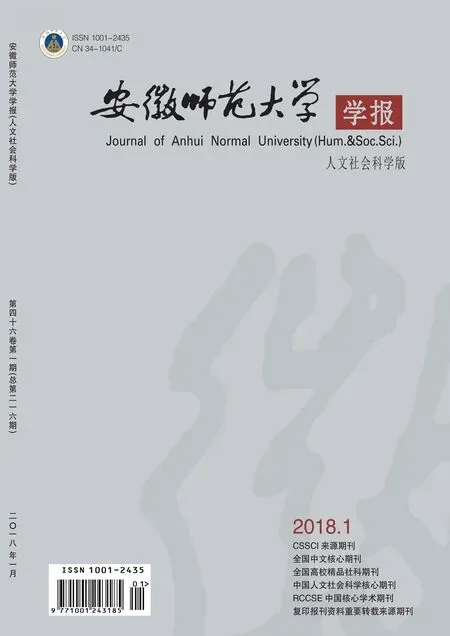重庆开埠与传统金融业的现代转型(1891-1937)*
刘志英,张格
(西南大学 1.历史文化学院 2.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经济史苑】
重庆开埠与传统金融业的现代转型(1891-1937)*
刘志英,张格
(西南大学 1.历史文化学院 2.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重庆;票号;钱庄;现代化;转型
1891年重庆正式对外开埠后,重庆金融业随着开埠而发展壮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并不是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金融业不断向现代金融的方向转化,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金融业虽仍以传统金融为主体,但在逐渐转型过程中明显体现出一系列现代化特征,不仅反映了中国西部城市走向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也折射出了西方列强不断深入中国内陆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金融业的传统形态是以票号、钱庄、银号、典当等为主体。在整个近代,这些旧式金融机构虽然逐渐走向衰落,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它们在中国不同地区的金融市场上仍起着程度不同的作用。与此同时,代表中国金融业现代化趋向,以银行为主体的新式金融机构,包括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在近代中国也在逐渐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在近代,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并不是并行的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传统金融业的变迁,呈现出一条不断吸收现代金融的先进制度,并逐步向现代金融方向转化的轨迹。虽然近代新式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但中国金融现代化却并非直接或被迫移植、嫁接西方的模式,而是一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的过程。
近代以来,重庆虽地处中国西南地区,但也较快地进入通商口岸行列。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确定重庆作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商开辟从宜昌到重庆的轮船航线,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设立,重庆成为了西部地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重庆开埠后,列强不断扩大对华商品输出,重庆逐渐成为了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开埠给重庆金融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晚清末年开始,代表着金融业现代化趋向的以银行为主体的新式金融机构不断扩大发展,体现了西部地区的金融业缓慢地向现代化的迈进;同时,由于与上海为中心的东部现代化金融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重庆传统金融业也发生着深受现代金融业影响的一系列变化。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重庆钱庄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成果中:唐学锋《抗战前的重庆钱庄》(《成都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陈敏《民国时期的重庆钱庄业》(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吕树杰《和成钱庄的现代化变革》(《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等。对于重庆典当业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秦素碧《民国时期四川典当业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等。由于典当业在重庆开埠之后到1937年之间,并未出现显著变化,本文在论述时不涉及典当业。对于重庆票号的研究则相对缺乏。,重点探究作为中国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重庆,从开埠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以票号、钱庄为主体的传统金融业在逐渐转型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化特征。
一、晚清重庆票号钱庄的现代化趋向
位居西南的重庆,到19世纪80年代,已经逐步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重心、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的口岸。据统计,1881年重庆进口洋货量占上海进口洋货量(鸦片除外)将近1/9。1891年重庆开埠后,在销售进口洋货的地位上,重庆仅仅次于上海、汉口和天津;在许多进口商品中,“重庆作为货物集散重心,甚至超过汉口。”这些洋货自重庆分别销往成都、嘉定、叙州、绵州和合川等地市场,有些还取道泸州、叙府,继续运销到更远的内地——云南与贵州。[1]72-73伴随着如此大量中转贸易的是金融机构的参与中介与资金融通,出现了大量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也渐行活跃,于是奠定了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重庆与下游地区上海、汉口之间资金清算,基本上依靠两地的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的汇划来完成。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山西人创办,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前后(清嘉庆、道光年间)。票号以汇兑为主,兼营存款借款等,其汇兑业务是为了适应埠际贸易的开展,解决不同地区间由于长途贩运而形成的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承担了城镇间的货币清算,以汇兑方式代替现银输送,节约了社会劳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票号的产生就始自山西人在重庆、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从事颜料店经营的商业活动中,从初期兼营汇兑业务中逐渐脱离出来,成为专业汇兑的金融组织。[2]12-13
票号实行的是总、分号制的组织结构,来重庆开设分号的票号主要为山西帮(又称西帮或西号,历史悠久,力量雄厚)和云南、浙江帮(又称南帮,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据相关资料记载,清同治、光绪年间,为重庆票号的极盛时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重庆在最盛时有票号28家,其中除南帮票号天顺祥、兴顺和(云南帮)、源丰润(浙江帮)3家外,其余25家均为西帮票号。[3]77
19世纪80年代,重庆设有16家山西票号,已垄断了邻省的主要业务,同时也在广州、长沙、汉口、贵阳、南昌、北京、沙市、上海、天津、云南、芜湖各地设有汇兑代办处。每家票号都握有白银10万两乃至30万两的资本。与官府联系紧密是票号的一大特色,这16家票号足有半数可以认为半官方机构,因为他们经手相关的各省汇到北京户部财库的公款,此外,还担任汇兑捐纳官职的款项并转发文凭、执照等事。[4]66
除山西票号外,云南人王炽于同治十二年(1874年)在重庆创办的天顺祥票号是清末一家重要的南帮票号。它因与重庆地方政府联系紧密而很快发展起来。清政府在重庆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为川东道,同治末年,川东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3万两,道台向重庆商界洽借,却没有一家愿意借款。而天顺祥票号却一口应承,且不要利息,垫支3万两,解救了川东道的燃眉之急。此后,光绪六年(1881年),川东道台唐炯,兼署四川盐茶道,督办四川省的盐务,为改善以自流井为中心的川盐生产设备,急需白银10万两,向重庆商界筹集而被拒,王炽的天顺祥票号不仅答应借钱,还仅用8天时间便将10万两白银全数筹足。[5]60-61天顺祥票号通过对重庆及四川地方政府的借款,不仅加强了与当地政府的密切联系,更是在商界竖起了信誉,逐渐成为清末重庆南帮票号的代表。
清末重庆的票号,专以经营凭票汇兑为其主要业务,票号内部无一定之规章,大抵由财东出资,交付“管事”或“大掌柜”经营,而“管事”对于号内事务,具有操纵处理之大权,除经营凭票汇兑外,并兼代当地绅商官户捐纳功名,集收官场存款,以及代汇京都解款与代缴公款等业务。晚清时期重庆重要的票号有:日升昌、百顺通、协同庆、协同信、新泰厚、乾盛亨、中兴和、晋昌升、源丰润(浙江帮)、源丰久、三晋源、乾盛晋、永泰蔚、蔚泰厚、天成亨、存义公、蔚盛长、蔚丰厚、大德恒、大德通(云南帮)、天顺祥(云南帮)、兴顺合(云南帮)。[6]
重庆开埠促进了当地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传统金融业的发展,这种发展既表现出机构和业务总量的大幅增长,也表现在由参与国内贸易到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转变。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庆设立海关时,重庆已有票号23家,自流井(自贡)、内江、万县、顺庆(南充)、嘉定(乐山)等城市,均有票号的代理机构。[7]21891年重庆洋货净进口为137万余关两,1894年便增加到510万余关两;同期,土货出口额也从138万余关两增加到500万关两,四年中进出口值各增3倍多。随着重庆输出入贸易的开展,大宗棉纱的购买,大量农副产品的外销和烟片买卖等商业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以及由此引起的各地区间金融调拨和清算的巨大需求,迅速推动了传统金融业的发展。从19世纪90年代以后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重庆票号的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增长,能够左右当地金融市场。[1]108迨满清逊位,共和肇成,官场存款以及代缴公款等业务,因事变境迁,不复存在,票号至此逐渐衰微。[8]
重庆的钱庄比长江中下游城市出现晚,大约是在清朝初年,当时称为钱铺,从事银两和制钱的兑换,即经营换钱之店铺。“钱铺买卖另星,俱对客成交”,并无钱市和经纪。[1]3而重庆钱铺最初的汇兑业务主要依赖于票帮,“凡遇汇兑事务发生必向票帮介绍,形同经纪,代人汇兑,每千两约得用钱二三两而已,俟后商业日渐发达,汇兑业务日多,业钱铺者,资本起初至多三数千两,经手既久,能得票帮信用,赊与期票,放以款项,转贷他号,以收运用之益。”[6]当时贩运棉花的花帮比较兴旺,钱铺于是将钱贷与花帮,运往沙市、汉口等地,购买棉花。钱铺或钱摊,大多设在重庆较场口及关庙街等处。光绪初年,换钱摊铺布满各街,依此而谋生者,在数百家以上。光绪二十年(1894年)间,市面禁用毛钱,其利遂微,难以维持,换钱摊逐渐减少。于是,钱铺便依赖票号的扶植做汇兑,其资本虽仅三数千两,但资金运用,能渐趋灵活,业务亦随之发达,遂有钱帮公会之成立。在清光绪年间,重庆钱铺即有上半城与下半城之分:上半城大都设在较场关庙(即今民权路之旧址)一带,悉多专营换钱业务;下半城则设在陕西街(今之陕西路)一带,大半皆兼营倾销,汇兑贷款等业务。[8]这些钱摊、钱铺就是重庆最早的钱庄。相对而言,钱摊资本较少,一般不过几十两到百余银两,业务为兑换制钱,且始终无多变化。自从银元和铜元开始流通后,市场上制钱逐渐消失,钱摊业务就由兑换制钱转变为兑换铜元。只有钱铺发展迅速,它们的资本比钱摊多,一般为四五百银两,也有数千两的。清同光时期,重庆主要的金融机构是票号,它们的业务对象是地方政府和官吏士绅,与商场的往来较少,故重庆城市中商贩的资金周转大多依靠钱铺融通。钱铺因历年获利的关系,资本逐渐雄厚,开始办理存放业务,如同生福钱庄,就是由钱铺直接改称,并成为晚清时期重庆比较有名的钱庄。民国建立后,因长期与清廷官府利益过分捆绑,导致重庆票号由于政局突变而带来重大损失,纷纷倒闭,于是钱铺乘机正式改为钱庄,并替代了票号曾经的地位,成为重庆金融界主要行业之一。
晚清时期,票号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操纵着重庆的金融市场,重庆汇兑主要由票号经营,重庆的钱业虽然参与其间,但主要是代票号经手汇兑,获利甚微。加之当时轮船不通,重庆、宜昌交通水路,全恃木船,每立汇票,必先期一个月,并须向票帮预定,若外埠汇兑,到期未能售出,必须下比(即下半月)始能售出,则折耗半个月之利息。宣统年间,各汇兑钱铺,资本日益雄厚,上下货运,日渐发达,汇兑款项,不复仰仗于票号,而操诸钱铺之手,于是钱铺始向外埠开庄立号或委托他人代理,自行立票交兑,再不依赖票帮。[8]重庆票号与钱庄业务对象还有着明显差别,一般而言,票号与一流商人交易,钱庄与二流商人交易。虽两者皆做存放款业务,但显然票号占据着主导地位。
自1891年重庆开辟为商埠后,银两就从陆路和水路涌到四川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和分配中心,而票号则掌控着与邻省及国内主要城市的汇兑业务。尽管因汇兑地点、商业情况以及时令季节,汇兑比率变动甚大,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渝平银100两与各地银两的兑换还是有一个大概的比例,表1即反映出从1892—1901年间,重庆市场中渝平银与各地银两及交易不同商品时的比价表。

表1 1892-1901年渝平银与各类平银之比价表
资料来源: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由表1可知,随着重庆开埠,重庆内外贸易增多,银两的兑换更加复杂。从地域来看,在重庆与各地的银两兑换中,邻省贵州和云南来的银两为数不多,而与四川省内各地以及沿长江沿岸的城市兑换频繁,特别是从上海用汇票兑来的大宗款项,比如鸦片贸易每年多在夏初,上海鸦片市场最旺盛时将款项以汇票兑到重庆,由重庆运进内地收购鸦片的生银逐渐又返回重庆投资于购买洋货。
重庆开埠,不仅促进了重庆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积极参与进出口的商业贸易活动,而且在流通领域活跃之外,还进一步将从商业贸易中赚取的利润投入到当时逐渐兴起的近代工业与交通领域。如重庆的南帮票号天顺祥票号,在洋务运动开展的1887年,就曾帮助在云南的总号在四川为云南铜矿承办招股业务。再如在清末的商办铁路运动中,1907年从官商合办改为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在重庆、宜昌、成都、上海四地集掖股款,并且分别储存在上述四地票号和商店的达681万余两。[1]177重庆票号也参与了为川汉铁路公司收存股款的业务,其收存的铁路股款为1 395 965两之多。川汉铁路公司曾与四川机器局联合在重庆设厂,试办铸造铜元。在购置机器、建造厂房中,除提借地方政府存放当铺、盐局生息款100万两以外,并向票号借款50万两。[9]390-391这表明重庆票号从融通资金上对商办川汉铁路事业的创办与经营的支持。
总之,晚清时期的重庆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从东向西不断扩大侵略过程中,尤其是随着重庆的开埠,其业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票号、钱庄的资本由参与国内贸易拓展到积极参与进出口贸易,这一转变,为外国商品内销中国西部内陆及外国侵略势力掠夺中国西部土特产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扩大了自身的力量。以汇票、庄票为手段的信用制度得到日益完善,传统金融机构不仅参与近代商业贸易成为新型贸易体系的融资中枢,而且还向资本主义工矿交通企业投资或提供融资服务,这些转变共同促使了传统金融机构从传统向早期现代化的转变。
传统金融机构都曾顺应经济环境变化做出了某些改变,但票号与钱庄因做出的选择不同,导致不同的命运。票号从根本上并未脱离合伙制的窠臼,固守传统的经营思想和忠实为体、勤俭为用的理念,且业务过分依赖官府。尽管票号建立了庞大基业,把机构扩展到全国八九十个城镇,拥有横跨大江南北的全国性经营网络,但还是由于其内部缺乏创新精神与服务社会的观念,最终还是跟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走向终结。相较于票号,钱庄则较为独立,不依赖于官府,且较注重吸收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运营方式,最终能够在动荡不定的时局中生存和发展。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钱庄的现代转型
民国建立后,由于票号相继收歇,作为传统金融机构主要代表的票号退出了重庆金融市场的历史舞台,钱摊、钱铺正式改为钱庄,真正成为重庆传统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与此同时,晚清时期的典当等传统金融机构在重庆也得以继续保留下来,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因此,从民国建立以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的传统金融机构主要以典当和钱庄为主,其中钱庄的实力最强,成为重庆金融市场中的主体。
民国以后,重庆传统金融业的主体是钱庄,他们逐渐强大,其活动范围,亦日渐扩大。据统计,到1913年底,四川钱庄达243家。[10]其中重庆钱庄在1918-1919年间进入极盛时代,共有钱庄50余家。以后逐年减少,到1925年,减至30家。1927年初,钱庄又回升至49家。[11]122但好景不长,此后政局动荡,钱庄倒闭、歇业不断。1930年时,重庆全市有和济、协和等30余家钱庄,资本数万数十万不等。其营业者存款、放款、抵押汇兑,与银行略同,惟不发行兑换券,以汇兑为大宗营业。[12]1931年长江下游城市遭受特大水灾,重庆出口贸易受阻,再加之“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致使业务原已不振的重庆钱业进一步受到影响,数量锐减,只余12家勉强维持营业。[3]941932年初,重庆钱庄业务略有起色,家数又回增到20家。1933年又收歇5家:裕丰(资本10万元,倒欠32万元)、宝庆(资本7万元)、福星恒、同丰、安康(后3家属自动歇业,未累市面)。[13]1934年1月29日,重庆恒茂钱庄宣布歇业。这家钱庄原有资本12万元,营业额计申票900余万元,长短借贷200余万元。曾于1932年改组一次,但因历年亏空过巨,经手人长用已达10万元;部分存户纷提存款;该号股东多丰都帮字号,1933年因汉口烟土字号倒闭甚多,颇受影响;再加之做空申票,损失过大,债务达40余万元。[14]1934年,加上重新开业的6家,重庆计有同生福、正大永、谦泰、益庆、久大、和成、和济、信通、同丰、裕泰、益康、益友、复兴、安定、永大、永庆、德安、益源18家钱庄。[15]1935年10月底,重庆市陕西街福兴钱庄因受连号福兴玉盐号倒闭影响,宣告停业。[16]由于市面清淡,重庆钱业大多采取紧缩方式维持业务。重庆钱业公会的会员钱庄,除结束和归并者外,仅余7家,为历年会员钱庄家数最少,[3]961936年回升至17家。
民国之后,虽然重庆已经有了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但由于商民对之不甚了解,所以业务未能广泛展开,钱庄则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承担了社会金融的主要调剂任务。从重庆出口的药材、山货、盐、糖、烟叶和从沿海进口到重庆的匹头、棉纱、五金、杂货等帮的存贷款与汇兑事项,无不依赖重庆的钱庄办理。据资料显示,当时上下货帮的款项收交和城市商贩的资金周转多由钱庄汇兑融通,钱庄每年吸收的存款约合白银1 000万两,贷给货帮的款项则高达1 500万两。[7]3其中仅对丝帮的贷款即达300万两,从1912—1920年间,钱庄在重庆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超过了银行。[3]94到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各钱庄,成为了西部地区金融积汇转输之所。1936年各钱庄之资本及其负责人情况统计如表2:

表2 1936年重庆市钱庄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渝市钱庄统计》,《四川月报》第9卷第2期(1936年8月),第119-121页。
表2所列是1936年时重庆钱庄的基本情况,重庆全市有17家钱庄,到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7月,又增加到23家。[17]从总体来看,重庆钱庄的规模与数量,1919年达到高峰,此后逐渐减少,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数量上更是起伏不定。这说明,钱庄逐渐让位于新式金融机构银行,只能在金融市场上起到补充与辅助的作用。
民国建立以后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的钱庄按照规模大小及营业范围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为规模较大者,主要业务除大宗存放款项外,在上海、汉口等外埠设有分号,办理汇兑等事宜;第二级则为规模较小者,除做存放款外,关于汇兑事务则委托人代办收交;第三级则仅仅经营普通兑换业务,大批买进或卖出辅币以期从中取利。重庆钱庄的组织结构与上海及其他各地的钱庄并没有多大区别,一般由五个部分构成:会计、出纳(管称)、出店(赶场)、文书、经理(掌柜)。[18]
在此时期里,新式银行对钱庄经营方式的改变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34年5月,吴晋航创办和成钱庄。他曾受刘航琛邀请,出任了川康殖业银行的总务主任,对银行的业务有一定了解。因此,在钱庄创办之初,就借鉴了银行制度,如在组织结构上,没有采取当时重庆大多数钱庄的独资经营方式,而是采取合资组织形式,资本定为15万元,并采用了发行股票的方式,钱庄股份以1 000元为1股,1股1权,以伙友会为最高监督机关,凡有重大事项之决定,须有过半数股权之出席,出席过半数以上之决定乃得发生效力。[19]在经营中,和成钱庄借鉴银行的经营理念,侧重扶助川省进出口贸易,打破了钱庄大多不设分庄的常规做法,不仅在上海设立分庄,还在成都、万县、涪陵、南充等四川省内各地增设办事处,“树立了川省省内汇兑之基干”[20]。随着业务的迅速发展,作为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于是增资改组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和成钱庄遂走出了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1937年2月1日,由发起人会议正式通过《和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决定将和成钱庄改为和成银行,设总行于重庆新街口,并于国内外重要商埠设立分支行或办事处。[21]1937年5月,和成钱庄增资60万,正式呈准改组银行。[22]除此之外,钱庄除了经营传统的存款、放款及汇兑业务之外,还开始参与到新式金融业务中,如1931年间,“因受二十一军财务政策之赐”,屡发库券与公债,钱庄积极参与其间,营业鼎盛。[8]在此后的重庆证券交易所中,钱庄也多做经纪人,代客买卖有价证券,藉以获取佣金,也有直接经营公开库券者,“其间自不免有买空卖空之投机交易”[8]。总之,全面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钱庄,无论在组织机构与业务经营方面都受到新式金融机构银行的影响,呈现出现代转型的趋向。
三、申汇市场对重庆传统金融业转型的助推
民国以后,重庆传统金融业走向现代化的表现,还体现在重庆钱业代替票号逐渐成为了申汇市场的主要掌控者,从而跨越了钱庄业务的传统领域而步入了现代金融领域。
首先,以重庆申汇市场为纽带,钱庄将西南地区的资金网络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申汇又称为“上海头寸”,是近代中国各地同上海之间电汇的简称。由于上海在近代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内地商埠大都依上海转运结算。随着贸易量的增长,各地对申汇供求数很大。各地同上海的资金划拨十分频繁,申汇即是一种埠际资金调拨方式,通过申汇将各地与上海联系起来,于是在天津、汉口、重庆、西安、南昌、宁波、杭州等全国各重要城市形成了申汇市场,进而构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范围内的汇兑体系,使商埠之间的资金调拨畅通无阻。
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工商业中心,而西南地区的重庆则是长江上游的经济金融重心、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口岸。重庆在埠际贸易中以上海大宗,汇出汇入款以申汇占多数,与其他商埠交易均以申汇为清算标准。晚清时期,重庆与长江下游各地区间金融调拨和清算,绝大部分都要通过重庆票号的金融活动来完成。自民国建立以来,由于票号的衰亡,钱庄接替票号,成为了申汇市场的主要操控者。四川全省汇兑,以渝票为中心本位,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年平均约为关平银7 000万两。[23]3
重庆与上海之间的资金流量比较大,故申汇之涨落,成为重庆市场繁荣或疲弱之关键。清末民初,川省进出口贸易多系出超,渝申间资金供需持平,申汇相对稳定。渝市申汇稳定时,约以上海归元1 000两恰等于渝钱平银950两左右。重庆素来以九七平7钱1分合洋1元,向无洋厘起落。故凡以渝钱平952两,按九九八折合九七平,再以每元7钱1分合洋1 338元1角6分,即合规元1 000两,“是为平过”。[24]67-68民国之后,随着票号衰落,川江轮运开通,贸易的扩大和汇划往来的增加,重庆钱庄势力迅速膨胀,开始在省外口岸城市设庄自行办理汇兑,逐渐取代票号而成为重庆汇兑市场的主力,操控了重庆货帮与上海的资金汇兑,这从1922-1931年间的重庆申汇市场的涨跌即可得到印证。
表3显示了十年间重庆申汇市场的涨跌。重庆对于上海汇水伸缩,主要是受重庆与上海间货物往来贸易的影响,以重庆与上海的进出口贸易之比差以及重庆银根之活滞为转移,如进口繁盛或当银根呆滞时,由重庆汇往上海之汇水即涨;反之,如为出口繁盛或银根活动时即跌。其次才是受时局的影响。如涨跌幅最大的1924年就是受往来贸易的影响,年初的1—3月间,申票价在960—1 006两之间,3月半以后,因上海纱价过高,买者停手,而各商调出之款,搁置颇巨,汇价遂陡落至960—970两,直至5月上旬,江水渐涨,大轮畅行,申庄渐渐进货,票价始渐增涨至980—990两,嗣后更逐步升高,11月底增至1 172两,直至年终始降。而涨跌幅排第二位的1931年则既有贸易的因素,又受时局的影响。

表3 1922-1931年间重庆申汇市场涨跌幅度表
资料来源:重庆中国银行编:《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1934年版,第44-59页。
从这十年的整体情况来看,前五年的涨跌还算正常。从1927年起,钱帮将投机申汇视为有利可图之利薮,趋之若鹜;汇兑交易中,买空卖空盛行。加之正值北伐战争,江浙吃紧,沪市金融发生极大变化。渝申间进出口陷入有入无出状态,川帮欠申之款,不能如期措还,导致申汇行情暴涨至1 179两合洋1 647元,此后渐趋稳定。1931年夏,长江水灾,渝市入口锐减,汇价为1 400元(1931年重庆实行废两改元,上海汇兑每千两以规元折合计算)上下。“九一八”后,沪市银根逐步紧缩,川帮在申活动能力全赖调款挹注,有出无入,导致申汇率由1 400两涨至1 600多两,投机家更行活跃,商人、非商人、银钱业或货帮均参与其间,市场出现极度动摇,一日之间申汇率有三四十元的升降,波及弱小钱庄,宣告搁浅者多家。[25]
其次,以重庆申汇市场为阵地,钱庄由经营汇兑发展到利用证券交易所开拍申汇。
1932年之前,重庆的申汇市场就设在重庆钱业公会内。每日上午十一二时,各庄派员齐集公会,短期借贷及汇兑,多在钱业公会接洽,尤其关注买卖申票、汉票、或蓉票、叙泸票,“或一千、两千,或三万四万,赌汇水之涨落。例如申票一千元,此地交一千零若干元,或不及一千元,在上海对期交付一千元,于中取利。亦有所估汇水涨跌不洽,以致折本者。”[26]期间,重庆“申票大王”石建屏通过建记字号,大肆投机申汇,先后卖空申票达300余万元,获利极丰。不久遭遇“九一八”事变及武汉水灾影响,石继续卖空,导致亏折数十万元,宣告破产,牵累市面甚大。到10月31日,汇合、恒美、鸿胜、康济等家受牵连相继停业,在重庆酿成金融风潮。[24]59此后,地方军政机关开始对申汇市场进行整顿。刘湘部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刘航琛将申汇交易交给了由银行公会主办的重庆证券交易所整理、经营。钱业公会及各庄商号认为申汇系其专营业务之一,“此项利益,交易所不能强夺,于是又惹起极大风波。”终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明令禁止,加之钱帮团结不坚,遂先后完全加入交易所。[25]这样,重庆的申汇交易市场也就从原来的钱业公会搬迁到了重庆证券交易所。
重庆证券交易所中的申汇市场,每日分前后两市,成交总数,从200万两到数10万两不等,由于申汇行市的公开,得到进出口货帮商人的赞许,汇价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还算稳定。但时间一久,因受利益驱使,经纪人与受托人竞相捏造虚假信息,致使汇价因此剧烈变动。1932年6月30日,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在四川美丰银行召开第十六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申汇奇涨问题,作出六项决议:“1、平定汇价治本办法,另由经济研究会从长计议;2、平定汇市治标办法应呈请军部撤除运现禁令;3、开禁一层,如不能办到,请准军部发给临时现金通过证以资调剂汇市,使其渐趋安定;4、现洋流出后,利率如见提高,本会承认今后贷与政府之款项息率,不得过二分,逾一分半时应随市作定,但市息超过二分时应请政府救济;5、公推康主席会同钱业公会刘主席*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康心如;重庆钱业公会主席刘闻非。与财政当局接洽给照办法;6、现金外溢,各行库存必见低减,应由公会妥筹,相互保障办法。”[27]然而,申汇市场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7月中旬竟将申汇烘托到1 800元,此为渝申汇率最高记录;不及十日,行情遂步跌至1 620元,7月20日以后又达到1 720元。[25]8月1日,庆钱业公会与交易所的“钱交风潮”发生,钱业公所请求取缔交易所。“钱业公会每日均在报纸沥陈交易所操纵申汇,危害市场。交易所除详自辩诉外,对兹攻讦,皆置不理。”后经市政府召集两方代表,要求钱业公会与交易所互相合作。[28]自石建屏投机申汇失败后,交易所与钱业协议,对于申汇,钱业做近期,交易所做远期。但在此后的交易中,钱业中仍有做远期的,而交易所又搞投机,业务矛盾日深。此后经军方多次干预,才允许钱业入所。12月3日,申汇又暴涨至1 400元时下令交易所停拍,才告解决。[29]1933年4月,渝市申汇在1 600元至1 700元间徘徊,因中央通令废两改元,4月16日为1 196元(比较规元千两仍在1 670左右),8月底到10月初因上海货物品质欠佳,松到1 008元,10月中旬后又涨到1 130元。[25]1934年下半年申汇由8月底的1 230元,因种种原因,10月半时即涨到1 420元左右。[30]1934年10月,重庆市商会为平准渝申汇水,曾具呈二十一军部,请由官商合共出资100万元组织公司,收买土产货品运申销售,由政府特予免税出口,以一笔为期。“军部业已照准,其商股50万元中拟请重庆银行公会担任大部分;对于平准汇水原则,重庆银行公会极端赞成。”对于重庆市商会的提议,公会认为,将来公司如能组织成功,重庆市银行公会各行对于商股部分决不加重负担,至于认股方法则与政府协商。[27]
由上可见,1933—1935年间,重庆申汇市场完全变成赌场,由渝汇申,每千元汇水曾达700元以上。[31]申汇市场中的涨跌起伏,反映出时局人心的不稳定。1935年2月1日交易所被迫关闭,停拍申汇,仅由银钱业组织交易处经营。[32]
民国之后的重庆申汇市场虽然有着很大的投机成分,但申汇市场的波动仍受制于上海。上海作为商品流通网络的中心以及汇兑中心,主导着全国主要商品的价格和内汇市场,并主要经由钱庄向全国传导相关市场信息。重庆的钱庄则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枢纽,相关市场信息经过重庆向更广大的西南腹地渗透与扩散,西南地区的资本也因此以重庆为集中地。这样,以重庆申汇市场为纽带,将西南地区的资金网络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重庆的申汇市场还集中反映了传统金融业的现代化趋势:一是顺应时势,将业务从传统的业务经营顺利转到进出口贸易的货币清算为主,二是钱庄在掌控重庆申汇市场的过程中,还能利用现代化的重庆证券交易所开拍申汇。
四、结语
1891年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重庆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对外开埠的口岸城市。重庆也因它独特的地理位置,逐渐发展成为了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中心,重庆的传统金融业因此开启了向现代金融的艰难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出清晰的由量变到质变的特点。重庆开埠,不仅使传统金融机构和业务总量大幅增长,也使之由参与国内贸易发展到参与进出口贸易。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由汇兑发展到开拍申汇、投资公债,也开始将资本投向现代实业。总之,重庆传统金融业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不仅集中体现了西方列强不断深入中国内陆,侵略中国西部的历史影响,同时,也呈现了中国西部城市走向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历史。
[1] 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
[3] 重庆金融编写组.重庆金融: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4] 周勇,刘景修.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5] 杨耀健.王炽与天顺祥票号[G]∥重庆市渝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渝中区金融工作办公室.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十八辑·渝中金融史话专辑(内部资料).2008.
[6] 黎父.重庆金融市场考略[J].银行周报,1926,10(8).
[7] 四川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金融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8] 李荣廷.论重庆钱庄业[J].中央银行经济汇报,1941,4(11).
[9]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10] 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辛亥革命至抗战前夕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一)[J].四川金融研究,1984(4):19-24+26.
[11] 周开庆.四川经济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
[12] 重庆钱业概况[J].中行月刊,1930,1(5).
[13] 张舆九.四川经济之分析及其重要性[J].四川月报,1934,4(4).
[14] 重庆恒茂钱庄歇业[J].四川月报,1934,4(2).
[15] 唐学峰.抗战前的重庆钱庄[J].成都大学学报,1991(2):20-23.
[16] 重庆福兴钱庄停业[J].四川月报,1935,7(4).
[17] 重庆钱庄调查[J].四川经济月刊,1937,8(2).
[18] 致高.重庆之钱庄[J].钱业月报,1932,12(9).
[19] 和成钱庄组织与增资及改组银行股东创立会会议录[Z].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和成银行未刊档案,档号0300-0002-00001.
[20] 和成银行十年来业务概况[J].四川经济季刊,1944,1(3).
[21] 和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37年2月1日)[Z].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和成银行未刊档案,档号0300-0002-00008.
[22] 和成银行总管理处沿革[Z].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和成银行未刊档案,档号0300-0001-00408.
[23] 重庆中国银行.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M].重庆中国银行,1934.
[24] 重庆中国银行.四川金融风潮史略[M].重庆:中国银行,1933.
[25] 卢澜康.从申汇问题说到现金问题[J].四川经济月刊,1934,1(4).
[26] 重庆金融机关及货币状况[J].工商半月刊,1930,2(24).
[27] 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纪录(1932年6月30日)[Z].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未刊档案,档号0086-1-117.
[28] 重庆申汇风潮之追述与现状[J].四川月报,1932,1(2).
[29] 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辛亥革命至抗战争前夕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四)[J].四川金融研究,1984(9):35-44.
[30] 四川地方银行经济调查部.重庆申汇市况[J].四川经济月刊,1934,2(4).
[31] 张舆九.抗战以来四川之金融[J].四川经济季刊,1943,1(1).
[32] 四川地方银行经济调查部.二十四(1935)年四川金融大事日志[J].四川经济月刊,1936,5(1).
Chongqing’sPortOpeningandModernTransformationofTraditionalFinancialIndustry(1891-1937)
LIU Zhi-ying, ZHANG Ge
(1.SchoolofHistoryCulture2.ResearchCenterofChongqingastheGreatRearAreaoftheAnti-JapaneseWar,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Chongqing; draft bank; money shop;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fter Chongqing’s port opening in 1891, the city’s financial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and modern financial industry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has kept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a modern one.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1937, Chongqing’s financial industry, although generally a traditional one, possessed a series of modern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ing the way of a city in western China to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western powers’ infiltration into China’s inner regions.
10.14182/j.cnki.j.anu.2018.01.015
2017-09-20;
2017-11-0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3BZS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SWU1709122)
刘志英(1964-),四川资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金融史;张格(1989-),四川内江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金融史。
F832.37
A
1001-2435(2018)01-0119-09
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