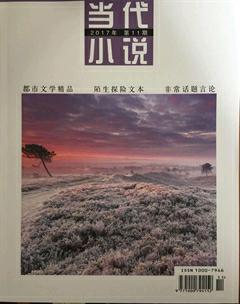危险人物(短篇小说)
邱贵平
严有金瘦如痨病鬼,却什么病也没有,感冒发烧都少有。他的头发自然卷曲,好像生他的时候,母亲子宫带电,被电卷曲了。严有金虽然瘦,眼睛却不小,尤其两个眼珠,又肥又大,白的多于黑的。当他极度兴奋或者愤怒的时候,眼球可以瞪出眼眶5毫米,恐怖至极。
别人瘦,情有可原;严有金瘦,没有天理。严有金是采购员,在石牛水泥厂,除了厂长、财务科长和供销科长,油水最多的就是采购员。那个时代的腐败,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主要体现在大吃大喝上面,基本动口不动手,只吃不捞或者只吃少捞。人民群众对腐败的认识相当朴素,当一个老百姓怀疑一个官员是否腐败时,其身材肥瘦是重要衡量标准。在人民生活尚未提高到大鱼大肉一吃就腻的水平之前,这条标准是很管用的。石牛水泥厂历任厂长、财务科长、供销科长乃至司务长,一个个吃得肥肥胖胖,有的像家鹅,有的像企鹅。有的人不仅嘴上吃,手上还捞,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年采购员几多人民币。严有金只要年均贪污个两三千,十六年下来也有三四万,那个年代的三四万块,可是大钱。
纵然火眼金睛,难从严有金身上发现丝毫腐败迹象:穿粗布喝粗茶,饮淡酒吃淡饭,不嫖不赌,唯独对政治感兴趣,好谈国事。
严有金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老婆病退在家,每月拿百分之四十的工资,负担很重。但大家都认为这点负担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直到上大学的女儿因为没钱吃饭而坐台的消息传出,才相信他是个好同志,不是装穷。
严有金老婆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女儿不久,莫名其妙瘫了,不是全瘫,是偏瘫,左脚不太听使唤,走路影响不大,上坡尤其上楼梯,困难较大,每上一级楼梯,得停下来,双手抓住左大腿,将其托上台阶,如此周而复始。轻瘫不下火线的她,厚着脸皮坚守在幼儿园保育员岗位上。不幸的是,女儿十三岁的时候,她的右脚开始萎缩,必须借助凳子才能直立行走,不得不病退。幸好严有金母亲身子骨硬朗,尚可照料一家生活起居。
老婆行走虽然不便,严有金工资却由她领取。每到发工资那天,她便扶着高脚板凳,一步一个脚印,气喘吁吁来到出纳室。
一个进厂不久、喜欢招蜂惹蝶的出纳,不知深浅,好心劝她:“阿姨,你腿脚不方便,老严叔是个老实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严有金老婆好心当驴肝肺,从牙缝蹦出三个臭烘烘的字:“臭婊子!”
“你说我什么?”
“臭婊子!”
出纳打量了她几眼,一字一句道:“你有病,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严有金老婆猛地把凳子一跺:“我是有病,也比你丑,可是我比你干净!”
“你不仅身体上有病,心里面也有病!”出纳说完,扭着陡峭的屁股,转身疾步而去,高高的鞋跟马蹄般叩击着地面。
严有金老婆不甘心,扶着凳子疾跄几步,使出全身力气,将凳子朝出纳砸去。与此同时,失去支撑的她颓然倒地,坐在地上破口大骂。
严有金坐在办公室,大气不敢出,一支接一支抽着香烟。
严有金老婆骂够骂累,自己扶着板凳回去了。
从那以后,排队领工资的人一见她大驾光临,主动让其先领。严有金老婆得意洋洋对严有金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做人嘛,还是要强一点。”严有金怕老婆怕到骨髓,一切唯老婆马首是瞻,老婆的话无论对错,不管自己真心还是违心,表面上无不赞同:“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毛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无论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道理是一样的。”
发不出工资的日子里,严有金老婆坐在财务室门口,祥林嫂般絮絮叨叨:“好端端的厂子,怎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呢,你们这些当官的,干什么吃的……”
严有金如果在办公室里,依然大气不敢出,一支接一支抽着香烟。
严有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头跑,除了港澳台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全国各地跑遍了。
段子是严有金每次出差回来必带的“特产”,大多和政治有关。没有网络和手机的时代,段子主要靠口头传送。严有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段子自然最多也最新鲜。比如苏联解体之后,他就带回一个有关戈尔巴乔夫和撒切尔夫人的经典段子。
这个段子后来广为流传,政治色彩却渐渐消褪。但在当时,传播这种段子是要冒风险的,其效果也是震撼性的,大家对他益加刮目相看。严有金很有成就感,感觉良好之际,厂党支部书记突然找他谈话,给予严厉批评,严正警告他这样下去很危险,赶紧悬崖勒马。幸好他不是党员,否则即使不留党察看,也要记大过。
严有金并不一味充当传声筒,偶尔也有独到见解,比如针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热和苏联解体,恰到好处引用了四句毛诗。前面两句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后两句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随后,严有金高度总结道,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啊,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变色,让我国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这些国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这也使我国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压的对象……
“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和“当前的国内形势不容乐观”,是严有金议论时政的口头禅。
严有金喜欢读书看报,尤喜政要秘聞外传,报纸嘛,主要看时事新闻。严有金最爱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有瘾,一天不看寝食不安,出差在外,到了对方单位,第一要事是找《参考消息》。订阅《参考消息》,是每个单位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待遇。严有金东奔西走,无论身在何处,每天基本能看上《参考消息》,在厂里看《参考消息》反而困难一些。厂里订了两份(厂长室和阅览室各一份)《参考消息》,想占为己有的读者有好几位,往往报纸还没送到厂长室和阅览室,就被截留。
门卫兼收发员,是个极不负责任的老家伙,信件都敢乱丢,自然不在乎一两张报纸,谁对他好,他就把《参考消息》送给谁。严有金无疑是对门卫最好的人,门卫给了严有金多少张《参考消息》,严有金就给了门卫多少根香烟。
严有金不往外跑的时候,常有本地或外地业务员上门推销零件和设备,业务员为了套近乎,不停递烟,一天下来收获可观。为了方便收集香烟,严有金特意从隔壁技术科要来一张绘图板,架在桌面上。绘图板有角度,一边低一边高,低的那边对着抽屉,业务员香烟往绘图板上一扔,香烟便自动滚到拉开的抽屉里。
我当上通讯员后,报纸由我收发,严有金使劲和我套起近乎来。我不会抽烟,严有金又拿不出、也舍不得拿出其它糖衣炮彈,就一个劲夸我,夸我长得英俊,工作认真,上进心强。
如果厂办主任这么夸,我会心花怒放。厂办主任是我的最高领导,他的评价,将直接影响我的去留。通讯员一般干个三两年,最多五年,必须转岗,否则干油条了。评价好,我有可能留在行政,至少可以去化验室;评价不好,就得去车间吃粉尘。石牛水泥厂生产车间的粉尘,密度和浓度跟如今北京的雾霾差不多,但直径要比PM2.5大得多,少说PM5.0。
严有金算什么呀,连个主任科员都不是,人微言轻,夸了等于没夸。何况夸我工作认真、上进心强的人不止他一个。夸我长得英俊,倒是只有他一个,可当时我尚未成年,并不在意自己的长相。营养不良致使我发育迟缓,又黑又瘦又小又矮,看上去像个非洲难民。许多人一看到我,忍不住伸出手摸我的头。他们摸我的头,也许是表示亲昵,对我来说却是一种屈辱,但我并不怪他们,要怪就怪自己身材落后,地位低下。马善被人骑,人矮(小)被人摸,要是我长得人高马大,谁敢摸我?想摸也摸不着。即使我永远长不高,只要转了正,成为石牛水泥厂真正的主人翁,也没人敢摸我。
如果说严有金夸我工作认真上进心强,是马屁拍在马尾上。夸我长得英俊,则是马屁拍到马腿上。这么一来,别说当天到的《参考消息》,前几天的《参考消息》,严有金也休想看到。我当通讯员的时候,阅览室不再订阅《参考消息》,这意味着严有金东方和西方都不亮了,要想看《参考消息》,尤其要想第一个看,只能通过我这里。
一般情况下,我是这么处理《参考消息》的:邮递员把报纸送来,我先把《参考消息》锁进抽屉,分发完毕其它报纸,再把它拿给和我关系最好的人先睹为快。这个人看完后,又转给另一个和他关系好的人,报纸回到我手中,已经成为晚报,有时索性有去无回。好在厂长和办公室主任他们没时间看报纸,对《参考消息》不太感兴趣,这才给了我“以权谋私”的机会。
那些如饥似渴《参考消息》的人,估摸邮递员快到了,集体守候在我办公室兼卧室翘首以盼,口头马不停蹄巴结着我。
有一天,严有金突然夸我毛笔字写得好。我一有空就在报纸上练书法,给大家造成好学的印象或者错觉。也许是我的毛笔字写得太难看,还没有人这么昧良心夸过我,严有金是第一个。严有金这个马屁拍得很到位,一拍拍到屁眼上,爽死我了,第二天他一跃成为《参考消息》首席读者。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把兴趣转移到写作上,书法是我最大的爱好,成为一字千金的书法家,是我最大的梦想。
严有金夸我不久,把他亲戚——一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介绍给了我,在书法家悉心指导之下,我的书艺突飞猛进,说我毛笔字写得好的人越来越多,连厂办主任和厂长都这么说。与此同时,我和严有金的关系越来越铁,《参考消息》几乎成了他的专供,即使出差,我也帮他留着。
我转岗化验室后,严有金看《参考消息》困难多了。我的接班人是个职业道德低下的小青年,经常把报纸随意送人,尤其《参考消息》。
几年后,我当上厂办秘书,严有金仿佛他乡遇故知,握着我的手摇了又摇晃了又晃,而且提前给我升了一级,不叫小邱或者邱秘书,直接叫邱主任。
严有金第一个叫我邱主任,好比当年他第一个夸我的毛笔字写得好,让我非常受用。我虽然不是办公室主任,领导通讯员的权力还是有的,我告诉通讯员,我很爱看《参考消息》,你每天必须把《参考消息》准时送到我手上,否则算你工作失职。我领导之下的这位通讯员,是石牛水泥厂第五任通讯员,我既是领导又是祖师爷,说话还是有分量的。我一发话,严有金读报就有保障。
高尔基看见书籍就像看见面包;出差回来的严有金,看见《参考消息》就像看见肉包。当年出差全是坐火车,出远差一坐几天几夜,火车上看不到《参考消息》,回到厂里,严有金的当务之急,是到我办公室看《参考消息》,同时汇报最新的政治段子。
除了《参考消息》,每晚中央、本省、本市新闻联播,严有金也是必看的。如果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新闻,第二天一上班,他便端着茶垢斑斑的茶杯,无声无息走到你跟前,递上一支烟,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突然扯一下你的袖子,把瘦如面片的嘴脸凑到你耳旁,眨巴着白色恐怖的大眼球,用神秘低沉的口气问你,昨天晚上看新闻没有?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啊。如果你说有但没注意,他就循循善诱;如果你说没有,他就不无遗憾地摇头,然后娓娓道来。反正他不把自己的发现说出来,胃就胀心就闷神就慌坐立就不安。
至于本厂和本市人事变动,他更是兴趣浓厚,一有风吹草动,他的小道消息即上升到国际国内形势的高度问世。
某天,上任不久、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来厂里指导工作。副县长指导完工作,正要上车离去,恰好被从街上采购回来的严有金撞见,严有金双眼大放光芒,仿佛看见失散多年的亲人,手忙脚乱停下自行车,自行车没支好倒在地上,他也不管,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双手紧紧握住副县长的手,声情并茂道:“县长,您好您好!”
副县长迟疑地望着他:“你是?”
“我是严有金啊,您初中同学。”
见副县长没什么反应,一旁的厂长赶紧解释:“严有金是厂里的采购员,很不错的一个同志。”
副县长这才哦了一声,说了声辛苦,上车走了。
一起回办公室的时候,厂长乜着眼睛问严有金:“妈个巴子,你平常不是老说,副县长是你最要好的初中同学么,他怎么不认识你。”
严有金嘿嘿干笑几声:“我们同校不同班同楼不同级,他低我一届,是学习尖子,全校有名,无人不知。当领导的日理万机,记不住我不奇怪。”
严有金说完,掏出一支香烟小心翼翼递上。厂长很不情愿接过,瞄了一眼牌子,嗯了一声,把香烟掉了个头,严有金握着打火机的手,伸出一半又缩了回来。
厂长突然说了句,看你那手脏的,手指微微一掐,香烟断了,然后大踏步走向厂长室,一进办公室,把断成两截的香烟扔进废纸篓,朝里面吐了口浓痰。
严有金刚才上街采购螺栓,选货时手上沾了不少机油和铁锈。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严有金何尝不想混个一官半职,在老婆面前扬眉吐气,可是十几年下来,连个主任科员也没混上。他是个套狼舍不得孩子、生孩子舍不得贞操的人,平时见了厂长温良恭俭让,老实得像个三好学生,又是递烟又是倒水,关键时刻从不往厂长家里跑。严有金总希望厂长能够良心发现,甚至幻想通过自己和副县长虚无飘渺的同学关系,使厂长对他刮目相看。可是,厂长换了一任又一任,没有一个良心发现者。平心而论,厂长们并没有昧良心,一朝君子一朝臣,石牛水泥厂主任科长换了不少,他这个采购员却是万里长城永不倒。
严有金只好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副科长。
除了厂长,严有金是石牛水泥厂电话最多的人。上世纪80年代,通讯还很落后,打电话必须通过四楼总机转接,除了厂长室、销售科和保卫科,一般科室不安装外线电话。严有金办公室在二楼,和厂长室仅三墙之隔,凡是找他的电话,接线员大都转到厂长室。好长一段时间,电话那头指名道姓找严有金。有一阵子,情况发生了变化,找严有金的电话越来越少,找严科长的电话越来越多。
开始,接线员觉得纳闷:“我们生产设备科只有一个王科长,没有严科长,你有没有搞错?”
电话那头强调:“不会错啦,严有金副科长,名片上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哦,我明白了。”
接线员于是把电话转到厂长室,厂长室那天正好没人,对方又有急事,她只好放下耳机,走到走廊上大叫:“严科长,长途!”
严有金恰好不在办公室,大伙听到了,很好奇:“严科长?哪个严科长?”
“严有金科长啊。”接线员说完,捂着嘴直笑。
于是,大伙便一起叫:“严科长,长途!”
没有回答,大伙又叫:“严科长不在!”
不一会儿,严有金上街采购回来,大伙争先恐后告诉他:“严科长,刚才有你的长途!”
“严科长,你终于回来了,刚才有好几个长途电话找你。”
“老严,科长都当上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怎么事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严有金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这些鸟人,有奶就是娘,只要你买他的东西,叫你爸爸都可以。我可不吃這一套,质量不过关,别说叫我严科长,就是跪下来叫我爷爷也没有用。”
“严科长,你可真是铁面无私啊。”
“那当然,严科长这个姓可不是白姓的,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拒腐蚀永不沾,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严科长,什么时候请客啊?”
“请什么客?”
“庆祝你荣升科长啊。”
从那以后,大家都叫严有金为严科长,厂长都这么叫。开始,严有金脸上的表情还不太自然,久之坦然,偶尔叫严有金,反而不高兴。
名片流行起来后,石牛水泥厂二层领导全部用公款印制了名片,严有金是采购员,情况特殊,也印了。名片由办公室统一到印刷厂印制,严有金名片上的头衔是采购员。严有金自己掏钱印了一盒,给自己安了个生产设备科副科长职务。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只要正职不在场,称呼副职的时候肯定把副字省略。印名片前不久,生产设备科副科长调走了,严有金原以为能当上副科长,厂里也这么传闻,他便提前在名片上当起了副科长。没想到名片印好不到一个季度,副科长被别人当去了。
严有金只好继续当他的虚拟副科长。
石牛水泥厂股份制改造期间,严有金错误估计形势,站在被工人讥笑为“刘草包”的刘副厂长一边。厂长因贪污货款下台,刘副厂长小人得志,暂时主持工作。几个月后,另一位姓吕的副厂长被任命为厂长,刘草包继续当他的副厂长。一年后,吕厂长在推行股份制过程中出现偏差,上级不仅不承认第一次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还撤销了吕的厂长和“改制工作小组”副组长职务,保留其“改制工作小组”成员身份,责令其配合改制小组和刘草包的工作。
在改制小组的强硬领导下,再度主持工作的刘草包,不择手段推行股份制。刘草包要想真正统治石牛水泥厂,必须当选为董事长,打算东山再起的吕厂长是他唯一的竞争对手。
刘草包只有小学文化,酒量大于肚量,体力大于能力,威信逊于威风,只好贿选,严有金是重点贿选对象之一。刘草包不仅借了一千元股金给严有金,还答应他,只要自己选上董事长,马上提拔他为生产设备科副科长,了却他多年心愿,科长退休后,还可以让他更上一层楼。
科长已经五十八点六岁,曙光在前头。那阵子,严有金容光焕发,逢人就说刘草包好话,把刘草包说成刘金包。在说刘草包好话的同时,必说吕厂长坏话,但严有金不直接说,而是间接说吕厂长太年轻,年轻人容易感情用事,不懂政治。
吕厂长一上任,提拔我为厂办主任,我当然是吕厂长的人。严有金站到吕厂长对立面,等于站到我对立面,我虽然没有和他撕破脸皮,但他再也不是《参考消息》的首席读者了。
有一次,我忍不住警告他:“严科长,你不要鼠目寸光。”
严有金笑了笑:“小邱,你虽然年轻,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道理,不至于不懂吧?”
他居然叫我小邱,我非常不爽:“严有金,你活了一大把年纪,‘笑到最后才是胜利者,这句话你应该听说过吧?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严有金依然笑着,把手放到我肩上:“小邱,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没有利益冲突,和为贵,你说是吧?”
我冷冷地拨开他的手:“道不同,不相为谋。”
严有金叹了口气:“唉,国际国内形势不容乐观啊。”
吕厂长果然东山再起,可是,石牛水泥厂却无法东山再起,股份制把厂子搞得元气大伤,把大伙搞得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厂倒人散了。
严有金连虚拟科长也没得当了。
下岗后,我到福州打了半年工,回来当上了自由撰稿人,基本闭门不出,国家大事,我通过电视和网络了解得很及时,县城里发生的事,我却知之甚少,偶尔上一趟街,竟然惊叹其翻天覆地的变化。
严有金不住在厂里,下岗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他,不过,有关他的情况,我还是陆续从工友口中得知一些。下岗那天,严有金痛哭流涕:“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啊,国际上,日本首相不顾亚洲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执迷不悟地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亚洲金融危机还在加深;国内,物价不断上涨,农民收入持续下降,下岗失业人员成倍增长,天灾人祸频频发生。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说下岗就下岗了,我心里难受啊。毛主席说得好,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我虽然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可我这颗太阳还没有落山嘛,还满目青山夕照明嘛。你们不能让我下岗啊,我下了岗一家子吃什么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下岗后的严有金,开始是找不到事干,后来是找到事不能干,大多时间呆在家里,或闭目养神,或埋头电视,每晚的中央和本省本市新闻联播以及每周三次的本县新闻是必定要看的,分析彩票和股票一样分析国际国内、省里市里县里的形势,依然是他的最爱。此外,到县图书馆看《参考消息》,也是严有金每天必做的功课。在前往图书馆和从图书馆返回的路上,严有金的脚步十分緩慢沉重,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探头探脑,一个挨一个盯着行人看。看到熟人,妓女般热情地附上来,先递上一张名片(这时他已经正式公开提拔自己为科长,并自费印刷了名片),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之后,把你扯到一旁,脸几乎贴到你鼻梁,两颗黑白混乱的眼珠,怔怔盯着你,口气神秘得像巫师,知道吗?×××出事了,老子早知道他要出事。然后再分析一通国际国内、省里市里县里形势。也不管对方爱不爱听耐烦不耐烦,一说老半天,直说得嘴角冒泡。说话的时候,一直围着你转,谨防逃跑,想走都走不了。
有一回,一个在外地工作、多年未见的同学回家探亲,街上邂逅严有金,严有金并没有认出他。同学不了解他的情况,主动上前打招呼,本想叙叙旧,严有金却把他拉到一旁,环顾四周数遍之后方才开口,一开口就把同学镇住了:陈良宇出事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早知道他要出事,这家伙看上去道貌岸然,贪起来似虎如狼啊。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啊。咳,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啊,由于美国的武力干涉,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世界陷入以暴易暴的混乱局面;国内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贪官前腐后继,要钱不要命……
这谁不知道啊,全国人民都知道。同学发觉不对头,头皮发麻,拔腿而逃。
就在我打算去看看严有金的时候,一工友告诉我,不用了,他已经去闽清了。
闽清是个县城,工友说的闽清,指的是闽清精神病院。闽清精神病院是福建省最大最著名的精神病院,在我们这里,当一个人说另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去闽清时,那一定是说他去闽清精神病院了。
就在我差不多把严有金遗忘的时候,他突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唤醒我的记忆。
严有金在精神病院呆了好些年,治愈出院了。出院后,该吃吃该喝喝,一切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对什么和什么话题都不感兴趣了,包括他热衷的政治和政治话题。他总是一个人呆坐着,雕像一般,不说一句话。即便薄熙来出事,钓鱼岛“国有化”这样轰轰烈烈的重大政治事件,他也不置一喙,无动于衷。
严有金的母亲已经死了,老婆的健康大有好转,左腿虽未完全康复,却摆脱了板凳,在不借助任何工具的前提下,重新直立行走,左脚上楼梯也无需借助双手,只是速度慢些。总而言之,越活越精神。这缘于儿子混得一官半职,女儿找了个大她十几岁的有钱女婿,严有金家里终于“有金”而且有权了。金钱对于曾经一穷二白的人,不仅能改善生活,还能活血化瘀。吃好喝好的严有金,很快发福起来,胖得像尊佛陀。
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发生没几天,严有金做了一件轰动全县的大事,他把日本人给污辱了。
小县城山高皇帝远,哪来日本人?这您就有所不知了,小县城虽然偏僻,却是绿色腹地,这些年大力开发有机食品,小有名气,笋产品更是名播日本,出口以来供不应求。南方遍地是笋,笋产品多去了,没啥稀奇。稀奇的是,其他地方出产的笋,皆是黄的;小县城出产的笋,是白的,天然纯白,少女肌肤一样白,口感比黄笋好,品相比黄笋佳。物以稀为贵,日本人喜欢得要命,客商经常到县里最大的笋加工厂参观考察。春笋上市时,加工鲜春笋系列产品;春笋下市后,加工笋干系列产品;冬笋上市时,加工鲜冬笋系列产品,一年到头都在生产。
那天正好有一日商前来参观考察,严有金不知哪里得来的准确消息,蹲守在日商下榻的星级酒店,当西装革履的日商参观完工厂,在相关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酒店之际,严有金突然蹿出,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包报纸包着的辣椒酱,奋力向日商脸上掷去,嘴里同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日本滚出中国去……
毫无防备的日商,被掷了个正着,辣得他哇哇大叫。
顺便提一句,辣椒酱也是小县城的特色有机食品,虽然不像白笋罐头那么有名,也没有出口,在省内却很有名气。还有,包辣椒酱的那张报纸,居然是《参考消息》,头版头条正是钓鱼岛“国有化”的报道。
事后,严有金被迫重返闽清,这一次,怕是回不来了……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