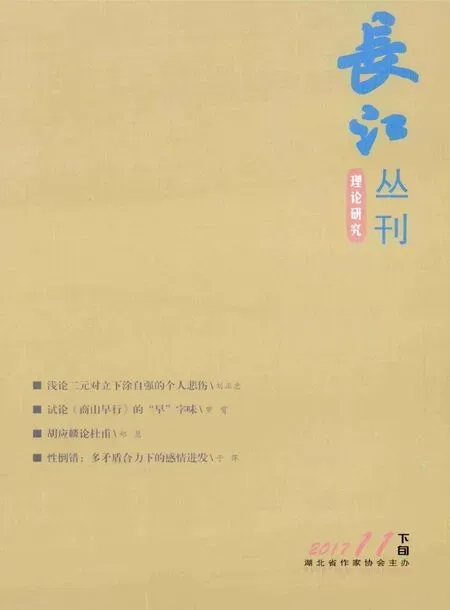为母亲洗头
李小坪
母亲在这个夏天住进了医院。
印象中,这是母亲第一次住院,她很害怕。那些害怕写在脸上,她不懂得隐藏,也不需隐藏。脑埂塞、心脏病、胃病、颈椎病,都是一点一滴的岁月囤积,到了临界点便爆发出来。服老,是她需要修习的课程了。她被安放在市中医医院内科10病室34号床上,是加塞的一个铺位。现在,她已由农妇身份转变为病人角色,在弥漫着来苏水、药物、还有各种体味、汗臭味的空间里,听从医生的安排与发落,以对抗那漫无边际的病痛与衰颓。
看着母亲,我突然感到她的病与老来得太快,感到岁月妄图拿走我所剩不多的拥有,感到自己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许多感情没有表达。三年前,这世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她在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那眼神,将我的心扯得生疼。她是我的外婆。我用了很久的时间与很大的力量,才从那份伤痛与无力中拔出生气来。
对于母亲,大约由于我觉得她跟多数母亲的形象有些异样,始终只能保持一份谦恭与客套。我知道这样不好,却莫名地倔强着。外婆是跟母亲不同的,她劳苦一辈子,乐观,从容,慈爱,坚定,不乱发脾气,不轻易落泪。外婆带过我,都说我继承了外婆的长相、脾性乃至部分的命途。母亲似乎一直在外婆、丈夫和子女的夹缝中生活,她随时会发作小脾气,大家谁都顺着她,维护她的盲目骄傲与自信,只要她高兴。
成了病人,母亲开始在生活上学会忍受,但别的都能忍,唯有洗头这件事她忍受不了。她让我把耳朵送到她面前,十分严重地对我说:你侄女今天闻了我头发好几次,肯定是嫌我臭了,我要洗头。说完,还模拟了侄女闻她头发时鼻腔里发出的夸张怪声。可病房是狭小的,只能提供病人躺卧的床位与行走的窄道,有时探视的人来多几个,连插足之地也没有,洗头显然很不方便。我说,那我就送你去洗头房洗吧。母亲摇头,说不去,不喜欢别人洗头,平时都是你爸爸给我洗的。
我心里不由一惊。
由于父亲回了乡下,我只好跟母亲商量,让我带她去我在城里的家中,给她洗一次头。母亲听了,显得犹豫,分明是怕我不习惯与她亲近,却说免得给我添麻烦。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我偏不依,牵了她的手,走出中医院,慢慢往我住的小区走。一会儿,我忽然感到母亲也在用劲抓住我的手,好像生怕我在半路上把她丢进了洗头房。
18年前,我叛逆地离开父母,落户这座城市,以对生活一无所知的盲目,一头扎进自以为安稳的柴米油盐里。当生活向我敞开许多不堪的真实面目时,我又不得不以决绝的姿态告别自己选择的生活。那时,我或许的确固执而冷漠,母亲看得见我的表面,却不知道我内心里掩埋了多少伤心的隐秘。可我没必要告诉她什么。告诉了她,又能怎么样呢?让她保持一个普通农妇无忧无虑的快乐、或者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得到的三方优待便好。当然,我也拒绝向她和父亲表达歉意与内疚。
在我心里,“坚强”地与他们划清了一条界限。
偶尔会做梦,梦见我抱着母亲睡觉,就像七八岁时的样子。醒来,母亲摸着我的小脸,问你怎么只有下巴像我呢……
热水放好,帮母亲解开高高挽起的发髻,头发便缓缓飘散开来。
母亲站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的脸。我从侧面看她,心里惊叹:这哪里是一位农妇?67岁的人了,脸上的皮肤光润而饱满。但我知道,母亲一生只用过白雀灵与大宝,一切都因为她的家人带给她的岁月不曾为难她。她还坚持蓄着长头发,这在做农活的妇女中,是难得一见的。她的头发向来柔韧顺畅,到现在居然找不出几根白发来。飘逸的长发伴随母亲一生,那是她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记忆中,母亲剪短过一次头发。有一阵子,村里的女人都把头发剪了卖钱,母亲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也这么做了。我不知道母亲的那把头发换了多少钱,只记得那个收头发的人没把母亲的头发剪齐,母亲嗔怪他剪得像被狗啃的一样。好长时间,母亲出门进门都戴着帽子。到了冬天,她的头发勉强可以扎成一个小揪揪,但她很少出门。
母亲坐到凳子上,静静的,很乖,像个小学生似的。我给她的头发湿水,上洗发液,轻轻地揉搓。母亲的头发很密,发质有劲,捏在手里,能感觉它们不曾经历过摧折与慌乱。相反,我的头发总是容易分叉断脱,一派营养不良的样子。头发洗到一半,母亲轻声问,还有异味吗?我说本来也没有呀。母亲和我,彼此习惯了保持羞涩与客气的距离感,甚至隐约带有歉意。我把她头发上的泡沫抹掉,开始给她轻按头皮……
这时,母亲闭上眼,嘴里喃喃道:真舒服。
洗完头,我用吹风机帮她吹干头发,她的身体不经意地靠着了我。我心里不由一柔:原以为自己拒绝任何形式的亲近,其实也渴望亲切的被依靠与依靠啊!
母亲开始说话,说到底是姑娘,手好轻的。接着就描述父亲给她洗头的情形:总是不耐烦地嚷嚷着,咕哝咕哝地嫌弃着,但一边还得蹲下身,帮她一遍又一遍地洗,一遍一遍地冲,用毛巾帮她把头发包好,再用吹风机吹干。母亲笑了一下,说你父亲的手指头抠在头皮上,像钉耙一样,抓得人生疼。
我脑子浮出父亲给母亲洗头的画面:父亲不耐烦,母亲抱怨,空气中弥漫着洗发液的香味……春天的花朵在开放,秋天的果实挂在枝头。小的时候,父亲也给我洗过头,那时我也被他的大手洗的头皮生疼,我一边跺脚,一边哭嚷,像是被屠杀似的。他还帮我梳头,扎辫子,用橡皮筋狠劲地缠,我的眼睛会因为头发勒得太紧,显得更细更小,我烦他,他却憨憨地笑。
母亲小的时候,家中的生活在乡下算是好的。因为外公在航运公司上班,每月有固定的收入;再加上常跑江湖,见多识广,思想也开化。这样,母亲便在乡村的环境中养成了固执的骄傲与优越感。可惜,外公早逝,家道中落,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母亲带着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心理,变得敏感起来。她一边骄傲,一边自卑;一边倔强,一边气馁。关于婚姻,她认定她的丈夫绝对不能是村里的村长与会计之类。
一路挑挑拣拣,一晃就到了25岁,母亲遇见父亲。父亲高大帅气,是那个时代不多的端铁饭碗的骄傲青年;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一生会和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女子发生关联。那个秋天的下午,父亲陪他的同事回家,遇到一场大雨,避雨到了母亲家中。母亲在屋里纳鞋底,父亲向母亲借雨伞,这一借加上后来的一还,两人就在一起过了一生。
父亲年轻时,是讨女孩子喜欢的。母亲曾经多次数落,每次她去父亲的单位,总有女人莫名其妙地对她说些酸话,她听得懂,又听不出所以然;父亲信誓旦旦,她信,却愤愤地想骂人。可以想象,母亲要骂人,而那个脏字跑不出喉咙眼时,脸色憋得像泼了猪血。村里也不消停,有女人说,作为乡村妇女的我母亲配不上我父亲。面对危机,母亲的方法也简单,抛下农活,带着我和哥哥,一路转车转船,“空降”到达父亲的单位宿舍,住上几天。父亲明白,为了让母亲安心,每月的工资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后,及时向母亲颗粒归仓。
生活总是到处漏风。有一次,我见到母亲抹着眼泪回家。那时候我还小,不知事。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天她带着哥哥去学校报名,一个曾喜欢过父亲的女人不屑地对她说,瞧你儿子长得那么好看,你这副样子,应该感到羞耻。羞耻!多么严重而恶毒的字眼。从此,“羞耻”二字伴随了母亲大半辈子。只要有机会,她就爱拿这件事在父亲面前念叨,以期得到父亲的再次安慰。父亲傻傻地笑,说都过去了。
因为“羞耻”,母亲有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向父亲表达怨怼,并确立存在感。大约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母亲抱着我跟随父亲走亲戚,半道上争吵起来,母亲突然将我放在公路中间后拔腿就跑,父亲一边急着抢回我,一边还得去“抓”着母亲。这事,是父亲后来当笑话讲给我听的,我曾在许多的深夜里浮想那个场景:在空旷的乡村公路上,年轻的父亲咬着牙,不吭声,奔跑着,一手稳稳地抱着我,一把抓住倔强的母亲……
母亲的心情一度似乎坏到极点。她想到了“死”。她藏了很多药品,她还喜欢一个人跑到水边发呆静坐,父亲为此十分惶恐。好多次,无助的父亲找到我,说得眼泪直流。一个那么骄傲的男人,面对一个缺乏智慧而仅有爱的妻子,除了体谅,便是小心伺候。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每次与父亲争吵,后来都以父亲认输告终。他搞不懂母亲为什么老是无端生气,他一直担心母亲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而且,父亲是上门女婿,是一个把命运交给异乡的人,他的内心注定了孤独。当年,外婆将母亲留在家里招女婿,是希望女婿帮助照顾抚养几个未成年的弟妹,这样也给母亲带来了获得无尽宽容的地位。
记忆中的很多个夏夜,繁星满天,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家来,这是我和哥哥的节日。父亲的包里,必有书本和糖果,有时候还会有一件花衣服。可是,我们的节日里总是听到母亲与父亲的争吵。有一次,母亲大声赶父亲滚,滚得越远越好。父亲没有“滚”,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稻场边上,闷声不响地抽烟,烟火忽明忽暗。我慢慢走向父亲,像小狗一样蹲在他的身边,也不说话。那样的时候,蹲在父亲身边是我的本能:父亲能滚到哪里去呢?他远离父母与故土,这个家不爱他,他就没有家了。
父亲进到这个大家庭时,我的三个姨都未成年,舅舅才五岁。有很多次机会,父亲可以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到城里去住的,但是母亲不允许。她留在家里招女婿,最大责任就是把几个弟妹抚养成人,而且这个任务只有靠父亲来完成。父亲依了她。后来三个姨先后读书、嫁人,都是父亲一手操持的。而舅舅读完高中,又读中专,父亲更是像他的长辈一样,行使家长的职责,给他报名,交学费。实际上,他们的年龄差别也像是两辈人。秋季的一天,父亲去给在卫校读书的舅舅送被子,当父亲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班上的同学们叫喊我舅舅,说你老爹来了,舅舅窘得没办法,父亲更是不知所措。
母亲毕竟以她的“手段”获得了成功。父亲头上的白发、脚上的泥土、手上的硬茧以及肩头被扁担磨破的皮肉,都是母亲可以握在手里的生活。疼与暖贯通在岁月里,父亲早已认命,只是越来越沉默。能听到父亲轻松说话,能看到父亲笑一次,是我儿时最大的心愿。而父亲沉默着的脸,也是让母亲不高兴的理由。在母亲眼里,父亲不笑,便是对家人的嫌弃。她不知道,父亲很累,已失去微笑的力气。
长大后,我心里时时不买生活的帐,我希望自己的点滴理解与疼爱,能够让父亲过得稍微快乐一些。我不允许任何人说父亲的坏话,尤其是我的舅舅和姨们,惹恼了我,我便翻脸不认人地训斥他们。父亲由此认定我是这世上唯一能理解和体谅他的人,但他从未用言语表达。有一次,我离家很久后回去,他没来由的说了一句:你一回来啊,我怎么就感觉浑身舒坦呢?
于是母亲开始对我有意见了。
她认为我对她不好,遇事总偏袒父亲。有一次,她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在文章里写了不爱她、恨她的话,将我骂得不知所措,还要我解释清楚她到底哪里得罪了我这个小祖宗。当时,我一人坐在书房,将手机开成免提,清晰地听着母亲恨恨地咒骂自己,惊讶中,没有争辩,也不解释,唯有泪如雨下。其实,在那篇小文中,我也曲意表现了她的质朴与善意,是她还嫌不够。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家里联系。亲情有时和爱情一样,一旦有说不清的情绪横亘在彼此心里,怎么开口,如何开口,又该说些什么,真的是隔一座山。可是,有一天,母亲突然打通我的电话,小心翼翼地问:小坪,你真的不理我了吗?我按捺住内心的慌乱,连声回道:没有啊没有啊,妈!
母亲的“低头”倒让我有些于心不忍。外婆在世86岁,将她这个宝贝女儿心疼了63年:未老的时候帮母亲包揽家里地里的大部分活路,老了则为母亲管一日三餐;生活中有太多凶险,外婆为了不让母亲受到欺辱,曾经叉着腰骂人,甚至跟人打过架。母亲在外婆的荫庇下做了63年的女儿,这是多么奢侈的人生!三年前的冬天,外婆走了,母亲病了三个月……
但是,家事不断,我与母亲的关系并没有从此柳暗花明。
比如,如何处理婆媳关系,母亲很是焦灼。因为她没有做过媳妇,缺乏媳妇的立场与角度,时常弄出磕碰。外婆在时,会时时帮她宽心,将一些矛盾处理得非常妥贴。外婆不在了,许多的问题让母亲束手无策。而我总是试着以做过几年儿媳妇的经验劝她学会体谅、宽容与放手。可她认为我的立场有问题,觉得生活处处在为难她。哥哥嫂子想要搬出去住,她不同意,认为小两口带不好孙女,会吵架,会把一个小家搞砸锅。由于哥嫂很坚持,她开始向亲戚朋友诉苦,直到升级为很老一套:去水边发呆静坐,莫名其妙地流泪。我自以为是个清醒的旁观者,却不宜插言,只能暗暗给哥嫂打气,建议他们尽量安抚母亲,但不要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母亲不傻,很快判定是我在背后给哥嫂出主意。一天清晨,我正要出门去上班,她突然来了,进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黑脸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慌,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这么对恃了好久,她猛然发飚:你以为你读了几句书就了不起了,你跟他们合起来欺负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她已站起来,准备夺门而跑。这下,积攒在我心里的火气终于点燃了,一把抓住她,开始一阵噼哩啪啦大喊。那天,我像她一样任性,吼过,哭过,嗓子都喊哑了。我把这些年对她的所有不满都说给她听,告诉她她每次任性的耍脾气让我们有多为难,问她为什么就不能体谅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我甚至指责她,作为一个女人她有多幸福,为什么不知足……我的态度突转使她大为惊讶,她被震住了,然后,听话地由我牵回到沙发上坐下。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可我心里一点都不爽,反而隐隐地疼痛:如果外婆在天有灵,得悉我对她的宝贝女儿进行责备与怒吼,会不会回来狠狠揍我一顿?
不久,哥嫂的房子装修好了,很快就真的要搬出去了。母亲没再反对,只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哪里都疼,而且心里乱七八糟的。她给我打电话,说真是恨不得我哥嫂马上搬走,她侍候得烦;一会儿又唠叨他们不会过日子,让人不放心。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不舒服,父亲就陪她来市中医医院检查,一查,到处都是小毛病。父亲说,那就去住院休养几天吧。
洗完头,母亲坐在阳台上,傍晚的微风,轻轻撩起她的发丝。她用我的手机给父亲打通了电话,开始压低声音讲话,竟然带着几分温柔。我听不到电话那头的父亲在说什么,但听得见母亲的回应:知道知道,按时吃药,听医生的话,你放心。接着,母亲以“领导”的口气问起家里的猫猫狗狗、两头小猪仔和菜园地里的情况,却是反复叮嘱父亲不要太累,太阳大了千万不要下地干活,免得中暑。大约父亲说到给母亲洗头的事,母亲笑呵呵地说:洗啦洗啦,是姑娘给我洗的,你不用专程赶来洗头。
我站在门边,听着分别几日的母亲与父亲对话,突然发现,在母亲和父亲之间,许多看不见的情意,早已经由箪食瓢饮种在了彼此的骨头里;而那些被生活逼迫出来的慌乱、争吵、诅咒与抱怨,或许一直都是他们在努力打掉的残枝败叶……
同事打来电话,嗔怪手机老是占线,我说,我父母在电话里谈恋爱呢。
偷听了母亲与父亲的电话,再想起母亲的偏执与倔强,便油然而笑:如果母亲去商场看中某件衣服,父亲第一时间不给她买,她便会像个小女孩一样的生气,再买给她,她是坚决不要了的;若是买来的衣服颜色和款式不对她的味口,她是一定要换掉的,哪怕调换的过程好麻烦,她也宁愿看到父亲为了她而不怕麻烦。
父亲真的磨炼到了以默默服从为享受吗?
有一次,父亲陪母亲逛街,到了午餐的时候,打电话叫上我一起吃午饭,吃着吃着,不知道什么原因,母亲突然不说话了,闷闷地吃着,眼看着眼泪就要掉下来。我不解,看父亲,父亲朝我眨眼,我便不作声。等吃完饭出了店,母亲仍是赌气似的走在前面,我用眼神问父亲,父亲正欲同我耳语,母亲突然转过身来,父亲立马朝她挤眉弄眼地讨好,母亲本该发火的,却突然噗嗤笑了。
我恍然明白,一直以来,母亲看似从来没有长大,其实她是有方寸、很强大、坚守爱的,她的经营之道就是抗拒成长。我还真是有些羡慕她呢。
父亲和母亲结婚42年时,我动员他们说去拍一套婚纱照吧,父亲不敢同意也不敢反对,决定权在母亲手里。母亲心里有意,面上忸怩着,父亲趁势好说歹说,母亲貌似勉强地同意了。后来照片拿到手,母亲的欢喜果然超出我们的预期。他把照片拿给别人看,看过的人自然夸她漂亮。这一夸,她便飘飘然,说年轻时候那才叫好看呢。而我想起很久以前,想起父亲和母亲站在春天或秋天里,母亲的辫子又粗又长……便不去怀疑她的夸张。
一天,母亲一个人坐车从乡下来城里,送我一套照片,说哪一天她和父亲都走了,让我有个念想。
夜深了,我在书房里看书,母亲轻手轻脚进来,不知所措地观望书架,走拢去翻翻这本,摸摸那本,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自言自语地找话题。然而,这时的我总以为自己正在与真理沟通,总是对外物心不在焉,何况母亲要说的无非是些鸡毛蒜皮,我便有一句没一句应答着。不一会儿,她提高了声音嘀咕道:明天不来了,就在医院住。我不由一惊,放下书,抬头望着她:怎么呢?母亲摇摇头:没什么,你忙。
我的心里顿生歉意,连忙起身,牵了母亲走出书房,去卧室安置她睡觉。然后,我挨着她睡下,期望今晚回到童年。可是,一路走来的往事太重,时空中仿佛依旧弥漫着生疏,我怎么也无法进入梦乡。咬紧牙关熬到半夜,等母亲发出鼾声,我轻悄悄下床,赤着脚回到书房,拿起一本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母亲坐在我身边,对我说,半夜不见我的人影,她去阳台上没找着,吓得她连忙朝楼下张望,后来看到我在书房睡着,才放心了。我说,我都是大人了呢。母亲抬手搭到我肩上,喃喃地自责道: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这么多年,你的婚姻经受了那么多磨难,我什么都没有帮上你。
她的鼻子一訇,我的眼眶也湿了……
可我在心里念着:我的母亲啊,这世上有很多未知的苦恼,你若从不体会,便是最好。你撒娇,你倔强,你委屈,你哭泣,你喜欢买花衣服,你没有读过几本书,你说不出人世间的许多大道理,你一辈子可以像个孩子一样任性……但你的背后一直有宽容与呵护随时伺候,为你的生活缝缝补补。这是你的幸福,也是我们的幸福。
我抚着母亲的长发,对她说:妈,我爱你呢。
而且,这一次我一点也不感到羞涩。
母亲仰起头,眯眯地笑,头发垂到腰际,那么柔顺好看的样子。

李小坪,70后,宜都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第六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有散文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丛刊》《三峡文学》等报刊。有散文集《温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