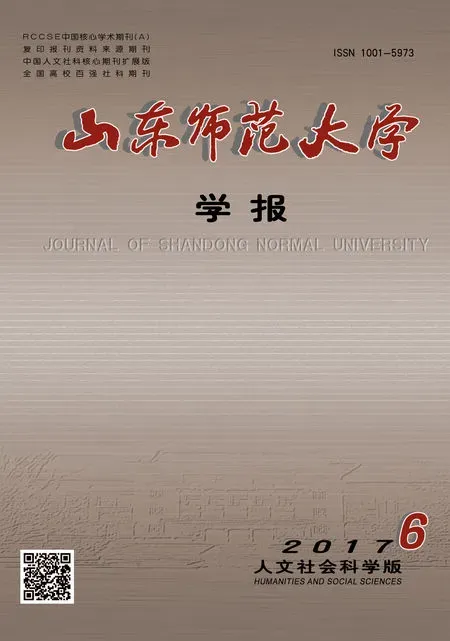诗是生命的表现
——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探微*①
兰希秀
(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48 )
诗是生命的表现
——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探微*①
兰希秀
(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48 )
结合其具体诗词作品来看,方东美的诗学本质论可以概括为:诗(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表现”既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与方法,又指向诗(艺术)审美境界的创构,具有本体意义。“生命”并不是指物质的生命肉体,而指向一种生命精神,方东美称之为“普遍生命”。“普遍生命”的实质是一种以实现生命理想价值为旨归,绵延不息于宇宙中的生命创造力和生命精神;“普遍生命”的五种要义,即是它在时间进程中显示出的“创生”、“广生”、“继生”、“新生”、“恒生”五种功能。
诗学;表现;生命;普遍生命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内学界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展开,被方克立等人列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方东美的思想逐渐为人所关注。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方东美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领域,论域涉及他的比较文化哲学、儒释道观、哲学体系与架构、哲学本体与功能、学术身份定位等问题,而对他的美学思想特别是文艺美学思想却鲜有关注。我们知道,方东美被海内外思想界誉为“诗哲”。这种称号的获得,不仅仅是因为方东美在哲学叙述上的诗化表达方式以及近千首诗词作品的创作实践,更因为方东美哲学与文学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诗学*本文对“诗学”作广义上的理解与使用,涵括文学、艺术等文化范围。美学思想。但这一点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实为遗憾。本文不避浅陋,在综研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与具体诗词作品的基础上,提出方东美的诗学本质论:诗(艺术)是生命的表现。
一
从思维方式上看,一般认为,西方重理性逻辑,中国重直觉感悟,这早已成为学界共识。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折射于文学艺术领域,则产生了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的创作方式的差异,其最终导致了西方在史诗、戏剧、小说、以写实为特征的油画等叙事文学艺术方面强大,而中国在诗、词、以写意为主的水墨画等抒情(言志)文学艺术方面发达。方东美,这个被钱钟书称为最后的“中国古典诗人”*方东美去世后,钱钟书说:“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参见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32页。,显然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倾向于“表现”的理念,他在诗词创作实践中对这一理念贯彻始终,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一理念给予肯定并将之升华。
在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收录的近千首诗词作品中,无论抒情还是叙事、写景还是说理,其中无不传达出诗人强烈的“表现”欲。抒情诗《思京》:“独夜风兼雨,江声咽苦辛。频年万里客,肠断金陵春。”诗中黑夜、风、雨、江声、万里客(异客)五个意象,勾画出一幅动感的画面: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伴随着呜咽的江声,身寄异乡的诗人静坐室中,感叹世事艰辛,思念家乡的美好。这种寂寥而又悲凉的意境,完美地表现出了抗战时期方东美寄居巴渝、远离家所(南京)的真实生活与情感状态。其中首联“独夜”二字,作为“诗眼”,甫一出现便为整首诗的意境定下了寂寞、苦恼、伤悲与凄凉的基调,神似于杜甫《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中“独夜”所传达出的旅人在外漂泊无依的孤寂之境。但是,艰苦的物质生存环境却没有阻挡方东美精神上的洒脱与超然。同一时期,在描写巴渝自然景观的一系列诗词中,方东美为我们展现了“用艺术的眼光看世界”的理想价值观念以及艺术化生活态度。请看《嘉陵夜色》:“岸镫流影人垂泪,山月回光客沦心。寂历寒江东逝水,盈盈输梦不言深。”复看《 歌乐山观云》:“云叠旧山川,巍峨纷在眼。恶风吹不坏,时作红蕤显。”再看《石门侵晓》:“云衣雾褧旧时妆,翠羽明珠倚绿杨。吐纳春词身口意,晓风残月梦中香。”诗中,岸灯、倒影、月光、逝水、翠羽(小鸟)、露珠、山云、绿杨、晓风、残月等自然景色无不濡染人的情彩,与人的泪、心、梦、身、意直接关联一起,景摄含情,情契入景,情景交融,人与自然在生命层次上交感呼应、圆融无碍、合和一体。这正是方东美所要建立的自由艺术境界。在这种“天人一体”的大境界中,整个世界艺术化、生命化了,自然与人在生命层面上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真正地实现了平等自由的交流,其所表征的是方东美在精神气质上对庄子式的逍遥与自由的无限追求。这也恰恰印证了方东美说的“在性情契合上我是道家”*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8页。的身份定位。

具体经验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产生普遍意义。到了中晚年,结合中国传统诗学创作理论,方东美将青年时期的创作方式(方东美百分之八十的诗词作品完成于抗战前及抗战时期*据笔者统计,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共录存诗词954首,其中作于抗战前有56首,抗战期间有715首,抗战后183首。具体请参阅拙文《方东美与坚白精舍诗集》,《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升华为“表现论”。在1956年完成的《中国人的人生观》一书中,当谈到中国人的艺术理想时,方东美明确指出,“中国的艺术方法是真正的表现”*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7页。,将“表现”看作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典型方式。但是,方东美眼中的“表现”仅仅是与我们常说的“再现”不同的一种表达方式或修辞方式吗?当然不是。“‘表现’乃是活泼泼的勾画出一切美感对象,它把握了生命的黄金时刻,最擅于捕捉自然天真的态度与浑然天成的机趣。”*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9页。显然,方东美将“表现”看作是一个“美感对象”——艺术本体的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把握住了最能彰显艺术对象生命气象与盎然生意的时刻,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构造出种种毫无凿痕、浑然天成的艺术意象,完美地弥合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缝隙。所以,在方东美看来,“表现”是一个艺术创构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其所呈现出的主客体生命之间水乳交融、相互蕴涵的交互状态,以及营构出的虚实不分、圆融和谐的审美境界,直接关联到艺术本体的构成,是艺术本体的内在构成因素。
综上可见,方东美的“表现”论,有方法论和本体论两方面的意义。在艺术方法论层次上,“表现”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对此毋庸置疑亦无须赘言。但是,方东美所说的“表现”,并非仅仅是“诗言志”、“诗缘情”等传统诗论中所谓的情感宣泄,其更加着力于情感的最终蕲向——审美境界的营构。对此,方东美指出,“表现”有似于中国艺术中的“传神”,其特点不重写实,而在造境。一方面,创作主体要化除滞碍,对物质性进行否定、超升;另一方面,则以直觉来把握物象,捕捉美的本质,透过“超越常情,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幻想”*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8页。之“思”,创造出艺术审美境界。简言之,“表现”就是透过“艺术性的直观”*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8页。,以审美的态度,驰情入幻,融理想于作品,美化现实苦难,表现出生生活意,幻化出纯美的艺术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方东美所谓的“表现”,显示出艺术本体创构的价值,即“表现”不仅仅是一种与“再现”相对的艺术表达方式,而成为艺术创造审美境界的一个实践过程,直指艺术本质。可见,“表现”即艺术,是方东美“表现”理论的内含之义。这表面上貌似于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观念,实则不同。克罗齐的“表现论”过于强调艺术创作的意识过程,而完全忽略了艺术创作的物态化阶段;方东美则深深地认识到,艺术的价值不只表现于艺术家神奇的构思与幻化境界的构想,更在于艺术家如何以艺术技巧将其示之于众。所以,方东美一方面强调艺术自然是想象和神思的产物,要在创造能够“点化万物,激励人心,促使大家高尚其志,……表露对生命的喜悦之情”的“诗艺化境”;*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8页。另一方面,方东美不忘艺术神思只有物化成真实的艺术品才能实现其最终价值,“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宣畅,就能浃化一切自然……人类受此感召,更能奋然有兴,振作生命劲气,激发生命狂澜,一旦化为外在形式,即成艺术珍品”*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9页。。总而言之,方东美的“表现”论,贯穿了艺术创作从“形之于心”的构思状态到“形之于手”的物化状态整个过程,成为了文艺生产活动的重要枢机,具有了艺术本体层面的价值。
二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命题:诗(文学、艺术)是一种“表现”。但是,“表现”总有某种意向性,即它归根结底要指向表现的对象(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那么,诗的对象是什么,或者说诗表现什么,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方东美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让我们先看几首方东美的诗:
款款频相语,飘飘会列仙。碧添春浒涨,圆撱甲文钱。密荫莺声滑,清含旭泽妍。幽情舒缱绻,为舞绮窗前。(《风叶》)
青松老更狂,劲节一身藏。雪澡龙筋瘦,风培鹤骨昂。贞心常傲古,耿性自凝香。春色来天地,掀髥看世妆。(《松》)
冰雪神仙骨,芬氲梦寐姿。欢心披点点,妙相啓时时。旭泽催微笑,和风衍静思。虚斋天地阔,缦窖养新诗。(《瓶梅》)
朝雾同心者,披诚卫山川。山川欣所遇,含笑发真妍。(《晓》)
以上四首诗向我们呈现出了不同的自然风景:或有风中婆娑之树叶,身姿绰约,如深情之恋人,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翩翩起舞;或有直入云霄之老松,那傲岸挺拔的身姿,耿介贞心的品性,长髥飘飘的逸态,如青年活力无限,老而弥坚;或有香气弥漫之瓶梅,以不屈的风骨、乐观的心态迎接寒冬的来临,倾说时序的交替变更;或有破晓前之朝雾,如朋友知己,同心无异,“诚”卫山川,宛若君子,破晓后之山川,如旧友再遇,欣喜相逢。通过这些诗,我们看到,整个自然界在诗人眼中是活跃的、积极的,生机盎然的。在这里,自然人格化、生命化了,万物都是生命的载体,一切都透出一种永恒不息的生命精神。在方东美看来,诗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流衍创进的生命精神。
方东美认为,在以美为追求的艺术创造活动中,充分地展露生命机趣,表现生命的盎然生意,是艺术的主要内容与目的。“中国艺术所关切的,主要是生命之美,及其气韵生动的充沛活力。”*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2页。在艺术的世界里,生命的美好与活力得以完美展现,人生可以达所欲生,畅所欲为,苦难化为幸福,丑恶化为美好,生命亦变得丰富而理想。在此意义上,方东美说,“生命正是艺术,艺术富有生命。美的创造为人生根本意义之所在,离却艺术,人生即无以耀露它的自由。美感是生命的节奏,诗人是生命的明灯,艺术有起死回生之伟力”*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8-149页。。这是方东美对生命与艺术关系的最直接表达。不难看出,方东美所谓“生命即艺术”也即生命与艺术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两者对美的价值共同追求的基础之上,美是生命对真善美价值世界的内在追求,艺术则是对生命在创造活动中所展现出的生命机趣与生香活意的外在形式表现。在这里,美、艺术、生命三位一体,构成了一个理想的价值境界。此境界虽然指向精神,但却是真实的,是每个生命可以亲身体会领悟的,“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1页。。换言之,唯有亲身体验生命历程,才能获得艺术的、审美的感受。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与审美感受,并不是瞬间审美体验式的心理活动,而是一个长期的生命创进活动。因为在方东美看来,美与艺术的根源在于生命的流行变化与创造过程中,“宇宙之美寄予生命,生命之美形于创造”*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5页。。
但是,用艺术表现生命,并不是对具体生命现象进行刻板地描绘,而是“以精神染色相,浃化生命才情,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8页。。“大生机”指的是个体与宇宙普遍生命之间的水乳交融、交光相网的宏大生命气象,表现在艺术上是“天地大美”的最胜意境。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最早提到“天地大美”的应是管子。管子在《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是管子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构建的一种天人和谐的美好境界。但真正使“天地大美”境界广为人知并作为最高人生境界来追求的则是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基于天人关系与人格修养两个方面,庄子认为,圣人是通过“无为”、“不作”顺其自然的默观审美方式,洞察并欣赏到天地万物“不言”、“不议”、“不说”的无言之理与无言大美。历史上,从原始儒家到宋明新儒家,也都提出过相似于“天地大美”的人生境界,如“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无间”等表达的天人一体关系,实际上都是“天地大美”理想境界的不同表达。那么,“天地大美”的根源又源自哪里呢?显然,管子与庄子认为是建立在天与人的和谐关系(尽管两者在构成和谐关系的方式认知上并不相同)上,儒家则认为是建立在天人之间的先验一体关系上。而方东美在内化儒道等诸家思想的基础上,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6页。在这里,方东美表达了两层意思:“天地之美”的载体是生命,并布濩于生命的普遍流行当中;“生命之美”的本质在于“创造”,并呈现在生生不息、创进不已的生命历程之中。很明显,方东美把生命的创进奔流看作是生命的本质精神,而这种生命精神的终极指向是完美的生命境界即“天地大美”的境界,因为“生命的本性就是要不断地创造奔进,直指完美”*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7页。。可见,在方东美看来,美不是外在于生命的,而是生命的内在本质,这就是所谓的“寄于生命”的意思。作为以美为追求的诗和艺术,其价值正在于对生命盎然生意的呈现,对宇宙生命精神的全面颂扬。这是中国艺术的通性,也是中国艺术的价值理想。
进一步追问,艺术追求的“天地大美”源于生命的不断创进,这种观念是方东美的杜撰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诗学穷究“天地大美”的原因深深地埋藏于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方东美认为,中国艺术家们深通生命与宇宙的直透之法,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能够协和宇宙,参赞化育,人与自然浃而俱化,所以,他们的艺术才能表现宇宙生命的宣泄、生命机趣的表露以及大化流行的描绘。在原始儒道家哲学中,方东美发现了宏大的生命气象,发掘出浓浓的生命趣味:老子将生蓄、长育、亭毒与养覆,当作“妙道”与“玄德”的表现,将“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作为道的特性,无不表现出创造性和生生不息之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与“一”作为万物本原有生育万物之能;“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万物依恃“道”与“一”才具生生不已之势。孔子在《周易》中所谓的“万物资始,乃统天”,“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视天有大生之德,地有广生之德,承天地之德,万物才得化育,流衍不息。这些都是宇宙生命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方东美指出,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具形,化为外在形式,即成为艺术珍品。特别是儒家,其将宇宙人生视为充满纯美的太和境界,并将“善”、“美”作为人生的高级价值追求,最终形构成“美善并举”的诗学(艺术)理论。在方东美看来,儒家生命与艺术的同气相求,是双方一体关系的表征。这一点在《礼记·乐记》中得到印证:“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明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些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表明,艺术的兴起源于天地万物的流衍与同化,其中无不透现出宇宙生命的创进不息与生动气韵。据此,方东美认为,儒家对音乐和诗的重视,都是因为“其审美的主要意向都是直透宇宙中创进的生命,而与之合流同化,据以饮其太和,寄其同情”*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0页。。在这个意义上,诗与生命是同一的,是“生命之诗”,也是“诗之生命”。*方东美:《生生之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8页。
三
从“诗是生命的表现”这个命题中,我们看到了诗的表达对象(内容),但是这个对象——生命,究竟是什么?这个貌似多此一举的问题,实际却是理解方东美生命诗学的关键。
通常,我们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理解生命。从物质层面言,生命是宇宙中能够自我生长、繁衍、进化的一种自然现象,在生化本质上是能够自我复制的氨基酸结构,范围包括细菌、真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从精神层面言,生命是生命体所具有的情感、理性等心理意识。前者关乎物质世界,倾向于生命的物质性,而后者关乎意识世界,倾向于生命的精神性。在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在共同认可(或明确或暗合)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的前提下,虽然不同人对生命关注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例如在现代新儒学家阵营中,牟宗三注重生命的“道德的主体性”,唐君毅关注生命的“道德理性”,徐复观则侧重生命的艺术精神,但是,他们在生命的精神性倾向上是相同的。方东美也是如此。
方东美对生命的精神性蕲向首先从他的哲学观缘起。在其早期著作《科学哲学与人生》中,方东美认为哲学是对“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境”是生命生存之环境(世界、宇宙),“情”是生命之情感、欲望与冲动,“就境的认识言,哲学须是穷物之理”,“就情的蕴发言,哲学须是尽人之性”。*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页。可以看出,方东美的哲学定义包含了宇宙论和人生论两个方面,“穷物之理”是对外在宇宙的追询,“尽人之性”是对内在人生的要求。方东美不仅把宇宙与人生结纳入同一个学科体系,而且还为它们构建了一种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建设哲学时,每提到生命之创进,便须连类及于世界;每一论及世界之色法,亦须归根于生命。”*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页。显然,在方东美看来,宇宙与人生是一体的,他称之为“情理的连续体”、“情理的集团”。*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页。那么,宇宙与生命如何能为一体?方东美给的答案是“情因色有”、“色为情生”。“情因色有”的根据,在于人的生存总要寄身于客观的环境,没有外在物质环境,恰如无皮之毛,无处安附;“色为情生”的根据,在于世界的价值正在于为人生,没有人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人生,假使没有你,知识(笔者按:知识是宇宙之理)又值得什么”*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页。?“情因色有”是铁的事实,“色为情生”则是方东美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审视生命对世界的意义。从这两方面我们看到,宇宙与人生、宇宙与生命是一体的,不可分的,也可以说,宇宙是有生命的。
在哲学上将“生命”推广至整个宇宙,已经透显出早期方东美在“生命”范畴上的精神性蕲向。到了中晚期,方东美立于“万物有生论”的观念,将生命的精神化倾向更加明确化,“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现象里边都藏着生命”*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页。。在这里,方东美不是在物质实体层面来指称现象中藏着的生命,而是就宇宙中到处都充塞的生命气息或者生命精神而言“生命”。方东美将这种非实指的普泛生命精神名之为“普遍生命”:“中国人的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的活动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页。在内容上,“普遍生命”涵盖宇宙有机界与无机界,是物质界与精神界的合一;“‘宇宙’,从我们看来,根本就是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毫无隔绝”*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5页。。在实质上,“普遍生命”是宇宙万物机体所展现出的一种创进不息、生生不已的盎然生机与活意,“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广大生机,是一个普遍弥漫的生命活力,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无一处不在流动贯通”*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6页。。
以上方东美对“普遍生命”概念的直接使用,使我们在感性层次上对其有了初步的认知。真正让我们对“普遍生命”有深刻理解的,是方东美基于原始儒道“生生”哲学与“大道”哲学基础上对“普遍生命”的进一步阐发。在1937年《哲学三慧》一文中,方东美用简洁至极的语言点出中国哲学的六大原理,其中“生之理”即“普遍生命”的主旨与五点“要义”:“生命包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无方无体,亦刚亦柔,趣时显用,亦动亦静。生含五义:一、育种成性义;二、开物成务义;三、创进不息义;四、变化通几义;五、绵延长存义。”*方东美:《生生之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2页。这一原理在方东美晚期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深化。
第一,育种成性义。“育种成性”是指“普遍生命”具有创造生命的功能,可简称为“创生”义。具体而言,普遍生命虽然“无方无体”,但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生机”*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4页。,却与“大道”共同一体流衍化行,具有本体功能,成为生命的源泉。自微观方面,一草一木,一物一人,从种子、胚胎到出生、长成,从如日中天到夕阳暮年,生命由微及著,由小到大,赓续连绵,其中时时蕴含着盎然生意,勃勃生机,这是“普遍生命”的功能;自宏观方面,动物、植物、人类整个族类生命的繁衍生息,及至各种生命的演变进化,再推至整个宇宙的形成,这是“普遍生命”的流行。所以,无论大小与种态,在普遍生命精神的贯注中,各类生命都显示出一种本源式的生命创造力,并使宇宙万物都充满生气与生机,宋代大儒程颢所谓“天地生物气象”即是。
第二,开物成务义。所谓“开物成务”,指“普遍生命”把化育万物作为自己的使命与事业,孜孜不已,亹亹不穷。这可称为“普遍生命”的“广生”义。详言之,乾元坤元同属“大道”,乾元“资始”,主创造,坤元“资生”,主涵养,两者合之,则意味着生命的生成开展。生命浃化“大道”,从“大道”中汲取营养,获取永不枯竭之创造力与周济万物之化育力,不断拓展生命宽度,提升生命价值。即使生命在发展中遇到羁绊与阻碍,也可“返初复始,会归大道”*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8页。,寻找到解决的办法,终归实现自我价值与意义。这是方东美所谓的“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
第三,创进不息义。“创进不息”,突出生命在时间之流中向前进展、一往无遏的绵延状态,可称为“普遍生命”的“继生”义(“继”意为持续不断,《周易·离卦》有“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普遍生命弥漫于整个宇宙系统,一方面横向空间拓展,扩大生命种类,增加生命数量;另一方面纵向时间延伸,增益生命价值,提升生命质量。就时间向度而言,生命创造不息,前后相续,从不间断,构成无穷持续的时间序列。生命之流,原其始,可追根溯源到无穷的过去,要其终,则延展趋向无尽的未来;而终始之间,正是生命绵延不断的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从原始萌芽到成长壮大,从不完善趋于完善,“如是而新新不已,以迄一切摄归性海”*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9页。。
第四,变化通几义。“变化通几”,意为在生命变化过程中不断萌发出新生命,强调生命流行的创新性,可简称为“普遍生命”的“新生”义。生命之流与时间之流合而为一,绵延无穷,不存在停滞的空间化瞬间即“影像化的时间”(柏格森),亦不存在暂停片刻的活的生命,一切存在都在持续的绵延中潜移默化,变变不停,恰如我们所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言“变”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时,与时间合体的生命之流并不只是简单量的积累,而总是去芜存菁,推陈出新,在扬弃旧时自我的同时,拥获质变后的新生。如方东美所说:“盖万物后先递承,绵延不断,先往者、刹刹现于前,旋成历史之陈迹;后继者,亹亹出于后,不啻时间之新蕾。其营育成化,先后交奏,而生生不已;其进退得丧,更迭相酬,而新新不停。”*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9页。但是,与时间系于一体的“普遍生命”,其变化呈现出多样性或不确定性,并非是一种线性或平面单维的流动,而是弥贯万物、充塞天地的立体式蔓延,所以方东美才说普遍生命“无方无体”。同时,也正是因此,生命的创造才层出不穷,无限拓展,体现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伟大。
第五,绵延不朽义。“绵延不朽”,强调生命非静而动、生生不已的永恒情态,这是“普遍生命”的“恒生”义。首先,宇宙包罗万象、生机无限,无时不发育创造,无处不流动贯通,其中蕴藏的生命创造活力一往无前,除旧立新,总呈现出一种“未济”的动态。这是“不朽”的第一义。其次,生命的创进过程是现实可见的,存在于此世的生生创造之中,是“当下可成的”*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54页。,并不在于彼岸世界的神性永恒。“当下可成”显示出了生命创进的现世性与现实性。这是“不朽”的第二义。再次,生命“不朽”的第三义,表现于生命价值的永恒,“生命之不朽,即价值之不朽”*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9页。。这种“不朽”价值,来源于生命潜能被激发后喷薄而出的创造力,而“不是指神的恩典所赐”*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5页。。一方面,人类激发生命潜能,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实现生命价值。另一方面,人生而具有神性,因为神性才成就了人性的伟大,方东美常说“to be human is to be divine”*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页。(译文:要做人,就要成就他的神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方东美所谓的神性并不是位格神,而是源自于“大道”的创生力量。“在中国哲学里,人源于神性,而此神性乃是无穷的创造力,它范围天地,而且是生生不息的。”*方东美:《生生之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4页。可见,造物者通过生命表现其创造力,并在创造活动中完成不朽的价值,正是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以及“通往精神价值宝地的智慧之门”*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5页。。
“普遍生命”的五种要义,即其在时间进程中显示出的“创生”、“广生”、“继生”、“新生”、“恒生”五种功能,将“普遍生命”范畴的主要特征呈现了出来:本源性,创造性,创进性,价值性,精神性,不朽性。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普遍生命是一种以实现生命理想价值为旨归,绵延不息于宇宙中的生命创造力和生命精神。
要之,方东美的“生命”范畴,在内容上,涵括了整个有机界和无机界;在实质上,“生命”更多是由“普遍生命”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与“生意”,是一种生命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命。把实体生命精神化、虚指化,而无限放大生命的“意义”,成为方东美生命哲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与方东美用“艺术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观念不可分的。在构建中国人的艺术理想时,方东美指出:“中国人在成为思想家之前必先是艺术家,我们对事情的观察,往往是直透美的本质。”*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2页。因此,用审美、艺术的方式来透视宇宙与生命,在方东美看来是中国人认识宇宙与人生最重要的方式。据此,生命(普遍生命)精神成为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对此,同样主张“生命美学”的宗白华有着类似的诗学理论观点:“我以为文学底实际,本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流露喷射出的一种艺术工具,用以反映人类精神生命中真实的活动状态。简单言之,文学自体就是人类精神生命中一段的实现,用以表写世界人生全部的精神生命。所以诗人底文艺,当以诗人个性中真实的精神生命为出发点,以宇宙全部的精神生命为总对象。文学的实现,就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实现。文学的内容,就是以一种精神生活为内容。”*《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诗(艺术)是生命(精神)的表现”这一命题的意义在于,把诗的表现内容(对象)从传统的情感(诗言情、诗缘情)推广到更具普遍性的“含情”且能“契理”的生命(宇宙生命和人类生命),大大拓宽了诗的表现域,使诗在精神内涵上与哲学、宗教具有了共通性,并使整个文化在生命的基础上构成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系。
PoemsAretheExpressionofLife:aStudyonthePoeticThoughtsofFangDongmei
Lan Xixiu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Through studying Fang Dongme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poems, this paper presents Fang’s idea of poetics: poems are the expression of life. The expression is not only expressing itself, but also directing the poem itself; life is not the body, but a kind of spirit of life, which is called universal life by Fang Dongmei. The universal life, aiming at the ideal value of life, is essentially the continuously creative power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The five points of universal life are the five functions including creating life, enlarging life, continuing life, refreshing life, and enduring life.
poetics; expression; life; universal life
李宗刚
I206.7
A
1001-5973(2017)06-0105-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11
2017-10-05
兰希秀(1977— ),男,山东青岛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美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2016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世纪皖籍美学家研究”(SK2016A0815)的阶段性成果。
——《青瓷》作者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