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菜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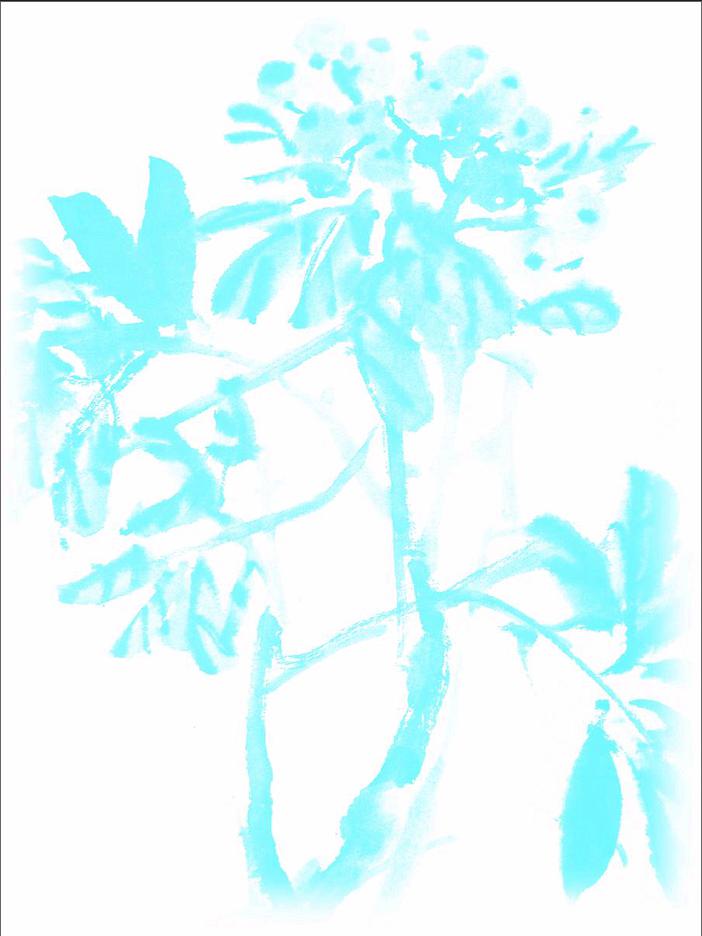

笋 子
这是三十多年前少年时代的光景。
家乡没有楠竹,野生小竹子倒是不少。村前小河的两岸,小溪边,园土的高坎上,这些地方的小竹子长得尤其茂盛,一篷一篷的,小指粗的竹竿高高窕窕,密密实实,尖长的叶子绿得发黑发亮。对门岭的油茶山,每年摘下油茶之后,就有农人成天地垦荒,挖翻茅草,挖断小野树,挖出粗壮蜈蚣般的光亮竹根。只是到了来年春天,几场春雨过后,茅草,小野树,小笋子,又哗啦啦地长了出来。
长笋子的日子,自然是孩子的最爱。三五成群地,在村边宅旁的野竹丛里梳理,只要笋子露出了头,甭管粗细长短,一概拔了,嘻嘻哈哈,多带了玩耍的成分。真正扯了满满一篮筐一篮筐的笋子,扛在肩膀上,一路络绎回村的,是每家的主妇。那些日子,我的母亲就常约了几个伴,上午提了一個空篮筐上了山,要下午才回来。这些笋子大小长短均匀,比竹筷还长,比手指还粗,村人叫做红花笋,是黄泥巴山上长出来的,笋根部往往还带着黄泥色。
剥笋是每天的必修课。做菜之前,母亲从篮筐里拿一把笋,我们就一同剥起来。母亲两个大拇指的指甲又黑又厚又长,她剥笋子很快,用指甲像刀子一样沿着笋划开一道竖缝,稀里哗啦,三五几下,就剥去了笋壳叶,剥出一条翠嫩光洁的笋子来。有时,她从笋尖往下剥,用食指卷着笋壳叶,几卷几卷,一边就剥光了,然后,又是几卷几卷下来,另一边也剥光了。她的粗糙的手指是如此灵巧,简直就是一把刀子。我剥笋则缓慢笨拙得多,一圈一圈从下往上剥,每一片笋壳叶都是完整的,缩卷成小喇叭,剥得拇指甲生痛。有时,一些粗大的笋壳叶,我还特意放在一边,铺开来,反折几道,撕成小栅栏,松手后,笋壳叶自然卷缩,就成了一把小伞,这是村里孩子爱玩的一项小手工。
剥好的笋子,切成指节长,绿玉一般,清炒,放一点红辣椒灰,色泽明丽,清香可爱。和猪肉同煮,更是佳肴。那时节,溪河水田,鱼虾泥鳅颇多,往往捉了来,油煎,和了小笋子同炒,也是美味。小笋子切成细末,与鸡蛋鸭蛋同炒,更是我向来喜爱。
扯来的新笋子不能放太久,否则易坏。往往全剥了,滚水焯后,晒干。一小扎一小扎,用细苎麻线绑好,白白亮亮的。到了盛夏,干笋子泡水后浸软,切指节长,与青辣椒同炒,真是好吃得不得了。
雷公菌
那时候的雷公可真狠,脾气大得很。
尤其是在经历了一个长冬的沉闷之后,在一个寂黑的春夜,突然之间就起了惊雷,霹雳一声巨响,电光闪耀,震天动地,随之大雨倾盆。他犹如一个刚从牢笼里释放的囚徒,愤怒着,奔跑着,咆哮着,东冲西突,仿佛要把满腔怒火向着天空和大地倾泻。在这样的雷雨春夜,年幼的我常躲在被窝里吓得心惊胆战。母亲多次告诫我,打雷的时候不要做声,千万别张嘴对着耀火(土话,闪电)舔舌头,否则要遭雷劈。我曾惊问原因,母亲说,只有妖怪成精了,才舔耀火吃,雷公看到了,就要打。
到了天明,雷停雨收,太阳东升,草叶碧绿,山明水秀,我们又活泼起来,全村人也活泼了起来。村边的草地上,山石间,很多人提着小竹篮子,俯身在捡拾雷公菌。经过一夜雨洗的青草,干净翠嫩,叶尖上顶着一颗颗滚圆晶亮的水珠。一块块的雷公菌,乌黑柔软,皱皱的,牵牵连连,依附在青草上。我们一一拾起来,放进篮子里。回到家,倒入盆中,拣去草叶草茎和泥土砂石,清洗干净,母亲就能做一碗时鲜的水煮雷公菌,吃起来十分柔软。
说起来也很奇怪,这道天赐恩物的无根无叶的野菜,似乎只是在春夏雷雨夜之后才生长出来,在人迹罕至青草茂盛空气清新之处,越发长得肥大娇嫩又密集。或者正是这个原因,才博得了雷公菌的美名。
20岁参加工作,我正是一个文艺小青年。一个微雨拂面的春天,我回到乡间,在村前的木桥边,看到青青草色之中,有一片熟悉的雷公菌的身影,犹如盛开着的黑色花朵。一下触动了我的心怀,当天写下了这样一首十四行诗:
雷公菌
是羡慕下界的纯朴明媚,
还是厌倦虚空寂冷的天庭?
在黑沉沉的春夜里,
伴着雷电交加的暴风雨降临。
象一朵朵黑色的玫瑰,
悠然开在辽阔的绿原。
我们把你拾来,在晨阳里,
感谢你,善良的天使!给了我们美味的菜食。
你本是凡间的仙物,却甘愿依附泥土,
与山溪作伴,与草木为伍,
不屑进入上流人的圈子。
我们好久不曾谋面了。今天,
在微雨拂面的木桥边,我又见到了你,倍感亲切。
我要献给你,我由衷的敬意!
蕨
“一子尖尖,二子拳拳,三子像把伞,四子划龙船……”
儿时,我们的嘴巴上,常挂着一首“十子”的谜语儿歌,谜底都是村野常见之物。其中的“二子拳拳”,指的就是蕨,村里的土话也叫大叶撸箕。
常听母亲说起,昔日困难时期,村人家家户户都到山上挖蕨根,捣烂,做蕨根粉蕨根粑粑充饥。蕨根粉我没吃过,但蕨是经常看到的,只要上了山,随处都能碰见。这种丛生的小植物,茎叶扇开,状如凤尾,十分漂亮。它的根部,常有拳曲的嫩茎长出来,毛茸茸的,这就是可以采来做菜的蕨。
或许是父辈们当初吃蕨根吃得厌了胃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几乎没有关于吃蕨菜的记忆。我最早吃上蕨菜,是参加工作,在永兴县城居住生活之后。
永兴是一座山清水秀的小山城,生活节奏缓慢,十分宜居。环城周边的山岭,多生长毛竹和小竹子,清明前后,县城的街边和几个菜市场,每天都有山民挑了大笋、小笋子和蕨在卖。小笋子多是剥了壳叶,一扎一扎绑扎好,一扎一斤,上下悬殊不大,论扎卖。蕨也是如此,扎成修长墨绿的一扎,层层叠放在箩筐里,顶端是拳曲的嫩芽,有如灰白熟睡的毛虫,又像欲开未开的花苞。
永兴人似乎很爱吃蕨,周边山岭野生小竹和蕨类植物又多又密,住在城里的人,也常常呼朋引伴去山上扯笋采蕨,既作春日之游,又得天然食材。受其影响,我家也尝试买了蕨来吃。水焯后,用凉水清洗绒毛,切成小段,放猪油清炒,清香四溢,吃起来脆嫩,便觉乃是美味。有时加酸辣椒同炒,也十分好吃,又开胃口。这个季节,县城的饭馆酒店,也多备这一道时鲜野菜。endprint
有几年,县城周边的乡镇村组,掀起了栽种冰糖甜橙的风潮。甚至在城的每个单位,都分配有承包山岭,烧荒种植的任务。冰糖甜橙成了全县推广种植的代表性果木。那一座座全是长满了野生小竹子和杂树的山岭成片放火烧毁,火光冲天,浓烟弥漫。过后雇人挖山撩壕,种上冰糖橙苗木。山山岭岭,顿时成了黄皮秃头。甜橙树一天天长起来,小竹子和蕨类植物一天天少下去。
若干年后,冰糖甜橙长得高高大大,枝繁叶茂,县城周边的山岭又覆盖了浓绿。每到甜橙开花的那段日子,整个县城清香飘拂,渗人心脾。只是昔日清明前后,那种山民挑着剥好的小竹笋和刚采下的鲜蕨,络绎来到县城,沿街边摆摊贩卖的场面已然不在了。那种全民出城,扯笋采蕨的盛况,也成了永远的历史。
栀子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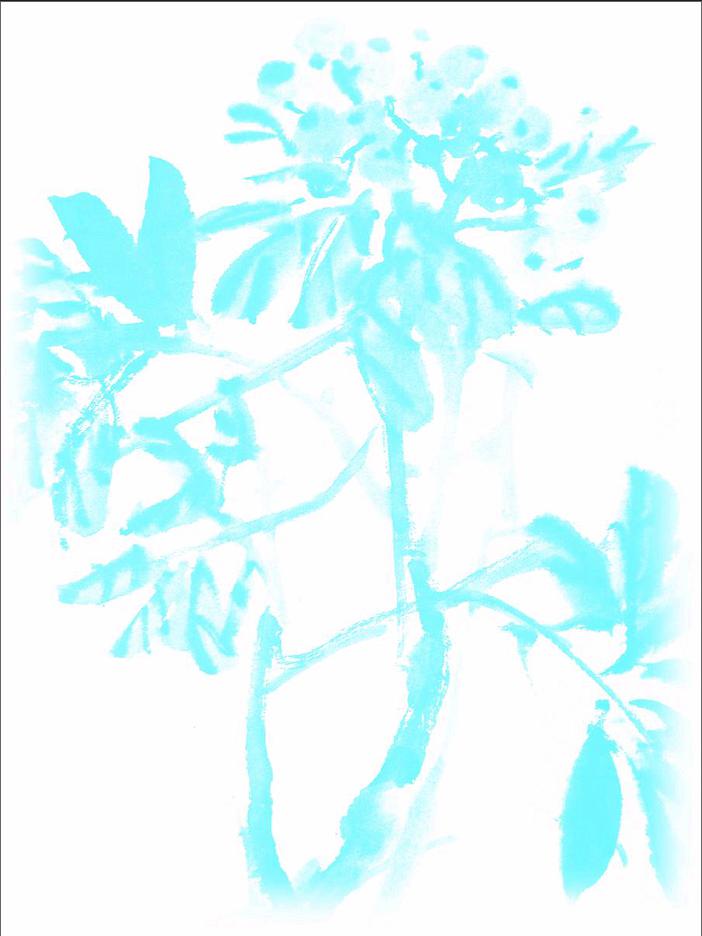
这段时间,正是栀子花开的时候。
我所寓居的义乌市区的住宅小区,每天早上,有老妪和老翁,拿了小板凳,坐在小区街边固定的位置,在地上铺一块彩色的塑料布,从篮子里把刚摘来的新鲜蔬菜,水灵灵的,摆在塑料布上卖。这是一群住在小区的居民,他们的身份已从农民转变成了市民,但生活习性,依然改变不了农民的勤劳。小区街道旁边的绿化带,暂时未曾开发房地产的空地,都被他们见缝插针开垦成了菜园。四时不断,随着季节种上各种蔬菜。这几天,我常看到地铺上,有食品薄膜袋子装了一掬洁白的栀子花在卖。想必,这是他们起了大早,从街边或公园摘了来的。
便自然地想起了那首抒情的《栀子花开》的歌曲来,并在嘴里一遍遍无声地吟唱,有了一种深深浅浅的惆怅。昔日在乡村生活采摘栀子花,以栀子花做菜下饭的情景又倏然来到眼前。
那时候的家乡山岭,可不像如今这般荒芜又没有生气。山上有葱葱郁郁的树木,有四季都能听到的流泉的声音,有老鹰,有喜鹊,有乌鸦,有猫头鹰,有各种飞禽走兽,有不息的鸟语花香,虫吟天籁。当然,还有大片大片的野生栀子花的绿色小灌木。
栀子花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入乡随俗的名字,叫做黄珠子花。大约是它的果子成熟之后,就如同一枚金黄色的珠子。记得常常是初夏雨后,它们仿佛一夜之间就全部约定齊了,在绿色的山林里开出一树树繁星似的喇叭状的花朵来。栀子花开的信息,也似乎在雨夜的酣梦里就通知了村人。新开的花朵,洁白如雪,清香四溢,摘下即可生食。一大早,无论山谷还是山腰,都有大人和孩子提着竹篮采栀子花的身影。
每天一篮子一篮子的栀子花提回家,成了这个时节家家户户的时鲜菜肴。母亲做鲜栀子花这道菜,通常变换着两样做法:一是水焯后清炒;再就是炒一升米,炒至焦黄喷香,到石磨上磨成米粉。做菜的时候,将栀子花放入窝中水煮,加油盐,水沸后,倒入米粉,用筷子迅速搅拌成糊状,装碗,就成了香喷喷的米粉栀子花。当天吃不完的新鲜栀子花,沸水焯后,铺在簸箕上或禾场上晒干。等到端午节后,新鲜的辣椒也出来了,抓一把干栀子花泡水切碎,炒青辣椒,也是村人一道不错的美味。
山野未曾采摘的栀子花,到了深秋,长成了状如指节的金黄色的黄珠子,采来浸泡红薯土酒,色泽金黄,香气浓郁。
菌 子
最近一次吃到野生菌子,也是多年前在报社做记者的事了。
那次去一个偏远山区县采访,在林区小镇一家简陋餐馆吃午饭时,上了一道野生干蘑菇炒肉的菜,是那种红皮的蘑菇,我一眼认了出来,就是我小时候在村里后山常捡的那种。
我们村子有两片茂密的枞树山,原本都是禁山,一片在村后,是后龙山,另一片在村北,叫下首山,两山掌管着一个村的风水命脉。山上主要生长着高大的枞树,以及其他原始状态的各种知名不知名的高大乔木和密集的灌木。
进入夏天高温季节,晴闷的雨后,是上山捡菌子的好时光。两片枞树山里,满是提着小竹篮捡菌子的大人和孩子。菌子多种多样,有针状的,有斗笠状的,有平伞状的;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黄色的,有棕色的,有淡蓝色的;有长地上的,有长朽木上的……千奇百怪,令人眼花缭乱。母亲招呼我们,针状的,黑色的,不要捡,荷树下面长的菌子也不要捡,有毒。我们捡的菌子,主要是那种枞树菌,长在高大的枞树下,从铺满枯黄枞毛的地面拱出来,平伞状,棕色,有着麻点子,肉质洁白。还有就是那种红皮的菌子和浅蓝色的菌子。菌子捡回家后,母亲要一一检查筛选,把有毒的菌子剔除。
时鲜的菌子是一道特别鲜美的菜肴,不过,稍有不慎,也会引起中毒,甚至出现毒死人的惨剧。几乎每年这个时节,都会从村人的言谈中,听到某某村庄有人吃了毒菌子的消息。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么些年来,我们村庄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种菌子,几乎村里人人都认识,并且都知道无毒又好吃,那就是茶树菌。我们村庄,田土少,山多,而且除了这两片枞树山外,全部是油茶山。茶树菌就生长在油茶山上,运气好的时候,一棵高大的油茶树下及附近的空地,往往能捡到几个茶树菌,令人十分开心。这种菌子,表皮泥土色,伞下洁白,菌伞大的胜过巴掌,杆子高挑,比拇指还粗。
菌子多的年成,母亲晒一些干菌子,用袋子装好。等到过节过年买猪肉的时候,发一把干菌子炒肉,味道更是美妙。
大约是刚刚分田到户的那年,两片枞树山遭到了村人疯狂的砍伐,各自将砍倒的大树抱回家,元气大伤。以后,建房的人家日益增多,村下首的那片枞树山更是绝了迹。到如今,连年荒芜火烧,偌大的村庄,连绵的山岭,泉流枯竭,油茶树也几近于无。村庄的山岭,哪还有野菌子呢?
薤 白
这是我尤为喜爱的一种草本植物,在村里,它有一个土邦邦的名字,叫做野波荞。
春天里,村庄的旱土,河畔溪岸,山边沟渠,到处都能看到它娇嫩的身影,碧绿细长的针叶,像丛生的藠头和香葱。一株薤白往往长有三五片针叶,茎部大的,有竹筷粗。在上一年翻垦过的疏松园土里,粗大的薤白尤多,拔出来,根部就是一粒滚圆的白珠子,大如指头,犹如微缩版的独头蒜。扯猪草的时候,我们十分喜爱这种香气浓郁的薤白。
薤白做菜很好吃,尤其适合炒蛋,黄绿相配,香气四溢,看着就咽口水。煎泥鳅鱼虾,当然更是美味。不过,我的母亲经常说,这菜不能多吃,吃多了,糊眼睛,视力下降,这是她为此并不常做这道菜给我们吃的理由。其实,我吃了薤白炒蛋,薤白煎鱼煎泥鳅,除了还想下次再吃,并不觉得眼睛模糊,视力有任何变化。
到了盛夏,薤白长出箭杆子,状如蒜苗,顶端结一个紫色的花球,球的表面是一粒粒小小的圆珠。不久便开出紫色的小花,异常漂亮。
相比与它同属的植物,薤白的生命是短暂的。它生在春天,夏天过后就进入了生命的迟暮。记得有一首远古的挽歌,名为《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相传,汉初,高祖召田横,其不愿臣服,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此歌。意思是,薤上零落的露水,是何等容易干枯。露水干枯了明天还会再落下,人的生命一旦逝去,又何时才能归来?感叹人生苦短,奄忽而逝。
【作者简介】黄孝纪,1969年生,湖南永兴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班学员。近年致力于散文写作,作品散见《福建文学》《湖南文学》《时代文学》《鹿鸣》《奔流》《小品文选刊》《佛山文艺》《阳光》《绿洲》《牡丹》等期刊。著有散文集《八公分记忆》《时光的味道》《晴耕雨读,江南旧物》《老去的村庄》。散文集《时光的味道》入选2016年度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选题。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