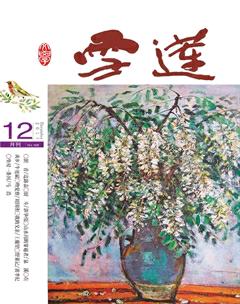聪明的狐狸
刘国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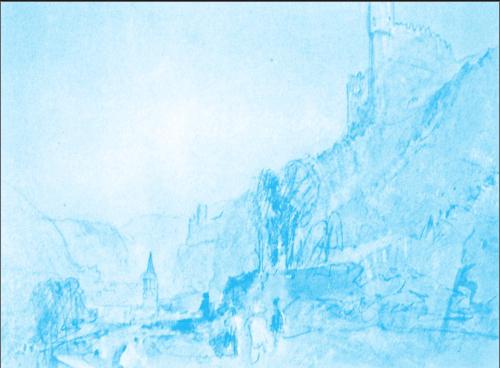

很少会有人喜欢狐狸。因为它在人们的眼中通常是心狠、狡猾、令人憎恶的动物,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非常聪明、机灵的动物。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北大荒的草甸子里度过的,经常和狐狸打交道,亲眼目睹了狐狸的机敏和智慧。
进入秋季,狐狸就开始不满足于捕捉野生动物了,因为它也和所有动物属性一样,要为机体过冬储存大量的能量。
一天黄昏后,大人们来到场院掰苞米,我们小孩在场院门口看大门,防止鸡鸭鹅来捣乱。天气很闷,没有一丝风,我和小弟在门外边跳绳玩。正玩得起劲儿,突然前边传来一群鸡鸭慌张的奔跑声和尖叫声,打破了傍晚的沉静,我一听就知道准是狐狸又进村干偷鸡摸鸭的勾当了。果然,两只火红的狐狸从村子里跑出来,嘴里都同时叼两只大鹅。我第一次看到狐狸能叼两只鹅,感到很惊奇。被叼住颈部的鹅,眼神里透出绝望,嘴里发出凄惨的哀鸣。小弟见状喊着:“大黄,上!”我家的大黄狗听到命令,嗖地朝那两只狐狸追去。要不说狐狸狡猾呢,它两见大黄狗追来一点儿也不慌张,为了快速脱身,它俩竟老练地将头一甩,就把嘴里叼着的大鹅顺势甩到背上,一边搭一个,嘴里仍然还叼着鹅的脖子。两只狐狸各驮着两只鹅在前边跑,大黄狗在后面撵,我和小弟跟在后面追,眼看着大黄狗追上狐狸了,它却不冲上去咬,而狐狸也不反扑,它们就面对面地停下,然后都后腿趴下,前腿直立地对坐着,大眼瞪小眼地相互看着喘粗气,就像三个刚刚吵完嘴的伙伴儿在赌气,十分有趣儿。等我和小弟赶到时,大黄狗一见主人来了,顿时就来了精神,狗仗人势地狂吠着,但两只狐狸却各自背着两只鹅跑远了,小弟只好喝住大黄狗,目送着它们远去。
又到了春季动物反群的时候。家乡人把在春季动物发情称为“反群”。春天,是农村最忙的季节,一年之季在于春。家家户户都在这时候迎接新生命的诞生:狗生崽儿,马产驹,鸡抱窝,猪下崽儿。我这时放鹅得格外当心,狐狸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偷吃没有抵抗能力的鹅崽子。
一天下午,我和小弟把鹅群赶到小河边的草地上吃嫩草。这里有刚刚发芽的野菜长在坡势平缓的草地上,春风吹来,芨芨菜、苣荬菜、婆婆丁、车辘辘菜就像碧波般地荡漾,鹅群用不着看管尽情地享受着它们喜欢的美餐,我和小弟则躺在绿毯似的草地上,吸着清新的野菜味儿,享受着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自由而辽阔的栖息之地。正在陶醉之间,我听到小弟在喊我:“大哥,你看,那是什么?”我侧身往小弟手指的方向望去,草甸子上依旧是安详平静,没有异样的感觉。“什么也没有啊?”“你好好看看,你扎的草人会走了!”我一看,果然我扎的草人在慢慢地移动,越移离鹅群越近。这里面一定有文章!细瞧,草人下面遮着一只火狐狸,正顶着草人慢慢地向鹅群靠近,边推草人边斜眼偷瞧我和小弟的动静呢!这个鬼东西,为了麻痹我和小弟竟推着草人匍匐前进,想偷偷地袭击鹅群呢!这还了得?我忙取出弹弓,安好石弹,对准草人下火狐狸的头射去。只听吱地一声怪叫,草人倒了,火狐狸现了原形,正翻身打滚地在草地上用爪子挠脑袋呢!“打中了!打中了!”小弟手舞足蹈地欢呼着,边喊边操起鞭子往狐狸那儿奔。可没等他跑到狐狸的跟前,只见那狐狸一溜烟儿似地逃走了,边逃边往我这儿看。可能它在想:是什么新式武器打得我的头这么痛呢?
我九岁那年,和小伙伴儿们去甸子里捡野鸭蛋。甸子里的苇塘有一人多深,苇草有半人多高,苇塘上到处都是野鸭窝。野鸭也很狡猾,它们利用密集的苇子杆儿作为窝的支架,再衔些苇叶编织成一个宽敞、舒适的苇窝。这些野鸭窝在水面上浮游着,随着微风和水波的荡漾而逍遥地摇晃着。
我脱光衣服钻进苇塘,立即看到好多好多的野鸭蛋,便啥也不顾了,把一窝一窝的野鸭蛋端下来,靠拢在一起,借着水的浮力往前推。当时我那个美呀,暗自庆幸自己亏得想出个好主意,伙伴儿们肯定没有我捡得多,他们只能像黑瞎子掰苞米一样,掰呀,挟呀,最终只能剩一穗!我美滋滋地推着连成片的野鸭窝往前走,边走边前后左右地寻找伙伴儿,却发现他们全不见了。我顿时急了,扯着嗓子大声喊,也听不到回音。四处全是苇草,我不知从哪儿能游出去。此时,我才知道自己迷路了。我以前听妈妈讲过,进了苇塘,如果迷了路是十分危险的,有时一天都游不出来,那十有八九就困死在苇塘里了。想到这里,我哇哇地哭起来。正在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当儿,突然听到远处有哗哗的水声响,连忙蹲下身子向声音望去。进过苇塘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长满苇草的水面上,如果你站起来朝遠处看,只能看到眼前近处的景场。但是如果你蹲下身子向远处瞧,让眼睛的视线贴在苇草上,就能看到较远的地方。这一招儿真灵,我果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东西向我游来,仔细观瞧,是一只狐狸。我没有动,把身子悄悄地向水下潜去。那狐狸越游离我越近,离我只有一丈多远。这时已是傍晚时分,苇面上荡起紫红色的波光,没法形容这美丽的景色,可此时的我却没有心思欣赏美景,只是紧张地盯着向我游近的狐狸,眼看着它向我越逼越近。不能这样等死,我还要上学呢!这样想着,我悄悄地用苇叶把脑袋遮盖起来,身子沉入水中。我知道,因为浓重的水腥味可掩盖住人体的气味,只要狐狸看不见我,我就有可能逢凶化吉。顺着苇叶的缝隙观察狐狸的动静,只见它游着游着突然站了起来,然后又慢慢地往下蹲,让身子一点儿点儿地沉到水里,只在水面上露出一个头来;它的头在水面上向四处观瞧了一阵子,也慢慢沉下去,只露出尖尖的嘴巴和两个一张一张的鼻子孔。我感到奇怪,狐狸钻到水下去干什么呢?就在我胡乱猜想的当儿,就听到远处传来水鸭子的叫声,接着就是水鸭子挣扎着拍打水面的声音。只那么一会儿,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想,那野鸭一定是被狐狸吃掉了。这东西真鬼道,偷袭的技巧也实在是高,别说是野鸭子,就是遇到我也是防不胜防啊!不多时,我的眼前出现一只母野鸭,它的身后跟着五六只小野鸭。它们浑然不知有一个可怕的埋伏和致命的危险正在等待着它们。果真按我的预想那样,突然一声嘎嘎地惨叫,母野鸭的头被狐狸叼住了,只扑楞了几下,就被狐狸咬断了脖子。它的崽子见状纷纷逃命,可它们哪里逃得出狐狸的魔掌?也接二连三地被狐狸叼住,一甩头,便咬断了它们的脖子。可那狐狸并没有马上吃它们,可能是刚才它已饱餐了一顿,没有食欲了,只是把一大四小的野鸭摆在水面上,左顾右盼地欣赏了好一阵子,才心满意足地用嘴巴推着它们向远处游去。
我把这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又一次亲眼目睹了狐狸的聪明智慧,也庆幸自己是狐狸给指引了方向才游出苇塘,绝处逢生。我看狐狸在苇塘边挖了一个坑,依次把一大四小五只野鸭埋藏好了,悄悄离开后,我才心满意足地走到近前,把它们扒出来后又用清水洗了一遍,才用衣服兜回家。我边走边想:“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人,若不是遇上你,说不定我会在苇塘里折腾多久呢,况且,哪里会逮住这五只野鸭?拜拜吧,狐狸,我还真得谢谢你呢!”
一转眼的工夫,冬天就到了。刚下完头场雪,大地就像一张洁白的纸张,留下各种痕迹,不管是人的还是兽的,就像写在纸上的字,抹都抹不干净。狐狸这种动物专拣只保留自己爪子印的地方走,一旦发现爪印有了间隔,它就倒退几步,然后快速地助跑,腾空跳过去,蓬松的大尾巴平平地展开,产生了滑翔的效果,一般能蹿出四五米远。兽夹子尽管小心翼翼地埋在它的必须之路上,一点儿痕迹没露,可是狐狸爪子却怎么也仿制不像,再精巧的兽夹子也失去了用武之地。
七十年代,家乡的肉蛋供应越来越少,家家户户却自养很多鸡,等到腊月便提前宰杀,留着过年享用,就像曲波先生笔下的《林海雪原》中描写的“百鸡宴”一样,一点儿也不夸张。家乡人有句谚语:“宁吃飞禽三两,不吃走兽半斤”。意思是说,禽类的肉就是比兽类的肉香,是肉类中的上品,既然是肉类的上品,不光是人愿意吃,狐狸更愿意吃。那时我家养了六十来只鸡,没有那么大的鸡架,就在院子的房东头处用土坯垒了个地方,晚上把鸡圈进去,白天再放出来。雪后的一天早上,我打开圈门去放鸡,看到圈门口印着乱七八糟的五瓣梅花印,就觉得不妙,一点数,果然少了一只老母鸡。
亡羊补牢吧,我急忙采取措施,用土坯把围墙垒成一人多高。心想,这回可保险了。果然,一连几天,鸡圈前再没有出现五瓣梅花印。但隔了些日子一数,鸡又少了两只。我感到纳闷,真邪门了,难道狐狸真能成精,变成人了进圈里偷鸡?我连忙转到院外的东北角观察,结果发现挨柴草垛的墙角新掏个洞,洞口有狐狸的爪印。看来只有提前宰杀鸡,冰冻起来才最保险,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自杀完鸡后,我想起了在二龙山看人参园子的三爷,打算给老人家送两只白条鸡。走到山脚时,突然觉得小肚子胀得慌,便把装鸡的兜子扔到身旁,解开裤带小解。突然,从楱子丛里蹒跚着走来一个似狼似狗的动物,慢慢向我接近。仔细一看,是狐狸,一定是偷我鸡的狐狸!它走到离我十步远的地方站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大眼瞪小眼地对视着。过了几分钟,它猛地转过身,飞快地蹿进楱子丛,还不时地回头张望,我觉得蹊跷,也跟着回头看。这一瞧不要紧,啊?装着两只白条鸡的兜子不見了!只见一只个体稍小一些的狐狸嘴里叼着我的兜子颠颠地跑远了。它兜了个圈子,与和我对眼的狐狸在楱子丛中会合了,我这才恍然大悟,狐狸竟用“调虎离山计”骗去了我送三爷的白条鸡!
没有办法,我只能空手上山去看山爷。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我替三爷看几天房子,让三爷回家品尝鸡去。恰巧,三爷下山的那天晚上刮起了“大烟炮”,一连刮了三天,刮得对面不见人,好多泉眼都冻死了,只有三爷的人参园子里的那个泉眼还没冻死。
人参园子里的泉眼是个倒置的立体梯形,上口是个长50米宽20米的长方形,逐渐缩小,底部只是一个约三米见方的泉眼,汩汩地冒着热气腾腾的泉水。
那天晚上,“大烟炮”刮过去了,月亮升起,大地一片银白。我正躺在三爷的小炕上望着如水的月光出神,突然听到有爪子挠门的声音,隔一会儿又是几下。我悄悄地下炕,推开门一瞧,见院子里蹲着一个狐狸。它跑来干什么?我回屋从门后拎出一把铁锹,便朝狐狸奔去。这时那狐狸边点头边向人参园子里的泉眼方向跑,还边跑边回头向我示意。突然,从泉眼方向传来少女般的嘤嘤哭声,忽高忽低地哭得挺伤心。过一会儿,哭声停止了,又传来像未满周岁的娃娃哭声,哭得有来道去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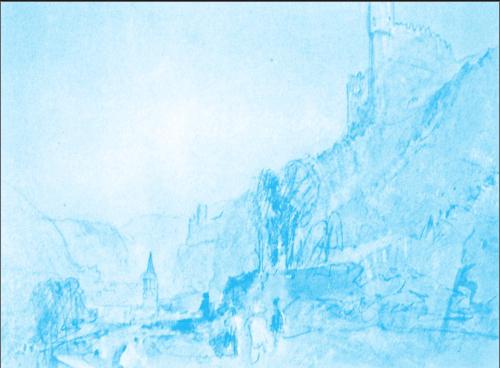
循着狐狸的影子我追到人参园子里的泉眼旁,果然看见那只个子稍小的狐狸在泉眼边来回跑。边跑孩子般地哭叫着。它几次想跃到第二层台上,无奈都是冰坡,它爬不上去,摔得直叫唤。我慢慢地沿着较缓的冰坡往下滑动,眼看着滑到它的近前。心想:这回看你往哪儿跑,我要来个瓮中捉鳖!但还没等我滑到最下一层台阶,只听嗖地一声,它两只爪子有力地搭在我的肩上,紧跟着又两只爪子蹬在了我的腰部。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已借助我的身体跳上了第二层台。可第三层台它还是跃不上去,我站在最底下的台上看着它往上跳,可它猛蹿了几次都没有跳上去,只好趴在二层台上喘粗气,两只爪子从二层台上耷拉下来。上面那只狐狸见状又发出娃娃似的哭声,那是在召唤它快点儿爬。它似乎受到鼓舞,又挣扎着往上蹿,但还是没蹿上去。我慢慢踱过去,猛地抓住它耷拉下来的爪子,一把拽了下来。这时它竟一点儿也不挣扎,温顺极了,大概它实在没有力气了。我把它托起来抱在胸前,突然感到它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一下一下地蠕动。噢,这原来是只坐了胎的狐狸,若不然它喝了水怎么跳不上去?我不禁有些可怜它了,慢慢地把它举起来,让它蜷着趴在我的后脖子上,我手腿并用地抓着冰棱往上爬,终于爬上泉眼的台阶。这时,那只公狐狸跑过来围着它转圈儿,并不时地用警觉的目光扫视着我。我知道此时该走了,它们才放心。我进屋回头的当儿,见那母狐已恢复体力,在公狐的簇拥下向夜色深处走去。
那年冬天,村里要办夜校,给社员们扫除文盲。生产队长跟我父亲说:“你家的学生正好放寒假,让他当扫盲教员吧,每天晚上教两个钟头,记半天工。”父亲一听说两个钟头记半天工,上哪找这便宜的活计,当即就答应了。
来扫盲的都是村里的三、四十岁的妇女,我和她们都很熟,平日里嫂子长嫂子短地叫着,现在让我给她们当“先生”,她们才不会把我放在眼里呢,一个个奶着孩子,叽叽喳喳地扯东家唠西家地尽说些爷们娘们的“夜生活”。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哪能听得下去这不堪入耳的“闲话”?便扯着嗓子喊:“别光顾喂奶了,你们也得把吃奶的劲儿使出来学点儿文化……”我的话还没说完,刘老大的媳妇和王二的媳妇就接茬了:“啥叫把吃奶的劲儿使出来?你做个样子给我们瞧瞧!”说着便抛下孩子发出号令:“姐妹们,上!让咱们的‘先生尝尝吃奶的劲儿是啥滋味儿!”我一看大势不好,推开门就往外跑,可是这些女人却没等我跑出生产队的大门,就把我按在雪地上了,一个个解开了怀,掏出了雪白的奶子,对准我的脸,便开始了“机关枪”的扫射……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吃这么大的亏,不停地用双手捂着嘴,可抗不住她们的轮翻“扫射”,嘴里免不了灌进不少奶水……
等我爬起来时,想看看时间,一撸袖子,手表没了。这是我跟大嫂借的手表,为的是给她们讲课时好掐个点儿。我赶紧说:“谁看见我的手表了?”一听我这么说,这些女人全愣了,当时手表可算是“大件”的,便七手八脚地在雪地里划拉,像找大针似地也没有找到。我十分懊丧,可又不好说什么,我好歹也是个男人,站直了身子说:“算了,一块旧表也不值几个钱。今天你们都回家吧,明晚早点儿来,把今天的课补上……”这些女人可有台阶下了,像群苍蝇似地轰地一声散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门,突然觉得脚下一硌,抬脚一看,哎?一块手表,正是昨晚我丢的手表!一点儿没坏,只是表带儿开了。细瞧,黑皮表带上有几个尖锐的牙印……再仔细往雪地上一看,又是那我已熟悉的五瓣梅花的爪印!难道是狐狸帮我找到的手表?我又惊又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