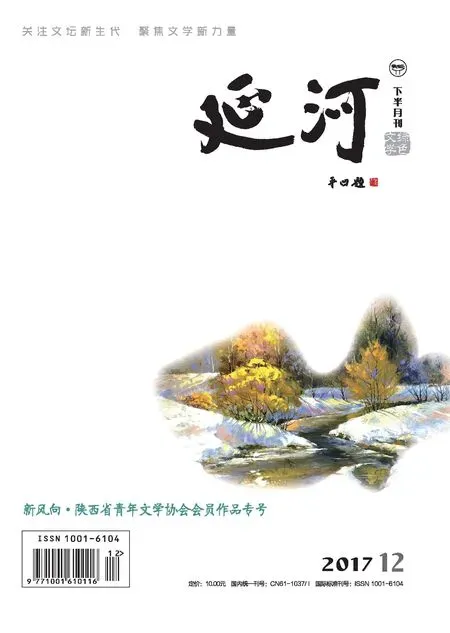相见不如怀念
□ 王振强
相见不如怀念
□ 王振强
一
西贝不是他的女朋友。虽然齐鲁有想过他们在一起,也试着去采取实际行动,然而他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她个子中等,身材苗条,毕业后去一家教育培训公司当助管员。干助管费心费力,她正准备辞职换一份教师的工作。她下班回来会喊齐鲁去学校东门外吃饭,那里有一条幽暗的巷子,巷内人烟密集,大大小小的餐馆不计其数,大概囊括了全国各地的特色菜。他们最喜欢去一家陕西面馆吃饭,老板看着不像陕西人,面也不是陕西面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有东北餐馆、川菜馆、北京小吃、新疆拉面、山西菜馆等等,夜晚各色烧烤让本已狭窄的街面更加拥堵,汽车喇叭声、三轮车师傅叫喊声、摩托车铃声,再加上由于拥堵而絮絮叨叨的行人,让人厌烦的蒙蒙细雨中,令人有些绝望。但是,多数人并不绝望,相反却感到作为一名小市民的幸福。这儿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校园中出来的某位平平常常的人,有可能就是一名赫赫有名的教授。北京,没有什么不可能。他初来北京在巷子的一个宾馆住了几天,非常简陋的一间屋子,每天两百多块。那时,天下着雨,他拉着重重的行李箱走进这条窄胡同,地面凹凸不平,污浊的雨水顺地势缓缓流淌。雨水淋湿他的衣服、头发和脸庞,鞋子也湿腻腻难受,冷风吹过,他浑身打个哆嗦。
此刻,他们一起走到巷子深处,他觉得他的生命不停前进。那有一家卖过桥米线的饭馆,米线做得特别棒,齐鲁非常喜欢吃。西贝却讨厌过桥米线,见齐鲁吃得那么香,她觉得不可理解。他依赖她,达到可怕的程度。但他并不表现出来,他几乎不主动去叫她吃饭,虽然他们住同一层楼房。有次,他们去鲁迅博物馆,他从头到尾跟着她行动,把她累个半死,就坐在西土城公园的石凳上休息。那天,天气出人意料的晴朗,她刚休班回来,穿着高跟鞋便带他去玩,一直兴致勃勃观赏整个博物馆,而他却寥寥草草走马观花。阜成门内宫门口有许多胡同,墙面重新砌过,整齐划一,显得有时代气息。搭配上太阳斜射下的阴影,或明或暗,仿佛一下子穿越了千年的岁月。她显得非常兴奋,愣是要跟一间门房前的花坛合影。她撑着一把遮阳伞,美人如花,画却只是死物,终究不如人。
他们在鲁迅博物馆门前的北京小吃馆填饱肚腹,然后坐公交达到西土城站,两人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公园,公园人烟稀少,郁郁葱葱树木遮住左右来来往往的车辆,连嘈杂的声响也几不可闻。树下的阴影特别凉快,他递给她矿泉水,她仰起头喝了几口又递给他。其实,他喜欢这样的时刻,温馨且舒适,却又难以持久,稍纵即逝。她脱下高跟鞋,用手掌摩挲脚后跟,被鞋卡得几乎出血,磨掉一层皮。对于他们而言,没有负担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快乐。毕竟,为了在大都市过得不那么烦恼,两个人的确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他内心总是对她充满依赖,害怕会失去她,即使在她身边,听着她的抱怨,他也没能彻底安心。对他矛盾的心情他搞不明白,又越来越痴迷于那种心安理得的状态,只能表现得像一个单纯的人一般。
当他们前脚搭后脚走在平坦又崎岖的道路,感受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时,常常幻想未来会有惊喜发生,不单单是他们,这是大多数选择在北京发展年轻人共同的梦想。他们明白的懂得了这个世界正在围绕他们这一代人运动,他们生活艰辛,踉踉跄跄,生存条件恶劣,极力想抓住稍纵即逝成功的机会。
他要了一碗过桥米线,而她选择了三鲜纯菜砂锅。当然,他要了一瓶啤酒,而她微笑着向老板要了杯白开水。齐鲁吃得非常开心,总是给她夹肉丸子。她摇着头,漏齿一笑,爽快的又夹到他的碗中,嘴里还说:“你吃吧,看你瘦的!”吃完出来,他们到附近的超市购物,他有点架不住长途跋涉,老是累得提不动腿。那家超市是她和她前男友经常去的地方,即使现在分手了,她依然喜欢去那儿购物。他也不介意,很害怕她会又突然哭着向他将过去的点点滴滴,那次毫无防备的情感爆发的确让他受到惊吓,但又非常高兴,了解一个依赖之人过去的伤心事,是可以得到心安和满足的。
二
说实话,女人真是男人的救星,虽然她们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短视,然而身边没有女人的男人,生活那是一团糟。
天色已晚,街道冷冷清清,高大粗壮的梧桐树遮蔽了路旁的小门小店,偶尔三三两两的行人匆匆走过,一些小贩守着铺子,冻得直打颤。饭店接近打烊,店主们结束一天辛苦的劳作,坐在桌旁聊天,厨师也难得歇息,穿着白色油渍渍的大褂。他们深夜经常去一家饼屋,这家店的女主人和蔼可亲,各种饼的价钱公道,分量也足。他们点了两份葱花饼,一人一小碗鸡蛋汤。
“你的脸怎么了?”西贝看他淤青的脸颊问道。
“没什么,挤公交的时候不小心被人碰了。奇怪的很,那么多人偏偏我碰到一个醉汉,你简直想象不到他挤公交拼命的样子。”齐鲁撒谎说。
“不像,感觉有人狠狠揍了你一顿。”她说,神色狐疑。
“哈哈,你想多了,”他赶紧接着说,“就我这温和的性格,哪会轻易得罪别人,再说有人揍我我打不过就跑啊,哪会让人家一顿暴揍?放心啊,我从来没有得罪人,也没人会处心积虑揍我。放心吧,我得比兔子都快。”

“不过,舍友说前几天有人在咱们楼里闹事,有个人被打惨了。”
“好了,”齐鲁说,“不要瞎猜了,我生龙活虎,一点问题都没有。”
气氛有一阵的难堪。饼和汤端上来,齐鲁用勺子不停搅拌鸡蛋汤。西贝看她郁闷的模样,给他夹了一块饼。
“快吃,不然待会凉了。”她说。
“我想说的是……”齐鲁抱歉的语调说,“提到不光彩的事多少有些别扭,我交了几个朋友,他们用我的名字和地址惹上麻烦,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尽管我现在依旧不解气。过几天,我们会一起去讨个说法。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一个疯狗乱咬人而已。”
“讨说法?”她冷静地说,“有说法么?”
“当然。”齐鲁斩钉截铁的回答,一本正经地看着她。
西贝一边听,一边敷衍点头表示赞同。但齐鲁可以感觉到,她表面上认同可骨子却对此嗤之以鼻。毫无疑问,她认为他们在多此一举,她的理智穿透了事件的表面。她甚至可以点破他们内心一直逃避的疑惑,在这个风高清亮的夜晚给他上一堂生动的人生课,就像一个看破人生的智者,向迷途的人指明方向。但是她知道她并非他人人生的裁判员,况且依照齐鲁的性格,恐怕会闹得很不愉快。
“我支持你去讨回公道,不过你不应该好好上班么?”西贝夹起一块饼放进她的盘子中,然后用筷子拔掉葱花。
齐鲁一口一口闷声喝汤,对她的问题不予回答。西贝似乎也生气了,用筷子不停扎盘子。齐鲁坐在她对面,背后是老板三人聊天。他抬起眼皮见她不快的样子,心里颇感后悔,为了缓和他们尴尬的气氛,在她无声的抗议下,他给她夹了一块饼。齐鲁喜欢她。是的,他毫不怀疑地喜欢她,他不忍心看她伤心。在离家上千里的异乡,他们称得上彼此心灵的依靠,撇开男女关系不谈,由于在繁华都市共同生活而深切体会到彼此的不易,这份难得的默契变得弥足珍贵,好像彼此是对方的影子。
她在齐鲁心中的地位别人无法取代,可他对西贝的了解却很少。高中毕业后数年她们未曾见面,几年的大学生活了无音讯。这大概就是他们并不熟悉的原因。此时,他们的相遇需要时光的滋养,就好像他们需要时光填补过去数年因为陌生而拉开的沟壑。他们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可以开辟一块自个的小天地,在那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中,可以感到的舒适和安全。
“好吧,我听你的,不再胡混了。”齐鲁假装道歉。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愿意做什么去做。”她漠不关心。
“不了,好好工作攒钱娶老婆。”
“哪个女人看得上你!”
“为什么看不上我?”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
她不说话了,微笑着喝完蛋花汤。这样没有营养的对话已经发生过多次,齐鲁常想有朝一日把他们之间的对话记录下来。但他只是想想而已,从来没有付诸实行。很有意思的是,西贝如果生气了,这些幼稚的对话往往可以令她发笑,齐鲁便有意识的充当幼稚对话的对象。
“吃完了么?回去吧?”
“走吧。”
“嗯,很晚了,明天还要上班。”
“对。”
三
他心不在焉的上了一天班,下班后匆匆忙忙地跑回宿舍。他坐在公交车,看着外面或明或暗的街道,一排排黑黝黝的树木,一辆辆闪光的车灯,一个个匆匆的身影,都从眼前晃过。往日堵车的印象今日却毫无反感,只觉得世事无常。一眨眼地功夫,他已经到了目的地,选了一家经常去的饭店开始大吃特吃,可心情却非常沉重,菜嚼在嘴里却嚼不出味道。这会儿,他看着新闻联播,厨房里厨师正在熟练的炒菜,顾客正在跟服务员点菜,老板娘坐在收银台点钱,除此之外显得静悄悄的。然而就在此刻,窗外下起了滂泼大雨,哗啦啦的声音瞬间掩盖了世间的喧嚣。他咽下最后一口菜,来到收银台前向老板娘交钱,外面的街道已然成雨水的海洋。他走出饭店,站在门口发呆,地面飞溅起的水花弄湿他的鞋子和裤腿,冰冷的紧贴着他的小腿。刚才热闹繁华的街道一下子人烟寥寥,机动车也不见了踪影,他难得在狂躁的雨水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他看着昏暗的夜色,心头竟然生出一丝爽快的情感,试图张开双臂拥抱那份满足,才发觉身边挤满了躲避突如其来大雨的人们,仿佛在这场秋雨中未曾约定的聚会。
“下雨天真好!”西贝在他身后说,熟悉的声音仿佛有穿透时空的力量,不论多么嘈杂的环境都可以清晰地听见。“我本来可以跑回宿舍的,无意看见你在饭店东张西望,便停下来陪陪你。”一阵暴乱的雨滴又落下来,无数败叶夹杂着胡乱落地,噼噼啪啪的声响成了世界主旋律。
齐鲁惊讶的忘记了说话,目瞪口呆看着眼前突然冒出的美女,对她的问候报以沉默。然后隔着人群他看见她发光的眼睛:“这么晚才回来啊,刚才没有听清楚你的话,吃饭了么?”
她挥手示意他到饭店的边角,齐鲁挤过人墙终于与她并肩站在一起。“没想到会猛然间下这么大的雨。”西贝说。她冷得打了哆嗦,双手不停挥舞搓胳膊以保持温暖。
“穿我的外套吧。”齐鲁大声说。
“不用。”她连忙拒绝。
“那你这么冷,怎么办?”齐鲁又大声说。
她狡黠的看他一眼,神秘地微笑。
“现在雨小多了,你追到我我就答应你任何请求。”她说完,举起包踏雨跑了。
再就无言了。齐鲁愣在原地半天,她跑动溅起的水声在他耳旁回响,淅淅沥沥的微雨迎风飞舞打湿他的脸颊,清凉的感觉让他一下子回过神来,拔腿追上去。
他们的世界安静了。他们前后奔跑,凉飕飕的雨水滴落下来,打湿他们的头发、脸颊、衣服和裤子,地面的积水飞溅起来,鞋子早已湿透。他们最终躲进学校内的联通收费室,窗外的雨又下的更大了,雨滴顺着玻璃哗啦啦流个不停,路过的汽车开着模模糊糊的灯向前冲去,一下一下溅起一大片水浪。“我们先在这儿避避雨吧。”她跺跺脚,用手紧紧衣服,拉着长长的音调说道,齐鲁感觉鞋子和裤子已经湿透了,黏糊糊的粘住他的皮肤。他见西贝冷得发抖,想要上前去抱团取暖,但他鼓不起勇气,一种无形的压力横隔在他们中间。现在,他们只能尴尬的站在一起,看着外面不知何时停息的大雨。他想说点什么缓解他们的气氛,可惜他说不出。西贝仔细看他局促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突然他们注意到暴雨小了。西贝推开玻璃门,伸手出去,几滴细细的雨水落在她的手心。
“雨停了。”她高兴地喊道。
“走吧,我们回去。”齐鲁赶紧说。
“等下,我有话对你说。”西贝又把门关上,拉住他的手。“你知道我喜欢你吧,你难道不喜欢我么?”
齐鲁曾经无数幻想把她拥抱的那一刻,体会她的温柔,用他们的双手营造未来幸福生活。不过,也许将会发生的事实全然不如他的想象,他们的结合可能会变成彼此的累赘。当然,此刻他全然没有确定两人关系的冲动,眼睛怯弱地看着她,徒然浪费她的热情。或许为了证实他的想法,西贝又朝他靠了靠,盼望他可以拿出男子汉该有的做派。他微笑起来,仅仅摸摸她的脑袋。西贝的忍耐力已经到达极致,她从来没有如此生气却无气可出,所以憋着脸低下头狠狠踢了他的小腿,转身便走,不再理会齐鲁的呻吟和呼喊。以旁观者的角度,似乎齐鲁拒绝了西贝的示爱,但仔细思索其中情况,他在犹豫不决中错过了对的人。事实上,他过了疯狂的年纪,虽未到大叔的程度,起码也是该妥妥当当成家立业,这些不同身份转换的过程是痛苦的。他边跳边追赶上去,大雨停歇了,微雨还在密密飘洒,地面积水如同小湖泊,一个接连一个,有深有浅。他踏出一个水潭又踩进另一个,裤子完全湿透,脸上沾满泥点,头发湿漉漉紧贴头皮。他刚一追上西贝,一把拉住她,有点气急败坏,立刻唾沫星子乱飞质问她跑什么。西贝很烦,甩开他的手,瞪了他一眼,抬起脚狠狠剁在他的脚面。齐鲁的表情一下子定格在目瞪口呆的模样,半天不见反应。西贝再次只顾只朝宿舍走去,这时齐鲁钻心的疼痛才经过他迟钝的脑袋。他咬紧牙关,单脚蹦蹦跳跳,双手握住鞋子揉搓,根本顾不得多么脏。当天晚上,他颇气闷回到宿舍,闷闷不乐,失去洗漱的动力,呆呆坐在桌前发呆。他想要去找西贝解释,但他拉不下脸。不过,他觉得他的脸面其实次要,内心深处他对他们的感情感到恐惧,可他不愿意承认他是懦夫,他宁愿认可他并不喜欢他。这时,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真路来电话了。他看着那个电话号码,有种不好的预感,不知怎么回事,他觉得宿命中会有个电话,似乎从前经历过相同的一幕。他猜不到结尾。
“你在哪里?”他问道,声音稍微颤抖。
“在宿舍。怎么了?”齐鲁问。
“我在南门,你出来,有事商量。”说完,他便挂了电话。
齐鲁收拾心情,重新换上衣服,他这种人总是勇气可嘉,能力和远虑却不足,好像冥冥中总与纠纷有缘,也就是这会,他踏出那学校的大门,看见真路带着帽子站在一家水果摊前,双手插在口袋,衣服领子高高竖起,咋看像极电视中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们好几天未见面,齐鲁敏锐觉察到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恍恍惚惚鬼鬼祟祟,有一丝躲避别人的意思。他们一起来到角落的一家小吃店,店里空落落的,店老板懒懒散散给他们端来馄饨,顺手递过来两个勺子。正当他思索怎么开口向他询问叫他出来的原因,真路七上八下述说他这几天的遭遇,整个叙说的过程像一个绕舌鬼,或者说一个说唱歌手,根本不知他在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你到底嘟嘟囔囔说啥。”齐鲁打断他说。
真路明显在隐藏他的经历,模模糊糊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齐鲁知道他心里藏着秘密。渐渐地,真路进入重点,齐鲁听见外国人三个字精神一振。他从真路口中听到外国人三个字并不是第一次,他知道真路的态度非常激进,每次说出这三个字都充满轻蔑和嘲弄,而这次却轻描淡写带过,仿佛在谈论已过去的人。“你把外国人怎么了?”齐鲁警觉地问。“没怎么。”他回答。“真路,我想听真话。”齐鲁有点慌。“不知道,我用刀捅了他,不知道生死,我不知道自个怎么了。”他低着头说,声音低到只能他们听见。“什么?你疯了!”齐鲁忍不住惊呼。“啊呀,镇定点,你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啊!”真路见他慌了,赶紧叫出来,示意他注意周围。齐鲁强忍住心头的忐忑,脸色苍白,惊恐地看他,冷汗从额头冒出。“瞧把你吓的!”他笑起来,笑声抑扬顿挫,“我开玩笑的。”他拍齐鲁肩膀的说。“哎哟,吓死我了,你个傻帽!”齐鲁松了一口气,擦擦汗。“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他又补充一句。“不过,我喜欢反转,我没开玩笑。”他这次认真地说,整个人镇静下来,表情严肃,看样子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了。“真的?”齐鲁也严肃问。“嗯。”他点头回答,端起碗喝光汤,留下二十块钱走了出去。
四
西贝可爱的脸庞闯进他的脑海,明媚的阳光下她的裙子像一朵绽放的花朵,旋转飞舞,吸引他的眼神,一阵阵清脆略带撒娇的笑声,撞击他柔软的心脏。齐鲁掏出手机,拨通了西贝的电话,铃声响了一会。她没有接。齐鲁看看手表,按照日常的时间,她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或许,她在人烟嘈杂的公交车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令她无力去掏出手机,也许她根本听不见她的手机响了。他决定去她必经之路去接她,他想改变一贯的生活习惯,做一些大胆的尝试,要争取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屋外的空气清新,带有夜晚降临前特有的暧昧的、依依惜别的特色。伴着寒冷的西风,他站在大门口,目睹车水马龙的街道,匆匆而过的人们。他又拨通西贝的电话,依旧无人接听。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响,便沿街朝南走,再向左拐进一个小道,再向南有一处卖麻辣烫的小店。他平常喜欢打包回屋吃,这次破例吧。他发现店里人特别多,一间窄窄的店面坐满了,外面摆放五六张小桌子,三五成群的小年轻人坐着,嘻嘻哈哈谈论琐碎生活。突然间,透过老板向顾客传递麻辣烫的玻璃窗,他看见西贝和一个男生吃饭。他们每人跟前摆放一只大腕,热辣辣的串串冒着热气,熏得他们脸蛋通红,头顶直冒热气。据他所知西贝在北京独身一人,更不会有亲近的异性朋友。这么长时间他压制他的感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心底默认为她属于他,他们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对夫妻,不论眼下他们的距离多么遥远或者两人多么亲近。而这个男人的出现,让他的幻想变成水中月镜中花,当然对于他而言,所有的一切日常生活,迟早都是水中月,迟早都是镜中花。他对此提不起丝毫的兴趣,他更关注的是精神世界的纯粹,是另一个层面的满足。然而,他看见他们一起开心的吃饭,互相夹菜,西贝拿出抽纸递给他,两人幸福的微笑,那画面像一幅挂在墙上的油画。他喜欢站着静静品味其中的味道,从未想过充当画卷的主人公。内心的冲击一会散去,他强装微笑,脸部的肌肉有点僵硬,看上去的笑容狰狞。他从容走进去向西贝打招呼,毫无难过之态,夸赞她漂亮、温柔。西贝脸色更加红润,站起来言语不清介绍她的男朋友,原来他从深圳回来只为求和她复合。她没有拒绝。店面更小了,左右各一个门,可依旧解决不了顾客拥堵的问题。他们三人站在中央,其他顾客绕道而行,老板见他们三人的架势,也装作不知道身后出现的状况,不停叫号摆碗。天气寒冷,尽管月亮已升起,大地却依旧被黑暗笼罩,不解风情的汽笛声永远让人燥热的思维越发急迫,刚刚散发暧昧气氛的夜晚失去光泽,只有黑沉沉的土地上长着死气沉沉的植物,还有奔波不止的人。他吸了一口气,寒冷的空气沿着的喉咙进入身体,冰意直通心底,他的全身冻得几乎发麻。这时,这次意外发现的痛楚卷土重来,他忍耐强烈的悲怆向他们告别,连忙扭转身意识模糊冲出饭店。“真不错,终于解脱了,不必再幻想承担无谓的责任。虽然我们是同学,是同乡,但我要默默祝福他们得到尘世的幸福,而我要向伟大的事业努力。”他像醉酒的人,眼睛盯紧脚下的路,脑海反复念叨,跌跌撞撞回到宿舍。稍微晚点,他鼓起勇气敲开西贝宿舍,一个面熟的姑娘打开门,告诉他西贝今晚在外住宿。他的心跌倒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