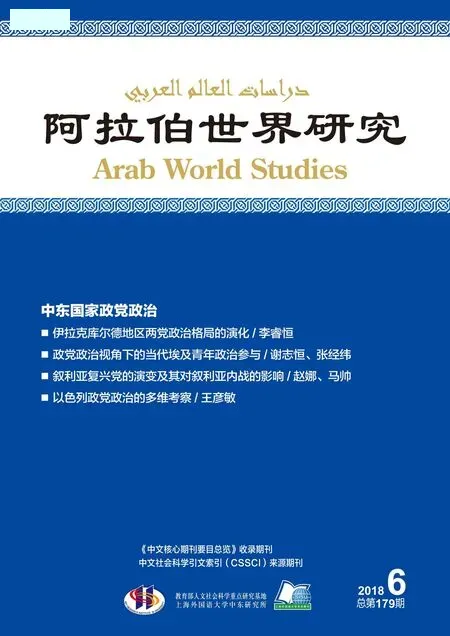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以索马里为例*
徐亚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亚、非洲、南亚、中亚和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内部的异质族群之间因权力利益冲突、谋求自治或分离而暴乱频发,族际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冲突形式之一,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推动国家间深度互动,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融,族际冲突外溢风险增大,挑战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当前,在西亚和非洲地区,也门、苏丹、索马里等失败国家[注]国家失败是对国家建构失败的抽象描述,相关国家被称为失败国家。这两个概念,既是对国际体系中相关国家客观存在现象的表述,也有一定的西方话语色彩。因此,文章中对相关表述添加双引号的部分,除为了表示特殊强调外,也意在说明其体现西方政治理论特色的概念内涵,以便与其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加以区分。的治理困境愈益影响地区与国际秩序的重塑进程,而这些失败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安并危及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存在且水火不容的族际冲突。
索马里地处非洲之角,扼亚丁湾和红海贸易航道,战略地位显要,历来是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象。自1991年以来,该国始终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被国际社会视为典型的“失败国家”。长久以来,索马里族际冲突问题严峻,这不仅制约着其国内政治和解与重建进程,甚至不断外溢,使其成为非洲之角和西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博弈场。本文试以1991至2017年间索马里的族际冲突问题为分析对象,探究其复杂的表现、成因及对索马里国家重建的影响,以进一步揭示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之间的关系。
一、 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的学理分析
族际政治是族群之间基于族类情感认同和不同利益诉求,围绕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并由此形成一种政治认同和政治影响。正如民族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族群及其政治互动则影响着国家内部的次结构生长。长期以来,族群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各占一隅;而在当代国际体系下的国家建构中,各族群以多种方式,主动或被迫参与政治经济利益博弈,对国家发展和国际体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也逐渐凸显了其政治学内涵,使族际政治研究成为政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族际冲突是指发生在种族、民族、部族、氏族等不同层次的族群内部,某两个或以上群体间为争夺利益而发生冲突的政治互动形式。族际冲突可以分为国家内部的族际冲突和跨界族际冲突,其原因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性。解决族际冲突问题,既需要实现国家内部基于合法性、权威性政府主导下的族际和解与整合,又需要国际社会在尊重国家发展独立性和特殊性基础上给予一定支持。在当今国际体系中,许多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族际冲突问题。其中,失败国家的族际冲突问题尤其突出,它不仅影响一国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地区和世界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
在学理上,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具有同源性,其最重要的共性即二者都与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存在关联性。在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下,族际冲突多源于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充分和不完备,而这也是国家失败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中,民族国家起源并发展于欧洲,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发展形态,与民族和民族主义相生相伴,强调国家与某一“民族”在疆域上基本一致,从而使自然形态下的“民族”转变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注]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7页。民族与民族国家乃是一体两面,民族主义为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合法性。根据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在“主体民族”发育不充分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族群之间为获取国家主流认同而争夺政治经济权益,导致族际冲突的产生;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或民族国家建构滞后的政治状态下,“民族”概念处于缺位状态,“民族”抑或“主体民族”同样缺乏发展的充分性,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其他族群,在国家运转和发展中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氏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盛行的非洲国家,氏族或部族对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尤为显著,甚至发展为族际冲突之现实。[注]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0页。
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下,国家失败意指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冷战结束后,被传统意识形态冲突掩盖的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显现,部分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国内冲突激增、分裂主义凸显、经济发展脆弱、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等问题。鉴于此,有学者试图用“失败国家”定义相关国家,并分析相关问题。[注]采用“失败国家”概念对相关国家进行分析的学者有杰拉尔德·赫尔曼(Gerald B. Helman)、史蒂芬·拉特纳(Steven R. Ratner)、罗伯特·罗特伯格(Robert I. Rotberg)、罗伯特·贝兹(Robert Bates)等。此外,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艾勒·威廉·扎特曼(Ira William Zartman)、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与世界银行还分别提出了“准国家”(quasi-states)、“崩溃国家”(collapsed states)、“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s)等概念定义此类国家。参见Gerald B. Helman and Steven R. Ratner, “Saving Fail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Vol. 71, No. 89, 1992, pp. 3-20; Robert I. Rotberg, When S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10; Robert Bates, “State Fail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No. 11, 2008, pp. 1-12; Robert H. Jackson, Quasi-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3-26; Ira William Zartman,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5, p. vii; World Bank, Engaging with Fragile States: An IEG Report of World Bank Support to Low Income Countries under Stres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6。“9·11”事件后,美国频繁使用“失败国家”指称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并将其视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温床,自此,“失败国家”日益频繁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事实上,“失败国家”既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现象,又是西方社会针对这种现象提出的一个体现西方政治理论特色,并为其反恐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提供理论支撑的政策性概念,而在关于国家失败的学术讨论中,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是其最重要的判断标尺。[注]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失败国家处于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在政权合法性、权威性、现代性方面存在不足,无法为人民生存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公共服务保障,由此引发的国家混乱不仅影响本国及其人民的生产与生活,甚至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也成为西方衡量所有国家建构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参见Robert Bates, “State Fail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No. 11, 2008, pp. 1-12; Stewart Patrick, “Failed States and Global Security: Empirical Questions and Policy Dilemma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9, No. 4, 2007, pp. 644-662; Robert I. Rotberg, When S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p. 1-47; 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The Guardian, April 7, 20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apr/07/1, 登录时间:2018年1月3日;“Failed States Index,” Fund for Peace, May 10, 2005, http://www.fundforpeace.org/fsirankings-2005-sortable, 登录时间:2018年1月3日。
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视域下的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关系密切。在许多西亚和非洲国家,以传统部族主义和氏族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国家运转及发展现实,与西方推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结果非但未能有效推动其部族、氏族等族群转变为政治民族,实现民族身份建构,反而刺激了更多基于部族、氏族等族群的社会动乱,导致诸多国家在西方标准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走向失败。从欧洲文明进程中发展而来的民族国家理论,不仅没有考虑二战后诸多新独立国家的族际政治现实及其殖民历史遭遇,反而以“失败国家”概念定义这些在民族国家建构中不断受挫的国家,甚至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将自由民主价值观视为“拯救”失败国家的“灵丹妙药”,结果不仅未能改变此类国家失败的现实,反而导致族际冲突日趋激烈。
纵观十余年来的《失败国家指数》名录,位列前十的失败国家大都来自西亚和非洲地区,而且均面临族际冲突问题。以索马里为例,自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uhammad Siyad Barre)领导的军人政府在1991年倒台后,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被西方国家视为典型的“失败国家”或“崩溃国家”。[注]自2005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和美国和平基金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失败国家指数》名录,2014年改为《脆弱国家指数》。其中,索马里七年高居指数名录第一位(分别为2008~2013年和2016年),三年仅次于南苏丹,位居第二位(分别为2014年、2015年和2017年),2006年居第六位,2007年居第三位。参见“Failed States Index,” Fund for Peace, http://fundforpeace.org/fsi/category/publications-and-downloads/, 登录时间:2018年1月3日。虽然国际社会多次出面助其重建政府,先后于2000年建立索马里过渡国民政府、2004年建立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但这些政权都未能获得国内各部族、各政治派系的认同。2012年,索马里结束过渡期,索马里联邦政府宣告成立,但新的联邦政府仍面临国内派系争斗、地方分离主义、暴恐势力猖獗、社会动荡不已等国家建构的现实困境。
国内外学者对索马里国家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而在次国家层面,只有少数学者指出氏族主义是索马里民族主义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索马里国家崩溃的根源,也是索马里国家重建过程的基础性力量。[注]参见Walter S. Clarke and Robert Gosende, “Somalia: Can a Collapsed State Reconstitute Itself?,” in Robert I. Rotberg, ed., State Failure and State Weakness in a Time of Terro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 132; Hussein M. Adam, “Somalia: A Terrible Beauty Being Born?,” in Ira William Zartman, ed.,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5, pp. 69-89.但是,相关研究将索马里族际政治简化为氏族主义,着重分析氏族之间为争夺国家建构主导权进行的斗争,而忽视了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根源与表现的多元性和多层性。在国内外关于索马里族际政治的研究中,普遍对索马里不同层次族群的定义和划分含混不清,甚至存在较大分歧,影响了对索马里国家失败原因及重建进程的准确分析。
实际上,索马里是非洲鲜见的民族成分单一的国家,其疆土内的国民同属索马里人,同操索马里语,同是逊尼派穆斯林;但其国家内部又生活着多个次民族意义上的族群,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渊源和生活方式。
在民族层次上,索马里既是当代国际体系和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可以表述为索马里国家[注]当前索马里的国家名称为“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又是历史、文化、社会意义上的索马里人共同体。在不同语境下,“索马里人”或“索马里民族”的表述各有其义。索马里人在其历史发展中建构了相对独立且完整的社会形态,因而在索马里独立后成为其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族群。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家陷入混乱,索马里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建构过程中断,因此,索马里人很难被称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意义上的“民族”。但是,在涉及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之间的“大索马里主义”问题时,索马里人又是一个展现出浓厚政治色彩和特殊政治诉求的概念,人们仍认为索马里人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民族,以区别于埃塞俄比亚人、肯尼亚人等异质民族。概言之,索马里人或索马里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
在次民族层次上,不同的专家学者对索马里主要族群形态的划分各不相同。结合相关学者和国际智库分析报告的定义及分类,本文认为索马里或索马里人由达鲁德、哈维耶、伊萨克、迪尔和拉汉文五个主要氏族家庭联盟(clan-families)组成,[注]Mohamed Haji Mukhta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New Edition,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3, pp. 1-5.并简称其为五大“部族”。在政治学和民族学中,部族是指在特定生活地区,具有一定血缘基础的氏族或者氏族家庭的聚合体,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特色。在索马里,这五大族群各都有自己的始祖,按照父系追溯血统的习俗从始祖传下姓氏,且各有其方言、标志和生活习惯。
在五大部族内部,又有若干支系,即氏族。索马里的氏族表现为典型的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形态,由若干家庭组成,具有家族特点。其中,父系血统对家族聚合及政治效忠的约束力,超越了对部族首领的依附,因此,氏族关系内部的家庭集团的对立和合作,都是以父系追溯血统的习俗为基础的。[注]顾章义等:《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页。氏族内部起到约束作用、最经常调动忠诚关系的,是其从属的“血亲复仇集团”(Diya-paying Group)。在氏族内部,各血亲复仇集团互相敌对,但当氏族遭到外敌攻击时,他们又会联合起来保护集体利益。[注][英] 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赵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0页。
索马里的族群主要包括氏族(哈巴尔·吉迪尔、阿布加尔、伊塞、盖达布尔西等)、部族(哈维耶、达鲁德、伊萨克、迪尔、拉汉文)、民族(索马里)三个层次,而索马里的族际冲突就是指发生在氏族之间、部族之间以及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跨界索马里人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它们对索马里政治生态和国家建构有着重要且深刻的影响。
二、 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性质及表现
自1991年西亚德政府垮台以来,族际冲突对索马里国家建构影响深远,成为国家长期陷入无政府或冲突状态的重要原因。索马里的族际冲突有着鲜明的特点和复杂的形式。
(一) 部族认同与殖民历史相结合,催生地方分离主义
1960年6月,英属索马里与意属索马里先后独立,之后合并建立索马里共和国,在索马里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开始了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但是,在此后30年间,由于索马里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民族冲突、地方政党权力分配失衡、军人政府的政策失当、国外高压干涉等因素的合力影响,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屡遭挫折,实现统一民族国家的愿望最终落空。其间,原英属索马里的主体索马里兰,在索马里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引起索马里兰人的不满。随着法属吉布提宣布独立、欧加登战争失败,索马里兰人逐渐意识到建立包括法属吉布提、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肯尼亚北部边区等索马里民族聚居区的“大索马里”国家的目标遥不可及,于是,索马里兰人开始表现出谋求独立建国的倾向。他们以殖民历史经历为依据,认为英属索马里即索马里兰有权通过公民投票方式重获独立,成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并获得国际社会对公投结果的尊重。[注]王磊:《索马里兰独立问题浅议》,载《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3期,第24页。最终,索马里兰在2001年通过立宪公投,宣布政治独立。此后,在国际社会支持的多次索马里全国和解会议中,索马里兰公开拒绝接受索马里政府的管辖。2017年11月,索马里兰进行了新一轮的总统选举,在索马里政治进程中与联邦中央政府“渐行渐远”。
索马里兰的独立建国主张基于伊萨克部族认同和英属索马里殖民历史传统,其中,部族长老积极推动力量凝聚,深化了索马里兰与索马里其他地区的认同差异,并因此加深了其与索马里中央政权之间的裂痕。索马里兰地区以伊萨克为主体部族,在索马里文人政府期间,伊萨克部族在国家政治进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先后产生了两任总统和一任总理;英语成为索马里官方语言后,索马里外交部长、外贸商务部长也都来自伊萨克。[注]Mohamed Haji Mukhta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New Edition, p. 122.然而,在西亚德军人政府时期,达鲁德部族控制了中央政府,伊萨克部族逐渐被压制,由此引发了索马里兰地区伊萨克人的强烈不满。索马里民族运动,就是一个在伊萨克部族长老的支持和动员下、以伊萨克为主体而形成的抵制西亚德政府的反抗组织,并随后宣布建立索马里兰政权。
索马里国家长期处于战乱和无政府状态,而相形之下,西北部的索马里兰却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之“国”。[注]Mark Bradbury, Becoming Somaliland, El Paso: University of Texas, 2011, pp. 109-136.虽然尚未获得索马里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索马里兰也只是被称为“半自治国”,但在政治建设中却表现出与索马里过渡政府或联邦政府迥然相异的政治理念,显示出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挑战统一索马里民族国家的建构路径。
(二) 基于部族和氏族的利益集团派系化、军阀化导致的长期武力冲突
自1960年索马里建国以来,各届政府内部就充斥着部族和氏族利益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立国初期,为解决索马里与邻国的边境争端、实现“大索马里”民族国家目标,索马里表现出明显的团结凝聚态势,民族主义一度超越部族主义和氏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但是,欧加登战争失败以及西亚德政府倒台后,根深蒂固的部族及氏族排他性浮现,代表不同部族和氏族利益的派系与军阀之间争端迭起,各派割据一方,成为统一国家政治建设的阻碍力量,索马里由此陷入长期混乱,国家动荡而民众涂炭。
20世纪80年代末,索马里各地因为反抗西亚德政府,以部族和氏族为基础,组建了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派系政权,主要包括以伊萨克部族为主的索马里民族运动、以米朱提因氏族为主的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以哈维耶部族为主的索马里联合大会党、以拉汉文部族为主的拉汉文抵抗军等。在反抗运动中,各派系之间因部族和氏族利益分歧无法实现联合,各自为战;西亚德政府垮台后,为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权,各派之间又拒绝和解,继续割据一方,以致陷入混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索马里联合大会党中代表阿布加尔氏族的阿里·马赫迪·穆罕默德(Ali Mahdi Mohamed)与代表哈巴尔·吉迪尔氏族的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uhammad Farah Aideed)之间的对峙。
西亚德出走摩加迪沙后,马赫迪和艾迪德在权力分配上发生分歧,最终他们所代表的两个氏族之间矛盾激化,将摩加迪沙分割为南北两个武装阵营,阿布加尔氏族控制北部,哈巴尔·吉迪尔氏族控制南部,并分别宣称建立“全国性”政府,致使首都长期处于武装对峙状态。1992年索马里遭遇旱灾,到1993年初,“天灾人祸”已导致100多万难民逃亡异国他乡,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注]毕健康、陈丽蓉:《索马里难民治理的困局及出路》,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6期,第51页。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开展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但救援物资因国内派系争斗而无法顺利到达受援地,其最大阻碍来自被称为“死亡三角”的三个地方派系之间对救援物资的争夺:艾迪德为首的占据拜伊、巴科尔地区的索马里民族联盟;马赫迪控制的索马里联合大会党;穆罕默德·西亚德·荷西·摩根(Mohamed Siad Hersi Morgan)统领的西亚德政府残余势力。[注]EIU, Country Report 1st Quarter 1996: Ethiopia, Eritrea, Somalia, Djibouti, Londo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6, pp. 28-30.面对人道主义危机加剧的现实,联合国和美国主导了对索马里的两次维和行动,以保障救援物资顺利送达,并推动解决派系争端,解除地方武装,恢复索马里和平。但是,维和行动引起了各派系的暴力抵制,美军在遭受“黑鹰坠落”(指1993年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惨痛经历后撤离索马里。
在各大派系和军阀的割据争斗中,其领导人利用氏族和部族认同,动员本氏族或部族内部成员加入对其他派系的斗争,以获取本氏族或部族对地方甚至对全国的领导权。在此过程中,虽然曾经出现派系内部不同氏族或不同部族之间的联合,但各族群的终极目标仍是企图攫取相应的政治权力,并在随后的国家政治进程中分得一杯羹。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各政治派系和军阀之间的冲突,是氏族、部族认同及其利益分歧的政治化表现,并使索马里陷入长期的武装冲突。
(三) 跨界民族问题导致周边国家卷入,索马里内战“外溢”为地区冲突
跨国界居住的民族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与周边国家政府或国内其他民族发生冲突而产生的一类族际政治问题,常被称为跨界民族问题。[注]周平:《民族政治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如上文所述,索马里人是非洲之角地区同操索马里语、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域性的人群共同体,但其民族性和政治性却因殖民时期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的分而治之的殖民历史而破碎化。依据国际法对非洲各国疆界划分的规定,索马里人并未全部聚居在索马里共和国。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肯尼亚东北边区和吉布提,均有相当数量的索马里人分布。为实现索马里民族统一,建国后的索马里与三个邻国关系趋于紧张,冲突不断。1963年,肯尼亚东北边区的索马里人聚居区被纳入肯尼亚东北省地区建制,实现自治;1977年,吉布提公投独立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1978年,在欧加登战争中索马里战败,欧加登地区以自治的方式继续接受埃塞俄比亚政府管辖。自此,索马里期望联合非洲之角各地索马里人建立“大索马里”民族国家的希望宣告破灭。但是,生活在共同边境地区,因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带来的跨界民族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
20世纪90年代以来,索马里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与邻国的索马里人基于族际认同以及利益交织,导致索马里形势日益复杂化,而周边国家因担忧甚至恐惧而不断卷入索马里内乱,最终使索马里境内的族际冲突外溢为地区动荡。在欧加登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索马里人虽然获得自治,但很难融入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内战后大批难民涌入欧加登地区,不仅增强了以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索马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成为影响埃塞俄比亚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也因此成为地区国家之间的一大角力点。[注]张湘东:《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第51页。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在边界争端问题上敌对情绪严重,因此,厄立特里亚利用欧加登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暗中支持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为其提供援助,以抵消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为该地的紧张局势火中投薪。[注]Terrence Lyons, “The Ethiopia-Eritrea Conflict 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the Horn of Afric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6, No. 120, 2009, pp. 170-173.此外,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与索马里艾迪德集团关系密切,并且在南部索马里有大批支持者。为削弱欧加登民族分离势力,埃塞俄比亚持续干涉索马里的派系冲突,或支持艾迪德集团的死敌,或援助拉汉文抵抗军。[注]ICG, Somalia: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a Failed State, Nairobi/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y 23, 2002, p. 9.基于其对欧加登索马里民族主义威胁的担忧,埃塞俄比亚似乎始终坚信,只有使索马里保持一定程度的分裂,才能有效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注]Jamal Osman, “Ethiopia Must Let Somalia Determine Its Own Fate,” TRT World, September 27, 2017, http://www.trtworld.com/opinion/ethiopia-must-let-somalia-determine-its-own-fate-10633,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10日。这种源于跨界索马里民族问题的国家间关系,直接威胁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外部势力的卷入反过来又加剧了索马里局势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四) 追求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难以实现族际和解与国家重建
自2000年以来,为解决索马里国家失序困境,重建和平,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伊加特”)多次主导召开索马里和解大会。但是,在长期的和解、过渡和国家重建过程中,各族群之间对于国家体制、议会民主选举、政府机构运行等问题中的权力及利益协调问题一直分歧重重。难以实现族际和解始终是阻碍索马里国家政治重建的重要因素。[注]Domink Balthasar, Thinking Beyond Roadmaps in Somal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8, 2014, pp. 2-5.
在和解会议的框架下,为解决参会代表席位的分配争执,2000年吉布提会议期间制定了关于参会代表席位分配的“4.5分配原则”,即四大主要部族(达鲁德、哈维耶、迪尔、拉汉文)与其他少数部族在代表席位分配中的比例为1∶1∶1∶1∶0.5。此后,在历次索马里大会以及政府权力机构人员构成中,“4.5分配原则”一直是各部族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注]ICG, Salvaging Somalia’s Chance for Peace, Nairobi/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ecember 9,2002, p. 4.该原则的确立主要体现了哈维耶部族精英及伊加特索马里事务委员会的利益诉求。哈维耶部族在过渡国民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占多数,他们期望通过缓和与其他部族的关系而强化其主导地位;伊加特则希望以该原则为切入点,实现部族间的真正平等。然而,该原则忽视了各部族人口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对部族内部和部族之间的人口流动预计不足,缺乏对少数部族权力与利益诉求的尊重,引起了少数部族对于共同分配大部族1/2席位份额的不满。其他三个部族也不满足于与哈维耶享有同样比例的权力分配。最终该原则未能写入索马里过渡时期宪法,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法律效力。[注]Mohamed A. Eno, “Inclusive but Unequal: The Enigma of the 14th SNRC and the Four Point Five (4.5) Factor,” in Abdulahi A. Osman and Issaka K. Souaré, eds., Somalia at the Crossroad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in Reconstituting a Failed State, Nigeria: Adonis & Abbey Publishers, 2007, pp. 58-81.该原则虽然在索马里和解、选举等各级大会的组织过程中已经成为一项惯例,但却无力规制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结构,未能在索马里被广泛接受,从而导致和解徒有其名。
在国家体制的选择和推进方面,部族间的权力斗争持续存在,以哈维耶和达鲁德部族之间的分歧尤为突出。在2002年埃尔多雷会议上,对于是否选择联邦制的问题,在伊加特技术委员会的高压下,各方以最小的政治代价实现妥协,同意共同组建中央政府,并于2004年成立了过渡联邦政府。但事实上联邦制度一直存在争议。继此前过渡国民政府主要由哈维耶部族建立之后,过渡联邦政府则成为达鲁德部族的权力基地。尽管肯尼亚大会多次强调“4.5分配原则”在政权分配中的地位,但是达鲁德的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Abdullahi Yusuf Ahmed)当选总统后,过渡联邦政府很快成为达鲁德实现其政权目标的工具。艾哈迈德总统及埃塞俄比亚支持下的索马里和解与复兴委员会成为政府的主导者,他们任命与其利益一致的部族联盟参政,哈维耶部族逐渐被边缘化。事实上,在此期间,哈维耶部族控制了首都摩加迪沙地区,并据此展开与达鲁德对整个索马里控制权的争夺。到2005年,过渡联邦政府出现了哈维耶和达鲁德两个主要部族及其阵营的对立,达鲁德部族获得了埃塞俄比亚和国际社会联邦派的支持,哈维耶部族则在阿拉伯世界、厄立特里亚、伊斯兰法院联盟(索马里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援助下拓展势力。[注]Peter Haldén, Somalia: Failed State or Nascent State-System, Stockholm: FOI Report R-2598-SE, 2008, pp. 30-42.至此,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建立的两届过渡政府都谋求实现部族和解,但每一次均被其中一个主要部族所控制。
经过长达八年的过渡,索马里于2012年正式成立联邦政府。但是,索马里在政治重建中仍面临制定联邦宪法和推进议会民主选举等方面的挑战。当前,索马里联邦政府主要由索马里兰[注]索马里兰虽然拒绝接受索马里政府的管辖,自称为“索马里兰共和国”,但并未获得国际承认,仍被认为是索马里的一个联邦成员州。、朱巴兰、西南索马里、希尔谢贝利、加尔穆杜格、邦特兰六个联邦成员州组成,[注]《索马里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550/1206x0_678552/,登录时间:2018年10月9日。它们与主要部族的分布基本一致,因而进一步以政治分权的形式强化了部族认同。此外,各联邦成员州之间各有其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并未在政府建构问题上达成妥协或一致;联邦政府也缺乏协商一致的政策或框架,难以解决地方政权之间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争端。各州在宪法上接受索马里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管辖,索马里中央政府则承认地方政府在地区事务上拥有一定的自治权,拥有各自的警察和安全部队,联邦政府在打击海盗、反恐等国家安全治理行动中难以有效调动地方资源。
三、 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深层原因
索马里族际冲突已经渗透到索马里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导致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它是国内各族群政治诉求的排他性无法得到有效协调的结果,但与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利用族际冲突强加干涉也不无关系。此外,索马里青年党在“基地”组织等中东地区宗教极端力量网络的支持下,对索马里各个族群推行分化和拉拢政策,不仅严重威胁索马里及地区安全,也极大地阻碍了索马里族际和解进程。
(一) 族际认同及政治诉求的排他性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族际冲突的“本质主义根源说”认为,族际冲突本质上是一种根源于族群间安全困境的权势争端。[注][美]阿舒托什·瓦什尼:《族群与族群冲突》,载[美]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唐士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页。在传统的索马里社会生活中,人们遵循父系血统追溯的习俗,在政治生活上,这种习俗表现为以父系血统、家族血缘为根据,展开氏族或部族之间的合作或斗争。索马里各个族群的“血缘性”和“地域性”,使得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它们视本族利益高于一切,将他族视为对本族的威胁,排斥和无视他族利益。[注]顾章义等:《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第74页。索马里独立后,氏族、部族作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进入国家政权建设,它们与政权建设的结合并未摆脱根深蒂固的族群排他性,导致各个族群在国家建设中政治诉求各异,成为族际冲突不断爆发的缘由。代表部族或氏族利益的政治派系领导人甚至利用人们对本族的效忠,展开对权力的争夺。此外,传统的氏族或部族认同与现代民族认同之间的巨大张力,则造成了索马里族际政治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冲突。
在索马里独立前,英国、意大利利用索马里部族社会的排他性,划分殖民区域。索马里独立后,临时国民议会曾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削弱人们的部族认同和部族势力,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反对国家分裂。但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以部族为基础的党派组织重新出现,人们的部族认同再次凸显。西亚德政府曾经大力推行反对部族主义政策,但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反对派势力,其政权很快便蜕变为代表达鲁德部族的集权统治。[注][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200-206页。西亚德政府垮台后,索马里并没有重归和平与稳定。部族的排他主义强劲发展,原先结盟反对西亚德的各个党派,纷纷以各自部族或氏族为后盾,展开对国家权力的争夺,索马里由此陷入无政府状态。此后,在推动族际和解、促进国家建设的进程中,索马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始终受到氏族和部族认同的巨大冲击。
(二) 周边国家利用族际冲突相互博弈并进行干涉
索马里族际冲突从来不是简单的国内族际政治问题,非洲之角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深涉其中。它们各自支持不同的族群,进行战略博弈,一度使索马里成为地区国家的“代理人战争”场域。地区国家间博弈与索马里族际冲突相互纠缠,使得原本脆弱的索马里政治和解与国家重建进程愈加举步维艰。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因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尼罗河流域控制权的争夺等原因长期对峙,在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后,双方将角力场扩展至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东部边境地区居住着大量索马里人,虽然他们在欧加登战争后接受了埃塞俄比亚公民身份,但是仍被埃塞俄比亚视为易受索马里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企图破坏埃塞俄比亚团结的潜在力量。因此,埃塞俄比亚时刻警惕“大索马里主义”的影响。此外,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索马里人和其他边境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国民抱有一定的对立情绪。2000年过渡国民政府成立后,索马里获得联合国的承认,并成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对过渡政府表达了同情和支持,积极倡导索马里国家和平重建进程。埃及的政治立场不仅源于共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还由于索马里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密切的贸易联系和重要的地缘关系。[注]ICG, Somalia: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a Failed State, p. 9.2001年3月,一些军阀势力在拉汉文农牧区成立了与政府对抗的索马里和解与复兴委员会,埃塞俄比亚趁机全力支持该组织,以对抗埃及所支持的索马里过渡国民政府。埃塞俄比亚与埃及对各自青睐的氏族或部族以及派系的支持,直接影响了2002年埃尔多雷和解会议进程。[注]ICG, Salvaging Somalia’s Chance for Peace, p. 6.埃塞俄比亚除了与埃及进行角逐以外,还因为与厄立特里亚的历史纠葛而在索马里展开博弈。2006年,当埃塞俄比亚出兵打击伊斯兰法院联盟时,厄立特里亚则对后者表示支持。
土耳其、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也因地缘政治争夺卷入索马里事务,以实现各自在非洲之角的利益诉求,从而拓展地区影响力。2009年以来,土耳其积极采取诸如参与打击海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倡议索马里和平谈判等多种手段,与索马里联邦政府保持友好关系。[注]ICG, Assessing Turkey’s Role in Somalia, Nairobi/Istanbul/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ctober 8, 2012, pp. 5-11.2017年9月,土耳其打着为索马里提供军事训练和安全保障的旗号,在摩加迪沙建成并投入使用其在非洲地区的最大海外军事基地。[注]“Turkey Sets Up Largest Overseas Army Base in Somalia,” Al Jazeera, October 1, 2017,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10/turkey-sets-largest-overseas-army-base-somalia-171001073820818.html, 登录时间:2018年10月9日。作为土耳其的竞争对手,同时也为了增强在红海和亚丁湾地区的影响力,并阻止伊朗在该地区的战略进取态势,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主动参与索马里国家建构。[注]Ahmed Soliman, “Gulf Crisis Is Leading to Difficult Choices in the Horn of Africa,” Middle East Eye, June 30, 2017, http://www.middleeasteye.net/columns/gulf-crisis-leading-difficult-choices-horn-africa-2121025667, 登录时间:2018年10月9日。除明确表示对索马里兰的支持以外,2017年2月,阿联酋越过索马里联邦政府,与索马里兰达成了建立柏培拉军事基地的协议。[注]“Somalia Calls for UN Action Against UAE Base in Berbera,” Al Jazeera, March 28,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3/somalia-calls-action-uae-base-berbera-180327172528871.html, 登录时间:2018年4月17日。阿联酋的这一行为强化了索马里兰的分离主义倾向,直接影响了索马里的族际和解进程。
由此可见,非洲之角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利用索马里族际冲突展开战略博弈,而外部力量的渗透不仅加剧了索马里的族际冲突,阻碍族际和解与国家重建进程,甚至有导致索马里进一步走向国家解体之虞。
(三) 国内外宗教极端势力企图渔利于族际冲突
2006年至2007年,伊斯兰法院联盟失势后,伊斯兰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迅速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控制了索马里大片国土,在非洲之角策划并组织了数百起恐怖袭击,成为威胁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毒瘤”。青年党利用族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人们加入宗教极端组织,加剧了索马里政治安全形势的不稳定。同时,中东恐怖组织也利用青年党内部矛盾,大肆进行渗透,打造东非恐怖主义网络,导致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形势愈益脆弱不堪。
青年党主张建立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在其发展壮大期间,逐渐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是以艾哈迈德·阿布迪·戈登(Ahmad Abdi Godane)为首的国际派,他们在伊萨克部族“大索马里主义”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主张将暴恐活动扩大到整个非洲之角地区,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家”;二是以精神领袖谢赫·哈桑·阿维斯(Sheik Hassan Aweys)、副领袖谢赫·穆赫塔尔·罗博(Sheikh Muktar Robow)为首的本土派,他们大都来自哈维耶部族和达鲁德部族,主张将袭击活动局限于索马里境内,以实现国家伊斯兰化为首要目标。[注]严帅:《索马里青年党发展动向》,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期,第28页。中东恐怖组织利用青年党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分歧,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国际派的渗透、分化和拉拢,不断向其输入资金、武器和人员,声援和支持青年党的“圣战”活动。2012年,青年党正式加入“基地”组织,并在后者支持下,大肆清缴本土派势力,进一步密切与中东恐怖势力的联系,从而成为“基地”组织在东非地区“开拓进取”的一大跳板。[注]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71页。
青年党虽然是一支由来自多个部族和氏族的“圣战”分子组成的武装,但在本质上是索马里众多族际武装当中的一支。为了兼顾不同族群的利益,青年党吸纳不同部族和氏族成员进入组织管理体系,以弥合组织内部矛盾,并提高宣传动员能力。尽管其最高行政机构的领袖成员来自不同部族,但在青年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伊萨克部族起到了关键作用:前任领袖戈登、副领袖易卜拉欣·哈吉·贾马·米阿德(Ibrahim Haji Jama Mee’aad)均来自索马里兰地区的伊萨克部族。他们沿袭了曾在伊萨克部族盛行一时的“大索马里主义”梦想,将宗教信仰与民族情绪相结合,并企图通过暴动手段实现“大索马里”梦想。在行动中,他们经常利用族际认同达到其目的,通过扶植某个部族或氏族来对抗其他部族或氏族,体现了其族际武装的本质。[注]宁彧、王涛:《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第39页。
青年党一方面跨越族群界限,利用“大索马里”的民族认同塑造一种高于族际认同的政治信仰,为其行动披上了“正义”面纱;另一方面又利用族际认同进行宣传动员和政治分化,使其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宣传工具,结果使得其族际武装团体的本质在不同族类群体中虚实难辨,进一步恶化了国家及地区安全形势。当前,青年党与中东恐怖势力相互勾结,使得非洲之角与中东地区面临更严峻的安全形势,而要从根本上剿灭青年党,并防范类似极端组织的出现,必须要回到索马里国内的族际政治并从中寻找答案。
四、 结 语
长期以来,索马里不同氏族和部族各自的族群认同构成了索马里社会组织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几乎每个氏族或部族均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在索马里国家建设进程中表现为毫不妥协的政治诉求及经济利益;内战爆发后,在外国干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作用下,族际冲突不断蔓延和升级,致使国家长期处于“失败”状态,甚至“外溢”为地区安全威胁,不断冲击地区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与重塑。
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遭遇挫折的后果,而族际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失败的原因。从索马里的国家失败经历来看,不论是无政府时期基于氏族和部族的派系冲突,还是过渡政府时期的权力分配矛盾阻碍族际和解与国家重建,族际政治始终是一项关键性的因素。它与地区干涉力量和宗教极端组织等其他因素深度交织,共同构成了阻碍索马里国家建构的几大结构性因素。同时,索马里族际冲突源于大历史时空维度上的族际认同与利益诉求。在索马里独立后的30年间,各部族搁置矛盾,共同致力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而在西亚德政府垮台后,索马里陷入长期无政府状态或国家失败困境,从而为索马里族际冲突以暴力形式呈现并加剧创造了条件:各部族和氏族及派系为争夺国家权力爆发冲突,联邦制政府建构艰难曲折,索马里兰在内战中宣告独立,另一些地方的分离主义倾向时隐时现。
在诸多受到族际政治困扰的国家当中,陷入近30年的族际冲突和国家失败困境的索马里成为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极端案例。从索马里案例可以看出,一方面,族际冲突与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干涉、宗教极端势力等共同作用,成为导致国家失败和国家重建屡遭挫折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国家失败的无政府状态又削弱了民族与国家认同,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无力推动族际和解,地方性族际认同进一步被强化,由此加剧了族际冲突。所以,在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框架下,族际冲突与失败国家构成一对“正相关”关系。同时,族际冲突又与国家建构形成一对“负相关”关系,这是索马里及同类失败国家在政治和解与国家重建时面临的根本困境。
从索马里内部次国家层次的族际互动关系视角研究族际政治与国家建构,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西亚、非洲以及其他地区一些类似国家的族际政治现象和原因,对于国际秩序重塑背景下此类失败国家的重建和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由于地区相关国家和大国力量的卷入,以及宗教极端组织网络的作用,索马里冲突与也门内战、叙利亚战争存在某种相似性,凸显了本案例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战乱未已,几乎处于崩溃边缘。在叙利亚,国家建构也存在着复杂的、多层次的族际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巨大张力,如在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之间,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各方因为不同诉求而冲突不断。在也门,南北之间在宗教认同、政治诉求、利益分配等问题上长期对峙,加上地区大国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干涉与分化,如沙特和伊朗通过支持不同派系而在也门展开战略博弈,冲突各方毫不妥协,导致国家乃至地区长期动荡。在这些国家的和解、重建与治理中,需要充分借助国内国际多个平台,协调族际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调和族群之间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实现族际政治和解,增强社会与国家凝聚力,建立善治政府,为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建设创造必要条件,同时也要警惕和排除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的干涉与分化,从而引导国家逐步走出战乱频仍的失败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