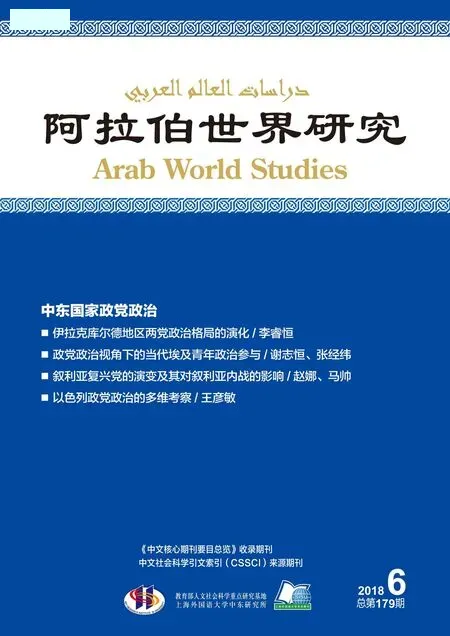多维视域下的中东国家人口治理探析*
陈小迁
中东变局发生后,地区国家在动荡局势中艰难地开启了国家治理转型进程。然而,历经7年多的调整与变革,许多国家仍远未走出阴霾,深陷治理困境之中。中东国家的治理失范,既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受到长期积累的人口问题的深刻影响。就该地区的人口问题研究而言,国外学界的成果较为丰富,概括起来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人口问题的整体研究,如迦德·吉尔伯(Gad G. Gilbar)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中东地区人口控制政策的研究,指出地区国家处于人口增长引发的经济困境之中[注]Gad G. Gilbar, Population Dilemma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17;其他相关成果包括Michael E. Bonine, Population,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ities,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Gabriel Baer, 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the Arab East, New York: Routledge, 2016。;二是聚焦于中东国家青年、移民、妇女、民族等问题的专题研究,如拉奎·阿萨德(Ragui Assaad)等对中东青年问题的考察,强调政府应强化青年技能,使年轻化挑战转变为发展机遇[注]Ragui Assaad and Farzaneh Roudi-Fahimi, “Youth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Demographic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December 2010, https://assets.prb.org/pdf07/YouthinMENA.pdf,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17日。;三是对中东变局衍生的特定问题的研究,如艾曼·哈瓦德·塔米米(Aymenn Hawad al-Tamimi)对叙利亚内战中人口变动的考察,他认为巴沙尔政府推行增加什叶派人口数量的政策,以在未来叙政治重建中增添砝码。[注]Aymenn Jawad al-Tamimi, “The Syrian Civil War and Demographic Change,” Middle East Forum, March 15, 2017, http://www.meforum.org/6600/the-syrian-civil-war-demographic-change, 登录时间:2018年1月16日。
当前,国内外学界基本没有将人口问题纳入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范畴中。中国学界对中东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并非显学。[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对中东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曲洪:《中东国家的人口问题》,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4期,第43-48页;何景熙:《中东阿拉伯国家近期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人口迁移》,载《人口与经济》1994年第5期,第59-62页;曲洪:《中东:人口爆炸与资源失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2期,第59-61页;卢光盛:《中东人口问题试析》,载《阿拉伯世界》1999年第1期,第38-40页;周意岷:《试析中东人口问题及其影响》,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第115-131、146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涵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要素。西方学者注重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政治、管理、经济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注]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基于国家主义治理路径,有学者指出,治理是政府政策执行能力的体现。[注]Kaufmann D. Kraay and Mastruzzi,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Vol. 3, No. 2, 2011, p. 27.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基础,人口治理与政治群体、社会结构、阶层分离、发展质量等密切相关,成为中东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因此,分析中东国家人口治理的特征与类型,探索其人口治理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理解当前中东国家治理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东国家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的共性与差异
人口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受到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及影响。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它们之间有着大致相似的发展经历和制度特征,在人口增速、人口再生产、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一定共性。然而,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时局因素、治理能力与人口矛盾,中东各国的人口治理又显现出一定的差异。
中东国家的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的共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人口增速高,人口规模大。当前中东地区人口平均增速达1.84%[注]从国别来看,中东地区人口增长率超过2%的国家有埃及(2.1%)、伊拉克3.2%)、约旦(2.4%)、科威特(3.6%)、黎巴嫩(4.2%)、阿曼(5.8%)、卡塔尔(2.9%)、沙特阿拉伯(2.1%)、巴勒斯坦(2.9%)和也门(2.4%)。参见 “Population Growth(annual %),”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GROW?locations=ZQ,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3日。,在世界各地区中高居第二位。[注]Keith Crane, S. Simon and Jeffrey Martini, “Future Challenges for the Arab World: The Implication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Trends,” Rand Project Air Force Report,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1, p. ix.依照指数增长模型估算,2050年中东地区人口数量将接近7亿,其中西亚地区为4.5亿人,北非地区为2.4亿人。[注]Farzaneh Roudi-Fahimi and Mary Mederios K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opulation Bulletin, Vol. 62, No. 2, 2007, p. 5.其二,基于人口增长快所致的人口总量大,中东国家的人口死亡率相对较低,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再生产模式仅处于由原始向现代的转变期,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存量。其三,除个别国家及社会群体外,中东国家人口治理普遍受到伊斯兰文化的深刻影响。[注]Abdel R. Omran, Family Planning in the Legacy of Islam,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59-65.其四,各国政府是人口治理的责任主体,社会力量的作用并不显著。[注]Tareq Y. Ismael, J. S. Ismael and G. E. Perr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3.因公共部门治理能力较低,中东国家的人口治理大体属于妨碍型管制模式。[注]妨碍型管制,即在政治治理能力低下、治理结构僵化的情况下,私人部门无法融入到治理体系中,而公共部门又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甚至横加干涉、妨碍私人部门的行为,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介入型管制是指政府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能够成为治理的主体,也有学者称其为“干预型(interventionist)的规制”,“interventionist”具有干涉主义的含义,是西方出于自由市场过度崇拜心态,对国家主义治理的一种非公正话语,因此笔者将其译为“介入型管制”。参见Christoph Knill and Dirk Lehmkuhl, “Private Actors a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Governance,” Governance, Vol. 15, No. 1, 2002, p. 49。
根据不同的标准,中东国家的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特点大致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从自然资源与人口治理的关系方面看,大多数中东国家表现为过度人口与匮乏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中东地区可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平均值仅为4.7%,不到世界平均值的一半[注]“Arable Land(% of Land Area),”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AG.LND.ARBL.ZS,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17日。;2016年中东人均可用水资源为1,076立方米,比世界均值少7,424立方米,预计10年后还将下降20%左右。[注]Shobha Shetty, “Water,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World Bank Report, July 2006, p. 3; Karim Elgendy, “How Sustainable is Your Oasis?: A Review of Water Resources in Middle East Cities,” Carboun, July 22, 2015, http://www.carboun.com/energy/how-sustainable-is-your-oasis/, 登录时间:2018年1月12日。自然资源的匮乏导致中东国家粮食自给能力差,每年超过50%的粮食依赖进口,使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注]“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Middle East,” World Bank,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MENAEXT/0,,contentMDK:20528258~pagePK:146736~piPK:226340~theSitePK:256299,00.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1日。当然,对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而言,石油财富支撑起了庞大的日常生活与基础设施开支,暂时掩盖了自然资源短缺的问题,甚至面临着过度浪费与自然资源加速消耗的双重压力。例如,沙特第三个五年计划(1980~1985)期间,政府加大对灌溉农业的补贴力度,加之不科学地利用水资源导致地下水位骤降,地表植被退化。[注]Tim Niblock and Monica Mali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85.此外,海合会国家普遍缺乏节约能耗意识,不仅能源“近似于免费”,政府还缺乏对经济型低能耗产品的补贴刺激政策。例如,部分卡塔尔民众在夏季外出度假时不关闭家中的空调,只是“为了回来时室内凉爽如初”。[注]Steffen Hertog, “Redesigning the Distributional Bargain in the GCC,” in Michael Hudson and Mimi Kirk, eds., Gul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 Hackensack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4, p. 35.
第二, 由于地区冲突与人口的关系并无规律可言,并非所有中东国家都是可根据指数模型预测的稳定型人口变动,部分国家可能表现为人口突变模式。饥荒、战乱等因素都会造成人口数量骤然增减、年龄或性别结构失衡等结果。21世纪初以来,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的战争对这些国家的人口问题影响很大。由于战乱的烈度和持续时间不同,伊拉克与叙利亚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从2003年至2008年,伊拉克成年男性死亡率增加了31.16‰。[注]“Mortality Rate, Adult, Male (Per 1,000 Male Adults),”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DYN.AMRT.MA?locations=SY-YE-IQ-LY, 登录时间:2018年4月17日。对于叙利亚而言,在巴沙尔总统第二任期(2007~2014)内,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成年男性死亡率直线上升,至2016年上升了120.81‰,其中2012年死亡率达到峰值(289.9‰)。在此期间,叙利亚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3.842岁,其中2014年达到最低点(69.82岁)。[注]“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Total (Years),”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DYN.LE00.IN?locations=SY-YE-IQ-LY, 登录时间:2018年3月12日。人口变动造成这些国家国内男女比例失调,年龄结构失衡,人口空间分布发生逆转,不利于战后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第三,从人口治理的水平与能力方面看,以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为衡量标准[注]如果该体系存在缺陷,将造成大量非计划性怀孕的结果,并拖累个人、家庭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东各国的差异较为明显。2016年19个中东国家育龄女性采用避孕措施及现代避孕措施的平均比例分别为49%和36%,远低于62%及56%的世界平均水平。[注]“2016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Human Needs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s,”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http://www.prb.org/Publications/D atasheets/2016/2016-world-population-data-sheet.aspx, 登录时间:2018年1月24日。根据避孕普及率(占15~49岁女性百分比),中东国家可分为四类:一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伊朗与土耳其均超过73%,这得益于两国完善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以及民众较高的人口再生产意识水平;二是高于地区平均水平(57.66%)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埃及、以色列、巴林、摩洛哥、约旦等国的避孕普及率在60%左右;三是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但避孕普及率达到50%的国家与地区,如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巴勒斯坦等;四是生殖健康服务体系极不完善的国家,如阿富汗和海湾君主国等。其中,阿拉伯半岛的避孕措施采用率大多不及30%。[注]“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any Methods (% of Women Ages 15-49),”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DYN.CONU.ZS?end=2013&locations=ZQ-YE-CY&start=1981&view=chart, 登录时间:2018年2月22日。这既与国家人口政策与治理能力有关,也受到民众文化观念与人口意识的制约。
第四,中东国家的人口治理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以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为代表的干预型人口治理政策。这些均为共和制国家,它们建立了诸如埃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Board)等机构,旨在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速率。[注]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1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3, pp. 154-256.二是以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君主国为代表的替代型人口治理政策。这些国家的人口核心矛盾是外来人口比重过高和劳动力市场本国人口不足的问题,因此不实行生育控制,采取如“沙特化”、“阿曼化”等劳动力替代政策。三是以土耳其、伊朗等国为代表的增长型人口治理政策。这些国家近年来生育率下降,老龄人口增多,因此鼓励人口增长或保持现有人口增速。如伊朗自2012年开始禁止育龄妇女采取永久性避孕措施,鼓励青年早婚,旨在提高出生率。[注]Lizzie Dearden, “Iran to Ban Permanent Contraception after Islamic Cleric’s Edict to Increase Population,” Independent, August 11, 2014,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iran-to-ban-permanent-contraception-after-islamic-clerics-edict-to-increase-population-9662349.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12日。四是以巴林、叙利亚为代表的转换型人口治理政策。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与民众的教派相异,并且在人数上相差悬殊。出于政治考虑,统治者们大量归化本教派的外籍人口,或驱逐压制其他教派的民众,试图扭转人口数量的天平。[注]Simon Mabon, “The Battle for Bahrain: Iran-Saudi Rivalry,”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9, No. 2, 2012, p. 87.
二、 人口治理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
自2011年至今,中东地区持续动荡,从国家内战,到地区教派冲突、极端伊斯兰势力兴起,再到难民危机等跨地区问题,无不侵蚀着原本就很脆弱的中东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在当前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受到持续冲击的背景之下,人口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多重问题为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一, 中东地区迅速膨胀的青年人口,成为群体性政治运动之源。由于生育率飙升、人口存量过高等原因,近年来中东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迅速年轻化。目前,中东地区15至29岁的青年人口达1.1亿人左右,约占地区人口总数的近27%[注]Hassan Islam and P. Dyer, “The State of Middle Eastern Youth,” The Muslim World, Vol. 107, No. 1, 2017, p. 9.;14岁以下少年人口占比达28.1%。[注]“The World Factbook,” C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xx.html, 登录时间:2017年7月13日。但中东青年所处的时代充满了经济动荡、就业困难、政局不稳、国家内战等诸多挑战。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个体认同感的增强,青年对政治变革的诉求明显提升。[注]陈小迁、韩志斌:《中东变局以来阿曼国家治理转型述评》,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第117页。
上述现实使某些中东青年运动形式逐渐向两个方向流变。一是受到西方“民主促进”政策影响的青年追求世俗的西方式民主观念,对僵化低效的政治体制颇有微词,呼吁普选政治与人权自由。[注]参见Peter Burnell, “From Evaluating Democracy Assistance to Appraising Democracy Promotio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Political Studies, Vol. 56, No. 2, 2008, pp. 414-418; 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Future of ‘Real-Existing’ Democracy,” Society and Economy, Vol. 33, No. 2, 2011, pp. 401-403。二是投身于政治伊斯兰运动甚至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的青年,要么寻求调和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的关系,要么追求政治及社会等方面的伊斯兰复古实践。[注]Dietrich Jung, M. J. Petersen and S. L. Sparre, Politics of Modern Muslim Subjectivities: Islam, Youth, and Social Activism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132-139.然而,无论哪种政治运动路径,都对当前中东政治的稳定性造成自下而上的冲击。从中东变局的发展趋势看,青年的政治参与极易演变为暴力事件或催发社会失序。此外,青年看待政治问题的情绪化较为严重,缺乏开阔且深层次的政治眼界,在日益普及的网络平台上“针砭时弊”时,容易激起一定规模的民众运动,增加中东国家的政治治理压力。
第二,中东地区人口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全球性的治理难题。学界一般将人口移民分为两类,即劳工移民与避难移民。[注]Orn B. Bodvarsson and Hendrik Van den Berg,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 157.劳工移民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经济机会,海湾地区是这些移民的主要汇集地。但是外籍劳工普遍认为海湾国民好逸恶劳,加之雇主的压迫,导致他们时常发起示威活动,呼吁保障劳工权益、建立工会组织等。2005年至2007年间,阿联酋迪拜爆发了超过20次有组织的外籍劳工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待遇。[注]Louay Bahry, “Qatar: Democratic Reforms and Global Status,” in Abbas Kadhim, e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Handbook,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287.此外,劳工移民也与本国政治思潮联系紧密。海湾战争期间,也门、巴勒斯坦等政权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府,致使这些国家的劳工与海合会政府之间矛盾骤起,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多国将他们驱逐出境。[注]Neil Quilliam, “The States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in Tom P. Najem and Martin Hetherington, eds., Goo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Oil Monarch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41.
就避难移民而言,2015年逃避战火和政治迫害的中东国家民众数量超过2400万,占地区总移民数量的45%。其中,叙利亚有超过710万的避难移民,伊拉克有470万,约旦有290万,黎巴嫩有150万,也门和土耳其各有280万[注]Phillip Connor, “Middle East’s Migrant Population More Than Doubles Since 2005,”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18, 2016, http://www.pewglobal.org/2016/10/18/middle-easts-migrant-population-more-than-doubles-since-2005/,登录时间:2017年11月17日。,利比亚2011年的统计数据则超过100万人。[注]Karin Laub, “Libyan Estimate: At Least 30000 Died in the War,” San Diego Union-Tribune, September 8, 2011, http://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sdut-libyan-estimate-at-least-30000-died-in-the-war-2011sep08-story.html,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5日。上述国家的移民问题有的主要表现为移民输出,有的主要表现为移民输入,也有少数国家同时存在显著的移民输入和输出。一方面,避难移民使用或侵占移民接收国民众所享有的公共资源,还因教派等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部分移民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进而引发了群体性武装冲突。如巴勒斯坦政治移民相继牵涉到约旦“黑九月事件”[注]“黑九月事件”指1970年9月约旦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严重流血冲突事件。由于巴解组织的激进分支“人民阵线”劫持西方客机,巴勒斯坦人支持叙利亚军队入侵约旦,以及巴解游击队与约旦政府的长期矛盾,约旦政府军对境内的巴解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据称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超过4,000人死亡,巴勒斯坦难民则死伤数万人。、黎巴嫩内战等战乱冲突中。[注]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pp. 311-317.除此之外,近年来中东地区逃避战火的民众还引发了波及欧洲的难民危机,很多欧洲国家疲于应对难民偷渡以及暴恐袭击等事件。这加深了欧盟的内部分歧,使西方政治生态趋于保守化,不利于全球治理合作的开展。
第三,中东国家宗教及民族的人口数量变动触发四类政治权利问题。
一是少数族裔对主体民族的政治冲击,尤以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为代表。2011年后,库尔德人在纷乱的地缘局势中实力渐强,所谓“阿拉伯之春”演变为“库尔德之春”。[注]David L. Philips, The Kurdish Spring: A New Map of the Middle East,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5, p. 2.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库尔德人的生育率较高,人口比重日益上升。鉴于2015年议会选举中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获得13.12%的选票而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派,有学者认为,从人口演进的角度看,未来土耳其的政治形势将更加复杂。[注]Tristan Duning, “Rising Tide of Demographic Change Spells Trouble Across Middle East,” The Conversation, March 2015, https://www.theconversation.com/rising-tide-of-demographic-change-spells-trouble-across-middle-east-36598, 登录时间:2018年1月28日。这些情况促使埃尔多安政府加大了对库尔德人的管控力度,并且因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力量而日益陷入叙利亚内战。
二是宗教及教派人口变动影响权力平衡。以黎巴嫩为例,其政治架构建立于教派分权的原则之上。[注]根据黎巴嫩宪法,黎巴嫩总统、议长和总理分别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和伊斯兰教逊尼派人士担任。参见David S. Soren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Middle East: History, Religio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2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4, pp. 311-312。如果教派间人口比重、经济水平等因素发生变化,加之外部力量的影响,脆弱的政治平衡极易被打破。近年来,黎巴嫩穆斯林人口数量攀升,已大幅超过基督徒人口数量,同时什叶派人口数量上升至与逊尼派大体持平。[注]“The World Factbook: Lebanon,” C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e.html#People, 登录时间:2018年2月26日。加之成分复杂的150万叙利亚难民流入黎巴嫩,不可避免地加剧伊朗与沙特在“新月地带”的地缘政治竞争,黎巴嫩本不牢固的政治平衡恐怕难以为继。类似于2017年11月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的政治风波可能还将上演。
三是以以色列为代表的不同民族及宗教间的权利抗争。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外,世俗化犹太人的生育率较低且进入了老龄社会。预计2030年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将只有现在的56%。相比之下,阿拉伯人的生育率较高。正如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所言:“阿拉伯人最好的武器便是生育。”[注]Gregg Roman, “The Myth of Israel’s Demographic Doomsday,” Middle East Forum, December 2016, https://www.meforun.org/6421/the-myth-of-israel-demographic-doomsday, 登录时间:2018年2月26日。长期以来,以色列政府持续关注国内阿拉伯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认为这一问题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及国家的犹太属性紧密联系。[注]Fania Oz-Salzberger and Yedidia Z. Stern, The Israeli Nation-State: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hallenges, Brigh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4, p. 36.随着阿拉伯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在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地区局势紧张复杂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诉求更易被激发,进而增加地区动荡的可能。
四是以巴林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的教派矛盾问题。巴林的统治者为伊斯兰逊尼派的哈利法家族,但国内什叶派人口占比约72%。[注]Raymond Hinnebusc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5.出于历史、宗教等原因,哈利法家族认为什叶派民众是伊朗的代理人[注]Uzi Rabi and Joseph Kostiner, “The Shi’is in Bahrain: Class and Religious Protest,” in Ofra Bengio and Gabriel Ben-Dor, eds.,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 177.,对他们实行就业和福利歧视,禁止其加入军队,并在政治上将其边缘化。[注]Rodman R. Bundy,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Gulf,” in Richard Schofield, ed., Territorial Foundation of the Gulf States, London: UCL Press, 1994, p. 184.此外,哈利法家族为维护自身统治,对外来阿拉伯人及非阿拉伯人逊尼派实行“政治归化”政策,以求抵消什叶派的人口优势。[注]Justin Gengler, Group Conflict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Bahrain and the Arab Gulf: Rethinking the Rentier Stat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43.这引起了巴林国内什叶派的普遍不满,导致数次抗议活动的爆发并在2011年演变为暴力冲突。
三、 人口治理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
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多数国家的GDP增长率起伏不定。一方面,中东共和制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较低,错过了21世纪初期世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沦于边缘地位。近年来中东变局引发的发展困境依然存在,导致地区国家经济迟迟未能恢复。另一方面,以海湾国家为代表的中东君主制国家多元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除国际环境、政策机制等因素外,人口问题也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多重挑战。
第一,大多数中东共和制国家的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未能形成人力资源优势。相反,日益膨胀的人口数量稀释了经济发展成果。2000年至2016年,西亚北非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98%;同期地区人口增长率则达到了2.02%。在也门、埃及、突尼斯及阿尔及利亚,经济增长率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率。依据人口经济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人口增长抵消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迫使人均收入退回到原有水平。[注]Xan Rice, “Population Explosion Threatens to Trap Africa in Cycle of Poverty,” The Guardian, August 25,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aug/25/uganda.mainsection,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7日。令人担忧的是,中东变局至今,该地区的“人口陷阱”效应仍在持续,虽然自2015年开始情况逐渐好转,但未来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能否实现持续增长还有待观察。
当前中东共和制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潜力巨大,正处于“人口窗口期”。数量庞大的青年具备了劳动生产能力,由平均消费多于生产的“赤字年份”转为了“盈余年份”。[注]“Promo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nclusion of Young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Youth Initiative, https://www.meyi.org/apps/search?q=Promoting+the+Social+and+Economic+Inclusion+of+Young+People,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6日。2016年,中东大多数国家属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社会负担较轻,国民经济应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正是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见下表)。然而,“人口红利”如果无法有效释放,将导致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一代人之后,整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将转变为老年型,这对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与社会资源分配构成了潜在的风险。因此,如若错过了“人口窗口期”,不能利用人口结构优势发展经济并积累财富,数十年后中东国家所承受的经济与社会治理压力将会成倍增长。

中东共和制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资料来源: “The World Factbook,”C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html,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7日。a.土耳其属于年老型年龄结构初期,仍有一定人口潜力有待发挥。
中东国家“人口红利”被抑制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的经济贡献率过低,不能产生较高的劳动力价值。首先,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公共部门雇佣率过高,埃及甚至超过35%。正如欧洲研究者所言,公共部门较低的人力资源比重不一定确保经济的强劲增长,但高比重则可能扼杀经济发展的动力。[注]孙罗南:《经济问题是中东变革“导火索”》,载《经济导报》2011年2月15日,第A4版。就中东国家而言,公共部门几乎成为政府机关的代名词,少量担负生产建设任务的部门也不可避免地效率低下且体制僵化。其次,中东地区的教育和培训体制存在明显短板,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较低,许多大学毕业生的能力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技能错配”(skills mismatch)[注]Hyam M. Nashash, “The Extent of Skills Mismatch Among Childhood Education Graduates of Princess Alia University College,”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Vol. 6, No. 17, 2015, p. 180; Elise Gould, “Still No Sign of a Skills Mismatch: Unemployment Is Elevated Across the Board,”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January 2015, http://www.epi.org/blog/still-no-sign-of-a-skills-mismatch-unemployment-is-elevated-across-the-board/,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8日。。对于管理岗位而言,私营企业普遍关注青年的语言表达、团队协作、应急处理等非认知素质,这些正是中东地区高校毕业生所欠缺的。[注]Ryan A. Brown et al., Youth in Jordan: Transitions from Education to Employment,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 16.就应用技能岗位而言,该地区教育体制培养高需求技术及专业领域人才的能力较弱,并且软硬件条件均比较一般,不利于帮助学生提高职业能力。[注]Ali S. Al-Musawi, “Current Statu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at Omani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ir Future Prospective,” Education Tech Research, May 2007, p. 409.
第二,中东产油国的人力资源矛盾掣肘了经济转型发展。相对于中东共和制国家,海湾国家经济看似成功,却仍在全球经济震荡的影响下具有巨大脆弱性。[注]Michael Hudson and Mimi Kirk, eds., Gul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4.特别是巴林和阿曼,两国的石油资源或已经枯竭或储量较少,但它们在经济转型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境。简言之,经济多元化转型是对经济类别与生产手段的变革,强调政策支持、资金输入、产业联动与人力资源供给。然而,海湾君主国大多受制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人力资源矛盾。
其一,海合会国家普遍受到劳动力不足的羁绊。尽管这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很高,但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需要。[注]Louay Bahry, “Qatar: Democratic Reforms and Global Status,” in Abbas Kadhim, e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Handbook, p. 272.因此,海湾君主国不得不依赖外籍劳工从事生产活动。2014年,中东地区的劳工移民数量达到3,100万,海湾地区的外籍劳工人数便占到地区劳工移民总数量的79.4%[注]Phillip Cnnor, “Middle East’s Migrant Population More Than Doubles Since 2005,”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18, 2016, http://www.pewglobal.org/2016/10/18/middle-easts-migrant-population-more-than-doubles-since-2005/, 登录时间:2018年1月23日。;2015年,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的外籍劳工甚至超过总劳动人口的90%。[注]Tareq Y. Ismael, J. S. Ismael and G. E. Perr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Continuity and Change, p. 509.二是外籍劳工长期主导生产服务性工作岗位,反而不利于海湾本地民众的自我提升与发展。而海湾国家民众对工作环境挑剔,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注]Ibid., p. 502.与此相对应,除少数精英外,海湾国民大多无法胜任私营部门的技术及管理岗位工作。在福利国家的制度保障下,民众并没有进入并主导劳动力市场的诉求,最终导致海湾君主国至今仍未形成能够真正代表本国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各国国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的是“老板”角色,以至于许多研究者称其为“食利国家”。[注]Lisa Anderson, “Policy-making and Theory and Theory Build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in Hisham Sharabi, ed.,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Arab World: Critic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37-45.
虽然海湾君主国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改革,但效果差强人意。一方面,劳动力的本土化政策遭到诸多批评阻碍。阿曼政府官员私下承认,政府不能强迫私营公司雇佣缺乏培训的阿曼人去代替印度人,并且前者的工资是后者的三到五倍。巴林的企业高层则抱怨:“巴林人没有工作是因为没有技能。哪有巴林人能胜任外国人的工作?即使司机这类工作都找不到人做。”[注]Marc Valeri, “Sate-Business Relations in the Gulf: The Role of Business Actor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Bahrain and Oman,” in Michael Hudson and Mimi Kirk, eds., Gul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67-71.另一方面,改革政策往往存在悖论。沙特“2030愿景”的目标之一就是加快私有化进程,利用市场活力解决就业问题。然而,从20世纪末期沙特推行私有化改革伊始,政府为了保证沙特人就业,附带了私有化劳工合同,使原公共部门的沙特人继续留任。[注]Tim Niblock and Monica Mali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audi Arabia, p. 112.经验表明,如果政府提速私有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取消这些保证条款,这意味着沙特人必然面临着失业。
第三,中东人口空间结构演进处于高速城市化阶段,造成了劳动力过度集聚与城乡经济失衡等问题。二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城市化增速位居世界前列。2015年,中东地区有18个国家超过了城市化转折点[注]城市化转折点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目前中东地区只有埃及、也门、阿富汗的城市化比例低于50%。参见 “Urban Population (% of Total),”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IN.ZS?locations=ZQ-AF,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3日。;科威特、卡塔尔的城市化比例早已达到98%以上,成为名符其实的“城市国家”。[注]Geoffrey Parker, Sovereign City: The City-state Through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 219; David Roberts, Qatar: Securing the Global Ambitions of a City-State,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1, p. 16.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西亚北非地区的城市化人口流动较为盲目。乡村劳动力大多为了经济及生活目的进入城市,但并没有立即纳入到现代工业部门,而是从事商贩、非熟练服务人员、手工业者、建筑工人等职业,亦即流入到所谓的“城市传统部门”,随后才能缓慢过渡到现代工业部门。[注][美]迈克尔·P. 托达罗、[美]斯蒂芬·C.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11版)》,聂巧萍、程晶蓉、汪小雯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435-460页。例如,叙利亚约42%、埃及约55%的城市人口从事小贩、运输司机、洗衣工等工作岗位。[注]Keith Crane, S. Simon and Jeffrey Martini, “Future Challenges for the Arab World: The Implication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Trends,” p. 72.
事实上,中东国家的经济政策很少能够为乡村到城市的人口空间结构转换预留缓冲地带,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通病。在发展经济学视域下,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与乡村中的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并存状态,推进工业化旨在将二元结构合并为同质的一元经济结构。[注]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但事与愿违,许多中东国家的工业化政策促使人口集聚到城市,却未能将二元并存的经济结构合二为一。这使得中东地区工业化水平低下的城市区域占有了大量的人力和生产资料,同时乡村地区从事初级生产活动的劳动力稀缺,进而造成了人口空间结构超速转变、工业化演进动力缺失等结果。
四、 人口治理与中东国家的社会文化观念
人口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人口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分支。正如现代化理论家所述,生育观念等人口问题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相辅相成。[注][美]安斯利·科尔:《人类的人口史》,载[美]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中东国家人口的婚姻、生育、性别、族群等观念受到宗教、文化、群体认同等因素影响,尚未全面形成现代人口观念,削弱了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甚至导致不同族群、教派间社会文化上的群体割裂现象,迟滞了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东人口文化观念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中东地区的婚育观受到传统、保守观念的影响。以婚姻观念而论,近亲结合及一夫多妻是该地区传统文化观念的遗产。据统计,中东地区约25%至33%的女性嫁给了堂兄弟或亲属。[注]Hoda Rashad, M. Osman and Farzaneh R. Fahimi, Marriage in the Arab World,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05, p. 5.根据伊斯兰教法和文化习俗,在保证待遇平等的前提下,男性可以迎取四个妻子,这一风俗在阿拉伯半岛尤为突出。同时,在经济欠发达以及伊斯兰教观念浓厚的地区,早婚早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注]Shehada Nahda, “Between Change and Continuity: Age and Marriage Trends in Gaza,” Journal of Wome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slamic World, Vol. 6, No. 2, 2008, pp. 315-323.2013年阿富汗53%的结婚女性年龄低于18岁,21%的女性低于15岁。也门每年超过一半的结婚女性小于18岁,其中不乏年仅8岁的“小新娘”。[注]Haley Sweetland Edwards, “Yemen’s Child Bride Backlash,” Foreign Policy, April 30, 201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0/04/30/yemens-child-bride-backlash-2/,登录时间:2018年1月28日。2011年以来,流入约旦的叙利亚难民童婚比例从13%上升到32%。[注]Benedetta Berti,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Regional and Human Security Implications,” Strategic Assessment, July 2015, pp. 34-35; Abigail R. Esman, “The Next Syrian Refugee Crisis: Child Brides,” Frontpage, February 29, 2016, http://www.frontpagemag.com/fpm/261981/next-syrian-refugee-crisis-child-brides-abigail-r-esman, 登录时间:2018年1月17日。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土耳其,童婚率也高达28.2%。[注]“Turkey: Child Marriag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July 17, 2013, http://www.unfpa.org/webdav/site/eeca/shared/documents/publications/Turkey%20English.pdf,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7日。
就生育观念而言,中东的宗教文化普遍鼓励多生多育、多子多福。[注]Mohammad Jalal Abbasi-Shavazi and Fatememeh Torabi, “Women’s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in Islamic Countries,” in Hans Groth and Alfonso Sousa-Poza, eds., Population Dynamics in Muslim Countries: Assembling the Jigsaw, Berlin: Springer, 2012, p. 44.联合国卫生署东地中海办公室研究员阿卜杜·拉希姆·奥姆兰(Abdel Rahim Omran)指出,《古兰经》并没有禁止节育、人口控制的经文,也没有对生育间隔的明确表述,原因是真主“洞悉一切”以及伊斯兰教永恒不灭,不会受人口增减的影响。[注]Abdel R. Omran, Family Planning in the Legacy of Islam, pp. 59-65.此外,伊斯兰教认为家族是社会的基础,只要家族成员幸福安康,社会平稳发展,便可以实行某种程度的生育控制。但是,宗教学者认为终止妊娠是杀婴行为而被伊斯兰教法明令禁止,因此伊斯兰教的生育控制行为严格限定在受孕之前。[注]Farzaneh Roudi-Fahimi, “Islam and Family Planning,” PRB: MENA Policy Brief, August 2004, https://www.prb.org/islamandfamilyplanning/,登录时间:2018年2月7日。当前,中东地区宗教团体往往发挥着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注]Farhad Kazemi, “Perspectives on Islam and Civil Society,” in Sohail H. Hashmi, ed., Islamic Political Ethics, Civil Society, Pluralism and Conflic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8-40.,它们恰恰欠缺人口生育方面的现代化理念,本地区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不健全的现实,都不利于抑制过高的生育率。
第二, 中东地区的不平等两性观,是人口治理与社会文化现代化演进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中东地区的两性差异并不是依据自然的生理属性划分,而是在社会文化、家庭生活、经济机会、政治权利等多方面表现为一种男尊女卑的特征。[注]Eleanor A. Doumato and Marsha P. Posusney, eds., Women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Gender,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 8.沙特的不平等两性观念最具代表性,沙特妇女从衣食住行到就业参政,都受到了法律与风俗的限制。[注]David S. Soren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Middle East: History, Religio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 148.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尽管沙特已经扩大了某些女性权利,如允许女性驾车等,但大多数沙特女性仍然处于性别隔离状态。此外,受中东地区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的价值属性仍然局限于生育及抚育子女等家庭事务领域,其社会价值并没有发挥出来。[注]Ruth M. Beitler and Angelica R. Martines, Women’s Rol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lifornia: Greenwood, 2010, p. 52.早婚行为缩短了女性受正规教育的年限,陷入了低教育水平、低社会融合度、低工资水平、高失业率及高生育率的循环。
有学者认为,赋予妇女相应的权利,不仅可以改善她们在社会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她们的社会角色和心理期望。[注]Robert McNown and Sameer Rajbhandary,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Fertility and Female Labor Market Behavior,”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16, No. 3, pp. 501-523; J. Siegers, Jong-Gierveld and E. Van Inhoff, eds., Female Labor Market Behavior and Fertility, Berlin: Springer, 1991, pp. 101-129.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政府推行增加女性权利、转变不平等两性观念的政策,未来中东女性所拥有的健康婚育行为、良好教育经历以及积极的工作态度,将改变传统妇女依附于丈夫、单纯负责生育子女、操持家务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当面对婚姻年龄、生育子女数量及生育间隔等问题时,她们会理性地权衡个人发展与生育成本及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女性做出降低生育率及追求生育质量的决策,从而推动中东地区逐渐形成女性权利、生育观念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三, 中东地区的族群意识是政治与社会文化割裂的根源。中东伊斯兰世界从来不是一个步伐统一和目标一致的整体,它被宗教派系、种族认同、部落纷争等因素分割成了零散而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单元。[注]王泰、陈小迁:《追寻政治可持续发展之路:中东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页。中东地区既有阿拉伯、波斯、犹太、库尔德、普什图、科普特、柏柏尔等种族,又存在着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及其分支等一系列宗教和教派,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的族群意识结构。此外,中东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大多为威权人物推动,其间受到西方势力的干涉与扰乱,具有偶然性与强制性的特点。国家构建速度明显快于民族构建,从而形成了国家民族(state-nation),缺乏循序渐进的认同过程,造成人口文化中自我叙事的族群意识较为强烈。[注]Alfred Stepan, Juan J. Linz and Yogendra Yadav, “The Rise of ‘State-N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3, 2010, p. 57.
除催生政治冲突外,族群意识还对社会稳定与人口治理政策的贯彻实施产生阻碍。一方面,中东社会因不同族群间的矛盾与隔阂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不利于社会的凝聚,政治经济资源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短期利益交换甚至“零和博弈”。此外,除目的性联姻等方式外,族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婚姻、迁移等为手段的社会交往和流动,从而固化并加强了地方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中东地区较强的族群意识造成了不同群体间人口观念差别显著的局面,不利于政府制定统一的人口政策,一般性人口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特别是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一些国家仍存在较多的部落群体,它们的生育传统和人口文化的特异性较强,人口政策很难在“部落孤岛”上推行。
五、 余 论
中东国家长期积累的人口问题羁绊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中东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中东国家不仅要解决当前的人口问题,还要聚焦未来人口形势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从国家治理体系上把握人口治理的基本矛盾、转型方向与推进效果,进而为破解国家治理困境找寻出路。具体而言,在人口治理视角下,以下三点应成为中东国家破解治理困境的关键。
第一,坚决控制人口规模是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当务之急。高速增长的人口不仅造成“人口陷阱”效应,还稀释了政府财政投入,降低了人口质量提升速度,造成经济资源过度消耗,对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因此,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降低人口增长率,排除这一羁绊国家治理与长远发展的隐患。一是应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利用惩奖并重的办法,重点控制城市的人口增长率,降低城市膨胀对经济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消耗,力求避免发生严重的粮食危机。二是应建立完善的生殖保障体系,对相关医护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供避孕器具等相关生殖健康服务。
第二,中东国家应以提升人口素质为抓手,尽快释放“人口窗口期”中的劳动力价值,为经济良性发展注入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动力。一是现阶段需要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保证青年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二是进行以人力资源需求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改革,均衡提升人口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质。政府需要制定政策使部分青年向职业教育分流,细化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差别,重点加大技能培训方面的财政投入,尽早释放“人口红利”。三是提高妇女地位,赋予妇女以更多的劳动经济属性。这不仅可以增加女性的劳动价值,将她们转变为经济贡献者,而且有利于调整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应关系,使更多男性劳动力投入到重体力、技术等岗位,使劳动岗位的性别分类合理化。
第三,中东国家应推动社会的传统人口观念向现代科学观念转型,为人口政策施行及社会发展发挥必要的辅助作用。中东各国政府需要拓展功能化的施政体系,在制定和推行统一政策的前提下,采取灵活与多元化的施政手段。一是根据目前人口与社会状况,政府应设立专门的人口治理机构或综合发展委员会,负责政策推行与理论宣传,引导人口观念的现代化转型。二是针对当前社会的价值取向,根据不同的族群、宗教、文化观念,以民众易于和乐于接受的形式推广国家人口政策。三是注重社会文化嬗变与人口观念转变之间的联动效应,以人口意识现代化转型作为社会观念发展的突破口,塑造整体性和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观念,为中东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