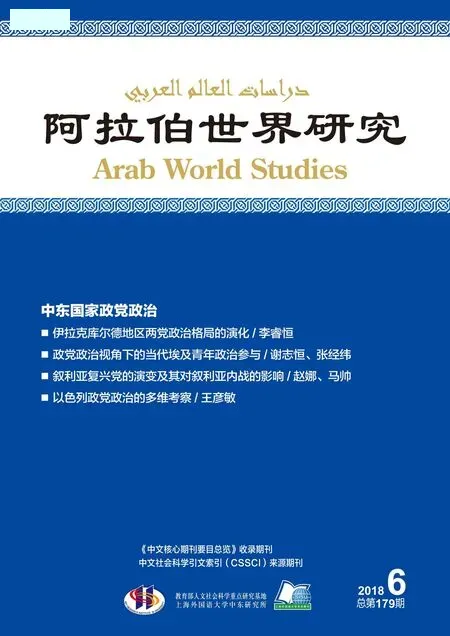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多维考察*
王彦敏
早在建国前,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格局和传统便已基本形成,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政党政治在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促进了其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以色列政党政治有着诸多特殊性,本文拟从移民社会、历史传统、宗教文化、族群矛盾和地缘环境等诸方面予以探究。
一、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
世界上有许多多党制的国家,但以色列的多党制却“多”得与众不同:党派林立、分化组合频繁、碎裂化格局越来越明显,这也成为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据统计,以色列建国70年来,有数百个党派参加了共20届议会的选举,每届议会的参选党派最多时达33个,最少时也有14个,最终能踏入议会门槛的党派均不少于10个,多时达15个。不仅如此,在下届议会选举前,通常会有一些议会党团出现分裂,从中产生许多小党,导致议会政党数量的增加,最突出的如第9届议会、第15届议会最终增加到20个,第14届议会甚至达到21个。[注]“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Knesset,” Knesset, http://www.knesset.gov.il/history/eng/eng_hist_all.htm, 登录时间:2017年7月6日。这一基本特征主要源于如下四个因素。
首先,移民社会的多元性。以色列是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建立起的一个移民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为以色列多党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既反映了建立在种族、宗教、语言等因素基础上的亚文化差异,反映了社会经济阶级关系上的分层,也反映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兴起。”[注]王长江:《世界政党比较概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受来自不同地域移民的教育水平、职业状况、生活经历、思想观念和日常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伊休夫)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以色列国家呈现出多元化的社会群体结构。各社会群体为表达群体诉求、维护群体利益纷纷建立政党组织或推出选举人,继而形成党派林立的政治格局。
其次,单一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以色列是“不折不扣地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唯一国家”[注][美]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钱乃复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78年版,第187页。,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大选区而全部实行比例代表制,又称单一比例代表制。[注]比例代表制的议席分配方法第一步要计算出一个议会席位所需要的基本票数,也称当选基数,第二步要用各政党所得总票数除以当选基数,即得出各党在议会应得的席位数。比例代表制意指各政党所得选票与其所得议会席位成正比关系。该选举制有利于小政党的发展,能使那些少数选民、弱势群体和特殊利益集团比较容易使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进而获得表达自身诉求的机会。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即采用比例代表制以调动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参与复国运动的积极性。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更加全面地反映民众意愿。以色列建国后,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将单一比例代表制最终确立为基本的议会选举制度。较低的议会准入门槛的规定也极大地推动了新党和小党的建立,导致许多有抱负的政治家脱离母党另组新党参加议会选举。
再次,总理直选法案的推动。1996年以色列总理直选法案的实施促进了党派的分化组合,加剧了政党格局的碎裂化。总理直选制度使以色列选民在选举投票时需要同时投总理候选人和党派两张选票。选民投选总理后,另一票不一定投给总理所在的大党,而是常常投给能更多代表和维护选民自身利益的政党。由此,许多新党和小党获得了大量选票,传统大党得票率明显下降。尽管2001年以色列废止了总理直选,但党派林立的碎裂化政党格局已经形成。
最后,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以色列政党政治碎裂化格局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色列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进程加速发展,私有经济开始代替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受到严重销蚀,追求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成为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以色列社会结构更趋多元化,代表小群体利益的社团、组织和党派不断涌现。
二、 宗教政党的特殊历史地位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先驱西奥多·赫茨尔最初规划的“犹太民族家园”是一个现代世俗民主国家,1948年以色列《独立宣言》重申了以色列作为一个现代世俗民主国家的性质。但从建国70年的历史来看,以色列国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犹太教实际上处于国教地位,以色列宗教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超出了通常人们对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解。这种局面的形成既受到犹太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又是以色列现实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唯一标识,成为以色列宗教政党独特历史地位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聚合剂,对于犹太人来讲,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已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在当今以色列,约有20%的犹太人承认自己是正统犹太教的信奉者, 约有25%~30%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世俗的,而多数犹太人则认为自己是遵守犹太传统的。[注]Reuven Y. Hazan and Moshe Maor, Parties, Elections and Cleavages: Israel in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0, p. 113.大多数犹太人认同在公共生活中保留浓厚宗教色彩,也认同宗教与国家政治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其次,以色列宗教组织、宗教政党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成为其特殊历史地位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基础。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的《追寻锡安》一书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注]张倩红:《以色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他积极争取世界犹太人联盟的支持和帮助,在以色列建立米克维农业学校。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欧洲正统派犹太教一分为二:一支力量是产生于俄国和东欧正统犹太教组织的世界精神中心运动(以色列国家宗教党的前身),强调不应坐等救世主降临,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是犹太人救赎的第一步,不违背犹太教教义。另一支力量是源于德国极端正统派的世界以色列正教运动,坚决维护犹太教传统价值观念,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在救世主降临前任何复国的努力都是违背犹太教教义的。希特勒上台之后,正教运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以宗教名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应该说,不管是精神中心运动的复国实践还是正教运动的思想转变,都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宗教上的合法性。
最后,以色列的多党政治制度为宗教政党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平台。在以色列独具特色的多党政治背景下,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超过60席)单独组阁,获得组阁资格的大党必须寻求小党的合作。宗教政党由于纲领、选民和组织结构相对固定,故成为大党组阁谈判时拉拢的首选目标。宗教政党也借此提高要价,获得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随着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发展,宗教政党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由虚变实、由防御到进攻的演变过程。
1948年至1977年间,工党主导着以色列政坛,其连续执掌八届议会,其他政党难以抗衡工党一党独大的优势地位。其间,宗教政党的力量虽然虚弱,但凭借国家宗教党与工党近三十年的“历史的联合”[注]1948至1977年间,国家宗教党参与了工党历届联合政府的组建,被称为“历史的联合”。而享有独特的政治地位。这种联合既是以色列建国前教俗关系“现状协议”[注]1947年6月,巴勒斯坦工人党与宗教运动领导达成了一份“现状协议”:在宗教和国家之正式关系确定前,有关宗教事务方面的现状需予维持;宗教组织支持国家的建立,同意参加联合政府的构建。根据“现状协议”,犹太拉比法庭可继续掌握结婚、离婚、皈依等方面的决定权;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要遵守安息日和犹太节期,犹太教立法在某些范畴内可作为世俗国家立法使用。的逻辑延伸,也是工党现实政治选择的结果。有学者分析指出:“工党联合宗教政党构建联合政府,考虑的不是共享权力,不是强化意识形态,也不是考虑社会计划的实现,而是着眼于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合作和协调。”[注]Asher Cohen and Bernard Susser, Israel and the Politics of Jewish Identity: The Secular-Religious Impass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7.其间,宗教政党为维护宗教群体的利益,曾围绕部分宗教议题向主导政党发难,但并没有撼动工党的主导地位。
1977年至1996年是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竞争对抗的时期,两大政党势均力敌,任何一方要想建立排除对方的小型联合政府,都需要借助宗教政党的力量。此阶段宗教政党的政治参与成为政府组建的决定性因素,其实力和社会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例如,1977年以色列大选后,利库德集团领导人贝京为联合宗教政党组建联合政府,不仅按国家宗教党的要求为该党安排了三个部长职位,而且在一些长期存在争议的宗教核心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包括安息日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禁飞、年满18岁的犹太宗教学院学生免服兵役、信奉犹太教的妇女免服兵役,等等。双方达成了一项包含43项条款的协议,其中涉及宗教事务的条款就有30条之多。[注]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69.1981年贝京再次组建联合政府时,宗教政党迫使贝京在更严格遵守犹太教教法和宗教立法方面做出进一步妥协。
从1996年开始,以色列政党政治格局的碎裂化日趋严重,联合政府组建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此格局下,传统大党不复存在,介于左右两大传统政党之间的世俗中间党派和宗教政党的力量不断加强。以第19届议会和第20届议会为例,进入第19届议会的党团有12个,分别为是利库德集团—以色列家园联盟(31席)[注]以色列家园党系前苏联犹太移民政党。、未来党(19席)[注]未来党由亚伊尔·拉皮德领导建立,属世俗中间党派,成立于以色列第19届议会选举前夕。、以色列工党(15席)、三个宗教政党(共30席:犹太家园党12席、沙斯党11席、托拉犹太教联盟7席)、运动党(6席)[注]运动党由原前进党领袖兹皮·利夫尼领导建立,属世俗中间党派,成立于以色列19届议会选举前夕。、民主以色列党(6席)[注]民主以色列党即“莫雷兹党”,属左翼世俗党派,比工党温和。1992年大选前由统一工人党、公民权利运动和部分变革党成员组成“莫雷兹集团”,1997年正式合并为“莫雷兹党”。、联合阿拉伯名单(4席)、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4席)和民族民主联盟(2席)[注]联合阿拉伯名单(拉姆党)、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哈达什党)和民族民主联盟(巴拉德党)系代表和维护阿拉伯人利益的政党。。这些政党基本形成了右翼、宗教、左翼和中间党派阵营各约占30%议席的格局,[注]Michal Shamir, ed., The Elections in Israel 2013,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5, p. 6.宗教政党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在组建第33届联合政府期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以色列家园联盟在联合了未来党、运动党和犹太家园党后,才建立起占议会68个席位的联合政府。以色列第20届议会中有10个议会党团,分别是:利库德集团(30席)、犹太复国主义阵营(24席,工党和运动党联合组建)、三个宗教政党(共21席:犹太家园党8席,沙斯党7席,托拉犹太教联盟6席)、联合名单(13席,由联合阿拉伯名单等四个代表和维护阿拉伯人利益的政党联合组建)、未来党(11席)、我们大家党(10席)[注]2014年,莫什·卡隆领导建立了“我们大家党”,即库拉努党,该党脱胎于利库德集团,属世俗中间党派。、以色列家园党(6席)和莫雷兹(5席)。右翼—宗教政党集团拥有57个议会席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联合了我们大家党、以色列家园党及三个宗教党后才完成了第34届政府的组建。
宗教政党独特的历史地位既受犹太民族独特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是以色列社会现实的需要。客观地讲,宗教政党政治的运作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对政府的执政效率也产生了一定的阻滞。然而,宗教政党作为联合政府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传统大党的专权可以发挥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三大宗教党从各自相对固定的选民群体中获取选举支持并通过政治活动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这对以民众政治参与为核心的以色列政治民主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总之,宗教政党的政治参与成为以色列民主政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族群矛盾影响下的以色列政党政治
复杂的族群矛盾是以色列多元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早在以色列建国前的伊休夫时期就形成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与塞法迪人[注]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m)又称西方犹太人,曾指中世纪生活在莱茵河畔及整个日耳曼地区的犹太人及后裔。后来,东、西欧犹太人,包括比较晚移民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普遍被称为阿什肯纳兹人。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多指文化和地理上起源于西班牙及葡萄牙地区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经数百年的生活变迁,生活在欧洲国家的塞法迪人已与阿什肯纳兹人融合;而生活在西亚北非等地的塞法迪人也与一直生活于此的东方犹太人无几差别。在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非西方犹太人有两种划分:一是塞法迪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二是把非西方犹太人统称为塞法迪犹太人即东方犹太人。笔者通常使用第二种划分方法。之间的两组族群矛盾,以色列建国后这些矛盾日益深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伴随苏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新、老犹太移民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形成。以色列政党政治深受这些社会矛盾的影响。
(一) 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
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既有宗教文化的冲突,也有因争夺生存权和领土权而产生的民族积怨,更源于以色列国家的阿拉伯人所处的极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根据以色列《独立宣言》和《国籍法》,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应享有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地位,但以色列在最初的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上,就已经将阿拉伯少数群体置于一种明显不平等的地位。
1949年至1966年以色列对境内阿拉伯人实行的军事管制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阿拉伯社区遭封锁,阿拉伯人行动自由遭限制,阿拉伯人65%~75%的土地[注]杨阳:《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发展现状及其政治意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6期,第58页。遭掠夺,并且阿拉伯人在教育资源的配置、升学途径、就业机会、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对自身所遭遇的不平等,阿拉伯人最初几乎是集体无意识,在以色列政党政治格局中处于被动地位。这一时期,巴勒斯坦工人党(以色列工党前身)作为主导政党在引导阿拉伯人的选举行为:引导阿拉伯精英构建“卫星名单”(satellite lists)[注]这些选举名单与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常被称为大党的卫星名单。,争取阿拉伯选民的支持,进而再选举支持巴勒斯坦工人党。[注]As’ad Ghanem, Ethnic Politics in Israel: The Margins and the Ashkenazi Cent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49.1969年前,卫星名单通常能获得40%~50%阿拉伯选民的支持。[注]Uzi Rebhun and Chaim I. Waxman, eds., Jews in Israel: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Cultural Patterns, Hanover and London: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51.军事管制解除后,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感增强,开始就不平等表达不满和诉求。在1973年选举中,维护阿拉伯人利益的政党——拉赫党赢得37%的阿拉伯人选票,获4个议席。[注]1965年,以色列共产党分裂为马基党(Maki)和拉赫党(Rakah),前者主要以犹太人为主, 1981年并入其他左翼政党;后者以阿拉伯人为主,认同以色列国家,也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主张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长期坚持亲苏联的政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为争取阿拉伯人选票,开始陆续吸纳阿拉伯人入党。这标志着阿拉伯人的政治自觉进程已经开启并开始影响以色列的政党政治。
1977年至1996年间,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的竞争对抗以及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自觉进程。在政治参与方面,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力支持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如在1977年选举中,拉赫党以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为名参加选举,获50%的阿拉伯选民支持,赢得5个议席。[注]As’ad Ghanem, Ethnic Politics in Israel: The Margins and the Ashkenazi Center, pp. 49-50.1984年,另一个代表和维护阿拉伯人利益并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建的“争取和平进步名单”成立,并在当年的选举中赢得近20%阿拉伯选民的选票,获2个议会席位。[注]安维华等:《以色列议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在1984年选举中,不再有阿拉伯选民投选卫星名单,[注]As’ad Ghanem, Ethnic Politics in Israel: The Margins and the Ashkenazi Center, p. 53.直接选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选票占49%,而支持代表或维护阿拉伯人利益政党或名单的选票占51%,1988年相应的数字分别为40%和60%。[注]Uzi Rebhun and Chaim I. Waxman, eds., Jews in Israel: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Cultural Patterns, p. 357.1988年选举前,因不满工党对1987年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态度,工党的阿拉伯议员达拉瓦锡退出工党而组建了阿拉伯人的独立政党——阿拉伯民主党。在1984年和1992年两届议会选举中,支持工党的阿拉伯选民约占其总数的50%和52%,“成为以色列具有平衡力量的选票”,[注]Adam Garfinkl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Modern Israel: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M.E.Sharpe, 1997, p. 174.使工党自1977年以来重回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1996年起以色列政党政治进入了碎裂化发展时期,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阿拉伯公民通过更多的途径强烈抗议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其突出表现是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选民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支持转而支持代表和维护阿拉伯人利益的政党。据统计,1996年支持犹太政党和阿拉伯政党的阿拉伯选民比率为38%和62%,1999年则为23%和77%。[注]Uzi Rebhun and Chaim I Waxman, eds., Jews in Israel: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Cultural Patterns, p. 357.在2015年的第20届议会选举中,联合阿拉伯名单、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民族民主联盟和阿拉伯复兴运动四方组建“联合名单”参加选举,共获13个议席,在全部10个议会党团中位居第三。[注]“Current Knesset Members of the Twentieth Knesset,” “Knesset Members by Parliamentary Group,” Knesset, http://www.knesset.gov.il/mk/eng/mkindex_current_eng.asp?view=1,登录时间:2017年7月6日。这标志着以色列阿拉伯人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参与和抗争,其族群凝聚力大幅增强,已成为以色列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长远来看,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会不断得到改善,但其作为以色列社会二等公民的身份很难扭转,因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两大族群之间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并对以色列的政党政治继续产生影响。
(二) 阿什肯纳兹人和塞法迪人之间的矛盾
与阿犹族群矛盾不同,阿什肯纳兹人与塞法迪人之间的矛盾属于犹太人内部群体间矛盾。阿什肯纳兹人和塞法迪人来自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区,加之塞法迪人是在阿什肯纳兹人的主导地位早已确立及以色列国建立后大规模移入的,[注]1948年,塞法迪人占犹太人总人口的25%,1961年占45%。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塞法迪人和阿什肯纳兹人人口大致相等,1967年中东战争后,塞法迪人口开始超过阿什肯纳兹人口,并保持上升态势,直至90年代大批苏联犹太人的涌入。故双方既有的差距日益固化。伴随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发展,两大群体间的矛盾既表现为塞法迪人“从议会外向议会内反抗模式的转变”,也体现为“其从支持工党到转而支持利库德集团再转而支持沙斯党的政治参与历程的转变”,[注]王彦敏:《以色列政党政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而这个过程正是塞法迪人政治觉醒和成熟的过程。
以色列建国后的最初20年间,塞法迪人总体上政治自主性低,由于其居住、就业、日常生活等主要依赖工党政府的安排,故在议会选举中他们更多地将选票投给工党以维护自身利益。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塞法迪人不仅在人口数量上开始超过阿什肯纳兹人,而且战争催发了他们的政治自觉。他们开始就自身所处的不平等社会地位向工党政府表达强烈不满,对工党的选举支持呈下降趋势。但总体而言,在工党主导以色列政坛的近30年间,塞法迪人的选举支持是工党在政治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1977年选举中,塞法迪人的支持成为利库德集团战胜工党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选中有46%的塞法迪选民支持利库德集团,支持工党联盟的仅有32%。[注]Don Peretz and Gideon Doro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Israel,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p. 248.塞法迪人开始将更多的选票投给利库德集团,并非是认同利库德集团的价值观和执政理念,而是出于对现存的不平等社会秩序的不满。利库德集团主政后虽采取了诸多改善塞法迪人政治经济状况的举措,但其力推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反而加大了两大犹太群体间的不平等和矛盾。塞法迪人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强调社会公平的工党更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故在1992年选举中,许多在上届选举中支持利库德集团的塞法迪人转而支持工党,这成为工党复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利库德集团和工党两大政党的竞争中,塞法迪人的政治自信得以加强,开始组建独立政党。1981年,因不满国家宗教党领导层长期歧视塞法迪人的政策,摩洛哥裔犹太人阿哈伦·阿布-哈兹埃拉脱离国家宗教党另立“泰米党”,并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3个议席;1983年,因不满正统犹太教政党内部和宗教教育机构中阿什肯纳兹人对塞法迪人的不公正态度,塞法迪大拉比奥维迪亚·约瑟夫等领导组建“沙斯党”,并在1984年的议会选举中获4个席位,之后在1988年、1992年的选举中两次获6个席位;1995年,因不满利库德集团内部阿什肯纳兹人对塞法迪人的歧视性态度,摩洛哥裔犹太人戴维·利维脱离利库德集团另立“盖舍尔”。
沙斯党为塞法迪人不平等的社会状况奔走呼吁,影响力迅速加强。1996年大选中,沙斯党一举获得10个议席。日益加剧的碎裂化政党政治为沙斯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沙斯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塞法迪犹太选民,如1996年大选中有85%的塞法迪选民支持沙斯党,[注]Asher Arian and Michal Shamir, eds., The Elections in Israel 1996,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77.1999年大选中,约有33%的亚裔犹太选民和50%的北非裔犹太选民支持沙斯党。[注]Uzi Rebhun and Chaim I. Waxman, eds., Jews in Israel: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Cultural Patterns, p. 63.这些选民此前曾经先后支持过利库德集团和工党。
塞法迪人从支持工党转向支持利库德集团,继而在两大政党之间不断调整支持取向,再到组建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政党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选举支持对象,整个政治参与过程旨在表达对自身不平等地位的不满,是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主导的社会秩序的抗议,既强有力地影响了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演变,也推动了以色列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 新旧犹太移民之间的矛盾
上世纪末期,有近100万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这批新移民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社会一个独特的群体。首先,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使他们异于其他犹太移民群体,尤其是其自身表现出的诸多“非犹太性”和“俄罗斯化”,导致他们常遭致传统以色列社会的谴责和排斥。其次,新移民群体的人口素质明显高于以色列的平均水平,他们在移民以色列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礼遇和享受的政策明显优于塞法迪人,这导致后者对他们的嫉恨和对执政党的不满。最后,新移民更多地被安置在被占领土的定居点上,由此形成了被占领土命运与新移民安置的密切关系。新移民对被占领土问题多持强硬态度,是右翼政党强有力的支持者。新移民的特殊性及与诸多利益群体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促使该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加强。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从最初支持传统大党到后来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政党。
在1992年选举中,由于工党在其竞选纲领中对于新移民安置工作给予很大关注,结果有约65%来自苏联地区的犹太选民支持拉宾领导的工党,这成为工党战胜利库德集团的关键因素。[注]As’ad Ghanem, Ethnic Politics in Israel: The Margins and the Ashkenazi Center, p. 145.工党重新执政后,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坚持“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触动了许多新移民的切身利益。为维护新移民群体的利益,1996年纳坦·夏兰斯基领导建立了“以色列移民党”,2006年大选前夏兰斯基加入了利库德集团。1999年阿维克多·利伯曼又领导建立了代表新移民利益的“以色列家园党”。伴随政党政治碎裂化格局的加剧,新移民群体的政治力量和影响迅速增强。在1996年的总理选举中,他们抛弃了工党而选择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为总理人选。但是,内塔尼亚胡在巴以问题上的退让(以色列撤出约旦河西岸13%的地区)引发了新移民的强烈不满,故新移民在1999年大选中又把54.5%的选票投给了工党的巴拉克,内塔尼亚胡只获得了新移民45.5%的选票。[注]周承:《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影响》,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而当巴拉克决定撤出西岸95%的地区时,他们又纷纷抛弃巴拉克而选择沙龙及其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2009年的选举中,“以色列家园党”获得的15个席位使之成为议会第三大政党,比工党多出2席。2013年,利库德集团与“以色列家园党”组建联合选举名单,才勉强维持了第一议会党团的地位。新移民群体成为以色列政坛的重要平衡力量,其政治参与都紧紧围绕捍卫群体利益,显示了该群体及其政党的巨大政治能量。
总之,上述社会群体间的矛盾伴随着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深入发展和演变,在此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得到疏通和缓解,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加强,政治民主化也随之不断发展。
四、 阿以关系影响下的以色列政党政治
阿以关系是指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及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它经历了从全面对抗到寻求政治解决的过程,对以色列政党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以色列政党分野、分化和兴衰的重要地缘政治因素。
工党主导以色列政坛时期是阿以全面对抗时期。其间,中东地区爆发了四次大规模的阿以战争。各犹太政党对待阿以关系的态度基本一致,即确保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战争的胜利、确保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的战争在客观上成为以色列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它“在以色列维系了人民的团结,激发起一种斯巴达式的勇敢精神,并争取到世界上其它地区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注][英]诺亚·卢卡斯:《以色列现代史》,杜先菊、彭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7页。。这对于维系工党政府的主导地位功不可没,因为它延缓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蔓延。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成为转折点,战后以色列社会围绕如何处置被占领土问题的大辩论造成了深深的社会裂痕。战争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场大辩论中持续发酵,社会舆论开始走向偏右,为右翼—宗教政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从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阿以对峙阶段。强硬派的利库德集团能战胜工党执政是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社会右倾化的结果。1978年利库德集团执掌的以色列政府与埃及政府达成《戴维营协议》后并没有带来阿以和平的连锁反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激化矛盾的事件——1980年《基本法: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1982年黎巴嫩战争、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义接踵而至,引发各党派和政治团体围绕被占领土地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解进程及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激烈辩论。有学者指出:“引发人们关注和引起公众辩论的问题,像往常一样,是安全问题、国防问题以及与阿以冲突相联系的和平进程问题,更具体一点,即巴勒斯坦大起义和以色列社会的反应。”[注]Bernard Reich,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8, p. 152.政党政治分化组合最为突出的1984年大选和1988大选即发生在这一时期。持强硬立场的右翼势力影响明显扩大,超级强硬派泰西亚党、佐梅特党、莫莱德特党在此期间相继成立。在1992年大选中,拉宾领导的工党获胜,这是自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围绕被占领土地位问题及和平进程问题左右两股势力角力的结果,也是以色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呼唤和平的反映。
1992年工党执政后,阿以冲突进入政治解决阶段。1993年和1994年,以色列先后与巴勒斯坦达成《奥斯陆协议》和《开罗宣言》;1995年,以色列与约旦达成《华盛顿宣言》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此后拉宾遇刺等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事件、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0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2006年)、以色列三次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打击(2008年的“铸铅行动”、2012年的“防务之柱”、2014年的“护刃行动”)一再使和平进程陷于困境。每一次危机来临时,有关阿以关系的核心问题——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被占领土归还问题、难民回归问题——就会引发以色列社会的分歧和争论,进而影响政党政治。
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且暴力不断升级的背景下,2001年以色列总理直选实际上成为工党和平政策和利库德集团强硬政策之间的一次角力。选举前以色列国家选举部门的研究结果显示,有79%的选民认为政府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安全问题和外交事务问题。[注]Asher Arian and Michal Shamir, eds., The Elections in Israel 1999,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 4.许多人认为,工党领袖巴拉克对阿拉法特的一味退让是导致巴以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所在,故此将以色列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利库德集团的强硬政策上。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以63.3%对37.7%的明显优势战胜巴拉克成为以色列近十年来的第六任总理。[注]Bernard Reich,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p. 218.第二届沙龙政府成立后,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以色列开始启动“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实施“单边行动计划”,巴以关系暂得缓和。此举遭致利库德集团内部右翼势力的反对,沙龙无奈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组前进党,这直接导致利库德集团在2006年议会大选中惨遭失败。
沙龙患中风后,奥尔默特主持的前进党政府未能继续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加之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铸铅行动”及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了以色列民众对外部威胁的敏感性及对巴以和平进程的失望,这导致以色列的政治生态再次滑向右倾,并在2009年的大选结果中得到体现:温和的中左翼阵营获得55个席位,对阿政策强硬的右翼—宗教阵营占65个席位,一贯力推阿以和平进程的工党仅获13席。2011年,巴拉克退出工党另组独立党,在对阿政策上开始持较强硬的态度。2012年以色列发动了强力打击加沙哈马斯的“防务之柱”军事行动,2014年又发动了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军事打击。紧随这两次行动的是19届和20届议会大选,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力量接连获胜。“铸铅行动”、“防务之柱”和“护刃行动”恶化了巴以关系,且分别发生在2009年、2013年和2015年大选前。这并非偶然,而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有意安排,一个重要目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大的支持。
自2015年内塔尼亚胡再次主政以来,巴以关系时有紧张,持续动荡的中东局势,尤其是“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形成及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的崛起,都使以色列民众更关心安全问题。2016年初以来,内塔尼亚胡长期陷于腐败指控调查,但在国内却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支持率,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选民相信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政党的强硬政策能给国家带来安全。可以说,紧张动荡的地缘环境成为利库德集团等右翼政党以强硬政策获取选票并主政以色列的重要因素。
长期的阿以冲突造成的战乱和由来已久敏感的生存危机意识,以及以色列自身国力的增强等因素,使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意识迅速膨胀。而现实中尚未解决的安全问题(时而发生的爆炸、冲突等)、长期冲突造成的积怨、定居点问题、水资源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等都关乎切身利益,因而不断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民众普遍支持政府在解决阿以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注]冯基华:《从加沙战乱解读以色列政党政治发展及其未来大选》,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2期,第56页。阿以关系对以色列政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以色列政党政治也影响并左右着阿以关系的走向。阿以关系和以色列国内政治之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阿以关系紧张导致右翼势力强大,右翼势力的坐大造成和平进程渺茫,暴力冲突也在所难免。
五、 结 语
党派林立、分化组合频繁、碎裂化格局日益明显是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宗教和族群因素不仅影响着从工党主导到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竞争对抗的以色列政党政治,还在碎裂化的政党格局发展演变的各关键节点上扮演重要角色,并成为以色列多元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及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对以色列政治格局的演变起着风向标的作用:阿以关系缓和,中—左翼政党处于优势地位;阿以关系紧张,则右翼—宗教政党居优势地位。这些成为以色列政党政治独特性的核心内容与典型表现。以色列政党政治源于犹太民族的历史并根植于以色列社会,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建设以色列国家的客观需要,并非欧美思想和制度的移植。移民社会的多元性、族群矛盾的复杂性、地缘环境的紧张性、犹太民族的宗教属性和以色列国家的犹太属性,使以色列政党政治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