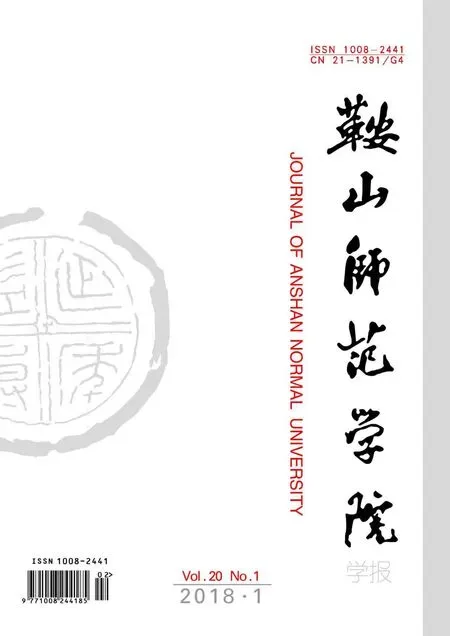高校“孝”文化的培育途径
刘 敏
(鞍山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辽宁 鞍山 114007)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是中华民族推崇并尊奉的重要道德伦理规范和做人基本原则,处于诸德之首、百善之先和教化之始的根本地位,常被看作是个体道德行为的起点,“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从“孝”德培养开始,孝文化教育是提高大学生道德水平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若使源自传统的孝道观念更好地融入当代人生活,“如‘忠’‘孝’等传统文化范畴和行为方式,其基本精神在今天虽然仍有价值,但在表达方式、表现形式、践行要求、评判标准等方面,都需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必要的改造转化和有针对性的创新发展”[1]。在高校,优秀传统孝文化与当代中国高校德育对接仍需要具体载体和有效途径,既要依赖校园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也需要课堂教学理论认识上的自觉提升,以及孝道榜样的典型示范和精神引领。
一、营造适于“孝”德生长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是学校教育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校园文化建设目标在于创设一种能够陶冶学生情操、构建学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环境氛围。高校校园文化承载了塑造大学精神文化品味和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若干功能。校园文化活动主体自主性强,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又因为参与过程的实践性而受到大学生广泛欢迎。一所高校是否能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中融入“孝”文化观念,有效彰显孝道育人功能,取决于学校能否足够努力培育。
(一)“孝”应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主题之一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在大学生中具有一定思想认同和情感基础,有些院校学生自发地开展“孝”道活动。如河北科技大学,学生依据传统孝道文化,结合大学生活,针对大学生在家庭、学习和社会生活及自身修养等方面问题创作了大学生版二十四孝:“儿行千里母担忧,常报平安系心头”“学好专业不逃课,依靠能力找工作”……他们把个人学习态度、生活方式、理想信念等融入其中,既扩大了传统孝道文化的外延,也丰富了其内涵。学生们自发的“创造性转化”正是高校德育工作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它启发我们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元素存在的“孝”,融入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还需要积极引导和具体策划。校园文化活动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思想品德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活动、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体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创业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等。“孝”德内容在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中不应缺席,要用心培育和营造适于大学生接受孝道文化的环境氛围,“孝”文化盛行无疑会提升学校的文化品味和精神风貌。
(二)感恩教育是现代“孝”道教育的延续
感恩是更容易获得当代人理解接受和情感认同的孝道概念,也可以说是传统孝道的现代延续。感恩是指人们感激他人、社会和自然带来的恩惠并意欲回馈的一种内在心理需求。感念父母之恩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可说是超越时空局限的人类共同情感,更容易使学生产生共鸣。如学生在观看《和你在一起》影片时,无不被影片中表现的父子之情感动,学生们情不自已、泪流满面。有些同学这样感受和反思她们的亲情和亲子关系:这场原本以为毫无内容的电影竟是把我看哭了,许是这么多年来,我亏欠父母太多了。虽然情感体验在思想道德教育中通常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但基于感恩的孝道情感体验和激发却是“孝”德理性认识提升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为了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会“行孝”,可组织“感恩从心开始”等主题讨论;利用感恩节、母亲节、父亲节、重阳节等节日,组织学生为父母做件小事,写封家书,发条短信。从孝敬父母感恩父母做起,有了感恩意识,常怀感恩之心,必然更有益于处理与家人、朋友乃至社会人际关系,这正是孝在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睦家庭、融洽人际关系等方面对于个体道德品质提高所能起到的无可替代作用,从这个意义讲,感恩教育可以实现孝道文化的当代转换和延续。
二、加大推进“孝”德教育进课堂的力度
(一)在思政理论课堂教学中可设内容明确的主题或专题
“孝”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基础,在高校德育课堂教学中,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和重视。2015年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虽然增加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家风家教问题的内容,却又因有限课时与庞杂内容的矛盾,导致教学中存在任意取舍现象,影响了“孝”德教育效果的实现。高校校园“孝”文化培育中第一课堂理论引领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理论上的接受和认同会直接影响第二课堂及其他校园文化活动开展的效果。因此,思政理论课应在“基础”课教学中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家庭美德中营造良好家风的内容,找出其与学生情感需求的契合点,并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如学生上了大学后,有的家长感到与孩子沟通存在问题;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变得冷漠,不懂感恩;有人甚至感叹“中国式父母的悲哀:付出全部,却养不出感恩的孩子”,等等,开展具有一定目的性针对性的主题或专题教学。大学生自发组织的孝道活动说明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也是我们加大推进“孝”德教育进课堂的基础。
(二)在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中渗透“孝”德教育内容
我们常把课堂教学之外的各种实践活动称为第二课堂,它是隐形教育环节,因为它潜移默化,常能起到课堂教学无法替代的作用和效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及知行脱节问题,取得更好教学效果,就必须探索稳定可行并可长期持续的实践教学形式。以“基础”课教学为例,很我院校探索出渗透“孝”德教育内容的实践形式。有的学校安排学生观看一些影片,并进行后续拓展和课堂分享,让学生写观后感等;有的学校开展书信传情活动,提供免费信封、信纸和笔给活动参与者,由活动参与者在信纸上写下表达感恩之情的文字给自己最为感激之人,写好邮寄地址封上信封后由活动组织者统一寄出[2];有的学校编写传唱孝敬父母的歌曲,到社会开展调查总结孝敬父母和不孝敬父母的典型,用身边例子教育自己的活动——通过系列活动让大学生懂感恩、会感恩、乐感恩[3]。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曾关注:“30年后,人类历史将迎来一个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小国而是大国,他们将如何与世界相处?这是福音还是灾难?”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独生子女,在与父母的沟通上并不善于表达内心,他们把对父母的感情多藏在心里,并未因为各种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而使彼此间交流更加深入。高校“孝”文化培育更应着眼于当代中国独生子女与父母的亲情关系,从而形成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新型孝道文化。
三、充分发挥“孝”德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
心理学研究成果认为,人类天性本身愿意模仿,而榜样即模仿对象,则是模仿行为发生的关键。雷锋、焦裕禄等都曾是影响新中国几代人的榜样,这些榜样曾给人带来的精神洗礼和灵魂净化让我们感叹榜样巨大的示范作用。当然,今天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道德模范的影响力会受到诸多限制,但人心中对善德的渴望依然存在,依然会因为老未得赡养、幼未得抚育而伤心难过,也会因为素不相识的微小帮助而感动,因为良知一直存在,只是有时被物欲淹没,唤醒良知,这既是“孝”德等各种典型模范能够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的基础,也是德性之人的义务和使命。要使“孝”德模范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榜样示范作用,需要我们做更多合乎时代要求和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推进孝道文化的努力。
(一)让地方上具有影响力的“孝”道典型到学校现身说法
近年来,就全国范围来看,国家评选和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模范,如“感动中国人物”“道德模范”“最美教师”等,而从地方角度看,各地也推出了一些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典型人物,他们都是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自身带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些典型和榜样不应仅限于电视和各种媒体上,还应该走进大学校园里,让大学生有机会切身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如鞍山孝星宋学丽义务照顾邻居老人17年,形成了堪比父母子女的亲情;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鞍山还建立了孝道“红黑榜”,将孝敬父母好儿女列入红榜,公开曝光虐待老人、不赡养老人的反面典型;开展邻里守望、跟着郭明义学雷锋等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并通过寻找“最美家庭”、孝老爱老好家庭评选等活动,倡导“爱国传家、敬业兴家、诚信立家、孝善安家、勤俭持家、廉洁守家、平安保家”,传播家庭文明正能量,形成以良好家风带党风促政风正民风,以家庭文明建设促进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新风尚。这些地方人文环境中的孝善文明风气对当地高校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发现和培育大学生身边的“孝”星榜样
大学生们朝夕相处,不仅彼此熟悉各自的脾气秉性,也有机会互相了解各自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让大学生们自己选拔发现他们周围的“孝”星,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孝道教育的一部分,他们会用自己心中“孝”的标准去筛选他们所认为的孝道之人。学生自己选出的“孝”星更易于接近和接受。网易新闻曾报道过的重庆师范大学学生刘刚,三年间勤勉求学,坦荡拾荒,靠“经营”垃圾赚足大学所有费用,在自己赚取学费的同时,还为更多贫困生提供了勤工助学机会,以自强则刚的人生观改变了周围同学的生活态度,同学们从最初的孤立嘲笑不理解到被他的精神和行为感动,理解尊重并帮他收集废品,他不仅是同学们心目中自立自强的典范,也是一个孝道榜样。因为有这样一个榜样,室友走出了迷恋已久的网络世界,丢掉了跟随多年的打火机,爱上了曾经放弃过的学业。榜样的力量可以健全学生人格,而同辈群体中充满正能量的榜样会使这个过程更水到渠成般不留痕迹。教育管理者的职责便是发现、引导、培育、鼓励和支持这些“孝”星典范的健康成长。如现在一些学校开设的国学课程,开展的“孝感天下”优秀学子评选活动,使学生在参与评选过程中更深入领悟孝道真谛,以受表彰的优秀学生为榜样,引领学生践行孝道,不仅常怀感恩之心,更行报恩之举。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项重要文化建设任务,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高校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方面更应责无旁贷,不是应不应、该不该,而是如何为之的问题。高校需自上而下戮力同心,课堂教学与实践环节并重,寻求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学生学习生活的契合点和突破口,并持之以恒,方能有所建树。
[1] 周桂钿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N].光明日报,2017-01-09.
[2] 王丽英.孝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教育[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85-188.
[3] 丁文林,郭英俊.论孔子“孝道”观念与当代大学生的感恩教育[J].社科纵横,2008(6):33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