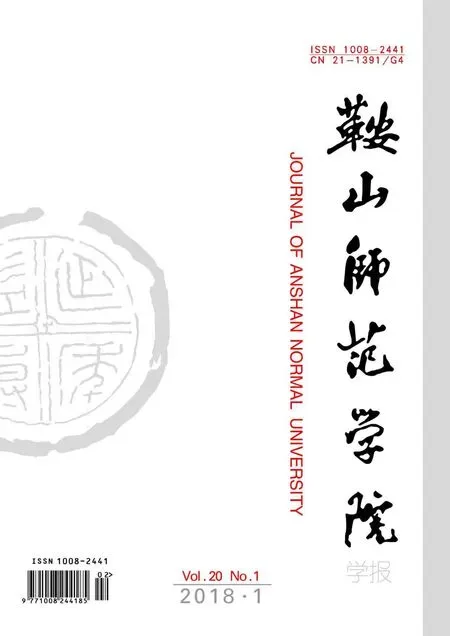《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根源及意义
刘会杰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海城学院,辽宁 海城 114200)
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珍品,主人公祥子的幻灭人生正是当时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缩影和真实写照。
一、曲折的人生境遇
我们不妨做一个倒置性的阅读,文末一段: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老舍先生用极简而又极深刻的语言将祥子前后鲜明的人生境遇进行对照浓缩在一个大长句子中,是同情,是呐喊,是哀叹,也是控诉。
小说的内容主线围绕着祥子三起三落的 “买车”“失车”经历展开,期间的欣喜、幸福、苦痛、屈辱以及与此相伴的“成长”,都是这个吃人的社会早就设定好的情节,然而却是20岁的祥子所不能也不敢预见的。
回到文初,20世纪20年代,20来岁的祥子,从破产的乡下来到北京,有的是让自己底气十足的身量与力气,“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他有自己的志向,“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1]
高频出现的“必”字,是犹如大树一样的祥子对人生的自信,他的天真得有些傻气的脑袋所勾画的因果关系是,不怕累、肯吃苦所能达到的终极目的,就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纯朴而又简单的愿望正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热爱生活的美好品质。
三年的节衣缩食,祥子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看到车的那天,书中这样形容祥子的喜悦之情:“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越看越可爱;买车的日子,算作他的生日……”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们也为祥子的努力成果感到心慰。然而幸福是很短暂的,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哪有劳动人民喘息的空间?时过不久,祥子连人带车都给乱兵捉了去,人勉强逃出来,车没了!独立自主的理想第一次被无情浇灭了!祥子心痛不已,重整旗鼓到人和车厂赁车拉,再次拼命地努力挣钱,为再次买车付出辛劳。及至来到曹先生家干包月,不料赚的钱又被孙侦探给洗劫一空,距离买车又远了一步,祥子再一次陷入悲痛之中。
无处可去的祥子,只好重回刘四爷的车厂,由此掉进了虎妞的婚姻骗局,被迫娶了强势大龄的车厂老板女儿虎妞,并由虎妞出钱买了二强子折价的车。此刻祥子尚有尊严的底线,他不肯去向虎妞的爸爸伏地告饶,他对比自己生活更惨的小福子一家还有着力不从心的同情,这与当年包子铺给车夫老马爷孙俩买包子的义举是一脉相承的。
虎妞难产而死,一尸两命,祥子只能变卖车辆办了丧事。人没了,钱没了,车没了,祥子用自己的力气去过生活的勇气也没了。
虎妞难产离世后,祥子已经被现实摧残得麻木不堪的头脑中尚且闪现有两个光束,他的救命稻草,他希冀着获得救赎的出口,一个是去曹先生那打工,一个是和小福子一起生活。如果说曹先生对祥子来说是生存的希望,那么小福子则是情感的皈依了,祥子穷尽一生唯一的一次爱的闪光,就是他和小福子之间底层挣扎中生出来的相惜相怜,他们也善良也要强,然而却抵不过生活的重压,小福子最后的惨死,祥子不曾开出的爱情之花彻底枯萎了。他精神上已是行尸走肉,彻底颓废了,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市井无赖,浑浑噩噩,奸诈欺骗,他也成了“白房子”的常客,他变成了自己曾经最厌弃的样子。
二、多重的悲剧根源
(一)黑暗腐朽的社会悲剧
从社会背景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转型时期,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没有基本的生存秩序,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喘息没有基本的保障。从祥子的人生经历看:军阀的乱兵,反动政府的所谓侦探,地主阶级车行老板的巧取豪夺,多重压迫让祥子代表的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出路,城市底层贫苦百姓每日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中。当代诗人北岛的《回答》,开篇中振聋发聩的呐喊可以看成是对一切黑暗、混乱的社会现状的控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祥子所处的腐朽、堕落的社会,对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来说,不仅仅是生存层面的考验,更深层次的摧残应该表现在精神层面[2]。祥子要生活的体面,小福子要做人的善良,曹先生要思想的进步……然而这些努力和坚持统统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而反观那些卑鄙无耻如孙侦探之流,因为泯灭了人性,反而活得自在逍遥。
祥子的悲剧并不是特例,笼罩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生存法则才是导致他,确切地说,千千万万像他一样有着原初的美好追求的人,必然走向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
(二)个人主义的性格悲剧
金钱至上的观念和驯顺、木讷的性格是祥子最终走向悲剧的主观因素。1950年开明版的《老舍选集》序言中,老舍先生对祥子的形象做了明确的解读:“我管他叫作‘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这里的“造反”应该是有明确指向的——祥子穷尽一生不过是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体体面面做一个靠力气吃饭的黄包车夫,这是典型的小农个人奋斗的理想[3]。
正如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客观存在必然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与社会发生关系。祥子虽然生活在城市,仍然植根于小农生产关系主导之下,他的身上深深打下农民思想意识的烙印。他对其他年老车夫的苟延度日感到不屑,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其实正是自己的归途,几个包子解决了老马祖孙二人一时的饥饿,却不能改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底层民众受苦受难的事实。
祥子屈从压力,也因为了金钱的诱惑,娶了虎妞,这是他懦弱、认命的性格缺陷,后来的自甘堕落,是传统美德的沦落值得人们痛惜,同时也深感无知、愚昧的民众在病态社会下的压抑、麻木的劣根性。
祥子想要的安稳以及这安稳的破灭,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悲剧。在他狭隘的思想观念里还意识不到整个社会的黑暗,反动的腐朽统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不是个人付出努力就能改变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祥子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与整个社会力量相抗衡,奢望通过自身的绵薄之力去扭转大方向的局势无异于螳臂挡车,个人生活的贫富也都只是暂时的表象,终究会异路同归,走向没落。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彻底打破枷锁,推翻腐朽的统治,才有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三)畸形婚姻的精神悲剧
祥子在最初谋划他的婚姻时,无不像憧憬拉车一样的,处处显出一个乡下人的规矩和淳朴,“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 文中第一次提及“白房子”,祥子的厌弃之感正是出于他想要一门干净、美好的婚姻的追求,“因为他一旦要娶,就必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所以自己也得像那么回事。”祥子洁身自好,对婚姻生活也有美好的憧憬,希望找个踏实肯干的、勤劳正派的姑娘一起奋斗,这与他后来堕落而频繁出入白房子,并染上脏病,肆无忌惮地与其他人议论宣扬,完全丧失廉耻,成为自己当初所不耻的人形成强烈的对比。
祥子对虎妞毫无爱意,可还是在她的诱骗下与之成了婚,祥子的头脑中没有什么文学的语言,然而却也用他的婚礼诠释了“乐景写哀”的文学笔法。结婚当天热热闹闹、吹吹打打,祥子像是个提线木偶一样,几乎不敢看那个擦胭脂抹粉的虎姑娘,“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像女的,又像男的;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细细地收拾他……[4]”
虎妞与祥子生活愿望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一个小资产者的强势大龄女与懦弱无产者男的强制结合,婚姻基础基于金钱利益关系之上,本身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注定了祥子婚后生活套上沉闷的精神枷锁,这样的畸形婚姻彻底封死了祥子个人感情的出口,就连虎妞出钱给他盘的那辆车,也没能像祥子得到的第一辆车一样,让他欢欣鼓舞、健步如飞,相反地,这辆车更像是他逃避现实婚姻的一个替代品。
对照一开始,祥子与生俱来的善意使得他有意识地要做一个“体面”的车夫,讲原则,不跟年老体衰的人抢活计;要面子,个人和车子都收拾得利索干净;计仁义,寒冷冬夜里买给老马祖孙二人的包子,都出自祥子敦厚、善良的本能,然而这些曾经熠熠生辉的品质与堕落后连骗带摸厚着脸皮占尽人家便宜的祥子恰成对照,给读者带来一种无法逃避的沉重感和无奈感。
人生存于世间,必然要有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寄托,生活才有希望,人们才能在繁杂的人世有付诸努力的动力,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能有所慰藉,也可勉强生存,祥子三次失车,身无分文,小福子自杀身亡,多重打击之下,祥子对人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抬头看见的是灰色的天空和黑色的太阳,信仰遭遇极端的尴尬,祥子的穷途没路既是身不由已,也是无可避免。
三、深远的现实意义
祥子的悲剧人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破产农民在吃人制度下喘息无望走向沉沦的过程,祥子的不幸既有社会因素,也有他本人性格、价值观等内在原因。我们在对他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旧社会最底层劳动者无奈的悲惨命运,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的结局。
祥子这一人物形象代表的是底层的劳动人民,要自食其力、勤劳创造的朴素愿望,被无情的现实碾得粉碎。悲剧总是提醒人们正视生活中的残酷和艰辛,也给人们提出一个严肃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即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出路的问题。理想和现实是共存的矛盾体,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是现实的产物,它不会为某个人理想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不幸而扭转,人们为了理想不断奋斗,最后可能事与愿违,比如祥子。社会腐朽,即使人再有韧性和执拗的毅力,与现实抗争,仍逃不掉毁灭的命运。只有贫苦大众团结起来,为了自由和理想,武力推翻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民才能看到光明,挣脱灾难深重的命运,获得解放。
[1] 王莹.浅谈《骆驼祥子》中的“北京味儿”的表现及意义[J].神州,2011(15):101-122.
[2] 黄立波.《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中叙述话语的翻译——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6):15-20.
[3] 严方,孔希凡.老舍《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内涵[J].文学教育(上),2011(11):15-33.
[4] 陈文婷.目的论视角下的《骆驼祥子》日译本研究[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