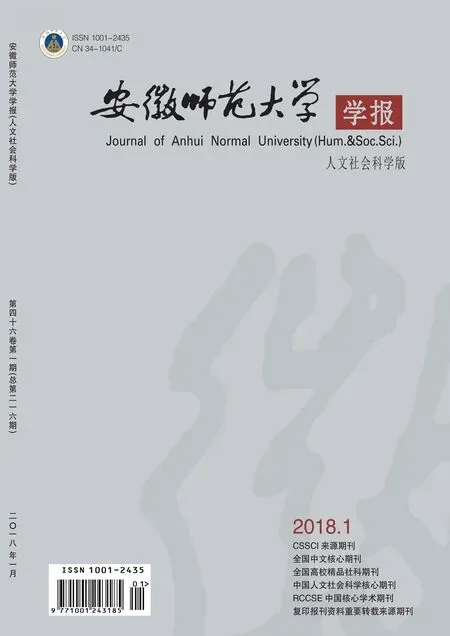1849-1940年间中国和日本移民秘鲁比较研究*
何美兰
(河北师范大学 秘鲁研究中心,石家庄 050024)
【社会史研究】
1849-1940年间中国和日本移民秘鲁比较研究*
何美兰
(河北师范大学 秘鲁研究中心,石家庄 050024)
中国;日本;移民;秘鲁
从19世纪中叶起,秘鲁近百年的亚洲移民浪潮中,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占据重要的地位。中日两国移民秘鲁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主要表现在两国移民的个人目的、生存方式及两者对秘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等方面;差别则主要表现在两国移民的时代背景、政府的移民态度和政策及两国移民与秘鲁社会的融合等方面。
1849年,第一批中国“契约工”(苦力)*根据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年)考证,“苦力”一词是印度某个部落的语言,最初指在收获季节做农活的人,后来泛指农田里的临时工。1835年起,指签约的劳工。19世纪用于签约到外国做工的中国人。抵达秘鲁,揭开了中国向秘鲁移民的序幕。中国苦力从澳门出发,在太平洋上航行数月,许多人不堪忍受,跳海自杀,也有一些中国苦力选择逃亡。由中国“契约工”逃走引发的“玛利亚·露丝号”事件间接促使日本和秘鲁建立了外交联系,*1868年,载有中国苦力的秘鲁船只——玛利亚露丝号,遇风暴暂停日本横滨港避难。其中一名苦力逃出,寻求日本当地政府的帮助,随后日本外务省介入调查,查实玛利亚露丝号是一艘运输奴隶船只,便将所有中国苦力释放回国。经过五年的斡旋,1872年,秘鲁派特使奥雷略·加西亚·加西亚(Aurelio Garcia y Garcia)同日本政府交涉。最终,俄国沙皇出面,解决了此事。这无疑为1899年两国建立官方的移民关系提供了契机。
20世纪前后百年左右的时间构成了秘鲁移民史上的两个重要时段,即中国移民到秘鲁的高峰期(1849-1900年)和日本移民到秘鲁的高峰期(1900-1940年)。追溯和探索两国移民在秘鲁的历史足迹,有助于解读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在当代秘鲁的状况及中秘、日秘关系。国内学术界关于秘鲁移民史上的这两个阶段有分别的研究,*国内关于秘鲁的中国移民研究,主要有张华贞:《斗争与融合:契约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赵宇,廖大伟:《李鸿章与秘鲁华工案》,《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3期;李中省,段海凤:《伍廷芳与秘鲁排斥华工的交涉》,《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沈燕清:《秘鲁华工交涉中的李鸿章》,《八桂侨刊》2006年第2期;王佩琏:《为秘鲁经济重获生机的人们——华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卜君哲:《秘鲁华人社团的形成与发展》,《八桂侨刊》2003年第1期;等等。关于秘鲁的日本移民研究,主要有胡新苏、韩涛:《二战前秘鲁的日本移民研究》,《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对中日移民问题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读他致国会的两份年度咨文》,《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9期;等等。但对两者的比较研究尚待开启和推进。*目前,已有国内学者尝试秘鲁的中、日移民对比研究,如刘兆华、祝曙光:《二战前拉美日裔同化与融合的制约因素——以秘鲁和巴西为例》,《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
一、不同的移民背景和相近的移民目的
中、日移民大规模到达秘鲁的时间前后相差近半个世纪。因此,中日两国往秘鲁移民的时代背景显然有不同。
17、18世纪的清朝实行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大好神州,变为鬼蜮之世界”。[1]815在这种山河破碎的情况下,人们被迫寻求其他维持生计的途径。而在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在厦门、澳门和香港等沿海通商口岸开设了贩卖人口的商行,为输出苦力提供了直接的交易场所。例如,英国投机商人康诺利,为了便于替秘鲁经营苦力贸易,积极活动并出任秘鲁领事。[2]52-53就这样,走投无路的中国贫民抱着寻找一份糊口差事的希望,怀着到“金山国”淘金的梦想,*加利福尼亚在中国被称为“金山”。见瓦特·斯图尔特著,张铠、沈桓译:《秘鲁华工史》(1849-1874年),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踏上了去往他们一无所知的太平洋彼岸的旅途。*秘鲁学者费尔南多·徳特拉塞格涅斯(Fernando de Trazegnies Granda)的En el Pais de las Colinas de Arena的主人公就是一名来自广州的小菜贩,他先是到澳门赌场碰运气,赌光后,觉得没脸见家人,便加入了去秘鲁的苦力队伍。中文本由竹碧、腊梅翻译,《沙国之梦:契约华工在秘鲁的命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与清朝的封建统治不同,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运动。为了创造“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金,政府实行地税改革。1871年,明治政府废除旧法,允许土地买卖,全国土地重新丈量、划价。这使得农民解脱了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同时,对农民征收新的现金土地税,这使得贫困农民卷入货币经济当中,大量小农失去土地,生存维艰。在传统小农结构冲击下,约一百万农民破产。[3]79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口持续增长,从德川幕府时的3000万增加到1888年的3800万。1920年,增至5600万。[3]78人口的增长加剧了人与地的矛盾,迫使明治政府向海外输出劳工。1899年,日本往秘鲁输出了第一批790名移民,他们以从事耕田的农民为主,来自日本相对贫穷的新潟县(Niigata)、山口县(Yamaguchi)、广岛县(Hiroshima)等。[4]443这些农民根本不知道秘鲁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只是耳闻,秘鲁在地球的另一端,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没有瘟疫,饮食习俗与日本相近,遍地黄金。[3]77于是,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要赚钱的理想地方。
秘鲁于1821年摆脱了西班牙近300年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后的国家百废待兴,但劳动力短缺是阻碍经济恢复的关键问题。造成秘鲁劳力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19世纪上半期世界范围内黑奴贸易禁令出台,间接导致秘鲁国内黑奴数量骤减。秘鲁1854年废除奴隶制。据统计,1821年,秘鲁国内有大约41 228黑奴人口,到了1854年,只剩下约17 000人。第二,1854-1885年,秘鲁废除印第安人贡赋税收,印第安人不用再以货币来缴纳贡赋,他们从此转向自给自足的经济,这也加剧了沿海地区种植园劳动力的缺失。第三,秘鲁政局动荡,战争频繁,对欧洲移民毫无吸引力。1826年后的40年里,秘鲁经历了34位“短命总统”,整个19世纪秘鲁战事不断,与周边所有国家都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战争和摩擦。所有这些使得秘鲁靠吸引欧洲移民来提升本民族质量的计划流产。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移民成为秘鲁解决劳力缺失的最佳选择。
从移民个人的目的来看,中国和日本移民两者基本相同,他们都是想去秘鲁挣钱,然后带钱返乡;但两国政府的移民态度和行动则大相径庭。中国移民总体上是缺少政府主导的民间移民,究其根本,是由其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所决定的。封建政府软弱无能,对移民百姓不闻不问,少数商人则从中牟利。而日本政府在对外移民上则表现得积极和主动,顺应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思想潮流,政府移民占主导地位。日本政府把向外移民作为一种手段,缓解国内人口,积累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甚至有意通过日本种族的移出来扩张殖民,改善和提高日本民族的素质。
二、被动和主动的中日移民政策
清朝初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摧毁后,清政府在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出海务工的合法性。但向秘鲁的劳工输出一直采取的是非法“苦力”贸易,从1849年开始的25年里,中国劳工几乎全部是被强迫或欺骗去秘鲁的。他们名曰“契约工”,实为一种变相奴隶。运气较好的被分配到种植园做工,或派去修铁路;运气差的则被送到鸟粪岛上,开采鸟粪。19世纪70年代起,遭受百般折磨和虐待的中国劳工掀起罢工、逃离等反抗活动,[5]413-414也开始集体向清政府联名申诉,请求政府援助。中国国内的公众声援他们反对秘鲁种植园主欺压的斗争,从而促使清政府萌生了承担保护国民的责任意识。[6]3311872年,基本得到解决的“玛利亚·露丝号”事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秘鲁政府派出海军上校葛尔西耶来华同李鸿章交涉。经过两年多的各方交涉,中秘于1874年建立外交关系,双方签署了包含废除“苦力贸易”协定的《中秘通商航海条约》,其中一条就是中国有权派调查委员会遣返那些愿意回国的劳工。1887年,清政府派遣调查委员会前往秘鲁沿海种植园调查中国移民在秘鲁工作和生活环境,涉及调查移民是否遭受殴打、庄园主有无欠薪或者其他违背契约的情况等。[5]39320世纪初,随着秘鲁排华运动的不断发生,清政府于1909年同秘鲁政府签署了一份《中秘条约证明书》,此条约既重新肯定了《中秘通商航海条约》,又较为圆满地解决了秘鲁排斥华工的问题。
秘鲁国会早在1839年就出台了专门吸引契约劳工移民的法规,规定凡是能够引进50名以上的10岁到40岁的外国移民的商人将获得每名移民30比索的政府补贴。1849年又出台新的移民法,因为该移民法是专门针对中国劳工的移民法,故又称作“中国移民法”。[5]390从1849年,中国“契约工”(苦力)开始大批被输送到秘鲁。到1874年,秘鲁输入了约10万名中国工人。*历史学家对这一数字的记录不一,瓦特·斯图尔特认为是9万, 见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olie in Peru, 1849-1874. 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 1970, p.74. 马里奥·巴斯克斯认为是15万,见Immigration and mestizaje in nineteenth-century Peru, in Magnus Mörner (ed.).Race and Class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Columbia U. Press 1970, p.82.学者们比较普遍接受的是10万。在秘鲁和智利的太平洋战争(1879-1883)期间,中国劳工纷纷加入智利军队,引起秘鲁人广泛的反华情绪和行动,促使秘鲁转而寻求新的途径来增加国内短缺的劳动力,从而为日本劳工移民前来秘鲁提供了契机。
明治维新开始后的日本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需求,积极推动海外移民事业。日本最初的首选移民输出地区是关岛和夏威夷群岛,其次是加利福尼亚地区以及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玛利亚露丝号事件后,日本产生了秘鲁移民的意向。1893-1894年间,日本政府派移民代表考察秘鲁和巴西两国之间的亚马逊地区。[7]1520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限制日本移民入境。*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亚洲移民的法令。日本加速转向拉丁美洲作为新的移民输出地。1899年,日本正式与秘鲁建立了官方移民关系。明治政府设立负责移民事务的机构。比如,1921年内务部下设社会事务局,1927年设移民中心,1929年设侨民事务部等。政府也直接或间接赞助移民公司,1868-1942年间,约776 000日本人移居国外,其中移民北美洲的占48.2%,移民南美洲的占31.6%。[3]78这些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是受到政府或者与政府有关系的私人公司赞助的。该时段的日本移民政策表现出“移民”和“殖民”的混淆,特别是内务省在1929年改为拓务省后,日本的海外扩张政策更加明显,因为其主要职能是管辖殖民地事务。[23]94
1854年废除黑奴贸易和1874年废除非法的中国苦力贸易严重影响了秘鲁的劳动力来源。秘鲁虽曾试图吸引欧洲移民,但欧洲移民更倾向于移民阿根廷、智利和巴西。所以,秘鲁不得不寻求新的移民出路。加之中国劳工在太平洋战争中亲智利的表现,令秘鲁人心生芥蒂,这更增加了接受日本移民劳工的机率。秘鲁政府在1893年通过一项专门针对欧洲移民和日本移民从事农业殖民地的法案,秘鲁总统还特别颁发允许日本移民以契约工形式入境的法令。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同巴西和俄国外交联系的加强,日本移民开始大规模定居巴西和俄国远东地区,向秘鲁的移民进入衰退期。同时,秘鲁政府加大了对日本移民的管控。1929年,秘鲁当局将所有的日本移民纳入国家的管辖范围,并特设秘鲁移民管委会。1936年,秘鲁政府颁布限制外国移民和外国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法律,极大地限制了日本对秘鲁的移民。
由上可见,清政府的秘鲁移民政策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冷漠期,封建天朝观念主导的清政府根本不鼓励臣民出海谋生,更谈不上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苦力贸易”。只是在秘鲁中国劳工的恳求下,才产生了了解移民劳工在外生活的想法。及至1874年的“苦力贸易”废止,清政府才在某种程度上担负起了国家保护其子民的职责。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也分为民间和官方移民两个时段,但即使在由私人公司操作的民间移民阶段,政府已经在发挥其指导作用。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第二阶段,向秘鲁移民成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日本政府对其秘鲁移民一直都在实行保护措施。[8]16、[9]70在这点上,与清政府的表现差别巨大。从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政府放松了对秘鲁日本移民的保护,及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秘日本移民陷入被其它民族敌视之境地。
三、中日移民在压迫下的生存
秘鲁的中国移民高潮期大致分为强迫“契约劳工”(1849-1874)和自由契约劳工(1875-1900)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移民几乎全是被强掳或欺骗而去秘鲁的,他们除了赚钱回国,没有别的想法。到了第二个阶段,中国移民产生了在秘鲁生活下去的想法。
在第一个阶段,几乎清一色的成年男性被送往秘鲁沿海甘蔗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做工,小部分则被分配去开采鸟粪或修建铁路。通常情况下,种植园主与苦力签4年或8年的劳工契约,他们每周只得1比索工钱,每日有1磅稻米和少许肉食用。[10]253容闳这样概述此阶段的移民性质:“表面上虽约定年限,实则此限乃永无满期。盖每届年限将满时,主人必强迫其重新签约,直欲令华工终身为其奴隶而后已。”[11]97张荫桓《三州日记》也记载秘鲁种植园主为吸引华工,“先给川资,立限造工四年扣还,有此机柕,则华工或先期后借,或期满而他适,均难逃该寮掌握,即非卖身,仍多轇轕。”[12]597
在自由契约阶段,多数移民工人是从之前的苦力转来的,大约30%-40%的苦力续约,成为自由劳工,他们中的一部分继续留在种植园做工。[13]33另一部分苦力合同到期的时候,迁往沿海和山区的城市与村庄,甚至雨林地区,在那里以经商或开饭馆为生。例如,位于秘鲁北部沿海的切彭(Chepen)曾经有数千中国人耕种,他们中的很多人留下来,开食品杂货店、酒窖和商铺。这些商贩经常会前往位于山区的卡哈马卡市贩卖和购买货物,从而形成了一个商业网络。[14]195-196
早期日本向秘鲁的移民也分为两个阶段,即“契约移民”阶段(1899-1923)和“邀请移民”或“资助移民”阶段(1923-1936)。[15]19第一个阶段的移民大多被分配到海边的甘蔗种植园或橡胶农场工作。种植园主与他们签订的契约一般为期4年,每月收入约25日元,除去食物等日常开销,4年之后可以赚取大约960日元,再除去回国路费100日元,合同期满时,每个移民可净赚860日元。[4]443-444不过,这只是按照合同条文计算得出的理想结果。*这是按照1900年的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计算的,1日元折合52美分。实际上,种植园主往往通过克扣、欠发工资,高价出售生活必需品等手段,把日本移民束缚在种植园里。日本移民做工的种植园的环境并不比中国移民的好。以潘帕斯(Pampas)地区的一个种植园为例,工人每天的食物只有1小片腌鱼和3碗大米粥,衣物少得可怜,这样的凄惨生活他们一过就是4年到5年,许多人患上了败血症。[4]447
在“契约移民”阶段,许多日本移民没有挣到所期望的那么多钱。加之国际蔗糖价格的降低,迫使他们离开甘蔗种植园,另谋生路。大部分人携带少量资金去利马和卡亚俄等大城市开始做小生意,只需少量启动资金的理发店成为日本移民在大城市的第一个营生。1904年,日本人在利马开了第一家理发店。10年后,利马的日本人理发店增至80家。他们渐渐地扩展到杂货店、饭馆、服装店和咖啡店等领域。到1930年,大约45%的日本移民有自己的小本生意,除了食品、理发等传统行业,还有机械、手表、维修等新行业。[3]85另外,20世纪20年代起世界棉花价格的突然飙涨,使日本移民看到商机,开始大面积种植。以香卡河谷(la valle de Chancay)为例,1940年,这里的日本移民仅占当地总人口的14%,其中3/4从事棉花种植,而他们的产量却占整个河谷棉花产量的一半以上。[7]27
中日移民在各自的移民高潮期的第一个阶段均在秘鲁种植园做工,但他们的实际身份有所不同;他们同样受种植园主的虐待、剥削和压迫,也都有过反抗行为,但中国劳工多是被动杀害,日本移民更多通过罢工形式来反抗。[16]62到了第二个阶段,两国移民的多数开始经营自己的小生意,但中国移民的生意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与原先的种植园主的关系,而日本移民更多地远离种植园,到利马、卡亚俄等城市定居,与本国生意上的联系更多些。总的说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移民在秘鲁城市里均以经营饭馆、理发店、杂货店、咖啡馆等小生意为生,他们被秘鲁人统称为“街角里的中国人”*此处的“中国人”泛指东方移民,主要指中日移民。。[3]86
四、中日移民与秘鲁社会融合上的差异
中国苦力在秘鲁经过20多年的种植园苦工经历后,没有挣到钱,反而背了一身债。因此,他们慢慢转变了返乡的想法,逐渐融入秘鲁主流社会文化。同时,从半奴隶的境遇,到获得名义上的稳定的移民身份,他们也萌发了保持自己祖国文化的想法。
中国移民带到秘鲁的第一个文化符号就是今天秘鲁街头熟悉的中餐馆chifa*“吃饭”的音译。这些小饭馆主要是以卖米饭开张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移民多来自以米饭为主食的广东、福建。。chifa(中国米饭)最早就是在这些小饭馆卖出的。根据官方数据,1869年利马有官方注册的中国饭馆有19家。[17]89随着chifa在利马各阶层中被广泛接受,它成为利马最普遍的餐馆,促进了秘鲁饮食文化的多元化。除了饮食外,中国移民的文化融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初期阶段的中国劳工移民改用秘鲁人名字,主要是他们的雇主,或他们的教父的名字。研究中国移民的著名秘鲁学者温贝托·罗德里格斯·帕斯托(Humberto Rodríguez Pastor)列举了1830年及之前出生的516名中国移民改用了秘鲁人的名字。比较常见的有何塞、胡安、马丁等,也有的保留了中国名字的一部分,比如,阿福·桑切斯。[17]107-1102.由于在“苦力移民”阶段来到秘鲁的都是20岁左右的男性劳动力,[18]453因此在缺少同族同乡女性的情况下,他们逐渐与当地女性同居或通婚。在19世纪80年代,有1万到4万索尔财产的中国小商人和秘鲁女性结合的情况在安第斯山区相当常见。[19]297罗德里格斯的上述研究中就提到一位1850年到秘鲁的中国苦力,先后与3名秘鲁女人结婚,共生育了13个孩子。[17]77-783.改信天主教。早期中国移民虽然不懂天主教教义内容,但是他们经常参加天主教圣礼。据卡涅特圣路易斯地区(San Luis de Caete)文件的记载,1840-1861年间,当地中国移民共有313名“成年人”参加了洗礼、婚姻和悼念死者的圣礼。1860-1940年间,在圣路易斯教堂做过洗礼和使用天主教葬礼的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分别有201人和106人。[20]414.随着秘鲁的中国移民的理念从“落叶归根”转变为“叶落生根”,他们意识到中国人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仍要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赢得话语权。于是,利马出现了中国移民组织的社团,其中成立于1886年的中华通惠总局一直存在至今。1869年,第一座中国戏院在利马建成,上演中国传统剧目。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也成了利马街头的中国文化符号,1856-1879年间利马有51家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21]187-189这些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发生摩擦,引起秘鲁人的不满和排华情绪,但最终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地人接受。
在契约移民阶段,日本移民的主要目标是赚钱后回国,因此,他们完全缺少与当地社会融合的意愿。同时,甘蔗种植园中大量伤亡的日本移民,使秘鲁官方认为日本移民不适应秘鲁的环境,应该被遣返回国;但早期日本移民与秘鲁普通民众阶层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15]75及至邀请移民阶段,日本移民主要移居中心城市,他们的生活显现出鲜明的日本族群文化特征。
第一,日本移民一般以社群而聚居,不与当地人混居和通婚。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日本移民致力于与秘鲁社会的混血人群体隔离是受其种族观指导的,即日本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与欧洲和美国的白人相等,但欧美人似乎不这样认为。[15]164其次,与几乎清一色的中国男性移民不同,日本移民中有少数女性。比如,1903年输出秘鲁的1 070名移民中就有108名女性。在20世纪20年代中到30年代中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移民女性人数大大增加,主要是通过发送本国女子的照片而达成的“照片婚约”。*照片婚约主要指的是20世纪早期在夏威夷、美国、加拿大和秘鲁等地的日本移民,通过本国媒人所寄来的照片,确定所要结婚的女性。然后,女性以移民的身份前往男性移民国所在地结婚。见Alice Yun Chai. Women's History in Public: “Picture Brides”of Hawaii,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 16, No. 1/2, 1988, pp.51-62.据统计,1939年在秘鲁的外国移民群体中,同族通婚的数量超过异族通婚的族群只有日本移民。[3]90
第二,日本移民的暂居情节不利于他们融入秘鲁社会。他们通过族群居住形式,来降低生存成本;他们把从秘鲁做小生意积累的资金寄回日本,来促进母国经济的发展,而不像欧洲移民那样在秘鲁投资,开矿山和建工厂。日本人的商铺里一般不雇佣当地人,而用自己的家人、亲属或同乡做工人。因此,秘鲁地方工会通常把日本企业主描绘成不关心当地人死活的万恶的资本家。[15]136
第三,为了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传承日本文化,日本移民开办日语学校,注重移民子女的日语教育,日语学校中的学生的日语水平明显高于西班牙语。学生每天都会宣誓效忠天皇,接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庆祝日本的民族节日。日本移民保持效忠天皇,绝不改信天主教。[3]89一些移民家长还把子女送回日本接受本土教育。
第四,日本移民建立各种行会和社团,凝结本族力量。1907年成立的日本理发师协会是日本移民在秘鲁的第一个行会。到20年代,各种小规模的协会遍及秘鲁。这些协会帮助建立日本人自己的学校,统一管理小商业企业,给移民提供贷款;同时,他们在日本移民中培养一种社群感,推动相互间的社会交往。行业协会的出现带动了日文报刊的出版。1913年,秘鲁的日本移民发行了第一份重要的日语报纸《安第斯之子》(Andes Jiho)。这些日语报刊的读者只限于日本移民。到1940年,秘鲁的日本移民开始出版西班牙语报刊,便于那些日本移民的后裔阅读。移民协会的建立和报刊的发行增强了日本移民的种族意识,保证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8]18-19
由上可见,在与秘鲁社会的融合方面,中日移民有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中国移民的地理分布超过日本移民,日本移民集中在利马和卡亚俄两个大城市, 1930年,秘鲁的日本移民共2万人,一半居住在利马和卡亚俄。[22]76而中国移民除了定居大城市外,甚至还深入到亚马逊雨林地带。其次,中国移民比较积极主动地融入秘鲁社会,尤其表现在改用秘鲁人名字、改信天主教和与当地女性的通婚等方面。而日本移民却偏重于保持日本种族文化,他们不改信天主教,与同族结婚,教育子女学习日语和效忠天皇。再次,中国移民建立的社团以文化社团为主,为的是在当地人面前造声势,提高中国移民在秘鲁社会的地位,这说明他们已经把秘鲁当成了自己的国家。而日本移民建立的多是商业行会,致力于移民族群内的经济协作和帮助,专注发展日本移民自己的商业。最后,中国移民在秘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欢迎当地人参与其中;他们也学习西班牙语,与当地人交流。而日本移民注重学习日语,建立学校,发行报刊,主要是为了保持日本文化的独立性,没有让当地人参与进来的意识。
综合比较19世纪中叶以后近百年的中国和日本向秘鲁的移民历史,可以看出,中国、日本向秘鲁移民的过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国移民最初都是为谋生而去的秘鲁,他们在秘鲁的谋生方式有不少共同之处,也都对秘鲁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中日移民也各有其特别之处。早期日本移民秘鲁过程中,有活力的资本主义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积极采取了保护在秘日本移民的措施。相反,软弱保守的封建清政府是被迫处理在秘鲁的中国移民的事务的。中国移民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自身设法通过多种途径融入秘鲁社会。总的来说,中日两国移民在融入秘鲁社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只是日本移民的融入多一些官方性,而中国移民的融入多一些民间性。或许由于这点,在今天的秘鲁,日裔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比华裔突出,而华裔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渗入更普遍。
[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M]. 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
[2] 李春辉,杨生茂.美洲华人华侨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3] Ayumi Takenaka.The Japanese in Peru: History of Im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Racialization[J].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2004,31 (3): 77-98.
[4] Toraji Irie,William Himel.History of Japanese Migration to Peru, Part I [J].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51,31(3): 437-452.
[5] Michael J. Gonzales.Chinese Plantation Worker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Peru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1989,21(3): 385-424.
[6] V. G. Kiernan.A review on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by Watt Stewart[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53,68(267): 330-331.
[7] Isabelle Lausent-Herrera.Psado y Presente de la Comunidad Japonesa en el Peru [M]. Lima: IFEA, 1991.
[8] Cheyenne N. Haney. Dreams of a Far Away Land: Japanese Immigration to Peru 1899-1950 [D]. Birm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2001.
[9] Evan J. Fernandez. Forging the pacific: Peruvian-Japanese Diplomacy, Migration, and Empire, 1918-1930 [D].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16.
[10]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G].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容闳.西学东渐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2]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G].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 Humberto Rodríguez Pastor.Hijos del celeste Imperio en el Perú (1850-1900):Migración, agricultura, mentalidad y explotación[M]. Lima: Instituto de Apoyo Agrario, 1989.
[14] Richard Chuhue, Li Jing Na,Antonio Coello. La inmigración China al Perú. Arqueología, Historia y Sociedad [M]//Milagros Lock Reyna.De la tiendita al supermercado: los comerciantes chinos en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Lima: Universidad Ricardo Palma, 2012.
[15] Stephanie Carol Moore. The Japanese in Multiracial Peru, 1899-1942 [D].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9.
[16] Peter Blanchard.Asian Immigrants in Peru, 1899-1923 [J].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1979,4 (7):60-75.
[17] Humberto Rodríguez Pastor.El Inicio de la trata amarilla al Peru,sus actores[M]// Richard Chuhue, Li Jing Na y Antonio Coello, La inmigración China al Perú. Arqueología, Historia y Sociedad . Lima: Universidad Ricardo Palma, 2012.
[18] Humberto Rodríguez Pastor.Transcendencia de los inmigrants chinos en la historia,la sociedad Peruana[M]// Richard Chuhue, Li Jing Na y Antonio Coello, La inmigración China al Perú. Arqueología, Historia y Sociedad Lima: Universidad Ricardo Palma, 2012.
[19] Isabelle Lausent-Herrera.Mujeres Olvidadas: esposas, concubinas e hijas de los inmigrantes chinos en el Peru republican [M]// Scarlett Ophelan, Margarita Zegarra (eds.), Mujeres, familia y Sociedad en a Historia de America Latina, siglos XVIII-XXILima: IFEA, PUCP, 2006.
[20] Rebeca Nely Carrasco Atachao.mecanismo de inserción de los inmigrantes chinos en San Luis de Caete[M]// Richard Chuhue, Li Jing Na y Antonio Coello.La inmigración China al Perú. Arqueología, Historia y Sociedad, Lima: Universidad Ricardo Palma, 2012.
[21] Antonio Coello Rodríguez.Medicos y boticarios chinos en la Lima del XIX[M]//Richard Chuhue, Li Jing Na,Antonio Coello. La inmigración China al Perú. Arqueología, Historia y Sociedad . Lima: Universidad Ricardo Palma, 2012.
[22] Toraji Irie,William Himel.History of Japanese Migration to Peru, Part III[J].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52,32 (1):73-82.
[23] 吴占军. 日本学术界近代移民政策研究综述[J].日本研究,2016(2):87-96.
ComparativeStudyonChineseandJapaneseImmigrationtoPeruduring1849-1940
HE Mei-lan
(PeruStudiesCenter,HebeiNormal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24,China)
China; Japan;immigration; Peru
Among immigrants from Asia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and Japanese immigrants to Peru play an important role. Chinese and Japanese immigration to Peru ha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n one hand, the immigrants from both countries show more or less the similar purposes, way of living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ibutions to Peru.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migration process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immigrants’ integration into Peruvian society.
10.14182/j.cnki.j.anu.2018.01.018
K778.0
A
1001-2435(2018)01-0148-07
2016-12-22;
2017-02-28
何美兰(1965-),女,广东兴宁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历史文化。
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