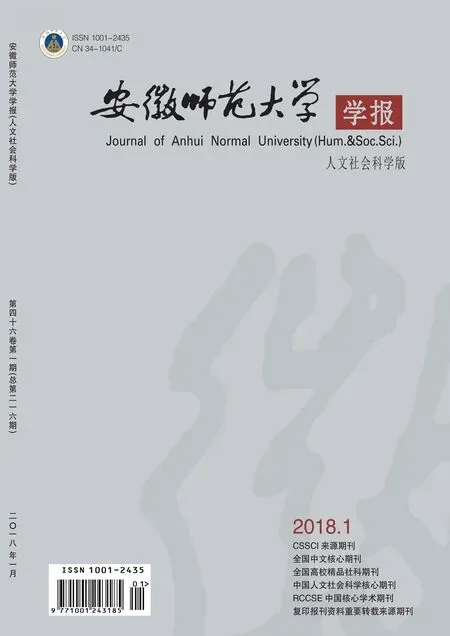说《论语》中的“义”*
臧宏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哲学研究】
说《论语》中的“义”*
臧宏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孔子;《论语》;义;天之四德
本文对《论语》中孔子说“义”的主要篇章,作了别开生面的解释。认为“义”是“天之德”,即天意、良知落入于人世间,或反过来说,在最最具体事物中包藏的天心或道心,就是“义”。换言之,“义”与“仁”“礼”“知(智)”,合称“天之四德”,皆为生命之本体,所不同的,是“义”较之其他三“德”,更富有“具体性”和“当下性”。也正是这个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义”在整个儒学中的基础地位。孔子所说的“义”与西方人所说的“正义”“公义”有本质区别,这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应走中国“义文化”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义文化”。
《论语》中有近二十处讲到“义”字,虽不算多,但其地位却很重要。因为它与“君子”“上”“知”“德”“学”等观念紧密相连,是《论语》的本体范畴,又是整个儒家学说的基础概念。《论语》中的“义”,也有出自孔子学生之口的,他们说的“义”,常与乃师有别。故这里只讲孔子说的“义”,而且只讲其中主要的。
一、“义”与“君子”
《里仁》篇第10章: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本章有多种解读,白子超先生将其归纳为两派,一曰“行事派”,二曰“待人派”。他说:“行事派主张:‘适,专主也……莫,不肯也。比,从也。’全句译作:‘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一定专主的,也没有一定反对的,只求合于义便从。’( 《论语新解》)有的更直白:‘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论语译注》)待人派主张:‘适、莫与比皆指用情言。适者,厚也,亲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全句译作:‘君子对于天下的人,没有厚,没有薄,唯对主张仁义的人亲近。’(《论语译说》)”[1]69
白子超先生认为:“两解都通,都在孔子语意之内。其实,后人理解此章,不应仅仅停留在字面义,还须懂得其深远意蕴。”[1]69他认为这深远意蕴就在于孔子的“中庸之道”,并认为,本章就是“中庸之道”的典型形式。他说:“‘无可无不可’与‘无适也,无莫也’完全是一个意思,自然不是某些肤浅之辈理解的‘墙头草,两边倒’或‘无所适从’,即不是被动的、消极的顺应,而是主动的、积极的选择,在可与不可、适与莫的对立两端之间寻找一种更超脱更合适的态度和方法。那便是中庸之道。上述两章文字的深刻思想意义,正在于此。”[1]69-70他说的“上述两章文字”,除本章外,还指《微子篇》第10章,在那里,孔子将逸民,即丢掉或放弃贵族地位而成为平民的人,如伯夷、叔齐等,分成三个层次后,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意思是讲,我和这些人不一样,我是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是针对隐遁者和身在庙堂的人而言的,讲的是如何处世的问题。逸民们,突出隐遁,强调出世;身在庙堂的人,强调入世,反对隐遁。而孔子则二者都不强调,只强调不立足于任何一端,超越任何一端,唯合于“义”便从。很显然,孔子的看法和做法是正确的。所以,笔者赞成白子超先生将本章和《微子篇》第10章看成是讲“中庸之道”的观点。
但是,笔者不赞成他依据庞朴先生的总结,认为“中庸之道”的形式有四种:A而B,A而不A',不A不B,亦A亦B。理由有三:第一,他割裂了中庸之道的整体。就本章而言,它的每句话,都是不可或缺的。你舍掉前后两句,单独地把中间的“无适也,无莫也”拿出来,当作中庸之道的一种形式,而且是第一的、基本的形式,这就把不可分割的中庸之道的整体,给以分割了。但他不同意这个排序,认为,用不A不B(AB代表事物对立的两端)作为中庸的典型的形式或第一种形式更为妥当,其理由主要是因为它是常用的比较普遍的句式,比如,除了“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外,孔子还引了《诗经· 商颂·长发》的诗句——“不竟不絿”来说明这个形式。竟者,争也; 絿者,求也。古人训解:“争竟者多骄,求人者多陷。竟求二义,相对成文。”孔子既不赞扬逞强又不赞扬示弱,既不骄狂又不谄媚,即赞成超越这两者的一种更高更适宜的境界,也就是“义”的境界。不只这样,他还认为,亦A亦B,也很重要,应从第四位提到第二位。这一点,笔者也赞成。
第二,但是他把A而B,A而不A',也当作中庸之道的基本形式,就是明显的不妥了。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这已不是不落两边,不偏不倚 ,而是以一方为主,即以A为主拿对立的B来弥补A之不足。或者以A为正确一方,只要A,不要B,但又防止正确一方过度膨胀发展,走向自己的反面,使“正”失去应有的位置。其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白先生退步了,在讲前两个公式时,他还强调“义之与比”这句话,而在讲后两个公式时,则把这句话忘掉了。他不知道 ,这不是小问题;庞朴的四个公式,若不与这句话联系起来,就不能叫做“中庸之道”。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白先生忽视了这些公式与“君子之于天下也”这句话的联系,说得准确一点,他不知“君子”在这整个一章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才能做到“无适也,无莫也”,才谈得上“义之与比”,即服从于“义”或靠近于“义”。因为按照孔子的意思,“君子”不是指一般的人,而是指与“道”合一的人,把握了生命本体,即“宇宙—生命”系统整体的人,认识了“天”之“四德”——“仁”“义”“礼”“智”的人,一句话,是认定生命本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即与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合一的“君子”,才能不为人世间的事物的矛盾两端所局限,实现由有分别的事物的知识,向无分别的生命本体的“般若智慧”的回归,才能真正理解“义之与比”的“义”的真实含义。何谓“义”?“义”,“宜”也。何谓“宜”?“宜”,乃“仁”即“天”。“天道”欲使人类“明明德”,“知天命”亦即“觉悟”所显示的“相”,也就是包含在最最具体事物中的“天意”,也就是“仁”在最最具体事物中的表现。由此可见,“义之与比”说的靠近“义”,就是靠近“天”、靠近“天道”,或者说的服从“义”,就是说的服从“天”、服从“天道”。
《论语·季氏篇》第10章: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本章既涉及“学”与“思”的关系,又涉及“君子”与“义”的关系。查阅历代注家对本章的解释,笔者发现,只有当代的心学家董子竹先生的观点最为新颖,又最具启迪意义。他在《论语真智慧》中说:“我以为这段语录,并不是要事事如孔子所提示的去做,关键是首先搞清‘见得思义’四个字。只要事事‘见得思义’,自是视明、听聪、色温、貌恭、言忠、事敬、疑问、忿难。‘见’之一字即上文视、听、色、貌……的总括;‘得’之一字便是视已明,听已聪,色已温……谓之‘得’。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在视、听、言、动之中一直‘思义’了。‘见得思义’,不是说‘得’了之后才思其‘义’。所以这段话应是‘欲得者必以思义为先,因思义为先,视必明、听必聪、色必温、貌必恭……’何谓‘义’?‘义’,‘宜’也。何谓‘宜’?即‘仁’欲令一切众生一切人类‘明明德’所显之相,纵使繁华似锦,冷寒若冰,料峭如刃,艰苦如死……无非一个‘义’字。识得么?识得了,视便是明,听便是聪,色也必然温……此乃天道,色何不温;此乃天意,貌何以不恭;此乃天命,言何不忠……”[2]384董子竹的解释,好就好在他抓住了这段语录中的关键——“见得思义”四字,并对其作了使人茅塞顿开的解释。他把“思义”说成是“见得”的原因,强调不是“得”了之后才思其“义”,而是“欲得者必以思义为先”。这就突出了“义”的重要地位。什么是“义”?多数注家都将“义”解释为人世间的道德规范,而董子竹则与众不同,他把“义”解释为“宜”,解释为包藏于最最具体事物中的“仁”“天道”“天意”“天命”。这样,“思义”,就与“求仁”“知天命” 没有什么差别了;“思义”也就成了“思学”了,因为孔子“志于学”,就是志于“知天命”。于此,我们便看到,“思”与“学”是密不可分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思”是“学”的工夫,是实现“学”的方法,它虽然包含着逻辑分析,但从总体上说,则不可以此为主旨,因为逻辑分析,对生命本体的把握即“知天命”“明明德”“致良知”,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就在本段语录中。不要忘记,这里讲的是“君子有九思”,而不是一般人有“九思”。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下学而上达”的人,就是“明明德”“知天命”与“道”合一的人,一句话,就是学“智慧”、学“觉悟”的人。这样的人,是决不会将“思”与“学”分割开来的。
二、“义”与“上”
《论语·子路篇》第4章:“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小人哉,樊须也”,是本章的关键词。要深入地理解本章,必须从这个关键词开始。
本章共分两段,此句之前的话(包括此句)为第一段,之后的话为第二段,而此句则是这两段的连接者,正是这个连接作用,显示了它在本章中的关键地位。第一,正是这句话,引导我们对本章的第一段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小人哉,樊须也!”这是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樊迟的话。这句话,用今天的汉语来说就是,“樊迟,真是个见识短浅的人啊!”孔子这样批评樊迟,根据就在“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和“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四句话中。前两句是樊迟向孔子请教种五谷和种菜的事,后两句是孔子对樊迟所问的回答,实际上,是一种拒绝。孔子拒绝回答樊迟所问,不是因为种庄稼、种菜有什么不好,也不是因为他看不起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只要看他在《子罕篇》中说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在《述而篇》中说的“富而可求,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的话,就会确信不疑。问题不在樊迟向孔子请教的问题的内容,而在于他压根儿就不应该向孔子提出这样的问题。身为孔子的学生,不知道乃师之教学目的,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儒式的高级管理人才,已是犯错,却又偏偏去问形而下的关于农耕的技术问题,不被批评为见识短浅的“小人”,那才怪哩!何谓“小人”?“小人”者,只求“下学”“下达”之人也。与“小人”相对应的是“君子”。必须明确,“小人”和“君子”之别,只与思维方式有关,而与社会地位、社会分工、道德品质都是无涉的。
第二,正是这句话,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孔子对樊迟的良苦用心。稍微细看一下本章的文字,便会发现这句话是在樊迟请学稼、请学种菜未得回答而退出之后说的,是对在场的其他学生说的。孔子这样做,不是像有的注家说的那样,是对樊迟的破口大骂和彻底的绝望。其实,这只是相对于第二段首句“上好礼”的“上”而言的,即相对于“君子上达”的“君子”而言的,亦即相对于在上位的君子式的领导者而言的。说樊迟是“小人”,是指他鼠目寸光,没有远大志向,并不是骂他,说他品德上有问题。也不是对其表示彻底的绝望,而是说他脑子过于迟钝,不理解对他说的“吾不如老农”和“吾不如老圃”的真实用心。孔子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不是培养种谷种菜的人,要种谷种菜,确实不是孔子的专长,所以,他说自己不如老农、老圃,这是实话实说,并没有错。他这样回答,是要樊迟换一个提问题的角度。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莫明其妙地退出了。这说明他没有理解乃师的真实意图。樊迟退出了,但是,孔子却没有放弃对樊迟的教育。他在樊迟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他的学生说:“小人哉,樊须也!”目的是让其他学生转告樊迟,他之所以拒绝回答其提的问题,是因为他把技术、知识看得比“明心”重,是只知“下达”的“小人”。“小人”与“君子”是可以转化的,只要“下学而上达”,就可以由“小人”变为“君子”。孔子是很希望樊迟由“小人”变为“君子”的,这根据就在本章的下一段中。
第三,正是这句话,引导我们对“明明德”的重视。前面说过,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不是对樊迟表示绝望,而是对之提出希望,希望他由“小人”变为“君子”。那么,如何使这希望变为现实呢?孔子紧接“小人哉,樊须也”这句话之后,又说了一番至为深刻的话,即本章的第二段:“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包涵这样几层意思:其一,是要做君子式的在上位的领导者。请注意,这里说的三个“上好”的“上”,无疑是指在上位的领导者,但笔者认为,它首先是指“君子上达”的“上”和“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上”,即它首先指的是君子式的领导者,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者。
其二,“上”即君子式的在上位的领导者,所“好”的“礼”“义”“信”,皆不是多数学者所解释的那样,是指道德规范,而是指“道”之“德”、“天”之“德”,即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宇宙—生命”系统的功能在具体事物中的显现,也就是包藏在具体事物中的“道心”“天心”或“良知”。换言之,这里的“礼”“义”“信”,有两层意义,一是从“体”上说的,一是从“用”上说的,首先是从“体”上说的。从“体”上说,就是说“礼”是指“宇宙—生命”系统运动的条理性、秩序性、和谐性,“义”是指“宇宙—生命”系统在最最具体事物中得到了恰当的表现,“义”者,“宜”也,“正刚好,无二择”之谓也。“信”,是指“风信”“潮信”,如同季风和潮水,是如时而来,如时而去的。就“用”上说,指的则是道德规范。“礼”,指“礼仪”,“义”,指义气,“信”,指信用。这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第二义的,在人类社会中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作用,但与前一层意义相比,它不是主旨。
其三,既然君子式的在上位的领导者所好的“礼”“义”“信”,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之“德”,那么,在下位的“民”即百姓,就不能不敬重他、服从他、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他。如果在上者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的做到了“己心”与“天心”的合一,那么,在下者即四方百姓就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在上位者的拥护,就会出现前面讲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那种政治局面。应当说,“为政以德”章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综观上述各点,我们看到,本章涉及到“君子”与“小人”、“形而上”与“形而下”、“上位”与“下位”、“以德”与“为政”诸种关系,正是从对这些关系的解决上,我们看到了樊迟的错误与孔子的正确。樊迟的错误,就在于他只知问“学稼”“为圃”这一类形而下的、为居下位者所做的事情,而不思在“学稼”“为圃”这一类形而下的、为居下位者所做的事情中如何“明心”“上达”而成为君子式的居上位的领导者。换言之,樊迟错就错在他把形而下的技术、知识看得比形而上的“明心”“明明德”“知天命”还重要,也就是一切为了形而下,心甘情愿地要做形而下事物的奴隶,所以,孔子批评他为“小人”。与樊迟根本不同,孔子认为,一切都不如“明明德”,都不如在“明明德”的过程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不欺骗自我。实际上就是不违背真实的客观规律,就是实事求是。孔子此处提到的“礼”“义”“信”等概念,不是指道德规范,而是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的别称。董子竹说得好,“在孔子眼中学种庄稼和一心只想通背三百首诗是一样的不正确,不是这样的行为不好,而是不能在这些行为中‘明明德’,便是错误的。一切为了‘明明德’,对自己的生命不明,对‘知’、‘心’、‘明德’不明,是人类的根本误区。不解决这个根本误区,一切事都做不好,表面做好了,反而可能陷入更大的误区,以致最后毁灭人类。”[3]211董的这番话,好就好在它是“中庸”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既突出形而上的本体地位,又不否定形而下的作用,而以在“形而下”中如何“明心”的思考路径,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三、“义”与“知”
《论语·雍也篇》第22章: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这里的关键,是要弄清楚“务民之义”的“义”和“敬鬼神而远之”的“鬼神”的真实涵义是什么。把这弄清楚了,“可谓知矣”的“知”的本义也就自然明白了。
对“务民之义”这句话,注家的解释不一。比较接近孔子本意的,有钱穆、李泽厚的解释。钱将此句译为:“只管人事所宜。”[4]158李则译为:“尽力做对人民适宜合理的事情。”[5]160他们都把“义”解释为“宜”,这是对的,是合乎孟子“心之所制,事之所宜”这一对“义”所作的界定的。但是,他们的解释,远不如董子竹的解释更为明快、直接、彻底。
董子竹非常推重孟子对“义”所作的界定,认为“义”即“宜”,就是“良知”。他说:“心之制”的“制”,“就是控制掌握这个事情‘宜’,事之‘宜’,即‘正合适’。在这个事情上最合适的做法就是这样。记住,‘良知’它最大的特点是,这件事情在这个‘当下’只能这样做,不能有别的做法,绝对没有第二个选择,就是‘正刚好,无二择’,这就是良知。在这里不存在第二个选择,绝对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叫‘事之宜’,这个‘宜’就是‘最合适’。这个东西绝对不是靠你想就能想得出来的,靠你推理就能推得出来的。任何‘当下’都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都是宇宙生命系统对你的‘义’。人类可怜的概念推理,怎么能完备地寻找到每个当下‘必有事发’的‘正刚好,无二择’?”[6]董子竹进一步认定“义”即“宜”的复杂形态是“致良知”。他说:“‘义’的本义是‘宜’”。“冷必衣、饥必食、热必荫……这便是最简单的‘宜’。‘宜’的复杂形态就是‘致良知’。更进一步,便是‘天之历数在尔躬’,我依这心中的‘历数’之‘势’,判断‘宜’与‘不宜’,这是最高级的‘致良知’。”[7]
董子竹更进一步认定“义”是“良知”获得后的决心,是“事”中之“觉悟”。他说:“‘宜’是自己当下的认知判断,但未必合于我头脑中固有的‘美之为美’、‘知见立知’的观念。怎么办?‘义无反顾’。正是由于此,所以‘義’(义的繁体字)字的下面为‘我’,即出征拚命拚争之‘我’,怀戈待旦之‘我’。‘羊’则是祭天,即问天意、佛意、道意如何。‘宜’则‘必行’,舍身忘我也必行。不‘宜’则不‘行’,不管多么大的诱惑,也不‘行’。‘宜’,‘义’也。义中可以有利,也可能无利,终是大利于我。因为‘天’、‘道’、‘佛’不可能不利于‘我’的大解脱。因为天、佛、道永恒的目的只有一个:步步引我大解脱、大觉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暂时的、浅薄的,无关于我通天达佛者,不管什么‘利’,我也坚决不取。义者,‘良知’获得后的决心。仍然是一个无主宰,一切皆我心的‘觉悟’。‘觉悟’永远不是空道理的觉悟,永远是在‘事’中之‘觉’,这便是‘致良知’,一旦致良知,肯定是‘义无反顾’。”[7]
依据董子竹的上述看法,孔子说的“务民之义”“可谓知矣”的话,便容易理解了。“务民之义”的“义”,既是“良知”,既是“致良知”,既是“致良知”获得后的决心,是一种“事”中的“觉悟”,那么,称它为不同于“世智辩聪”的“真智慧”,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为“良知”就是“智慧”,而使“己心”合于“天心”“道心”和“佛心”的“致良知”,则是名符其实的“大觉悟”“大智慧”。
对本章第二句“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的解释,也有几家值得注意。一是程子(不知是指大程还是指小程)。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8]90二是康有为。他在《论语注》中说:“中国之不为印度,不曰事鬼而专言人道,皆孔子之大功也。然高谈不迷信鬼神者,即拂弃一切,则愚民无所惮而纵恶,孔子又不欲为之,仍存神道之教,以畏民心,但敬而远之。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黩’是也。”[9]81-82三是李泽厚。他在《论语今读》中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前面已讲,这种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是中国的典型智慧。因为任何询求、怀疑和思考,都需要运用理性思辨,而用思辨理性是不可能证实或证伪上帝鬼神的存在的。这至今仍属真理。既然如此,又何必盲目信从上帝鬼神或者依据科学而力加排斥?荀子说;‘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天论》)‘物之罕至’,少见多怪,自属当然,但不必去畏惧它们而妨碍人事。现代学人都大讲荀子是无神论,其实乃实用理性的范例,与唯物唯心无关。亦见儒学之智、知,非止理解、认识,而乃行为、态度、境界。这句话大概因为执政者常不顾人民死活而迷信于致鬼神,抑殷人尚鬼之遗俗?问答均就执政而言。”[5]160-161
上述三者的共同点是,都赞成孔子的观点,强调“能敬能远”,才是智慧。特别是李泽厚,他把不肯定、不否定的态度,说成“是中国的典型智慧”。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不能像孔子那样,看一切问题,都要聚焦于“明明德”。和他们相比,在这方面,董子竹就显得高明多了。且看他对李泽厚上述解释的评语:“其实,何止是鬼神,世间一切相皆然。一切相都有极大的偶然性,即使不能说全是偶然,其必然性也是说不清的,迄今为止谁能把粒子界的运动与物质的运动关系全说清?粒子界本身也恍兮惚兮。其实李先生在论述这种探寻的不可能时,不光要看到这是中国人的机智,更重要的孔子是聚焦于‘明明德’的。一切外相包括鬼神外相,皆只是为‘我’,为我的‘明明德’而存在的。不能否认它,也不要太刻意地去追踪它。它——鬼神和‘我’所知的一切相一样,都只为提醒我认得如下内容:第一,明明德,即我能知之心的运动特点是什么?第二,我的宿命现在怎样左右了我的‘明德’?知了此轨迹,就是摆脱了宿命。第三,‘天命’令一切众生得以‘明明德’的轨迹是什么?正因为这样,孔子才不把鬼神放在心上,所以才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意相、想相、言相、事相、神相都是‘相’,是‘相’就不要纠缠,也不能排斥,缘可了不可逃。”[2]165-166稍作比较,便可看出,董比程、李、康高明多了。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不要把着眼点放在一切“相”(鬼神也是一种相)上,而是要放在“明明德”即对生命本体的“觉悟”上。因为一切“相”,只是生命本体“觉悟”路途中的一些路标,而不是根本的目的,根本的目的,是使“明德”“明”,使“阿弥陀”成为“阿弥陀佛”。什么是“智慧”?“觉悟”,特别是“终极觉悟”,即己心与道心、天心、佛心的合一,才是真智慧、大智慧。而这,恰恰是程子、康有为乃至李泽厚没有为我们明确指出的,这也正是他们的肤浅之处。
如果读了董子竹在另一处对“鬼神”的解释,就会深深感到,他对“知”的理解是多么的深刻。他说:“东方文化永远给‘不知’留有地位。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并非是相信鬼神的实有性,而是给‘不知’留了一个地位,对于‘不知’冠一个‘鬼神’的名字,有何不可?‘子不语怪力乱神’也说明了孔子忠于自己的学说。‘怪力乱神’这些词既然传之甚远,不必贸然否定,但它是‘未知’,更不可肯定,暂且存疑也没有什么坏处。”[10]13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说“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并非是相信鬼神的实有性”。这个看法,是不同于多数注家的。笔者深表赞成。因为孔子“敬”而“远之”的“鬼神”,已不是巫术图腾时代原始宗教中那种支配一切的“心外”之“鬼神”,而是自己的“祖宗神”,这种“神”,其实就是人。二是说“敬鬼神而远之”的“鬼神”,是一个假名,是用来代表“不知”的。给“不知”冠上个“鬼神”的名字,又要人们去敬畏它,这就把“不知”的地位突出了。在孔子看来,“鬼神”和“天命”一样,都具有“不知”的特性,都要对其有敬畏之心。三是说也不可把“不知”推向极端,说“不知”就是“真知”。应当说,这是不难理解的。既然是“不知”,或“未知”,那就不能对之作完全的肯定,只能是“而远之”,即“存而勿论”。否则,就会陷入神秘主义。对此,董子竹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也许是由于古典作家给‘不知’留下了地位,后世的儒、道、释三家一直没能彻底与宗教神秘主义一刀两断,有的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如果想概括一下,我以为可利用‘三神化’这个概念,说明‘东方文化’的现状。一曰:宗教神学化。这在儒家的早期,董仲舒是个典型。……二曰:神圣道德化。最典型的是朱熹的‘理学’。……三曰:神秘功能化。这个倾向主要表现在道、释两家。”[10]15-20综观这三层意思,便知道董子竹所理解的“知”的真实涵义了。他所理解的“知”,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段话中的“是知也”三个字。在他看来,“知之为知之”,即已知或被知,是一种“知”,“不知为不知”,即“未知”或“不知”,也是一种“知”,而且是更为重要的“知”,但是两者分开来说,都不是“真知”,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是真知、真智慧。这在前面已有细解,在此不再多说。
四、“义”与“德”“学”“不善”
《论语·述而篇》第3章: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多数的注家都把这一章今译为:“孔子说:‘道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 知晓了义理不能转变观念,不好的地方不能改正,这些是我所担忧的。”如此来译孔子这段话,孔子的忧虑就很难理解了。因为他们把孔子的原意完全搞颠倒了。
“德之不修”,不是“道德不去修养”,而是“道”不去修养。《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修道”即是“修德”。“修德”只是以己之“得”去合天之“德”。前面说过,人本无“德”,只有“天”赐予的“得”。任何人自命自己有”德”,皆是贪天之功。孔子忧虑的就是这种不去修“天”之“德”、修“道”之“德”,而又自命自己有“德”之人。
“学之不讲”。不是说“学问不去讲习”,而是不去讲习“大学”即生命之学。《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对生命本体的觉悟,“亲民”,亦即“新民”,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对生命的本体有所觉悟。“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对“宇宙—生命”系统整体的把握,即对“天”“天命”的把握。一句话,“学”就是“知天命”,一切“学”都是为了“知天命”。“学”之一字,绝不是学知识,学道德,学礼仪所能概括的。孔子忧虑的,决非是那些不去讲习学问的人,而是不去“明明德”“知天命”,即不去知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人。
“闻义不能徙”。不是说“知晓了义理不能转变观念”,而是不能为“义”而亲身赴之。“义”是“天”之“四德”(仁、义、礼、智)之一,是“良知”获得后的决心或觉悟,也是“天”之功能(生命本体功能)的显现。“义”的本义是“宜”。前面说过,其本字是“義”,它的下面为“我”,即出征打仗之“我”。它的上面为“羊”,用以祭天,询问“天意”如何。“宜”则“必行”,舍身忘我也“必行”。不“宜”则“不行”,不管多么大的诱惑,也“不行”。孔子担心的就是这种不为“天意”而“必行”的人。
“不善不能改”。不是说“不好的地方不能改正”,而是说不能清除那些障蔽“至善”的东西。只有障蔽“至善”的那些妄念,妄想,才是真正的“不善”。除此之外,天下无不善。因为“天”,即生命的整体或本体,是没有人间所谓的善恶之分的。
被颠倒的东西,应再颠倒过来。这一章的正确译文应当是:“孔子说:‘不培养天德,不讲习生命本体,不必行天意,不清洗至善的障蔽,这便是我的忧虑。’”必须强调,“德之不修”是本章的重点。因为“学之不讲”的“学”,“闻义不能徙”的“义”,“不善不能改”的“至善”,与“德之不修”的“德”,基本上是一个意思,都是讲生命的本体,或与生命的本体紧密相连的。
五、结语
从以上对《论语》中讲“义”的主要篇章的解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性的意见。第一,《论语》中孔子讲的“义”,是整个儒学的基础概念。首先,它是孔子儒学的基础概念。如前所述,孔子讲“义”时,总是和“君子”“上”“知”“德”“学”“至善”等观念相连的。他这样做,目的是告诉我们,“义”不是一般的观念,它与和它相连的那些观念一样,也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性质。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具体性”和“当下性”的特点。人们常说,“仁”“义”“礼”“知”(智),是“天之四德”。笔者则认为,“义”不仅是“天之四德”之一,是“本体之德”,而且是其他三个“本体之德”——“仁”“礼”“知”(智)的基础。前面说过,“义”是“仁”的具体当下的生发。这是说“义”就是“仁”,是具体当下的“仁”,或者说,“仁”是以当下的“义”为基础的。
其次,“义”不仅是孔子儒学的基础概念,而且是孟子儒学的基础概念。这可以从孟子说的“心之同然”的一段话得到说明。孟子说:“心之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章句下》)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理”与“义”就是“本体之德”。因为这两者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这个“同然”,是指“理”(“礼”)与“义”,是在“体”上的“同”,而不是在“用”上的“同”。孟子这段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把“理”(“礼”)与“义”连在一起说。你看他说得多好:“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本体之德”不是个概念问题,而是实践理性问题,是在实践理性中自然表现出来的“心之制,事之宜”,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是为了告诉我们,不要抽象地讲“本体之礼”,而要力求像“义”那样,具体的、当下的讲“礼”。
再次,“义”也是王阳明心学的基础概念。这可以从王阳明讲“心”的几段话得到说明。王阳明说:“心也者,吾所得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 《传习录·中》)这是专门讲“天之四德”中的“知”(“智”)这一“德”的。这里的“心”“性”,就是指的“知”。它不是一般的“人心”,而是能指挥视听言动的“道心”。它和“仁”“义”“礼”诸观念一样,也是“本体之德”,是不可与人间的“道德”混为一谈的。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一点,在王阳明这些话中,不仅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知”( “智”)的真实内涵,指出“知”(“智”)就是对一切的认知,特别是对“仁”“义”“礼”这样一些“本体之德”的认知,其本身也是“本体之德”,而且突出其中“义”的基础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他所说的“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清楚地看出。大家不妨对“仁”“义”“礼”“知”(“智”)这“天之四德”作一比较。通过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出,只有“义”这个观念最具有“具体性”和“当下性”。
至此,“义”在整个儒家学说中的基础地位,已经昭然若揭。因为强调“义”的基础地位的孔子、孟子、王阳明,前一位是儒学的创始人,后两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镇。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们如此这般地强调“义”的基础地位,这是和“心祭”相联系的,是和“德”字相联系的,是和“致良知”相联系的。这是董子竹先生告诉我们的。他说:“中国自黄帝、尧、舜、禹时代起,虽然各种祭祀仍然保留,但‘心祭’却是最重要的。从迷信祭祀转化为‘心祭’是中国文化之所以领先于其他文化的根本所在。其实我们为‘致良知’讲了许多,就是说的这种‘心祭’。‘心祭’必‘尚德’、‘崇德’,而这个‘德’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是‘天意’、‘佛意’、‘道意’在每个具体事物事件中的显现。……天之德合于我,我合天之德,我当然有德。有德之人,必‘得’。说到底,是一个‘宜’。冷必衣,饥必食,热必荫……这便是最简单的‘宜’。‘宜’的复杂形态是‘致良知’。更进一步,便是‘天之历数在尔躬’。我依这心中的‘历数’之‘势’,判断‘宜’与‘不宜’,这是最高级的‘致良知’。”[7]笔者非常赞成董子竹先生把“心祭”解释为“致良知”,也非常赞成他将“德”解释为是“天意”“佛意”“道意”在每个具体事物事件中的显现。因为这一解释与“义”的本义是十分切合的。这一点,只要认真地看一看他对“致良知”的界定,就会深信不疑。关于“致良知”,董有多个界定,这里只介绍一个,这就是:“良知”是“在某一件最最具体的事件中,隐藏的‘天意’、‘佛心’。如果以现代语言说,就是‘宇宙—生命’系统全息的显露。儒门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自己是要‘行’的。‘良知’即是‘天行’的显露。这种显露几乎是无处不在,处处在,但由于人类迷于自己的意识,便遮盖了‘天行’的正常显现。所以‘致良知’的戒慎恐惧,就是要时时小心自己的各种如瀑流一样的意识,妨碍你了知‘天行’的‘历数’”。[11]从这个关于“致良知”的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义”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因为“致良知”强调的是在最最具体的“当下”中求“天意”,求“佛心”,而这,正是“义”的根本特点。作为“本体之德”的“义”,它比其他的“本体之德”,更具“当下”的色彩。
第二,《论语》中的“义”不同于西方人说的“正义”“公义”,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西方人说的“正义”“公义”,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神,耶和华的“正义”“公义”。它必须以一神尊崇为前提,以“先知”的语言说教为前提,以教规、教诫为前提。这样的“正义”“公义”,事实上就是神这个主宰者的意志,就是对神的一种“信仰”,它还能是一种真正的“正义”“公义”吗?二是这个文化进入地中海北岸之后,与当地的海盗集团文化相结合,又加了一个前提,这便是以贵族、平民的利益为前提。这个前提没有什么神秘性,就是城邦海盗内部的一种分配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不给奴隶的)。它类似于绿林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称分金的做法。其内部也分阶级,平民、贵族、教士得利是不一样的。但由于是抢来的利益,这种有等级的分赃,是所有的成员都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家事先有约定。这个约定,先是契约的形式,后来就演变成为法律。就是说,西方人说的“正义”“公义”,是靠“契约”“法律”维护的。三是上述宗教教主的主宰者的“正义”“公义”,与海盗分赃的“正义”“公义”结合成一体,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这些“正义”“公义”,本身就是“公平”的,就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的。加上他们的哲学家,如康德这样的人对之作似是而非的提炼和升华,似乎真的成了一种“先天道德律令”,成了社会意识中的一种“公理”。
与西方人说的“正义”“公义”相比,“论语”中说的“义”,虽然从概念上说,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就历史内涵而言,却是大不相同的。首先,《论语》中没有一个定于一尊而又主宰一切的人格神,只有我“心”认定的“天”“天命”“天道”“天德”。这些概念,已从巫术图腾时代的鬼神迷信,变成为生命本体。说得更准确些,已变成为“我”的“当下”的“良知”。只要真正懂了《论语》中的“敬鬼神而远之”和“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两句话,就会深信不疑。
其次,《论语》中没有“先知”,只有“圣人”“仁人”和“君子”。这个区别也是很大的。“先知”听从“附体”之“耳”,“圣人”“君子”听从“良知”之“心”。孔子从不轻许自己是“圣人”,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论语·述而篇》)又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 《论语·述而篇》)所以,在《论语》中,他讲“君子”讲得最多,而且在许多地方又和“义”连在一起讲。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喻于义。”( 《论语·里仁篇》)“君子义以为质。”( 《论语·卫灵公篇》)“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篇》)从这些语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孔子所说的“义”的真实内涵。何谓“义”?对于天下的事物,即万事万物,不作亲疏、爱憎、肯定与否定的分别,这就与“义”靠近了(“义之与比”)。这样的“义”,就是“本体之德”,即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也就是落入人间的“天意”“良知”。既然“君子”是真正懂得“义”的人( “君子喻于义”),是以质直于心,求诸己心为根本的人(“君子义以为质”),认为“义”是最可尊贵的人(“君子义以为上”),而“义”又是“本体之德”,是落入“当下”的“天心”“良知”,那么,“君子”在儒学中,就只能是指“知天道”“达天德”的人,而不是指那些仅占据高位和道德高尚的人。从这些语录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将“君子”与“义”结合起来讲的真实原因。既然“君子”是“达天德”的人,而“义”又是落实于人间的“天之德”,那么,把“君子”与“义”连在一起讲,就成了必然。因为在“义”那里,“天德”就隐藏在人间的万事万物中,你这位“君子”若是离开人间的万事万物,去达“天德”,那你就会使“天德”成为架空之物;反之,你若只注目于万事万物,而置“天德”于不顾,那你讲的“义”,就不是本体之“义”,而是人间讲的“道德”之“义”即“礼仪”之“义”了。弄懂了把“君子”与“义”结合起来讲的原因,也就理解了人们为什么会说儒家是“贴着地皮说话”这一特点了,也就理解了孔子说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了。
再次,《论语》讲的“义”和西方人讲的“正义”“公义”的另一个根本区别是:西方人讲的“正义”“公义”,用李泽厚的话说,是一种“社会公德及制度”,如今日认为的民主、自由之类,都只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绝对不具备永恒的性质,更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正如李泽厚说的那样:“我始终认为,今日之民主自由建立在现代化生活基础上(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并非源自文化传统。”[5]366而《论语》所说的“义”,与西方人说的“正义”“公义”,有本质上的不同。它的“天德”虽离不开万事万物,但其本身却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是永恒存在的。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永不断灭的秘密所在。
第三,要深入探索《论语》中“义”的当代价值。首先,“义”的本义是“宜”,而“宜”的复杂形态是“致良知”。后来中国“义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待“良知”的态度和决心上。“义无反顾”,就是这种态度和决心的表现。“义无反顾”是“良知”获得后的决心和觉悟,是孔子“致良知”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在历史上,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身先赴死,在今天,它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其次,《论语》中的“义”,到了董仲舒那里就开始变味了。他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就将“德”与“得”分离了,“义”与“宜”割裂了。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就会发现孔子所说的“义”的“本体”性,全被扔掉了,全被道德化了,“义”在它那里,已经变成全民族应尊崇的“美德”。可以说,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为了神化一个“义”字。清代的多尔衮就懂得这一主题,他利用《三国演义》所说的“义”字,令多少汉人成了汉奸!我国的民间也懂得这一主题,他们建造了那么多的“关帝庙”,就是个证明。遗憾的是,今天有不少讲《三国演义》的人却不知这一主题,而在那里胡言乱语,七扯八拉,祸害民众。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力。靠什么来“提高”和“增强”呢?靠《论语》中孔子讲的“义”,只有它能够帮助我们永远走在中国“义文化”的正确发展道路上。
再次,“义”的复杂形式是“致良知”,而“致良知”则是“良知”即生命本体应有之“知”落入在“用”中,但又不迷于此“用”的意思。这就启示我们,对世间的一切的评价,要持慎重态度。不要纠缠于具体事物的是是非非,而要着眼于支配具体事物的那个“本体”,要为这个“本体”的正常运转、良性循环,开辟道路。《周易》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说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就是指此而言的。中国历史上,妨碍这一伟大思想正常运行的三大障碍,必须否定,这就是:把中国文化神秘化、宿命化的帝王文化;把中国文化迷信化、愚昧化的自耕农保守文化;把中国文人引向逃离现实的士大夫阶级自命清高的陶然文化或田园文化。“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重大课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不遗余力为此奋斗,所以这其中便必然包含着“义”。至于这其中出现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属于第二位的,是不必纠缠不放的。革命永远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一首美妙的诗,在革命的过程中,痛苦、残酷、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迷于此,而忘记它里面所包含的本体之“义”。
[1] 白子超.说《论语》[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2] 董子竹.论语真智慧——兼就教于钱穆、李泽厚先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3] 董子竹.论语正裁——与南怀瑾商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4]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5] 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6] 董子竹.阳明大学堂·中国心学史散论之二[EB/OL].(2010-09-26) [2017-11-10].http://blog.sina.com.cn/dongzizhu.
[7] 董子竹.心学史经纬之三十九·孔子“义”学辨[EB/OL].(2012-04-29) [2017-11-10].http://blog.sina.com.cn/dongzizhu.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33.
[9] 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董子竹.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11] 董子竹.心学史经纬之十三·从王阳明“辟佛”说起[EB/OL]. (2010-04-18) [2017-11-10].http://blog.sina.com.cn/dongzizhu.
“MoralRighteousness”inAnalectsofConfucius
ZANG Hong
(SchoolofMarxism,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2,China)
Confucius;AnalectsofConfucius; moral righteousness; Four Virtues of Heaven
The main chapters of Confucius's “righteousness” inAnalectsofConfuciusare uniquely elaborated. “Righteousness” is “the virtue of Heaven”, that is, Providence, conscience falling into the world. Conversely, the “Tianxin” or “Daoxin” in the most specific things is “righteousness”. In other words, “righteousness” and “benevolence” “ritual” “know (wisdom)”,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Four Virtues of Heaven”, are the noumenon of lif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virtues”, “righteousness” is more “concrete” and “present”. It is this characteristic that makes us further realize the basic position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whole Confucianism. From the explanation, also it is clearly seen tha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eousness” by Confucius,and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understand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follow the correct path of Chinese “culture of righteousness” and uphold and develop Chinese “culture of righteousness”.
10.14182/j.cnki.j.anu.2018.01.003
2017-10-21
臧宏(1933-),男,江苏宿迁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和儒道释三家原典。
B222.2
A
1001-2435(2018)01-0019-10
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