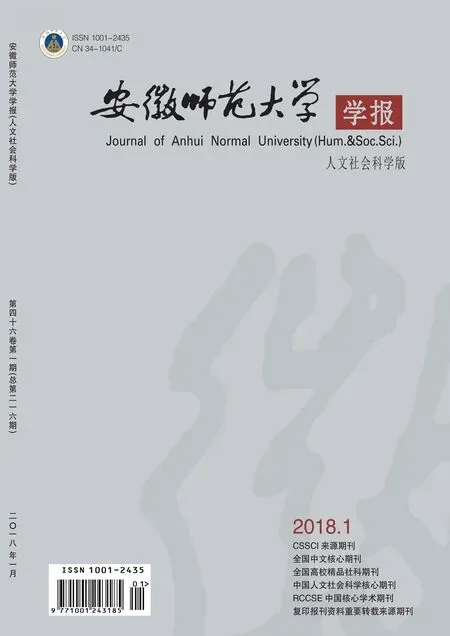苏联民族联邦制的理论逻辑与内在张力
——以列宁的国家结构理论为视角*
傅强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40)
【政治学研究】
苏联民族联邦制的理论逻辑与内在张力
——以列宁的国家结构理论为视角*
傅强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40)
列宁;民族联邦制;民族自决权;区域自治
苏联民族联邦制建立在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民族成分的区域的自治这两个基础之上,以民族原则来确定联邦结构的组成单元。列宁原则上支持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大国,视其为通向社会主义和民族融合的唯一道路。民族联邦制只是布尔什维克迫于革命后求民主集中制不得,而采纳的一种过渡性政治架构,倘若它在长时段内无法实现民族融合之最终目标,必然会崩溃于其自身两个基础所培育的民族意识和分离倾向。民族联邦制自身不具备自我维持的动力和权威,其唯一的支撑——民主集中制党崩溃之际,也就是它的消亡之时。
理查德· 派普斯曾指出,苏维埃俄国是第一个把民族原则作为联邦结构基础的现代国家。苏联学界也认为,苏俄联邦制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方式,它以民族区域原则和联邦主权与平等成员的自愿结合为基础。与美国、瑞士等国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不同,苏联的联邦制是一种民族联邦制,联邦结构的组成单元是基于民族原则而不是以行政区划来确定的。苏联民族联邦制最早、最完备的规定见于全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宪法》第2条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各自由民族自由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为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1]161俄罗斯联邦的基础是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自由联盟的前提是分离的自由,而民族自由分离权是民族自决权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同时,《宪法》第8条规定各民族拥有是否愿意以及在何种基础上参加联邦的独立决定权,第49条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职权的规定隐含着承认联邦各别部分的退出权。因而,苏联的民族联邦制是一种基于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联邦制。《宪法》第11条规定,“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的苏维埃,可以联合成自治区域联盟。……这些自治区域联盟根据联邦原则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1]163因而,苏联民族联邦制的另一个基础是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这些特定的区域联合为自治区域联盟,建立自己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机关,同时依据联邦原则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
全程目击苏联事变的美国驻苏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对苏联剧变和苏联解体有一个著名的区分:共产主义制度结束意义上的苏联剧变是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和终结,而苏联解体却根源于苏联成立之民族联邦制理论,苏联“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但它在形式上却是主权共和国的自愿联邦”。[2]758国内学界对苏联民族和国家结构形式理论的研究相当扎实:在民族理论方面,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作为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得到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在国家结构方面,关注到列宁在国家结构理论上的态度转变,也关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刘显忠认为民族自决权及联邦制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重建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但是,作为民族自决权重要内容的退出苏联的权利最后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列宁始料未及的。参见刘显忠《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第32-37页。周尚文和张祥云指出,苏联的崩溃不能归咎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及联邦制,而是由列宁之后的历届领导人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以致联邦的严重变形造成的。参见周尚文、张祥云《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与苏联解体有关吗》,《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第114-121页。还有少部分学者运用民族联邦制概念来展开对苏联政治和苏联解体的研究。*在国内的苏联研究中,明确提出“民族联邦制”概念的只有两篇文章。初智勇认为,苏联的联邦制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联邦制是因为它以民族邦为基本成员单位。他分析了民族联邦制在社会基础、制度资源、政治权力合法化方面存在的不足,同时认为民族联邦制在实践中遭到的破坏与践踏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见初智勇《苏联民族联邦制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04年第2期,第51-55页。侯万锋认为,苏联这种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是由若干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的,每一联邦主体单位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完整性。他以民族联邦制为切入点研究了苏联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同时认为背离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最终导致了苏联联邦制国家的解体。参见侯万锋《民族联邦制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以苏联和南斯拉夫为例》,《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1期,第76-79页。但是,这些研究或者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纳为对马列主义民族政策的背离所导致的民族问题的激化,或者归结为联邦制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变形。本文首先强调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辩证发展和不变的工具性质,考察列宁国家结构形式理论的原则与例外以及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进而,梳理和探究革命形势所迫之下,列宁采纳民族联邦制的实践考量;最后,总结和评价如此这般构建的民族联邦制所蕴含的内在张力,特别是这种张力在苏联解体事件中的意义。
一、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辩证发展
(一)民族自决权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民族自决权论述发生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前后。第二国际早在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就曾宣告,“大会主张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3]54而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则最早在俄国提出了承认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的主张。列宁在《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中,就其中的民族自决权条款做出了第一次阐释:民族自决权意味着,俄国社会民主党“无条件地反对任何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4]89民族自决权的这种阐释针对的是俄罗斯帝国内部严重的民族压迫,其运用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是完成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手段。但是,列宁同时也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主要任务并非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应当使得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民族自决要求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二阶段的民族自决权论述主要针对的是1911年后党内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滥觞。列宁认为,民族文化自治本质上是一种把教育事业从国家管理中分出来交给各民族管理的计划,这实质上使得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它鼓吹各民族在教育事业上的相互隔绝,从而产生和保持以这种隔绝为基础的民族特权,这不利于国家的彻底民主改造和民族和平,实质上也违反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分裂了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在批判民族文化自治观点的同时,列宁在其著作的三个不同地方重新归纳了民族自决权的实际操作形式,“(每个民族)都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可以同俄国分离的权利”[5]58,“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即分离的自由”[5]215,“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以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5]329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从政治自决的角度总结了民族自决权的新内涵,“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6]225俄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必须在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倡导和贯彻同俄国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自决权,这首先是为了为执行一般民主的原则。但是,俄罗斯帝国本身的特点却是必须执行民族自决权新内涵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俄国境内各民族差别大、受压迫程度深,俄国落后反动的国家制度,与俄国接壤的地区正处于导致众多独立民族国家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造进程中。
第三阶段的民族自决权论述在反驳卢森堡观点的基础上,主要阐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之民族自决权理论。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与自治》中认为,巨大国家的发展和资本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新时期的主要特征。这一方面使得较小民族根本不具备自决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在暴露和激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同时,也使得殖民地国家根本无力反抗。此外,民族自决权迎合和加剧了分裂情绪,导致政治和经济实体的小型化,破坏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不利于产生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国际市场和全球市场。因而,在卢森堡看来,民族自决本质上是一个伪问题,作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的民族国家已经完全过时了,随着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和步入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融合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7]150-181与卢森堡一样,列宁也认识到帝国主义新时期的两个特征,他还强调“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同样必须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联系起来”。[8] 316然而,列宁运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理论对新特征重新阐释,突出了民族自决的潜在进步性。列宁提出,以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区分为基础重新界定民族自决权的含义,即“要求民族有自决的自由,即独立的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9]85具体而言,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承认民族平等与实现工人之国际团结,应提出被压迫民族有政治上的分离自由权。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将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之工人团结提升到首要地位,从而抵制和粉碎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兼并和压迫政策。以这种基本区分为前提,列宁还从各国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进程所处的位置出发,区分了三类不同国家之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自决权应具有的态度: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和所有殖民地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践行民族自决权原则时,应要求立即无条件地解放殖民地,通过起义和革命战争最坚决地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最有效方式,从而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有力的援助。[9]262-3
(二)民族自决权的辩证发展与不变内涵
民族自决权是苏联民族联邦制最核心的基础概念。列宁三个阶段的民族自决权论述都有着各自针对性的特定议题,他在1902-1903年制定党纲时,将民族自决权界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反对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对民族自决的干涉。1912-1913年,民族自决权由模糊的被动防御干涉的含义明确为主动分离和成立独立民族国家之权利。1915-1916年,民族自决权被概括为帝国主义时代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分离自由。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所认识到的,列宁在“1914年之后在自决权理论上有个调整”[10]427。民族自决权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明显的辩证发展。1914年之后,列宁开始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民族解放运动这种崭新的革命主体概念,它是帝国主义新阶段能够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辩证法的对立面。民族解放运动是民族自决权原则在新时期的表现,它是促进各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运动进程,从而促发和援助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工具。因而,民族自决权从一个解决沙皇俄国民族压迫问题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具辩证发展为一个与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紧密联系的、普遍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工具。
尼尔·哈丁曾认为,“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复杂歧义与他在决定大多数其他问题的政策上的直率形成鲜明的对照”。[11]235然而,即使考虑到民族自决权的辩证发展,我们仍旧可以归纳出民族自决权的不变内涵。阿尔弗雷德·洛就坚持,“直到十月革命,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问题的思想有着相当惊人的连续性”。[12]9-10总体来看,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存在着两个不变的核心观点:(一)一切民族都享有不仅法律上的,而且是实际上的、直至从一个国家分离出去的自决权;(二)无产阶级坚决主张民族分离权,但并不无条件地主张民族分离,相反,无产阶级主张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自愿的民族融合。无论在目前还是在革命时期或者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目标都要求在解放被奴役的民族的基础上通过自由结盟建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这只有通过民族自决权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来实现,因为没有分离自由,自由结盟也就是一句谎话。换言之,民族自决权具有一种不变的工具性质,它起初是消除俄国民族压迫保证俄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工具,后来发展为援助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保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普遍性质工具。在1916年1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民族自决权的这种工具性质被提升到了与无产阶级专政同等的重要地位,如同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来实现阶级差别的消灭,“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9]258简言之,民族自决权所蕴含的自由分离权并非是要奉行建立小国的目标,而是以分离自由为工具反对民族压迫,它的最终目标是在真正民主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融合。但是,民族自决权分离自由之行动方式与民族融合之最终目标之间的张力也很鲜明,它最终反映在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民族联邦制之中。
二、理论建构中的原则与例外
(一)原则:反对联邦制支持民主集中制
列宁捍卫以民族融合为终极目标的民族自决权,在国家结构形式方面原则上反对联邦制共和国。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在1903年时曾经设想,由于俄国存在着很多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各个不同民族,将来的自由俄国应当建成为一个联邦制共和国。列宁赞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关于不要求民族自治而要求国内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基本主张,但是,他基于三个理由坚决反对创建联邦制共和国:其一,联邦的定义表明它是各单个完全独立体依据双方自愿原则,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订立条约来确定的相互关系。[4]303因而,联邦制共和国存在的前提只能是自治的、民族的、政治的统一体。既然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已经表示不支持民族自治,不支持发展那种政治上自治的民族统一体,那么它就绝对不应该要求联邦制共和国。其二,鼓吹联邦制和民族自治将导致成立自治的阶级国家的主张,这绝非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应致力团结所有民族中的工人群众,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其三,列宁在1913年致邵武勉的信中认为,反对联邦制还有更深刻的经济理由。联邦制会削弱经济联系,因而并非一个国家合适的结构形式。[13]380
列宁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支持中央集权制。广阔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大国会尽可能消除一切不利于经济的隔阂,形成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紧密经济联系。在这种地域更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将会更广泛地开展起来。此外,列宁还认为,中央集权制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4]148直到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仍然坚持地方和州在集中制共和国而非联邦制共和国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
列宁坚持,无产阶级拥护的集中制大国只能是民主集中制大国,它以广泛的地方自治,特别是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表现出其民主性的一面。列宁强调,“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儿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各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6]73正如相较于联邦制而言,集中制原则更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较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表现为特殊区域自治的民主集中制也更利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因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在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是真正民主集中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1914年“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中,列宁还就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详细列出了完备的实施计划:(一)俄国行政区之变动必须以当前经济条件和当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调查为依据;(二)调查委员会按照比例代表制和无记名投票规则组建,人口过少的少数民族最少也要保证有一名享有发言权的委员;(三)全国各地应按照比例代表制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地方自治机关;(四)地理、生活或经济条件以及居民成分特殊的地区,有权成立自治区并设自治区议会。[6]143与民族自决权一样,这种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思想主要针对的是民族压迫政策。它是一种反对民族压迫以及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民主手段,它的根本目的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各民族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联合和发展。
民族自决权原则并不意味着要求结成联邦的权利,与支持民主集中制也不矛盾。列宁坚决反对邵武勉那种将自决权与结成联邦的权利联系起来的主张,因为“联邦是各平等者的联盟,是一个要求一致同意的联盟”。[13]380然而,民族自决权是一种一方面要求另一方面同意的权利,即要求分离之民族通过全民投票从异族集合体脱离成立独立国家之权利。这种类型的权利根本无法与联邦之一致同意、双边协定的含义达成一致。同时,列宁认为民族自决权并不与民主集中制国家的要求矛盾,它是集中制这个总前提中的一个例外。民族自决权是一种政治民主要求,是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最彻底表现,但并不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和建立小国。大国无论对经济发展还是对群众利益的好处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一国的制度越民主,越具备充足的分离自由,那么它在实践中的分离欲望就越小。民族自决权作为一种消除民族压迫之彻底民主的政治手段,将促成真正民族融合之民主集中制大国成立。
(二)例外:“一定的特殊条件下”支持联邦制
在反对联邦制支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总的原则以外,列宁也在著述中为联邦制在特定条件下的存在保留了余地。列宁在1903年的《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中就曾指出,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可以支持以较为松散的联邦制的统一来替代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4]218在1914年《论民族自决权》中,列宁阐述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观点时说道,马克思在原则上虽然是反对联邦制的,但是,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他这次却容许联邦制。[6]271马克思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这种特殊历史现实下的联邦制反而更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更能促进社会迅速发展。因而,在反对联邦制这个总原则之外,列宁也并没有排除例外的存在。倘若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更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联邦制。
这种例外论在《国家与革命》中表现的更明显,列宁在评述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评》时说道,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德国无产阶级应当以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来取代君主制宪法和小邦分立制,但是,他也认为联邦制共和国存在的例外情形可以视为“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15]68这个特殊条件主要是指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问题致使国家分崩离析之际,联邦制可以视为对严峻民族分裂情绪的妥协,是最大程度保存国家统一和维护民族联系的手段。因而,可以作为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视为前进一步。
三、实践中的例外:民族联邦制
(一)革命实践中坚持民族自决权与特定的区域自治
二月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转眼之间,民族问题和国家结构形式从理论问题变为紧迫的政治实践问题。但是,即使在1917年以后,列宁仍然一如既往地捍卫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布尔什维克认为,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从而被兼并进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在当前革命形势下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只能是,“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16]1661917年8月底,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关于政权的决议案》中提出,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独立要求,这是当前必须立即实施的紧急措施,是切实实现各民族自决权的第一步。[1]46与此同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表示,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完全不排斥地方自治,这种自治一方面能够维护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又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当然,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已经将这种地方自治明确为以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为标识的区域自治。
十月革命后,民族自决权原则和特定区域的自治观点立即得以实施,临时工农政府颁布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将俄国各民族人民的权利细化为四项处理民族问题的具体依据。其中,关于民族自决权宣告到,“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享有主权;俄国各民族享有自由自决,直到分离并组成独立国家的权利”,关于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则要求,“废除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和限制;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和种族集团均得自由发展”。[1]66因而,俄国革命爆发以后,列宁始终坚持着民族自决权和特定区域自治的观点。按照革命前列宁在国家结构方面的原则性观点,既然仍坚持民族自决权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那么他也就应当合乎逻辑地要求民主集中制形式的国家结构。但是,列宁在坚持尽可能大的国家和各民族融合这种终极目标时,却越来越频繁地提及该目标只能通过各民族工人群众以自由分离为基础的自由联合来实现。换言之,在两个基础未变的情形之下,列宁在国家结构形式方面的提法从要求民主集中制大国转换到了强调各民族自由联合之大国。
(二)革命实践中联邦制之采纳及其理论地位
列宁态度的这种转变,正是源自1917年2月之后的俄罗斯帝国面临着那种联邦制可以作为例外而存在的特殊条件。俄罗斯帝国包罗有百多个民族。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段时期,在罗曼诺夫皇朝的民族压制结束之际,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纷纷脱离沙皇统治。在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境内大约出现了70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民族独立情绪严峻的形势下,不具备立即成立一个集中制统一国家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然而,各地区分裂、隔绝的状态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又是非常不利和极其危险的。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利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发展的。
有鉴于此,列宁从反对联邦制的总原则立场走向了采纳联邦制的例外立场,以求尽可能的维持国家统一与民族联系。最早在1917年6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俄国可以组织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联盟。最终,这种例外立场在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得到法律上的正式承认,人民委员会在民族政策方面应当实行的民族自决原则“将促使使用压迫和暴力把各个民族限制在自己区域内的旧帝俄,改变为依据联邦的原则自由联合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兄弟联盟”[17]8,从而也就采纳了基于民族自决权的联邦制架构。大会通过的《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和《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决议将这种观点表述为,应当在各自由民族自由联盟的基础上,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为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当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宪法序言,民族联邦制也就正式载入了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然而,苏俄在革命后采纳民族联邦制,并非列宁思想的根本改变,只是当时政治形势之下的权宜之计。革命前,列宁曾为联邦制的例外存在预留了理论空间。革命后,在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的同时,联邦制是在严峻政治形势和民族问题突出的状况下,团结俄罗斯境内各民族,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和暂时性的策略。列宁在革命后有所保留地提到,联邦制“只要它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实行,只要它是以真正需要某种程度的国家独立性的重大的民族差别为基础,那么它同民主集中制也丝毫不抵触”。[18]139在苏维埃这种真正民主的制度下,联邦制可以视之为实现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民族联邦制的过渡性质完整地展现在列宁对俄国政治实践发展的推演之中:首先,以民族自决权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为基础,以联邦制共和国为过渡,创建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统一苏维埃大国;其次,这个民主集中制大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道路,它最利于实现消除阶级差别和民族融合的社会主义终极目标。因而,列宁至始至终都认为,即使有民族联邦制这个例外的存在,俄国各民族最终都应当联合为一个民主集中制大国,从而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四、民族联邦制的内在张力与维系
革命后,列宁主持起草的苏俄1918年宪法一方面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始终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另一方面又以之为基础采纳联邦制作为国家结构形式,从而也就最终奠定了苏联的民族联邦制。通过1924年宪法以及后继的1936年斯大林宪法、1977年勃列日涅夫宪法,民族联邦制在地理范围上进一步扩展,组织架构进一步完善。但是,它作为过渡的工具性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埃拉扎尔才将苏联民族联邦制归纳为“作为手段的联邦主义”[19]97。民族联邦制之建构本身具有两个目标:其一,在保持苏联最大程度统一的同时,帮助各民族包括最弱小的民族集团实现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自由和文化上的发展;其二,消除民族差别,将各民族融合为一个新的历史性的、更高级的共同体——苏联人民。在第一阶段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为贯彻民族自决权原则,1924年宪法第3、4条和1936年宪法第15、17条以及1977年宪法70、72条分别载入了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主权条款和退出联盟的权利。这实质上也就为联盟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与此同时,为奉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苏联推行了那种依据语言分布创造新民族行政单位并将其领土化的民族政策。这实质上也就培育和强化了各族裔的民族意识。因而,民族联邦制走向民族融合之道路中所依靠的工具——民族自决权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它们本身也具有产生分离意识的能力。
列宁及其后继的苏联领导人一直对这种分离力量保持着清醒的态度和足够的警惕。但是,一方面,在社会主义传统中,民族问题相较于工人问题一直处于从属地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断定“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20]50,而列宁也强调“‘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6]265。另一方面,建政初期,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安危系于世界革命之发生,他们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及时援助和俄国革命的未来发展充满着乐观预期,一直期待着短期内社会主义之实现所带来的民族问题自动解决。在社会主义之民族融合目标很快来临的期待中,民族联邦制突显了自身作为实现最终目标的工具性价值,而隐匿和淡化了自身内含的张力。然而,当这种乐观想象最终被俄国以及世界的政治现实浇灭,打断了工人问题及其附随的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那么,即使斯大林宪法宣告建成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宪法宣布形成了苏联人民这种新的历史共同体,但是,纸上宣言与实践中民族问题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民族联邦制两个基础蕴含的分离力量也将愈发显著。
理查德·派普斯指出,列宁在经济进步力量最终消除民族差别从而将苏联改造为单一制国家之前,所拟定的解决苏联境内民族问题的办法是“在文化问题方面对少数民族作出广泛的让步,在立国问题方面作出少数的、基本上是形式上的让步,在党组织问题方面一点儿也不作让步”。[21]106实际上,在苏联存续期间,维护联邦、压制联邦之民族基础的分离倾向,特别是针对退出权的禁止使用,唯一的力量源泉和保障就是以消除工人剥削和民族压迫为己任的民主集中制共产党。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列宁在党的组织结构的方面立场一贯坚定而明确,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铁的纪律以及党的各分部对权威中心负有严格责任。早在建党之初,列宁就通过反对崩得在各民族组织基础上建立松散联盟党的行动以及在与马尔托夫关于党员定义的辩论中,阐述了自己建立民主集中制党的基本观点。十月革命之后,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党内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有统一的集中制的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的一切决议,党的各个部分(不分其民族成分)必须无条件地执行”。[22]567随着苏联的建立和苏联地域范围的扩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一直得以坚持并随之而进一步扩展。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中央批准成立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这标志着苏共民主集中制党的最终解体。因而,当党本身在90年初也背离自己一直坚持的民主集中制结构而分崩离析之时,苏联民族联邦制共和国就只得落入解体之命运。
苏联民族联邦制的内在张力就蕴含在其自身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之中,这种内在张力也正是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民族联邦制是一种过渡性的工具,它要在实现民族融合之最终目标的进程中取消自我。同时,作为民族联邦制基础的民族自决权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一方面是实现民族融合必须坚持的工具性原则,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又蕴含着民族分离的力量。相较于西方典型联邦制,即为解决一切共和国都面临的“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难题而建构的“既具有共和政体的所有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之联盟共和国[23]154,这种制度架构之目标本身所要求的联邦制的稳固长存特征愈发地突显了苏联民族联邦制的不稳固性。苏联民族联邦制的自我取消特征,特别是其构成基础——民族自决权与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自治——的工具性和两面性表明,它不具有固定法权结构,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最终,民族联邦制只能借助于民主集中制党的强制和糅合力量而维持持续存在,它或者沿着社会主义目标真正实现带来的民族融合的康庄大道而自我消解,或者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之中由于内在张力冲破了其存在的平衡点而解体。
[1] 谢·谢·斯图坚尼金.苏维埃宪法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2] 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M].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3] 伊·布拉斯拉夫斯基.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G].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
[4]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 中央编译局.卢森堡文选: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 Carr E H.The Bolshevik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M]∥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Vol. 1.London: Macmillan, 1950.
[11] 尼尔·哈丁.列宁主义[M].张传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2] Alfred D L.Lenin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y[M].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1958.
[13]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18]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9] 丹尼尔·埃拉扎尔.联邦主义探索[M].彭利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
[20]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伦纳德·夏皮罗. 苏联和未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2] 中央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TheoreticalLogicandInherentTensionofSovietUnion'sNationalFederalism—FromPerspectiveofLenin'sTheoryofStateStructure
FU Qiang
(LawSchool,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Lenin; national federalism;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regional autonomy
The national federalism of Soviet Union was based o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gional autonomy with special living habits. The unit of federal structure is determined by 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 As regard to the form of state structure, Lenin always supported democratic centralism which was based o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t was considered the only way to socialism and national fusion. Owing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olshevik couldn't adopt democratic centralism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o, National federalism is adopted as a temporary political structure. If national federalism couldn't achieve the final goal of national fusion for a long time,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tendency of separation which was fostered by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will make it collapse. National federalism didn't own self-sustaining power and authority, democratic centralism party is the only support for it. At the time of collapse of the Bolshevik party, the National federalism comes to the end.
10.14182/j.cnki.j.anu.2018.01.007
2017-04-15;
2017-05-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MZoom023);司法部法治国家建设理论项目(2014SFB3005)
傅强(1988-),男,安徽郎溪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苏联政治法律研究。
A821
A
1001-2435(2018)01-0050-08
陆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