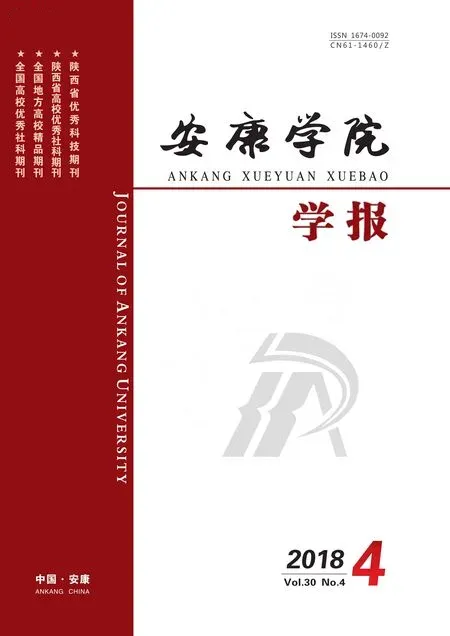论“灵”与“肉”冲突下的女性自杀现象
赵娜娜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灵”与“肉”这一永恒的话题,从西方到东方,从远古到当下,困扰着诸神,也使先哲们争论不休,成为作家笔下说不尽的话题。新时期以来,大量女性作家从女性命运这一视角关注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命历程,并凭借丰富的个人经验和创伤性记忆,立足于“女人”觉醒的精神空间来洞察“女性自杀”的内里,对女性“灵”与“肉”世界中难以调和的冲突进行深刻剖析,描绘了一幅幅引人深思的图景,实现对女性生存现状和存在价值的反思以及对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怀。
当读者进入文学的内部发现,“灵”与“肉”的观念在女性文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通俗地讲,“灵”与“肉”就是心灵与肉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灵”即心灵,承载着人的情感与内在思想;“肉”即身体,承载着人的个体经验与种种欲望。“灵”与“肉”都是确立女性身份的要素,在女性的成长和现实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也是真实存在的,觉醒而又敏感的女性作家极力捕捉这一冲突,以锋利的笔触挖掘女性内在焦灼的心理状态,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饱满、个性鲜明的自杀者形象。
死亡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持有“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观,即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向死的存在,生就意味着走向死亡的必然性。而自杀,又是死亡的一种基本方式。什么是自杀?“任何由当事人自己完成并知道会直接或间接产生死亡结果的某种积极或者消极的行动都是自杀。”[1]心理学理论认为,自杀者往往处于价值观沉沦的状态或者在压抑感、沉重感的逼仄下失去生的希望的绝望状态,但又无力摆脱这种生命状态从而产生大量消极情绪,为了摆脱这种无力感、压抑感而选择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求得身心解脱。自杀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方式,它不单单是个人主观愿望的主动放弃生命,而且还是人物在面对生存困境以及精神困境重重围困下不得不做出的“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难题。本文拟围绕严歌苓的《天浴》、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迟子建的《秧歌》、蒋子丹的《绝响》四个文本进行分析论证。
一、“肉”的无可逃避——生存困境
死亡,是生命旅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生命的终点。作者以人生的终点为起点追溯女性自杀的灰色人生体验,通过对自杀形态的展示来展现逼迫女性群体走向自杀道路的生存困境。哲学大师萨特曾说:“他人即地狱。”也就是说,任何个体的存在都对他人的自由造成一定的禁制和束缚,而女性作为自古以来的弱者、被掌控者,生存空间受到父权、夫权、霸权等各方强权的挤压,存在价值和尊严受到剥夺,在恶劣的空间中以微弱之力苦苦挣扎,她们或是以离家的姿态来逃脱掌控的“叛逆者”,或是想要向家庭寻求庇护而不得的“寻家者”,最后都沦为无家可归和无处可逃的流浪儿。
《天浴》中纯真善良的知青文秀天真地相信放牧期到了就可以回场部,然而却成为被遗忘者,苦苦等待的是知青们相继返城的消息。回家成为她唯一的期盼。“一个女娃儿,莫得钱,莫得势”该如何回家?贫瘠的生活、无望的等待、男人狼性般的窥视、茫然四顾的无助,她仅有的资本就是令无数男人垂涎的年轻鲜活的身躯。供销员成为文秀的第一个目标,没想到恶梦却刚刚开始。场部能够盖章子、批文件的“关键”男人们一个接一个闻讯而来,将文秀当作满足自己兽欲的工具。为了回家,文秀不得不忍受种种野蛮的蹂躏和各色充满贪欲男人的索取和抛弃。一个弱势个体因为一个微小合理的愿望——回家,被一个叫做“男人”的野性动物以及占有霸权地位的群体占有、压榨。不仅回城遥遥无期,肉体也破败不堪,肉体的欠负愈多,精神的亏欠也就愈多,怀着仇恨和绝望苦苦央求老金扣下朝向自己的枪口扳机,回归洁净的世界,以“天浴”完成肉体的洗涤和尊严的救赎。
《何处是我家园》中塑造了两个离“家”女性形象,她们同子君一样是出走的儿女,也是无以为家的流浪儿。寄居于姑母家中的秋月始终是这个“家庭”的局外人,受到花花公子表哥明玉的欺骗利用和冷漠姑母的无情逼婚,秋月未曾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人的真情,只有在爱人宗子萧和好友风儿那里才能得到些许的温情。姑母的逼迫促使秋月决意逃离自己的寄居之所奔向爱人的怀抱,奔向“归宿之地”。在宿命的安排下,秋月与风儿惨遭几个粗鄙下流男人的摧残,秋月无颜面对爱人决意自杀未果,从此与风儿踏上颠沛流离的路途,告别过去的单纯生活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走上风尘之路。同样的悲剧在宝红身上得到延续,不谙世事的宝红与情人土坷为爱远走私奔,在秋月处寻求庇护。然而宝红受到因强权压迫而走投无路的秋月的诱骗,在掌权者何团长与地主查老爷合谋下失身。在情人的殴打、谩骂和侮辱,甚至是被抛弃的沉重打击下,视贞操如生命的宝红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下自缢身亡。
无论是文秀、秋月,还是宝红,她们一生都在追寻一个归宿,寻找一片栖息之地,寻找一方幸福之所,可最终都难以逃脱如风筝一样无处为家、没有归宿的悲剧命运。两个自杀的故事及两个“叛逃”的流浪儿,诠释了女性在父权、男权文化心理和霸权的生存困境中,女性自由自主的合理要求在现实中不能实现,只能以出走和自杀的方式逃离当权者掌控的世界,实现身体的自由和精神的皈依。
二、“灵”的无处安放——精神困境
如果说漂泊无依、无处可归是女性生存的外部困境,那么情感的无处安放及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看透男性本质后的大彻大悟就是自杀女性群体所面对的内在的精神困境了。《秧歌》中的秧歌少女小梳妆是队伍里亮丽的风景线,因为她曼妙的身姿,正月十五成为众人的期待,街巷里的人早早地便满满当当。拒绝做四姨太的小梳妆在年复一年的秧歌表演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和活力,坚守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承诺,在多年寂寞的等待中,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没有薄情的男人,只有多情的女人”。小梳妆的存在是小镇居民长久迷人的梦,为艰难苦涩的生活带来一抹绮丽的色彩。当青春不在,自己守候一生的爱情只是虚妄,老年的小梳妆终于看开一切,从爱情的梦幻中清醒,放下等待,平静地服用砒霜孤独凄凉地死去。
蒋子丹的《绝响》又是一则女性为爱而亡的悲剧爱情故事。作者以诗意笔调书写了“追求戏剧性生活效果”的诗人、知识女性——黛眉信徒般地固守爱情神话,自导自演一出天下无双的绝恋戏码和以从容的姿态殉情的凄美故事。然而,精心设计的殉情悲剧却充斥着荒诞的气息:一方面,黛眉费尽心思地为自己的死留下足够的线索,在她的预期中,葬礼上的那个男人会为她的死肝肠寸断、悲痛不已,但精心设计的“爱情绝响”的剧目也因男主角的缺席成为自欺欺人的闹剧;另一方面,因生前单位“黄花鱼”风波,总务长文大肥在追悼会上的出现让人们相信黛眉是因为心胸狭隘、斤斤计较想不开而死,没人相信黛眉是为爱情而死。
女性之所以是女性而区别于男性,不但在于女性的身体,而且还在于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状态、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张洁在她的小说《方舟》中直接写到:“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她总要爱点什么,好像她们生来就是为了爱点什么而活着。或者丈夫,或者孩子……否则她们的生命便好像失去了意义。”[2]与男性注重寻求民族、社会理想的英雄情结不同,女性寻求的是爱,是情感的乌托邦。看透了男人的本质,走出爱情神话,所以小梳妆平静地离世、黛眉满怀期许地自杀沉溺于“柏拉图式的爱情”难以自拔,她们的死揭示了女性在男性中心传统文化圈中永远走着一条“坚信爱情——固守爱情——死亡”的不归路,她们难以逃脱“爱与死”的情感怪圈。
三、超越死亡:“自杀”背后的现实关怀
柏拉图说:“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叔本华说:“弃生是超越生存空虚和痛苦的一种无奈的方式”。“自杀”作为死亡的方式之一,只是生命的终结和存在的消失,是肯定生命和爱情的另一种方式,是生命哲学的深化和延续。“死亡哲学具有人生观或价值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只有具有死亡意识的人才有可能合理有效地筹划人生,更重要的还在于死亡问题是个同人生意义或价值紧密相关的问题。”[3]超越死亡,以死思生,才能更好地把握生的价值,才能更好地支配人生。关于女性“自杀”的书写,作者并不是冷漠的“看客”,而是将身为女人的独特生活体验和感悟以及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注入其中。
(一)女性作家性别文化的自我反思
严歌苓、方方、蒋子丹、迟子建等作家满含着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以明确的女性身份进入文化视野,成为女性生存状况的探照灯、审视者,书写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对那些不隐讳自己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始’,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女性之真的拯救。”[4]45她们对“自杀”女性的书写,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禁忌。传统封建文化始终将女性镇压于地表之下,反对以生命抗争的女性自杀书写。自杀女性“缺席”书写的微妙原因,萧红曾经在《呼兰河传》中这样写道:“那么节妇牌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他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温文尔雅,孝顺公婆……”[5]尖锐地指出传统书写中对自杀女性真相的遮蔽以及对传统男权秩序的维护。如果女性的生存注定被淹没、被无视,那么写作就是一种拯救,它呈现出女性欲说却又无人倾听的话语。觉醒的女性写作者关注到最顽固的性别意识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下,权利、政治以及暴力合谋时对女性生存的压抑,呈现出对性别文化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叙事指向。
(二)对小人物的关注
新时期的文学中塑造了大量自杀女性的形象,有精神分裂的黄苏子(《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有以男性身份自居的姑爸(《玫瑰们》)、有家族女人郝童(《羽蛇》)……自杀女性的书写在裂解伟大叙事、经典叙事的同时,展现了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被男性叙事遮蔽或者始终被男性话语所无视的女性生存。被遗忘在马场的知青文秀、小镇秧歌队一员的小梳妆、众多农村少女之一的宝红、知识女性黛眉,她们都没有显赫的家室,没有耀眼夺目的成就,更没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她们只是一个普通的过着平凡日子的女人。因为普通,她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改变生存现状,她们渺小而无助,不曾被人关注、书写。秋月和风儿虽然逃离了包办婚姻的挟制,宝红对她二人悲剧命运的延续一再警醒她们的无处可逃、无处所归。通过对这些不被关注的女性在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中的挣扎、反抗、无处可逃、无处可归的描写,凸显女性个体生存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彰显作家对生命个体的广泛关注和人道主义关怀。
(三)女性面对困境的选择表现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通过描写女性“哈姆雷特式”的生死抉择,在“灵”与“肉”困境中的突围,突出生的价值,彰显作者对生命的终极关怀。陈染在《我看“自杀”》中对“自杀”场景加以解释:“我们的肉体虽然已经死去,它如同一滩烂泥无权要求什么,但是,那死去的人的尊严和感情没有死,依然渴望人们尊重他的愿望。”[6]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人格发展需要的五个层次进行划分,自杀也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其中文秀、宝红、小梳妆和黛眉均是为了归属和爱的需要而自杀。她们以对生命的终结表征自我主体的支配权,并从中获得自我认同和精神不灭。
女性作者们对女人在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面前做出的选择进行了现实层面的探索,她们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于他人之外的个体的存在,因此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和生活态度。面对过去的创伤,秋月和风儿选择了遗忘,活在当下,憧憬未来;宝红选择了终结过去,斩断未来,以死明志;面对爱情,黛眉选择一厢情愿地固守爱情泡沫,移情别恋的丈夫则继续无爱的婚姻;而小梳妆在穷尽一生的等待中终于大彻大悟。“如何活着”和“怎样生存”都是小说中人物的自由选择。作家们剥去道德审判的外衣,对持有遗忘伤痛、负重前行的秋月和风儿与保有尊严地死去的文秀、宝红都未给出鲜明的评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不评价恰恰是对人性的热切关怀。作家们对自杀的叙述触及生活最原始最本真的状态,最细腻的心里还原、人最合理的要求和对爱的渴求以及在父权、政权、霸权的逼迫下难以实现的尖锐的矛盾状态,给死亡赋予独特的价值。这种对生存和生命的关注,才是死亡背后作家真正的人文关怀。
曾有学者给女人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女人’仅仅是有史以来那个被奴役、被统治者——弱者群体。……但作为一个群体,女性却不知自己除了‘弱者’之外还是什么,除了以弱者的身份反抗强暴之外还能做什么。”[4]21因此她们不得不以“自杀”的方式向难以逾越的父权、不甚了了的男权、无处可逃的强权发出微弱但终究是反抗的战叫。她们是弱者,更是勇者。她们渴望自由、渴望自主,但这一合理要求在男权话语的现实中又是最无望的奢望,只能以牺牲肉身的代价实现“精神不死”的乌托邦追求。“死亡的价值主要是指向生的,正是有了希望才凸显生命本身的价值。死亡意味着对生的价值的认同和肯定。”[7]女性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展现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无情剖析了女性在性别方面所受的“精神奴役”,以女性面对生与死的“自杀”选择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吁求女性主体人格的确立。她们从生命终结的地方开始追问生命的真谛,对生命和生存的关注才是在超越死亡的力量背后最真切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