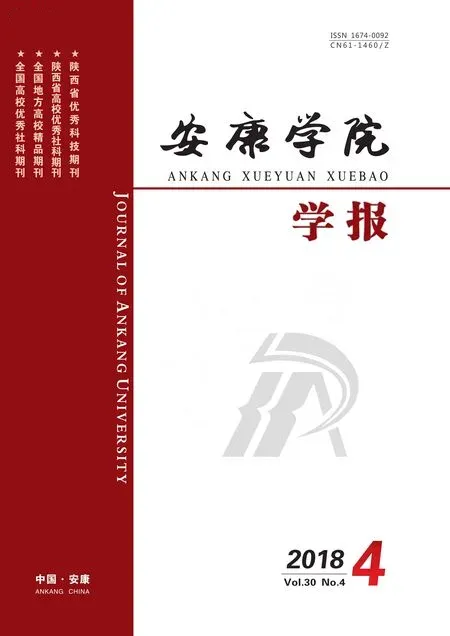重新认识《大雅·云汉》作为祝辞典范的价值
李豆薇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云汉》是《诗经·大雅》中的一首诗,共八章,每章十句。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视此诗为“诉天之词”,即言此篇是向天神表达诉求的言辞,在古代被称为祝辞或祝祷辞。刘勰《文心雕龙》的《祝盟》篇,即讲祝辞和盟誓的渊源流变。晚明贺复征编《文体明辨汇选》,收录文章七百八十卷,其中选有“祝文”八卷,关于“祝文”的性质,则引述刘勰《祝盟》篇开头第一段加以说明。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作《汤祷篇》,亦明确指出《云汉》与商汤的祷雨言辞一样同属于古代的祷雨辞①郑振铎《汤祷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东方杂志》,后收入《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对该诗的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关于这篇祷雨辞产生的时代,本文姑且仍按《毛诗序》所说,定为周宣王时代,即西周后期的文本。周宣王姬静是厉王、幽王之间的君主,在位46年(前827—前782)。虽然没有突出政绩,但处在厉王、幽王两位昏君之间,也没有大的过失,历史上称他为“中兴之主”。汉人依据《毛序》普遍认为该诗表现周宣王大旱之年的焦虑和忧民之心。如东汉王充《论衡》卷八《艺增》篇云:“《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也。”[1]所引诗句正是《云汉》中的名句。综合上述认识,本文尝试把《云汉》放在“祝文”体的发展脉络中,来理解其作为祝祷文的独特价值。
一、中国祝祷文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祝盟》开篇云:
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②本文所引《祝盟》篇原文均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5-177页。
古代皇帝即位天下,要祭祀天地及四方群神,此所谓“六宗”。“禋六宗”与“三望”一样属于特定祭祀礼仪。《国语·楚语下》:“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在男曰觋,在女曰巫。”[2]可见祭祀人员要选择那些聪慧爽朗之人,对神可流利陈词。所谓“祝文”,即祭祀神职人员对天神的祈祷性言辞,刘勰所谓“祝史陈信,资乎文辞者也”。常说文学起源于宗教,在祭祀天地神灵的仪式中,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体——祝辞。而“祝”,按《周礼·春官宗伯》的说法,就是负责向神灵祈祷的一种官员。
《祝盟》篇接着列举早期的祝辞形式:
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祝文之祖)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
伊耆即神农氏,他首先确立年终祭祀(蜡)的仪式,所祭者有“八神”:一是先啬,谷物之神;二是司啬,百谷之神;三是农,农耕之神;四是邮表畷,守望庄稼的神;五是猫虎,即食田鼠和田猪的猫神和虎神;六是坊,防水患的堤神;七是水庸,灌溉排涝的水沟神;八是昆虫,昆虫神①对“八神”的解释参阅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八神之名和所引的祝辞都出于《礼记·郊特牲》。虞舜祭田的言辞见《尸子》:“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3]771可以看出,记载于古代典籍中的祝辞都相对简单,但都是比较正式的“四言”,且有押韵特征。所以刘勰将“祝辞”置于“文”类(有韵者)。
《祝盟》接着专讲商汤的祝祷行为及祝辞:
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素车祷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禜②《说文》:“祷雨为雩,祷晴为禜(y ǒ ng)。”之文也。
“圣敬日跻”出于《商颂·长发》,是说商汤圣敬之德与日俱进。关于商汤“玄牡告天”的行为,最初记载于战国初年的《墨子》一书,其《兼爱下》篇云:“虽汤说即亦犹是也③孙诒让《墨子閒诂》卷四注此句云:“《周礼·大祝》六祈:六曰‘说’,郑注云:‘说,以辞责之,用币而已。’此下文(《墨子》下文)亦云‘以祠说于上帝鬼神’。若然,说礼殷时已有之。”“说礼”即以言辞沟通上帝的祭祀仪式。“祝辞”即与“说礼”相应,有“说礼”之时就有了祝辞。“祝辞”中的问句即“以辞责之”,所以早期祝辞多问句。。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4]。商汤名履,大旱之年,他“以万方罪己”,表示愿意以己身换取上天对下民的宽恕,他所说的话,就是典型的“郊禋之词”,即后世的“祝辞”。战国末期《吕氏春秋·顺民》中对商汤罪己行为的描述更加具体,“昔者汤克夏而正(治理)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酈其手④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以为“酈”当为《庄子胠箧》“攦工倕之指”之“攦”,还有《天地》篇“则是罪人交臂歴指”,以木夹十指而缚之。故“翦发”“酈指”俱罪人之形,有向天请罪之意。,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5],其彰显了商汤以己身为牺牲,精诚感动上天的行为。这样的仪式成为后来君主们纷纷效仿的行为。《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陆贽传》就记载陆贽曾上疏德宗皇帝:“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皇帝果然下“罪己诏”,结果“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6]。到西汉末年刘向《说苑》卷一《君道》篇还附会出汤祷的祝辞:“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7]从中可以看出,汉代祝辞以四言问句为主,这种形式更便于表达一种反省罪己之意。
刘勰所说的“素车祷旱”出自战国中期楚国人尸佼所著《尸子》:“汤之救旱也,乘盖素车白马,著布衣,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当此时也,弦歌鼓舞者禁之。”[3]432这也是对商汤祷旱行为的想象性描述。《荀子·大略》记汤之祷辞云:“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8]刘勰所谓“以六事责躬”的六事,即“政不节、使民疾、宫室荣、妇谒盛、苞苴行、谗夫兴”,这些被认为会招惹上天的不满而导致水旱灾害,国君和大臣都需要尽力避免。到汉代何休注《公羊传》时,将此“六事”推衍为一般政治行为。其“桓五年传”注云:“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使男童各八人舞呼雩,故谓之雩。”[9]由此可见,以问句为主是早期祝辞的主要特征。
二、《云汉》作为西周的祝辞
朱熹《诗集传》卷十八录《云汉》,原文如下:
倬(高大) 彼云汉,昭(明亮) 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向所有神都祷告过了),靡爱斯牲(献上肥牛、白羊之类的牺牲)。圭璧既卒(最珍贵的圭璧也呈上),宁莫我听(难道神还不宽宥吗)?(一章)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天还不雨,暑气蒸人)。不殄(绝)禋祀,自郊(祭天地) 徂宫(祀祖宗)。上下(天地) 奠瘗(将祭品埋在地下),靡神不宗(从郊外到庙宇,什么地方都祷祝遍了,什么神都求遍了)。后稷不克(管),上帝不临(仍然不雨,祝祷无成效)。耗斁(耗败,糟蹋) 下土,宁丁我躬(王愿以己身承担;一说我这一生竟碰上如此大旱)。(二章)
旱既太甚,则不可推(除去)。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在上天面前忧惧之甚)。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喻干旱引发饥馑疾疫,使人口大量减少)。昊天上帝,则不我遗(喻老天不肯为我留存人民)。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三章:可怕的大旱,一切都枯焦了,人民恐怕要没有孑遗了。上帝不眷顾我,祖先也不保佑。最后两句甚至说:怎么能不害怕?先祖的祭祀恐怕要断绝了)
旱既太甚,则不可沮(止)。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干热无处躲避)。大命(国运)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祖先),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四章:和上章一样,指出大旱的严重——死亡将至。呼吁上帝祖先神灵保佑)
旱既太甚,涤涤山川(草木枯死之状)。旱魃(旱神)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遯(逃)?(五章)
旱既太甚,黾勉(辛勤)畏去(畏旱而逃去)。胡宁瘨(灾害)我以旱?憯(竟然)不知其故。祈年(春天祝丰年的祭祀)孔夙(早),方社(祭四方)不莫(暮,晚)。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王那样恭敬于神,神该没有什么悔怒吧)。(六章)
旱既太甚,散(乱) 无友(有) 纪。鞫(穷)哉庶正(百官之长),疚(病)哉冢宰(宰夫)。趣马(主管王室马政之官) 师氏(司察朝廷得失之官),膳夫(管理君王饮食的官) 左右。靡人不周(赒,赈济)。无不能止,瞻卬(仰)昊天,云如何里(忧)!(七章:大旱太甚,无计可施。什么人都访问遍了,什么办法都想了,但没有人能够阻止,仰望霄汉,仍没有纤云——一种面对大旱的焦虑心情被写出来)①《云汉》第七章提及许多官名,屈万里《〈诗经选〉选注》以为本章的意思是:“这次旱灾,弄得百官都非常困苦,虽然每个人都被救济到,但并不能解除他们的贫困”(中正书局,1976年版,第281页)。这个解释虽然吻合“鞠”“疚”的字面义,但与实际不符。应该指这些官员都参与赈济下民,赈灾之事使他们既贫且病。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明亮的星星)。大夫君子,昭假(祭祀) 无赢(过失)。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定)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八章:仰望天空,繁星满天;所祷求的何曾为我个人,实在是为了安定百姓。老天啊,何时才会赐予安宁的日子?)
《毛诗序》云:“《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指出此诗是周大夫仍叔对周宣王在大旱之年忧民情状的摹写,属于纪实性作品。而朱熹《诗集传》卷十八释《云汉》云:“旧说以为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佩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仍叔作此诗以美之。言云汉者,夜晴则天河明,故述王仰诉于天之词如此也。”[10]“旧说”指《毛诗序》的说法,朱子未置可否,“言云汉者”以下是他的新解,所谓“诉天之词”明示此篇为告神之祝辞,且言辞优美,反复称说,属于有“文”之辞。相形之下,上引伊耆和商汤的祝辞,只不过是残简断片。从文体演变过程看,《云汉》标志着祝辞由只言片语的直接叹唱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文章形式。
首章前两句相当于祝辞的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描述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之景致。大旱持续,庄稼枯萎,此种天象让王十分忧虑。“王曰”以下为祝辞正文,其四言句式符合西周以来的常规文言,多以“胡”“宁”等词引起反问语气。其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等语句,显示一场旱灾之下,周代国王焦虑惶恐之情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焦虑。中间六章均以“旱即太甚”发端,向上天反复申述着一种惨痛的事实,以引出哀求之辞。末章为总结,为收束,再一次仰望昊天,发出最后的祈求,而且声明:这不是为自己,而实在是为了黎民百姓。
周人灭商之后,商代一些优秀的政治传统被继承下来,其中就包括汤祷罪己的祭祀行为。据《尚书·周书·金滕第八》记载,一年秋天,成熟的庄稼遭遇雷电大风,邦人恐惧。成王与大夫穿上朝服打开周公所留下来的金滕之书,见周公当年愿以己身替武王去死之说,成王认为天降灾害是为了表彰周公而提醒自己不敬之罪。这段文字经太史公改写后写在《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中,写成王罪己郊祀:“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熟)。”[11]可见周朝每遇天灾,总是国君出郊,向上天祷告,而祷辞则延续了商汤以来的那种罪己、责问等元素,只是《云汉》中的求乞成分明显多于往代。总之《云汉》是迄今所见的周代祝辞中最典范的一篇。
三、《云汉》的典范价值
《云汉》在祝辞发展历程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典范价值,只有把它与后世祝辞进行比较方能看出。刘勰《祝盟》篇评春秋以降的祝辞云:
自春秋以下,黩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至于张老成室,致善于歌哭之祷;蒯瞆临战,获佑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者也。
表明祝辞在周宣王《云汉》之后有两大变化,一是出现了一些“黩祀”“谄祭”现象,即不再依赖庄重的祝辞表达对上帝的诚意,而直接以钱币求媚于神;二是祝祷的目标与对象下移,祝辞的形式也发生变化。刘勰举了两个例子,其一见于《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诸大夫发礼以往)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谓之善颂善祷”。这一段被清人选入《古文观止》卷三中,题为《晋献文子成室》。晋献文子即被称为“赵氏孤儿”的赵武,为晋国名臣赵衰、赵盾的后代。他被封官后建造新宅。宅成后同僚前来祝贺,张老的祝辞不同凡响,三个“于斯”祝贺赵氏宗祖受到祭祀,赵氏家人可以迎来送往,赵氏宗室得以复兴。“全要领”表明赵武决心勤谨行事,以免家族再遭杀戮之祸。张老的祝辞因为切合赵氏家族的遭际,并表达了对未来的祝福,被称为“善祷”之辞。但毕竟不关乎社稷大事。其二见于《左传》哀公二年:“卫大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12]卫国太子蒯聩因请人刺杀父亲的宠妃南子夫人,而被父亲驱逐出境。此时他随晋国大将赵鞅讨伐郑国。祝祷之前,先向先祖申述事由:郑声公(胜)作乱,威胁晋国安全,赵鞅讨伐,我蒯聩义不容辞,亲临战阵。“敢告”以下表达心愿。周代祝祷必敬献以璧、珪,蒯聩拿佩玉以献,祈求祖先保佑不伤及筋骨皮肉。实为一个胆小鬼在请求祖宗保命,《左传》记下这段行事,实则对蒯聩表示讽刺。这两个例子可佐证后世祝辞的多样化趋势。刘勰对汉代祝辞的评价,也参照“成汤之心”,《祝盟》云:“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礼失之渐也。”他以为汉人祭祀山川百神的祝辞虽出硕儒之手,但到后来则参杂了方术,多以长生久视求告于神灵,有失祝辞为黎民祈福之本义。又如《史记·封禅书》所云:“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将罪过转移给臣下,又有失“罪己”之担当精神。
在战国祝辞中,刘勰表彰了宋玉的《招魂》,称其为“祝辞之组丽者”。《招魂》一千七百余字,为宋玉为招屈原之魂而作。其时屈原被无罪放逐,宋玉有为其师祈福延寿之意。全文有小序、正文四段和“乱曰”一段构成①本文所引宋玉《招魂》原文及分段参阅今本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0-1554页。。小序前六句代屈原声口道出“离(罹)殃愁苦”之意。于是托为巫阳招其魂魄以归之。正文第一段“去君恒幹,何为四方些”,以反问句阻止魂魄向四方离散,以神话中食人怪兽为意象,极言东、南、西、北、天上、地下都不能去。第二段假设屈原魂魄已归来,由巫阳(男巫曰祝)导引入城门(修门)。又以“容像”设于私室,便于魂魄识容知归。然后备言宫室之美。先说“高堂邃宇”的位置及外观,再言其冬暖夏凉——冬天置灶(突)于室外,火气自下而入,即成温室;夏天则“川谷径复”,风光宜人。“经堂入奥”以下讲卧室之美,“华容备些”以下又极言侍寝者容态之美,最后又进一步陈述园林果蔬之美。与第一段敷叙令人惊恐的情状不同,此段尽显华美优雅温馨之状。第三段假设魂魄归来,当有酒食之设:先写食材有稻、麦、黄粱,味则咸酸辛甘具备,还有飞禽走兽制作各种精美佳肴,再劝以美酒。第四段写饮宴中又有女乐歌舞相与为乐,演唱《涉江》等楚地优美乐曲,此间“士女杂坐”,极尽人间之乐。最后“乱曰”一段收束,摹拟屈原魂魄归来后在春天的云梦泽与楚王射猎的情景。“招”与“祝”音近义通,“招魂”即祝魂,故《招魂》可视为言辞“组丽”的祝辞。
刘勰对中国祝辞传统的描述实际上创立了一种评价祝辞的标准,而祝辞在后世要发展演变为一种文体,就必然需要确立典范之作,宋玉的《招魂》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范例。《云汉》作为产生于中国祭天仪式已高度成熟的西周后期,其本身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也高度成熟,堪称祝辞之典范形态。而刘勰《祝盟》却为何没有提及此篇?原因是此篇早已作为反映周宣王忧民美德的诗篇,被编《诗》者收入《大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