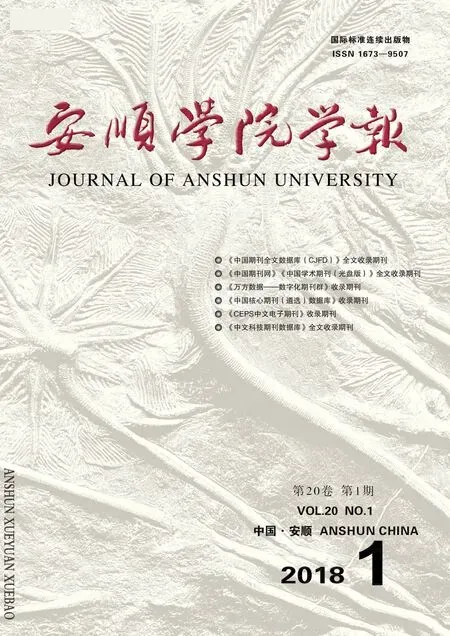国外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新动态
——以英国《民族志与教育》(2006—2015)为中心
(凯里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贵州 凯里556011)
教育民族志(educational ethnography)是指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它既是一种研究过程,又是一种结果呈现。然而,在科技迅速发展、前沿学术思潮侵袭和学科间交互作用三因素交互影响下,现今教育民族志已突破以往的工作方式和思路。研究建立在对英国《民族志与教育》2006年至2015年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阐述近年来此方法的发展态势。《民族志与教育》创刊于2006年,是在英国教育人类学发展中孕育而生,并在2008年被民族志与教育国际性组织纳入麾下。它旨在刊出民族志研究论文,其中包括研究者对教育民族志方法的反思和民族志方法对教育现象问题的分析两类。鉴于此,作为一种能很好窥探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文本,研究以民族志方法的工作流程为线索,从三个方面展开阐释。
一、研究者田野点的进入以及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建立
进入田野前,研究者首先需要找到工作的切入点,与研究对象建立关系。在学校民族志研究里,教师往往扮演着重要的“当事人”角色,成为访谈或观察的首选。但是,调研对象是否应该打破参与者仅限于教师的做法,让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其中?譬如,博比·卡布图(Bobbie Kabuto)主张父母参与研究,因为这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家、学校和社会是如何影响孩子们学习、认同形成和意识形态倾向的[1]。再有,熟悉田野点(‘the field’ location)和所在居民的情况是民族志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戴安娜·米尔斯坦(Diana Milstein)在考察国家政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所小学如何推行时发现,孩子们对世界的认知异于成人,因为他们的部分“时空”尚未被完全融入成人“约定成俗”的社会里[2]。由此,不仅儿童会从自己生活的世界里提出对一个事件的不同认识,而且研究者可对他们的想法进行区分和联系。黛博拉·塞格洛斯基(Deborah Ceglowski)和特丽莎·马科弗斯基(Trisha Makovsky)首先肯定了儿童作为共同研究者参与民族志研究的做法,并尝试将双重民族志(duoethnography)①用于低收入家庭儿童的调查中。他们认为,儿童会从自己生活的世界里(学校、贫穷、电视、技术和家庭)提出对事件的不同看法,而这给研究工作提供重要参考[3]。娜塔莉·贝兰格(Nathalie Bélanger)和克莉斯汀·康奈利(Christine Connelly)等用三年时间,研究加拿大一个半城市化、少数人讲法语、文化多元的天主教小学生中认同生成过程。他意外发现,真正的知情同意远不应停留在解释层面,还应让孩子积极参与其中[4]。
在与研究对象建立联系的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相处模式和融洽度关键还取决于彼此的身份。每个人都会因自己家庭的出生而被赋予一定的种族、宗教等文化背景,这势必奠定了他们日后与人交往的基础。也即是说,不同信仰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种族的、不同社会阶层的研究者对待某些事物或事件看法势必会产生分歧,甚至冲突。而这一点对于研究者而言,问题尤其突出。譬如,夏洛特·查德顿(Charlotte Chadderton)在研究伊始,就想尽力摆脱作为一个白种人研究者常持有的“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的态度,可他最后意识到:从学校领导介绍“入场”到访谈问题提出的整个过程,不仅没能去“白人至上主义”,反而在不知不觉中强化白人身份[5]。由此,研究者应该在“承认所有人都被种族结构化”这一事实上进行田野资料搜集,以一种平常心态、坦诚布公地待人处事方为研究上策。塔希尔·阿巴斯(Tahir Abbas)通过对89个南非学生和其中部分家长深度访谈,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种族身份的异同深深影响着访谈效果。譬如,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会因共同种族身份更易建立信任,而这有助于访谈者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6]。此外,O.马蒂(O.Marty)通过对自己前后四次田野工作的反思,提出作为一名在高校谋职的教育民族志者会面临三种认识上的距离(epistemic distances):一是离田野工作的文化距离,即民族志学者的参与研究度;二是离科学共同体的距离,即平时岗位工作的付出;三是离自我的距离,即前两者双重距离带来的舒适度。最后,他并将其设计成一种三角模式,以用来观测研究者的职业发展轨迹[7]。
二、田野工作的策略及技术手段的使用
田野工作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协商的动态过程,而这就意味着原计划中存有诸多不测与变动。一般研究者总是隶属于某大学或研究机构,也就是他被赋予一定的职业身份。当他或她在某单位机构,尤其自己所在单位调研时,更应审时度势地变换自己身份;当他或她在面临特殊研究对象时,也应根据研究或研究对象需要随时变更不同角色。譬如,韦·洛·约(Wee Loo Yeo)作为一个田野点里的“局内人”(insider),在调查英国圣安德鲁语法学校国际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状况时,自己身份发生三次位移:从曾经拥有国际留学生经历的生活辅导员身份到国际留学生(亚洲)的亲密朋友身份,再到该项目的研究人员[8]。米凯拉·布罗克曼(Michaela Brockman)对来自德国和英国的16名学徒身份的年轻人进行调查,并分别经历了“边缘成员”角色(‘peripheral member’ role)、积极角色(‘active’ research role)、模糊角色(‘ambiguous’ role)三种状态[9]。他总结认为,研究者身份的转变主要依据研究环境中线人与研究者关系,而它是流动的、脆弱的、在变化中不断被构建的。
研究者“进入”不仅意味“来到”(going into)一个田野点,而且要求研究者将自己转变为资料收集的工具。访谈是田野工作中常用的方法,但是它总是因访谈者与被访谈者话语支配权力问题而引发争议。简·希金斯(Jane Higgins)等一反常规,采用了“反履历”(anti-Curriculum Vitae)(又即身份文件夹,identiportfolio)来探讨新西兰新“自由主义一代”从学校毕业后的生活过渡期中的认同努力(identitiy work)[10]。文件夹存放照片、视频、作品和图像等类似媒介,给予年轻人充足时间用翔实的资料来表达自我,充分发挥了被研究者的主体作用。
田野笔记是民族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沃尔福德通过问答方式总结了四位著名研究者的心得,认为研究者要根据各自研究的方向和偏好,结合特定调研情境,采取不同策略记录[11]。比如,在现场速记方面,保罗·康诺利(Paul Connolly)主张详细记录信息,他认为根据研究目的及随后的思维启发,许多信息会“活跃”再现;鲍勃·杰弗里(Bob Jeffrey)和洛伊斯·韦斯(Lois Weis)主张记录可以含糊些,避免让被研究者看懂;从事教师和学校研究的德拉梅特主张计时结构记录方法。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通讯交通手段的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上日渐便捷。第一,影像拍摄使在同一时点或多地点展开两项以上的工作成为可能,并且与传统的参与观察和访谈相得益彰,彼此相互印证、补充。但是,研究者要注意被研究者的参与意向,及时采取技术处理,例如从不同方位取景或避免单人照拍摄。第二,作为一种实践和呈现教育研究的方法,数字视频(digital video)改变了文本、作者与观众或读者的关系,证实了观察对象的存在性。第三,线上线下调查交流成为研究的渠道,突破了实地田野工作与虚拟民族志在方法上的对立关系,关键模糊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鲜明角色的关系,并改变彼此的话语权。由此,建立在高技术手段基础上,有的学者用多媒体进行了跨国多田野点的实践研究,缩短了研究工作周期。譬如,凯思琳·加拉格尔(Kathleen Gallagher)和巴里·弗里曼(Barry Freeman)尝试用数字化多媒体对加拿大、美国、印度三个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五个田野点(加拿大两个)处于劣势地位学校的戏剧课进行调查[12]。克拉拉·鲁布纳·约根森(Clara Rübner J rgensen)用民族志方法对英国和西班牙移民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问题,认为跨国民族志的比较研究可使田野过程中既定的研究主题情景化,还使相关概念及其分类通过不同环境理解得到丰富。此外,一些网络游戏和交流方式也成为重要沟通途径[13]。萨莉·贝克(Sally Baker)认为,作为交流手段,脸谱网(Facebook)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访谈,成为一种新颖而独特的工具[14];塞布丽娜·菲茨西蒙斯(Sabrina Fitzsimons)以“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为平台对“高等教育的教与学”进行研究[15];沃伦·基德(Warren Kidd)在线长达18个月,对初任教师从岗前培训到初次授课的经历进行研究,认为博客(blogs)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民族志研究工具[16]。
三、研究结果的呈现及应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民族志研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主张维护事物多样化,不固守一个特定表达结构模式。这一点凸现在民族志结果表现上。卡尔·贝利(Carl Bagley)主张用艺术方法呈现或展现民族志教育研究资料。他在 “确保开端”项目(Sure Start)中将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定义为“导演-丑角”(impresario-joker),并以此为线索叙述了从制作到演出的全过程[17]。吉姆·米恩扎科斯基(Jim Mienczakowski)首肯表演民族志的合理性,提出可在表演正式上映前安插“托儿”,以便在放映过程中为剧情营造气氛,使观众完全耽溺于表演中,以促进观众、表演者和研究者间动态联系[18]。在表演民族志评判标准上,安德鲁·斯巴克斯(Andrew C. Sparkes)在比较标准逻辑取向和相对论取向两种主张利弊的基础上,提倡为了更好地欣赏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民族志的多种艺术形式,研究者必须努力地提升自己的鉴赏力(the quality of connoisseurship)[19]。
除了表演民族志这一呈现方式外,谢尔斯蒂·范斯莱凯-布里格斯(Kjersti VanSlyke-Briggs)指出,民族志小说具有不需要研究者避开情境冲突和外在情绪,能更深刻洞察问题,做出价值判断等诸多优点;但是,由于它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所以更多倾向文学的创作而非事实观察[20]。彼得·克拉夫(Peter Clough)则以讲故事的艺术方式,讲述了一名叫查理·科克(Charlie Cork)的教师,因上课过程中的“不良提问”而被女学生诬告,最后被迫辞职从农的人生经历[21]。艾莉森·菲普斯(Alison Phipps)和莱斯利·桑德斯(Lesley Saunders)则以对话方式探讨了诗歌如何能在教育和教育研究方法中的重要价值[22]。
沃尔福德承认,随着社会的瞬息万变,传统的民族志正在发生变化。他一方面力陈民族志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法;另一方面介绍了当下学界风行的自传式民族志和表演民族志的不足[23]。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要求民族志研究者必须遵循严谨的研究方法,以一种系统而清晰的方式呈现民族志成果。基于诸多学者对自传式民族志的“自我迷恋”,德拉梅特指出,自传式民族志不能达到社会科学的核心目标,因为:其一,从人类学角度看,不能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其二,基于道德问题,自传式民族志不能公开出版;其三,自传式民族志注重体验,缺乏对结果的分析;其四,反省不能替代资料收集[24]。可见,该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志的成果讨论上,其中表演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一种行动方式、一种批判方式和一种公民权利诉求的方式得到推崇,此外小说、故事和诗歌三种方式也以案例形式得到提及。对这些新兴的呈现方式,沃尔德福反复强调了要保持民族志研究一贯的精准性和严谨性。
同时,有研究者对最终研究成果出版产生的“余震”产生质疑,约翰·贝农(John Beynon)甚至将其视为“草丛中的蛇”(snaks in the swamp),给人出其不意的效果一样[25]。的确,即使民族志研究者穷尽其力恪守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当研究结果公诸于众后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道德问题。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当民族志成果出版后,研究者在若干年后却极少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回访,形成了“到来-拿去-离开”的研究轨迹。一系列令人深省的问题接踵而出:应该设计一个怎样的伦理道德指南才能防范研究成果出版后产生的不良后果?研究者的伦理责任应该在哪个环节结束?
总结
可见,以上研究都是建立在研究者对自己或他人田野过程或成果反思的基础上,主要体现于资料搜集与成果两阶段。而这一趋势在1974年保罗·拉比诺完成《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时是难以预测到的②。因为就当时研究气候而言,该书的出版曾遭到拉比诺导师格尔茨的极力劝阻,但是它的问世却是“语破天惊”。所以试想,倘若今天拉比诺看见《民族志与教育》上呈现出来的对教育民族志反思的写作范式,会感到何等欣慰。
具体而言,这种新的写作范式并没有停留在民族志研究“是什么”(what is),而是“如何做”(how is)的问题层面上,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尤其明显,以上有三点引人关注:第一,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许多貌似“客观”“合理”“权威”的观点遭到质疑。“儿童”(或学生)作为他者的一个例证走入研究者视野,他的特征和身份是成年人和人类学家在二元关系中用以建构他们对世界和自己认识的材料[26]。家庭作为学生生活栖息的关键场所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点,而家长作为他们成长的重要当事人参与研究中。此外,在展开调查前,研究者对自己“身份”毫无隐晦的剖析得到主张;因为这是研究者能与研究参与者建立联系的关键所在,是研究者获知“搜集资料和研究结果所以为如此”的原因所在,更是研究者以诚相待的关键所在。第二,“传媒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传统小型的、一体化的分离群域或社区被大型的全球化、国家化、多元化的力量渗透与连接。”[27]在人类学学科中,研究者们将多媒体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应用于研究实践中,享受与参与者时空对话带来的便捷。可以说,虚拟网络将不同时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实现跨时空的对话交流,缩短了研究周期和繁琐程序。当然,虽然虚拟网络的到来让许多不合法、不道德举止乘虚而入,但瑕不掩瑜。第三,现今“跨学科”不仅作为术语频频出现在学术领域,而且作为现象涌现于各学科。这不仅是社会应对整体问题思考的需要,也是某些研究领域永葆生命力,走在学术前沿的不二法门。教育人类学的跨学科触角也为其他学科借鉴(如艺术学、文学、政治学等),同时在符号互动、批判行动理论等的感召下,民族志的多种呈现方式纷至沓来。不得不承认,随着社会的瞬息万变,传统的民族志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正如沃尔福德认定的:无论如何,民族志研究者必须遵循严谨的研究方法,以一种系统而清晰的方式呈现民族志成果[28]。
注释:
①双重民族志是一种新的质性研究形式,包括两要素:一是两个或三个参与者,也即他们共同分享一个相似的生活经历;二是彼此间的对话,也即参与者们就他们相似经历或不同经历分享自己的观点。详情请参阅Deborah Ceglowski and Trisha Makovsky,“Duoethnography with children,”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7,Iss.3 (2012), pp.283)。
②保罗·拉比诺曾感叹道:随着田野作业的最初动机和它越来越理所当然的地位之间进一步偏离,田野作业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通过仪式”或诸如此类的仪式,无须被公开审查。问题是迟早要被提出来的。如果人类学这一学科依赖于参与观察或民族志田野作业,那么为何我们会这么少关注田野作业的本质和田野作业的经历?详情请参见美国学者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高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页)一书。
参考文献:
[1]Bobbie Kabuto.Parent-research as a process of inquiry: an ethnographicperspective[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3, Iss.2(2008):177-194.
[2]Diana Milstein.Children as co-researchers in anthropological narrativesin education[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5, Iss.1 (2010):1-15.
[3]Deborah Ceglowski,Trisha Makovsky.Duoethnography with children[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7, Iss.3(2012):283-295.
[4]Nathalie Bélanger,Christine Connelly.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in child-centered research about social difference and children experiencing difficulties at school[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2, Iss.1 (2007):21-38.
[5]Charlotte Chadderton.Problematising the role of the white researcheri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7, Iss.3 (2012):363-380.
[6]Tahir Abbas.A question of reflexivity i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SouthAsians in education: power, knowledge and shared ethnicity[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1, Iss.3 (2006):319-332.
[7]O. Marty A model of distance analysis. Epistemic field notes for education ethnographers[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10, Iss1 (2015):17-27.
[8]Wee Loon Yeo.Ethnographic positioning in a boarding house setting[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5, Iss.1(2010):111-122.
[9]Michaela Brockmann.Problematising short-ter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and multi-method ethnographic studies[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6, Iss.2(2011):229-243.
[10]Jane Higgins, Karen Nairn and Judith Sligo.Alternative ways of expressingand reading identity[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 Iss.1 (2009):83-99.
[11]Geoffrey Walford.The practice of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Iss.2(2009):117-130.
[12]Kathleen Gallagher, Barry Freeman.Multi-site ethnography,hypermedia and the productive hazards of digital methods: a struggle for liveness[J].Ethnography andEducation, Vol.6, Iss.3 (2011):357-373.
[13]Clara Rübner J rgensen .Three advantages of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from a study of migrants and minority ethnic youth in English and Spanish schools,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10, Iss1 (2015): 1-16.
[14]Sally Baker.Conceptualising the use of Facebook in ethnographicresearch: as tool, as data and as context[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8, Iss.2(2013):131-145.
[15]Sabrina Fitzsimons.The road less travelled: the journeyof immersion into the virtual field[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8,Iss.2(2013):162-176.
[16]Warren Kidd.Investigating the lives of new teachers throughethnographic blogs[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Vol. 8, Iss.2(2013):210-223.
[17]Carl Bagley.The ethnographer as impresario-joker in the(re)present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s performance art: towards a performance ethic[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 Iss.3(2009):283-300.
[18]Jim Mienczakowski.Pretending to know: ethnography, artistry andaudience[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 Iss.3 (2009):321-333.
[19]Andrew C. Sparkes.Novel 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and thedilemmas of judgement[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 Iss.3(2009):301-319.
[20]Kjersti VanSlyke-Briggs.Consider ethnofiction[J].Ethnography andEducation,Vol.4, Iss.3(2009):335-345.
[21]Peter Clough.Finding God in Wellworth high school: more legitimationsof story-making as research[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 Iss.3(2009):347-356.
[22]Alison Phipps and Lesley Saunders.The sound of violets: the ethnographicpotency of poetry [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 Iss.3(2009):357-387.
[23]Geoffrey Walford.For ethnography[J].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 Iss.3(2009):271-282.
[24]Sara Delamont.The only honest thing: autoethnography, reflexivity andsmall crises in fieldwork[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Iss.1(2009):51-63.
[25]John Beynon.Return journey:snakes in the swamp[J].Ethnography andEducation, Vol.3, Iss.1(2008):97-113.
[26](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4.
[27]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65.
[28]Geoffrey Walford.For ethnography[J].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Vol.4, Iss.3(2009): 27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