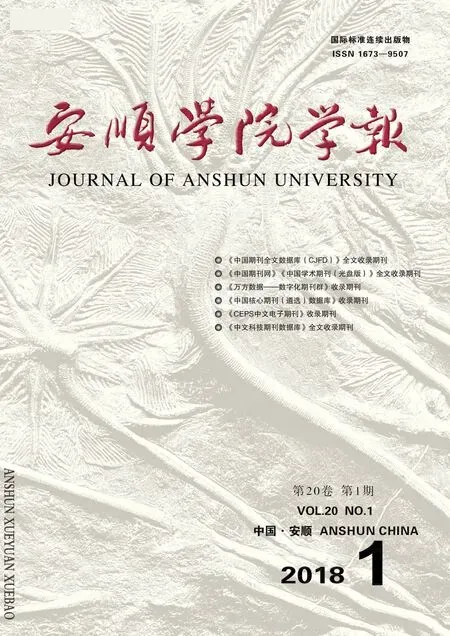儒家经典与“汉家故事”
——汉代奏议中的二重倾向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08)
两汉奏议“依经引义”的特点,早已为学人所关注并反复讨论;而现存汉代奏议文本中的另一主要组成成分“汉家故事”或“旧事”,却较少为人所留意。从西汉中期开始,“故事”逐渐和儒家经典一样成为汉代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话语形式;二者作为刑法、吏治、礼乐等国之大事的处理依据,其述作辑录、储藏管理和流传接受都受到重视。两汉奏议中,经典与“故事”呈现出一种相反相对、相辅相成的复杂关系,其实质是权力的斗争,知识和思想的冲突与交融,及以儒为主的知识分子逐渐适应大一统一人专制的家天下社会中“士大夫”角色的艰难历程。
一、“故事”字义溯源与词义演进
“故事”两字连用,大约发生在战国中晚期。现存资料中,最早见于书面记载的有《战国纵横家书》“且复故事,秦卬曲尽听王”[1]44;又《商君书·垦令》:“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2]19。
许慎《说文解字》:“故,使为之也。从攴,古声。”[3]123案《诗经》中共出现“故”字11次,其中9处用为本义,如《邶风·式微》“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4]98、《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4]464,皆表因某人某事而使某者做出不发自主观意愿的动作。又《小雅·占梦》:“召彼故老,讯之占梦”[4]566,所谓“故老”,亦为群体中某一类拥有驱使他人的权力或威望之人。或者组成这一类人物的个体,他们最普遍的“感性内容”便是年岁之长,由此渐渐引申出时间上的 “故旧”之义。则作为引申义的“故老”和“故旧”,与“使为之”的意义并未完全分离,而涵容了现存的“我”认知中的实有的“人事”与“强制力”两方面内容;且于时间上相去不远,与笼统、抽象的“古”不可一概而论。又《说文解字》:“事,职也。”[3]116-117“事”在《诗经》中共出现53次,其中“王事”出现18次,如《邶风·北门》“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4]111、《唐风·鸨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4]323,指的是人在社会或一统治集团内部与其地位相称的事务,即就阶级中地位相对卑下者而言的事奉王公、邦国的具体职分。因而“故事”的意义,一从时间上讲,属于某个或某类地位相对卑下者而言的“故有的分内之事”,亦即“原本固有”和“理所应有”的结合义。故《商君书》与《战国纵横家书》中的“故事”,前者为法家“一于农战”政策下,视农民为纯粹的可计数的劳动力,因而需要他们“无从离其故事”,继续耕种纳粮的本职工作;后者为说客在五国攻秦的形式胁迫下游说齐国国君所使用的恭谨之辞。
秦汉以降,“故事”逐渐成为人们习用的语汇,语义也有所变化。侧重于“故事”中“故”字的“故旧”之义,词义则接近于“历史上的事件”,并由杂史杂传的发达衍生出“小说故事”义;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5]61,又《滑稽列传》载褚少孙曰“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5]729。而这些“历史上的事件”中,又以著于竹帛的诏令、奏议、笺记等种种文书形式,容纳了一朝代的社会面貌、政治结构和种种具体政务的“处理惯例”,于是从西汉开始,它们逐渐也被总称为“故事”,并成为史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这是取“故事”一词原义中“原本固有”和“理所应有”之义,与“旧事”“旧制”“旧典”等相类。
二、儒家经典与“汉家故事”的系统形态
我们这里所说的儒家经典,是指以六艺及其说解为核心,以《论语》《孝经》等汉代儒家思想普及的重要文本为辅翼的经学系统,主要由三个系列构成:一为西周王官知识和贵族教育的传统内容,包括《诗》《书》《礼》《易》等古经部分;二为孔子的述作和对经典的传习、解读,包括《春秋》经文、《论语》的大部分内容及其它经、传中散落的记“说”等部分;三为孔门后学的著述论说,《孟子》《论语》中小部分内容和其他古经的传、说——如《韩诗传》《公羊传》等,当属此列。三个系列,虽然文本内容本身便纠缠不清,又因政治干预、史料淆乱、治学门户等因素,产生时间先后、文本真伪、地位排序、孔门正学等种种争议,但由孔子到董仲舒建构的儒家经典及其包罗万象的解释体系,为汉儒提供了为政、治学、人格等全方面的范型。在较为抽象的社会理想或更加具体的国家大政上,这种范型至少在上层士大夫中始终或隐或显地规范着他们的观念,因而在现存奏议文本中,我们得以将儒家经典视为与汉家故事并行的整体概念进行讨论。
秦火之后,儒学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官方礼乐与民间藏书、传诵仍未完全断绝。西汉前期,一方面,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具有入世性格的士人积极参政,为刘氏政权结构掺入了部分符合儒家构想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朝廷的帮助下,儒家经典逐渐恢复了原有文本及其传授系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学官、建立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的中央和地方教育机构,虽为专制皇权外儒内法的“缘饰”之举,却毕竟培养了大量借儒立言、以儒者自居的士大夫。在中央和地方上,深于经术的通儒虽然不多,但专精一门的大臣和以法律、辞赋、书法等才能晋身却能够广引经典的士人,都不在少数。因而儒家经典的内容,也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各层面得到了普遍而广泛的运用,并直接呈现在两汉奏议文本之上。
而根据现存文献资料,广义的“汉家故事”系统主要由三个系列构成:一为“汉承秦制”中的部分内容,来源包括刘邦入关时萧何等所收图籍,及从秦故吏、民处搜集的其他资料等;二为汉政权所自建立,并由官方保存的典章制度,来源是君臣长期处理政务形成的经验和轨范,表现形式有皇帝的诏令、吏民献书、上奏等;三为与上层统治集团相关的、由私人保存的杂言片语。《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言“作故事”,可知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原史料做加工。又应劭《风俗通义》:
孝成皇帝好《诗》《书》,通览古今,闲习朝廷仪礼,尤善汉家法度故事,常见中垒校尉刘向,以世俗多传道:孝文皇帝,小生于军,……“有此事不?”向对曰:“皆不然。”[6]93-94
若材料可信,则上至西汉晚期,汉家故事的重要性增大,其地位开始向儒家经典、朝廷礼仪等皇帝掌握的一般知识靠近,但同时“世俗多传”的故事中,虚构成分进一步增加,已近于街谈巷语、小说家言了。
三、高祖至武帝时期奏议经典与“故事”的成分考察
西汉前期,是汉家故事的发生期,也是文吏、儒生、方士、游士等各类人物积极献策的阶段。由萧何、叔孙通、公孙臣、新垣平等成分复杂的吏民先后形成的汉家故事,与儒家经典提出的社会形态产生种种冲突,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惠、高后、文、景四朝,政治上又崇尚简易敦朴,清静无为,少有改作,多遵旧制。这样,一方面,汉家故事在内容上缓慢地积累,随时间推移而自然产生了“原本固有”和“理所应有”结合之权威,并由一些零散的人所共知的政治约定、操作惯例或私人行为,逐渐被聚合为概念较明确的范畴;另一方面,具有积极入世性格的儒生或学习过儒家经典、吸收了部分儒家思想的士人,虽然处于弱势,却始终没有放弃增强自身的力量,意图以种种方式介入刘汉政权,并对政权的性质进行改造。
这一时期的奏议,如韩信《上尊号疏》、萧何《天子所服议》、陈平《奏议定列侯功次》、申屠嘉《奏议孝文为太宗庙》,大多止于对具体事件的状况陈述、利害分析和个人陈请;始于贾谊、晁错的篇幅长大、论证充分的疏文,则承战国余风,杂学旁收,且作者具有超凡的创造力,不拘于对古文献的学习和引用。儒家经典与“汉家故事”的成分,也只能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在为数不多的奏议文之中。
至于汉武帝时,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方面,严青翟等《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中明确出现了“他皆如前故事”语,汉家故事实质上的权威也逐渐显现。汉武帝在强干弱枝、削弱诸侯王的同时欲封皇子为王,上文中则说“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5]385-386,引用高祖故事、先帝法则为行动依据。《汉书·枚皋传》: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7]522
以不从故事显示对戾太子刘据的重视,侧面证明了人们对本属具体操作仪式的汉家故事背后容纳的政治意义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汉武帝即位之初的政治形势,要求对汉政权的运行框架做一定的修正;刘彻本人好大喜功的性格,亦使他从即位之初就有着强烈的建立万世功业的愿望。此时期对已产生一定权威的汉家故事的改作和不循故事的大肆兴立,正是以力量逐渐扩张的“儒”为缘饰逐步进行的。
经过西汉前期儒家经典文本的搜集整理和传授系统的恢复,儒士群体的学风、性格和汉儒的思想体系亦自然由杂糅趋向纯粹,由幼稚走向成熟,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中不乏窦婴、田蚡等和刘彻一样好儒术者。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次年五月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贤良文学对策,董仲舒这样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精深博通的醇儒与公孙弘一类学习过儒家经典、并至少在表面上以此为立言依据的士人从此获得了特定的入仕途径。而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应武帝诏书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国家政策的支持更进一步促进了儒学地位的上升。为了迎合武帝的喜好,原本长于文史、法律、言辞的其他官吏,亦不得不借用儒家经典的外壳和儒生的知识缘饰施政行为与陈请内容。如《汉书·兒宽传》:
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兒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鄉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7]591
当时奏议文本中的儒家经典成分不断增加,如主父偃《说武帝令诸侯得分封子弟》、吾丘寿王《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庄芷《上书发淮南王阴事》、令狐茂《上书理太子》等,都引用儒家仁孝大义,以及《论语》《礼经》《诗经》《孔子家语》等文本内容以为支撑。虽然绝大部分官吏对儒家经典并无渊深的研习与广泛的掌握,像董仲舒《天人三策》这样体现引经据典、温雅醇厚的“汉文本色”的奏议数量还较少,但武帝时期政治话语体系的儒化确实对后世奏议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者如桓宽辑录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廷议内容的《盐铁论》中,以商贾出身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官吏,和贤良文学方在你来我往的当场辩论中能够自如地使用儒家大义及部分经典内容,即是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揣摩、研习、濡染的结果。
四、西汉中晚期奏议中经典与“故事”成分的扩张
西汉中晚期,汉家故事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其中原因,除了随时间推移和国家概念的强化,其权威自然继续上升外,首先,昭帝一朝霍光对武帝部分故事采取因循态度,而宣帝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更是对武帝招选茂异、舆服制度等故事刻意效仿。其次,武帝为对抗相权而建立内朝制度、任用宦官的举措和同时期完备的文档管理制度,给弘恭、石显一类宦官掌握汉家故事的便利。《汉书·萧望之传》:
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恭、显又时倾仄见诎。[7]786
当时内朝中书宦官因身体缺陷和职责优势,天然获得皇帝的亲近、信任,在宣元两朝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长时期的典职枢机中,相对于熟习经典的名儒,对文法故事的掌握逐渐成为文化素养相对低下的宦官的一种政治优势。汉家故事在纵向上的变动改易与横向上的复杂繁琐,又使在奏议中以此为论据者易于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罗织诡辩,中伤他人。而弘恭、石显联合史高等贵戚势力,以汉家故事为话语资源,与萧望之等以儒术闻名的大臣进行政治斗争的行为,又得到宣、元帝在一定程度上的放任。宣帝对儒者与儒家经典的真实态度,从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和俗儒“不达时宜”、“何足委任”的评论可见一斑[7]69。而柔仁好儒的元帝虽然任用儒者,但当萧望之在《建白宜罢中书宦官》中意图运用“国家旧制”和“古不近刑人”的双重论据使他重新任用士人为中书令,从根本上取消宦官势力时,不亲政事的元帝亦不愿放弃这股能够有效制衡儒士大夫的政治力量。这样,汉家故事作为一种奏议中的话语资源,通过政治斗争而间接获得了皇权的支持和认可。最后,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尚古”的观念和现实形势使越来越多较为通达的儒者认识到了汉家故事的重要性。如宣帝时魏相《表奏采易阴阳明堂月令》、元帝时贡禹《奏宜放古自节》、成帝时梅福《上书言王凤专擅》,皆以汉家故事为支撑观点的有力论据。
不过,此一时期奏议中的主要成分还是儒家经典。与儒学的异化和儒者的堕落相对的,是奏议中儒家经典成分的极度增加和激进彻底的复古倾向。一方面,对儒家经典的运用,如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言治性正家》《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几乎全以经典内容和经义阐述作为论据,并出现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7]803这样古奥的语汇;谷永《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述唐尧虞舜、夏商周秦等往古之事,李寻《对诏问灾异》阐发阴阳五行的内容,皆以《周易》《尚书》《诗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内容为全篇要旨或起承转合的枢纽。另一方面,元帝以后,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文化环境下,西汉晚期的政治黑暗、社会混乱不可避免地全面催动了以奉天法古为最高标准的政治改革思潮。贡禹《上书言得失·钱币》欲使“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於农”[7]721,完全取消商贾、钱币制度,彻底恢复小农社会的自然经济;王商、师丹、翟方进等《徙南北郊议》、鲁匡《上言令官作酒》,以《礼记》《尚书》《诗经》之文,周公、孔子之事,欲法古制而行,都是借儒家经典中记录或构建之“古”对汉政权运行所倚赖的基本制度的反拨。
西汉宣帝以来奏议联结汉家故事和先秦之“古”的倾向、称引儒家经典大义的语言形式和激进的法古思潮愈演愈烈,最终纽合为王莽《奏罢悼园南陵云陵园》《上奏符命》等奏议和《大诰》《限田禁奴婢》等诏令中满篇古奥晦涩的语汇和不伦不类的“周公故事”“周、召故事”“皇始祖考虞帝故事”。问题在于,上文提到,“故”与笼统抽象的“古”之不同,一在时间相去不远,一在来源于实有之“人事”与“强制力”的权威。“故事”应有实存的证明、政权的认同,才能在社会上造成坚实的“原本固有”和“理所应有”的观念,而当王莽意图将他激进的复古思路用无所征验的上古故事表述出来时,故事权威的根本已十分空虚。在围绕汉政权的国家观念和受命之说已经建立两百年的西汉末期,从哀平之世兴盛起来的符瑞之说、王氏的政治势力、封建和启用刘姓宗室以缘饰政治目的的行为,以及完全模拟儒家经典的话语形式,最终都不能压制名不正言不顺的外戚身份和禅让称帝带来的巨大阻力。当复古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加剧,新莽统治最终亦走向必然的失败。
五、东汉奏议经典与“故事”成分的新变
东汉前期以儒为主的文治政策,研究者已多有论述;而光武、明、章三帝在有关汉家故事的问题上也做了不少努力。光武帝刘秀征选伏湛、侯霸等旧臣,使之居台相而总权衡,以处理政务,收录遗文,逐渐恢复故事;明帝对班固撰《汉史》由戒备转向支持,和章帝使杨终删定《太史公书》,虽然出于统治者的立场,意图掌握对西汉历史的解释权,但客观上,在光武时期搜集整理遗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与统合出一幅汉政权的立体图景。
一方面,皇帝对“帝师”的荣宠、对儒者的优待、对经学的关注等种种举措,造成社会上和朝廷中浓厚的儒学氛围,并极大地抬高了儒者与儒家经典的地位,使儒术成为大部士大夫的基本底色。另一方面,自光武始搜整遗文的工作,尤其建初中成书的《汉书》以文传人,而“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8]396,为众多一般士人提供了丰富的汉家故事资源和奏议文本写作的规范。这样,光武中兴之后的奏议,在形式上很快摆脱了新莽时期那种晦涩古奥的语汇和极端的复古倾向,基本恢复了西汉中晚期奏议普遍称引儒家经典和汉家故事,并有意追求一种雍容平缓、醇厚温雅的行文风格的面貌。如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张纯《奏行禘祫祭》、陈元《上疏驳江冯督察三公议》,皆引经典、汉事以议论而文风相类,是光武时期颇具代表性的作品。由明、章至于桓、灵,依经引义、排比汉事以申说主张的奏议文本更是层见迭出。
不过,两汉奏议仍有一些隐微而重要的分歧。仅就儒家经典和“汉家故事”的运用而言,东汉奏议虽然也以二者为主要成分,但选取的材料、言说的模式及其精神内涵却与西汉奏议存在相当的差别。这种差别亦与光武、明、章三朝的文治策略紧密相关,其中影响颇大而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以下几件:一是汉光武帝刘秀除南顿君等四世亲庙,二是《汉书》的成书,三是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及《白虎通》的撰写。一方面,当光武通过“除亲庙”、定昭穆的举动承认自己与子孙皇位的合法性和威权来源于由高祖至平帝一系的“祖宗”时,他就同时向“祖宗”交托了部分由“创革”而获得的专制权力,并间接使西汉故事对东汉历代帝王具有了一定的约束力。而班固《汉书》的成书,则以学术上的努力强化了此种观念。如《后汉书·陈忠传》载安帝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孟布奏请不再允许大臣行三年丧,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陈忠的上疏则广引《孝经》《春秋》《诗经》中的语句和故事加以反对。文中首先提到的汉世故事,也是最有力的一条,就是“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陈忠由此得以对建武故事下“礼义之方,实为彫损”的结论。[8]457-458这是在种种可做论据的故事中,择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材料;而表明仅存于高祖时代的久远故事,还能凭借史书上实存的证明,并以受命之祖的威权,使奏议作者寻得申说主张的空间。
另一方面,当儒学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化,经典实现了“话语的霸权”。原本便十分庞杂的经典文本和董仲舒《天人三策》开始构建的阐释系统,现在似乎能够延伸到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被套用到任何人与事上。如爰延《星变上封事》:
昔光武皇帝与严光俱寝,上天之异,其夕即见。夫以光武之圣德,严光之高贤,君臣合道,尚降此变,岂况陛下今所亲幸,以贱为贵,以卑为尊哉?[8]477
《后汉书·严光传》载光武与严光“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8]811,本是君臣间无伤大雅的笑谈,而在此处被爰延用来做严肃的例子。他前引《论语》以表“圣人之明戒”,又循着那套经由君主认可的阴阳灾异的阐释系统,以光武严光之事为佐证,将星变解读为“天”的谴告,由此劝谏桓帝远离邪臣、宦官。这种引用经典,并加以经义阐释的结构安排,也是东汉奏议写作最常见的模式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儒家经典与“汉家故事”既然经过权力的确认,皇权也不得不给予这两种话语形式一定的尊重。即至汉灵帝,仍有阅录故事、正定经典之举。不过,当皇权及其孳生的宦官、外戚、内宠问题不断冲击政治秩序时,皇帝或称制的女主对那些持“祖宗故事”和经典大义、激烈地批判政治之黑暗混乱的奏议,更多时候采取了不省、不纳、不答的处理方式。士大夫们很快发现,以“讽谏”干预政治的手段失效了,奏议的实际目的于是一变而为泄愤、邀名;与此同时,经典与“故事”两种在他们的认知中据有天然权威的话语形式也失去了实际影响力。不过,一方面,文体的话语形式总是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合法性与权威失坠的经典和“故事”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保留了一定的合理性。于是,奏议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它引经用事、深雅典正的范式,和时代清峻通脱、师心使气的文章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蒋振华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表谢忱。)
参考文献:
[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2]支伟成.商君书[M].长沙:岳麓书社,2011.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