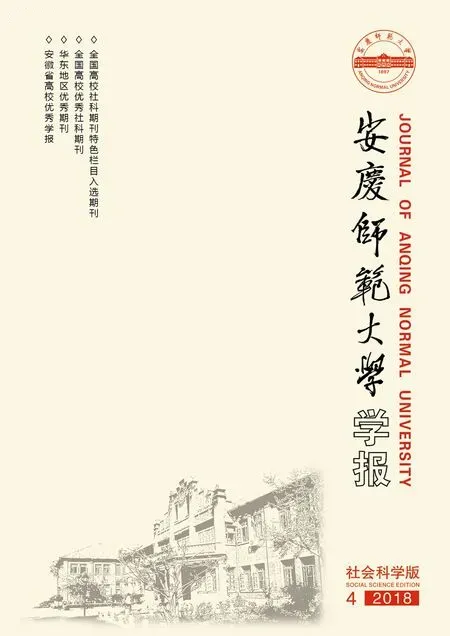晚明退隐士人的生计问题
郝健健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明代仕宦俸禄低,而中国士人向来追求“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理想人格,这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社会“恒情”背道而驰,所以明末清初的陈确提出了“学者以治生为本”[1]158的生存哲学思想。由此不难发现士人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生存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士人无论因为何种原因退隐,都需要生活所资,以为父母妻儿及自身所必须的物质保障寻找出路。面对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争不断以及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堕落等险恶的政治环境,晚明士人在政治社会的夹缝中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下,勇于跳出藩篱另谋生路,重新寻找其“本我”的人生价值,就必须面对古代士人在以“学而优则仕”来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被切断以后,将凭借什么维持生活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困窘局面。
明代仍然是建立于农耕经济之上的王朝,并沿袭“士农工商”分别对待的政策,由此形成世人“不读书登第,不足以保妻子”[2]112的观念。登第做官在实现自我抱负、获得丰厚报酬的同时也将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扩展其社交圈层,进一步扩大收入来源。然而主动退出和被迫退出的士人,就失去了这样优渥的治生条件,不得不另谋生路,同时众多未曾侧身仕宦的士人在主动放弃科举后,也不得不面对生计问题,因此对隐士的生计问题进行探讨显得尤为必要。结合各种历史资料分析,隐士治生之道无外乎“本业治生”和“异业治生”两种,诸如讲学、卖文字画、医卜算经、耕读治家和士商融合等。同时也有遗产继承,归入僧道等其他治生模式,不同治生方式也一并反映出不同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高低。
一、遗产继承
通常情况下,退隐之后维持生活的首要经济来源无疑是政治遗产。部分隐士,尤其是当世或在后世较为出名的隐士,他们多半并非从始至终都选择了隐而不出。古代中国自从北宋明确提出儒者当以天下为己任后,便以致君行道为宗旨,除非在迫不得已之时方才痛定思退。于此,也就有相当一部分士人是中途退出,或时隐时退的情况。不论他们在职期间是否受贿敛财,官员的俸禄相较普通人而言仍然为多。以明弘治、正德年间官员王献臣为例,其官至巡查御史,后因事弃官,却在苏州购置园宅营建了后世评为四大名园的“拙政园”。明代官俸相比于前代更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实际上官员收入至少包括正式收入和法外收入两种,可见其当官之时的收入并非如常人想象的那般微薄。而在明代大批选择归隐的士人中,多半是属于曾经有过从政经验的人群,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拥有一定的政治遗产。如唐伯虎曾因为泄露考题而放浪山水,屠隆因为厌恶官场习气而罢官归隐。然而,曾经的官员身份,对他们日后的经历仍意义非凡。
此外,官员也因为在职多年而形成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对于他们退隐之后的生活可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万历时期的李贽。李贽在万历八年退出官场后并没有选择回到福建老家,而是寄居在湖北麻城的好友耿定向家中,直至万历十二年与其家族关系逐渐恶化后方才离开。而且他和当朝为官的焦弱侯等也是好友,他们之间的往来也相当频繁。即便没有受到朋辈的终身资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他们一定程度的赞助。而且士人们也会因为联姻、交游、结社等形式扩大社交圈,在这期间无疑也为自我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这些资本对于归隐后的士人而言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另一方面的收入则来自家庭(族)遗产。如袁宏道在面对退隐的忧虑时说:“数橼残茆,十亩秫田,已付之妻儿管理,身口自足,无庸劳薪仕进。”[3]1932罗洪先也说:“有薄田百亩,岁入可给膳粥。”[3]1925可见,部分士人退隐的前提是自己有足以资身的经济基础,方能全身而退,过上安逸生活,这也说明了治生是退隐前必须考虑的问题。很多名士喜山水香茗、古玩字画,若是没有这种富足的家产作为支撑,必然难以为继。《明史》卷二十七记载,明嘉靖年间的文学家卢楠因屡试不第后输貲为国学生,但由于他官场不顺而退出,后遍游吴会。由此也不难发现其家产颇为殷实,否则无以为其谋得国学生,赋闲后也不可能在外游荡,不事生产。
二、讲学薪酬
士人凭自我能力解决生计问题最典型的方式是教授讲学。士人最大的优势即是其掌握的文化知识,在此领域他们也更加具有施展空间,且晚明讲学之风的盛行更为此种现象的隆兴起到助推作用。自王阳明始开讲学之举,后继者连绵不断,从正德至崇祯百十年间,虽频遭禁黜仍不绝如缕。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一个没有步入仕途的读书人而言,最能利用和发挥自我才学的方式无疑是“教授讲学”。儒者向来以“明道”“传道”为业,若以这种曲线的形式实现自我理想和价值仍不失为良策。
对于未仕的教授之士来说,最重要的收入即是学生的“束脩”。束脩的种类繁多,支付形式分为实物和货币等。且在不同时空、不同的人物、不同教授等级的情况下收入均不相同。对于一个自身学识高、社会声望高、教授效果好的老师,有些富有家庭“动辄费数千金”延聘。相较于北方多数地方,经济更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束脩也常常更高。而且江南地区普通教师年脩金达百两以上者亦时而有之。据记载,董其昌年少时,曾“授经当湖冯氏,岁暮将归,有旧姓子弟以古蹟求售者,云须得六十金可以卒岁。公如数与之,垂櫜而回。”[4]这“六十金”可能就是他一年的收入。此时的董其昌还只是位普通儒学生员,声名未显,亦能有年脩金60两左右的收入,说明在馆塾任教是可以维持生计的。加上教授学生的数量也直接影响这一年的收入。诸如扬州经师邹泉,虽只为生员,却因“大姓争延为家塾,邑弟子执经门下者,岁可三四十人,……岁可得束脩百余金”。袁应春在做生员时,“弟子执经游门下者胪列,大姓争延为塾师,岁可得馆资百余金。”[5]但并非说所有的教授之士皆能获得理想收入,这和学问、声望以及所处地域等都是密切相关的。对于那些学问修养不够,或家庭背景不理想的士人而言,生活可能还是陷于焦灼、入不敷出的困境。
士人凭借其所具备的知识文化不仅可以通过教授来满足自己的日常所需,还可以通过兜售自己的文字书画等作品的方式获取更多收入。尽管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君子以利为耻,尤其是通过自己所学来迎合市场更是不被倡导。孔子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即是此意。但对于没有稳定俸禄支撑的退隐之士,就不得不以这样一种治生方式供养家庭。
三、卖文鬻字,奔走公门
明代颇为流行为逝去的人写墓志、寿赞、碑传等,而这些活动无疑只有掌握文化知识的文人墨客方能做到,且无论仕隐,都有不少士人参与其间。西江先生刘绩,“家贫,转徙无常地,所至署卖文榜于门”[6]。当时有很多热衷于读书的人,却因为家中较为贫困,在江南地区游学并给当地宗族做族谱为活,反映了出于生计问题而兜售自己的文字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另外,对于一些没有这种机会的人而言也可充当“佣书”“鬻手”等。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山地租赁相当普遍,通常立下字据的并非是租赁双方的当事人,而多半由乡里粗通文墨之人代笔。如孙一元曾因“父早亡而贫,山人以抄书役某府中为养母”[7]。范大澈在长安“所养书佣、日抄,多至二三十人”[8],说明以“书佣”谋生也是一种方式。
对于善书习画之辈,则可以通过出售字画赚得利润。青门山人晚年因为家庭贫困,时时资绘画自给。嘉靖时的通隐士人张凤翼本来家底殷实,却因不问生产而家道中落,逐渐选择卖文资生。在明代的退隐士人中以鬻卖书画资生的士人相当多,这既是一种主动性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被动之举。不过,通过“卖文博食”解决生计问题的士人所得收入并非均一化。相对于技艺和声望更高的人,那写默默无闻的普通士人收入就相对较低。但是因为古代社会识字率低,在一个自然村落里如果能够具备基本的识文断字能力,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具备了卖文博食的市场与可能。
除了依靠自我学识之外还有些人奔走于公卿之门,以谋食博名的士人。如谭元春对山人的定义:“山人者,客之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之号也”[9],隐者陈继儒即是如此。陈氏不仅在山中闲不住,还曾周游天下,流连忘返。其本人甚至在官员王锡爵家做伴读,陪其子读书进学,在这个过程中与其族相交甚厚。时人将这种“游食”行为比喻为“打秋风”。而社会交往本就含有这种相互为用的深层原因和实际效用。实际上,退隐之士并非没有自己的社会交往,他们只是享受“无官一身轻”的状态,而无需卓然独立。万历时期,山人数量剧增,遍布市井,甚至朝廷不得不下召驱逐山人[10]。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们虽不食君禄而食仕宦的现象很是普遍。
四、耕读治家
尽管以上所述都是士人的治生手段,并非代表所有退隐士人都有上述的机会、能力或愿意通过自己的文化知识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既然很多士人选择了归隐,就意味着选择了远避尘俗,尤其是明代出现了大量以“山人”自居的士人。如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陈继儒,虽然在后期奔走公卿,他在退隐早期却长期寄居山中,选择了“退而躬耕菽水,结茅小昆山之阳。修竹白云,焚香宴坐,豁如也”[11]。于此反应出仍有部分士人至少在一定阶段选择了躬耕自足的治生方式。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为本的封建国家,土地对每一个人而言都举足轻重,加上历朝历代推行重本抑末的统治策略,使得农业生产更加深入人心。即便是当朝为官的士人对土地的渴望与索取也从未停止过。霍韬虽然身在仕宦,却仍然定下家规,“我家不力耕蚕者,以不孝论”[12]。因为农业是最直接最根本的治生手段,相较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更加具备可靠性与稳定性,所以在传统观念中常常强调“未仕者......必先以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13]。这在徽商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全国各地经营商业发财致富,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本用来购买各地及徽州当地的山林、土地和房产等。
实际上,在士人心中耕种田间不仅是一种治生方式,更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明代隐士高嗣初说:“仆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输王税,采樵以奉亲颜。于时新谷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鱼燔而召友。蓑笠在户,桔槔空悬,浊醪相命,击缶长歌,兹鄙人之快,而故人之所也。”[14]但这种文学性的描写只能停留于想象,至多也只可能维持极为短暂的时间,若想长此以往在这样的氛围里生活,几乎不具有可能性。而现实依然是冷酷的,对于少部分从家族继承下来较多田亩的士人,仍然可以拥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但是多数人并不会拥有大量的良田,姜守鹏根据万历时期徽州宁县十一都三图与十二都二图的民户研究显示:在总数694户人家中,拥有土地数量能称得上富裕的家庭只有2户,一般家庭32户,土地拥有极少的占到454户,余下的206户是没有土地的家庭[15]。这说明多数人不足以依靠农耕过上富足的生活。尽管说对于已经选择隐居的士人而言,“富贵”本不是所渴求的东西,但生活仍然需要物质财富的收入才能维持,也就可以想见,一个隐士的生活寒酸和贫困是一种常态化现象。
五、医卜经术
对于“躬耕”,也有很多隐者以医生、术士、风水先生的方式为生,这在众多的小说演义中也多有体现。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则证明行医救世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明史》记载:“左氏载医和、缓、梓慎、裨灶、史苏之属,甚详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张其事以神之。论者谓之浮夸,似矣。而《史记》传扁鹊、仓公,日者,龟策,至黄石、赤松、仓海君之流,近于神仙荒忽,亦备录不遗。”[16]8陈确说:“吾辈自读书谈道而外,仅可宣力农亩:必不得已,医卜星相,犹不失为下册。”[1]327王夫之也说:“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17]虽然说在多数士人眼中,士当以弘道为上,并对职业进行了高低划分,但至少选择其他职业仍然是可能的,也往往为现实所迫使。明代科举制度发达,对入学和获得科举资格的限制相对宽松,使得读书士人激增,但是有明一代科举取士的承载力却没有很好地关照到这一突出变化。据顾炎武研究,明末“合天下生员,县以三百记,不下五十万人”[19]。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势必导致天下读书人众多而入仕者较少的现状。
由于医生是一门技术较强、事关生死的行业,即便在古代社会医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前提下,仍然无法否定它的重要性。所以很多富裕之家都会“求名医厚结之,亲有疾则信之必专,召之必来”。尽管医生之职业被视为末技、小道,但也不失为一种治生手段。而且医术以“术”见称,可见在古代医术具有一种神秘性。这固然是中医本身的非科学性导致的,也是医者谋生而刻意为之,但最重要的是医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这对于士人而言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于是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儒医”,他们多被描述为“妙手回春”“悬壶济世”和“医者仁心”的形象。无论士人如何恭维或褒扬,对于医者本人而言都是他生活来源的途径。江南昆山有一沈愚,他“通理博涉百氏,以诗名吴下,与刘溥诸人称十才子......或劝之仕,曰:吾非笼络中物也。敛迹不出,业医授徒,以终其身”[3]1034。可见,沈愚自认为做官不是自己的追求,甘愿以行医收徒的方式来支撑生活。包括后来的凌云、李时珍,他们都是在这种以医为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隐”的目的,只不过是将“医道”合一而已。
六、亦士亦商
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中,士人的谋生之道中最为不齿的就是为商为贾。但对于治生而言,商贾的效用却是最大的。晚明时,读书人想完全摆脱商品经济的影响,已经很难了。古人那种“学不谋食”的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王阳明在此前已提出“四民异业同道”的观点。晚明时期的归有光也清楚注意到这一变化“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而为贾者,独为学者之好。”[19]甚至连内阁首辅严嵩和徐阶都在民间售卖高利贷,尤其是徐阶在松江地区经营的丝织业规模巨大,获利颇丰。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自然是士人的普遍贫困化,而士人的求处无疑又加重了这种赤贫化,造成他们不得不为生计另寻出路。甚至大儒吴与弼亦尝“思债负难还,生理蹇涩,未免起计较之心”[20]。可想而知,那些普通的士人又有多少生计的无奈。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由儒入商自然在所难免。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士人群体的不断扩大,这一“士商融合”的现象就更加明显。部分士人或者“亦儒亦商”,或者“弃儒从商”,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商业领域,不变的是他们作为儒者和士人的本源身份,这样一种趋势在江南地区体现得更为突出。“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21]这难免有夸张之嫌,但士人的介入其中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相对于政府官员和农民,退隐之士的生活来源问题就更为关键。福建莆田的著名诗人陈昂就曾因为家庭贫困而“领妻子奔豫章,织草履为日”[22]。万历时松江陈守贞“孑身事母,有田属弓,旱潦,惟种棉花,所收常倍。手自纺绩,精绝一时,远近称为孝子布”[23],这种将读书种地和商业活动结合起来是很常见的。尽管他们从事的是一些极为简单的交换过程,但难以想象没有这种时代大潮的转向,士人何以完成这种身份转变。由于时代的种种缘故,晚明涌现出大量的从事文化商业化的群体。这里面比较成功的如张岱、冯梦龙、凌濛初,他们都没有进入官场,甚至科场也不成功,但是他们却在那时创作了大量迎合市场需要的文学作品。因为拥有了大量的市民阶层,也就涌现出大批的市民文人。在市场的需要和推动下,他们被各大书商邀约,逐渐出现了今天仍耳熟能详的作品。但是在众多的以“隐”为名的士人中能够以文学艺术谋生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走街串巷,做一些小买卖来聊以资生,以此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过着昼入市治贾,夜归读书的生活。
晚明退隐士人在选择放弃科举或远离官场之后,又不得不面临生存的困境,他们或教书以续其志,或践耕以养其身,或以卖文鬻字、医卜算经等方式来维持生计,在此展现出各种价值取向以求其治生之道,并在此重新发现自我的存在意义。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未能像在朝为官的士人那样为天下谋福,事事关心。但他们至少也没有参与到败坏朝政,祸国殃民的行列中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应该就是一个士人最基本的操守。但在生计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他们也未能尽如人意,有些人找寻到了生命真正的旨趣,志得意满;也有些人仍然穷困潦倒,生活入不敷出,情绪低沉彷徨,究其根本是在晚明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所有人都被裹挟于其中,不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