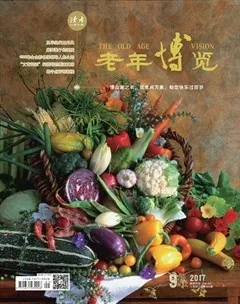苏雪林的“信癖”
古人云,人无癖不可交。衣食住行皆可成癖。近读苏雪林长达50年间的四百万言日记,发现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信”,我姑妄称其有“信癖”。事一成癖,趣随之生矣。
苏雪林年过花甲后,日记中常有“还信债”或“一天光阴又在写信中度过”或“今日为写信最多之日”的记录。94岁时则曰:“余现别无所乐,唯得知音者之信,及自己有文字刊于报章,乃稍稍开心耳。”(1991年8月24日)
苏雪林一生节俭,用她自己的话说“近乎啬”。但由于她爱写信,邮资成为她生活中一笔不小的开支。日记有载:“于今每个月邮费及信封、信纸不知用多少,以往十元邮票可用数月,今则半月耳。”(1959年1月17日)为节省邮资,信封她常用商家塞在信箱内的广告自己糊制,信纸则由随手抓来的各样替代品充当,甚至包括餐厅的餐巾纸。80岁时,她偶见旧物中一叠老得发皱的信纸,“熨了一下。此信纸乃余20年前自法国携归,或20余年前台北所购,早已微黄而皱,幸熨后尚可用”。
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邮资下调,她十分高兴:“我可以写薄信纸四张,而不用航空信笺,殊方便也。”好景不长,后台湾邮政当局宣布作廢了一批邮票,她牢骚不已,说“这是坑民”。20世纪70年代台湾邮政当局又出新花招:凡在邮局定做寄信用的规范化橡皮章者,钤此印八折收费。她专定一枚,云:“定做此物以来,今始用之。若居心不贪,发出三四封信皆加此章,则回信不致冷落。”她是求信若渴,想广种多收罢了。
寄台外邮资昂贵。某次她让女佣到邮局挂号寄两本书到九龙,一过秤要250元,她嫌贵,让女佣改为平邮。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航空信笺从9元涨到10元,她盘算着还是寄航信划算。可是一旦超重便会被退回,还要罚款,她叹道:“以后不便写信矣。”苏雪林写信如作文,往往下笔千言。她喜用薄纸,正反面都写,仍稍不留心便会因超重被退回。鉴于此,她专备了一个小秤,信封口前先过秤,如果超了,去掉一页便是。
另一件令人捧腹的事,是1991年台湾邮资大涨,她很是不满,以实际行动“抵抗”:“邮资增资后,即少写一二封,乃市民之消极抵抗也。信少,邮局收入也少,则增邮资实为失策,或不久的将来又将减资,则我辈胜利矣。”(1991年8月1日)还有更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她由法赴台,船泊西贡一天:“余听说西贡写信到巴黎航空亦仅需十五方,竟欲占占便宜,遂以整天工夫写信,计写五封……下午写完去寄,问管信件之船员,则由巴黎写航信到西贡为十五方,而由西贡写航信到巴黎则需五十五方。”(1952年6月25日)遗憾的是此日记无下文,不知信她最后寄了否。
为省邮资,苏雪林常请从海外回台的朋友带信。“因明日公宴陈通伯(陈西滢)先生,余将利用渠飞欧机会托其携带信件,故今日将学生作文束之高阁,大写其信……共十三封,直写到晚上11时始睡。”(1952年11月2日)20世纪60年代她一度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该校各人来信一律存在图书馆。图书馆距其住地较远,她为了能及时读到朋友们的来信,不得不每日奔波到图书馆取信,虽然直喊划不来,但仍照跑不误。她寄的信数量多、质量高(长),而所得回报极不平衡。在日记中她历数友人不够朋友:“叔华来信,余立复一航笺,写得密密麻麻,比她来信的字多五六倍。”她常抱怨谢冰莹写信像写条子,“不知她一天到晚在忙什么”。她发誓要“以牙还牙”,写短简,可一挥笔又刹不住了,非千言不罢休。
苏雪林写信的热情,笔者深有体会。1996年的半年内,她共致我7封信,用的都是超薄型大白纸,密密麻麻,正反面均写,有一封字密到与落款重叠,看都看不清楚。最长的一封长达3000字,而那时她已百岁。她致我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距她50年日记终结的1996年10月19日只有11天。那时她的字已歪扭重叠、笔画不全,几不成形。这或许可称是她的“绝笔”了。
苏雪林晚年耳朵失聪,不能接电话,与人面对面交流也只能靠笔谈。特别是与她共同生活的姐姐淑孟过世后,她一人独居,终日面壁无语,更赖写信排闷遣愁取乐自娱了。
苏雪林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且看“今日为余烧信日”一篇记载:“昨日烧信纸未尽,又到后院烧之。下午睡起,看报二份毕,续烧废纸。三四年来积信上千封,连一些被白蚁蚀之物皆付一炬,足足烧到晚餐的时候。”(1974年11月2日)笔者又从苏淑年《雪林师与我》中获悉,仅她收藏的苏雪林的信就有300多封。与苏雪林有书信往来者很多,包括胡适、曾虚白、蒋梦麟、王雪艇、张道藩、谢冰莹、潘玉良、凌叔华等等;晚年她与大陆友人的通信也多,包括冰心、钱钟书、萧乾、袁昌英、舒乙等等。苏雪林自言,友人的信她是每信必复;而友人复她者,“唯半数耳”。由此我估计她一生写的信,谅有一二万封之多,或可获当代文人写信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