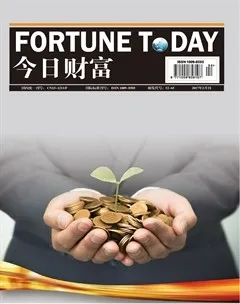市场经济下的公民社会的理性分析与构建
公民社会是20世纪在全球兴起的一股民主浪潮。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也因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而受到国人的重视。然而公民社会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是经济的,随之而带来的平等、自由、合作的精神以及组织化发展给予中国的政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今天,公民社会已经被称之为与政府、企业并称社会的三大支柱,与公民、政府及私人部门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共治体系。可以说,公民社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经成为了社会不可缺的一员,并且其作用也愈来愈重要。
公民社会已经成为平等与自由的代名词,公平正义的使者,普通大众的保护神。但是,抛开公民社会耀眼的光环,我们不难发现在公民社会内部也有着鲜为人知的缺陷。 公民社会内部各社团之间的不平等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现实问题。
中国学者张静从公民社会的“法团主义”角度分析,国家法团主义一般是指由国家建立和掌控的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和权力影响的利益共同体,自由法团主义则是指的民间形成的,代表基层普通群众利益的组织实体。二者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在(国家)法团主义社团内部仅有精英民主或实行寡头统治;它们往往垄断了某种职业或行业的利益代表权和参与政策代表权。这种垄断的特权地位得到国家认可或系由国家创设。国家通过这些收到特许的社团组织来控制生产者并防止他们成立新的组织。垄断法团主义是西方社团兴起时的初级阶段,在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和自由精神的推崇,各种利益代表为了追求平等,自由法团主义开始出现,自由法团主义要求各种社团之间平等对待。” 美国的戈兰·海登和英国学者戈登·怀特因此都呼吁,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要建构公民社会中各团体间的平等关系,“民主的宪法或民主的其它方面不纯粹是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竞赛,而且也依赖于公民社会不同部分之间在利益、规范和权力这三个方面冲突和合作的方式。”
在我国,以上种种问题也明显存在。首先,很多协会或社团成为政府精简机构后,政府转移资金建立的“小金库”,或是政府安置退休干部的“敬老院”。这明显是社会不公的后遗症。另外,目前我国行业垄断问题十分严重,比如铁路、电力、通信等集中于几大利益集团手中,一系列霸王条款,不公平竞争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这些利益集团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姻关系,是政治强势的附带产品。很多行业协会名义上是维护行业利益,实际上是维护的几个独大利益集团本身的利益,小的公司或私人部门很难在这些协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分到应有的一杯羹。当然,也有一些普通企业,为了获得更大利润,联合起来,制定行规,私定产品价格,阻扰其它企业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不公平竞争。 因此社团之间的平等,维护社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民主关系是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重要条件。这种民主关系的维护需要一种完善的民主机制予以约束和规范,它包括社团之间的联络,社团之间公平的裁判,社团之间自由竞争机制以及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监督机制等等。
一、建立社团间平等联络和裁判机制
这就要求我们弱化垄断组织的权力,削减其行政色彩,对于基础薄弱的草根组织则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和法律保护力度、制定处理社团间关系的法规或者成立社团联盟,在联盟内制定民主平等合作原则。再者可以建立社团与社团之间的联络机制,一是社团自身建立联络部,专门用于与其它社团的交涉联系。二是政府可以以民政部门的民间组织管理局(司、处)来负责社团之间的联络沟通事宜。三是社会支持组织,这些组织一般是指对基层社会组织提供资金,资源等支持的组织(当前国际这类国际组织较为普遍,如卡特基金、福特基金、国际救助基金等),可以以这些组织的资源和便利来提供社团之间的协调联络事宜,或者是社团之间协商成立的社团联合会或社团促进会等社团联盟组织,作为社团联络合作的平台。以上只是三种选择性途径,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机制,以解决社团之间的沟通问题,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或者促进它们之间更好地协作发展。
二、在维护社团之间平等基础上,引入社团竞争机制
使社团运营符合市场规律,将资源向资质优秀,能力强,信誉好,服务好的社团转移,淘汰不合格的社团,从而净化社团市场,优化社团系统进出机制,引导社团良性发展。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存在缺乏竞争机制的问题。如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第2项的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民间组织,没有必要成立的,对于民间组织的成立申请不予批准。另外,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可以看出,我国在民间组织问题上实行的是垄断政策,这不利于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也不利于整个社团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打破这种封闭机制,在现行政策环境允许的条件下,适当放开,通过增量的改革促進存量的调整,逐步形成社团优胜劣汰机制。
三、政府应加强对社团依法引导和监督
我国尚处在社会转型期,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社会自治能力较弱,还远不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所以政府应加强对社团的规范、引导和监督。目前,我国除了《社团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组织管理条例》等少数法律法规外,其它非盈利组织的法律地位、责任及其行为的监管等,还处于无法可依状态。另外,我国长期条块分割的体制特点加上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形成的权力真空,以及党政体系权力相对独立,对社团的行政、许可及监管职能分散在了登记部门、各主管部门和部分监管机构中,使得社会组织特别是那些无法通过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得不到集中统一监管。建议在现行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民间组织监管委员会(简称民监会),将目前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使、以及分散在相关部委和单位行使的对民间组织的各项主要的行政监管职能统一到民监会中来。由民监会统一行使对社团的监管任务。
四、除了政府作为监督社团以外,还应积极发动社会监督力量
如,新闻媒体、公民个体等。对于违规违法的社团,媒体予以曝光,对于社团的预算开支也可在相关网站或报刊进行公开公布。甚至,媒体也可以对社团进行评估排名,将优秀的和不合格的社团公示于众。相关部门,如银行也可建立信用评估机制,专门建立社团信用档案,将不守信用的社团登记在册。同时,考虑到一部分从事教育、卫生、环保、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的民间组织具有很强的专业要求,应当由相应的业务部门或政府授权的中介组织进行资质认证和必要的业务指导,和业务考核及监管。作为公民个体,积极发挥社会主人翁精神,将社团的不法行为揭发并通报给相关部门。
正确理解公民社会,认识公民社会的优点与不足,为公民社会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理念支撑,同时在此基础上积极建构社团外在民主机制,规范和约束公民社会的行为,是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当前这方面工作已经展开,但还不够系统和具体。在具体实施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法律文件,机制建设还只是点上的实验或摸索,没能成为政策上或战略上的考虑,因此这个工程任务还很艰巨和迫切,需要我们为此再努力。(作者单位为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