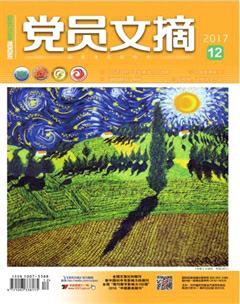巴金的灵丹妙药
2017-12-13 10:22周铁钧
党员文摘 2017年11期
周铁钧
1935年,巴金任上海《文化生活丛刊》主编时,与茅盾一起参加一个文艺界举办的酒会。人们刚刚就座,一个叫袁豫鸿的画家突然发病,抱头叫痛。
袁豫鸿的朋友说:“他患脑神经痛多年,发作时必须立即吃止痛药,刚才还说来时匆忙忘了带药,不想真的发病了。”
巴金上前察看,說:“袁先生,我和你一样患有脑神经痛,我的止痛药十分奏效,吃一片马上就好。”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小瓶,倒出一片,让袁豫鸿吃了下去。
不一会儿,袁豫鸿的头果然不疼了,他抹一把额角的汗水,握着巴金的手连声道谢。
茅盾在一旁感到奇怪,他把巴金拉到僻静地方,问:“从没听说你有过脑神经痛,怎么会带止痛药呢?”
巴金神秘地笑笑,说:“他头痛多年,发作必须立即吃药,已形成依赖,我觉得是神经焦虑、紧张,吃下药心理得到安慰,神经会松弛,头也就自然不痛了;我给他的药不过是抑制胃酸的苏打片。”
巴金的话,让茅盾想起一个《中央日报》的记者朋友,他成天要遵照上司旨意胡编乱造假新闻,患上严重的焦虑症,烦躁失眠、眩晕头痛,历看名医,用遍药品都疗效甚微。后来,他辞职离开报社,不再绞尽脑汁撰伪造假,心安意顺、夜眠酣稳,不用任何药物,病症全消。
后来,茅盾将这段情节写进文章,说:“我们的许多病不是因为细菌感染,而是源于自身的焦躁,远离烦闷、紧张的环境,放松心绪,百倍胜过灵丹妙药。”
(摘自《做人与处世》2017年第14期)endprint
猜你喜欢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21年8期)2021-08-13
故事家·花开不败(2019年5期)2019-09-10
长寿(2019年4期)2019-07-19
艺术品鉴(2018年9期)2018-01-30
实践·党的教育版(2017年9期)2018-01-05
人人健康(2017年1期)2017-01-24
中老年健康(2016年8期)2016-10-17
医学研究杂志(2015年11期)2015-06-10
发明与创新(2015年33期)2015-02-27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年11期)2011-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