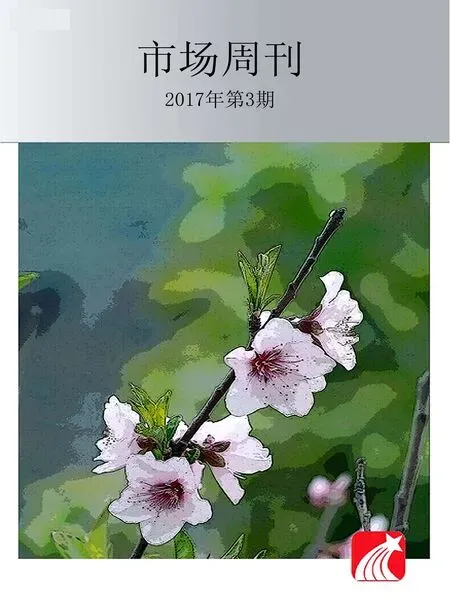论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法律规制
徐华
法学研究
论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法律规制
徐华
我国反收购法制亟待完善,目标公司董事于反收购中可能损害目标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通过信义义务规制来平衡各方利益值得研究。制度完善首先应回归董事信义义务的法理基础,包括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目标公司股东与董事的利益平衡、中小股东保护原则以及目标公司债权人保护原则等,剖析现行信义义务法制缺憾所在,提出制度完善路径应从明确董事信义义务具体内涵和外延、完善少数股东的诉权救济、反收购决策权归于股东(大)会、法律体系的内外部统一。
信义义务;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利益平衡
公司收购与反收购,其目的在于目标公司控制权的取得或维持,在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的“攻防大战”。目标公司董事身处利益冲突之中,督促董事尽到信义义务,确保其不利用反收购措施以维护私利的手段,是反收购法制建构之核心。法制的建构须从其法理基础做出本源审视,评判现行法制是否符合立法主旨。
一、董事信义义务规制的法理基础
(一)股东利益至上原则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发展,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的根基发生动摇,但仍至关重要。《收购管理办法》第8条:“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当公平对待收购本公司的所有收购人。被收购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做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应当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不得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该规范明确在反收购中董事负有法定忠实义务,也是判断反收购行为是否合法的基本标准。公司的固有特征之一是营利性,作为股东经营管理者的董事采取反收购措施之时,应当服从于此目标约束。
(二)目标公司股东与董事的利益平衡
反收购法律关系的真实利益主体是目标公司股东与董事,利益平衡也在其中。在反收购中讲求利益平衡,在于公司经营模式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董事利益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并非完全重合。董事的自利性与逐利性可能催使其滥用职权,采取不恰当措施妨害公司合并。在收购实务中,区分目标公司董事行为的真正目的很难操作。要期望董事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股东利益无异于痴人说梦。
(三)目标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相较于收购者、目标公司董事和控制股东,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董事实施反收购措施时,往往难以全面顾及全部股东利益,中小股东极可能地成为附属,因而存在着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利益矛盾。实践中收购者为促进收购顺利完成,往往给予持股较多的股东以一定优惠条件,这无疑是对中小股东的不公平待遇。董事义务从表面上源于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之规定,实质上源于董事与公司之间存在的某种特殊的法律关系。
(四)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原则
反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股东关注重心偏向于股票短期盈利,而非公司可持续发展收益,因此易导致董事、股东贪图较高的溢价收益,而对收购公司的收购意图、能力、发展预期等因素漠不关心,将公司股权拱手转让。然而实践中往往存在这样的现象,即收购公司在收购成功后掏空目标公司的资产退出,严重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产生该现象的一项重要因素是董事未尽必要信义义务,对公司经营信息知之甚少的债权人,其利益需要董事尽到合理的义务以维护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可能风险,债权人之保护亦属重要。
二、我国现行董事信义义务法制评析
公司法未对董事注意义务做出全面详尽的规定,仅在第148条和151条设置了勤勉义务并作出基本架构,第149条列举董事的禁止行为,《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第97条和第98条规定对目标公司做集中规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第8、32、33、34条等确立了信义义务的基本框架,《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及《禁止证券欺诈行为办法》等规范较少涉及上市公司反收购。公司法对董事的注意义务除了原则表述之外,几乎未涉及任何具体的内容。此外,现行公司信义义务法未对注意义务作出届分,也未对其行为模式作出分类归纳。同时,呈现出注意义务功能面临弱化的局面,只规定了董事勤勉义务,同时董事注意义务没有到位规定,而勤勉义务仅是注意义务的项下内涵,涵盖范围上注意义务宽于勤勉义务,以勤勉义务规范替代注意义务,上下位颠倒而有漏洞。董事勤勉义务的认定标准未臻清晰,因而产生可诉性适用疑问。其三,对于忠实义务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公司法“规定+列举”模式并不全面。该立法模式仍停留在自我“经济利益冲突”的矛盾解决上,传统思维上稍显僵化,对于其他形式的个人目的与公司利益的冲突尚无规制。其四,对信义义务的规定缺乏在司法上可执行的检测标准。
虽然《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了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其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但该规范是否包括注意义务,在法律解释上亦存在疑问。其二,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仅限于上市公司,未将居于数量多数的非上市公司囊括在内,主体有限决定法律适用范围有限。此外,虽然列举了董事会不得采取的反收购措施,但收购市场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穷尽董事层出不穷的反收购措施。尽管规定了一系列董事会不得采取的措施,仍有难以列举全面疑虑,而应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际。
三、反收购董事信义义务的法律规制完善
我国反收购法律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可从以下路径着力:
(一)确立董事信义义务内容及法律责任
对公司收购与反收购中董事信义义务的具体规制有四个方面:1.决策谨慎义务,旨在保证董事会决策的合理性与妥当性,以及限制董事会反收购的提起权及董事会未经股东会批准单独采取某些措施。2.防御适当义务,不得超出明显不合法界限,以及侵害公司、股东、债权人之利益;3.全面信息披露义务,目标公司董事会应及时发表意见和决策,独立董事独立发表意见;4.股东利益保护义务,包括为股东判断、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为股东争取最有利的收购条件,尽到最大限度的股东利益保护。
(二)完善少数股东的诉权救济
公司法对于质询权的规定简略,质询权的行使与救济等有待于立法进一步明确。譬如遭到被质询人(董事)的无理拒绝,应当赋予提起给付之诉的权利,即要求法院判决被质询人履行说明、解释之义务;以及被质询人在股东会会议上不履行义务或者故意告知不充分、虚假信息的,依据此信息表决的股东,也应当在事后得以会议程序下次为由主张提起决议撤销之诉,此点有待于纳入股东诉讼的类型之内。
(三)反收购决策权的权利主体予以明确
这一点已为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8条第2款采纳。反收购决策权主体应为股东会,股东(大)会未做出准予收购决策之前,董事会不得决定或采取任何反收购行动。但是,基于股东至上原则考虑,董事会享有向股东大会提议与建议的权力,对重大的反收购举措应由股东会决定,对于技术性的反收购措施或急迫性的反收购措施可以由董事会决定,但事后应当取得股东会的追认。
(四)法律体系的内外部统一
宏观的法律体系内,公司法制与其他部门法的联系和衔接也存在问题。举例而言,《反垄断法》虽已颁行,但在与公司法律制度中的反收购制度的衔接上尚有问题,以反垄断视角对反收购的合法性审查尚缺乏制度支撑。“立法应当鼓励和引导并购活动向创造价值的方向发展,在发展中立足于制定公平的并购游戏规则。”
[1]陆文山、项剑.论目标公司应对措施有效性的界限[J].王保树.公司收购:法律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85.
[2]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3][刘俊海.公司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1.
[4]范建、蒋大兴.公司法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388. [5]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94.
[6]王建.董事义务构造的两大发展趋势及我国公司立法的不足[J].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04).
[7]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94.
[8]曲冬梅.目标公司反收购的法律规制[J].法学论坛,2004,(02).
[9]李建伟.公司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55.
[10]刘俊海.公司收购与中小股东的保护[J].王保树.公司收购与法律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
[11]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研究[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02).
汤欣.公司治理与公司收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56.
徐华,男,江苏溧阳人,东南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D923
A
1008-4428(2017)03-1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