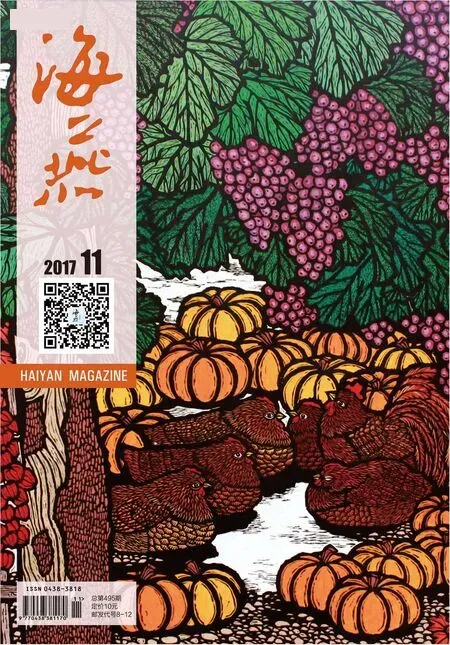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
□夏寒
散文诗
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
□夏寒
文明如满天星斗
人类的文明,从江河的源头,跋涉一段又一段。
江河水,夹着远古的遗风,追赶农耕的足迹。
此起彼伏的江河浪涛,在人类的血脉里爬过岁月、爬过花开花落的日子。
我们生命的根,扎在荒原里田野里,从刀耕火种里从垄沟垄背里培植我们坚硬的骨骼。
我们歌唱黄河,我们也赞美长江,是因为她乳汁充沛。
她喂养了中原,喂养了华夏,她的两岸长出桃花和麦子,生出了文明的星斗。
巍巍群山,莽莽江河,哪一处不养育我们的祖先?哪一处不绽开生命?
人类的文明,便是满天星斗延伸出的想象。
红山之上,是太阳的遗落容颜。
我们也歌唱梦渚的一方池塘,那一块黑泥陶片,五千年的川灵,依然保持着水与火的沉默。
但我脚下的土地多么深远,我看见今天的河畔连接着远古的荒原。
我看见了那曙光冉冉升起的地方,有一缕炊烟在慢慢地扩散。
我断言,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是家园的方向。
千山万岭间,我相信有一千条河流,就有九十九个村落。
有我八千年前的先民,在磨砺石头,在采集野果,在追逐野兽,在捕鱼捞虾。
我的小河西,我的兴隆洼,一定有远古的璧月传神,一定有远古的星光拂动我们的黎明。
月色融融,东方的鱼肚白沾满我情感的追忆。
群山,江河,平原在感叹,我的祖国啊是多么辽阔……
从游猎到兴隆洼
深山里,游猎的身影叠加,原始便开始了过度。
茅草与茅草的叠加,搭起了茅草屋的高度,眺望遍地野花。
赤脚的身影,走出深山老林,又在一幕水光接天的原始村落洞开了昨日野岭荒山的神奇……
山水相连的心事,一头沾满了沧桑,另一头的陶罐里装满了向往。
风动,小西河的水,跳动的浪花千朵万朵,每一朵都沾染了岁月的沧桑和巨变。
雨下,小西河的水,从远古的光阴里流淌,传送着深山里不便破解的歌谣。
八千年前,我的先民在深山里采集野果,过着围猎的生活。
到了兴隆洼,用树枝和茅草搭成窝棚,抑或从遮风挡雨的地窨子上空有青烟飘过。
他们在河边住下,有一幅久远的风景,一家两家三家,在水里捕鱼捞虾。
后来,他们的脸庞也绽放出了花,女人采来山花也把妆来化,苦读春天的发芽。
哦,远古的风声,你呼啸着落寞,也传送着文明。
我的先民不再漂泊。
这时有炊烟升起,我看到赤脚的先民,拿起石头制作的刀斧斩断荆棘。
开辟一条窄窄的小径,他们要把这条小径在日出日落中不断地拓宽,拓宽成明天的宽广。
原始的生活,在一片苍茫里开始改变。
从清晨到日暮,从黄昏又到黎明,西拉沐沦河,穿越了岁月的凌乱,铺展开了宽阔的水面。不断地瞭望,兴隆洼,飘渺了八千年的炊烟,飘到了黄河上下,飘过了黄河两岸!
瞬间,炊烟和我的日子,把古代文明的种子播撒!
从野生到种植的谷物
荒原里的谷子,侧耳倾听,粒粒米曲酿造的音符,跳跃着黑色的远古。
是那些细小的籽粒,塑造远大的情怀,诱我一双手掌,为古老的兴隆洼遗存炭化的植物,在野生与栽培之间,拾起一枚枚粟与黍的生长。
七千多年了,是谁在兴隆洼撒下了第一粒种子,延续了子孙的叹惜?
也许那时的兴隆洼,有蓝灵灵的天,也有清亮亮的水;也许后来教我们种植庄稼的黄帝,划开红色的波浪,炎热那个夏天,直到树木喧哗过去,青蛙的哭笑声回旋生命的需要,一任庄稼摇动起原始的谷穗。
若干年之后,兴隆洼就在那个秋天,碾子碾出了小米,捣碓的舂相盛满了碓臼的月光……
小米,那是人类最早的粮食。晨夜,一只司旦之鸡,另一只司夜之鹤。
为我,以扑鼻的米香彻底告别了深山生活的过去。
山涧溪流,杵声回荡。小米和糜子的翻滚,喂养着我的先民,也让我的先民不断地生长智慧,剩下的炊烟藏起无限的袅袅幻象!然而,原我的留香,送你——
兴隆洼的这一缕炊烟,在种子的孕育中升起,在骨制的刀锋上升起。
兴隆洼的这一缕炊烟,是从夹砂壶里升起,从石刀石斧的披沥中升起。
猛然的一刹那,兴隆洼的这一缕炊烟,化成一条腾龙,南达渤海,北至乌尔吉沐沦河,西起洵河,东到医巫闾山。
几千年了,朝朝暮暮,在黄河上下悠悠弥散,远远不仅仅是一个村庄那么简单。
空旷。苍茫而辽远的兴隆洼,百十户人家,每一户人家上空的炊烟,都在渐行渐远的蓝色里传出划时代的文明缕缕。
那是一座人间殿堂,那是人类播撒文明的心脏。兴隆洼,远古的兴隆洼……
石头和玉
石头的记忆,就是我的先民的记忆。
石头的坚实,可以堆垒生活的现实,也可以堆垒可靠的明天。
新石器时代的曙光,勾勒八千多年的颜料和品质,黑色的石头,灰色的石头,红色的石头,坚硬的石头,软质的石头……
垒砌的希望,是对美的憧憬。
石头,碰撞出耀眼的火星。
火能烧出陶罐,陶罐就能盛来繁衍生命的清水。
有了水的小小的村落,人间的炊烟才会从远古向今天延续!
西辽河的水啊,一万年磨砺的石头。
石头的光滑,磨出的日子,亮出了乳白与浅白的对话,也闪出了石头温润的心,那里涂抹着淡绿的、黄绿的和深绿的记忆。
后来的他们都知道,流水打磨的光滑,以石对石的打磨也能光滑。
尚玉之风从此兴起。
爱美的先民映着石头的性灵。
男人掘起了自然的生命,审美的风情,女人把光洁温软的玉玦戴在耳侧,装饰自己,也装饰苍茫的岁月。
然而,我的先民是虔诚的心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在性与情的分辨中,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水,甚至崇拜动物。
一颗感恩的心时时刻刻,把精美的玉器埋在这古老的土里。
时空的参证,就是他们永远的寄托与怀念。
祭坛高高,宗庙层叠。
粗犷的新石器时代,每一个千年,仿佛是刚刚过去的昨天,又好像是遥远又遥远的群山。
兴隆洼的玉器多么久远,遥遥回望,有八千年的遗香,也有七千年的魂痕。
这时,已隐隐看到青铜的光芒,在远处若隐若现。
红山文化
我站在兴隆洼的村头,遥望六千年前,回旋五千年前。
月光,那远古的意象朦胧,灵显一幕红山文化的标签,从此,神灵穿越了懵懵懂懂的眼睛,以膜拜的方式打开黎明的天窗。
路过的身影嫣然一笑,爬起的月色阅读起窗外的无限视野……
我的先民乘着原始的跫音,潜入历史的河道,用本能的翅膀把遥远驮起。
把西拉沐沦水域的月光作为意象,斜倚着岁月的墙角在前方为你引路。
等待风雕雨琢,让石头上远古的刻痕把古老呈现!
它远比人类的语言还要久远两千年。
远古,有石对石的碰撞发出来的声音,那是远古先民最早唤醒人类走向文明的天籁之音。
那种声音,从兴隆洼升起,被远古的风驮到了三星他拉,拱起了脊背,展开的想象,在石头之上写下红山玉龙的魅力华章。
风吹着远古,从遥远地带铺开一条通往文明的命脉。
先民的联想与认知在岁月里发酵,在繁衍中编织凤凰涅槃,那是一种蠕动的思想在文明里闪光。
我从斑驳陆离的光芒中,嗅到了先人的血脉在流淌,仿佛春天的种子,生发的嫩芽是森林里膨胀出的光辉。
文明,开始在红山之上,凸现思想与历史文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