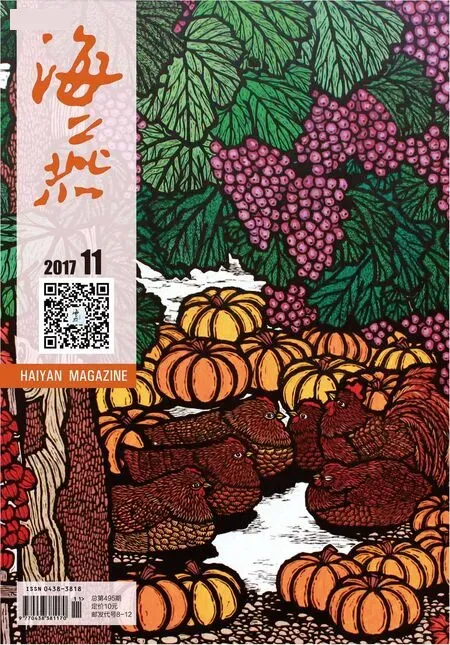北方有佳人
□柳小霞
北方有佳人
□柳小霞
那天,陆东阳在酒吧里喝酒解闷,意外地遇到了高中同学何清芳。当时,酒吧里人很多,两个人拼在一张桌上喝闷酒,喝到一半时,猛一抬头,才发现对面人很眼熟。记忆一阵旋转,俩人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在酒的烘托下,连尴尬都免了,干脆搭起伙儿来继续喝酒。直到喝得交心交肺,在午夜的街头依依惜别。
何清芳是男人性格,全无半点女子的矜持和含蓄。他们站在明晃晃的路灯下,像两个男人一样拥抱在一起,唱完了整首《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互相拍了拍肩,各奔东西,谁也没想着留联系电话。
故事如果这样豪爽地结束,倒也不失为一桩美谈。可是,第二天,不知从几时开始,陆东阳开始难以遏止地思念起何清芳来。她的妻子陈小娥自打第三次流产后,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身体不景气倒也没什么,可以慢慢地调理嘛。可陈小娥情绪受到了影响,脾气见长,要么说话刻薄,喜欢挖苦人,要么不说话,一副与世界为敌的样子。陈小娥越是怨气冲天,陆东阳对何清芳的思念便会越加强烈,想压也压不下去。要命的是,他的思念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豪迈情趣,而纯粹是一个成熟男人对一个成熟女人的思念,从头想到脚,从里想到外。起初是,昨晚何清芳穿什么衣服呢?想不起来;何清芳梳什么样子的发型呢?想不起来;何清芳脸上是什么样儿?还是想不起来。何清芳外观的一切越模糊,陆东阳的思念越强烈。他再也无法抹去临别拥抱时,何清芳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火辣辣的矫健气息。偶然一起念,一个怪念头猛可地跑到陆东阳脑子里。他想,跟何清芳这样的女人在一起,日子一定不会寂寞。这样的女人就像一坛历经发酵的老酒,有后劲,经得起在风浪里慢慢品咂。而陈小娥就是一碗清汤,放放就变味了,经不起几番细斟慢酌。想到这儿,陆东阳已经将何清芳从思想上凭空剥去了所有的衣服,而且好好意淫了一番。真想联系的话,电话一定能找得到吧,可是,纵然联系上了,又能怎么样呢,总不能再喝一次酒,再唱一回歌吧。想一想后果,陆东阳不由心惊。
隔了一天,陆东阳的思念非但没有降温,而且温度越来越高。他的思念已有些伤心动肺了。他开始拼命回忆前晚与何清芳见面时的一切细节。俩人没有认出前,他什么样儿,她什么样儿?然后,谁第一个说话,说的什么话?想不起来,怎么也想不起来。唯一能记起的,依旧是两个人拍着膀子,跺着脚唱《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情景。就像他喜欢的电影镜头一样,这一幕总在他脑海里慢慢回放。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陆东阳哼着变了调的《三国演义》主题曲,越想越伤感。一定得找到她,哪怕是叙叙旧,然后呢,然后呢,陆东阳不敢想。
管他呢,大不了再唱一回《三国演义》。就我和她,就那么豪迈地唱。对,就这么办。这个念头也只是稍纵即逝。陆东阳什么决定也下不了。怪就怪陈小娥那个病兮兮的女人,把我大男人的气慨全消磨干净了。陆东阳想一阵儿何清芳,又想一阵儿陈小娥。心波荡漾,难以了断。
好像有人在院子里喊了一句:
“陆乡,你的对象来了。”
陆知道这句话仅仅是一种乡镇干部的调侃,毫无恶意。可他不习惯,心灵有所受伤。他们所说的对象是乡上的一个傻姑娘,名叫宝花,十七八岁。两个月前,陆东阳刚到乡上,看见宝花在乡政府院子里瞎转悠,以为是前来办事的群众,就过去搭讪了几句,结果被这个宝花姑娘活生生缠上了。打那后,宝花每来院里,就必要来看一眼这位新来的陆副乡长。陆东阳其实只是个挂职,身份微妙,里外都得夹着尾巴做人,谁也不敢得罪。听到这种调侃,心里不爽,面上还不能表现出来。
陆东阳皱了皱眉,站起身想关门。
他的对象却已经进来了。让陆东阳颇感意外的是,这次来的不止宝花一个人,后面还跟着一位上了年岁的农村妇女。不用问,一看模样便知是宝花的亲娘。母女两个一模一样的圆脸,小眼睛,短头发。
陆东阳又好气又好笑,只得坐下来静看事情的发展。
宝花还是像前几次一样,进来后也不落座,而是好奇地问东问西,和陆东阳说一些三四岁小孩子的话。
宝花妈妈一脸愁容,慢吞吞进来,坐到陆东阳身旁的沙发上,用一种极慢的语调说:
“老天又降下罪给这个傻丫头了,你可得帮帮忙啊。”
陆东阳一头雾水,没听明白,心情不好,心里依旧惦记着何清芳。于是摞下一句:有事儿你得去找别人,我不管这儿的事呢。陆东阳的动作已经是准备出门的样子。
宝花妈妈这下子不再慢吞吞了,而是急切地说:“找了,都找了,他们都说管不了,也不归他们管,书记说,你是城里人,兴许有办法。”
肯定会有办法的,只要问问别的同学,就一定能查到何清芳的联系电话。然后,然后……陆东阳想,想得非常刻苦。
宝花妈妈自顾自地说:“这个傻丫头,我一直不知道,前天才发现,都四个月了,医生说,像她这种样子,做手术得镇上签字了才行。”
前天,何清芳怎么会一个人喝闷酒呢?我是老同学,管一管她不算过分吧。一会儿就打电话,问号码。陆东阳看了看宝花母女,奇怪她们怎么还不走。
宝花妈妈说:“他们都说,你有办法,能帮上忙。不行你就打个电话,我们自己去找城里的医生。”
一提电话,陆东阳的心总算收了回来。他脸上明显带着诧异,问宝花妈妈给谁打电话,到底是什么事情。
宝花妈妈表情严峻,一副只想解决问题的样子,简短地说:“不知道谁欺负的,前天才发现,医生说,都四个月了,做手术得镇上签字了才行。”
陆东阳与其说是听明白了,不如说是看明白了,因为宝花配合着她妈妈的话,走到他跟前,掀起衣襟,让他看自己鼓起的肚子。
陆东阳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吃惊于眼前这个十八岁傻姑娘的意外怀孕,而是立马痛心起妻子陈小娥的三次流产。
她怎么就不流产,一怀就是四个月,还人不知鬼不觉,连自己亲娘都能瞒过去。陆东阳总算放下了何清芳,心思纠结到了女人的怀孕和流产上。流产两个字成了陆东阳心头的毒刺,时不时要冒出来扎他一下。他很怕听见别人提起这俩字。女人为什么会习惯性流产,陆妈妈有一个一针见血的解释:肯定是以前刮过呗。
女人看女人多么透彻,这一句话让陆东阳从此对妈妈和妻子都有了隔膜。
陆东阳有些纳闷,问:“为什么不能流产?”
陈小娥流产了三次,他陪着去了三次医院,从没听哪个医生说过不能流产的话。
宝花妈妈已经找过好几个乡干部,解释了好多遍不能流产的原因,知道哪些是废话,哪些话才算是说到了点子上,所以这次她两句话就向陆东阳说明白了:月份大了,孩子长结实了,得做大手术,宝花是傻子,要有能担事的人签了字医院才能做引产手术。
陆东阳眼前尽是陈小娥流产后发黄的脸。他悲悯地从回忆里走出来,感叹了一句:多好啊,一下子就能长结实。
宝花妈妈听了这句感慨,愣住了,早已沉淀在岁月深处的母性有所萌动,心中绷了很久的弦仿佛被什么人弹了一下。她心头一紧,不由想,就是呀,那也是个小人儿哩,哪里能说取就取了。这几天几次三番碰壁早已使她意志薄弱,此刻听陆东阳这么一慨叹,她那女性的心彻底软了下来。她有些讨主意似的,向陆东阳一字一正地说:
“这儿书记说,你们城里人老爱流产,有的是办法。”
这句话太刺人了,简直是向陆东阳心口开了一枪。陈小娥第三次流产后,陆东阳为了照顾她,请了几天假。请假时,出于一种男人无助的心理,他曾向乡书记提起过妻子的流产史。没想到自己的坦诚竟给他等来了这样的事情。王八蛋。陆东阳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决定小小地报复一下乡上的书记,给他找点事做。
陆东阳给宝花和她妈妈倒了茶,让她们慢慢喝,不要着急。他甚至暗示了一句:女人怀孕不见得就是坏事呀,现在这社会里,很多女人想怀还怀不上呢。
一句话把宝花妈妈从悲摧境地给提到了烟火人生的光明坦途上。她一面喝着茶,一面敞开心肺,向陆东阳说了一些陈年旧事。她提到了自己的五个女儿,提到了自己未出世而被乡上计划了的儿子,提到了自己死了十年的老伴,也提到了宝花除了脑子不灵光,其实是个好姑娘。她还说了一些村里谁谁谁家没有孩子的话。
陆东阳耐心地听她絮叨完,正了正坐姿,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医生到底怎么说,娃娃四个月了,应该挺好的吧。
宝花妈妈心里漫过一层感动的泪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问宝花肚子里的孩子好不好。人家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啊,会说话,会想事。
“好着呢,医生看了B超。我也看了,那个娃娃会动,一跳一跳的。”
提到B超里的娃娃,宝花妈妈脸上明显浮出一种优越感。村里的女人,有几个亲眼见过肚子里的孩子。别人没见过,她见过,她便觉得自豪。
“娃娃的头又圆又大,像个男娃娃。”宝花妈妈又得意地加了一句。一提到“男娃娃”三个字,这个乡下老妇人的心又翻腾了一下。对啊,应该是个男娃娃,她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呢。
陆东阳的心里莫名地升起丝丝醋意。他假想了一阵那个站在B超机前看屏幕的人是他。他看着,笑着,激动地只想拥抱一下妇产科的每一位医生。
他理了理气,用一种貌似平静的话语说:
“怀娃娃好啊,是好事,女人就该怀娃娃。”
宝花妈妈心头的暖流又一次激荡了起来,这句话简直就和夸她的姑娘聪明,有本事一样。
她说:“就是。”
“宝花多大了?”陆东阳问。
“虚岁也该二十了。”宝花妈妈说。
“我看您身体也挺好的,还不到六十吧?”陆东阳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起来。
“刚好六十哩。”这次宝花妈妈没有说虚岁。几句家常话一下子抚平了这个乡下女人心头的震惊和无奈。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娃娃兴许是上天专门送到我家来的呢。你看看我,真是老糊涂了,这两天一时心急,差点做出傻事来。宝花傻可我不傻呀。心一触到这儿,宝花妈妈吃惊不小。
陆东阳关切地说:“要不行,我问问城里的几家私人医院,看看有没有办法。不过,那些医院费用高,还不安全。”
宝花妈妈慌忙拉起女儿说:“不麻烦你了,你可千万不要问。我这半天总算想明白了,这么好的娃娃到了我家该是我家的福气才对。我要宝花好好生出来,等我拉扯大了好给这个傻丫头养老哩。”说完,母女二人一阵风似的走了出去。
陆东阳看着她们的背影,报复的快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室内的静寂助长了他的落寞心情。怅茫、无助仿佛长了翅膀,从宝花妈妈的脸上飞到了他的脸上。必须得有个孩子,他痛下了一阵决心。
电话响了。到乡下后,陆东阳的电话明显少了许多。这个时刻响,十有八九是陈小娥。那张泛黄的病脸又兜回了陆东阳的脑海。陆妈妈嫌恶的话像刀子一样扎着他的自尊心。
陈小娥例行公事式地问:“在哪儿呢?”
陆东阳干巴巴地说:“乡上,还能在哪儿?”
陈小娥声音矮矮的,带着八分的讨好语气,又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陆东阳说:“不知道。”
陈小娥再问:“真的有那么忙吗?”
陆东阳已经不耐烦,说:“忙,忙还有真的假的,你以为是你们女人怀孩子啊。”
陈小娥声音更矮了。她顿了顿说:“以前没听你说过忙啊。”
陆东阳说:“以前不忙,现在忙,忙着抓计划生育呢。”
陈小娥不说话了。陆东阳听了几秒钟,没听出什么动静,“啪”一声挂上了电话。过了不到三分钟,电话又响了。陆东阳有点生气,抓起来,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你有完没完啊 ,这儿全是大肚子女人,忙得很。”
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既而爆出一句充满磁性的声音:“老同学。”
何清芳火辣辣的气息扑面而来。陆东阳只觉得心膜间的冰川顷刻消融。他望了望门口,低声说:“怎么是你,你哪来的我的电话?”
女中音的中气更足了,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后是一句男人式的问候:“忙什么呢,老兄?”
陆东阳干脆起身关上门,用幸福的男低音说:“乡下受苦呢,才送走一个为了计划生育上访的。”
何清芳说:“怎么,还抓计划生育!不是全面二孩了吗?你糊弄谁呢!”
陆东阳说:“出了一点小意外,群众利益无小事,尤其生孩子。你呢,在忙什么?”
何清芳说:“这两天净想你了,专等着你请我喝酒呢。”
这分明是一句调侃话。陆东阳听了很受用,闷头闷脑来了一句:“真的?”
何清芳又笑了。她转了话头,夸陆东阳嗓音好。
前天午夜街头悲壮的一幕一下子推到了陆东阳的跟前。《三国演义》主题曲像咏叹调一般在整个房子里弥漫开来。
陆东阳没有接着夸何清芳的嗓音,也不想问她在哪儿,在干什么。他想满足一下自己心头的渴望,想解开这两天困扰心头的那一个个谜团。
他问何清芳前晚穿什么衣服,自己怎么总是想不起来。
何清芳并未觉得唐突,而是淡淡地说:“不记得了。”
又问何清芳梳什么发型。何清芳说:“我能有什么发型,短发,学生头,二十年没变过。”
陆东阳像个孩子一样,有点不依不饶。他又说了一遍,真奇怪,我怎么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何清芳说:“想不起来就对了,我说你一个大男人,那么婉约干什么?”
陆东阳心头有点发酸,说:“那晚唱歌的样子真叫悲壮。”
何清芳被“悲壮”两个字逗乐了。她夸陆东阳有才,唱个歌都能引发悲壮情怀。
陆东阳又一次孩子气十足地说:“就是悲壮嘛。”
何清芳不想纠结于细节,干脆就此打住话头。她说:“得了,少谈往事,往事早就该滚滚长江东逝水了。老同学,今晚请你吃饭,老地方,不见不散呐。”陆东阳还未反应过来,何清芳已经挂了电话。
短发,我怎么记不起来她是短发。陆东阳一面从淡淡的回忆里拽着何清芳的影子,一面心急火燎期待起晚上的重逢。他和陈小娥的生活早已锈迹斑斑。他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时间还早,还有一个漫长的下午。陆东阳什么也干不进去,干脆打开电脑听歌,歌曲自然是《滚滚长江东逝水》。
他照了照镜子,理了理头发,哼着旋律,躺到沙发上,进入了人生最曼妙的回味之中。
《三国演义》主题曲的旋律一会儿结束了。陆东阳正准备起身压重播。正在欲起未起之际,又一段低沉的旋律响了起来。这段旋律陆东阳始料未及。他几乎被迷住了。旋律更宽厚,更低沉,歌词不长,只有短短六句: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
陆东阳以前从未听到过这首歌,一定是刚才操作电脑时,心情过于激动,没有看清屏幕,不小心选了上去。他无暇细究电脑操作,旋律的深厚令他大为诧异。
陆东阳是中文系毕业,对这首古诗他是非常熟悉的,熟悉到知道它的作者,产生背景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只是这旋律,这歌唱者的嗓音,好像是隔着渺茫时空向他包围了过来。他此刻的心情只能用一句极庸俗的话语来形容:他的心扉被打开了。
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要生孩子?因为爱。真是瞎扯淡。陈小娥的三次流产已经让陆东阳彻底明白了,男人和女人生孩子纯粹是因为怕被这个世界遗弃,因为惧怕婚姻生活中出现虚无的黑洞。他陆东阳什么都能扛,就是扛不住这深邃的寂寞。好像世界能与他失去所有的关联,他的人生掉进了布满灰尘的无底洞里,需要他时刻聚起能量去抗争。不想则已,一想便是一阵难以抵制的绵软的恐惧感。
现在,他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对每一位个体的人生有了一种很自我的看法。他认定时代的兴旺和一个人的兴旺一样,一定出现在生育力最强劲的时候。生育力败了,一切都扯淡。
陈小娥枯黄的脸颊在陆东阳眼前再次晃了一下。他心头一狠,低声骂了一句:“该死的女人。”
他早已没有心情继续伪装下去,就像是一种本能,他对所有带有枯萎迹象的生命力会产生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从他内心最隐秘的角落里蔓延出来,好似无意间打开了潘多拉的宝盒,心魔已成了他七情六欲的一部分。
他想,换了别的男人,会不会认为流产很爽,很值得人去怜香惜玉呢。每念至此,委屈伴着愤怒便会一起到来。如果陈小娥是一株弱不禁风的花,他恨不能将花连根拔起,烧成灰烬。
说真的,他厌倦极了陈小娥那张哀怨、无助,甚至无辜的脸,仿佛是陆东阳伤害了她,而她则用女性特有的宽仁胸怀承受着,容忍着。
有时候,陆东阳甚至对女性生出一种普遍的厌烦情绪。陈小娥在她生活中代表着一切容易受伤的女性,还有他那个说话刻薄的妈妈。
那一天,陆东阳走在大街上。他落落寡合,看着身边各色女性走来走去。他惊奇地发现,所有的女性,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丑陋的还是美貌如花的,无不带着一种相似的表情:她们个个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这一发现令他有了一种切肤之恨。在层层恨意的包裹下,他将每一位走过自己身边的女性都从意念上脱光了衣服,然后怀着报复的快感,将她们的隐秘世界翻了个遍。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真的能看见每一个女人衣服下所掩盖的一切,比如色斑,比如暗疮,比如手术疤痕。他甚至能隔着老远闻出她们身上不同的气息,哪怕是隔着一整条马路。
他被自己短暂的灵魂出窍状态吓坏了,等意识稍稍有所恢复,他便钻进附近一家酒吧里喝起了闷酒。就是这一天,他遇上了同样喝闷酒的何清芳。
他回想起午夜街头相拥高歌的那一幕,心中的悲壮情怀日渐浓烈。此刻,他的心怀里,他和何清芳已经幻化成了一对乱世英雄,整个世界都渺小得成了他们脚下的那一块砖。
何清芳洒脱、不隐忍的表情激活了陆东阳身上的雄性意识。男人真的需要一个广阔而自由的空间释放自己的能量,而不是在女性的隐忍下独自抚摸折断的翅膀。
《北方有佳人》古朴的旋律结束了,屋子里一片静寂,一种足以吞噬人心的悲凉漫了上来。陆东阳享受了一会儿悲凉的心境。很快,对何清芳的坚实思念盖过了无人分享的孤独感。何清芳已不再是一个具象的女人,而是一种心底的渴望。何清芳的形象一会儿是丰神炯仪的白领丽人,一会儿又变成了驰骋沙场的花木兰;一会儿在湖中采莲,一会儿在月下浣纱。这种种幻象最后都会对陆东阳回眸一笑。在胡思乱想中,陆东阳一次又一次地满足着他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自尊心。他痛恨着貌似伟大,实则虚伪的隐忍,渴望着坦露心迹。在他看来,哪怕是女人的仇恨也比隐忍强。他只需要这一点点。
何清芳是个守时的女人。她比陆东阳早到,而且已经点好了菜和酒水。这样,连点菜时的虚套话都免了。
何清芳见面第一句话便是:坐吧,老同学,菜已经点好了,你今天随我吃。
陆东阳的开场白则显得有些寡淡。他用一种惯常的外交辞令说:
“哪能让女士请客,你点菜我埋单。”
何清芳依旧大大咧咧,她两眼直盯着陆东阳,说:
“好吧,你掏钱,早知你大方,我该多点几个菜。你前晚的壮怀激越到哪里去了?”
何清芳一提壮怀激越,消失在午夜街头的那种悲壮气息登时回来了一部分。原来,她也感念那晚的情调呢。两人间的气场随之呈现出温暖、张扬之势。
借着何清芳的打趣,陆东阳大着胆子看了一眼这位昔日学友。他吃惊地发现这位女同学并不是传说中的短发,而是一头浓密的波浪长卷。何清芳脸上略施薄粉,显然她很注重外在的形象。
何清芳猜透了陆东阳的心思,她故意抖了抖肩上长发,说:
“看什么呢,难道就不兴我时尚一下。这两年才留的长发,以前可不都是短发。”
陆东阳问:“你们女人为什么喜欢把头发弄成外国女人的样子?”
何清芳说:“看不出来啊,老同学,竟然欣赏东方美女。知道吗,女人烫头发是因为懒得梳头。”
这个答复着实让陆东阳感到新奇。在他的感官里,何清芳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母豹子。他无法将这样一个女人和懒散画上等号。
何清芳说:“女人有两种,一种勤快,一种懒散。勤快女人都是贤妻良母,喜欢在家相夫教子;懒女人嘛,喏,这酒吧里的全是。这里的女人,家里基本上是指望不上的。”
陈小娥苍白的脸像个幽灵一样又钻出来刺了陆东阳一下。纵然在想像中他也无法抹去对病态女人的反感。他恨不能将这个无时不出没的幽灵打入十八层地狱中,永世不得翻身。
就连这幽灵昙花般地一闪现,何清芳似乎都洞穿了。她含笑望着陆东阳,一脸天真地问:
“你们男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婉约女人呢?”
陆东阳没有听明白,问她什么叫婉约女人。
何清芳说:“婉约女人嘛,就是动不动哎哟哈哟,这儿疼那儿不舒服,处处想让男人关心一下的女人。这种女人是不是特能满足你们男人的保护欲。”
尽管大学毕业十多年了,可陆东阳对文学至今还心存着最基本的敬重。一提婉约,他立马想到了南宋词人李清照。何清芳对婉约的轻描淡写引起了他稍许的反感。他一本正经地说:
“婉约可不能这样解释。它是一种文学表达手法。李清照可是真正的女中豪杰呢,她只是写的词婉约。李白写的词照样也是婉约的。”
何清芳看着陆东阳的认真样,努力抑制住笑。她没想到陆东阳竟会和她在酒吧里大谈文学命题。她只读过中专,而且是经济类的,毕业后没有工作,一直在经营一家玩偶店,连她的丈夫都是她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说真的,她更喜欢将丈夫叫作合作伙伴。如果有人称丈夫为她的爱人,她会觉得不自在。
她明显感觉到了陆东阳微妙的情绪变化,故意眨巴了一下眼睛说:“老同学,赶明儿闲了你也给我这个粗人补补文化课呗,别光你高雅,而我不高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你是阳春白雪,我是下里巴人,对吧?我粗放经营惯了,也好好婉约婉约。”
大约是受酒吧里朦胧气息的熏染,何清芳的性子有些兜了起来。她故意抿了抿额角鬈发,翘起兰花指,冲陆东阳挤眉弄眼了一番,接着说:
“你看我这叫婉约吗?”
陆东阳被她逗笑了。他打趣了一句:“你那叫贵妃醉酒,杨贵妃可是豪放到家的女人。”
菜陆续端了上来。这些天,陆东阳陪着陈小娥吃淡饭,肚子里很缺油水,尤其今天,他几乎连午饭都没怎么吃。这会儿见到热气腾腾的菜,他的饿劲儿立马上来了。因此,这场关于婉约派与豪放派的论争就此打住。在最真切的欲望面前,凭空谈论文学和人性也未免太滑稽了些。俩人都拿出饮食男女的本色开始对付桌上的菜,话题顺理成章地转入了对中学时光的缅怀之中。
就像所有的逢场作戏一样,追忆和清点同学当下状况似乎成了同学见面时必经的程序。没有这一关,似乎就有点亵渎纯洁的同学情义了。
倒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用心去钩沉。何清芳的不耐烦很快将两人从无趣的回味中捞了出来。只是现实生活庸俗的本来面目仍旧延续了下来。
陆东阳痛惜着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悲壮情怀。他不再怀念前夜他们抱头高歌时的火辣辣气场,而是为今天下午听《北方有佳人》时的那些浮想联翩莫名地伤感着。就是那样独享孤寂,而梦想犹存的时分也是不多见的呀!
何清芳在这短暂的庸俗气息冲击下,心跑到了自己生活的深处。她忽然没头没脑地问陆东阳:
“你说我像女人还是像男人,为什么他老嫌我不像个女人,没个女人样。女人样是不是就该老得个小病,时不时歪叽歪叽?”
陆东阳心想,你本来就是个女人,有什么像不像的,女人再装她也装不出个男人样来。何清芳这一句话等于将自己的生活全部敞开到了陆东阳面前。很显然,她和丈夫琴瑟不谐。她的丈夫全不拿她当回事。他们的婚姻纯粹是靠生意维系着。何清芳心里是有隐痛的。
陆东阳没有直接回答何清芳的问题,而是说:
“你喝酒时的样子最可爱。”
这句话有点讨好意味。何清芳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悲壮情怀似乎又在慢慢往回走。陆东阳看着何清芳脸上的红晕,心跟着酒劲飘摇了起来。
他心想,此时此刻,唯有女人脸上的红晕才算是真正的婉约。不过,这话他说不出口。他不忍将婉约扯进庸俗里。
何清芳抚着面颊说:“真是有点醉了。他最嫌我喝酒,说我全无女人样。女人是什么样啊,我最烦女人哼哼歪歪。”她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无助,不过很浅。
陈小娥的脸又闪了一下。何清芳的这句话立马使两个人产生了同壕战友的情分。陆东阳举杯说:“对,打倒病病歪歪,向一切豪放派女性致敬,干杯。”
酒下肚后,陆东阳问:“知道我喜欢什么歌吗?我跟你说啊,今天下午……”
何清芳说:“得了,又要滚滚长江东逝水了。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歌。高三毕业时,班里搞临别联欢,你上台唱歌,说你最喜欢一首歌,然后你唱了几句。你那个调跑得呀,都跑到旧社会了。那时,我都想替你唱下来。”
陆东阳愕然。他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喜欢过什么歌。他是一个对音乐没啥感觉的人,唱歌于他更多的是身体语言。何清芳一提醒,毕业联欢会上的情形他记起来一点点,不过也只是这一点点而已。
陆东阳是复读生。第一年他以五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他打了半年工,做苦力,卖草药,甚至在街头帮人刷过小广告。有一次,他帮一户人家搬东西。他费尽气力将一箱物品扛到了六楼,打算往地上放时,结果气力用尽,箱子倒了下来。箱子上面的几本书散落地面。陆东阳爱书,一本一本往箱子里归置。出于一种对学生时代的留恋,他捡拾那几本书时顺便打开翻了翻。书的主人见他翻书,颇为不耐烦,说,快搬东西吧,你又看不懂,翻什么翻。几句话让陆东阳受了刺激。从那晚开始,他收拾起闯荡江湖的野心,找到旧书包和中学课本,开始发愤读书。余下的半年里,他天天三更灯火五更鸡,连头悬梁,锥刺骨都用上了。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二年,陆东阳以超过重点线十八分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何清芳就是他复读这半年里的同学。所谓的毕业联欢其实和他并没有多大关系。他心态轻松,带着对学弟学妹们的鼓励上台演唱,想用歌声激起同学们赶赴人生第一考场的斗志,也算是自己给自己打气。至于细节,他倒是全忘了。
何清芳说:“那天,没人愿意上台表演,你第一个站起来,一上去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第一句你就开始跑调,不过,你越跑调,大家越高兴,气氛也越来越活跃。那时我还真有点喜欢你呢。”
这句话颇让陆东阳感动,能记住自己喜欢的歌,这同学情义立马又稠了许多。
前夜的感觉又回来了,悲壮,热切,带着火辣辣的气息。陆东阳真有点迷恋这种气息。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他陆东阳永远只喜欢坦露心迹的时分。“北方有佳人”,那位古人,他心中的佳人到底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呢。那位倾城又倾国的女子到底拥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惊天之美呢。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美?陆东阳的心又不免带上了一层理想主义光环。如果世间真有那么一位佳人,他宁愿抛弃一切去找寻这种美。连他自己都觉得他现在所有的欲念其实都是在做困兽之争。争来争去,陈小娥苍白的脸最终幻化成了几面刷了白粉的墙。他就在这墙里面。
何清芳举杯,俩人对饮。何清芳说:
“不为别的,只为了青春年少时代的壮怀激越。”
是啊,壮怀激越,他陆东阳也曾壮怀激越过。大学毕业后,陆东阳又冲刺了一把,考取了故乡的公务员,算是解决了终身的就业问题。别人眼里,他的人生已是春风得意,前程辉煌了,而只有陆东阳自己知道,他的心灵总是怀揣着怎样的一种危机感。他每天都跟林姑娘进了贾府一样,小心翼翼,谁也不敢得罪。他知道他没有得罪人的资本。在生活中,他完全是一个奉行中庸之道的人。而他的本性却又告诉他,他陆东阳并不愿意在庸俗生活彰束手就擒。他喜欢绚烂,喜欢跌宕有致的生活。他多么希望漫长的生命能开出花,结出果来。
陆东阳说:“对,为了壮怀激越。这年头,啥都好找,唯独难找壮怀激越。”他喝酒很干脆,一口下去,酒尽杯立。他真想把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抽出来,然后加一把酒精,再亲自把它点着。他一定会为了这把火且歌且舞一番。
何清芳忽然问,你们怎么还抓计划生育呢,不是可以生两个孩子了吗?
下午的玩笑开得有点重了,陆东阳只得将宝花姑娘的事向老同学说了说。岂料,何清芳听完,含笑望着陆东阳,直望得陆东阳心里发怵。望完了,又兜头来了一句:那姑娘天天找你,八成是喜欢上你了,那孩子该不会是你的吧?
一句话差点让陆东阳将酒喷到何清芳脸上。下午见到宝花母女后的种种思绪一晃而过。他到乡上挂职已经两个月了,对乡镇上那种庸俗到近乎无聊的调侃他已经逐渐麻木了。现在经何清芳这么一打趣,他终于明白他陆东阳何以会陷入宝花姑娘的迷魂阵里怎么也脱身不了。原来那傻乎乎的姑娘身上自有一种生命之初的天真无邪劲儿。那姑娘从来没有让他感到过庸常生活的压力,相反,他见到那姑娘心情就会轻松起来。乡镇上的干部们虽然有事没事爱拿宝花取笑,但对这个姑娘谁也不讨厌。除了开开玩笑,谁也不会动粗口。相反,大家都会有意无意地保护宝花。如果宝花在饭点上出现在乡政府院子里,总是会有人给她端碗饭去。谁也不觉得这个举动有什么不妥。这个宝花好奇心永远停留在三五岁,见啥问啥。人们竟像喜欢三岁娃娃一样喜欢她。呀,原来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姑娘身上永远洋溢着一种健康的生命力啊。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莫不对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充满了迷恋。没有人会真正喜欢病态的生命。在乡间广阔的土地上,也没有人会去追究“那么,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这个命题。追究是毫无意义的,明摆着会和乡镇即定秩序产生严重的违和感。人们其实都不愿意让任何现代文明思维介入到这个傻姑娘身上。所有的人都是在有意无意地阻止着“流产”这件事情的发生。大概这才是宝花母女最终出现在陆东阳面前的真实背景。正如人们所料,陆东阳的几句话便促成了“留下孩子”这个潜愿望的实现。假如他陆东阳一时头昏,真帮助宝花母女流产了孩子,那么他陆东阳怕是在乡上待不下去了。他会背负上深沉的生命罪恶感。
真是醍醐灌顶呐。就是在酒精的作用下,陆东阳也不免一心惊。汗随之如雨而下。倏忽间想明白了这一切,陆东阳心头不由豁然。他用真诚接住了何清芳的取笑。说:
“那要真是我的孩子,我还高兴死哩。”
何清芳自知问得莽撞,嫣然一笑,说:“有句话咋说来着,看来没文化还真不行,说什么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陆东阳替她说了。
和面包会有的同时出现的还有何清芳的丈夫。奇怪的是,陆东阳并没感到突然。
何清芳的丈夫似乎是带着三两酒出现在他俩面前。他没有理会陆东阳,而是直接对何清芳说:“妖精,你是不是该回家了。”然后俩人一阵风似的出去,把个陆东阳尴尬地扔在了酒吧里。
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大概就是我陆东阳一生的注解呐。陆东阳自我解嘲了一番,结清账单,借着酒劲,在众目睽睽之下唱着《万里长城永不倒》走到了大街上。街市上华灯绚烂,如同他对命运的期冀。他仰望着并不明朗的星空,不由一阵感叹: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他甚至有点感激起何清芳的丈夫来。若不是他横刀出马,这午夜的街头,他将该如何结束这第二次的亲密接触。他讨厌谢幕的感觉。
回家已是凌晨。屋内漆黑一片。陆东阳实在不想面对清醒的陈小娥。他舒了一口气,向卧室走去。
这时候,身后的沙发上猛可地传出陈小娥幽怨的声音:
“你的计划生育搞完了?”
陆东阳不提防,给吓了一大跳。他回头发现陈小娥漠然地坐在黑暗里,那形象简直有点鬼魅了。
陆东阳的情绪一落万丈,他明显底气不足地说:“你搞什么名堂呢,跟鬼似的,吓我一大跳。”
陈小娥说:“你还知道害怕呀。”说完,紧闭双唇,站起来,兀自走进了卧室。
陆东阳木然地站了一会儿。陈小娥脸上坚不可摧的隐忍令他又开始心灰意冷。凄苦、无助像烟幕弹一样从屋子的各个角落钻了出来,开始缠绕他,吞噬他。他定了定心神,跟在陈小娥后面也走了进去。
这可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两个人在黑暗中各自掀起被子一角躺了下去。陈小娥似乎已不是一个有血肉的人,而是一缕满含着哀怨的空气,随时准备着无孔不入。这一想法很快在陆东阳身上产生了反应,他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宛如死人叹息般的恐惧感。生活在随时准备着塌下它光辉明亮的一面,他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能支撑着,而不至于沉沦。
现在,连空气都是隐忍的。
陆东阳心头升起一种强烈的破坏欲。可是隐忍,这坚不可摧的隐忍……他有所洞悟,最终他也选择了隐忍。也许,在恐惧面前,只有隐忍才能抵抗得住。他内心深处得意地笑了笑,然后又开始了对何清芳无休止的思念。今晚的思念来得更强烈,也更真切。沉闷的空气有所松动,一丝曼妙而又婉约的情调漫过了他有些灰凉的心田。
他毫无出息地想着何清芳的发型,她略施薄粉的脸,她说过的每一句话,暗暗品咂着她身上灼人的气息。他有点妒恨起何清芳的丈夫来。尽管何清芳将他称之为生意合作伙伴,可在陆东阳心目中,丈夫就是丈夫,他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尤其当一个女人抱怨男人的时候。
必须得再见面,好好说一说我的这种思念。陆东阳在半梦半醒中想。
梦很快来了。何清芳穿着一袭古装向他走了过来。越走越近。陆东阳心情激动,急忙去拉手,仔细看时,向他走近的人却不是何清芳。来人短发,圆脸,小眼睛。陆东阳想,这个年轻女子如此眼熟,他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呢。
陆东阳遽然惊醒,才发现自己满身大汗。他翻了翻身,看见身边陈小娥已睡着了。城市灯影下,陈小娥的身影越发显得单薄无力。陆东阳的心中不免一阵酸楚。哎,女人呐,你的名字叫弱者。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猛可地跳了出来。陆东阳叹口气,将被子往陈小娥那边拉了拉。
陈小娥在梦中嘟哝了一句“管他呢。”翻个身,又睡了过去。
责任编辑 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