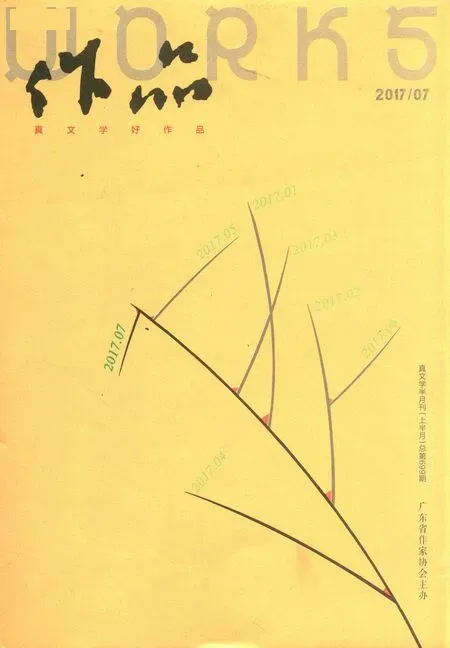忆父辈的诗友
文/王则楚
忆父辈的诗友
文/王则楚
王则楚1945年3月出生于浙江温州,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聘参事,广东省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文史专员,广东广播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近日,在永昌堡(我们家宗祠)后人的群里有人发了一幅夏承焘先生书写给施执存的字,内容是父亲(王季思)论诗的一段话:山谷谓作诗如作杂剧 临了须打诨 方是出场 其和子瞻戏效庭坚体诗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 公如大国楚 吞五湖三江 皆能诗 言结云 小儿不知客 或(可)许敦庞 诚堪(婿)阿巽 买红缠酒缸 则打猛诨出矣 。勾起了我对父亲与亲人、友人诗词来往的回忆和思考。在父亲111岁诞辰和去世11年之际写下来,做个备忘。
温州是诗人谢灵运的故乡,诗词歌赋和南戏一样,在温州人的生活里是一个有机的组成,在文人墨客来往之中都有许多记载。我们家的祖上有许多的诗文和戏曲故事留下来。记得父亲就讲过,戏剧《荆衩记》里,丞相的原型就是我们王家的先祖。清朝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清廷曾经下旨对温州免赋救灾,但府县地方官仍匿旨不宣,照常征赋。曾祖父王德馨字仲兰写文章揭露知县陈宝善违抗朝廷,匿旨擅征。被县官派人捉拿。仲兰公越狱逃亡北方,流亡了好几年。归来之后,他在积谷山下的东山书院当山长,面对诗人谢灵运的池上楼与春草池,他吟诗作画,成为一时名宿。他的诗曾被民初大总统徐世昌编入《晚晴簃诗抄》,至今在温州图书馆还留有诗集《雪蕉斋诗抄》。
家传的诗文爱好自然也一直在王家这个书香门第里影响着每一个人。在父亲那一辈里,父亲的大姐夫陈仲陶是南社的成员,和柳亚子先生都是同期的南社活跃分子。他与温州刘节的父亲都有聚会的记录。他的《剑庐诗钞》有柳亚子的题词:豪气元龙百尺篓。瓯江江上旧风流。一门更喜都人杰,六秀从来世少俦。章士钊也题长句一律,其中说他“吐纳众流成别士,推排细律作词人”。他在重庆的时候,还收了民国第一侠女,为报父亲被割首示众之仇而亲自开枪打死孙传芳的施剑翘为徒,成为诗坛佳话。父亲在《剑庐诗钞》的“后记”里承认:我青少年时期写的诗文经常得到他的指点,他后来写的诗词也往往抄给我看。这种家传的诗风,也使父亲得以交会了许多诗友。
前面提到的夏承焘就是与父亲有深交的诗友。他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这些来往在父亲的书里、夏承焘的日记里、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章里都有提到,但最集中、最有影响的还是1957年1月父亲邀请夏承焘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交流的那次活动。整个活动、以及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交流都有详细的报道。我当时只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大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我是不了解的,但家里准备饭宴请夏承焘先生的美味佳肴倒是记忆深刻。那天,妈妈是特别用心地安排父亲和夏先生之间喝酒的菜,一般的凉菜当然有,但温州的鳗鱼片夹肉我记得就吃过这一次。那是头天晚上就把鳗鱼干泡软了,热后斜斜地切成薄片,和水煮熟的五花肉凉冷了切成薄片,梅花间竹的放在盘里,再上蒸笼蒸熟,放到温热才端上桌。那在厨房里的香味,就已经让我忍不住偷吃了。那天是父亲53岁的生日,饭前,爸爸请夏承焘先生书写他自己撰写的对联: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卿同梦,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这是父亲描写他和母亲爱情的一副对子,母亲也特别喜欢。那红底宣纸上是撒着碎金点的,铺在家里的饭桌上,父亲把书房里的笔砚拿过来,父亲亲自研墨。后来,我还去帮着研墨。夏先生写到“卿”字之前,母亲也过来观看,对“卿”字,母亲提出改为“子”字,夏先生遵嘱写下。字裱好之后就挂在家里的饭厅。我一直记得写的是: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子同梦,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文革前在北大的政治学习的思想汇报里,我还说过这副对子,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父亲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孝子贤孙。此汇报还被高年级的同学看到,很羡慕地抄下这副对子。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近日,则柯哥哥在回忆文章里也肯定了是“子”字。并且抄录了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在夏先生的日记里写明是:“午饮季思家,是其五十三岁生日。属写一联曰: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子同梦;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其夫妇二三十年前故事。”一年之后,母亲因病去世,一字之改,深深地把母亲对子女的母爱、和希望父亲能够与子女同梦的爱情化在了这个对子上了。可惜,文革之后再也没有找回这副对子。
我记忆里,在搬到东南区1号之后,书房布置好之后,父亲给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翠叶庵”,请商承祚先生的父亲、清末健在的探花商藻庭(衍鎏)先生为之书写。我随父亲到过他们当时居住的东北区许崇清校长坡下的家,进门就能够看到案桌上玻璃罩着的御赐宝剑。不久之后,就看到父亲书房圆拱门上挂着这个竖写的牌匾。
此外,父亲的藏画里一幅黄宾虹的翠叶庵读曲图,这是黄宾虹先生应父亲的要求而画的,并从杭州寄来羊城。父亲收到之后,当即写下《洞仙歌》词一首作答,谓“黄宾虹先生自西湖巢居阁写寄《翠叶庵读曲图》,赋此答谢”:
西楼倦卧,任榕阴移昼,梦想阑干压金柳。
费经营,凌溪一桁轩窗,帘卷处万壑千岩竞秀。
巢居阁子里,一老婆娑,湖上阴晴几翻覆!
头白喜春来,腰鼓秧歌,想画里长开笑口。
愿把酒为公祝长年,看劫后湖山,重铺金绣。
为此,父亲还专门请詹安泰先生书写该词来配在画头。詹安泰先生在书写之后的说明里写道:一九五零年一月 黄宾虹先生为季思兄写翠叶庵读书图自杭州寄来羊城 季思贱此词谢之而嘱余别书一通以配图 词自佳妙 惜余书拙劣 不免佛头着粪之诮耳。
在反右之前,毛泽东诗词也已经发表,而且还有和柳亚子先生之间的唱和。内地知识分子在那段比较起来几乎最好的日子里,享受到比较宽松的“早春天气”,互相之间的诗词唱和也是比较多的。中山大学里也一样,例如1957年4月1日,广州京剧团来中山大学演出,演出以后,演员与教授欢聚一堂。陈寅恪先生非常高兴,写了三首绝句,送“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陈寅恪的诗和三位教授的奉答之作,均刊登在其后的《中山大学周报》和《南方日报》。
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在1956年的十一假期,晚上和董每戡、詹安泰还有另一位教授,在中大北门叫了个小艇,从北门划到黄埔岛再划回来。四位教授在艇上就着艇家的新鲜鱼、蟹、虾、蚬,吟诗作对,喝酒至父亲大醉而归。
反右时,董每戡先生由于在陶铸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詹安泰先生由于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竟然被打成右派。詹安泰这位饶宗颐先生的老师、诗词成就非常高的广东学者,因而早逝于文革之中,实在令人惋惜。文革后,黄宾虹的画和画上詹安泰先生书写的父亲写的词裱在一起,直到父亲去世,都一直挂在家里的客厅。后为大哥所收藏。父亲的词也编入了大哥整理的《王季思全集》里。自反右之后,我所见到的教授们之间的诗词唱和就少了,一是父亲北上北京大学讲学和编辑《中国文学史》,二是1963年他回中山大学,而我却北上北京大学读书,彼此交集很少,也再难见到诗词会友的场面了。
打倒四人帮,父亲是诗兴大发,写有不少诗词,来表达他对打倒四人帮的高兴和对改革开发的支持。当时,许多人把“四人帮”看成横行霸道的螃蟹,父亲又是最喜欢吃螃蟹。即兴写下了《齐天乐》:
四凶落网,普国欢腾,持鳌把酒,共庆胜利。
潮回暂落吴江水,尖团一时俱起。泽畔横戈,泥中拥剑,喷沫都成毒气。
秋风渐厉,看汝辈横行,为时能几?竹篓禾绳,元凶行见骈头死。
玻杯兴来高举,劈双鳌一盖,连呼快意!
海市烟消,蜃楼泡灭,玉宇澄清无际。
豪情万里,正月到天心,潮生眼底。料得明朝,丰收歌“四喜”。
他特意把这首词,抄寄给上海的三弟王国桢(我的三叔)。三叔还特意请人书写了保留下来。
1978年1月,父亲向商承祚先生出示文革之后尚存之齐白石所绘的《群蟹图》,还请商先生为之书写了他1919年所作的咏蟹诗,装裱在画顶。诗曰:
公子无肠不解愁,江湖豪气孰能俦。横行郭索空千里,直吐玑珠泻九秋。入簖有时倾泽国,乞符何日属监州。平生玉质真知己,换得尖螯妙句投。
至于那篇在政协会议上即兴写的讽刺向钱看的《水调歌头》,调侃的写到“我亦万元户,年年爬格子”,见报之后,不时被人提起。文革之后,教师节,父亲也写过词,请商承祚先生书写,发表在中大盟讯里。那些复印的底稿,在家里的废纸堆里,我看到过。
父亲晚年,更多的是与王越先生有诗词歌赋的来往。1983年王越先生寄来他的诗集,父亲回信:“论诗绝句对前代诸名家大家,不是一味拜倒,而是一分为二,分析批判。一年多来夏承焘论词绝句,苏仲翔论诗绝句,先后出版。他们都是一代专家之学,诗词功力,兄或有所不及,胸襟见地,兄实过之,不悉以为然否?”
1993年12月26日父亲写了《鹧鸪天》:
新岁将临,沉阴放晴,东廊曝日,喜而成吟。
万里晴光透碧霄,寰球渐见息烽飙。朝阳软似黄绵袄,淑景鲜如五彩绡。
人意好,岁收饶,同心为国看今朝。持盈防腐归中道,珍重中华百炼刀。
父亲嘱我抄好寄士畧(王越先生的号)学长指正。
1994年1月29日,父亲还亲笔写下:甲戍新春抒怀(又一首)
贺卡联翩到枕边,谢天放我老来闲。窗前花影无心顾,楼外莺歌不费钱。
春意好,物华鲜,江山词笔两坛妍。爱他逐日追风客,掷杖成林又一年。
1994年3月29日,根据父亲与我和董上德老师的谈话整理出来的父亲的文章《说“服老”》在《羊城晚报》上发表。里面写到:“不服老”是空话,“老当益壮”是空想。一个人由少壮而衰老是自然规律,哪里有老当益壮的呢?廉颇老年并没有为赵国再立战功;马援到了五溪蛮以后,看到那里气候环境的险恶,羡慕起他弟弟在故乡的悠然自得,并没有真正的不服老。至于文学作品的句子,曹操写《步出夏门行》这首诗时不过四十岁上下,并没有到暮年;王勃写《滕王阁序》时不过二十岁左右;往往带有理想的色彩,并非自己亲身经历。
王越先生看到之后,专门写了诗《读“服老”篇》寄给父亲:服老不服老,如何为怀抱?孔丘常发愤,不知头白了。生入玉门关,班超见机早。圣哲与英雄,殊途同归好!
看着父亲签名、大哥手写的1994年给王越先生的信,里面写道:我和兄青年时在南京同学,南来广州后,又在中大、民盟共事多年,诸蒙照扶,两家子弟也亲如手足。则柯、则楚在中大附小多蒙操心照料,得以有成。
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日子已经随着这一辈诗人的离去,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愿我们这些不学文科的儿辈能够慢慢体会他们的诗友情谊,记下来留下记忆。
(责编: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