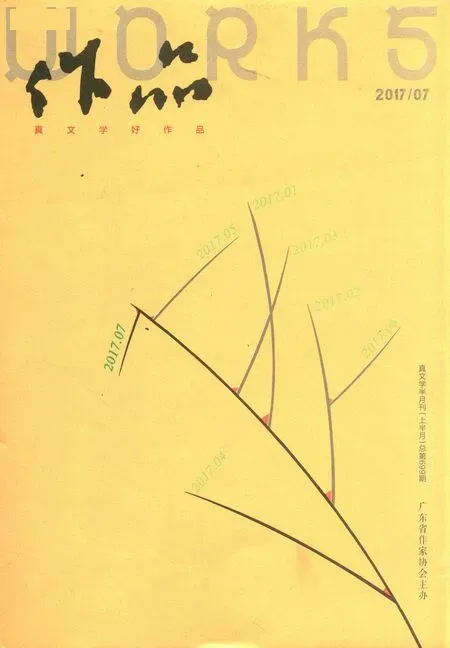殊途旅馆
文/马 拉
殊途旅馆
文/马 拉
马 拉1978年生。中国作协会员,广东
文学院签约作家,虚度光阴文化品牌联合创始人。在《人民文学》《 收获》《 上海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芝》《 东柯三录》《 未完成的肖像》,诗集《安静的先生》。曾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新人奖、《 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孙中山文化艺术奖等奖项。
三年前的七月三号,王思冕第一次坐在这张桌子前。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天,她穿的是碎花的过膝长裙,扎着马尾辫,喷了若有若无的香水。她的脸是光亮的。和她一起进公司的还有六个几乎同龄的男女,他们挤在人事科灰黑色的沙发上,略有些紧张。有人给他们倒了杯水,让他们先坐一会儿。这一坐便是一个多小时,接着有人拿了表格给他们填。填完表格,人事科长走过来说,我带你们去各个科室走走,认识一下。他们礼貌,小心敬慎地跟在人事科长后面,鞠躬,微笑,接受同事们的审阅。
回到办公室,科长指着一张空桌子说,以后,你就在这里办公了。那是一张白色的桌子,和电视里的一样,躲在一个个小方格里。桌子擦得一尘不染,台面的电脑也是崭新的。王思冕打开电脑,一整天,她都在看文件,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好几次,她抬头看看周围,同事们埋头呆在格子间里,很少走动,几乎不说话,雕像一般,四周沉寂如同无人,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挨到下午四点,科长走过来敲了敲王思冕的办公桌说,晚上公司组织新入职员工聚餐,你不要走。
吃的是火锅,王思冕猜不出来,到底是谁的主意,这么热的天去吃火锅。尽管开了空调,房间里还是很热,火锅热气随着风向不停摆动,吹到王思冕的脸上,胸前,手臂上,一阵凉,一阵热。刚开始,新员工还有些拘谨,几杯酒下去,他们放松下来,老练的给领导敬酒,说以后还请多多指教等等,类似的话。饭吃到十一点才散场,王思冕喝得晕晕乎乎的。她的酒量不算小,如果单喝,不会落下风。问题在于领导抿一口,她得喝完,领导说谁和谁喝一杯,她得喝。其他的新员工都很积极,她不能表现得落后,毕竟是要在这里混的,江湖的规矩,她懂。领导把手搭她肩膀上,扶下她的腰,腿上蹭下,她都懂。回到家里,王思冕闻了闻身上的味道,浓烈的花椒味混杂着牛油味儿。她把裙子脱了,洗了个澡,反反复复洗了三次头发。她不喜欢吃火锅,尤其讨厌身上沾着火锅味儿。早知道要去吃火锅,她就不会穿碎花裙子了,前几天刚买的,花了差不多两千。裙子算是废掉了,洗多少次都洗不回来。
一晃,在这张桌子前坐了三年。她从刚入行的菜鸟变成了半个老油条,之所以是半个,仅仅因为她还做不到完全接受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或者说工作。桌子还是那么干净,像她刚入职那天一样,只是她变得有些旧了。这三年,和三年前似乎没什么区别,她还是一个人。期间,谈过一次恋爱,分了。昨天晚上,她喝酒了,和陈思嘉,她大学同学。陈思嘉在深圳,大学一个宿舍的。她们的关系说不上太好,也说不上差,女生之间的关系看似亲密,深度却是有限的。每次陈思嘉来找她,原因都一样,她失恋了,想找个人陪陪,只有她是最方便的。三年里,陈思嘉找过她四次,这意味着陈思嘉至少失恋了四次,深圳速度到底和小城不一样。王思冕偶尔会羡慕陈思嘉,尽管陈思嘉把她的生活描叙得惨不忍睹,说压力大到爆炸,可从她的精神状态能看出来,她很享受。喝完酒回家,王思冕抱着陈思嘉睡的,她握着陈思嘉的乳房,又大又结实,她的小腹平坦滑顺。聊了会儿天,王思冕说,我真想是个男人。陈思嘉说,男人有什么好的,没一个好东西。王思冕捏了捏陈思嘉的屁股说,我要是个男人,第一个把你操了,这骚货太性感了。陈思嘉笑了笑,把王思冕拉到身上,抱着她的腰说,操我啊,你操我啊,快来操我。王思冕亲了亲陈思嘉的耳垂,翻下身,叹了口气说,老娘快一年没有性生活了。陈思嘉说,不会吧。王思冕说,怎么不会,老娘男朋友都没一个。陈思嘉说,没男朋友怎么了,没男朋友就不能有性生活了?王思冕说,你以为我像你,三天没男人到处流水。陈思嘉说,你以为你和我不一样?王思冕想了想说,也是,都是欠操的货。陈思嘉说,欠操又怎样?转过身抱住王思冕,陈思嘉说,操得再舒服也留不住个男人,这混蛋的世道。说完,两人都笑了。
中午下班前,王思冕给陈思嘉打了个电话,起来没?陈思嘉说,早起来了,我在练功。王思冕说,一会儿一起吃饭。见到陈思嘉,她春风满面的,坐在对面,完全不像失恋了。王思冕喝了口橙汁说,你这哪像失恋,不哭不闹,也不诉一下衷肠。陈思嘉切了块牛扒塞进嘴里说,我犯得着为那傻逼哭哭啼啼?王思冕说,那你也别每次到我这儿混吃混喝,我穷着呢。陈思嘉笑了起来说,你就别哭穷了,你那土豪单位,谁不知道啊。说完,补了句,我辞职了。王思冕一点都不意外,陈思嘉每失恋一次辞职一次,似乎她失恋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王思冕随口搭了句,辞了也好,换个环境。陈思嘉问,你去你们公司三年了吧?王思冕说,到今天刚好,整三年。陈思嘉说,你还真挺有耐性的,没想过换个单位?王思冕说,换什么单位,我能去哪儿,我会干嘛?陈思嘉说,除开你们哪儿,别的地方能死啊?干什么不是干。王思冕倒也不是没想过辞职,始终没下定决心,这份工作清闲,收入不错,在小城让人羡慕,像她这样的姑娘,怕是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了。创业她是没有那勇气的,也吃不了那个苦。即便这样,王思冕还是会心慌,她偶尔羡慕陈思嘉,她自由奔放得像一只鸟。她呢,就像一条鱼缸里的鱼,每天看到的都是重复的风景。她必须忘掉,才有再来一天的勇气。读大学那会儿,两人没多大区别,工作几年,分化日益明显。以后的事情,不敢再想了,她很怕有一天,陈思嘉朝气蓬勃地出现在她面前,带着新交的男朋友,她已成为大腹便便,整天围着老公孩子转的中年妇女。
回到办公室,王思冕喝了杯茶。同事们还在低头工作,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来公司三年,王思冕知道他们的工作非常简单,程序,他们每天坐在那里,脑子空空荡荡。她也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不能像陈思嘉那样?这个想法猛烈地蹦了出来,像是一根一直压着的弹簧突然松开了一样。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对不对?我不喜欢。是的,我不喜欢。陈思嘉比我漂亮,比我有钱,比我能力强?不,不是,只是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找了不同的工作。我过得比陈思嘉好吗?王思冕想了一会儿,答案让她失望,她觉得并不比陈思嘉好。大学毕业后,她应父母要求回到小城,进了父母梦寐以求的公司。刚进公司那会儿,父母见人都是眉开眼笑的,费了那么多力气,他们终于把女儿的后半生安排好了。有了这份工作,他们不再担心女儿的婚姻和未来。凭王思冕的样貌、学历和单位,会找到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然后结婚、生孩子,开始计划中的下一代。王思冕看着周围的同事,想起他们的家庭,门当户对,志得意满,只要他们愿意,每年可以来一次欧洲游。这就是她未来的生活。王思冕突然伤感起来,几乎无法克制,她想哭,她看到二十年后的她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她。微胖,富态,手脚圆滚滚的,熟练地和同事们交流最新款LV的价格。她充满渴望地看着王思冕,向她招手,你过来,你过来,我就是你。她要哭了。
等缓过神,王思冕站起身,她的胸腔剧烈地起伏,她觉得有些话必须现在说出来,要不然,又会失去勇气。王思冕绕过办公台,敲了敲科长办公室的门,科长从电脑前转过头看着她问,有什么事?王思冕咬了下嘴唇说,我想辞职。科长愣了一下,起身关上门说,你刚才说什么?王思冕重复了一遍,我想辞职。科长点了根烟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王思冕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不想干了。科长说,总得有个原因吧?王思冕说,我有点害怕,没有安全感。科长说,你指的是工作?王思冕点了点头。科长说,我们这工作还没有安全感?王思冕说,我说的不是工作本身。科长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都有个适应期,过了就好了。科长的意思,王思冕懂,王思冕在公司能说话的人少,科长算是一个。科长中大硕士毕业,来公司八年,平稳上升。业务方面他从不操心,也没什么好操心的,他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玩游戏,带孩子。刚进公司,王思冕听人说,科长在中大是学校书画社社长,写得一手好字,油画据说还参加过级别不低的展览。王思冕害怕的正是这个。想到这儿,王思冕问了句,你还画画吗?科长说,早就不画了。王思冕说,我想辞职。科长把烟头掐灭,不耐烦地说,行了,这样吧,我先放你一个礼拜的假,回来了再说。王思冕还想说什么,科长把头扭到电脑前面说,先这样,你去写个请假单。
回到公寓,王思冕把下午的事情对陈思嘉说了。陈思嘉叫了起来说,好啊,辞就辞嘛,多大个事儿,哪用得着那么纠结。我们先出去玩一圈儿,回来再说。过了那股劲儿,王思冕有点后怕,她皱了一下眉说,我要是真辞职了,你说我能干嘛?陈思嘉说,想那么多干嘛,世界之大,哪儿容不下老娘。王思冕说,我还是有些担心。陈思嘉抱着王思冕说,宝贝儿,你才多大?二十五,你才二十五,你怕什么呀?你是不是在这儿把脑子给呆坏了。松开王思冕,陈思嘉说,赶紧想想,想去哪儿玩,我们一起风流快活去。大理,丽江,还是阳朔,或者去拉萨?艳遇之都啊,我要艳遇!陈思嘉兴奋起来,催着王思冕订机票。王思冕说,你定,我去哪儿都行。她想,去他妈的,反正有一个礼拜的假了,先玩了再说,要死要活先不管了。
到伏安古镇全程八个小时,她们转了三次车,不算远,也不算近。王思冕的主意,陈思嘉说去大理,丽江,阳朔或者拉萨,王思冕不想去,都去过了,太热闹,也太折腾。她想起了伏安古镇,上次是和男朋友一起去的,一年多前。伏安古镇靠山,近水,和其他的古镇一样,不外乎狭窄长长的街道,沿街都是古老的建筑,远不过晚明。镇上人不多,白天多数店面关着门,晚上开的不过刚刚过半。镇子完全被荒凉的村野包围,镇政府离古镇大约一公里,隔着一条河。从伏安古镇到镇上得穿过一座桥。和男朋友来那次,他们对古镇有些好奇,太突兀了,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古镇,和周边完全搭不上调。问过老人家才知道,很多年前,这里是水上交通要道,西南的盐商、布贩从这里去中原。后来,商贩就近建了房子,半是居住,半是店铺,久而久之成了个镇子。都没人了,年轻人都走了,剩下的全是老弱妇孺,要不就是外地的生意人。老人感叹说。王思冕说,多好的地方。她是真心喜欢的,青山绿水,一到夜晚,河边的灯亮起来,树影婆娑。她和男朋友躲在桥洞里接吻,那是多么美好的亲吻,四周寂静无人,河面碧彩,微风徐来。她想,有这么美好的亲吻,他们会相爱一辈子。在镇上的几天,她的心是软的,身体里涌动着整个春天。这么好的地方,一开发就可惜了。王思冕说。老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开发?领导倒是这么想,穷乡僻壤的,吃没吃喝没喝,坐个车都不方便,哪个来?王思冕笑了起来说,我来,我喜欢这儿。老人看了她男朋友一眼,宽厚地笑了起来,也就你们这些谈恋爱的过来。临走,王思冕买了老人一斤姜糖。回到家,糖还没吃完,她和男朋友分手了。
王思冕和陈思嘉拖着行李箱,古镇街道铺的是青石板,几百年的打磨,青石板油光水滑,要是下雨,怕是能照出人影子来。陈思嘉边走边埋怨,王思冕,你到底想干嘛,到这鬼地方干嘛?人都见不到。王思冕安慰陈思嘉说,这是白天,晚上就有人了。镇上有几家酒店,王思冕不想住在镇上,她想住在伏安古镇,不要像一个游客。古镇里面有三家民宿,藏在临街店铺后侧,上次来他们住在那里。找到地方一看,还是三家,只是名字换了,看来这里的生意真不好做。她看到了那颗高大的柿子树,似乎就在昨天,她坐在挂满果子的树下喝酒,一杯一杯的啤酒,带着浓郁的麦香味,树上满是红灿灿的果子。王思冕问,这柿子甜吗?过了一会儿,旅馆老板拿了两个柿子过来说,送给你。柿子晶莹光泽,王思冕都不忍心剥开它。那么甜。站在巷子口,陈思嘉问,住哪家?王思冕的视线从柿子树上收回来说,就这家吧,都差不多。只要不住在柿子树那家,哪家都行。三家民宿都小,多的不过五六个客房,万一睡在上次那张床上,怎么也睡不好了。
从外面喝酒回来,王思冕认真看了看三间旅馆的名字,一家如归,一家殊途,住过的那家叫春分。以前似乎不叫这个名字,具体叫什么,王思冕忘了,谁会记得一家旅馆的名字呢。春分,这名字真好,到了春天就分手。她们现在住的叫殊途,王思冕莫名地觉得有些意味深长。刚才,她和陈思嘉去了桥上,她指着桥洞说,上次,就在那儿,我还亲嘴儿呢。陈思嘉笑了笑说,犯贱。说完,看着王思冕说,这地方太不好玩了,想找个男人浪一下都难。她们喝了不少酒,镇上冷冷清清,如果是周末,可能会热闹一些。
回到旅馆,两人坐在院子里抽烟。王思冕平时不抽,容易呛着。喝了些酒,她想抽几根儿。里面的灯亮着,住进来有一会儿了,她们还没有在里面好好转转。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有人走了过来说,外面凉,到里面坐吧。陈思嘉的眼睛亮了起来,她说,我们想喝酒。挪到屋里面,他拿了一打啤酒说,我叫赵毅阁。像是不好意思一样补了句,这个旅馆是我开的。王思冕看了看赵毅阁,方脸,短发,络腮胡,眉毛粗大。很快,他们喝完了一打,又喝了一打。陈思嘉看赵毅阁的眼神,赤裸热闹,她几乎要靠到赵毅阁的怀里了。陈思嘉拿起赵毅阁的手,要给他看手相。她把手贴在赵毅阁的手上,叫了起来,你手怎么那么大!又将手指从赵毅阁的手心勾滑过去说,你的手好软滑,像个女人,肯定没干过什么活儿。赵毅阁喝了口酒,和王思冕碰了下杯说,小嘉喝多了。王思冕扫了陈思嘉一眼,她大约是有点多了,但肯定没醉,她清醒得很。舔了口酒,王思冕说,没事儿,她酒量大,你肯定喝不过她的。陈思嘉悄悄给王思冕树了个大拇指。又喝了半打,王思冕说,我醉了,我要回房间了。赵毅阁说,我送你。王思冕说,不用,你好好陪小嘉。
回到房间,王思冕洗了个澡,顺便洗了头发。喝得不少,洗完澡,她身上微微发热。在床上靠了一会儿,她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陈思嘉歪歪斜斜地挂在赵毅阁身上。赵毅阁说,不好意思,小嘉真是喝多了,麻烦你照顾下她。王思冕皱了皱眉。两个人把陈思嘉放在床上,脱了鞋子。王思冕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赵毅阁说,没事。说完,笑了起来说,小嘉挺好玩的。王思冕说,她是挺有趣的。刚刚关上门,她听到床上有响动,陈思嘉坐了起来。王思冕说,就知道你没喝多,装死。陈思嘉点了根烟说,妈的,一晚上的酒白喝了。你说他是傻逼了,还是性无能?王思冕说,要不,我另外开间房?陈思嘉说,狗屁,他是老板,他没房间?老娘都勾搭一晚上了,就差脱衣服了,都这样了还不知道带老娘回房间为所欲为。禽兽不如啊,简直禽兽不如。王思冕笑骂到,骚货,你不是失恋了吗,这么快就走出失恋的阴影了?陈思嘉叫了起来,就是失恋了才要报复社会,我要男人,我要艳遇!她脱了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摆了个性感的姿势说,宝贝儿,要不要,要不要嘛?王思冕给她盖上被子说,别闹了,睡觉!
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活生生被饿醒的。走到院子,赵毅阁正拿着把水壶给花浇水,见王思冕和陈思嘉出来,他扭头说了声,起来了,饿了吧?陈思嘉没理他,王思冕说,嗯,正准备出去吃点东西。赵毅阁放下水壶说,我让人给你们煮了点小米粥,喝了那么多酒,吃点粥舒服些。王思冕说,那怎么好意思。赵毅阁说,没什么不好意思,我自己也要吃的。吃完粥,陈思嘉眼神又活泛起来,她问赵毅阁,你们这儿有什么好玩的?赵毅阁想了想说,也没什么好玩的,古镇都是这个样子,看看房子,买买东西,喝喝酒。哦,如果觉得无聊了,去河边走走,虽然没什么特别的,散散步还是不错的。陈思嘉努了努嘴说,昨天晚上去过了。赵毅阁说,晚上和白天不一样的。不过,好像大家更喜欢晚上去。陈思嘉托住下巴,看着王思冕说,都怪你,我说去丽江,去大理,你非得来这个破地方。赵毅阁从上到下扫了她们一遍,又弯下腰看了看她们的脚。陈思嘉收了一下腿说,看什么看,大色狼。赵毅阁笑了起来说,你们都没穿高跟鞋,去后山逛逛倒是不错。陈思嘉问,后山有什么好看的?赵毅阁说,有个溶洞,去的人少,还没开发。我去过几次,觉得还不错。说完,像征求意见一样看了看王思冕说,要不要去看看?王思冕说,你带小嘉去吧,我去河边走走。赵毅阁说,一起去吧。王思冕看了陈思嘉一眼,陈思嘉说,一起去啦,河边你都去过多少回了。
从旅馆去后山不远,青灰色的石灰岩,山上长满高高低低的小树,路不难走,陈思嘉和赵毅阁走在前面,王思冕跟在后面。走到溶洞口,陈思嘉抓住了赵毅阁的手,紧张的样子,赵毅阁看上去有些尴尬,还是任由陈思嘉握着。王思冕嘴角带着不易觉察的笑意,她想看看接着应该怎么发展。不用猜也能知道,赵毅阁最终肯定会被拿下,正常的男人,很难抵挡漂亮姑娘的攻击,何况陈思嘉还有一对如此饱满活跃的乳房。溶洞口不大,阴森森的,赵毅阁拿手电往里面扫了扫说,洞挺大的,里面也平坦,不比山路难走。王思冕说,安全吗,会不会缺氧?赵毅阁说,不会,我去过几次,不深,另一头是悬崖,有个大平台,站那儿可以看到河道走向。赵毅阁扭头对她俩说,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着,要是害怕就和我说,我们往回走。王思冕去过几个溶洞,开发得五光十色,像是在夜总会里。这种没开发的野洞,她还是有点害怕,总觉得里面会有点什么,比如蝙蝠之类的。恐怖片经常这么拍,几个青年男女去溶洞,成群的蝙蝠尖叫着从头顶飞过去,总会有人死在里面。她还犹豫着,赵毅阁已经往里走了,陈思嘉跟在后面,她硬着头皮进去了。没了灯光的修饰,溶洞没什么好看的,石钟乳、石柱、石笋全是灰白色,偶尔会有滴答滴答的水声。王思冕边走边想,如果配上灯光,应该也很漂亮。溶洞像个姑娘,也是要打扮的。走到中途,赵毅阁停下来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他指着溶洞上方说,你们顺着手电光看。他举起手电,横着从溶洞上方扫过去,王思冕看到奇异的反光,一点一点,像星星在瀑布里闪烁。赵毅阁扫得很慢,王思冕承认她被眼前的光镇住了,她在溶洞里看见了银河。那么近,似乎触手可及。王思冕闭上眼睛,又睁开,光,不可思议的光藏在溶洞里。她有种强烈的孤独感,觉得整个人在上升,成为银河的一部分。王思冕坐了下来,赵毅阁和陈思嘉也坐了下来。关了手电,除开清脆的滴答声,只剩下他们的呼吸。在黑暗中,她能感觉到陈思嘉靠在了赵毅阁肩膀上。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她的手,王思冕挣扎了一下,那只手抓得更紧,她的手松弛下来。过了一会儿,那只手松开了,接着,把一个什么东西塞到了她手里。手电再次打开,他们看到了更灿烂的银河。
从后山下来,天微微黑了。回到旅馆,赵毅阁说,我做几个菜,随便吃点吧。陈思嘉去厨房帮忙,王思冕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她抬头望了望天空,月光皎洁,她的影子斜斜地躺在地上。王思冕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东西,一个玉观音。也许是塑料的,或者是最低劣的玉,它看上去像一块玻璃。想到赵毅阁,王思冕微笑着摇了摇头。晚上又喝了不少酒,趁着陈思嘉上厕所的间隙,王思冕问了句,你开这个旅馆不赚钱吧?赵毅阁说,为什么这么问?王思冕碰了下杯说,没什么,随便问问,感觉吧。坐了一会儿,王思冕说,我累了,先回房睡觉了。回到房间,她把玉观音放在手袋内侧的小袋里。晚上,她醒了三次,十二点,两点,四点。她身边是空的。
早上,王思冕起得很早,一个人去镇上转了一圈。远方的山上还有雾气,河水依然平静。她走到桥洞里面,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她甚至想拿出手机打个电话,只为了告诉某个人,她又站在这里,一个人。回到旅馆,太阳升得很高,柔和的光铺在院子里,洁净透亮。王思冕泡了杯茶,点了根烟。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她看见陈思嘉牵着赵毅阁的手走了过来,动作自然,仿佛他们已经认识一百年了,正准备结婚。在王思冕对面坐下,陈思嘉说,这么早起来了?王思冕喝了口茶说,一个人睡不着。陈思嘉的脸居然红了一下,赵毅阁问,你吃了早餐没?王思冕说,吃过了。赵毅阁站起来,把手放在陈思嘉肩上说,我去煮点面。等赵毅阁走开,王思冕笑着对陈思嘉说,终于得手了,恭喜。陈思嘉双手握着拳头,眉开眼笑地说,太棒了,真是太棒了。王思冕说,骚货。陈思嘉说,真的真的,器大活儿好,温柔体贴,太好了,太棒了。王思冕说,你就发骚吧,祝你怀孕。陈思嘉端起王思冕的茶杯喝了口茶说,你这是嫉妒我。王思冕拉过茶杯说,滚!
接下来的几天,王思冕是一个人睡的。白天,他们三人一起出去玩儿,走遍了附近的山水。晚上,回到院子喝酒,喝完,各自回房睡觉。有天晚上,一直喝到深夜,陈思嘉说,我困了,我想睡觉。王思冕说,睡吧,我再坐一会儿。陈思嘉拍了拍赵毅阁的腿说,我要睡觉了。赵毅阁说,我想再喝两杯。陈思嘉撒娇说,不嘛,我要睡觉了。说完,拉起赵毅阁,手挽住了赵毅阁的腰。赵毅阁回头看了王思冕一眼说,那你继续坐会儿,要什么跟服务生讲。他眼睛里有些东西,陈思嘉没看到,王思冕看到了,她不想看到。王思冕摆摆手说,去吧,去吧,春宵一刻值千金,别在这儿浪费钱。陈思嘉搂着赵毅阁,一边走,一边拍着赵毅阁的屁股。王思冕想起了溶洞中伸过来的手,还有那只玉观音。
临走那天,王思冕去前台买单,服务生说,不用了,老板有交代,免单。王思冕说,不,不行,一定要买单的。陈思嘉说,算了,老赵都交代了。王思冕说,不行。买完单,收拾好行李,王思冕对陈思嘉说,赵毅阁不来送你?陈思嘉说,谁要他送。王思冕说,还真是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陈思嘉说,不是,老赵说要来送我,我不让他来。王思冕说,果然是戏子无义,婊子无情。陈思嘉说,你懂个屁。说完,眼睛红了,想哭的样子。王思冕赶紧搂住陈思嘉说,好了好了,逗你玩呢。陈思嘉揉了揉眼说,你干嘛一定要买单?王思冕说,我想多了。陈思嘉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贱,拿肉换钱?王思冕没说话。陈思嘉叫了起来,就你有钱,就你自尊,就你有爱情。王思冕说,好啦好啦,我错了,我现在去把钱要回来好吧。陈思嘉说,狗屎,给了的钱还能要回来啊。
送走陈思嘉,王思冕回到了日常的生活轨道。陈思嘉拖着行李走进车站时,王思冕抱了抱陈思嘉,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说,保重。她站在原地,看着陈思嘉进站,上车,直到影子也见不到了。从伏安古镇回来,王思冕再次安静下来,她看到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城市和人群。她在其中,蝼蚁如尘,谁会在乎一只蝼蚁的感受。她生来就不是那种激烈的人,如果真是,一开始就不会回到小城。既然回来,那意味着她已经接受了被编排的命运。每年一次或两次的长途旅行,那是生活的意外,或许也是被安排的一种,它像镇静剂,让你还有接受这种生活的勇气。
办公室还和以前一样,她的桌子还是那么干净。见王思冕回来,科长说,你到我办公室一下。进了办公室,科长说,没事了吧?王思冕低着头说,没事。科长点了根烟说,我懂你的感受,其实吧,没什么好折腾的。我倒不是教你庸俗的人生哲学,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你再怎么折腾,也没什么意思。王思冕说,我明白了。科长说,明白就好。王思冕说,我不辞职了,谢谢你。科长说,那就好,干活儿吧。回到办公桌前,王思冕给陈思嘉发了个信息,我又坐在办公桌前了。陈思嘉回了简洁的三个字,我知道。王思冕说,你是不是很鄙视我?陈思嘉回,傻瓜,我们是闺蜜,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看到陈思嘉的信息,王思冕苦笑了一下,她打算继续看看娱乐新闻,她知道香港娱乐圈的各种八卦,知道几乎所有艺人的名字。如果她不知道,那只能说明这个艺人实在是太没有名气了。
刚回来那个月,赵毅阁给王思冕发过几次信息,王思冕礼貌客气地回复,她还记得那只握住她的手,拍着他屁股的手。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旅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旅行插曲,随便翻开一本书,类似的烂俗故事一堆一堆。过段时间,她会把这事儿忘了。接到赵毅阁的电话,她有点意外,两个多月了,他应该早忘了。古镇虽然冷淡,也不至于缺一波又一波的姑娘,像她这样普通的姑娘,不值得让人惦记那么久。电话铃响起时,正是一个漫长的午后,她睡意沉沉,想着晚上去哪儿吃饭。她以为他在伏安古镇,午后无聊了,随手翻开电话,找个姑娘消遣一下。他说,我到你这儿了。王思冕说,别开玩笑了。赵毅阁说,真的,晚上有空一起吃饭不?王思冕说,你别骗我。赵毅阁发了个地址,又拍了几张图说,现在信了吧?图片上是王思冕熟悉的街景,他是真的来了。想了想,王思冕说,好啊,你定地方。下班,王思冕没急着赴约,她回家换了套衣服,又洗了个澡,刮了刮腋毛腿毛。她穿上了她喜欢的碎花长裙,镜子里的她腰身苗条,脸上光滑细腻。她喷了香水,淡淡的,要近身的人才闻得到。看到赵毅阁,王思冕心跳了一阵,很快,平复下来。她想,赵毅阁也许不是过来找她的,他只是凑巧路过,顺便看看她。
吃完饭,还不到八点,他们喝了点酒,微醺,算不上多。时间不早不晚,王思冕还不想回去,她说,我请你看电影吧。赵毅阁说,算了,跑大老远的看个电影,我还不如回房间睡觉呢。王思冕说,那我请你喝酒吧。赵毅阁笑了起来说,这会儿酒吧还没开门吧。王思冕看了看手机说,是早了点儿。赵毅阁说,要不去我房间坐会儿,就在楼上。王思冕说,不太好吧。赵毅阁站起来,拉住王思冕的手说,走吧,没事的。王思冕脸红了一下,似乎是她想多了。进了电梯,王思冕抽出手,双手交叉揉了揉,又掐了掐自己的胳膊。进了房间,关上门,开了床前的小灯,房间发出柔和的黄光。赵毅阁看王思冕的眼神温暖甜蜜,王思冕避开赵毅阁的眼神,低头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指甲。指甲油有点花了,该重新上了。赵毅阁靠了过来,他的腿碰到了王思冕的腿。赵毅阁侧脸看着王思冕的耳垂,吸了口气说,我喜欢这个味道。王思冕说,是吗?赵毅阁说,像是你身上的味道。他的手从王思冕肩上绕了过来,搂住了她。王思冕肩膀抖了一下说,我去下洗手间,有点热。进了洗手间,洗过手,她擦了下脸,太热了。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挺住啊,一定要挺住。等她从洗手间出来,发现赵毅阁站在门口,她推了推赵毅阁说,你干嘛?赵毅阁一把抱住了她的腰,脸贴了过来说,我想你了。说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王思冕推开赵毅阁说,你别这样。又问到,你和小嘉有联系吗?赵毅阁说,有。王思冕说,小嘉挺好的。赵毅阁说,嗯,是挺好的。
重新在沙发上坐下,赵毅阁像是想起了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玉观音说,我在你们房间发现的,我送给你的,为什么不要,嫌丑?王思冕说,我觉得不是我的。回来之前,王思冕犹豫了一下,把玉观音放在了房间的抽屉里,同时放进去的还有六百块钱。房费是买单了,在古镇几天,他们吃吃喝喝几乎都是赵毅阁买单的,她不想欠这个人情。陈思嘉买不买单是她的事情,她这一份,她得给。赵毅阁说,如果我再送给你,你要吗?王思冕说,不要。赵毅阁问,为什么?王思冕说,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不是我的人我不争。说完,王思冕笑了起来,你买了多少个玉观音,一百个有没?赵毅阁说,就一个,随身戴了好些年了。我想吧,有天碰到合适的姑娘,就当定情信物了。王思冕不自然地转过脸说,我不信。又问,你那旅馆不赚钱吧?赵毅阁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整天在那儿泡妞?王思冕说,难道不是?赵毅阁说,如果我告诉你真不是,你会怎么想?王思冕说,我不信。赵毅阁伸手抱住王思冕说,我想要你,可你不要我。王思冕挣扎了一下,赵毅阁把她抱得更紧了。她能听到赵毅阁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抱着她的手微微有些抖,王思冕身心软了下来。赵毅阁的嘴唇贴在了她的嘴唇上,手伸进了她的裙子。
进房间之前,王思冕想过这些,都是成年人,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她知道。等她发现她在回应着赵毅阁的亲吻时,赵毅阁已经握住了她的乳房。眩晕,身体里的蜜蜂让王思冕想继续下去,她是喜欢的,甚至做好了准备。王思冕从赵毅阁的挤压中挣脱出来,理了理头发和裙子说,不要,还是不要了。赵毅阁说,怎么了,你不喜欢吗?王思冕说,不是,我觉得不好,特别不好。赵毅阁说,没事的。王思冕用力地摇着头说,太奇怪了。赵毅阁说,怎么奇怪了?王思冕说,我老想到小嘉。说完,摸着赵毅阁的脸说,我们不要这样,好吗?感觉太奇怪了。赵毅阁说,嗯,我就抱抱你。
一个晚上,两人没怎么睡觉。王思冕想回家,赵毅阁一次次地求她,让她不要走。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留下来。天终于亮了,王思冕松了口气,她从来没有如此渴望天亮。王思冕拉开窗帘,清晨的阳光清新明亮。赵毅阁靠在床上望着她,满是渴望期待。一个晚上,他们纠缠在一起。赵毅阁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她,她像小野兽一样挣扎,反抗,弯着腰,紧绷着身体。她完全可以回家,那么,一切都结束了,不用那么费劲。如果她真要回家,她相信赵毅阁不会为难她。但她没有,她躺在床上,挣扎,反抗,不让赵毅阁进入她的身体。她是赤裸的,赵毅阁也是。有好几次,她抓住赵毅阁的性器,双腿差一点就张开了,她有种想死的感觉。刷牙,洗脸,穿戴完毕,王思冕走到床边说,我去上班了,你好好睡,中午我请你吃饭。赵毅阁张开手臂说,抱抱。王思冕俯下身抱了抱赵毅阁,又亲了亲他的脸说,乖,你好好睡。走出酒店,上了出租车,王思冕一点没有虎口脱险的侥幸,相反,她有点恨自己,太作了,真他妈太作了。赵毅阁走之前给王思冕发了条短信,我是来找你的。王思冕回了一个字,哦。赵毅阁说,谢谢你。关上手机,王思冕看了看窗外,这么好的天气,适合散步,野餐,或者干脆跑跑步。她打开电脑,依然没什么事情可做。赵毅阁说,欢迎你来伏安古镇,就当是来看朋友。他牙齿洁白,有柔软漂亮的胡子。
王思冕突然很想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孩子。她想,她的孩子一定不会过着像她一样的生活。王思冕偶尔会想起陈思嘉,她没有来看她,这意味着她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失恋。陈思嘉能做的事情,她做不到,永远做不到,这可能和勇气无关,仅仅只是态度,生活的态度。就在前几天,陈思嘉给她发了条微信,她说,我在伏安古镇。赵毅阁背着她,她打着V字形的手势,开怀大笑。陈思嘉说,我不回深圳啦,我决定做个村妇,劈柴喂马,当街卖酒。王思冕说,你不回来,我也不离开。你看,这就是我们。王思冕心里隐隐有一点疼,她看到陈思嘉脖子上戴着一个玉观音。她相信那是一块玉,而不是玻璃。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