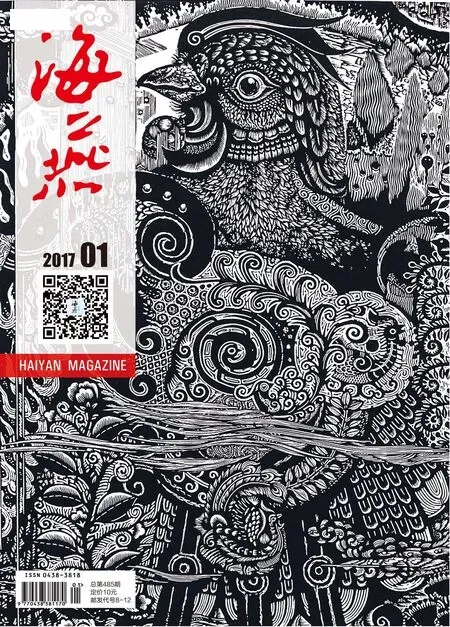周 围
□柳沄
周 围
□柳沄
行 船
大雨落在船上
船更像一座牢房
它善意地囚禁我
又让我随起伏跌宕的江水
一同起伏跌宕
驶入巫峡
大雨更大了
雨落在船上是一种声音
落在牢房上
肯定是另一种声音
几次朝舷窗外望去
什么也看不清
但我明显感到:船
在赶往上游的同时
两岸的山峰正朝下游奔去
这一切使我愉快
真的!这一切
使密封度很好的舱室
与密封度同样好的囚室
彻底区分开来
这一切使我与从前的岁月
于迷蒙中交错而过;使
啼不住的猿声于交错的过程中
进化成下铺那双情侣的
窃窃私语……
雪后的下午
雪,终于停了
雪占据了从窗口望出去的
整个下午
从落雪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再出门
而是躲在家里想着和做着
与雪花无关的事情。就好比
那只腆着腹部的青花瓷瓶
很空很空地满足于
自己的宁静
更空更静的,是窗外
那片被雪覆盖的草坪
除了十几只觅食草籽的麻雀
那里什么也没有
可麻雀太小了,小得
很容易被我忘掉
如同秋天,很容易
忘掉十几粒甚至更多
微不足道的草籽儿
一连几天,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那个雪后的下午,仿佛还在
我的意思是想说——
迟迟不肯融化的雪
使那个雪后的下午
迟迟不愿结束,不愿离开
今天早上,我去
附近的小卖部买烟
看到麻雀的脚印
依然被雪清晰地记着
吃过早饭
吃过早饭
便直接走进
小小的书房里
我经常这样
经常用一上午的时间
把一支支香烟
不紧不慢地吸成
一个个烟蒂
我的书房
远算不上一处避风港
却是享受寂寞的地方
并在享受的过程中
成为寂寞的一部分
有时,风即使不吹
窗前的那棵老树
也在神秘地低语
然而只有坐在
我此刻坐着的地方
才听得见
我坐着,一副
还想坐下去的样子
直到那只乳白色的烟灰缸
满得不能再满
记得有一次
我吃惊地盯着它们
可除了一小撮就要被倒掉的骨灰
我实在看不出
它们还能像什么
窗 外
早上醒来
下了一夜的雨
仍在下着
淅淅沥沥的雨声
使窗外那条街道
有些空旷
有些冷清
往日的街摊
一个都不见了
我常想:生活中若没有了他们
就好比庞大的交响乐团
没有了如泣如诉的小提琴
到了下午
雨停了。一处
摆满了各种水果的果摊
几乎是和阳光一起
同时出现在那里
雨后的阳光
竟那么认真
不仅仔细地照耀着
那个叫卖水果的人
还更为仔细地照耀着
几个挑选水果的人
江 边
江边散步时
遇见两个中年男子
在那儿捕鱼
我停下来
饶有兴趣地瞧着他俩
交替着朝水中撒网
那张撒出去的网
有时是圆的有时是椭圆的
却网网都是空的
离开后,我忍不住又回过头去
发现几片挂在空网上的阳光
鱼鳞似的闪亮
浮 云
一朵雪白的云
于湛蓝的天空里
缓缓地浮动着
它一直都在浮动着
并在浮动的过程中
不断地变换
形状或姿势
至于是像一团
蓬松而温暖的棉絮
还是更像一只
怀胎数月的母羊
它自己好像并不知道
就像我同样不是很清楚
那么多的人为何那么喜欢
将荣华富贵比作浮云
每次数完当月的薪水
老伴总是嚷嚷着
催我去卫生间里洗手
是啊,钱那么脏
荣华富贵又怎么可能
像那朵浮云那样干净
此时,隔着一扇
被老伴擦得透明的窗户
我长时间地望着它
而它那雪白得
一尘不染的样子
使窗户更加透明
晨 雨
拉开窗帘才知道
外面下雨了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雨
此刻,小心翼翼的雨点
正试探着落在
残冬与初春之间
窗外的那棵枣树
似乎有了反应,而
枣树旁的那堆积雪
明显地有了反应
我也有些兴奋
是啊,除了雨
还能有什么
让两个相互疏远的季节
更加疏远
可吃过早饭
雨就不再下了
短暂的晨雨短暂得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出了家门
我行走在
往日多次走过的街道上
突然发现不论走到哪里
无不置身在
雨后的地方
憋了一天的雪
憋了一天的雪
到了晚上,终于
无边无际地落下来
一同落下来的
还有无边无际的夜色
——天黑了,雪
紧跟着也黑了
几次来到窗前
什么也看不见
但唰唰的落雪声
在我的心里响个不停
天地间飘满了破碎感
因我比喻得不好不够贴切
而格外像鸡毛和蒜皮
它们简直就是
鸡毛和蒜皮,使
这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仿佛没了灵魂
然而,这一切
和坐在家里写下这首诗的我
没有什么关系
就像月亮和灵魂
那样没有关系
蒙锈的铁
在这个世界上
你无法找到一块
不会生锈的铁
就如同你难以遇见一位
从不伤心的人
其实,跟所有
暗自叹息的人一样
暗自生锈的铁
才是真正的铁
一直不清楚
被锈迹折磨的铁
与那些被悲伤折磨的人
谁比谁更能忍耐
却固执地认为
铁蒙锈相当于人蒙羞
在我的生活里
这样的类比随处可见
譬如那把断了木柄的锤子
和那位猝死于晨练中的朋友
好几年过去了,如今
他们仍在我的心里
相互比喻
写到这里
便再也写不下去了
我突然意识到
——说了这么多
远不如像他和它那样
闭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