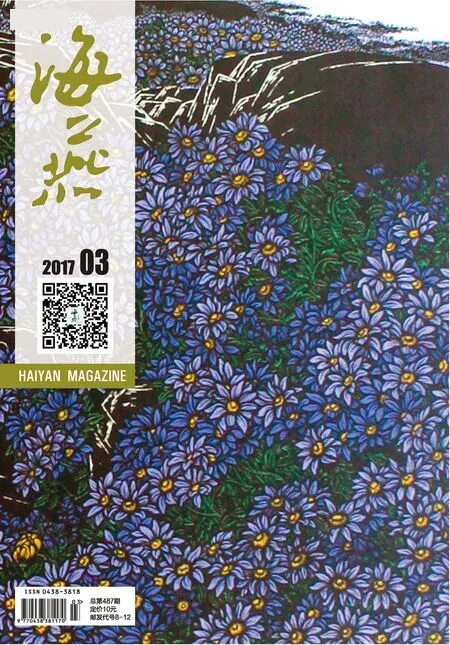长长的三月
□高海涛
长长的三月
□高海涛
胡世宗是我的朋友,作为著名的军旅作家和诗人,多年来他走遍南陲北疆,战地边哨,其行程之远,足迹之深,可能在同辈和同行中都鲜有可比者。尤其上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他曾两次重走红军长征路,堪称不凡经历,人生壮举,令我等羡慕不已。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有关部门为他举办了一场“重走长征路报告会”,时间正好是八一建军节,作为世宗的老朋友和一个也曾参过军的人,我接到电话就赶去出席。不见世宗久,忽忽又经年。
寒暄、拥抱、合影、开会。我一边听世宗讲他的在长征路上的见闻体会,一边翻阅他写长征的一本诗集。有些诗句很优美,有些诗句很传神,有些诗句很亲切,还有一些诗句,联系着诗人在台上的讲述,让我这样轻易不会感动的人也感动了。比如他写红军陵园,本来只有清净和寂寞,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背诵英语单词的少女,穿一身水红的衣衫”……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当年,我也是个背诵英语单词的人啊,而且也恰好认识背英语单词的少女。那是在1976年,我从部队复员,回乡当民办教师,不久就被选派到一个小镇上去参加县里举办的英语培训班。我们是从ABC学起,学员都是各公社选派的年轻教师,少男少女,一共三十。开头两个月,我们每天都是背英语单词,从早到晚,我们都在背呀背,一开始每天能背两三个,慢慢的能背八九个、十几个、二十几个,终于有一天,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课文了,并让我们试着翻译。
一个女同学站了起来,我忘了她来自哪个公社,只记得她每天的样子是既羞怯,又沉静,不管碰到谁,总是一低头走过去。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单词:Long March,问她是什么意思?我听到她声音很低回答说:很长的,长长的,三月吧。大家都笑了起来,老师也气得忍不住笑了——长长的三月?你是怎么学的呀?Long March——这是长征,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征,我们要进行新的伟大长征的长征!
那天中午这个女同学没去吃饭,她在教室里哭了很久。她穿的不是水红的衣衫,而是普通的蓝制服,男女不分的款式,这是当年的时尚,水红的衣衫离她还很遥远。但哭也没解决问题,在那之后,同学们偷偷地叫她“三月”。
直到培训班快结业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和“三月”说话。那是在校门外的小树林里,我们都拿着课本复习,准备结业考试。小树林旁边还有一条小溪,溪水清亮清亮的,据说是从南边的桃花山上流下来的,但为什么叫桃花山,不知道。我在小溪边散步,“三月”恰好想迈过小溪,于是就顺手拉了她一下,于是有了说话的机会。她还是那种羞怯的样子,低着头走路,后来把脸儿一扬,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有个问题我想不明白,你别笑话我行吗?我说啥问题呀?她说我就想不明白,既然March这个词有三月的意思,那Long March为什么不能译成“长长的三月”呢?
是啊,这是个问题。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回答了,好像说这是固定译法之类,总之并不太有说服力。而此刻,在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会上,我又想起了她的问题:Long March为什么不能译成“长长的三月”呢?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是绝对的错误吗?这样的译法,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在美学的意义上,有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呢?
那是1976年底到1977年初的时候,是“文革”已经结束,高考即将恢复的一段日子,我们在那个桃花小镇上每天学英语,那书声琅琅的小树林,那流水潺潺的溪边漫步,好像一切都刚刚开始,那么新鲜,那么美好,那么令人难忘。这期间确实有过一个三月,而整个的培训班生活,也好像都是在三月完成的。所以在结业的那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唱了许多的歌,有个男生喊道:啊,这真是长长的三月啊!大伙儿也跟着喊:长长的三月,长长的三月,就仿佛这是一首伟大诗篇的开头,而接下来的所有句子,都要等着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去续写似的。
不过没听说有谁后来成了诗人,多数仍然还是在乡村当教师。恋爱结婚,还是当教师;生儿育女,还是当教师;接近退休,还是当教师。有几个考上了大学,包括我。我在大学读的是英语系。许多年后,我开始试着译诗,还出版了一本译诗集。其中有一首我很喜欢,是美国诗人兰斯顿·修斯(Langston Hughes)的,共两段——
当年轻的春天到来,
带着银色的雨滴,
我们几乎都能
重新变得更好。
然后却到了夏天,
夏天用飞旋的蜜蜂,
红罂粟,以及海葵,
来取悦很老很老的爱神。
这首诗没有题目, 而如果要加上,我觉得就用我们当年的口号,叫《长长的三月》很合适。诗中春天和夏天的对比,几乎说出了整个人生。春天过去了,就到了夏天,但春天是本源,是起点,经常回到春天,真的能让我们重新变得更好。
俄罗斯画家列维坦有一幅名画就叫《三月》,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这幅画给人最难忘的印象就是春天的美,大地的美,劳动的美。特别是画中的那匹小红马,它像一面飘扬的旗帜,也像一个安详的梦境,一副“倚银屏,春宽梦窄”的样子。在小红马的梦境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劳动和耕作的渴望,表征着大地从冬冥中醒来的明亮与欢快。总之,小红马表达了对劳动的渴望,也象征着对改变世界的期冀,它就像一把英勇的、紫铜色的小号,响亮地传达着大地回春、万物新生的情绪。
实际上,列维坦的小红马也是有出处的。不久前读到一本英文书,《俄罗斯乡村的生活与爱情》(Life and Love in Russian countryside),书中提到一个关于“三匹白马”的俄罗斯民间传说,指的是每年的十二月、一月和二月,因为这三个月总是冰封雪飘,故被称作“三匹白马”,而三月春回大地,冰雪消融,则意味着“三匹白马”都已走远,于是,就像列维坦所描绘的,小红马出现了,小红马就是三月,三月就是小红马,因此它站在初春的雪地上,才显得那么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这就是八一节那天,在胡世宗重走长征路的报告会上,我的全部思绪。当轮到我上台发言时,我还沉浸在这样的思绪里。大脑一片空白。说什么呢?尴尬了好几分钟,我才振作精神,鼓足勇气,讲了我当年的女同学“三月”的故事。为了增强可信性,我还补充了一个另外的细节——
有一天傍晚,“三月”又和我出去散步,谈起背英语单词的体会,她说觉得“革命”一词,即revolution,可能是英语中最长的单词吧。我说那不一定,比如“菊花”,chrysanthemum,共十三个字母呢。“三月”看我能背出这么长的单词,回报了一个略带顽皮而不乏崇敬的眼神。
——我说多年以后,当我站在这里,很想重新回答那个叫“三月”的女孩当年怯生生提出的问题,她并非全是错的。古希腊人最早以战神的名字为三月命名,有没有逻辑和道理呢?应该有,而英语中的长征和三月,不仅在词源和语义上有形式的关联,在历史与现实中更有精神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长征就是长长的三月,长征的精神也就是三月的精神,春天的精神。
我说三月是早春,是初春,是春天的先声,是年轻的春天。
我说长征是艰苦卓绝的,也是可歌可泣的,但无论怎样艰苦,如何卓绝,就中国革命的历程而言,长征仍属于春天的记忆。或者可以说,长征就是从三月出发的,从春天出发的。而正如人们所说的,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根本,不能忘记初心,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每当人们提起长征,那种意气风发的气概,那种同甘共苦的情怀,那种崇高的理想和纯正的豪情,那种前赴后继的奋进和不屈不挠的坚持,哪怕只是一些片段,也都会在我们心中唤起强烈的春天感。
我这个即兴发言,不知道是否切合主题,也不知世宗是否满意。人在生活中的许多瞬间,都可能会被一种思绪和情调所充满,就像我那天,随着生命中一段往事的回忆,心境瞬间被三月的诗意和画面所充满,而这是很难控制和改变的。不过几天后,我接到世宗发来的微信:“被你的深情和优美而打动,一直在想着你的发言”。真不愧军人,话说得很谦逊,又很得体。他说自己正出行中,在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上,还随信发来与边防战士合影的照片。我问他去做什么?回答就像子弹,一下子把我击中:“我在寻找你那长长的三月啊!”
责任编辑 张明晖
——兼论 “训民正音”创制者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