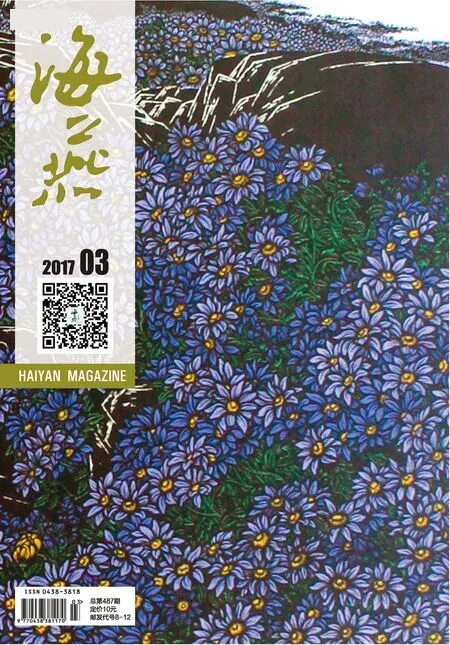大鼓书轶事(外一篇)
□王庆安
大鼓书轶事(外一篇)
□王庆安
我第一次听大鼓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是我们国家刚刚告别瞎折腾了N年之后的阶段,小平同志的新政给中国大地带来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我生活的那个小山村,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农民的院子里开始次第有了苞米仓子。吃饱喝足以后,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日渐凸显出来。电视机那时在农村还是属于传说中的东西,电影一年能演屈指可数的几回,于是,在农闲季节,听大鼓书、看驴皮影成了农民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
那是刚刚入冬的一个傍晚,二叔带回来一个消息:今晚河北生产队有说大鼓书的。
在我幼小的头脑里,大鼓书可不仅仅是个新鲜的词,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新奇、兴奋,纠结着我,连晚饭我都吃得潦潦草草的!
书场设在河北生产队队长张家的西屋。跟着大人们来到书场,入我第一眼的,不是说书人,而是听众,张家西屋是典型的东北农村里外屋连炕房屋结构,面积比较大,可屋里已经挤满了人,地下站着的,炕上坐着的,连屋地的柜上都坐满了人。入我第一耳的,不是说书人的声音,而是咚咚的皮鼓声、哒哒的檀板和点儿声、悠扬的三弦声!
站在人群后的我那个着急呀,人小个矮,只能听到声音,看不见人儿呀!一个坐在炕上的老头儿,看着我着急地往前挤,咧开嘴露出半截黄牙,说道:呵,听大鼓书,不是看大鼓书!听就行!嘻嘻!我看了他一眼,忍了几秒,又开始慢慢往前挤,终于挤进去了!
一张漆着黄色的办公桌,桌子上,一个小木架子上坐着一面小皮鼓,两只装着开水的暖瓶,一只二大碗,碗里是冒着热气的开水。说书人是一个宽脸庞的矮壮男人,头发油黑,梳着背头。坐在他旁边的抱着三弦伴奏的是琴师,我们叫“揽弦儿的”。琴师和说书先生简直对比鲜明,这是个小脑瓜、黑瘦的男人。眼睛实在太小了,伴奏的时候,他总是微闭着眼睛,左手在琴弦上下滑动拿捏,戴着指套的右手或快或慢拨动着琴弦,伴着檀板的和点儿,沉浸在或缠绵或激昂的曲调之中。
伴奏停止了,檀板不敲了,皮鼓不打了,说书人把鼓槌拄在桌面上,喝了一口碗里的开水,开口说话了:“打打皮鼓、溜溜三弦儿,打得皮鼓三千六百棒……”,开书了!
这位说书先生姓陈,琴师姓石,大家叫他小石子,说的是《童林传》。从那天起,我知道了侠客、剑客、金钟罩、铁布衫、飞毛腿、飞镖,还有那些奇形怪状的各种冷兵器和武术名称,比如,童林的铁砂掌,一下就能把人拍死!
陈先生的水平实在一般,这是长辈们在听完书后对他的评价,也是我听了以后几位说书人的节目之后评判出来的。陈先生后来说“穷肚子”了,也就是他记忆里的故事讲完了。他们这茬儿老艺人都是口口相传的师承模式,识字不多,有的甚至是文盲,不可能也没有相关的书去看,于是他就开始胡编滥造了,可能由于水平有限,编造的不合理。有些传统书目,一些读过书或者听过这段子的老人们对他开始有微辞了。他在我们周围的几个生产队只出现过一轮,从此就没再听过他的大鼓书!
听的最多的是一位赵姓说书人,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新甸公社人,为发家致富养过兔子,结果兔子都死了,于是重操年轻时的旧业,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农村,正值业余文化生活的荒芜季节,说书人很少,这些说书人的生意奇好,这场没结束,下场就有人预约了!对于赵先生来说,我想可能比养兔子更挣钱,而且有吃有喝,旱涝保收,走到哪儿都是人们的笑脸,到了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欢声和笑语,何乐而不为?
赵先生肚子里的书多,情节紧凑,不说那些没用的,不像陈先生,不打够3600棒是不开书的,热恋中的公子与小姐分别能分别个一小时,干送也送不走!赵先生还非常善于和听众互动,中场休息的时候喜欢和听众们开玩笑逗乐!赵先生的琴师也是那个小石子,有时,他拿小石子开玩笑,小石子就拿他养兔子的事儿回敬他!也博得听众哈哈大笑!
赵先生有“词儿”,开书前都要来几句词,比如《西江月》之类的词牌,可惜我那时太小一个字也没记住,一句也没听明白。他的开场唱词是:“几句残词说罢,请听学徒的要得了!”“得”字拉了很长的韵儿,然后鼓槌儿狠劲一敲皮鼓,檀板打起,三弦儿马上开始伴奏:“摇动了啊孤啊板哪,三弦定平,众明公哑言捧场……”
他说的是《三侠剑》。金镖胜英,使一口鱼鳞紫金刀,三支金镖压绿林,诙谐搞笑的贾明,勇猛无敌的傻小子孟金龙!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经过他的说唱在听众的头脑里顿时形象立体起来。唱了一会儿,鼓、板、弦儿都停下,开始道白,这时就与说评书一样了,说了一阵儿,又继续唱。大人议论,水平越高的先生唱的时间就越长,因为大鼓书除了让听众欣赏故事情节,还有那高低宛转带动人们情绪的唱腔和韵味,不然不就成了说评书的了嘛!
赵先生的说书水平,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所以,他经常在我们附近的几个生产队说书,应该是连续几年!直到电影、电视等其他文化娱乐方式逐渐增多,大鼓书逐渐淡出,他也逐渐淡出。听说,后来他又去养兔子了!现在想来,如果他健在,应该已是耄耋老人了!
最惹目的是一位王姓女说书先生,庄河人,年龄不大,应该三十出头的样子,处于女人风姿绰约的季节,长相也不错,身材高矮胖瘦适中。性别、年龄、职业等诸多因素注定她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议论的话题中心,就像现在娱乐界的女明星们!什么为了唱大鼓不管孩子,什么和揽弦儿的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反正农村妇女们闲着也闲着,也不管有没有什么证据,想当然地把这些能激起人们兴趣的事儿胡乱编排一起,也算是农闲时的消遣方式之一了。
王先生的唱腔丰富,曲调宛转动听,加之女性特有的声音特征,使得她在说书人当中更是有着别样的风采。我不是研究大鼓书的专家,唱腔流派怎么区分我也说不明白,但她的唱腔明显要与其他的几位先生不一样,而且,更好听。
我听她唱的第一部书是《呼延庆打擂》,开场唱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大宋~江~山……不~太……平~”,这一句唱得九曲十八拐,“大”字伊始就比较高亢,“宋”字压得很低,“江”字突然上扬,然后又在高处拐了几个弯,打了一个滚,“山”又突然落了下来,然后不停地起伏几回,悄悄转为“不”字,“不”字发音不长且轻柔,“太”字又突然爬上高山,在高处稍作停留,陡然又落到了“平”字,“平”字发的鼻音比较重,把声音兜在嗓子里团了又团,欲吐出又收回,反复几次,随着鼓槌对小皮鼓的敲击,平字悄悄地在她的嗓子深处慢慢消音,这一句高低起伏、悠扬宛转的开场唱词瞬间就把听众拉进了那个烽火连天的遥远北宋王朝!
王先生爱用新词,但总读错别字。那些古旧的词她似乎不太在行,一些新式的成语和用词倒是经常使用。那时我已经是小学生了,识得一些字了,比如,银子,她总读成翘舌的“人子”,水泄不通,她总读“水世不通”,可见她的文字识读水准着实难以恭维,看来,干哪一行文化水准太低都不行,尤其是与文化沾边的职业。
王先生的琴师是一个男的,年龄四十左右,精明强干的样子,大人们评论,此人的三弦水准极高。中场休息时,他总爱卖弄般弹出一些花样,并演唱一些传统曲目,比如《王二姐思夫》,还能讲一些笑话,笑话的主角总是那个名字叫“蹦高”的小孩!他在讲笑话逗得大家哈哈笑的时候,王先生总要静静坐在那儿,捂着嘴轻轻地笑,很淑女,眼睛间或地轻飘飘地瞟他一眼,眼里水水的。现在想来,“郎才女貌”,也是人们编排他们故事的原因之一吧。
这些说书人是乡村文化的传播者,是快乐和笑声的播洒者,他们走乡串户,洒下的是欢乐和充实,带走的是闲淡和无聊。他们给农民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欢乐,一轮又一轮的笑声,伴随着农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既丰富了农村的业余生活,又填补了农民的精神生活空白!
那时我正值智力启蒙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未知领域里的东西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可以说,大鼓书是我的文化启蒙载体之一,虽然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同在,但毕竟在我的成长旅途中打开了一扇另类的大门!比如正义、比如善良、比如追求极致和完美!与此同时,我也对说书艺人们描写的那些武术技能陷入了虚无缥缈的追求和幻想之中了。不过从客观上来说,也极大地激活和开发了我的想像力!现在我对文字的偏好绝对是跟小时候的这段经历有关。
岫岩的东北大鼓已于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县里的一些晚会上,总有一些说书艺人在台上表演一些颂扬类的小段,可那唱腔、韵味、那感觉和我小时听到的迥然不同!抑或是时位之移人也?还是心境已不是从前?
鼓韵咚咚远去,檀板声声消逝,三弦悠悠一如故里门前小河的淌水,在岁月的更迭里悄悄淡去!我记忆深处的这些说书人,你们,现在还好吗?
我的第一支钢笔
那是我的第一支钢笔,很不好看的那种灰色,裸尖的。
上小学三年级时(现在算来那是1980年8月份了)开始用钢笔了。那时,农村的小学生用的都是那种蘸水钢笔,笔杆和笔尖是分离的,笔尖或笔杆如果损坏可以随时更换。这种蘸水钢笔极便宜,笔尖和笔杆都是几分钱,钢笔水很少有人用那种瓶装的,用的“色片”,也就是一种类似感冒药片的那种片剂,容器(基本上都是空的钢笔水瓶)里放点儿清水,把这种片剂放里面,碾碎充分溶解后,就是钢笔水了,这种“色片”很便宜的,我记不清一分钱一片或者是一分钱几片。这种蘸水钢笔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一不小心就会把蓝蓝的钢笔水弄到衣服、书包或者书本上了。所以,衣服袖口及胸前的斑斑蓝迹,简直成了那时小学生的标志了。
自用上蘸水钢笔的那天起,我一直就祈盼着自己能拥有一支自来水钢笔,最好是老师给我们批改作业用的那种包尖自来水钢笔。于是,在课余时间我不止一次到小学校附近的商店去,那时叫供销合作社,那里的钢笔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包尖的,一种是裸尖的。包尖的有好几种,有红色的,有黑色的,都很好看。这些包尖的钢笔们静静地躺在柜台里,泛着高贵、油汪汪、清洁的光,透过柜台的玻璃看它们,怎么看都那么可爱。
最便宜的包尖钢笔是九角二分钱一支,裸尖的只有一种,是那种灰色的,和它附近的那些包尖的钢笔比起来,实在是相形见绌,不过,价格也比较便宜,八角七分钱一支。
从此,拥有一支自来水钢笔就成了我那时的一个梦了,从此就有一个小男孩经常去卖钢笔的柜台前看了又看,幻想着价格标签上的数字能变小,可惜那些数字一直都没变。跟父母要钱买一支这样的钢笔(哪怕是裸尖的钢笔)是不可能的事情,连比我高几年级的二姐和哥哥用的都是蘸水钢笔!再说了,同学们用的都是这种蘸水钢笔,我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购买和使用这种自来水钢笔!
那时,学生上学不用交学费,但要“勤工俭学”,也就是向学校交纳一些实物,学校再把这些实物变卖成现金。离我们小学校不远有一座养鹿场,鹿们冬天最好的饲料就是“青干草”,所以,我小学时的“勤工俭学”曾一度就是交纳“青干草”。所谓“青干草”就是将采集来的新鲜青草晒干之后的干草。不同的年级交纳青干草的数量也不一样,从低年级向高年级依次升幂排列的。那时我的任务数是10市斤,每市斤(每500克)7分钱,超过任务数以外的青干草卖得的钱都归学生个人所有。于是,我开始计算,8角7分钱需要多少青干草,可我不知道多少湿草能晒成一斤干的青草,后来,我就想,就算今年攒不够8角7分钱,明年继续攒,我一定要用自己的钱买一支自来水钢笔。
于是,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抓紧时间完成作业,还好,那时的课后作业远远没有现在的孩子们多。然后拿起镰刀和绳子就去割青草。这种青草我们叫它“树草”,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它的学名,也许是“黍草”或者“粟草”。它的特点是一棵草根上长出多茎,茎上再生出若干须根,须根继续长出茎叶,生命力极其旺盛,所以它总是一片一片的,扎进土里想把它全部拔出来,实在太不容易的。玉米地里的这种草既多又高,所以我们一般喜欢到玉米地里割树草。钻进玉米地,茂密的玉米叶子经常把脸和裸露的腿臂等部位划出细小的伤来,钻出玉米地,满头满脸混合着汗水和残落的玉米花粉及花蕊,还有混杂着其他一些灰尘。
这些青草割下来,打成捆,扛回家,放到院墙上,几个日头就晒干了,晒干的青草散发着一种特有的清香味儿,青干草必须放到厦子里了,万一让雨淋湿或者潮湿了,很快就要发霉,或者腐烂,发霉腐烂的青干草鹿场是不要的,因为有毒,鹿吃了以后会得病的。
看着厦子里的青干草体积一天一天在增加,我心中的希望也一天一天在增加,我感觉到那支钢笔离我越来越近了。
秋天开学了,我的青干草也积攒了一小垛儿了,每天早晨我都要不由自主地看它一眼,然后迈着轻快的脚步去上学。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和着山上鸟儿的清唱,我的心情好极了,路边清清的小溪汩汩而流,满载一个山乡少年不为他人所知的心事。
到了上交青干草的日子,早晨上学的路上,很多都是扛着青干草的小学生,从草捆的体积就能分辨出是高年级学生还是低年级的学生。彼此互相打着招呼,为对方估量一下草的重量。头颈夹在草捆中间,闷出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远远望去,乡路上只能看见一个个草团在游动,以及草团下面迈动的双腿,还有那和着脚步不停拍打着屁股的书包。除个别娇气的女孩是家长送的,她们只要跟在后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些男孩都是依靠自己。
小学校园里,一堆一堆的青干草依班级有序的堆放着,整个校园上空弥漫着青干草的味道。鹿场的人逐班级逐人称重,登记,班主任也即时记下每个学生青干草的重量,轮不到的班级在教室里上课。那天上午的课,我几乎没听进去,我总在心里算计着我的那堆青干草与那支钢笔的距离还有多远!
当小学校里那一堆堆青干草被鹿场来的大马车拉走的时候,我辛苦一夏的成果也出来了,我个人所得共8角4分钱,离8角7分钱还差3分钱呢,不过,没事儿,我自己还攒了几分钱。那时的田字格有两种,一种是蓝格的,7分钱一本,一种是红格的,6分钱一本,我和妈妈要来7分钱,买红格的,就剩下1分钱。现在我可以买那种灰色的裸尖钢笔了。
卖完了青干草,也就提前放学了,我拎着绳子,一溜小跑,来到商店,额头和脸上混杂着汗水和兴奋的表情,指着柜台里的钢笔,由于兴奋,声音竟然有些变声:我要买这支钢笔!将柜台里仅有的几支裸尖钢笔逐个挑了一遍,在售货员有些不耐烦的眼神里,在清空了自己手里的8角7分钱后,把其中的一支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高昂起头,挺起胸膛,阔步走出了商店。商店厨房门口趴着的那只大黄狗,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竟然没吱声,平时这家伙总是欺侮我们这些小学生,看到我们就要叫喊几声。
从此,这支钢笔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伙伴,伴我度过了天真无邪的小学生时代。后来,在参加各种竞赛时,获奖的奖品里就有钢笔,随着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也买过钢笔,总之用过很多钢笔,但只有这支笔让我至今难以忘怀。这支钢笔我一直用到初中毕业,上了高中以后,我把这支已经有些破损的裸尖钢笔存放到我的木箱里了,一直保留着,有时拿出它看一眼,就想起自己在玉米地里割青干草的情景,就想起在柜台前挑钢笔的情景。直到大学毕业在县城参加工作,这支钢笔还在,后来,结婚,忙于工作,忙于生活,现在已经不知道它在哪里了!
也许,此时此刻,它还在老家的老屋某一隅,静静地看着门前大山的花开花落,也许它已经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一角落,但这支钢笔却永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里,而且已经沉淀为我人生成长经历的里程碑之一。
钢笔虽小,笔端书写下的却是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责任编辑 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