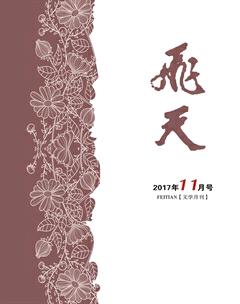夜听皮影道千古
阿舍
那一日,从兴隆山回到县城宾馆已经夜里十点多。正是暑热酣烈天干地燥的时节,在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间奔波了一天,彼时人人困乏,满面倦意,唯愿立刻钻进房间,洗去风尘,静候梦乡。可是同一时间又被告知:专为我们演出道情皮影的民间艺人已经等待多时。大概他们天一黑就等在了宾馆,具体多长时间,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也是不必问不必说的,在这乡土的盛情与真挚面前,个体的说辞或者身躯都会自觉地噤声和低下去。
之前,道情是听说过的,类似于说唱,宁夏也有,流散于或近或远的乡间地头和极个别的民间艺人之间,若非特别去寻,是无法亲耳聆听的。至于我,则是在参观了环县皮影博物馆之后才有所了解——道情是唱腔曲调,皮影是演出道具,两个糅合在一起,就有了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但是也有了疑问,如今民间的艺术传人稀少,传承困难,唱道情戏的人少,会皮影戏的人少,两个少摞在一起,那便是少之又少了。既然少之又少,环县的道情皮影要怎样传承与发展下去呢?还有另一个疑问,之前看过的皮影戏用的是秦腔唱腔,单薄的皮影影儿经亮烈旷猛的秦腔一拔,就有了辽远的意境和想象的空间。而道情是说唱的一种,曲调风格自然比不了秦腔的强劲与猛烈,如此一来,皮影影儿内在的蕴含怎么能够被淋漓地释放出来呢?
且不问,先坐下来听吧。艺人们早就准备好了,坐在大厅一头的舞台上,隐在被称为屏幕的“亮子”之后,“亮子”浸着柔软的明黄色的光芒,那光沉甸甸的,蜜一般稠厚滋润。这里的艺人还把“亮子”称为“神的脸面”。啧啧,这么恭敬!原来,他们对自己从事的事情、将要演绎的“戏”有这么高古的想象。就是不知道,每一次坐在台下欣赏他们表演的人,有多少人晓得自己正看着的是一张“神的脸面”。而“神的脸面”上,正上演着古往今来的忠良、奸恶、悲伤和欢喜。那是“神”在与人说话吧,不过这“神”倒是亲切得很呐,忽而让人笑,忽而又使人惆怅,不管怎样,真真假假的人物都编成了一曲三折的故事,有好看的女子,有刚猛的男人,有飞腾的神怪,有祥瑞的兽……开演之前,我下意识转头看了看空荡荡的大厅,觉得身后若是能有更多土生土长的环县人与我们共同观看表演就更加接近皮影戏的本质了。皮影戏不要大场地,富丽堂皇更是多余的,只需小小的一孔窑洞,或者窑洞前的一片空地,戏台子就能搭起来,为的还是乡邻们可以横七竖八地坐着站着或斜躺着,乡亲们一齐凑着炕烟味儿、咳嗽声和此起彼伏的长呼短叹,打发过一个又一个清寂又简朴的日子。是民间的风土与朴素滋养着民间艺术,反之,民间艺术又慰藉着乡人们漫长的心灵时光。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环县的道情皮影戏班子还去了意大利,在能装下一千人的一流剧场里演出,前来观赏这种中国民间艺术的意大利人,穿着礼服与盛装,彬彬有礼如同参加盛大宴席或者顶级的音乐会。略微遐想,就能觉出这是一件有趣并意味深长的事情,这土里生风里长的道情皮影戏,在家门口是可以脱了鞋叼着烟袋看的,到了国外,观众们却变得这么庄重与隆重,不知道当年前去演出的民间艺人面对彼时彼景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戏开场了。第一场是《康熙王》。起板就听——“耳听锣鸣梆又催……未曾提笔泪盈盈,拜上皇兄得知情”,曲调竟然丝毫不像我想象中的说唱那么平直简单,唱腔竟然有着意料不到的悠扬激越甚至炽烈,哭腔虽不似秦腔里那么摧肝裂胆,但同样入心入肺,似乎是一点一点地绷紧了力气,将人一寸一寸地扯进戏中人物的悲欢里。等到“嘛簧”声起的时候,之前的疲倦已经不知所踪,心思随唱腔上上下下,情绪随板音起起伏伏。听戏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先是忘了自己,而后也就忘记了疲惫忘记了烦恼,时间便在暂时的忘记里平安地过去了。想来这便是人们需要和喜爱艺术的原因,无论民间还是殿堂。另一出戏是《白蛇传》里的《盗仙草》一段。《白蛇传》,电影电视看过多个版本,里面的情节已然稔熟无奇,可是这一晚的《盗仙草》却令我连连感叹,有一刻,甚至联想到,如果眼前坐着一地六七岁的孩童该多好!如果当年我的孩子能看到这样的皮影戏该多好!那蛇精如何瞬间从蛇变成人,再从人变成蛇?那守护仙草的童子如何保护仙草?那仙草的主人如何深明大义……影人儿的来来去去可以任由孩子们想象,影人儿的唱词和念白都是比任何日常和课堂说教更好的德行教育,这活泼生动的民间艺术是那些粗糙却流行的动画片根本无法比拟的。《盗仙草》真是好,艺人的唱腔、挑线功夫都叫人敬赞,更精彩的是那些皮影造型,凤冠、翎子、桩桩、神仙朵子、神架子……时而款款而来,时而腾云驾雾,透过“亮子”的皮影道具已经看不出明显的色彩,但那一刻却只是感到满目的流光溢彩,真是越看越欢喜。不久即得知,《盗仙草》乃是环县道情皮影戏的老牌剧目,并于2015年获得全国皮影展演金奖。怪不得!
两出戏演完,时间已近零点。大厅的灯亮了,“顶灯”挑线子的艺人史呈林先生从“亮子”后面走出来,看着他沧桑黝黑的面容,大家都满怀感激和敬意,老人已经七十八岁了,为我们演出到这么晚!民间艺人是民间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和发扬者,无论地域多么偏远生活多么贫寒,乡土地里,总是会有这样一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人,就在无异于旁人的或简素或沉重的日常里为这片乡土种下一株株开满明艳花朵的绿树,而他的人生与命运,却也不会因此有更大的改变或者好转。这时思绪便跳回最初的那个疑问:环县的道情皮影是如何传续至今的?它浓郁而强烈的声气是以何种形式传布在这片丘陵沟壑之间的?细一想,这问题其实是感知环县的关键所在,就好比理解一个人,要由他言行举止后面的内心所求入手,才能贴切生动,入骨入髓。那么先看道情的历史。道情的发源得自于道教音乐,北宋时已在民间兴盛,环县自古便是道教崇奉之地,道情之乐的流传也就自然而然,而将道情与皮影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小戏”或者“灯影戏”,也在同一时期就有了成就。史书有载,范仲淹任环庆路兵马钤辖时,当地艺人便以道情皮影犒劳将士;清末董福祥曾以环县道情皮影为慈禧贺寿。诚然,一种民间的“小戏”能够如此这般地流传千余年,自有其值得考察的地方。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环县自古环境恶劣生活贫困,黄土地的偏远与闭塞,既使得它得以萌生——寄托内心的希望平复光阴里的艰辛,也庇护了它的生存——不受外界干扰的自娱自乐。于是就有了那些富于想象力的艺人,将那些寄予了因果报应福祸玄机以及日常悲欢的“小戏”,一代代地传继下来,直至今日,成为环县足以令人称道的氣质与品质。再细究,环县道情皮影的传继似乎更有其“难得”之大幸。这样说是因为自《环县道情皮影志》所见,从清末至今,其传续的步履及其记载未有明显中断,即使在二十世纪中国最混乱的年月里,艺人们的身影仍在山圪崂里的黄土细径上踽踽而行,并且有人将它们的身影记录在册。后一点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衡量一种地域文化的完整性,延续之外,更为关键的是“记录和保护行为”的存在;因为相较于“艺术的活动”,那些记录并保护这些艺术活动的行为,代表了更高一层的艺术理性和文化自觉,而这个文化自觉的存在与否,则意味着其所置身的这片地域对文化与生命的尊重程度,而这一点,恰好正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底蕴和品质的专业标准。所以,当打开绘制于近年的“环县道情皮影戏班分布图”,面对密密麻麻遍布全县的道情皮影戏班,无法不叫人感慨,环县道情皮影是幸运的,环县人也是幸运的,一条流传了千年之多的文脉不仅未有中断,迄今仍是蓬勃的。
自然,眼前的史呈林先生也在《环县道情皮影志》当中,他的名字早在1987年就被记录在“中国甘肃省民间皮影艺术团赴意大利演出”这条之内。望着史呈林先生淳朴的笑容,环县皮影一代宗师解长春的遭际涌上脑海。旧时惯将艺人称为“戏子”,这称呼大概一出现便含有偏见与敌意,那些从事这一行业的艺人们也就常常成了连黄口小儿都可以任意贬低的人群。解长春身为皮影戏艺人,自然也未能免遭此类轻慢。《环县道情皮影志》有载,1890年春,解长春因自收晚清贡生敬建功之子敬乃梁为徒与敬建功当堂辩理。敬建功说,你们唱戏的是捶皮打鼓之人,如何敢收我贡生之后为徒?你们是下九流中的数。解长春斥道,我们说古道今劝民从善,何以下流?贡生秀才才是下流。本县有名的老鸨死去,贡爷、秀才顶着皇上赐的四两高丽铜在灵前叩八拜,这难道是上九流做的事吗?此事虽在县老爷的支持下解长春大获全胜,既赢得了徒弟,也赢得了乡亲们的看重,但想必日后此类轻慢蔑视仍有发生,否则谢长春不会在晚年告诫子孙:“我一生走州过府,经见的多了,从没见过一个戏子成就家业,能得善终的,除了我。你们没有我的德行与忍性,休作此想!”到了临终之时,解长春的态度更加激烈:“好好守着田土,耕读传家,即使万不得已,宁可行乞,不可卖艺!”皮影戏的一代宗师说出这样的话,该是用怎样痛彻心骨的经历换来的?其间的隐情,如今唯有解长春先生的在天之灵能知。时光流逝,时代更迭,唯愿世间的丑陋能随着文明的脚步尽快消失。
那天晚上,曲终分别之际,史呈林先生与大家合影留念,举起手机拍照的一刻,老先生淳朴的笑容让我又有了疑问:不知老先生一生演过多少场戏?不知老先生和他的搭档一生给多少人带去过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