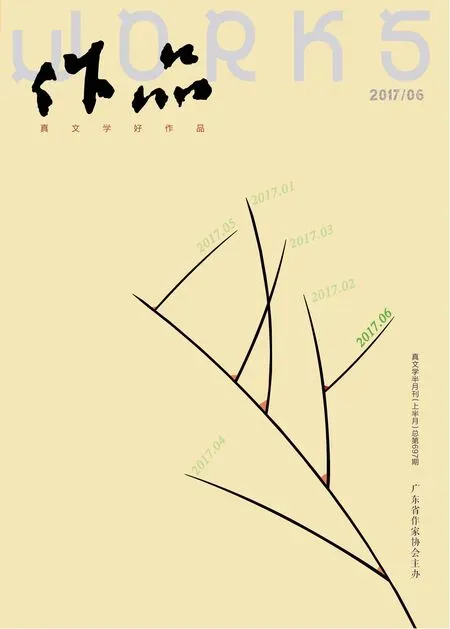从身体出发
——论徐晓的小说创作
文/徐 威
从身体出发
——论徐晓的小说创作
文/徐 威
徐 威男,江西龙南人,1991年生,广东省作协会员,中山大学中文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现居惠州。在《作品》 《诗刊》 《中国诗歌》 《诗选刊》 《星星·诗歌理论》 《当代作家评论》 《当代文坛》 《四川戏剧》 《创作与评论》等发表小说、诗歌、评论若干,著有诗集《夜行者》。
2017年3月,《作品》史无前例地刊发了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请你抱紧我》。在《作品》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访谈中,小说的作者徐晓被贴上“90后”,“美女硕士”、“莫言同乡”、“文学天才”等标签。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标签足够吸引人眼球,也容易引发更广泛的关注。从文学批评的立场出发,我则心生警惕——一者,文学批评始终以作品文本说话,而绝不是标签;二者,标签往往会将作家及其作品简单化、片面化与符号化,迷信标签容易陷入“片面认知”的危险之中。避免“片面认知”的方法简单而略显笨拙,那就是尽可能地大量阅读。于是,在集中阅读了徐晓的长篇小说《爱上你几乎就幸福了》《请你抱紧我》、诗集《局外人》及她的一批短篇小说、散文随笔之后,我终于在纸上写下我认为最重要的关键词:身体。
一、身体:商品或确认自我存在的路径
从古希腊柏拉图对精神的欣赏与对身体的贬低,到中世纪哲学与宗教对身体的双重压制;从尼采将身体视作哲学的中心与主体,到弗洛伊德、梅洛·庞蒂、福柯等人的身体美学及身体文化研究,再到消费时代对身体的消费与再生产,可以发现,“身体”一直以来都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文学等众多学科密切关注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身体”还是小说家、诗人数千年来持续不断在书写的重要主题。在我的观察与判断中,“身体”同样也是进入与理解徐晓小说的关键词汇。
2014年,徐晓长篇小说《爱上你几乎就幸福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小说由短篇小说《你是个好女孩》扩写而成,讲述勤奋、自立的贫困女大学生香米逐步变为被人包养的小三的故事。毫无疑问,徐晓写下了一出悲剧。读这部小说,容易让人想起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同样是出身贫寒,同样是渴望借助教育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美好的梦想最后同样毁灭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与涂自强一样,香米缺乏各式各样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社会资本等)[1],因而在生活中处境艰难;然而,相较于涂自强,年轻的香米又有着涂自强所不具备的“身体资本”,她的身体在一定情境中可迅速地转化为经济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香米的身体在小说中已经异化为用于交易的商品,成为了权力(经济)的消费对象:“香米悔恨自己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卖了呢?……无论怎样,香米想赌一把,用自己唯一的资本——青春,赌一把。”[2]事实上,香米对身体的发现,首先也是在它的商品属性上的:“一千块钱外加两件衣服,让他摸几下又有什么关系呢?”[3];其次才是身体自我的(生理的与女性意识的):“她是那么享受他的吻和他的抚摸,她空置了二十年的身体被他盈满了,她沉寂了二十年的身体被陈有胜唤醒了。”[4]因而,香米之后的各种打扮:烫头、画眉、换装等,实则都是对身体的包装与升级,目的在于将“商品”进行保值与增值,以期获得陈有胜对自己更多的关注与照顾。
与香米作为商品的身体不同,《请你抱紧我》里苏雅将身体视作一种确认自我存在的途径。故事开始之初,苏雅的人生是茫然而虚无的,她完全没法确认自我的价值与存在:“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身边匆匆走过,觉得自己仿佛是世界上最清闲的一个人,她并不是无事可做,只是不知道下一步的人生会向何处发展,她曾迷茫过一段时间,也曾下定决心要考研,但又不知如何下手,因此就这样顺其自然地每天过着相同的日子。孤独感像空气一样紧紧地包围着她,压迫她,啃噬她,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一样,苏雅恨透了这种虚无的焦躁的状态。”[5]今时今日,青年人精神的焦虑、彷徨与无法摆脱的虚无感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种时代病。阿乙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他”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学,精心策划一场惊天大案,目的在于让自己在警察铺天盖地的追捕中得到关注,于逃亡中体验生命的充实与确认自我的存在:“唯有逃亡,我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充实”[6]。徐晓笔下的苏雅则借用身体,确切地说,是借助性爱来破除虚无并获得活着的充实与前行的勇气。如同柏拉图将身体视作是精神的牢笼,苏雅也将身体与精神视作是对立的二元,认为处女之身对自己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束缚:精神的苦闷完全在于身体未能得到解放。这是小说发展的逻辑起点,亦是故事推进的原始动力。为此,苏雅大胆地约齐教授去开房,去挑战禁忌,去破除自己的身体束缚,而后“取而代之的是充实,是前所未有的轻松”[7]。“他”与苏雅都选择了一种极端处境以确认自己的存在。如果说第一次开房做爱是让精神在身体的解放中得以拯救,那么,苏雅与齐教授之后多次的性爱则是让苏雅在禁忌之恋中重新发现自我,确立自己存在的位置。苏雅借助身体的感官,在性爱中实实在在地、确定地认知到“这就是我”、“我就应该这样”。
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开篇便写“我”在浴缸里割腕,在肉体的破裂与鲜血的流淌中得到快感与兴奋:“从那之后,我就时不时地故意划破胳膊,让血淌出来,它们在我身体里一定憋坏了”[8]。《请你抱紧我》中秦小鹿因身体的缺陷而变得自卑、固执与偏激,令她遭受了一段惨痛经历……显而易见,徐晓对于身体有着令人惊奇的迷恋。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对于徐晓而言,身体意味着什么?为何她如此着力于书写身体?在这种书写背后,隐藏着什么?于我们而言,身体作为一个关键词,是进入徐晓小说世界的旋梯之一;对徐晓来说,身体则像是一张巨大的画板,她笔下的线条与色彩,她试图建构的世界,从这里出发也在这里扎根。徐晓在身体中认知、发现“自我”,种种意识觉醒与生长也是从身体内部出发的。这种对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发现与重视令徐晓的作品在90后小说中显得独具一格。
如果要试图真正理解徐晓重视身体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寻找线索——回到她的童年经验,因为“童年是人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最初阶段,在个体的经验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童年的记忆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9]徐晓的随笔《隐痛的肉身》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童年时期的一次坠伤带来的疤痕仍在,“对疼痛的感知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确地确认了自己在世间的存在”;班级里的早恋风波令还是小女孩的她开始“为肉身的深不可测感到惊叹和羞耻”;小学三年级,身体私处与自行车的碰撞所带来的隐痛持续至今,“童年时期覆盖在我身上的阴影注定伴随我终生”;面对割腕的表姐,徐晓感慨“女人,太过柔弱的物种,当我们委屈,愤怒,失望,我们想要摧毁什么东西的时候,却发现我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10]……凡此种种,可以看到,在童年时期徐晓对身体、对生殖器官、对性、对爱情都有着过早的认知与过于深刻的体验。因为深刻,所以它们带来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而这,或许正是徐晓着力于书写身体、反复借助身体来呈现她眼里世界的重要原因。然而,“身体不仅是肉体(这不过是生理性的肉体),它更是有灵魂、伦理和尊严的”[11]——如果仅仅将笔力局限于生理性的肉体之中,而忽视了身体的灵魂属性,那极可能走入身体的肉体性泛滥写作之中。那么,接下来需要探究的便是:徐晓作品中的身体书写是否仅限于肉体(性)?是否呈现出身体的灵魂与伦理?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二、冒犯:性、禁忌及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
就内容而言,徐晓的小说带有一种冒犯性:对性大胆书写、对禁忌之恋着力刻画,对伦理秩序勇敢挑战。《爱上你几乎就幸福了》(2014)、《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15)、《请你抱紧我》(2017),三部作品在主题上一脉相承,但书写日益深入。“女大学生”、“包养”、“情妇”、“性爱”、“师生恋”、“潜规则”,凡此种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都已司空见惯;但当它们一次又一次集中地出现在一个90后女作家的笔下,这又显得独特。从道德层面看,冒犯是不礼貌的行为;在文学创作领域,冒犯则可能是一种美好的品德,它意味着反抗、冲击与突破——新的认知与新的经验往往在冒犯中产生。
《请你抱紧我》对性的书写有时会令我想起卫慧的《上海宝贝》——一部在世纪之交引发众多关注与争论的冒犯之作。《上海宝贝》对身体、性、三角恋、颓废、毒品、欲望等的大肆书写令其名声大噪。然而在今日,即便《请你抱紧我》对性有着细腻而大胆的书写,或者说,哪怕它再更大胆、露骨一些——它仍旧无法再得到相似的“待遇”。原因在于:随着政治与文化对性的压制与管控力度的日益减小,伴随着媒介社会信息的广泛而迅速传播,性的神秘面纱在日常生活中逐步被揭开,性不再是令人闻之变色之物,突破禁忌所要付出的成本与承担的后果也不再那么令人胆战心惊。换而言之,那些曾经被视作大胆、先锋与禁忌之物,在今时今日已然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性成为公开的无所禁忌的普通生活,它既不丑陋,也无诗意;既不肮脏,也不圣洁。性的禁忌,以及根据这种禁忌而滋生的种种文化焦虑在最大限度上削弱了。性实践,成为一个庸碌的行动,它唾手可得,用之即弃,没有强大的事后效应,它如此之单纯、简洁、平庸,如同身体的另一种需求——饮食——一样毫无刺激,毫无悬念。”[12]
在此种文化背景之下,我们再回到徐晓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单纯的性书写的冒犯之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尖锐、强大。相比较而言,徐晓作品在身份禁忌的打破上更具冒犯之力。譬如她笔下恋人,苏雅与齐教授、“我”与“秦朝阳”最初都是师生关系。这令我想起她的诗歌《男人》:“你问我有男朋友没/口吻严肃像我爸/我说没有//你说为什么不找一个/语气亲切像我哥/我说没有合适的//你说赶紧找一个吧/双眼死死盯着我的胸/表情猥琐像我男朋友//我说就你吧/你眉飞色舞 眼笑成一条缝/活脱像我儿子”[13]以徐晓看来,在女人面前,男人的身份是可以肆意转换的,可以是爸爸、兄长也可以是男朋友、儿子;同理,在小说中,男人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情人。因此,男女社会身份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她笔下女性追求性与爱的阻碍,传统社会伦理在徐晓笔下屡屡被冒犯被打破。
从身体(生理属性)与精神(灵魂属性)等多个层面为被包养的女大学生进行勇敢的“自辩”,其冒犯之力最令人印象深刻。在《爱上你几乎就幸福了》中,香米面对好友翟丽的指责,她反击道:
“什么是道德?从古至今,它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多少人被它的假面具套得死死的,终身跨不出去半步?又有多少道貌岸然的人满嘴仁义礼智信,可是他们做的事情有一丝关乎道德么?至于你说我出卖身体赚钱,这有什么不对呢?有买就有卖,既然人家出钱了,我为什么不把身体交出去呢?这是双方公平交易,是你情我愿的事,还有,你以为我们之间就没有感情了吗?”[14]
香米的反问翟丽无法反驳。这是香米的“自辩”,亦是一代女性对道德、金钱、情感的新的认知。香米被包养是因物质(经济)的匮乏,所以其“自辩”更多地从道德与社会层面出发。相比较而言,苏雅不缺钱,她在与齐教授、方昊的禁忌之恋中的“自辩”与“自我正名”更多是在精神层面展开的,是自我的、隐秘的、内敛的,它更为确定也更为勇敢,更能体现出新一代女性(或者说90后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对婚姻、性与道德的理解。因而,苏雅的“自辩”与香米截然不同:
“其实苏雅心里是清楚的,她想恋爱了。确切地说,她想要性。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她想得都快发疯了!”[15]
“她喜欢他们带着那种片面的自以为是的有色眼镜看她,对,我们就是非正常关系,你们能怎么着?你们还来拆散我们不成?”[16]
“她对他说,和他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她需要的不是物质,更不是婚姻,她不要他为她负责,她不想让他们的关系陷入一种庸俗的婚外情之中,她不愿成为世俗意义中的小三。”[17]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一点点爱,你已经给我了。……我们这是交易?是买卖?你以为我就那么下贱吗?”[18]
“我们是不正当的关系,我是你的小三。”[19]
完全忽略一切物质层面的因素,苏雅遵循身体与精神的呼唤,大胆直接地向老师、向有妇之夫索要性与爱,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视作小三——这些书写,显然是对现有道德伦理秩序的一种冒犯。但是,正是在这冒犯中徐晓有力地彰显出属于这一代人的独特女性意识。我们说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对自己作为女人的一种主体自觉意识,包括对自身作为女人的感受、体验以及在这个客观世界自身的价值、地位、作用等方面的认知。斯帕克斯认为:“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20]事实上,苏雅对自我存在的发现与确认并非瞬间而成,而是在身体与他者的不断碰撞中逐步觉醒的。在这,我们又必须回归到最为关键的词:身体。在苏雅十二岁时,其女性意识的初次萌发是因为继父酒后对她身体的侵犯:“仿佛一瞬间,苏雅就长大了,她的性别意识的觉醒不是像大多数女孩那样来自于初潮,而是来自一个男人的侵犯”[21]。在小说开头,苏雅对性的幻想与发疯似的渴望,让她彻彻底底认清自己是一个女人,需要性的女人;与齐教授的性爱,则让苏雅进一步地在焦虑、虚无状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的价值:“苏雅在他的吻中一次次地认清了自己,发现了自己,重塑了自己,她就该是这样的,她的身体就该是这样被爱着的,她的灵魂就该是这样解放的,她早就该是这样的。”[22]
论述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身体始终是徐晓小说的出发点。她的性书写与身体书写并不仅仅局限于肉体,它也涉及身体的灵魂属性,呈现年轻女性的疼痛、羞感、勇气与尊严。徐晓的写作从身体出发,在身体中确认自我的存在;她用身体书写不断地去冒犯,并在冒犯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抵达:从个体到群像,由校园到社会
我们接下来需要探究的问题是,徐晓的小说创作从身体出发,它试图抵达何处?
我以为,诗歌往往将个人的体验极度浓缩,在象征与隐喻中袒露时代的核心秘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顾城用短短两句诗,在黑暗与光明的辩证中传达他对时代的观察。与诗歌一样,小说也始终观照我们的时代。不同的是,小说对时代、社会的观照不是浓缩的、象征的,恰恰相反,它是具体的、繁杂的、不断向外扩散的。也就是说,小说必须在具体的描绘、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中,才能饱满地展现出它的力量。为了把这些“具体”写得传神,小说家需要积累生活的、创作的、思想的等各种经验——而最好莫过于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1992年出生的徐晓目前仍身处校园,她对高校生活有着极为熟悉的体验,因而她笔下的故事往往发生在高校里,人物也大多是身处高校的女大学生。从创作的角度说,她的选择是稳妥而机智的。然而,我们也看到,她的文字书写校园生活但却并不囿于校园生活,其锋芒始终是指向整个社会的——将身体作为切入点与出发点,徐晓对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与人物进行刻画与书写,传达她对今日女性及今日现实的个人洞见。譬如,秦小鹿以裸照为抵押在借贷宝借高利债,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是近两年来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徐晓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故事里,呈现出当前校园生活的真实一角。
徐晓紧紧抓住“包养”这一社会症候,在这一方天地里努力挖掘当代女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香米到苏雅,我们看到了一个因经济艰难而走上被包养道路的女大学生,也看到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大胆独立的现代女性。香米也好,苏雅也好,她们是活灵活现的“这一个”,但显然,她们并不是这个社会中唯一的那一个。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与香米、苏雅相似之人。正是在这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徐晓的文学抱负——她试图在这些个人形象的塑造中为当代女性青年画像。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克制本能欲望的基础之上的”[23],徐晓对现代社会文明的书写与批判,从女性的身体出发,从这些被克制的本能与欲望中出发。最终,鲜明的个性与锋芒在此生成——从个体到群像,由校园到社会,徐晓努力将那些在道德与文明中被压抑、被克制、被剥夺的现代体验呈现在我们面前。
作为90后,徐晓的作品从身体出发,关注当下年轻女性隐秘的意识转变,其书写充满冒犯锋芒,在90后作家群体中显得独树一帜。徐晓有对现实的密切关注,亦有敏感细腻而又大胆独特的言说。她有敏锐的洞察力,目前着力书写的题材亦大有深入挖掘的空间。我们都还在探索、前行的路上,徐晓的小说创作因而也更值得我们期待。
注释:
[1]【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211页。
[2]徐晓:《爱上你几乎就幸福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3]徐晓:《爱上你几乎就幸福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4]徐晓:《爱上你几乎就幸福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5]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76页。
[6]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7]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91页。
[8]徐晓:《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西部》,2015年第12期。
[9]洪治纲:《“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10 年第2 期。
[10]徐晓:《隐痛的肉身》,《作品》,2016年第10期。
[11]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见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208页。
[12]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13]徐晓:《局外人》,卓尔书店,2014年版,第2页。
[14]徐晓:《爱上你几乎就幸福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15]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74页。
[16]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97页。
[17]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126页。
[18]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153页。
[19]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155页。
[20]王春荣:《新女性文学论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21]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83页。
[22]徐晓:《请你抱紧我》,《作品》,2017年第3期,第105页。
[23]【奥】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徐胤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