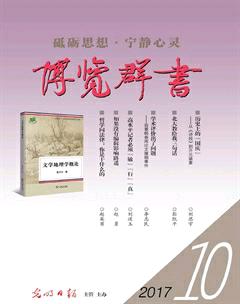从窦娥之冤到经典之冤
罗海燕
文学经典是经过历代读者反复阅读、鉴赏、评判而筛选出来的文学精华。作为人类文学的最高成就,它们一般都以近于完美的形式体现了人类共同的审美理想、思想情感、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等。中国学界关于文学经典化的论争始于20世纪90年代。截至目前,对于文学经典的概念界定及内涵阐释、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和生成机制、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重建、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未来走向等问题的解决,已经逐渐凝聚成共识。但是,在建构文学经典化的有效路径以推动传统文学经典走出现实困境方面,仍然有待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现实困境:当前文学经典化路径探讨
目前的研究者尚未能寻求出重建文学经典的有效路径。近30年来,通过对文学经典生成过程的考察,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文学经典化的建构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推动:
一是,政治意识和政治權力的推行。无论是《诗经》和四大古典长篇小说名著,还是鲁迅文学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红色经典”,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因为本身的价值理念与不同时代的政治意识相合拍,而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推行,进而成为政治宣传的标的与教育考试的内容等。
二是,文化学者的文学批评与作品删选。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郑振铎等人,秉持进化论思想,以现代学术自居,曾大规模地开展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胡适曾总结当时的文学评判标准:“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们重构的主要路径:一方面,按照新的理念重新梳理文学史,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之前原本不入主流文学史家法眼的作品,大力推崇;另一方面则依据新的主张,辑录、删选、编纂新的文学作品选或所谓“青年必读书目”与“青年爱读书目”等,使其所推荐的文学经典为学术界、出版界和读者大众所广泛接受。
三是,普通读者群体的自行选择。之前,普通的读者群体,在选择和接受文学经典时,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治权力和文化学者的制约,但是,随着商业性出版业和互联网等阅读媒介的发达,他们有了更多的阅读自主权,进而对文学经典的认定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武侠小说中金庸的作品和言情文学中琼瑶的创作等,之所以能够上升为当代经典,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人拥有庞大的普通读者群体。当代学者刘晗就曾对此评论说:“它打破了少数文学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打破了隐藏在经典确立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操纵,使得广大读者有机会参与阅读和批评,从而为经典的调整甚至重构提供有益的阅读经验。”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尽管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清楚了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以上三大主体的共同推动,而且,在实践中,也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调整中小学教材和课本、编纂各种文学选本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文学经典化建构,但是,文学经典阅读在当前依然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在讨论文学经典化问题时,不同的学者往往以《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和《诗经》《老子》《左传》《离骚》《史记》《汉书》,以及陶渊明诗、王维诗、李白诗、杜甫诗、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苏轼词、李清照词、纳兰词等古典诗词文赋为例来展开论说,他们多在如何阅读文学经典和怎样建构文学经典的层面上提出意见和看法。而令学者们极为尴尬和无奈的是,对于普通读者,甚至是文史专业的青年一辈,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现在更多地还停留在去读不读文学经典的层面。2013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曾根据近3000名读者微博、微信留言,统计出一个“死活读不下去前10名作品”排行榜。其中,《红楼梦》占据榜首,而其他三部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也都赫然在列。
可以说,随着文学经典传播和接受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相对于文字阅读,普通读者更愿意选择借由电脑与手机的多媒体阅读。美国作家亨利·密勒就不无极端地表达了对阅读纸质文学的漠视,他说:“有朝一日电影取代了文学,不再需要阅读,我会举手欢迎。你能记住影片里的面孔和手势,你在读一本书时,却永远无此可能。”并且,随着“大话”“戏说”“恶搞”“炒作”“碎片化”“浅阅读”的流行,亵渎经典的风气盛行,文学经典之前所具有的美学价值、道德规范和文化意义等,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破坏和颠覆,经典文章蒙受“冤屈”?
创造性阐释:文学经典的重生
阐释是经典形成过程中整合性的一部分,文本能否被保存下来取决于一个恒定的文本和恒变的评论之间的结合。文学经典因阐释与再阐释的循环而得以不朽。但是,在重新审视与思考当前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调整中小学教材和课本、编纂各种文学选本等在内的文学经典化实践路径时,我们会发现,能让文学经典获得新生的一个重要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这就是对文学经典进行创造性阐释。对于创造性阐释,赵沛霖《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曾指出:“文学经典虽有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但那只是一种潜在性的存在,而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要把潜在性的存在变成现实性的存在就需要学者对于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
确实,文学经典需要创造性阐释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一方面,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文学经典的文本具有多义性,因而为接受者自由发挥和创造性阐释提供了广阔天地。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同时具有开放性,处于不同语境的读者会对作品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可以说,作家创作出来的文本,只是意义的生长点,而不是意义的全部。只有加上读者的再创造,其意义才得以延伸和完充。
詹福瑞在《论经典》一书中,曾将文学经典划为来两个层次,他说:“经典可分为原生层和次生层,次生层包括整理与注释文本、评点与批评文本。”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则主要体现在经典的次生层面。亦即言,在进行整理和注释、点评和批评时,要从艺术、社会、文化等某一视角或综合视角,对文学经典加以创造性阐释。
首先,文学经典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它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审美。相反,若离开了艺术审美,文学经典也就失去了它作为文学经典的核心要素。因此,对文学经典进行创造性阐释,就是要立足于文学艺术本位,对它的艺术形式、结构、技巧、复义、双关、隐喻、象征等进行诠解、论评和研究,以此激起和唤醒读者的文学情感、文学想象和文学观照,最终使后者获得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艺术审美愉悦。其次,文学经典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伟大之处在于深刻地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尤其强调文学经典与社会现实的直接联系。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指出:“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基于这样的原则,对文学经典进行创造性阐释,就是要在文学经典的文本裂缝或表征中,揭示出其背后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纷繁关系和权力构成,从而帮助读者理解文学经典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语境、特殊指向和深层意蕴。最后,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还在于它最能体现人类共同的文化精神。正如英国学者霍加特所言:“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但总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创造活动,经典中凝聚了文化的因子。”因此,对文学经典进行创造性阐释,就是要着重分析和透视文学经典中深层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意识等,以此让读者更好地去接受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和文化理念。endprint
《窦娥冤》:作为个案的文学经典
元代关汉卿创作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简称《窦娥冤》,既是中国的文学经典,也无愧于世界文学经典。20世纪初,王国维在《元剧之文章》中,曾称其是“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剧作。到80年代,王季思又编选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窦娥冤》名列第一。作为一个文学现象,自元明到当前,《窦娥冤》具有历史性、运动性和开放性的文学经典化历程,体现出了创造性阐释在其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窦娥冤》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化始于20世纪初,由王国维、吴梅、郑振铎等人对其进行创造性阐释而肇基,截至现在,百余年来,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在1949年之前,王国维一辈,多从文学艺术审美角度对其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尤其是他的《宋元戏曲史》主要从两大方面展开:一是基于叔本华的文艺思想,引入西方“悲剧”这一术语,第一次提出《窦娥冤》是“最有悲剧之性质者”之一,并阐释道:“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之意志,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二是立足于元杂剧的艺术形式,以《窦娥冤》第二折[斗蛤蟆]一曲为例,评论道:其文辞具有“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的特点,并称赞:“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之后,以悲剧艺术阐释《窦娥冤》者,基本都是从此而延伸。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王国维等人的基础上,以刘大杰和游国恩诸侪为代表,又结合社会意识形态对《窦娥冤》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阐释。他们的开创性主要体现在揭示了《窦娥冤》所包含的社会现实意蕴。“社会黑暗”“吏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与“人民反抗强烈”等,构成了他们阐释的高频词语,并指出:这是“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的作品”。这种从社会意识形态切入,强调思想内容的阐释,直到现在还影响着青年学生和普通读者对《窦娥冤》的认识。在这一时期,《窦娥冤》的文学经典地位由之确立。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文艺理论再次大规模的传入中国,包括接受美学、叙事学、心理分析学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和方法,成为文学经典创造性阐释的主流,由之形成了多元化的阐释格局,《窦娥冤》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经典魅力。以章培恒为代表,他们从接受美学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窦娥冤》“揭示苦难,最终又通过多少是令人快意的结局使剧中的苦难有所消解,让观众既宣泄了内心中对社会人生的不满,又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和滿足”。而袁行霈等人则从主题学的角度重新加以诠释,指出:《窦娥冤》反映出关汉卿崇尚权力的思想局限,体现出他让受害者亲属惩治恶人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寄寓着对元代吏治沉重的疑虑。
进入21世纪以来,《窦娥冤》依然保持着其文学经典的持久活力。这从两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来:一是,据读秀“被引次数最多的图书(2017)”统计,《窦娥冤》被引次数高达334388次,在5460种“中国文学”图书中,位列第56名。二是,据“超星发现”搜索统计,自2000—2017年间,共发表相关的学术文章1792篇,在学术论著中“窦娥冤”总被引频次为89958次。近十余年来,学者对《窦娥冤》的阐释更多的是以文化研究为主的综合性视角。但是,也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变化,那就是针对之前出现的“虚假阐释”“空疏阐释”“过度阐释”,进而提出要:祛除遮蔽,回归文本,对《窦娥冤》进行还原性阐释。诸葛忆兵与杨健等人就在重读文本的基础上,再次审视了《窦娥冤》的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并作出了新的阐释。诸葛忆兵《论窦娥形象的内涵及〈窦娥冤〉的创作意图》(《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用今人“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套解古人的阅读方式,与事实往往会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是南辕北辙。而杨健的《存亡继绝的政治抱负——〈窦娥冤〉思想主题再辨》(《戏剧》2009年第1期)等,更是作出了几乎与前人截然相反的阐释。他认为,《窦娥冤》不是反封建,而是表达了民间大众坚持封建传统的顽强意志。在他看来,关汉卿一方面通过窦娥的贞烈孝行,展示了儒家礼教的人格美,还通过平冤狱的光明结局,向统治者预演了解脱社会危机的政治道路:通过科举取仕、改革吏治、名教治国等“用夏变夷”的方略,使倒退了的元代社会最终恢复和重建封建文明。
由以上的论述和举证,我们基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文学经典具有不可同化的原创性、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和不可穷尽的可阐释性。而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进程,与对经典的阐释进程密切相关。其中,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一方面立足于文学经典的文本本身及其产生的历史原初语境,同时又紧密结合现代人的实践,将历史世界与当下境遇紧密连接,进而形成了能够同时包容“原义”和“今义”的全新诠释,最终赋予了文学经典以新的生命,而不是让经典像窦娥那样,蒙受完全脱离“原意”的冤屈。詹福瑞曾呼吁:“读者阅读经典,最理想的是首先剥离经典的次生层,直接进入到文本的阅读。”赵沛霖则倡导,文学经典价值的实现,“首先需要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创造性阐释”。也许,两者结合,既回归文本,又进行创造性阐释,庶几就是走出文学经典阅读当前困境的最好途径。
(作者系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