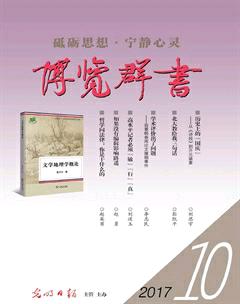嵌在新诗和旧体诗之间的“凝视”
在新诗和旧体诗之间应该有一个湖泊,这座湖泊可以称为“凝视”。
关于“凝视”,萨特认为,他人的凝视带来羞耻或骄傲,并呈现出凝视对面的我本身,使我有了生命。在萨特这里,“凝视”点燃自我反省、自我觉悟、自我认同,这就像李白“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和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很逍遥的生存状态。拉康则认为:“通过凝视,我进入了光,我接受的正是来自凝视的影响。”根据拉康的凝视理论,在诗歌中我们的词语将受到万物的影响,是一种万物的人格化或者自我化。品读我们的诗歌传统,能感受到这种凝视的存在。当然,凝视理论是西方的舶来品,换到我们自己的哲学系统来说,这种凝视体现天人合一,万物的秉性流淌在诗的血液里。
那么,我們今天说的新诗和旧体诗之间是否有相互凝视呢?
在这些年的诗歌创作过程中,我感受到文学的“凝视”包含了三个层面,即视力、视角和视野,这里的视角和视野和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后两重境界有某种相似性,视力代表天赋、才华,视角是生活经验带来的条件反射,引起人在所不惜的苦苦追寻,视野则是最高层次的境界,它体现情怀,有一种蓦然回首、豁然顿悟的意味。天才诗人具有独特的“凝视”视力,其诗句奇特而充满想象,一会儿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会儿疑是银河落九天。至于视角,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观照事物也有不同的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旧体诗中最为重要的凝视,以其持久关注,格物致知,深入物理,产生出一种人文情怀的视野,这可以说是旧体诗流动不息的古典风骨。
我们的新诗作为中国文学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树木,无疑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凝视般的照耀或者说是浇灌。而有趣的是,西方现代诗坛中很多大人物又都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穿越千年风云的“凝视”,像英美诗坛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庞德就对中国旧体的诗歌推崇有加,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从另外一个方向见证了新诗接受旧体诗凝视的巨大可能性。
但是,我们今天写作新诗,我们今天网络上的很多诗歌,应该说越来越缺少凝视,既缺少对万物的凝视,对心灵的凝视,也缺少对古典诗的凝视。不知道是否因为凝视本身具有的坡度和难度,我们自己在主动摆脱这样的凝视。今天诗歌创作即使有凝视,也是浮光掠影,泛泛而谈。我们有很多还值得一读的新诗,体现的主要还是视角的个人化,差异感,追求与众不同。但是在视野上,在情怀的挖掘和追寻中,众多的新诗丧失了旧体诗的那种风骨,而风骨往往就是普世的情怀!譬如说城市诗,今天一直在说要创作城市诗。其实古人中有很好的城市诗作,像辛弃疾的《青玉案》,凝视的不仅是“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的城市元宵夜,他的视野更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落寞和追求中树立了情怀,孕育出风骨。而我们今天的很多城市诗往往凝视得不够,只呈现了其万物生长的繁华表面,却很难穿透现实的薄膜,深入到情怀。所以新诗的视野,还是要向古人学习,向旧体诗学习。我曾经写过一首《中医文献馆:门诊的午后或者 一张药方》,一直被一些评论家和诗人称为城市诗,在这里,容我摘选其中的第一段:
午后瑞金二路的车流如我的胃部般
弯曲生疼。通向156号的中医文献馆门诊,
胃蓦然舒展,奇迹一般!
坐在神色安详的老中医面前,
我宁静如一片白芍开放。
制香附、佛手片——从老中医的笔尖
流向药方,纸质的,带着亚麻般
色泽和清苦的幽香。携着这一张药方,
如同携着一卷植物披拂的野地。
这首诗是向城市的凝视,也是向城市中那一颗脆弱的心灵的凝视,这一片疗救似的野地,就是我心中永远的守望和凝视,弥漫着中国传统诗歌乡愁般的情怀。
我想,新诗必须而且永远会从旧体诗歌中获得古典的“凝视”,但是,今天的旧体诗又如何从新诗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我个人其实也挺喜欢旧体诗,我平时也写一些旧体诗,也常常与朋友一起唱和旧体诗,但我个人认为(也可能是一种偏见之说),中国诗歌未来的希望只能是在新诗,中国新诗正在迈向一座新的高峰,自莫言之后,我相信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将有很大可能产生在中国新诗界,但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在主要写作旧体诗的诗人之间(这句话可能会说得言重,也可能会惹写旧体诗的专家们批驳)。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旧体诗无论怎样辉煌,如何走出国门是很难可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只是封闭在自己的这一片大陆上,终归只能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但是,新诗不同,当新诗勇于接受旧体诗的“凝视”,自觉接受古典诗光辉的影响,让东方诗歌传统的风骨生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诗歌之路一定会开拓得更深,我们的心灵湖泊一定会来得更为广阔而辽远……
(作者简介:杨绣丽,本名杨秀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副主编、《上海诗人》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常务委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