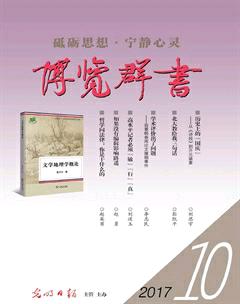《儒林外史》研究的陈美林现象
胡莲玉
文学经典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承载着人类在历史上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解,是我国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载体,蕴含着人类的大智慧、大灵感、大彻悟、大经验。因此,文学经典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是需要我们反复加以阅读的,而且也需要我们不断地予以阐释、理解和发现,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文学经典,不断发现文学经典的新价值,使它们能够继续成为经典。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呢?
《儒林外史》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陈美林先生在《儒林外史》研究上的经典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忝为陈先生的弟子,对先生的治学路径略有所窥,下面就结合先生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来谈谈这个问题。
·壹·
孟子云:“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被后人概括为“知人论世”。要读懂和评价一部作品,都必须先做基础性工作,要深入了解作者的家世、生平、交游、际遇、思想和著作,以及作者生活时代的政治、文化、社会习俗、学术潮流和作品产生的背景等。
陈美林先生研究《儒林外史》正是由这一路径入手。第一步,先搞清楚作者的基本状况。关于吴敬梓的研究,此前虽有学者进行过大量工作,如胡适曾编写《吴敬梓年谱》、何泽翰曾搜集整理《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但这些材料,仍不免有疏失之处。研究者依据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工作,难免有捉襟见肘、不能通透之感。先生在细细研读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广加搜求,撰写了系列论文如《吴敬梓身世三考》《吴敬梓家世杂考、《关于吴敬梓的家世问题》以及《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的先世资料》等论文,考证出吴敬梓生父是吴雯延,吴霖起只是他的嗣父,纠正了胡适以来一些学人的讹误;并在此基础上考订了吴敬梓进学的年龄、家难的实情等问题。或许有人会问,读一部作品,有必要去查考作者的祖宗十八代吗?但陈美林先生的考证显然是极有价值的,正如何满子先生曾在《伟大也要有人懂》一文中所评说的:“他从基础性研究着手,花力气探究作家吴敬梓的家史和生平,考证出了吴敬梓是生父吴雯延出嗣给长房吴霖起的,这一出嗣关系加上上代的嫡庶和功名显晦等复杂原因所导致的遗产纠纷,严重地影响了吴敬梓的人生选择,使之由缙绅子弟变成宗法制度的叛徒。因此他的考证与‘红学界考证曹雪芹直追到‘将军魏武之子孙的烦琐考据有别,对作家研究有其必要性。”与此同时,先生又进一步考证吴敬梓的交游,撰写了如《陈毅及其〈所知集〉中所涉及的有关吴敬梓交游资料》《吴敬梓与甘凤池》等文,初步完善了吴敬梓的交游体系。
在对作家生活的时代、家族传统以及个人际遇和交游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先生进一步揭示了吴敬梓的复杂思想内蕴。他的每一见解都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论述深入并可信。比如在论述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时,前人虽已涉及此点,但言之不深,先生则考证出李塨与吴敬梓曾祖吴国对的师生关系,李塨的弟子程廷祚与吴敬梓为至交,李塨另一弟子刘著又是吴敬梓之子吴烺的业师,李塨并曾南下至金陵讲学,再从吴敬梓的生平行事及其在文学创作中所表露的思想观念互证,从而成为不刊之论。当然,作家研究不能仅限于对作家本人的研究,先生复将自己的考证成果运用到作家的创作研究中,撰写《吴敬梓的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一文,深入探讨吴敬梓的创作与其家世的关系,如其先辈科考经历中所演绎的形形色色的悲喜剧对其题材的选择、思想的深化的作用,自己所亲历的家族“夺产之难”对其揭擿世情险恶的影响等,从而将作家身世的考辨与作家的创作研究贯通起来,将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贰·
阐释作品,自然离不开对文本的细读。显而易见,细读文本的首要前提便是读懂文本。陈美林先生对《儒林外史》所花的读解工夫,非常人可比拟,“读懂文本”充分体现在他的评点本《儒林外史》上。该评点本初以《新批儒林外史》之名于198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后修订增补,更名为《清凉布褐评本〈儒林外史〉》,由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出版。在作《新批儒林外史》之时,陈氏曾撰有详尽注解,但在出版之时,总编决定不要注解,这一遗憾至《清凉布褐评本〈儒林外史〉》得以弥补。该书全书82万余字,其中注文20余万字,批语近20万字,批注文字几与正文相当,可见作者所费功力之深。
由于古人的时代距今已远,所涉及的古代文化、社会生活很多已难为今人所了解。就《儒林外史》而言,书中不仅大量涉及古代的科举制度、官制,也颇多涉及前代典籍,其所涉社会生活面也极广,诸如天文地理、医卜星相、婚丧礼仪等。陈美林先生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这些普通人难以了解的知识做了详尽注释。可以说,如果没有经史子集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实难以揭示这部小说的深刻思想内涵。试举一例,王惠扶乩的判词“羡尔功名夏后”,王惠说:“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此句出自《孟子·滕文公》,朱熹注云:“此乃言制民常产与其取之之制也。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人以为贡。”指的是夏代的贡赋制度,与科举考试毫不相干。吴敬梓描写此节乃讽刺进士王惠连宋儒注疏的《四书》也不甚知晓,一味往功名得失上牵扯。如果不懂这一典故,就很难懂得吴敬梓讽刺的妙处所在。更加可贵的是,陈氏在注释时,不是仅仅将每一条目字面上的意义阐释清楚,还旁及与该条目有密切联系的有关知识,比如书中有關科举制度的注释条目有近200条,涉及方方面面,如第一回释“康膳生员”、第三回释“贡生”、第四回释“翰林”等,都详细阐明其内涵及其历史变化。将这些有关科举的注释分类组合,再参之以小说文本所叙写,读者可对明清的科举制度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凡此种种,足见作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文本细读功力。
先生对于作家的深度了解和把握,再加上对文本的精研,使得他对作品的阐释也具有了同样的深度。他对《儒林外史》主题思想、艺术成就等文本特点的研究和总结,正是其作家研究的延伸。在主题思想上,他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18世纪知识分子生活史”,而且“表现出作者对知识分子出路的不断探索”。由于《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始终的情节,没有统率全书的主角,在艺术结构上曾被诟病为没有“布局”,没有“结构”,先生对此则有独特的认识,认为全书以“楔子”提示全部情节,以正文展开“楔子”中浓缩的内容,最后以“幽榜”与“楔子”相映照,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正文部分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主线,第一部分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的一群士人,第二部分转向重点描写不受八股制艺牢笼,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这群士人,第三部分则分论前述两类人物,肯定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影响还在,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且更为不堪,并对未来的希望做出探索。而且,作者深思熟虑,精心安排人物进退场方式,紧扣它所描写的一切人物故事,组织起繁复的情节。因此,其艺术结构首尾一致,十分完整而严密。《儒林外史》是一部伟大的讽刺小说,对于其“讽刺艺术”,谈论者众,先生则从时代特点、家世渊源、文学传统等方面探索其讽刺艺术的成因,多方面地总结概括其讽刺艺术的特点,颇富新意。endprint
·叁·
知人论世是对作家及其生活时代的深刻理解,文本细读是对作品的深度把握,还需要有系统观、全局观,由理论建构将二者连接起来,推动自己的论述向前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
陈美林先生的《儒林外史》研究是一项完备的系统工程,即以对作者身世的考辨,思想内涵的探索作为基石,然后辐射到文本研究的其他环节上,始终注重作家、作品的互动研究。先生自言:“研究作家是为论析作品服务的。研究作家可以了解作家的思想(社会思想、哲学思想乃至文藝思想等)是如何影响乃至支配他的创作的;同样,从作品研究中可反映作家的思想,从艺术形象的研析中可以探寻作家的思想是如何折射到作品的艺术构思和形象塑造中去的。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从两个不同起点合成一个圆,彼此不可替代,又彼此不能分割。”这样从作家到作品,探讨思想与创作的关系;再从作品返观作家,研究形象与思维的关系。反复循环,无论是对作品的理解还是对作家的认识,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对《儒林外史》全面、深刻而又系统的阐释充分体现在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点上,这是他运用“评点”这一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所取得的新成就。该评本之特色,除了详尽而完备的注释,在批语方面,由“前言”“夹批”“回评”三部分组成。前言乃为总论,概括介绍《儒林外史》的思想意蕴及艺术特色;“夹批大抵是阐发文情,以数语点评小说的笔法,发明叙述上的前后照应,有时也随文起义,表述评者的世态评论和文化评论”;“每回后有就文起义的‘回评,相当于一篇紧凑的论文”。评点者采用散点透视与总体评述相结合的方式对小说内容作了精当地阐释,以夹批详细地阐明具体情节的思想含蕴、人物言行的特定内容及具体的艺术技巧,以回评总结该回主要内容及所写人物的主要性格内涵,交代情节前后的脉络,阐述其美学意蕴,既深化了读者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又使他们能对整部作品作一系统理解与总体把握,“熔欣赏与提高、普及与研究于一炉,为理解和研究《儒林外史》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范本”。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一评本看上去是一普及欣赏性读物,实则融入了作者毕生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回顾这一评本的产生时言道,“除了对既往评本进行研究以外,对作者的家世、生平、交游、思想、著作也必须有深入地研究;对作品的产生时代、思想主旨、艺术特色,尤其是它的结构、讽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相互制约的特色,也必须有细致的探讨;对吴敬梓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文化背景、学术思潮、文学创作也要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因此,何满子先生评论说:“评本是撰者研究《儒林外史》的成绩的综合体现,也是他的治学道路和他对小说所关注方面的生动反映。”
在西方解释学中,在对文学作品阐释的终极目标上一直存在争论,或认为阐释应尽量追寻作品文本的原意(即作者表达时赋予文本的意义),或认为阐释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前理解”,阐释过程是阐释者个人的“理解视野”同过去文本的历史视野积极地发生交互作用而达到一种“视界融合”,因此,文本没有固定意义,每一时代都依照自己的理解视野对文本作出阐释。从陈美林先生的《儒林外史》研究中,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给这个问题一个回答。一方面,着力把作者、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努力达到对作者“本意”的诠解;一方面,根据时代的需求、运用新的审美意识,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赋予作品以新的批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论话语的进入,使得文学批评者有了各路“利器”,一时,新名词、新概念纷至沓来,看似“创造性的阐释”层出不穷。事实上,却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或违背文本的实际,生搬硬套,或仍然是“新瓶装旧酒”,刨去堆砌的新理论的术语,没有任何创新。这种文学批评路径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既定的概念或理论出发,从文本中抽绎出可以印证理论的片段,故而失之于偏颇,只能热闹一时,经不起时间的冲刷流洗。梁海先生曾撰文指出,学院批评面临失语、失信的危机问题:除了来自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外在因素外,文学批评本身缺少原创力。陈美林先生在运用传统文学批评方法解读《儒林外史》时,也并不拒绝新方法的运用,他常常教育弟子的是“法不前定,以笔所止为法”(谭元春《诗归序》)、“法寓于无法之中”(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赞成鲁迅的“拿来主义”,什么方法能阐释清楚问题,能切实反映自己的见解,就采用什么方法。我们鼓励新理论的运用,但要做到理论方法的“化”用,即各种理论方法为我所用,而非被某理论自身的预设所左右。西方文学理论中,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都是文本解读的利器,但对研究者来说,对文本本身需要先有一个历史文化语境的认知。否则,见树不见林,推导及结论就有随意性,从而成为经不起推敲的“伪创新”。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