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为谁而鸣?
何宇轩
1
2016年11月,一则音乐会报道赫然充斥各大古典音乐社交媒体版面——俄罗斯小提琴家维多利亚·穆洛娃在上海演奏会后于推文上剑指中国听众“没素质”:
一半上海听众在我演奏巴赫的时候从未中止地拍画质低劣的照片和视频,而宁愿错失聆听音乐的重要性。
我就想知道,这些拍视频的人之后会拿这些视频做什么呢?难道他们就喜欢那种糟糕的声音和模糊的图像吗?
消息一出,中国爱乐者和当时在场的听众纷纷表示“抗议”。他们反驳道:确有一些人在演出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但人数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更别提“一半”了。且完全没看见有人“从未中止”地拍摄,都是偷偷地拍两下,然后收起手机(这种事儿虽在国中居多,但在国际音乐厅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这样刻意夸大事实“骂人”的做法,实在不是一个被人口口称道的艺术大师该有的风范。
于是乎,一场关于是听众还是演奏家素质低下的争论占据朋友圈、微博热点头条,甚至一些非音乐爱好者也纷纷刷屏转帖。
2017年5月,我刚忙完大学毕业杂事,坐四小时短途飞机去蒙特利尔闲散一番。傍晚,听了一场早先订了票的长野健与布雷哈驰(Rafal Blechacz)在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上半场“老肖第十五”乐章间隔,闻一坐席老人手机铃声大响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铃音实属太大,全场观众皆惊。只见本来准备开始指挥的长野健骤然转身,嘴角上扬,用法语面向老太道:“这可能是加演曲目,现在放还有点早。”
对比之下,这样的玩笑既可爱又不失礼节,与穆洛娃事后诸葛又带有恨意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是,听众哄然大笑,随即慢慢安静,默待第二乐章到来。
为何两位音乐家对待听众“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难道他们的音乐追求如此不同吗?
这么一问,关于“素质”的问题在我脑袋里更加作怪了:“素质”到底是何物?演奏家仅仅是音乐的“代理者”吗?听众是音乐“唯一”的聆听者吗?一场音乐会上,演奏家需求什么?听众又需求什么?或者再简略点:
音乐究竟为谁“发声”,又因谁而发生?

2
音乐当真只为自己演奏吗?
大艺术家最常被人解释的“气派”——他们不在乎他人,他们只为自己创作。
他们只为自己演奏!
格伦·古尔德,而立年始逐渐作别音乐厅,隐匿自我,好像遗世而孤立的艺术王子。从单一纬度看,古尔德确可称为“为自我演奏”的人。但古尔德称自己喜爱沙龙氛围,坐拥满堂的音乐挚友才是他的音乐理想。而且,他做电视节目、录制唱片来推广音乐。——古尔德不爱接触人,但希望有品位的人欣赏他(或者互相交流),亦希望通过电视和录音为听众传递艺术信息。而这摄像机和录音筒的“对面”不正是大众么?这些大众的数量动辄万千,岂是一座音乐厅容纳得下的?古尔德走出音乐厅,却获得了更多的听众。

如此说来,不想接触人与单纯为自己演奏很可能是两件事情——古尔德不愿接触人,但他为听众演奏。
再回忆少年懵懂时期的自己。傻乎乎,经常是一到深夜,照着根本看不懂的乐谱,想象着歌剧院舞台的富丽堂皇,凭借记忆大声哼唱威爾第的咏叹调。当时心想:这音乐是给自己唱的啊!但仔细推敲根本不对——观众不在现实,却“生活”在幻想里。那幻想中的舞台和动人的嗓音,其实是为歌剧院里的观众而“存在”的。此刻端着乐谱一脸呆气却踌躇满志的我,其实“表演”的是舞台上那个为听众表演的美声男高。
只给自己演奏或创作的思维模式也许根本不存在。许多巴洛克作曲家为教堂写作,他们对应的听众是教会人员、信徒,甚至(心里想的)可能是上帝本人。古典主义音乐家为宫廷创作,并开始向大众过渡。浪漫主义时代,世俗全面袭来,作曲家直接面向听众,或是沙龙,或是音乐厅。乐评人、批评家也粉墨登场,音乐家的身份逐渐走向现代。如此看来,音乐家其实一直是有“对应”的听众群体的,他们在写作或演奏时分也定会以聆听者角度考虑艺术的创作思维。而对于当代人来说,即使是自己“瞎玩”,没事拉拉琴,唱唱歌,有时也是假设听众存在的,或者,根本就是假设自己是自己的听众。这个“众”字很重要,因为在假设自己是听者的同时也认为自己代表了一群人或一类人的欣赏感受。我们在自我陶醉的同时,也幻想着交流的快感与共鸣的乐趣。
关于艺术是否为欣赏者而存在,杜尚有种论调,但它可能代表一个极端。这位不羁的画家创造了“实物艺术”(Readymade),目的是去掉艺术家亘古不变的权威,以此增加欣赏者的权利。在他看来,观众远比艺术家大,他们才是艺术的决定者。当艺术品的制作不是由作者本人完成,而是拿来主义——直接购买现成的商品——的结果,艺术家就再也不是“老大”了,说了算的就完全是欣赏者了。《泉》(Fountain,1917)、《自行车轮》(Bicycle Wheel,1913)、《瓶架》(BottleRack,1914)等等,其实都是“为了观众”的艺术。
我想,杜尚的观念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绝对的现代思绪。聊回音乐,在现代主义到来之前,音乐都是经历某个群体的“等待”而到来的,艺术往往是“为了观众”的产物。西洋作曲家少有东方水墨文人那种有感而发、即景抒情的雅致情趣。魏玛与科腾时代的巴赫为亲王和贵族创作,到了莱比锡时代,每周的教堂祷告都在“等待着”巴赫一部新作的到来,更不用说亨德尔、海顿为宫廷忙碌而辛勤作曲的故事了。总结说,这些作品因一些人群的直接“需求”而产生,它们不仅没有泯灭天赋,反而代表着在某种规格下更高级和更纯粹的天才。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慨叹“订件时代出天才”并非无理取闹。当艺术的“设定”处于统一规格,创作的主题和对象也由观者预先定好,天赋可能更容易“显现”。同样是画耶稣,大小、构图也都“按要求”类似,你若画得好,岂不一眼便知?谁若是天才,不想与众不同都难。相较下,今天的艺术家实在处境艰难,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却为了个人风格和刻意的创想而闹破脑筋。每个人创作的东西都不一样,你不揪尽全力去“与众不同”,怎可能展现天才?逐渐,人为的造作愈发演烈,自然的天赋也就无法分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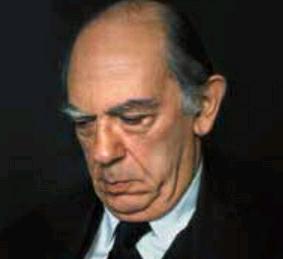
关于这种说法,你不得不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若是诸位去过欧洲大小教堂、宫殿,或再有幸于这些场所听过一两场音乐会,当有如此感受——贵族音乐在宫廷听,宗教音乐在教堂听,还是对味。这也解释了为何国中乐迷爱好浪漫主义音乐,缘吾土音乐厅众多,大多浪漫主义音乐正是为音乐厅创作的。而教堂和宫殿的音乐则由于缺乏场所而潜在失去了演奏家、场所与听众三位一体的“对位价值”,故在我地不太吃香。虽然我们不必苛求聆听场景,理论上所有的“联系”都可以靠音乐引发的“高级幻想”而完成,但在音乐厅听马勒,在宫廷听亨德尔,在教堂听巴赫,总是那么挠人软肋。
那灵感又是什么呢?灵感偶存于作曲家创作思维深处突觉遁入无人之境之时——将自己交给音乐,无所谓听众,无所谓自己,也无所谓时间和空间。这样的体验,不少演奏家也有,但它并不代表演奏的一切,这些偶然发生的“奇妙体验”不是演奏的整体思维,仅是缪斯“突袭”的神秘旅行,演奏的整体还是要面向听众,曾经和现在的作曲家也还是要面对教会、宫廷、贵族、批评家和爱乐人的。当一个天才般的点子或体验突然降临,你也还是需要用那些“烦人的”条条框框将它们规整起来,从而完成一次完整的创作或演出。艺术的产生需要“形式”,每一个灵感都在期待某种形式去完善它,也正是这种形式促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可以具体化地为观者或听者欣赏和聆听。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说:
艺术既超越现实,也不是想象中的东西。艺术同现实进行着一场不可知的游戏。就像一个孩子在模仿我们,而我们则在模仿那个创造了并还在创造世界的上帝。
克利的话大致接近我阐述的意思,但更进一层。他尝试讨论艺术的产生与现实的对接关系。艺术有种本能式的灵气,这灵气是野性的、天真的,“就像一个孩子在模仿我们”。而现实则需要我们用学习和“模仿”来的结构去创造一个围绕着这份灵感的“世界”。灵感本身是不能成为世界的,因为它是纯粹个人的,而世界是需要相互交流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架构它,也就是学会如何交流。话深理不深。克利还有一句名言:“伟大的艺术能够在生活的幻觉和艺术技巧之间得到一种快乐的联想。”“幻觉”代表的是内心极致的个人体验,而“技巧”的建构则是为了与这个世界(的他人)沟通。两者缺一不可,缺一者則不能被称为艺术。
几年前,我见过纪录片中英姿华发的米尔斯坦。记者在演奏会结束后前去采访,一问:“能谈谈你对今天演出的理解吗?”米尔斯坦将手中的小提琴轻轻放在自己精心收拾“打扮”的旅行箱里,细致地将锁头关好后转身曰:
我的音乐不需要谈论,我的想法需要你去聆听!
聆听!聆听需要听者,演奏是为了听众,演奏的本质是一种交流,借作曲家的音乐和灵气来连结“我(演奏家)”的理解与“你(听者)”的认知。说透,米尔斯坦对艺术的理解与克利无异。
演奏家的作用跟文学书籍的翻译家有些许相似之处。比如不同的翻译家译出的同本小说,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觉。我曾分别读过两种版本的《罪与罚》与《复活》,读完竟一时以为俄国出了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两个托尔斯泰。音乐亦通此理,听过米尔斯坦的“柴小协”和奥伊斯特拉赫的“柴小协”,居然顷刻仿若世上同时存在着两个柴科夫斯基:一个凌厉哲思,一个自然温暖。翻译者是个半作家——一半创作,一半读者。演奏家是半个音乐家——一半是演奏家,一半是听众,是鉴赏家。但有时,对于文学译者来说,当作品全部翻译完,自己重读译文之时,很可能全然走出创作层面,摇身变为单纯读者,即使改正纠错也会跳出作者身份,以读者的角度“找毛病”。可对于演奏家来说,这个任务就只能借助唱片和录像了——演奏家每每聆听自己的唱片时,总会发现毛病,无不妄自叹息:“原来听起来和我想象的不同啊!”这时的演奏家,是自己录音的聆听者,也是自己的听众。再一论,听众虽然是演奏家需要“对付”的永恒主题,但个人的性格也不该泯灭。那么,个性的位置应该摆在哪里呢?
复制时代,穿越而来的古人可能会吓出心脏病。走进音像店,一下子就见到唱片封面上一百张霍洛维茨的脸,更别提内中曲目了,那是多少个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曼啊!在一种人格的一百个复制品面前,它们的个性还在吗?或许,只有当你打开一张唱片,单独听,细细品味其中奥秘,方能体会演奏家隐于作品背后的个人心绪吧。
2015年去世的萨蒂钢琴作品权威奇科里尼,生前平淡,死后来潮。不少乐评人这样评价他的萨蒂:“他的好在于将自身的个性、情绪隐藏在结构和形式之后。”此话讲得好,奇科里尼的伟大正是于此,他将自己奉献给音乐本身的纯净——这也是伟大演奏的奥秘之一。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全然匿藏自身,个性是可以尽情展现的,但要像里赫特那样,将自身的个性与“伟大的”作品结构结合一同、相得益彰。好的演奏一定是不丧失形式的。只保留自我情绪的演奏是灾难,因为它们不仅违背了作品的“本意”,也隔绝了与听众交流的能力,成为自我迷醉的宣泄垃圾。
3
2016年末,我随友去波士顿参加通俗管弦乐团(Boston Pops Orchestra)的圣诞音乐会,未曾料想遭遇一场空前“饕餮”。此“饕餮”非为比喻,却当实在——我居二楼席位,本以为听众如云,结果头往下望,一楼座位已清一色被换成圆桌,桌上罗列各类饮品小吃。此刻“纯听众”只得退居二层,主要座次是食客与狂欢者的家园。音乐韵起,席间众人更是鼓掌叫好、欢呼合唱。在音乐厅吃饭,与台上如此互动,这样的音乐会我是没见过的。如今忆起,竟一时恍惚,音乐曲目居然“皆空”,脑子里尽是狂欢的热闹非凡。
我的意思不是厌烦(我不仅不厌烦这种狂欢,甚至享受其中),而是一种思索:这番热闹欢腾还是否是一场音乐会?台上的演奏家自然不为自己演奏,为的是烘托年度圣诞的欢愉,这是与观众的一次最大程度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并非通过音乐,而是通过氛围。更重要的是,此刻台下在位的也不是听众,而尽是狂欢的众人。我的目的本是音乐,此间经历迷惑、吃惊、恍惚,片刻也化为节庆的呼声与彩带,融入美国人民的节庆热闹中去了。
再想想我们看电影的经历,不亦是如此吗。我们早就习惯背景音乐在影像流动的同时“自我行走”,根本没人在乎音乐讲什么,我们看的是电影,音乐的作用与波士顿的圣诞狂欢同理,是氛围的烘托者。话粗理不粗,电影音乐就是来告诉你电影讲的是什么,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反之的。在观看电影的时候,虽然音乐就在耳边,可我们根本不是听众,而是电影的观众。
更不用说我们成天挂着耳机的手机和mp3了,它们让生活现实里充满了千奇百怪的“背景音乐”。用着这些高级电子科技的产物,有时我们的确会单纯享受音乐,但大多时刻我们无存欣赏,仅为了生活的琐碎增加耳朵的轻松。
真正的音乐听众到底在哪儿?
张爱玲说,音乐是“圈套”,听音乐是需要“中计”的。儿时听唱片,好听,有趣,因此爱上古典音乐。后来年少长成,有幸進入音乐厅听,结果根本傻掉,连约翰·施特劳斯都比唱片和想象中的震慑百倍。自叹,原来来到现场,音乐的“诡计”这才奏效。
而现在的我,俨然一名音乐爱好者,摇身成为音乐会座上客里的“老菜皮”——当浩瀚音乐入耳,已如止水般冷静。当初始的心绪全然消散,心中默然生疑,儿时那种无知的聆听和震撼的“傻掉”(如此这般美妙的经验),在成为“老菜皮”以后的我心中还会出现吗?
明代大儒王阳明一语中的:
破山中之贼,易。
破心中之贼,难。

在演奏家和音乐会的商业时代,试问,中音乐计的“家伙”还有几位?“闭眼聆听”的体验还是否存在于世?我想,多数人是中了商业的计,中了信息的计才前去听音的吧——你选择一场音乐会本身不就是甘愿落入宣传和名气陷阱的结局吗?见一张海报,看到上面的脸和名字,抑或听闻一则媒体或网络的宣传新闻才会选择购买门票。在进入音乐厅之前,我们本身就不是“闭眼”听众了。当这些充斥着信息的“贼”悄然闯入心中,你的聆听也就不再纯粹了。反而是那些被专业人士或爱好者口口称鄙的“外行人”倒成了音乐的纯粹聆听者,他们蒙忽忽进来,根本不知演奏家是谁,也不知曲子的来历云云。他们的聆听只能源于音乐本身,美妙抑或糟糕的体会,完全是出自于此刻声音的聆听带来的感受。“闭眼”在于无知,是因无知而带来的纯粹,没有多余信息笼罩的艺术才叫纯粹的艺术。比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在小说《巴黎永无止境》(Never Any End to Paris)中这样写道:
理解可能成为一种判决,而不理解则可能是一扇敞开的门。
这就是在概括这层“不理解”和“无知”在艺术体验中的重要性。然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用全新的艺术告诫人们,进入二十世纪,想逃掉商业是不可能的。商业的信息早已融入到艺术本身,成为艺术的一部分了。音乐演奏后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有多少是献给巴赫、勃拉姆斯、贝多芬的?对许多听众来说,赫赫闻名的“三B”可能只是死后亡灵,他们是给演奏家的表演添油加彩的,所有的激动与热情还是要统统献给演奏家的。“演奏家”这三个字可真是要了亲命,它既不代表音乐,也不代表演奏——它就是“演奏家”本身,是明星,是名气。此刻的我们,竟一味为名气二字在鼓掌啊!
名气的“贼”一旦作祟,谁也逃不开,我们都中了信息和商业的诡计。这是一面:我们借音乐的聆听来间接帮演奏明星助长声誉(音乐会的上座率直接显示着演奏家的知名度)。而另一面,更有甚者,直接走向极端,成为装腔作势的投机分子,“利用”音乐来证明自我人格的存在。《巴黎永无止境》还引用过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话:
装着去爱而不变成情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有些人就是喜欢“装”。他们违背了自然规律,一辈子没能变成音乐的“情人”,却“装”了一辈子“情人”。无论是听众还是演奏家,都不乏这样的“人才”,他们往往享受于他人对自己高雅姿态和学识渊博的慨叹中无法自拔。对于这些人,贡布里希的解释冷酷且周到:
他们害怕一旦承认自己喜欢那种明显惹人喜欢的作品,就会被认为是无知之辈。于是冒充行家,失去真正的艺术享受,却把自己内心厌恶的东西说成伟大。

一番论调过来,不禁失落惆怅。自己听乐多年,虽有幸未成为“装”的那一圈子人,却怎奈也距本来的纯粹和无知越来越远,愈加阻隔——人的、事的、社会的、时代的。想到这层,我猛然忆起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电影《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电影里那纠结不安的艾森巴赫,其实是托马斯·曼以马勒为原型的创造。而它的主题,正是描绘作曲家与“美”的层层阻隔:艺术家追求美感,却被事实处处打断,导致终无法亲近而遁入挣扎。影片里展现的那种道德的阻力实际暗含着社会和人性对于艺术与纯粹的羁绊。
遥谈至此,我并非欲意加重不安,只是为了看清事实,才能找到改变的道路。在被信息包围的时代,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寻索音乐的初衷。
上一部分谈到演奏场所与音乐的关系,好像如此说来,在准确的场合听相应的音乐是可以增强聆听者对于音乐的体验,也更接近“无知的纯粹”的。没错,我想有过体验的诸位也会认同,此法确有促进效果。但宗教音乐在教堂听,宫廷音乐在殿堂听,对于很多欧洲本土人来说,都根本是古历之事,早是前世的记忆了,更别提我们这些“外地人”了。现今谈及,岂不等于乌有?那么生于音乐厅时代的我们,到底该如何找回这种感觉呢?
关于此折,作曲家欣德米特曾有过“应对措施”。他创作一系列“实用音乐”,意欲让音乐回归到对应相应人群的“老路子”中去。说白了,是巴赫、海顿和亨德尔的原始模式——为特定的群体写作特定的音乐。比如,根据现有时代,欣德米特专为学生写一些作品,其主题和格式都是为了学生这一特定群体而写的。以此类推,可以为工人写,为广播电台写,为艺术家写,为特殊场合写……
欣德米特的方式承接古典主义之前,确有理据,也有“实践价值”,但它的“操作方法”仅限于新作品的创作。我想,对于喜欢听“老作品”的我们来说,“操作方法”自然有所不同,但若看清、看透,做起来就不难。
那就是,找到自己。
那就是,在极度喧嚣的年代,敢于脱去炫耀才学与资本的尘埃,敢于面对无知,享受无知。
摒弃他人旁观,勇敢面对未曾包裹信息入侵和商业攻势的赤裸裸“站”在你面前的艺术珍品,才能走进纯粹和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