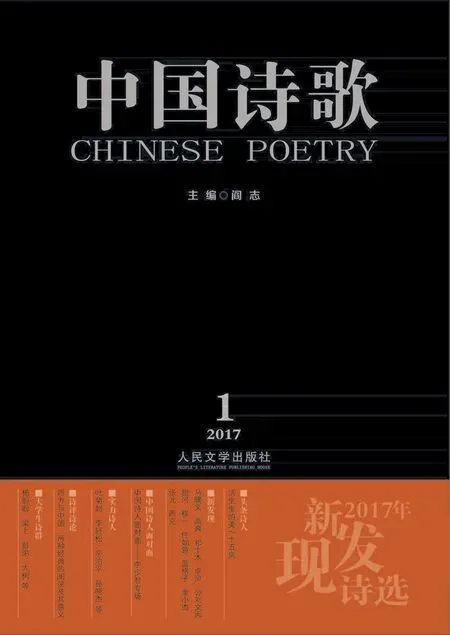缪克构的诗
缪克构的诗
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灯笼花
好啊,我喜欢这个称呼
谁叫它们就在门口长着呢
儿子也喜欢
在他小小的年纪里
需要提着它寻找萤火虫
照亮心中的路
是那样一种绵长的温暖
捉虫记
在小小的庭院
养花,种菜,施肥,捉虫
是抵抗虚无的全部手工方式
一种长久的敌人叫蛞蝓
从美好的春天到果实飘香的盛夏
它们吸食植物的芳香
甚至不放过佛手的一瓣落英
在雨后它们大量繁殖
用多余的体力爬进密封的厨房
以及四楼的阳台
辣椒水,大蒜汁和生姜粉
我都一一试过,均告失败
除了用稀释的农药和它们自身的齑粉
我已无计可施
一杯盐水和一把夹子
是我最原始的出征记
好吧,它们每个夜晚都消失了
在第二夜复现
那是另一波敌军
反正,会出现在你任何想象不到的地方
我请教隔壁的老王
他们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情况
他的回答令人叫绝:
当你对它们视而不见
谁都不会缠上你的生活
鬼话哩!
我和他不是一类人
但从他的话中我也想明白一个道理:
当你把捉虫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并且乐此不疲,倒也不失美事一桩
无尽夏
这一季的乡愁是无尽夏
人又称紫阳花的
因为在渡边淳一的小说里写着
顿时有了暧昧不清的情愫
我和太太更喜欢的名字是无尽夏
热烈而悠扬,几日就是一大丛
一直蓬勃和葱茏的绵延
这让人喜悦于盛夏除了果实
其实也有清凉的风
当然,有时候在夜里
我也会记得它有一个名字叫紫阳花
现实
在炎热的季节
命令柠檬开花是不现实的
果实毕竟已经结好了
第二春至少要等到明年
甚至后年也未可知
现实是令人悲观的
但人们往往不喜欢悲观这个词
他们只要看到蜜蜂在嗡嗡飞动
就吩咐所有的植物开花
橡皮树在疯狂地长叶子
晒不死的茉莉吐露芬芳
红豆杉在拔节
吊兰、长春藤撒下一小片绿荫
双喜藤背着花蕾在攀援
这一季有这一季的嘹亮
戴斗笠的人忙着浇水
摇扇子的人仍然大汗淋漓
他们,都不能拨动任何一片云彩
马槽
秋凉之夜,有虫鸣声声
仍觉——静极
一轮明月前来映照
鱼池里的莲花也睡着了
白日里她则灿然开放——
饶是无根地采来
竟也这般神奇
突听得,马蹄声声,似近,似远
又闻得,马鸣嘶嘶,似有,似无
城中夜,何处有飞扬的鬃须?
凭栏望,哪见得喧嚣的尘土?
双耳依次贴近大地
才感知勃勃的涌动
来自那一方马槽
木质的、鼎状的马槽
数月前被淘至我的院中
有说是清代的,有说是明朝的
至于木头,是榆木,还是枣木
我都不知
曾侍奉于官宦宅邸,还是贫苦人家
亦无所知
只知来自齐鲁大地的乡间
我用来养了花
没有念想去告慰那些绝尘而去的马
花倒也一日日的开不尽
马的气息寻觅而来
好啊!这是一匹骏马
年轻时曾征战沙场,老来亦甘心驮着粮食
举目曾傲视盘旋的群鹰
低首亦舔过干涸的沙泉
纵然身上有累累刀伤
也不去提啦
无妨!活在世间不过与众人一般
这是马槽养育的众多马匹中的一匹
奔跑,跳跃,老来坦然接受寂寞
与另外一些羸弱的马一起
构成了马槽的一生
如今,静静卧于墙之一角
听虫鸣声声
看一轮明月朗照
睡莲
为了给鱼池增加一点亮色
几片浮叶,一朵睡莲,被采来了
日光暴晒,锦鲤穿梭其中
风景竟也真的不同往常了
睡莲白日里纯净而利落地开
天色将晚,就地一滚,和衣而眠
我自然是见过万亩莲塘的
更不消说一池的绽放
但怎么看
眼前的这朵睡莲都更像一个寄人篱下的女子
未几,她便恹恹的没了生气
无法收拾果实
当然亦无需顾影自怜了
好生后悔将她采摘啊
现在,不知如何收场了
理由
雾霾是我忧伤的醒目理由
它们是大时代里充斥着的小悲哀
小情小调小惆怅
怎么办呢
我的日子里只剩下空气质量报告了
——小小的颗粒
遮住了太阳、星光和月色
一夜
黄猫惦记着石槽里的锦鲤
灰鸽则念想着地里刚撒下的种子
它们不会反着来
我希望写几首诗
脑子里出现的却是一朵正在盛开的茶花
河对岸又传来了公鸡的打鸣
三更刚刚过去,是否起得太早?
——头顶偏右
一轮明月正在朗照
最早的春天
昨夜,河面还在冰封
今日,爆裂已上了枝头
小鸟的叫声也在凌晨开始不同寻常
热烈里有了躁动不安的情愫
而春草呢?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响起
毕竟,一百四十七年来最早的春天来了
通过一场北风凛冽的倒春寒来告知
该是多么沉痛的决定
午睡醒来,我听说错恋的侄女回家了
带了一个五岁的女儿
她没有婚姻,却在家暴中隐姓埋名多年
对过去一无所获,对未来一无所盼
春天啊,最早的春天
这一刻我只祈求——
你把我的那份花香都留给她吧!
梦中
刚才,就在刚才
梦见故去多年的父母要离异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嘛!
一向善良隐忍的母亲对我说
父亲要去找那个男的,还有他的女儿谈谈
“他也是苦出身,力气蛮大的
扫起地来一点也不吃力”
我听了不知所措
印象中父亲很像一个临危不惧的领导
我什么话也没讲
只盯着家中的一套老家具在看
在现实中我正在搬家
正在寻找一件古色古香的老古董而不得
赶紧起来,记下这些,待老来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