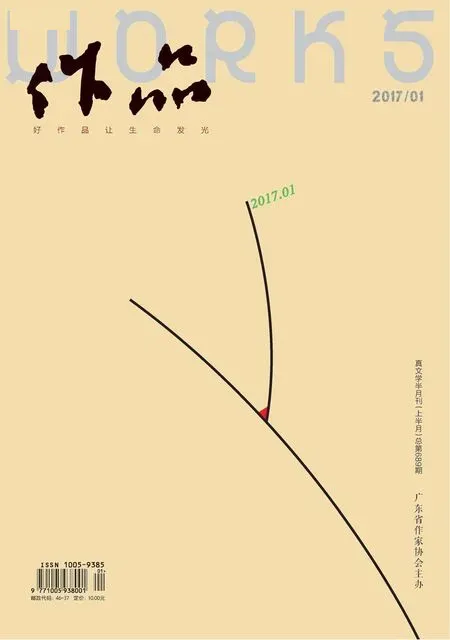虚无,假晶,出埃及:《忏悔录》笔记
文/杨无锐
虚无,假晶,出埃及:《忏悔录》笔记
文/杨无锐
杨无锐俗名杨伯。文学博士,大学教师。著有《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花山出版社)、 《其实不识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汉语世界,流行青春造反的故事。从巴金小说到偶像剧,一脉相承,没完没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却写一个征服了一切的中年人,自己造自己的反。这本书,我读了好几年。
去年重读《忏悔录》,写了一篇《带着托尔斯泰去草原》,放到新出的小册子里当后记。想不到,梁卫星老师写了长篇书评。更想不到的是,梁老师的书评,从这篇关于托尔斯泰的后记讲起。梁老师说,我的书,也是一本私人忏悔录。托翁写《忏悔录》,踏上他的出埃及之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埃及要出走。梁老师的书评,就题为《你的埃及你必须走出》。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写到五十几岁。此后,托翁又活了将近三十年。看晚年日记,宣布归信之后,他没有获得一劳永逸的安宁。相反,罪感日深,困惑日重,信心载浮载沉。归信后的三十年,应该是一部更加惊心动魄的《忏悔录》。
写《带着托尔斯泰去草原》,其实是取巧。因为刻意避开了《忏悔录》之后的三十年。那三十年,托翁的痛苦更深沉更壮阔,可惜,我理解不了。倒是托翁从青年到中年的心路,觉得亲切,甚至熟悉。他讲到的那些精神挣扎,我正在经历着,尽管是庸俗肤浅的版本。不管我的版本多庸俗多肤浅,故事是同一个故事:一个人,想从丑陋躯壳里挣脱出来。
一个人,人到中年,忽然自觉丑陋,想从丑陋躯壳里挣脱出来。这就是梁老师所谓的“出埃及”。
一
俄罗斯伟大作家里,读托翁,最有亲近感,也最少震撼眩晕。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他们,似乎有更纯正的“俄罗斯心灵”。相反,很多人视为俄罗斯良心的托翁,却是一种较易为我所知的“现代西方心灵”。
《忏悔录》就是个例子。这部书最有趣的地方是:托翁屡屡向纯朴虔敬的俄罗斯心灵致敬;他想拥抱那样的心灵,但他所有的颂词都是旁观者的颂词;而他的自我救赎之道,则是在西方的哲学丛林里摸爬滚打,绝处求生。
《忏悔录》,如果忽略救赎的问题,很像一部个人哲学追忆。青年托尔斯泰,是启蒙的造物者。人到中年,厌恶了启蒙话语的空洞、启蒙者的虚妄,他开始探究其它的哲学可能。从苏格拉底到叔本华,从唯物主义到尼采,从数学到物理。从46岁到50岁这段时间,他的救赎渴求,无意中转化为知识渴求。知识问题,取代了灵魂问题。
托翁曾经计划专门作文,驳斥三种当代迷途者:唯物主义者、实证论者、尼采主义者。这些主义,以各自的方式参加了那场众声和鸣——让人不敢、不愿、不屑、不好意思把自己当成“人”的哲学劝说。它们从不回答“我为什么活着”、“我该怎样活”。它们只是提醒人:你不配问这个问题。
托翁明了“尼采主义”的虚妄。但他自己,就是一个无意识的尼采主义者。“尼采主义者”,与尼采的信徒不是一回事。尼采根本不曾创造什么新思想,他只是时代精神状况的伟大代言人。有一条主线贯穿着他精采绝艳的哲学警句,那就是“重估一切价值”。“重估一切价值”无非是说,把一切神圣之物转换成它的生成过程;把信仰转换成对信仰生成过程的理解。尼采所有机智雄辩的宗教、道德评论,都是这条公式的化用。
这就是尼采所代言的最新的时代精神:从前,人们为了洞悉事物的意义而追寻其起源。现在,人们越是接近事物之源头,越是觉得索然乏味。从前,讲述本源意味着讲述事物的意义。现在,揭示本源意味着使事物丧失意义。“尼采主义”的核心,是用“知识”消解“信仰”和“价值”,用“知”的探究替代“信”的痛苦。
凡把“知识”视为“救赎”的替代方案的,都可以说是尼采主义者。他们共同参与了“重估一切价值”这场声势浩大的现代群众运动。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都可能是不自知的尼采主义者。他们各自宣布发现了真理。他们无不声称,世界和人的拯救,希望在此。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种种现代的主义者,无不带着拯救者的激情传播他们的知识。他们传播知识的方式,就是把往昔神圣之物宣判为原始的、错误的知识。
托翁比尼采年长二十岁。但他最初选择的出埃及之路,正是以“知识”为“救赎”。出埃及,唯一的希望,在于艰苦卓绝的跋涉。而尼采主义者,更热衷机智博学地评论地图。
写《忏悔录》的托翁,意识到尼采主义的虚妄。但他反驳尼采式思维的方式,仍然是求助于知识。他的灵感来自数学。所有现代的科学知识、主义知识,向人提供的是恒等式。0=0;1=1……。而信仰者所要知道的,是0、1、2、3……与无限的关系。所以,科学知识、主义知识,在信仰问题面前,永远答非所问。由此,托翁区分了两种知识。一种关乎事实,一种关乎永恒。
面对信仰问题,理智提供的知识无效。这是《忏悔录》的伟大洞见。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洞见本身,也是理智挣扎的结果。托翁出埃及的工具,仍是才智(intellect),不是灵魂(soul)。托翁崇拜纯朴虔敬的俄罗斯灵魂,但他终生未曾获得那样的纯朴、虔敬。当然不是说,托翁缺乏伟大灵魂。正是依靠伟大灵魂,他才得以同伟大的才智搏斗,他的生命和生活,就是战场。
《忏悔录》的第一层故事:一个伟大灵魂决心与自己曾引以为豪的伟大才智决裂。《忏悔录》的第二层故事:决裂本身仍然要通过才智,并有止步于才智的危险。第二层故事,比第一层更加惊心动魄。
尼采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西方心灵。有“看穿”的眼睛,没有“看到”的心。托翁,有“看穿”的眼睛,却渴求“看见”的心。这是一个经受双重痛苦的西方心灵。
二
我所谓的“尼采主义”,在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这样的现代心灵观察家那里,有个更著名的称呼:“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正是借着讲述尼采谈论“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海德格尔所谓的虚无主义,绝不仅仅是不信上帝那点儿事。尽管人们常常滥用“上帝死了”这句常谈。海德格尔关注的虚无主义,是一桩形而上学事件。而他所谓的形而上学,也不仅仅是某种学说、某个学科。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之真理的思考。而存在者总是在一个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对峙的整体结构里存在着。超感性世界,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观念、道德法则、进步、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虚无主义是指,所有这些超感性领域的崩塌、腐烂。它们彻底丧失了构造力量。
关键在于,“超感性世界”不再是构造世界的力量。所有古典形而上学,都把“超感性世界”视为绝对真实、经验世界(或曰感性世界)之根。经验世界只是真实世界的仿品、造物。那个绝对真实的“超感性世界”,不只是一种思辨的假设。它切实参与着人类的生活。人们的希望、恐惧、对美善的追求、乃至愤恨、暴行,都与它息息相关。
虚无主义,就是“超感性世界”的坍塌。无论人们如何称呼它:上帝、天道……。从此,世界和生活与它们无关。上帝、天道推出世界,人就成了终极统治者,统治自然,统治自身。所以,海德格尔说,虚无主义还有一个等效的说法:人之获得地球统治权。
“虚无主义”听起来令人沮丧。“人之获得地球统治权”则振奋人心。为后者兴奋不已的,恰恰是纯正的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者,是不需要、不愿意,或者没能力与上帝、天道建立关系的人。他们与“信”绝缘。上帝、天道,转换为关于“上帝”、“天道”的知识。这就是尼采那句“重估一切价值”的根源所在。从前,人们渴欲上帝、天道。虚无主义的时代,那些最有灵性根基的人,也只能渴欲关于上帝、天道的知识。“重估一切价值”的结局,不是发现真正的价值,而是无穷尽地重估下去。人们提防价值,热爱重估。
海德格尔说,虚无主义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它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也不仅仅属于19世纪。只不过,到了19世纪,这个词儿忽然变得司空见惯了。或者说,虚无主义成了人们的主要心灵模式。
“虚无主义”不是特殊的身份标记,或者说,不是某种特定的“主义”。不同身份的人,可能共享同一种虚无主义心灵,操持同一种虚无主义语言。虚无主义语言的主要模式,是戳穿。对虚无主义心灵而言,戳穿,是唯一一桩“神圣”的志业。戳穿的方式,是把所有的神圣之物转译成社会、经济、心理、生理现象。路德不是获得启示的圣徒,是一名十二指肠溃疡患者。
现代人文学术,最大的成就,是探索并积累的异常丰富的戳穿技术。所以,虚无主义从不自报家门。它登场,总要戴上各式面具。
尼采把信仰和道德解释成心理疾病。他的前身是启蒙哲人,继承人是弗洛伊德。
达尔文主义者把历史解释成生存斗争。他们的近亲,是信仰经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眼里,历史只有残酷、压迫和反抗。社会主义者和他们使用同款历史望远镜:看到眼里的,只有残酷、压迫和反抗。
人不是动物,也不是神。人的历史,永远芜杂。神圣与邪恶、高贵与粗鄙、善行与不义,总是如影随形。路德是圣徒,也是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所有的戳穿术,都能道出部分事实。虚无主义的心灵,把部分真相当成全部真理。他们对“真相”轻车熟路,对“真理”无能为力。
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虚无主义首先是一桩现代西方的精神事件。随着西方的扩张,虚无主义成了全球性的精神事件。塑造俄罗斯人托尔斯泰心灵的,正是那种由尼采代言的虚无主义。塑造中国人杨无锐的,也是同一种东西。
三
“虚无主义”有西方的心灵故土,也有海外的心灵殖民地。
在虚无主义的西方故土,始终存在着神学的、哲学的、伦理的论辩生态。有虚无主义,也有对虚无主义的辨识、反省、抗争。有不自觉的尼采主义者,也有极度自觉的尼采,还有敌尼采者。虚无主义是西方的精神硕果,对虚无主义的抗拒,同样是西方精神的硕果。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自愈机制和自愈机会的生态。而在西方之外的地方,人们接受虚无主义,却无法辨认它。人们开门纳客,以为迎来了希望:富强、独立、进步、解放……。所有这些振奋人心的口号身后,隐藏着一位不速之客。
西方之外的人们,没有西方式的论辩生态。对他们而言,某种西方语词,先是作为口号,继而成为真理,终于形成专政。当一个语词脱离了自己的论辩生态,它就成了不能被思考,因而不能被反驳的东西。人们心存善意,接纳一个自己无力思考无力反驳的语词,也就是接受了一种心灵专政。
尼采提醒人们抵制思想专政。西方之外,虚无主义实施了最成功的专政。因为,在那些地方,到处都是不自觉的尼采主义者,连一个自觉的尼采都没有。
《忏悔录》里,托翁青年时代遇到的志得意满的彼得堡精英,正是这样一群遭遇心灵专政而不自知的人。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的托翁自己。托翁的双重痛苦是这样的:他从往昔的自我身上看到彻骨的虚无,想要挣脱出来;他崇拜未被污染的纯朴虔敬的俄罗斯灵魂,想要重新拥抱它们。悖论是:他需要灵魂的力量抵抗才智的污染;被污染的才智阻碍他重获灵魂的力量。
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托翁的双重痛苦,正是斯宾格勒所谓的“假晶现象”。《西方的没落》里,这是一个重要洞见:
我想用“历史的假晶现象”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种情形,即:一种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不但无法达成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识。从此种年轻心灵的深处喷涌出来的一切,都要注入该一古老的躯壳中,年轻的情感僵化在衰老的作品中,以至不能发展自己的创造力,而只能以一种日渐加剧的怨恨去憎恶那遥远文化的力量(《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2006年版)。
“假晶现象”的基本情节是:一种强大的外来文化与一种相对软弱的本土文化相遇;无力抗争的本土文化被塞进外来的躯壳;于是,本土文化失去了表达自己的能力,也就随之失去了生机;而外来的文化躯壳,既得以实施专政,也势必遭致怨恨。
斯宾格勒的确把近代俄罗斯视为“假晶现象”的案例。从1703年彼得堡建造之时起,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假晶现象,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先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再后是19世纪的种种新思潮。近代俄罗斯的特有现象是:人们唯有借助西方涌入的新话,才能观察自己,表达自己。极端状况,则是人们出于道德激情,借助新话,解剖旧式的俄罗斯灵魂。
斯宾格勒说,这种“假晶现象”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是大城市的知识幽魂,聚散啸傲,指点江山。这样一群人,托翁在《忏悔录》里描述过:
很快,托尔斯泰发现信仰“进步”的精英们,除了使用同一个概念偶像,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各说各话,喋喋不休,向民众灌输进步的真谛。当然,免不了互相责难,嘲讽,诅咒。“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一群对自己的生活无话可说的人,却习惯对一切人的生活指手画脚,美其名曰“启蒙”。托尔斯泰说,启蒙者们自己就组成了一座疯人院(《其实不识字·后记》)。
除了这群“假晶精英”,俄罗斯广大土地上,还遍布着下层人民。他们仍然保有俄罗斯灵魂,但他们根本无权也无力表达自己。他们只能任由“假晶精英”们操弄各式新话,对自己施行病理分析。
这就是在“假晶现象”当中撕裂的俄罗斯。掌握新话的精英不理解他们的土地。那些真正活在俄罗斯大地上的灵魂,无力自我表达。精英圈子蔓延着傲慢。大地之上积聚着怨恨。
大地上的俄罗斯灵魂,更多地显现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而托尔斯泰,则是“假晶精英”的伟大硕果,和伟大叛逃者。托翁曾是最有天才的新话操弄者。正是他,从新话中看到了虚无。
从新话铸造的才智躯壳挣脱出来,重回俄罗斯大地,这就是托翁的出埃及记。
在斯宾格勒的表述里,“假晶现象”是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占。这很容易引发庸俗化的理解。尤其是在汉语世界,人们很容易从“假晶”联想到中西文化之争,继而联想到现代化与民族性之类的无聊纷争。
其实,斯宾格勒的“假晶现象”首先是一种心灵模式对其它心灵模式的侵占。说得显白一点儿,就是虚无主义这种现代西方特有的心灵模式走出西方,在所有土地鸠占鹊巢。其结果是,其它一切别种心灵模式失去了表达自身的能力,继而丧失生机。
比如托翁。长久统治他的,是“看穿”的心灵模式。伟大如托翁,“看见”,几乎成了不可能之事。
阅读托翁,我时时想到自己身处的汉语世界。汉语世界,孤陋如我,未曾见到托翁式出埃及者。汉语知识精英,似乎更加怡然自得地生活在假晶当中。
所谓假晶,无非是用新躯壳装载旧生命,直至旧生命失去生机,新躯壳趋于僵化。这在汉语世界,早已不是危险而是事实。
我大学念中文系。深造、教书,专业是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照流俗意见,这该是最贴近本土的知识圈子。正是在这个圈子,我得以见识到最纯正最僵硬也最庸俗的“假晶现象”。
犹记当年恭听学界泰斗的报告。主讲泰斗、主持泰斗,都是德高望重老先生。他们都以不事浮词崇尚实学著称。在古代文学这个行当,崇尚实学的意思是,对外来理论没兴趣,皓首穷经沉潜古典世界。一位沉潜古典的老先生告诫年轻人,要扎实读书,不要迷信理论,要说理论,还是,马克思讲得最好。另一位老先生点评:我同意你的看法。接下去,他告诉我们,古典材料处处印证着马克思的教诲。
问题当然不在于老先生崇奉马克思。问题在于,对这样的老先生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被作为唯一真理接受下来的。他们皓首穷经沉潜古典,但中国古典只是等待解剖的材料,并不向他们提供真理。他们奉为真理的东西,他们未必有能力知晓其来龙去脉。
这就是假晶现象的困境所在。在一个假晶式的心灵中,两种文化都失去原本赖以生存的论辩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从始至终都处于论辩生态之中。中国古典,原本也延传于生机勃勃的论辩生态之中。当二者在一个假晶心灵中相遇,则同时脱离了论辩生态。结果是,二者都是僵死的。一边是僵死的真理,一边是僵死的材料。而假晶的心灵,对此毫无觉察。
我的意思,不是苛责老先生。他们是古典材料的伟大整理者守护者。我的意思只是说,即便在最与世无争的淡泊心灵中,也可能存在着假晶。假晶的本质,是僵化真理实施的心灵专政。
假晶文化的共有标志,是论辩生态的丧失,并且是双重丧失。本土文化早已沦为遗址和化石。汹涌闯入的外来文化,也脱离本来的生态,变为支离费解的话语碎片。
假晶心灵喋喋不休,却不理解自己的语言,也不理解所说的对象。托尔斯泰所见的彼得堡精英正是如此。他们用他们不理解的语言,揭露他们不理解的上帝,指点他们不理解的俄罗斯。对两者,他都不具反省能力。我所亲历的汉语学术圈儿,何尝不是如此。
假晶的世界是这样的:一堆空洞的语词,飘浮在沉默的大地。一堆空洞的语词,禁锢着渴欲的灵魂。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埃及。
四
托翁是俄罗斯假晶心灵的样本,也是假晶心灵的叛逃者。他意识到内心对神圣事物的渴欲,也意识到渴欲被虚无主义的思维外壳禁锢着,于是踏上出埃及之路。
托翁反省虚无主义的第一步,是把青年时代奉为真理的那些口号视为问题。那些口号,无一不是来自西方。在西方,自由、民主、平等、解放、人权、进步之类的字眼,是从深厚的思想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那片土壤,长出自由、民主、平等、解放、人权、进步,也长出对自由、民主、平等、解放、人权、进步的反思和警惕。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论辩生态。在这个论辩生态里,“自由”有意义,对“自由”的反思和警惕同样有意义。
当“自由”、“进步”之类的字眼进入异质文化时,它们便脱离了原来的论辩生态。异质文化的心灵,把它们当成无可置疑的美好真理接受下来。“无可置疑的美好真理”,这几乎是“口号”的同义词。人们相信,甚至崇拜这些口号,而不是在论辩生态中思考它们。这就是口号对心灵的专政。当舶来的口号实施其专政时,本土原生的论辩生态便随之生机尽失。
假晶心灵和假晶文化的悲剧在于,它同时丧失了两种论辩生态。它不在任何论辩生态当中,它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它无力反省自己。从它自己的角度看,则根本不需要反省:真理在握,何必反省。
托翁的《忏悔录》,很大篇幅,是这位小说家对西方哲学的贪婪研读。他的动机,不是为小说写作锦上添花。他是要把曾经深信不疑的口号重新置于本来的论辩生态当中。唯有如此,才能对它们“祛魅”。祛魅,是挣脱口号专政的第一步。挣脱口号专政,才能重新与神圣之物相见。无论结果如何,出埃及的第一步,只能这样走。
中国近代史,同样是假晶心灵和假晶文化的形成史。近来读严复。我把他视为观察中国假晶文化形成的样本。一个不同于托翁的样本。
严复先生翻译《天演论》、《国富论》、《群己权界论》,动机何其伟大。他坚信,为国人引入了真理。凭此真理,定可保种保国臻至富强。然而,斯宾塞、赫胥黎、斯密、穆勒诸说,在欧洲本土,乃是论辩生态中的草木。斯宾塞承接达尔文,却已对进化论在伦理学上的施用有所顾虑。赫胥黎更是趋向保守修正。至于斯密、穆勒,他们的观点在其本土都不乏高贵的批评者。而当严复将斯宾塞、斯密理论引入汉语时,略去整个论辩生态,径直把它们宣布为科学真理、公理公例。
《天演论》原著,本为赫胥黎系列演说。不仅观点意在修正进化论,文风也充满英国绅士的犹疑、辩难、自嘲。严复汉译,演说痕迹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启示录式的古雅雄浑。风格的错位,意味深长。幽默演说,是成熟心灵的围炉夜话。启示录,则更像颁布不容质疑的真理。
更有趣的是,严译种种,真正植入国人心灵的,并非书中义理,而是几个掷地有声的口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开明自营……。正是这些口号,迅速点燃国人激情。从此之后,所谓近代思想史,几乎等同于口号专政史。
严先生是第一批汉语口号铸造者,也是较早的口号警惕者。晚年,他多次指责康有为、梁启超、胡适,认为他们依托报纸,以浅薄的口号蛊惑人心。可是,当他有所警惕的口号专政,正由他导夫先路。
舶来口号实施心灵专政的第一个灾难性后果,是本土论辩生态的斵丧。严复先生曾有《辟韩》雄文。主要内容,是以达尔文理论驳斥韩愈“道统”叙事。此后,本土学问日渐失去构造心灵的能力。它们完全沦为材料、尸体、历史的谬误。每一种新登基的专政口号,都会通过斥责传统小试牛刀。
严复先生是第一批古典道德的戳穿者。民国之后,他痛感国人道德崩溃,迅速转向保守,倡导孔教,支持君宪。当他意识到共同体道德之重要时,希望借古典道德力挽而复振之。悲剧恰恰在于,所有道德,一旦戳穿,便不再有效。道德不是法律,它不约束人,而是塑造人。被戳穿的道德,决不可能塑造人。严复先生始终不愿承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现代汉语戳穿古典道德的第一把利器。
此后的故事,不是口号绞杀道德,而是一批口号绞杀另一批口号。直至一个垄断一切的权力,垄断了所有的口号。
五
对托尔斯泰,斯宾格勒有两个判断。一,他把托尔斯泰视为俄罗斯假晶心灵的样本。对此,我花了很长时间理解。二,他说托尔斯泰,“站在彼得大帝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父”。对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愤怒。然后,愤怒不起来了。
斯宾格勒的话,不是实证主义的史学判断。他当然不是说,托翁生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儿子,托翁资助过布尔什维克分子,或者,托翁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导师。当然,完全不是这样。斯宾格勒关心的,也不是这些问题。斯宾格勒要说的是,布尔什维克在一片土地登场之前,这片土地一定经历了长久的心灵准备。托尔斯泰所代表的那种心灵,正是这漫长心灵准备的中间一环。
斯宾格勒勾勒的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化历程,始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彼得大帝当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预设计师。他的西化改革,完全出于一个伟大的野心:强大、文明的俄罗斯。从此,彼得堡精英引进西方的富强之术,也引进西方对富强之术的最新解释。西方的新话源源不断满足着彼得堡精英的需求。他们用这些新话指引国家,教训百姓。对他们而言,这不是新话,这是可以引领俄罗斯抵达富强的真理。
托尔斯泰青年时代置身其中的,正是这样的精英圈子。他是圈子的中心,精英中的精英。后来,他从朋友和自己身上看到彻骨的虚无和虚妄:
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忏悔录》)。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与昔日之我的决裂。他意识到虚无主义是灵魂绝症,他想依靠哲学上的探索治愈自己。可是,依靠哲学治愈灵魂,这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山穷水尽。他是用虚无主义的方式療救虚无主义。山穷水尽之后,没有柳暗花明。
斯宾格勒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两种伟大的理解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大地之上的各种灵魂拥有浩大的悲悯。而托尔斯泰,则是启蒙心灵、都市心智的伟大观察家。深感灵魂痛苦的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诊断和忧心,仍然是社会的、经济的。他对自己的恨,是一种哲学家的恨;他对私有财产的恨,是一种经济学家的恨;他对社会的恨,是一个社会改革家的恨;他对国家的恨,是一个政治理论家的恨。他是彼得堡启蒙精英最激烈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他们最具典型的样本。
虚无主义心灵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
尼采勇敢接受虚无主义的逻辑结果。他期盼两种强力意志。一种,把“重估一切价值”当成唯一的价值,做永远的知识游魂。一种,则是亲手创造价值并把它强加给世界的“超人”。
托尔斯泰选择与昔日之我决裂,重新踏上寻求信仰之路。尽管不知路在何方,他知道灵魂的渴欲真实不欺。
托尔斯泰想要走出来,尼采想要走到底。托尔斯泰不常有,尼采不常有。至于众人,不愿走出来,不敢走到底。他们看不见世界的根基,却又必须抓住点儿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选项之一,而且可能是最高效最诱人的。
斯宾格勒说,布尔什维克登场,不是一个单纯的俄罗斯政治事件,而是一场欧洲孕育出来的心灵事件。它的前奏,是各种虚无主义心灵的登场,包括那些实际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高贵心灵。
从启蒙哲学家到尼采,再到彼得堡的精英,再到严复,都是高贵的清场者。他们在知识上戳穿旧道德。或者出于对真理的忠诚,或者出于对美丽新世界的渴望。
清场之后的世界,不会向着高贵者期盼的方向前行。既然上帝是假的,那么高贵也是多余之物。桑丘不关心骑士风度,心心念念的,唯有面包和马戏。纯朴的桑丘,愿意与堂·吉诃德同行。启蒙的桑丘,会嫌堂·吉诃德疯癫迷信碍手碍脚。纯朴的桑丘,依从良知,尊敬堂·吉诃德。启蒙的桑丘,富于知识,可以熟练地操弄口号打倒并杀死堂·吉诃德。
曾经,道德的根基是上帝或天道。清场之后,面包和马戏才是道德的理由。这样的道德,容不下堂·吉诃德,桑丘才是它真正的主人。世界只剩下两种桑丘。一种,在意自己追求面包与马戏的权利。一种,向往人人都有面包马戏的安全。他们不关心托尔斯泰的上帝,不耐烦尼采的超人。他们要的,是可以带来面包和马戏的超人,把他奉为上帝。
斯宾格勒说,托尔斯泰站在彼得大帝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中间。这句话,当然不是要给托尔斯泰定罪。他只是提醒人们,颟顸权力的登场,绝非单纯的社会现象,在它之前,是旷日持久的心灵病变。
斯宾格勒的判词,一点也不影响托翁的伟大。《忏悔录》,我读了好几年。越读越对托翁心生敬畏。他是如此勇猛深刻地剖析自己的心灵疾病,不找借口,不留情面。从这个角度讲,斯宾格勒说错了。伟大的托尔斯泰不是布尔什维克之父。颟顸权力害怕的,正是托翁式的、渴望走出埃及的灵魂。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