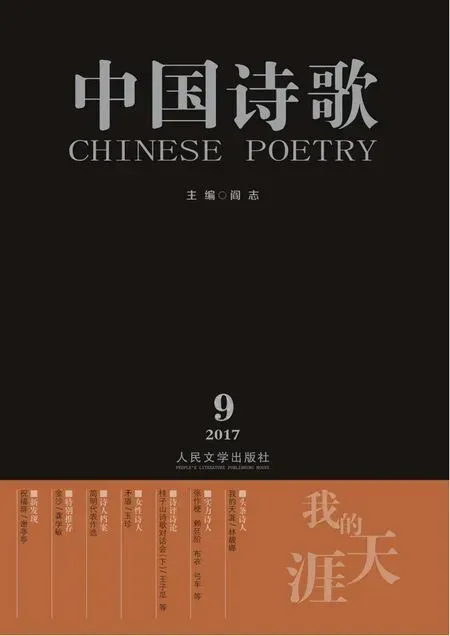简明诗歌论:哲学与诗歌的博弈
□章闻哲
简明诗歌论:哲学与诗歌的博弈
□章闻哲
"每逢我进行哲学思考时,诗的心情却占了上风;每逢我想做一个诗人时,我的哲学的精神又占了上风;就连在现在,我也常碰到想象干涉抽象思维,冷静的理智干涉我的诗."
---节选自席勒《给歌德的一封信》
哲学与诗歌的博弈发生已久.我相信,席勒的遭遇同样发生在简明身上.事实上,在诗人的大脑中,哲学一直魂牵梦萦,只不过它在大部分诗人身上是隐性的,偶尔出现显性,譬如席勒,譬如简明.在简明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道路上,曾经有过三次井喷式的爆发和三次极其重要的系统性总结,它们引人瞩目的成果是:诗集《高贵》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诗集《朴素》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和诗集《手工》 (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
一、哲学显性---从简明的"姿态"说起
"哲学:工具不万能"---诗人简明在他的诗集《高贵》中给读者扔下这么一句,"高贵"就这样充满"姿态"地开场了。
简明的姿态是什么姿态?答案可想而知:"姿态"即"哲学的姿态"。
"哲学的姿态"是什么姿态?上溯到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古希腊,也即柏拉图时代,在那里,哲学是贵族阶级用来巩固统治的工具,柏拉图哄抬哲人为第一等人,而把诗人赶入第六等的队伍.这不仅因为当时的希腊人把写诗与其他手工业、农业、烹调、骑射等具有"匠"性质的行业统称为艺术,更因为哲学在那时基本上是掌握在贵族阶级的手中.哲学在那时的姿态正是"高贵",不可侵犯.哲学之所以高贵,正在于它的工具性,惟其所以工具,它才能居高临下,统领百科,垄断思想,它的姿态与其说高贵,不如说傲慢,甚至是势利.所谓"哲学:工具不万能",同样意味着哲学本身对真理的发现和对人类社会方向的指引是受到局限的,它所指明的真理只能适用于一个或数个时代和社会,而不是全部.照此逻辑,我们尽可以对哲学再宽容些,我们可以允许其傲慢,因它对这个时代和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或许是有用的,但我们不能指望它穿透宇宙和整个时空,哲学非神.读者可以欣赏诗人简明的高贵与傲慢,并对其诗歌中含有的工具性甚而至于抱有感恩---这就是读者对哲学家和文学家们应持有的科学态度.你可以排斥,你可以附和,但我劝你最好抱有欣赏和感恩,我们需要哲学的姿态,需要这种傲慢的姿态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提神。
在文学界,这种高处的"姿态"极为稀有,但也并非简明独有,孤独而倨傲的才子大多有表现这种姿态的欲望,像《红与黑》开篇引用丹东的话:"真理,严酷的真理";像艾略特在《荒原》中的开篇: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我要死".西比尔所要的"死"和丹东的"严酷的真理"有着同样平静背后的巨大沉默,文学家们都想让自己成为那个找到万物本源的人,都想找到这样一种效果:言既出,则闻声者立刻声噤,肃穆而醍醐灌顶.像上帝对着吵闹的人群训话:纷扰什么!抽出你们自己的一根骨头瞧瞧吧---当文本变成文学家们表现姿态的场所,这恰好又应了《艺术的故事》中开篇的一句:"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这句话可以作为"姿态"存在的理由.但实际上我们有更合适的判断词,即:立场."立场"对艺术家来说是本能的结果,也是后天认知的产物,而对艺术本身来说,则成为必然---没有一种艺术可以做到面无表情,不发一声,相反,它总有大声呐喊的欲望。
这可以作为简明姿态存在的最充足理由。
二、哲学:冷峻的狂热和清醒的审美
斯丹达尔们使用哲学是为了概括文本精神,而简明诗歌中的哲学,则更多表现为浸淫和入迷.认知是令人快感的,站在哲学高度上的认知尤其令人兴奋,在哲和诗的冷静外表下,简明对思辨的膜拜却是狂热的.打开《高贵》,光从标题我们就可以领略到矍铄而严谨的"哲学之象":《对猴子的再认识》、《钟表:精确的误差》、《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依赖》……如果说《高贵》第一卷,简明已自动概括为哲学的精神,这一点似乎毋庸旁人赘述.除哲学篇外,《高贵》中还有战争篇,爱情篇,自由篇,它们又如何呢?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些领域的标题气息中闻到哲学的冷峻:《消息树》、《想象死亡》、《掩体对话录》、《平庸的黄昏不请自来》、《成熟从被埋葬开始》……这里弥漫着一股哲学森林的迷雾,望之翠绿而幽深,似乎迎面而来的正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正是《寂静的春天》……标题单刀直入哲学状态,文本则以"哲"为楔子进行雕塑,其形态亦无可避免地陷入"大卫的沉思"。
哲学对真理的企图正如简明对诗歌的企图:简明要的就是如真理般清醒而永恒的艺术.事实上简明哲学是什么呢?就像一棵树,树根越往低处,而树身越伸向高处,诚如简明在《卡夫卡自传》中所言:"一直往低处走,反而成为高度".哲学对其自身命运的发展了如指掌,正如哲学本身的高度,而掌握哲学的人则如掌握了银棒的音乐指挥家,轻轻一拨,音符即扬起或低伏,万物便讳莫如深,哲学的任务便是让万物臣服,开口说出实话.简明的诗歌正是带着这样的"臣服"企图而来.抛弃呓语,拒绝隐晦---这与口语诗无关,与其说简明写诗,不如说他是以诗歌为载体,来完成他哲学的思考.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诗歌以现象完成诗人的表层抒情,而哲学则以内质完成诗人的深层抒情.前者无序,而后者有序,后者更容易长时间地占领读者的意识领域,促成摹仿和借用,完成诗歌在审美基础之上教化意义上的价值使命。
但简明并非纯粹的哲学家,他的骨子里存在着诗和哲的双重属性,他的思考过程必然是一次博弈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充满着艺术布阵和思辨布阵的双重冒险.也正是这两种个性鲜明的阵地对垒和交战,构成了简明诗歌的独特体质,一言以蔽之,这种独特体质即:清醒.马克思说:"思想的武器成了武器的思想."哲学之于简明诗歌而言,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思想的诗歌成了诗歌的思想.哲学力图保持清醒,简明的诗歌也在竭力保持清醒,我们可以从他的《最后的对手》里一段对人生的回顾中审视这份清醒:"只有英雄与女人统治过我的生命/英雄给过我野心/女人给过我欲望/这一切,构成一部男人的历史/……英雄比我多了一次胜利/女人比我少了一次失败."复杂的人生在加减法中凌厉地呈现,诗人的自我批判在自负而傲慢的辩证中破解了冗长的诡计,神清气爽地回到了诗意的审美轨道上。
当然,这"清醒"对一个杰出诗人来说,最终只能归于唯心主义者的"清醒".诗人从根本上来说,他并无哲学的任务,诗人是歌者,他只抒发情感,表明态度和立场,他的哲学并非为了认识世界这一终极目标,而归于对诗歌审美意图的补充.同样,尽管哲学对诗人来说,它是一个企图统治诗歌的对象,但诗人的本质却要返回审美,他必须让诗性的功能最后凌驾于哲学的功能之上.如果诗是心脏,那么哲学就是动脉,它受诗心脏的指挥,随心脏的跳动而脉动。
正因为如此,简明为我们在诗中呈现的哲学现象所以是形而上的形而上,从一开始哲学的企图占领诗人的意志,而最终诗的功能将重新维持诗人的秩序,回归诗的本质.哲学何狂,但它是刚性的,诗者则以柔克刚,后者更胜于前者.如果让一个哲学家和诗人同时开口,诗人的话常常更具鼓惑力.所以如果你只看到简明的哲学,那并非对简明的褒奖。
正如成于九十年代、备受大诗人周涛推崇的《最后的对手》,如果你仅仅对一个诗人的兵法进行顶礼膜拜,那么诗人简明无疑将倍感失望:"击毁对手为下/制肘对手为中/强大对手为上".拿破仑说:"假如我早日见到《孙子兵法》这本书,我是不会失败的."《孙子兵法》一切目的为求胜,这是真正的兵家之道,简明的兵法却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击毁一个弱者,是对手的耻辱,惟有与强大的对手为敌,才是对手的荣耀,哪怕败在对方手下,也将是无上光荣."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霸王的自尊最终让他成为万众瞻仰扼腕的悲情英雄,简明赠给读者的"对手"也正是带着《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这样的古典主义英雄印记,自负,更且自傲:"不君不臣不忠不义者不配为对手/……专横跋扈自命不凡者不配为对手/好高骛远花拳绣腿者不配为对手/血气方刚有勇无谋者不配为对手……/不敢越雷池半步者不配为对手/……不作为者不配为对手/小人不配为对手/懦夫不配为对手/不以对手为业者/不配为对手"."对手"对对手的定义是带有偏见的,然而一部英雄史诗的辉煌正是由两个带有不同偏见的旗鼓相当的对手演绎而成.英雄不在乎失败,而更关心败在谁的手中,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高手的较量令人敬畏和仰止.显然,诗人心目中理想的对手是带有主观愿望的,英雄对对手品行海拔的主观性限定,使英雄形象得以接近大众,换言之,即他之于对手的审美是符合大众心目中那个介于高尚与褊狭之间的愿望的,英雄身上具备的凡人因子,将在读者身上产生共鸣,惟此,他带着缺陷奔赴悲剧时才能让读者对悲剧感同身受。
悲剧,正是诗意建筑的核心。
简明的"对手逻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主义逻辑,一个悲情的逻辑.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如此言道:"当两者(日神的造型艺术和酒神的非造型艺术)在永久的调和和不调和中,艺术才得以成为不朽……而希腊人凭借'意志'这个形而上的奇迹,使得他们彼此联姻,终于因此产生了阿提卡的悲剧(雅典悲剧)."
这个悲剧诞生的说法同样适用于简明的"对手艺术":当对手和对手在相互的膜拜和制约中,对手哲学才得以成为不朽.而对手之间始终存在着那份决一雌雄的意志正是对手们互相欣赏和互相敌对的联姻者,对手的悲剧因此诞生.对手之间的较量正如人类与自然的较量:自然孕育人类,人类仰赖自然,人类征服自然.人类与自然从和谐到敌对,再从敌对到试图回归和谐,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也即悲剧的过程.对手同样:对手创造对手,对手之间的认识过程同样是曲折的,艰难的,惊心动魄的:
"自那个贯穿着悲伤与绝望/那个凄美的黄昏沉没后/一种情绪便从我的双足/自下而上地飞速生长/我因此变得极度惊恐/不敢行走/不敢说话/不敢睡觉/不敢造爱/不敢思考/不敢让眼睛自由飞翔/不敢让耳朵正常耸起/不敢在阳光下/干任何一件事/甚至不敢认为自己/活着",这是《最后的对手》中最初的较量,对手颠覆了对手的世界,对手的秩序遇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对手通过这场灾难成功地创造了"最后的对手".新的秩序开始了,对手将认识对手,敬畏对手,学习对手,强大对手,最后击败对手,建立新的史册。
"现在,我躺在/巨大的时空之格中/人类的渺小/反衬着时间之空洞/仿佛最后的飞翔/永远无法休止/没有悬念/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无止境",诗人简明发现:对手从诞生到毁灭,再到重生,对手是永无止境的,生生不息的.简明对对手的这一辩证叙述,正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简明为这一方法论找到了合适的象征体,从这一点来说,《最后的对手》这一具象和抽象的复合体被称之为经典的意象和不朽的艺术将毫不为过。
"他们像独来独往的蛇/身披四季迷彩/胸怀辽阔山河/蛇,惟有攻击/才能无足而立/柔韧/吞吐天下冷暖/冬眠/蛰伏下一次杀机";"朋友是轿子/抬举你/对手是镜子/矫正你/朋友关注你的前程/只有对手/才真正关注你的才智";"对手都是行动主义者/善于伺机出拳/不屑屏息防守/南拳北腿/北棍南刀/招数不断创新/秘籍只有一个/先发制胜/一击克敌";"绝无伦比的事物/总是在最后一刻出现/终极的决斗/是意念之战/是王牌对王牌/是绝招对绝招/是共同的灭亡与新生".每一次认识都不同凡响,每一次解剖对手都是生与死、存与亡的预谋.对手哲学就在这生死之间绽放出令人惊艳的诗意:哲学从悲情中回到了诗歌。
三、简明诗歌与哲学博弈的本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交媾
在哲学史上,柏拉图和维柯,他们都曾把诗与哲学对立起来.柏拉图站在政治的立场上,把诗人蛮横地列入匠人行列,跟下九流混为一谈,却把哲学家放在第一等的社会人上;而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更是经纬分明地把诗人看作人类的感官,把哲学家看作是人类的理智.但事实上,诗歌与哲学并非如此势不两立,从柏拉图时代往上翻古希腊历史,我们就知道希腊人最初的教育材料主要来自像"荷马史诗"这样的叙事诗,诗人在古希腊被公认为是"教育家"、"第一批哲人".诗歌到底该以怎样的容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如果单从美学角度来为诗歌定义,那么我们或可从黑格尔的"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中找到诗歌的答案---不光是诗歌,任何一种艺术都应该在感性之上佩戴理性或者说哲学的徽章,否则这"美"就是苍白无力,缺乏意蕴的,换言之即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正如雅典娜如若光有美丽而无智慧就成不了人类心目中真正的女神一样。
虽然如此,哲学与诗歌依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站在美的概念之上,它们既对立而又统一.这主要表现在:哲学的思考在原则上是反对感性而尊崇理性的,然而哲学又能深刻洞察和理解感性,更能认识到感性对于人类的不可或缺.哲学有其自身的语言美学,以及思维美学,追求真理即它至高的美学.诗歌同样具有探索自然一般规律的"生理需求".这种"生理需求"充满着人对自身构造美学的尊重和赞美,充满着人性的真实与质感.事实上,理性与感性存在于人类每一个个体之中,惟艺术家与哲学家频繁地审视着这两种认知方式,形诸笔端,成就风格。
回到简明的诗歌文本上,我们说简明是理性的,然而光有理性并不能成就一位伟大诗人.我们发现简明诗歌中的感性,这毫无意外,意外的是,简明的感性并不缺少理性.一首《暗器》让我们看到简明骨子里不受理性羁绊的另一面,它是奔放的,自由的,甚至是蔑视传统的---这份天性对艺术来说是珍贵稀奇的,天才和后智都有江郎才尽的时候,惟自由不羁的天性可以使艺术生命常青。
你能到我的身体里来一下吗
像昙花,一下就是一生
---《暗器》
如果说浪漫主义有时不乏虚幻之处,那么简明的浪漫主义却显得真实远大于虚幻.例如尼采的哲学和他的散文诗式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们虽然也见到了尼采蓬勃蓊郁的反抗精神,见到了尼采的"酒神式的"精神舞蹈,然而,在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尼采的自画像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却是一位智者,一位遗世独立者,一位傲慢不羁的精神领袖,因此查拉图斯特拉仍然是一位理性而冷峻的哲人,却不是一种生命体的自在形式.简明的自画像则再生在"卡夫卡"身上:
我在地球表层刻下一刀
简洁的刀法,与我的命运相似
…………
一直往低处走,反而成为高度
我从未超越过别人,只完成了自我
我走了相反的路
我的偏执抑或深刻
羞于后人勘测
---《卡夫卡自传》
简明的浪漫主义修复了尼采这种纯精神上的偏颇,赋予了生命体以更真实可触的,强烈的形体存在感和温度感,例如《雪把雪传染给了雪》:
天空从来就不是
雪的故乡.雪一边舞蹈
一边飘落,谁能够让雪
重返高空?正如凡夫俗子们
只是神农山的过客
他们的庸碌幸福近在眼前
而一朵雪只需要
一朵雪那么大的地方
安置善良和故乡
它们远行,它们路过天空
抵达朴素的人间
---《雪把雪传染给了雪》
生命哲学在简明的诗中得以彻底地还原为生命自身的形状.我们从简明的书名(如《高贵》、《朴素》、《手工》),可以一窥简明的基本精神和一贯秉持着高洁的精神志向,为什么"高贵",为什么"朴素",为什么"手工",又或者"什么是高贵","什么是朴素","什么是手工",在简明那里是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的.这个答案简言之,即:对情感真实的维护与对诗性真实的维护.事实上,我们在简明的诗中,常常能够看到简明的"弱点",这也是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通常具备的"弱点",它就是对真理的维护,哪怕这个真理对自我来说是完全不利的.例如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哲学家马克思,毕其一生精力却是用来反对资本主义,而一个同样出生于旧式富有家庭的作家鲁迅,毕其一生精力却是用来反对旧社会.尽管诗歌并不对真理有惟一的要求,但诗人简明在其诗中所表现的哲学思考同样具备了一种"不达真理不罢休"的勇气.因此,也许我们会在简明的诗中看到一个放浪形骸的形象,甚至一个好斗者,一个执剑者的形象,而不是相反,一个谦和的,中庸的君子,甚至一个老成持重的学者或文人形象,但这恰恰反映了一个哲学思考者的本在精神,一个真诗人不羁的自由的形象---而这正是其手工打造的高贵与朴素之处.显然,简明有对自身的清晰评价,这种自我评价又不无带有挑战和傲慢之意,他试图向人们提问:什么是高贵?什么是朴素?什么是手工?而他的回答也是空前绝后的---"它的绽放不是为了炫色,而是为了绝尘"(《读诗笔记》)。
反抗精神,求实精神始终贯穿着诗人的精神史,这不仅体现在"哲学"上,也体现在"性感"上---在简明的诗中,古典主义和性感实际上是一体的,这是因为在其"性感"中恰恰蕴含着一种原始的牧歌精神,如:"自然香的女子/为什么像闪电一样就出嫁了/……为什么你只用一天,百媚千娇/却用一生做女人?"(《我将怎样迎合你死去活来的妖娆》)牧马民族单纯清澈的情歌风格与草原民族自身的奔放、豪迈的情感和简明的精神可谓十分契合,尽管它同时又契合了"性"的术语和"性"的形象,但却完全不能等同于"下半身"对于"性器官"的张扬而专一的宣泄性描写.对此,简明更有洞察:他认为"下半身诗人"关于女性身体的作品总是不可抑制地弥漫着下体的气味.他们对女性面部、颈部、腰腹和四肢等充满诗意与想象的部位,总是缺乏自信、修养与好奇心……相反,他们在女性的双乳和臀部上,却显出"野心",表现出一种夸张的"暮年之渴".简明对"下半身诗人"的揶揄,正好从侧面反映了他对自身"性感诗写"的严格甄别和自觉.无疑,简明诗中的性感更倾向于形而上的美学.这不仅是一位学者对性文化的诠释,也是一位诗人对诗歌、语言纯洁度的维护。
华山以孤高名世,普天下
谁能与它齐名?云越低
越孤独,树却越高越独立
根扎一尺,树高一丈
一动不动的飞翔,才是真正的
飞翔!天地之间的行云流水
游人只观喧闹,喧嚣背后的故事
落在诗人笔下.诗人写春秋
也写风月,古往今来
只有一个名叫徐霞客的人
醉生梦死过一回
我渴望与这位独具风范的行者
在山顶上相遇,我们席地而坐
简明望着徐霞客
徐霞客望着简明
---《在华山上,与徐霞客对饮》
不妨,让我们把诗的"真实"与哲学家的"求真"精神再次联系起来:当卢梭把小偷的罪名转嫁于一位女仆身上,他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残酷的时刻更让我远离邪恶了",卢梭在当时毫不愧疚,甚至有点得意.他的这份得意在简明这里找到了同谋,这份善感的思辨让哲学家看起来不近人情,事实上不过是出于对这种思辨模式的叙述之崇拜而已.但笔者认为,卢梭虽有他不负责任的流浪者的气质,但是哲学家的忏悔却避免了基督徒式的形式主义,虽然同样不够虔诚,却直抵问题的核心."残酷"和"邪恶"同时为被告和原告提供了最深刻的证词,而这正是比"痛哭流涕"的忏悔更有效的理性的自我批判.哲学将始终避免多愁善感的呈词.这种哲学气质在简明的诗中是前后贯彻的.但是与"不负责"的卢梭相比,简明却是极度"负责"的,正是这种"负责"将哲学的温度提升到了诗歌的温度.诗人在他自身的情感和语言的情感中表现为以"一生"为期限,他的情感以"人理"为基础,而哲学家的情感则以事理为基础,诗人"置身"于情感,而哲学家尽管在忏悔却仿佛置身于情感之外,似乎他所叙述的只是一件客观上存在,而主观上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简明恰恰是理智的,而卢梭却反而无理智,因为完全哲学的态度与主体的忏悔完全是两种人文境界.简明对诗的诸多独创性的观点,也正好证明了其古典主义向度上的规范与节制。
众所周知,规范在古体诗范畴内曾造就了诗体的诞生与辉煌,这些筑成诗歌史的诗体,除了代诗人言志,为社会立象,造就文明的同时,也揭示了规范对于诗体自身的正义性.换言之,诗,乃至文学的德性正在于其规范的形式和思想性.简明的诗文本以及与之贯彻一致的相关诗理论,正在或已经构架了简明大诗人的格局和气场.简明给予我们的不仅具有柏拉图理念上的正义美好,也具有严肃诗学上的探索和启示.作为极有代表性的当代诗歌文本,它无论在精神指南上,还是阅读兴趣引导上,还是在语言技术上,抑或在个性化的、非潮流性的审美品性上,都足资借鉴,堪为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