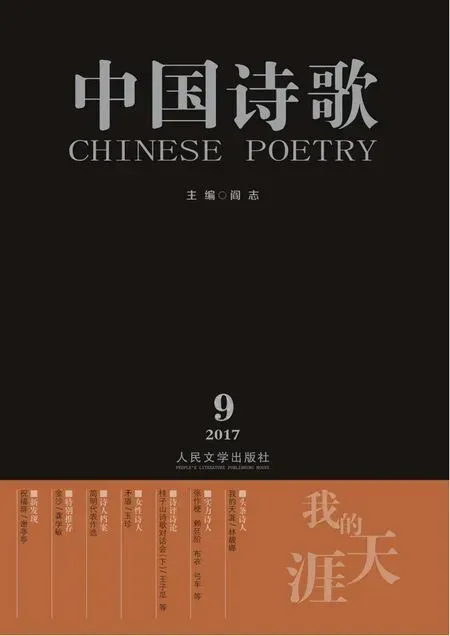江山多娇 (二十五章)
□皇 泯
散文诗章

江山多娇(二十五章) 皇 泯
江山多娇 (二十五章)
□皇 泯
我看见,我新生在北京
今天,立冬。
一个平凡的生命在躁动了五十七个秋天后,重新降临。
旧生命的句号结束在零点,在阿拉伯数字的0点中,呈椭圆形;
新生活的脚印,歪歪扭扭出一串省略号……
睁开眼睛,寻找陌生?
金水桥,纪念堂,前门,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找不到一个陌生的面孔。
只有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头顶圆日,站成一个巨大的疑问号。
我看见,我新生在北京!?
世界,也只在一对脚印里
大水坪好大,不知道。
听说,从将军庙到接龙堤,骑高大的白马还只走了一半。
躲过长辈的眼睛,跨过三寸高的门槛,溜过五米见方的地坪---
大水坪,成为阔大而又遥远的世界。
其实,大水坪,就只有一对脚印大;
当然,世界,也只在一对脚印里。
脚印,丈量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世界。
惟有呛水,生命才能成为畅游的鱼
人和巷码头,是挑水、洗衣的地方。
撒野的泳姿想试水,光屁股打浮湫,呛不了岸上的衣服,会呛了生命.祖父严酷的南竹丫枝,会痛出血。
人和巷码头,不仅只是挑水、洗衣的地方。
不试水,哪知水会呛人?
生命源于水,活于水,死于水。
惟有呛水,生命才能成为畅游的鱼。
老实宫巷子,很幽深
老实宫巷子,很幽深。
呈弧线的巷墙布满了青苔,稍不小心,历史就打滑。
爬山虎珠帘一样半掩着巷道,只有光溜溜的青石板,眯缝着一线天空。
阳光,比顿号还短暂,很吝啬的停留,只眨了一下眼睛,时间,便阴了。
老实宫,庙门敞开着,零星香客的功德,守不住孤零零的香火。
油灯如磷火,闪闪烁烁,年轻的尼姑来了又走了,只有老尼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清扫着冷寂的庭院,清扫完早晨的光,再清扫傍晚的风。
将军庙,好威武的地方
将军庙,好威武的地方。
什么将军骑什么马,怎样耀武怎样扬威?我只有仰头眺望。
眺望,只是一种姿势,这种拔高望远的姿势,成为中国人几千年的定式。
我们在四四方方的围棋盘里生活了一定的时间了,时间是生命,但也只是数字,仅供参考。
一个被栅栏门牢狱久了的孩子,不知道自由的味道,是酸,是甜,是苦,是辣?
当然,知道将军庙离我家大概一百米远,站在瓦檐下,看见将军庙的人比蚂蚁大不了多少。
我很小,成人后才知道我比小草还小。
将军庙,其实只是一个历史的地名,丁字形的路口对丁字形的路口,像一个工人的"工"字,到底有好威武?
---我的家庭成分是工人!
拉卜楞寺
阳光,让蓝色的天空独善其身;
红色的袈裟,穿行净土;
黄色的僧房,打坐草原。
红黄蓝,轮廓分明的拉卜楞寺,组成生命的三色帆,在神性的引领下,慈航佛海。
夜晚的礁上,星星是耀眼的航标灯。
香火,袅绕着祥和;
经文,在念诵中风平浪静。
唵嘛呢叭哞吽 ,阿弥陀佛!
迭部跷起大拇指,赞美
扎尕那,天空很低。
星星,撒落在毡房上,卓玛顺手抓一把---
串成晶莹的镯子,戴在脚腕上,脚步更响亮;
串成透亮的项链,挂在脖子上,歌声更甜美。
扎尕那,大地很高。
绿草植入白云里,羊群牧入彩虹中。
炊烟,袅娜着吉祥如意的风,一个饱嗝,飘出茶香和酒香……
迭部跷起大拇指,赞美!
饮一杯水,醉成一壶酒
青稞酒、马奶酒,度数很低。
歌后酒,酒是三十度的柔情。
扎西、卓玛,热情很高。
酒后歌,歌是高八度的烈性。
喝酒令---一条牛,三只羊,八匹马,从八九点钟的阳光,放牧到吴刚捧出月光杯。
"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
酒嘛,水嘛!酒壮胆,水滋润。
我在甘南草原,饮一杯水,醉成一壶酒。
古丈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1976年腊月十七就立春,197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冬衣挡不住春寒,来不及融化的冰,在顽固的零度下,拽住冬的尾巴。
急不可待的春,踩在交春的门槛上,由不得你冬。
身扎稻草,头佩草辫,土家人的毛古斯,在摆手中载歌载舞了;
老人击鼓,女内男外,苗族的团圆鼓舞,在一唱众和中团年了。
敞胸露背的汉子,林立在寒风里,威风凛凛;
绣花饰银的女子,手捧拦门酒碗,盛满热情。
喜欢提前过年的古丈---
初春,很冷;春节,不冷。
呼伦贝尔,是近还是远
那一年,呼伦贝尔,越来越近。
就像阳光飘落。
飘落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天空之下,草原之上,云朵和羊群连成洁白的地平线。
我们在天空放羊,在草原牧云,自由的风从南方放牧到北方,蛇一样蜿蜒的旅程甩响长鞭,甩掉两点水的马,脱缰。
就像月光飘落。
飘落在呼伦贝尔湖,银河流淌湖水,湖水闪烁星星的鱼鳞,生活之网,网不住撒野的心。
我们在传说里奔月,所有的故事都响亮银色的声音。
这一年---
阳光还在飘落……茂盛的草原却稀疏了;
月光还在飘落……丰盈的湖水却枯瘦了。
呼伦贝尔,是近还是远?
威海,真干净
威海,真干净。
雪,洁白的雪,让我这并不怎么样干净的人,滞留湿黑的脚印。
在野天鹅洁白的翔舞中,我,似乎冰清玉洁了。
寒冷走了。
走在纷飞的雪花里,走在晶莹剔透的冰冻里---
我的生命,在封冻的行程中,期盼一丝阳光,或者是一线暖风。
扑打在车窗上的雪粒,一路叮叮当当……
风力发电机,站在风口浪尖,三片转动的叶片,让我看见了电。
有可能融化的冰,在等待春天。
在烟墩角,我看见了野天鹅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衰老的目光镀上一片年轻的亮色。
在烟墩角,我看见了野天鹅!
平均十二岁的野天鹅啊,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飞去,只有生肖的一个轮回,却超过了我近四个轮回的生命旅程。
从春天到春天,为了生命的繁衍。
从冬天到冬天,为了生活的温暖。
当夕阳残留的叹息,被野天鹅欢快的翅膀抖落,我仿佛回到了我出生的那一个黄昏---
洞穿天空的那一个弹孔,在滴血的啼哭中,结束了一场生与死的战争。
嘘,喜欢拍摄翔飞动态的摄影师们,别吆喝,别惊飞了雪白的平静。
世界,需要安宁!
被烫伤的时间,仍有回忆的温度
七月,去喀纳斯湖,温度很高。
目光与阳光贴在车窗外,强光,在对撞中聚焦成墨黑。
心与心贴在车窗内,呼吸,中暑。
用情勾兑的十滴水,再苦再涩,也有爱的味道。
老诗人于沙说,热爱儿童,热爱大自然,热爱美女。
火辣辣的车窗玻璃,是一扇亮开的心扉。
再热,还要爱。
许多年后,被烫伤的时间,在零下的冰天雪地,仍有回忆的温度。
我想见你,你在那里
我想见你,你是天山.天山有高峰,登上高峰是峭壁,等待我的是粉身碎骨。
我想见你,你是喀纳斯湖水.湖水有旋涡,跌落旋涡有水怪,等待我的是葬身鱼腹。
我想见你,你是呼伦贝尔草原.草原太辽阔,脚印迷失在草丛里,找不到归途的路.等待我的是不断向草推移的毡房。
我想见你,你还是天山,等待无止境的攀登?
我想见你,你还是喀纳斯湖水,等待畅游的水鬼?
我想见你,你还是呼伦贝尔草原,等待吃草的羊?
我还是天真地相信仓央嘉措,见与不见,你就在那里。
生命的废墟上,绽开一叶嫩芽
高昌古城,没有了灯火,没有了炊烟。
坎儿井的清泉潜流了,一两滴泪湿不了干涸的土地,三五滴血染不遍赤色的岁月。
穿行在羊肠小道上,冷清清的风,除了卷翻几片黄叶,黄土仍是厚了又薄薄了又厚的黄土。
从酒家到戏台,见不到杯盏,听不到戏文.只有一粒鸟雀生吞活剥的种子在鸟粪的肥沃下---等待雨水。
我从江南生搬硬套到边塞的生活,怎样编撰土地与人?
如果将目光枯入黄土,再也不挪动浪荡的脚印。
也许,在我生命的废墟上,会绽开一叶嫩芽。
交河故城
三十年前,我游交河的时候,带着两千年的尘土。
库尔班大叔的热瓦甫,从历史的残垣断壁里隐约出弹唱,弓箭崩断的弦,绝响;
阿依古丽的小辫子,交织一种岁月的月光与阳光,在马车颠簸的铃铛里,锈绿了铜质的光芒。
阿里巴巴,芝麻开门,芝麻再也不开门。
那个土戏台,只唱皮影戏了.历史,都是皮毛和影子的演绎;
那盏庙台上的香火,无法再续前缘,只在刀光剑影里,袅着一缕狼烟。
三十年后,我再游交河的时候,干枯了两千年的阳光,即使躲在阴影下吸一根香烟,也会将一息尚存的生命点燃。
等
等在风中,身体被寒风凉透了。
等在雨里,心思被雨水湿透了。
站台,不是等车,是等时间,车可以拐弯,时间不拐弯。
路口,不是等人,是等心,人可以叉路,心无叉路。
等是双刃剑。
等在有限之中,路程再远,也有终点;
等在无限之外,耐心再久,也有极限。
风,暖了,那是火焰山滚烫的回忆。
雨,干了,那是坎儿井凉爽的怀想。
圆梦吴兴潘公桥
恍然间,我重返潘公桥。
一弯月,勾引了我的相思。
倒映在水中的吴兴,就像我那前世结缘的绣女,在丝绸上款款走来……
一丝一线的呼吸,比月光还纤细、还清纯。
尘封的钱三漾,荡开丝绸之源,乌篷船,承载历史的悠远---
五千年长的丝,很温暖;
五千年宽的绸,很柔软。
回想当年十五之夜,我幻入圆月,作茧自缚。
如今,五千年的等待,终于夜梦醒来。
破晓时分,舔穿蚕茧的吻,亮丽了我羞涩的相思。
在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我看见了鸟声
我看见鸟声了!
那是一群麻雀,在我的头顶叽叽喳喳。
洞庭湖的天空,不再寂寞。
我看见鸟声了!
那是一群鱼雁,捎来湿漉漉的语言。
洞庭湖的湿地,不再枯瘦。
我看见鸟声了!
在高倍望远镜延伸的视觉里,一群来自西伯利亚的白天鹅,伸长脖颈,吻响洞庭。
退田还湖,平垸行洪。
洞庭,返老还童。
重新长大,渐渐丰润。
在重生的洞庭湖---我看见鸟声了!
我用听觉,看见了鸟声。
即使呼吸濒临停顿,我就是你的氧---忆写贞丰
除了双乳峰,还有哪一座高山,可以在引领中攀登?
除了夹皮沟,还有哪一个深壑,可以在缥缈中跌落?
除了生命泉,还有哪一汪清泉,可以在滋润中呛水?
有了你身体里,支撑我软肋的那一根骨头,我就在人世间站立---
一分一秒。
在你的崇山峻岭,也许不再种植带刺的玫瑰。
花,来不及开,就一败涂地。
撒播芳菲的鸟翅,承载不了狂风。
只要你的生命,在冷静的角落里,还珍藏一丝温热。
即使呼吸濒临停顿,我就是你的氧。
洞庭湖
小时,你的身体是蓝的,你的呼吸是蓝的。
八百里的蓝,盛下比八百里还大的天空。
我一拥入你的怀里,天空就飞翔了!
后来,你的蓝褪了。
再后来,你不再蓝了。
沙滩,赤裸裸的一丝不挂。
坑坑洼洼脚丫子,凌乱在孤鸟的哀叫里。
搁浅的鱼,只剩下瘦骨嶙峋的刺.天空,被划伤。
洞庭湖呀!
还未来得及为别人而乐,就开始为自己而忧。
我被干涸在浅湖中
洞庭湖的鸟,在弹丸洞穿的时空里,噗哧一声---
停电的视觉一样,坠落……
再也找不到寒冬了,更找不到暖春。
四季分明的江南,仅剩几只怪得没有尾巴的麻雀,在唏嘘着一两条模糊季节的曲线。
站在干涸的浅湖中,看一尾没来得及逃走的黑鱼,我知道---
我,被围困了。
无法回到生我养我的羊水;
无法吮吸我曾吮吸的奶;
无法呼吸我的呼吸。
银华,初春的故事之后
一个初春的故事之后,爱情的细节还未来得及经历十二年的轮回,就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段落,戛然划上一个不完整的句号。
五一路的斑马线,成为找不到终点的省略,十字路口---
理智,色盲于红绿灯。
行走的感情,不知所措。
又一个轮回的初春了,从天空飘落彩云之南,语言在阳光下有了一点温度,而白天与夜晚温差太大,冬衣和夏衫穿梭在同一座古镇。
季节,在七弯八拐的麻石上,语无伦次。
今天的窗外,风和日丽,明天,试图走出空调房,不知可否有倒春寒?
想在西董住下来
我想在西董住下来。
老宅,深远的历史,却浅居不了时髦的浪漫。
房前屋后千年不息的流水,掠过瞬间即逝的泡沫。
一袭彝族的传统装束,穿过小巷,现实便古装了。
小桃园的桃花,飘落在火山岩青灰色的方砖上,凋零几瓣春的叹息。
我真想在西董住下来。
夕阳,斜过巷道,我苍老的影子,死皮赖脸地粘贴在土巷墙。
温泉,流到洗衣亭,凉了。
你遥指高黎贡山顶的余晖,已日暮西山。
感情的草原
没有草原任马儿驰骋了。
自从铁丝网分割了你和我,只有伫立的蹄印空响回声。
没有草原任牛羊咀嚼了。
自从栅栏圈养了你和我,只有如水的目光滋润饥肠。
感情的草原,已经退化。
生命,便是沙漠里风化的一滴泪,来不及听到湿润的哭泣。